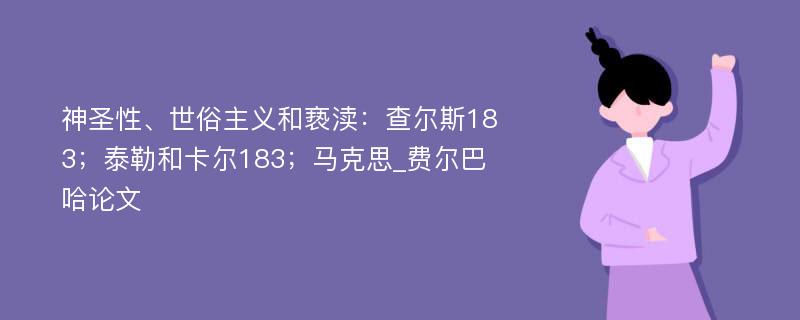
神圣、世俗与亵渎:查尔斯#183;泰勒与卡尔#183;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勒论文,卡尔论文,马克思论文,查尔斯论文,世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令我重新思考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看法。在《世俗时代》中,泰勒让我们不要把世俗主义(secularism)看作一种信念、原则的体系,或一种组织国家和社会的方式,虽然它的确也包括这些,而是把它当成最深刻意义上的人类经验问题。泰勒想让读者把现代西方世俗主义领会为一种存在、认识和定居于世界的特殊方式。的确,作为一种以特殊方式存在、认识和居于世界的状况,世俗主义是当代西方人的非选择项,正如多神论是古代希腊人的非选择项一样。简而言之,他对世俗主体性的历史建构做了令人惊叹的广博、细致的描述,通过他博学的讲述,世俗主义的现象学第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泰勒的世俗主义故事和背后的历史编纂不仅是为了取代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也是为了质疑他所认定的对西方世俗化过程的唯物主义解释,这是在世俗主义的信念和观念史中居中心地位的一种解释。泰勒对其研究进路的唯一一次直接讨论,出现在该书第五章“观念论的幽灵”中。与该著作的其他部分相比,这一章颇为奇怪:不仅内容简短,而且对观念论的指控采取强烈防卫的姿态,并以漫画的手法描绘出一个明显浅薄的、几乎辨认不出的唯物主义版本,作为他假定的对手。①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实现的。
一开始,泰勒把唯物主义认定为一种受经济动机驱动的人的理论,这个认定让唯物主义分析从试图解释是什么造成了历史条件,转变为是什么在心理上激发了人类行为②,这些解释代表了史学和历史变化十分不同的问题框架。一个人不需要接受人类受经济或物质驱动的观点就可以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整个要点实质上可以说在于把人的动机或目标与形成、限制和实施它们的条件区分开来。换言之,在一种对历史变化的解释中,生产方式被解释为人类过多的激情和能量尽情释放的主要舞台,与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有着决定性的区别。当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③时,他就在探察这种区别,他认为,我们的任何动机、行为和可能性都受制于我们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认识的力量。因此,当一个唯物主义者解释历史可能性时,感兴趣的不是行为的动机,而是产生和构成这种动机的条件。实际上,观念论的做法就是把唯物主义误解为一味关心动机、欲望、兴趣或目标之类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可以从观念上加以构想的。
将唯物主义还原为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行为,不是泰勒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进行的唯一的古怪表述。他也在“有效的历史因果联系”的意义上谈论历史唯物主义。④但是,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并非经济的强制力“引起”或直接“决定”了人类存在,而是说在一种特定的经济及其连带的社会关系的秩序中,对信念和行动来说存在着许多可能性,但并非无限的可能性。例如,从长远来看,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就不能与某些特定的传统价值并存,美国的门诺派教徒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尽可能远离当代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商品。
泰勒反对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理由包含在他对被他称为“化减论证”(substraction arguments)的更一般的批判当中。⑤我基本上赞同这种批判,它抨击说,对启蒙的任何解释(不仅唯物主义的解释)都是以下三点之间内在一致或彼此相互蕴含:(1)个体的出现;(2)理性和透明真理的统治;以及(3)对习俗、偏见、神秘事物和宗教的完全抛弃。与福柯对“压抑假说”(repressive hypothesis)的批判一样,泰勒对“化减论证”的批判不仅针对本质论(essentialism),也针对所谓的中立论(neutrality)和无视角论(aperspectivalism),从而也针对这类论证意图给出却未加验证的规范性主张。在世俗主义的案例中,泰勒指责为化减论证的是一种通行见解,即认为由于摆脱了宗教和对习俗的盲目遵守,世俗主体对世界的经验和认识要比以往的人更加清楚、真实。泰勒通过对历史差异性而非真理的欣赏,对世界观(Weltanschauung)而非客观性或中立性的欣赏,对一种建构的而非本质的人类经验以及一种解释学的而非透明的自我的欣赏,来打破这种狂妄自负。如泰勒所言:“[成为世俗的]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涉及认同、社会想象、建制和实践的重新建构。”⑥
但是,如何来领会和表述世俗的主体,如何追踪它的历史,哪些是与它的出现最相关的条件,哪种意识是世俗的宗教意识?在此,我对化减论证的批评不免异于泰勒。泰勒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来自一个脱胎于拉丁—基督教观念与实践的复杂故事,如我已指出的,这个答案削弱了(并未完全回避)产生和形构世俗主义的历史力量,世俗主义并非首先体现为观念或清晰的人类目标。本文将通过重新考察马克思宗教批判中的复杂的唯物主义来部分地说明这一点。毋庸讳言,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有其缺点和局限,在某些地方甚至显得粗陋。他的唯物主义也容易受到质疑。我的目标不是要挽救或全盘接受他的思想,而是思考由于泰勒在其世俗化研究中过于匆忙地弃置了马克思和唯物主义,以致让我们丧失了对当代境况的哪些深刻洞察。
费尔巴哈
马克思大量吸取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宗教在本质上是人的异化的表现,是人的需求、能力和力量的想象的投射,是人对主权、自由以及与他人联合的欲望的告解。不过,马克思并未采取费尔马哈相对轻易地予以抛弃的宗教路线。
对费尔马哈来说,一方面,人有一种独特的意识能力,能意识到超出自身的存在,费尔巴哈认为,这种能力使人将其自身当作一个“类”来意识——反思人类的本性和可能性。正是这种特殊的能力发明了上帝。在费尔巴哈看来,上帝是我们对自身类本质的意识以及投射到一个想象人物上的类力量。他是我们的神圣本性——我们的理性、爱和善的能力以及我们作为类最重要的无限性——富有想象力地在别处赋予的。不仅只有人能设想无限,而且我们只有作为一个类才有无限的能力。相反,一只狗只能思考和活出它自己特殊的狗性。而在我们存在和意识的独特力量中,人却能够独一无二地制造出费尔巴哈认为是宗教迷误的东西来。狗不能创造狗的上帝,因此也不能“自身分化”,不能把它们的能力及力量投射到别处。⑦
对费尔巴哈来说,如果宗教的一个来源是我们的意识超出自身经验能力的直接后果,那么“人的依赖感”则是第二重来源。⑧尤其是,对自然原有的依赖感令人感到渺小和无能,于是我们通过发明一个拟人化的存在来消解这种无法忍受的依赖感,赋予他创造自然的属性,即我们在不堪忍受的依赖和臣服景象背后放置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形象,从而间接地复活了我们对自然的权能和主权。
至此,马克思全盘同意费尔巴哈对宗教的看法:投射,异化,经由依赖的臣服,人性未满足的可能性和愿望的标志,等等。但是对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完全是历史的,而且他指涉的历史过分强调上层建筑——政治形态和世代。费尔巴哈始终把意识看成相对独立于历史上特殊社会安排的东西。换言之,马克思认为,由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粗糙的和非历史的,由超常的需要和欲望构成,而非由历史生成的、系统的需要和欲望构成,因而他就未能贯彻他的洞见,即宗教反映人的物质生活的扭曲和投射。
马克思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创造世界的并非什么神圣的力量,而是经由资本主义降生但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能完成的世俗主体,他也是真正的主体,一个能把握真理、真实地理解世界和人的主体。确实,正是这样的理解使泰勒把马克思主义归入“化减论证”的行列。但是,马克思实际上谈论的是否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稳步走向世俗化和去神圣化、揭露或揭示世界及主体的真实本性的故事?他是否提供了一种使错误意识或宗教意识让位于对世界的真实认识或理性认识的“化减论证”?的确,这类看法包含在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类似句子如“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⑨当中。更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把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关系撕碎了以往所有神圣的或温情脉脉的关系”的论证当作这样的论证:资本主义以一种世俗或透明的方式提供了它的真理,或世界的世俗化揭示了人类历史和人类存在的真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淹没了宗教热诚的最神圣迷狂”——都证明了这个观点。⑩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段落:“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1)乍一看,这段似乎又是一个化减叙事,讲述的是去掉一切妨碍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透明的东西,解释资本的力量如何消除了所有偏见、宗教和其他神秘模式,让人赤裸裸地站在自己和他人面前,只暴露出作为根本的人类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关系。
虽然这样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去神圣化叙事无可置疑地存在于马克思那里,这段话仍然可以被用来反抗这个叙事,讲述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首先,马克思并未论证说,人已经获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说人的状况的真实性被超出他掌控的条件、特别是被资本的力量暴露无遗。“迫使”人们面对“他的真实状况……和他的关系”的是某种在他之外的东西,就像这些状况和关系本身是在他之外的东西的产物一样。人和世界不是被资本剥除了它们的世俗本质,而是被资本亵渎了。神圣的东西不是被揭露而是被亵渎、玷污,从而让它不能以它真实的形式呈现出来。那些资本主义关系揭露出来的东西无不是秩序及其价值的暴力,其单一的利润之神的暴力。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雇用的工资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2)
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狂热,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3)
这些段落常常被解读为:马克思要么在为撕下了职业、家庭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温情面纱而欢呼,要么在表明这些不过是迄今为止被宗教掩盖的经济功能,但是我们阅读的重点也可以落在不同的地方。马克思在此识别出了资本加之于人类事物及其关系——职业、社团等——上的暴力,而这些东西的价值本是不言而喻的,从而也不会作为一种“现金交易”的价值被勉强保留。资本主义关系并非在本体论上或认识论上揭露了这些职业和社团的本质,反而是玷污甚至破坏了它们。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不是暴露而是暴力,不是揭示而是玷污、甚至扭曲。
因此,我要说的第二点是,马克思并非在庆祝“对这个世界的亵渎”,也不是将它等同于关于人及其可能性的真理。虽然剥除人类关系中“被掩盖的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是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难以回避的维度,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点,但资本主义揭露出来的却不是人性而是它自身。当资本按照它自身的形象创造人和世界时,就会发挥出一种宗教的力量,这种力量取代了人自身的主权,取消了人自身作为类存在和作为创造者的本质属性。因此,在马克思用“亵渎”(profanation)一词来描述资本的作用时,表达的是一种去人性化和去神圣化,而非某种真理的浮现。毋宁说,资本的运动既损害了人类的创造,也损害了人的能力和创造性,彻底损害了神性和人性。资本的亵渎力量玷污了人的神圣性并颠覆了事物的固有秩序,把我们都还原为它的结果。“总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从而玷污了世界按照上帝形象的原初创造。或者,更准确地引用《创世纪》的话说,玷污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通过对经文的借用,这个句子悖论性地为一种亵渎的力量输入了宗教的创造力,同时资本自身也呈现为一种亵渎的力量。资本以亵渎的方式对神一般的力量不同寻常的召唤,引入了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素,即如果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让资本剥除了被“宗教的和政治的幻想”所掩盖的东西,他就在别处暗示了资本本身隐含着并需要它自己的宗教。对此更充分的表述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货币的简短阐述中,在《资本论》中也有一些。让我们来一一简述。
《论犹太人问题》
《论犹太人问题》第二部分对犹太教的讨论会让许多当代的马克思的狂热爱好者退缩。在那里,马克思宣称,犹太教的“日常”基础是“做生意”,其“尘世的神”是金钱,这就证明了犹太教是基督教国家的“实际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14)马克思继续指出,犹太教表现了市民社会的精神,既是后者的反映,又向后者顶礼膜拜。当金钱成为“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并且它]……剥夺了……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从而不再有“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15)
反犹主义的成见在这些段落里表露无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考察马克思竭力发展出的关于资本的宗教维度的表述——资本需要宗教,资本作为宗教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以宗教形式组织起来。马克思声称,犹太教构成了市民社会的精神,而基督教构成了国家的精神。市民社会是自利、“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的领域,而且首先是私有财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起作用的地方——甚至在私有财产已经被取消了作为公职人员或公民的“政治资格”之后。
但是,世俗国家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呢?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证分几个层次。首先,在宪政国家把自己表述为自由之所在的意义上,或用黑格尔的话说,把自己表述为自由理念的实现的意义上,宪政国家是基督教国家。马克思把这个表述称为宗教的,或更准确地说,基督教的,是因为人类独有的经验和实践——自由——被归因于一种独特的主权力量,即国家。人的主权从国家的主权中派生出来,同样,一种人类独有的东西——主权——被归因于一种想象的存在,即上帝。他相当公允地借用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说明:“宗教正是以间接的方法承认人,通过一个中介者。国家是人以及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约束性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无约束性交托在它身上。”(16)马克思没有论证说,把神性归于上帝和把自由归于国家是意识形态化的,因而是错误的,而是说这种归因(在费尔巴哈的术语中是“投射”)是我们的不自由的一种特定形式的表达,以及这种不自由的特殊基督教表现。
如果我们考察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督教性质的第二种方式,即把人的存在及其表达区分为两种秩序:政治的和市民社会的,或国家的和经济的(他定义为“天国的”和“尘世的”),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清楚。当国家宣布它把我们当成平等者来对待而无视令阶层固化的社会权力如财产、教育时,我们获得“解放”的方式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抽象和有限的方式,循此解释,马克思论证了政治国家甚至在其最世俗的方面也是基督教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国家标榜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反映了与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验相对立的理想,正如同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平等的,却在世间无平等可言。国家代表了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的一种基督教的政治想象: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相对,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是不自由、不平等和相互漠不关心的。由此,马克思总结道:
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处于同样的对立之中,它用以克服后者的方式也同宗教克服尘世局限性的方式相同,就是说,即它同样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在这里,即在人把自己并把别人看作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像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17)
在此,马克思的论辩同样是多方面的。在一个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自由宪政国家中,人民的自由、平等和联合被理解为是由国家给予的,而在现实生活、市民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却不存在自由、平等和联合,就此而言,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基督教的。马克思也论证说,国家本身在对生活和意识的组织上再现了基督教的宗教结构;国家靠着把自身确立为主权、自由和平等的来源,而建立起一种信仰结构,获得了合法性。简言之,马克思(在卡尔·施密特提出这个概念之前)提供了一种宪政国家的政治神学。(18)
“资产阶级社会的金钱力量”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货币的一节中,马克思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句,描写货币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使“陌路成兄弟”。他也把货币描绘成“人类的外化的能力”,人的“本质力量”不能做到的,依靠货币都能做到。马克思总结道,货币是最大的“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19)货币“混淆”和“替换”了一切“自然的和人的性质”,把世界颠倒了,让可爱、美丽、勇敢、令人尊敬变成了可厌、丑陋、懦弱、不值得尊敬。马克思把这种状况同另一种状况做了对比——在这另一种状况下,爱、信任、艺术、能力真实地存在或被认可——或者与这些事物未被交换价值所中介的状况(以与当代人更易接受的对本真性的怀疑相一致)做了对比。对我们来说,最引人入胜的是,马克思把这种颠倒、反转、替换和使陌生人变兄弟的力量视为货币的神性,“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20)。的确,马克思在此文中没有发起对货币作为中介或腐蚀势力的批判,即对人的力量和能力的异化的批判,而是把货币拟人化为一种亵渎神明的、去神圣性的、同时又是神明的力量。货币破坏了诸如爱、明智、美、勇敢和诚实之类不可言喻的善及属性,把它们变成了可买卖的商品,就此而言,它是亵渎神明的和破除神圣性的。与他在别处所阐述的商品化和拜物教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坚称货币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21)。因此,货币不仅被当成一个神来崇拜,而且在市场社会就有神的力量——“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是“至高存在者”(22),马克思如是说。但是,使货币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亵渎之神,它模仿上帝的力量和起源,却颠倒了事物的自然或固有秩序——使丑的变成美的,不可爱的变成可爱的,恶的变成好的……总之,对马克思来说,金钱像所有神明一样,是人自身力量的外化和投射,进而变成了主宰人的一种力量。但金钱不仅仅被崇拜,它还主动地破坏了世界的神圣性和真实性。金钱是一个打破和代替人的自然力量和能力的神明,一种破坏人与世界最圣洁部分的亵渎力量。
资本主义创造了除劳动力或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拜物教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出卖的无产阶级,造成了交换领域内公平自由的意识形态的(因而是错误的)表象,对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维持来说,什么是最为关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显示了盘根交错的两个过程,只有理解这两个过程的联系,才能看清楚资本的秘密。这两个过程一起推动了资本主义,并使之稳固和合法。从而,虽然对劳动力的榨取在商品生产中是资本的实际源泉,但是马克思指出,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的拜物教“同商品生产分不开”。(23)因此,一个是“物理”过程,一个是“思想”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来说,两者缺一不可。
让我们回忆一下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常被引用的段落中提到过,理解商品拜物教需要“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但是,马克思在那里真正要说的是什么?下面是这段话的完整表述: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属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4)
正如神明作为我们想象的产物能像真实的力量、创造世界的力量一样显现和活动,商品作为人用手创造的产品也拥有生命。商品和神都是人的创造物、人的关系的表现,都具有主权的形式。这就是对马克思来说为何拜物教与宗教如此接近的原因,为何商品拜物教需要“求助宗教世界的幻境”的原因。在马克思眼里,这种拜物教的或宗教的维度再次成为资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因此,尽管资本主义是亵渎的力量,但它并没有消除宗教意识或宗教对象,它并非与宗教信仰互不相容。正如利润在流通领域内形成的假象掩盖了剩余价值来自生产领域的真相一样,信奉商品有内在价值或有“生命”的假象,掩盖了劳动是商品价值来源的真相;我们的平等、自由借助受国家保护的权利来确保的假象,掩盖了私有财产造成阶级社会的真相。将这些假象的形成联系到一起的,是对人类活动造就的权力的错误解释,这种错误解释是通过神秘化过程发生的,也把人类自由送上了祭坛。将这些假象的形成联系到一起的,也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中的起源,这个历史尚不是属人的,即虽然历史是人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历史本身没有被人所理解和把握。
总之,马克思对宗教和宗教性的唯物主义批判并非是说,商品化、亵渎或国家对世俗化的宣告即等同于宗教或宗教性的丧失,等同于不信、去魅,甚或一个不再是“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更高级存在的……神灵、法术或力量”(25)居于其中的秩序的降临。毋宁说,资本主义在亵渎世界的时候,产生和吸取了被广泛传播的以世界为宗教崇拜对象的潮流。世俗国家也吸取和再造了一种“宗教态度”。资本所造成的一切关系的被亵渎——资本在此显露了它自己的价值和效果——同商品拜物教、同价值生产的神秘化性质汇聚起来。而且,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货币力量视为一种宗教的力量,一种颠倒的力量,一种亵渎的力量,一种创造的力量,尽管还并非一种属人的力量。亵渎和拜物教即刻便成为资本特有的力量、资本自身在宗教层面的席位。这是某种唯物主义,但不是靠简单地把人类历史还原为经济动机或过程、靠一个因果联系的世界就能得出的唯物主义,也不是一种把世俗主义等同于神秘力被穿透力所打破的叙事。这也是某种世俗主义,但既不是所谓在资本主义撕下宗教的面纱时暴露出真实世界或真实自我的一种化减故事,也不是把自身等同于本体论或认识论真理的世俗主义。
(查尔斯·泰勒的巨著《世俗时代》从宗教视角来考察西方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自2007年出版以来即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篇论文收录于关于此书的研究论文集《世俗时代的世俗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Secularism in a Secular Age),edited by Michael Warner,Jonathan Vanantwerpen,and Craig Calhou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2010),文章比较了泰勒与马克思关于宗教和世俗化的思想。译文有删节。)
注释:
①这一讨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泰勒特有的观念论风格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是他通过回避观念或意识的进步主义演变并全然抛弃辩证法而获得的。泰勒的观念论受福柯和韦伯的启发,有强烈的谱系学背景,旨在追溯当今世界的历史,但他讲的故事不仅关注工业化和政治革命,而且关注观念发展中的事件和突变,而不是讲述朝着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稳步前进的故事。
②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12-213.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85页。
④⑤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13,p.22.
⑥⑦⑧Charles Taylor,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530,p.33,pp.1-2.
⑨⑩(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1、275、275、275、274—275页。
(14)(15)(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93、194、171、172—173页。
(18)Carl Schmitt,Political Theology: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19)(20)(2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247、245—246、246—247、246页。
(23)(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39、138—139页。
(25)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47.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论犹太人问题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基督教论文; 资本论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