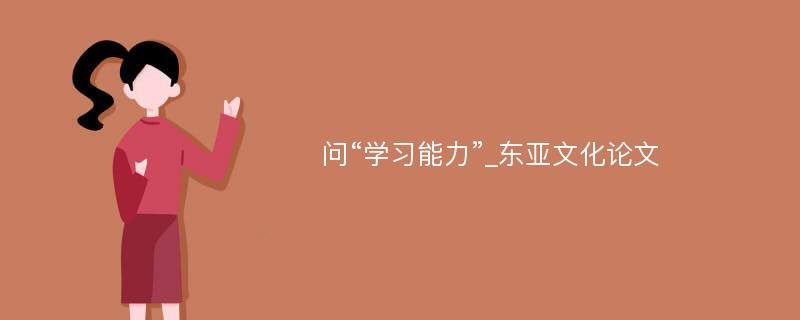
叩问“学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力危机的背景——“学力神话”的破灭
(一)社会秉持的“学力”尺度
学力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儿童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厌学”?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就得认识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与学力的关系。
在这里,需要再界定一下“学力”。我曾经指出,“学力”概念之所以如此混乱不堪,是由于并没有把“学力”(achievement)视为一种“基于学习的成就”的实体,而是视为“力”的功能了。进而又把“力”(能力、权力)的功能视为学力的实体,从而助长了围绕“学力”概念的混乱。根据“学力”的原文“achievement”,“学力”是“学校教授内容”的“学习成就”。这个定义是表达学力的“实体”的。但是,为了理解社会与学力的关系,在这里有必要界定“学力”的“功能”。
之所以把学力归结为“力”(power:能力,权力)的表征,是因为它可以充分地表达学力的社会功能。因为,拥有“学力”就是拥有某种“能力”,拥有某种“权力”。我把这种“学力”的功能理解为跟“货币”一样的功能。或许会令人惊异,学力是一种拥有如下三种性质的货币。
第一,学力同货币一样,具有作为评价的功能。正如货币是从数量上去比较多样质的物品、做出估价那样,学力也是按照一定的均质的尺度去衡量多样而异质的经验而发挥作用的。用同一的分数来表征音乐的学习经验、英语的学习经验与理科的学习经验,原本是滑稽可笑的。然而,学力却是具有这样一种功能性的意味:用同一尺度来评估多样而异质的经验的评价标准。
第二,学力同货币一样,具有作为交换的功能。货币是谁都想拥有的不会拒绝的唯一的商品,即便在需求关系之中不能得到相等的物品也具有间接地实现物与物的交换关系的功能。货币使得在物与物的交换中只能偶然地实现的交换关系,一举扩大并合理化了。同样,由于学力是谁都想拥有的不会拒绝的唯一的商品,具有在应试市场与劳动市场中作为交换手段的功能。学力在应试与招聘的场合,可以作为间接交换的手段,把未必一致的招聘者需求与志愿者能力的关系加以合理化的功能。
第三,学力同货币一样,具有作为储蓄的功能。由于货币是期望储蓄的唯一的商品,带来了经济活动的计划性与持续性,进而储蓄的欲望又促进了投资这一经济活动。同样,由于学力也是期望储蓄的唯一的教育概念,学习活动被赋予了计划性与持续性,而储蓄的欲望又进一步促进了作为投资的教育活动的基础。这样,学力从功能侧面看来,体现了货币与实物的双重特征。
学力的“货币”界定终究是抽象思维的想像的产物。跟基于经济社会的情势奇货可居、货币就会如同纸屑贬值一样,学力也有贬值的危险。就像货币的价值在通货市场的行情上不断变动那样,学力的价值也会在社会经济的状况中不断变动。
我的假设是,今日日本的学力危机可以理解为:作为通货危机的学力危机,亦即“学力神话”的破灭,引发了犹如通货暴跌般的学力暴跌。倘若我的这种假设是真的,那么,如今讨论的“学力低下”不过是预示着更大危机的来袭而已。
(二)所谓“学力神话”有效的社会
在学力的功能界定为“货币”的基础上,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厌学”的背景。
根据“国际教育评价协会”(IEA)1999年的调查,中小学生校外学习时间与学习的学生的比例。正如日本(1.2小时)、韩国(1.6小时)那样,东亚国家与地区中小学生的校外学习时间是世界上最低的。从校外学习的学生的比例来看,日本(59%)、台湾(55%)、韩国(5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0%),处于最低的水准。在作为调查对象国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之中还有一个新加坡是3.5小时,处于高位。但重要的是,在1995年的同样项目的调查中新加坡是4.6小时,四年间就减少了1小时。同1955年相比,由于台湾没有调查不能比较,但日本减少0.7小时、韩国减少0.9小时、香港减少0.9小时,均显示出除伊朗和希腊之外的国家少见的急剧减少的倾向。
就是说,“厌学”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性现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日本等都是学力成就垄断了第一位至第五位的国家或地区。究竟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学力成绩在世界独占鳌头,却刺激了“厌学”的作用呢?
我把鲜明地呈现“厌学”的东亚国家与地区的教育危机称为“东亚型教育危机”。这里所谓的“东亚国家与地区”是指中国大陆、朝鲜、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七个国家和地区。通常所说的“东亚”还包括马来西亚在内,但考虑到宗教背景和历史背景,这里马来西亚除外。
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以特有的方式,谋求基于学力竞争的社会移动(阶级与阶层的阶梯上升)的活跃化,从而达成了教育与产业的“压缩式现代化”。1980年日本的高中升学率是94%、大学、专科的升学率达37%。当时欧洲各国的全日制后期中等教育的普及率是70%左右、高等教育的升学率是10%左右,高于日本教育水准的国家只有美国。欧美各国花了几个世纪达成的教育与产业的现代化,日本仅用一个世纪就超越了。
“压缩式现代化”在韩国和台湾更加甚嚣尘上。日本花了一个世纪达成的教育与产业的现代化仅花了半个世纪就达成了。韩国大学的升学率超过了日本(50%)达到60%。实现这种“压缩式现代化”的秘密就是基于学力竞争的社会移动的活跃化。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实现基于学力竞争与应试竞争的高效的教育,从而实现了教育与产业的“压缩式现代化”。世界独占鳌头的学力就是其产物。
不应当忽略的一点是,东亚型教育与产业的“压缩式现代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冷战格局的世界体系,从经济发展这一点来看是“平等”的体系。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冷战格局下国民生产总值以4%的年率发展经济。不过,不应当忽略的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接受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特需,而且在美国军事战略的庇护之下得以维持保护贸易,使得国民生产总值(GNP)以10%的年率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日本由于安保条约,战前占国家预算三成以上的军费缩小到5%、6%,能够以庞大的国家预算投入经济发展。
从1970年到1985年日本的GNP比率实现了四倍以上的攀升。韩国也是同样,每一个国民的人均GDP在1970年只有数百美元,但到了2000年接近一万美元,获得了飞跃的发展。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正当教育与经济处于“压缩式现代化”的巅峰时刻,冷战格局崩溃,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全球化在一举扩大的状况下,爆发了被称为“亚洲危机”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韩国在大学升学率达60%、人均GDP接近一万美元的关头,国内经济崩溃而进入危机管理的体制,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曾经获得了飞跃性成功的“东亚型教育与经济”,如今正在成为破绽与危机的象征。
只要“压缩式现代化”在进行之中,基于学力竞争的社会移动的活跃化就可以顺利地发挥其功能,从而带来“学力”这一“通货”具有超常的价值。数十年前的日本,无论是儿童的学习积极性还是对学校的信赖,对教师的信赖与尊敬,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发挥着“学力神话”的效力。“学力神话”在韩国与台湾也发挥了超越日本的效力,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也在发挥着奇效。例如,韩国普通高中生从早上7时至晚上10时在校学习。正规课业尽管在下午3时就结束了,但学校成了私塾的替身,仍然组织应试学习直至晚上10时。中国城市的高中生更为惨烈,每天的学习从早上6时至晚上11时。
但是,“东亚型教育”达于教育现代化的巅峰之际,随着经济转入低成长时代,“学力神话”一旦破灭立刻就显示出破绽了。从以往“国际教育评价协会”(IEA)的调查结果来看,作为校外学习时间所表现出来的学习动机,显示出同该国GDP的成长率有高度的相关性。日本的儿童在高速成长期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学习动机,如今,日本儿童的学习积极性跌入了世界的最低谷,也是同GDP的成长率相关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压缩式现代化”的途程中,大多数儿童掌握学力、升入高一级学校,获得了高于家长的教育水准和社会地位。但是,“压缩式现代化”一旦终结,事态即逆转直下,通过学校教育已经不可能获得高于家长的高学历与社会地位了。“学力神话”的破灭,亦即“学力”这一“通货”的暴跌。
(三)“学力”与社会之间的落差
“学力”这一“通货”的暴跌,并不仅仅发生在学校与家庭(儿童与双亲)之间,也发生在企业与学校、国家与学校之间。“东亚型教育”是适应产业社会的教育,产业社会形成金字塔型的劳动市场。这种劳动市场、金字塔型的学历社会与学校体制,作为“压缩式现代化”的推进力,发生着交互作用。
但是,基于冷战格局的经济的全球化,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急剧地从产业主义社会转型为后产业主义社会。企业超越了国家的疆域转型为跨国企业,为了寻求廉价劳动力而转向海外。由于这种全球化,金字塔型劳动市场的底部瓦解了。
而且,在产业主义社会里是以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占据经济活动中心的,在后产业主义社会里,信息与知识的交换以及人际服务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后产业主义社会也称为“智能社会”。在智能社会里,“知识的创造与交流”替代了“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成为经济的中心。产业主义社会里发挥了拔群的效力的“东亚型教育”在转向后产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发生了极大的龃龉。这样,即便在企业与学校之间,“学力神话”也破灭了。在“东亚型教育”中形成的学力这一“通货”迎来了暴跌的危机。
在国家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中也是如此。基于“东亚型教育”的学力发生了更加复杂而深刻的龃龉。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中曾根首相执政以降,日本的国家政策是以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基调的。新保守主义对抗全球化,转向国家意识与家长制意识的固守;新自由主义则迎合全球化,面向国家责任极小化、个人责任最大化的“结构改革”。
在同学力的关系上存在着日本特有的复杂问题。欧美国家的新保守主义正在复兴西欧中心主义意识,而推进复活古希腊以来“博雅教育”传统的改革。但是,日本的新保守主义却是通过抵制西方科学、教养与民主主义精神,而推进扎根日本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的复兴。“心的教育”、“生存能力”或是“宽松教育”这些难以翻译的术语发挥着教育改革的标语、口号的作用,就是基于这种新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可以说,“人格重于学力”、“态度重于知识”这种教育评价的转型也是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就是说,受到“学力低下”论攻击的文部科学省的“宽松教育”的教育政策是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所推进的政策。如此错综复杂的发展使得“东亚型教育”的学力在国家与学校之间也发生了深刻的龃龉。
因此,学力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从“东亚型教育”的藩篱中解脱出来,重新界定适应新型社会的学力,恢复“学力”的实质性价值:从“勉强”走向“学习”。①不过,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面临复杂的困局。这个地区的教育原本是受战前日本的殖民地化政策的影响,以日本的教育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大陆显示出以年率9%的GDP的发展势头,正处于“压缩式现代化”的途程之中。但是,正如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在演绎日本教育改革的事态所表明的,无论哪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找不到有效的出路。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作为东亚学力危机复杂化的一个要因,是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所特有的二元对立的概念构图。
东亚国家和地区围绕“新学力观”的讨论如实地表明,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基于科学与生活、科学与道德、科学与艺术、知识与经验、知识与思维、知性与情感、理性与感性、国家与个人、男性与女性、教师与学生、成人与儿童等一连串二元对立的概念构图所形成的。可以说,把“知识与技能”的教育与“兴趣、动机、态度”的教育对立起来的“学力观”就是一个典型。“教”与“学”对立的教学观;“指导”与“援助”对立的教学观;“教师中心”与“儿童中心”对立的教学观,统统都是受二元对立的概念构图所束缚的思维方式的典型。甚至可以说,“学科系统”与“生活综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是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正如综观欧美的教育改革与教育言说所表明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以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构图来探讨教育改革的舆论本身,就是东亚教育根深蒂固的殖民地主义体质的反映。克服二元对立概念构图的新型学力观的创造,正是我们所祈求的。
二、如何克服“基础学力”的复古主义
(一)“基础学力”指的是什么
无论是主张“学力低下”论的人还是回应“学力低下”的文部科学省,都把教育改革的核心课题聚焦在“读、写、算”的“基础学力”这一点上,是不可思议地一致的。众多的教师和教育学者围绕“学力低下”的议论之所以显示出冷淡的反应,是同这个问题相关的。
担忧“学力低下”的见解总是由保守势力作为抵制教育的革新实践的言说提出来的。日本在战后对新教育的“基础学力低下”的评判是如此,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撒切尔为中心的保守势力也提出“基础学力低下”论,借以攻击劳动党推行的儿童中心教育。美国也是同样。保守势力发起了一场“回归基础”(back to basics)的运动,旨在抵制上世纪80年代初的开放学校与多元文化教育。学力论争隐含着保守势力不断发难的性格。
然而,“读、写、算”就是“基础学力”吗?确实,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和参与社会所必需的知识,是借助语言与符号操作来建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写、算”可以说是“基础学力”。不获得语言与符号的操作能力,任何学习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不过,倘若把“读、写、算”视为单纯地掌握读、写汉字的能力与计算能力,那就不能称之为“基础学力”。这是因为,“读写能力”原本就是不限于识字而言的。
例如,“会写信”不仅仅“会写字”而已,而是意味着能够运用“信函”这一种样式的文体与表达。信函一般是从时令的问候开始的。据说在日本近三十种的汉文教科书中涉猎了究竟该用哪些问候的措词。不仅是问候语,近三十种的汉文教科书几乎囊括了信函用的所有用词。所谓“文如其人”,之所以能够“读信如读心”,就是因为读了信,可以看透写信人的教养。我的祖母是明治初年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年幼时代就有了熟读四书五经的教养。90多岁了,还在埋怨“近来的人连封信也写不好”。据说森鸥外②在6岁时就饱读四书五经了。无论是森鸥外抑或夏目漱石③,明治时代的文人和教师都拥有汉文典籍的教养。可以说,所谓“会写信”就是以这种教养为基础的。不管怎样,“会写信”的本来意义和以“读、写、算”为教育中心的本来意义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是必须认识到的。
“会写信”的本来意义的“读、写、算”,是指英语的“Literacy”,被译为“识字能力”。“Illiteracy”被译为“非识字”或“文盲”,这种译语造成了误解。一般认为,“Literacy”最初的用法是17世纪的英国,当时“Literacy”的含义系指能够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今日美国,通常“Literacy”指的是“功能性识字”。它有别于“识字”,意味着作为社会人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共同教养。具体地说,是指具有读懂报纸的能力。因此,“Literacy”的译语视为“教养”是适当的。④“教养”(Literacy)这一语词可以在“基础学力”的意义上使用。美国联邦政府的“教养”(Literacy)基准,在19世纪中叶规定为小学毕业程度的教养;在上世纪30年代规定为初中毕业程度的教养;在上世纪50年代规定为高中毕业程度的教养,直至今日。就是说,适应大众教育的普及而规定了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教养”(Literacy)基准。
倘若要界定“基础学力”,我以为采用“教养”(Literacy)的概念来定义是贴切的。在今日的日本,几乎人人是高中毕业生,所以,应当设定高中毕业程度的教养是“基础学力”。倘若考虑到终身学习时代,把高中毕业程度的教养作为“基础学力”来设定是适当的判断。
(二)累积式学力观的谬误
不过,当今日本主张的,不是作为“教养(Literacy)的“基础学力”,而是限定于“读、写、算”的“基础学力”(basic skills)。这种“纯基础学力”果真能够提高教育的效果吗?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回归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我们从中可以获得珍贵的教训。
就结论而言,“回归基础”运动让复古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于学校教育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个运动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在不能解决低学力问题、且造成了青年失业者的扩大这一点上说,这个运动是以教育的失败而告终的。失败的原因大体有两个。
其一,没有认识到,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并不是通过反复练习来习得的,而是通过经验,功能性地加以习得的。
其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回归基础”运动展开的上世纪80年代前半叶的美国,正处于从产业主义社会(工业社会)走向后产业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在上世纪60年代末,蓝领工人占据了整个劳动力的70%的比率,到了90年代急剧下降到10%以下。由于这种转型,靠“基础学力”就业的简单劳动力市场处于崩溃状态,迎来了失业者充斥社会的苦境。重视“基础学力”的教育虽然满足了保守层的政治意识,却是一种同综合化的、由高深知识组织起来的社会变革背道而驰的改革。
因此,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降,美国的教育改革不是以“纯基础学力”为中心,而是以“提升教育内容的水准”为中心课题展开的。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1983年)的报告以后的美国,竭尽全力推进提升教育内容水准的教育改革。到了90年代,美国基于信息革命的信息产业带来了经济的转型,在这种转型过程之中,美国采取了支持新兴知识领域的企业、促进教育发展,借以解决失业问题的策略,是众所周知的。
美国“回归基础”失败的教训,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第一个教训是,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与其说是通过反复练习来习得的,不如说是凭借经验,功能性地加以习得的。
比如说,有一个小学5年级学生只有3年级学生的汉字读写水平。为了提高这个孩子的汉字水平,采用反复地在练习本上抄写小学3年级的新出汉字的办法,并不是徒劳的。但是,倘若这个孩子喜欢钓鱼,不如让他多读钓鱼的书籍,并让他在伙伴中表现,增加亲近汉字、使用汉字的机会,将会更加有效。确实,即便记住了小学3年级的汉字、小学4年级的汉字、小学5年级的汉字,倘若缺乏接触、使用汉字的机会,也会被忘得一干二净。哪怕是错读或是错写了汉字,只要增加了接触汉字、使用汉字的机会,效果也会好得多的。
作为反复练习的机械训练之所以受到重视,是迷信只要反复练习就可以得到“巩固”的神话。确实,有的技能经过反复练习就能无意识地巩固下来。例如,骑自行车的技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倘若年幼时代骑过,哪怕多年不骑了,仍然容易掌握。
然而,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大半并非如此。九九口诀通过反复练习看来是巩固了,不过,倘若没有使用的机会,会很快忘却。儿时有去海外生活的经验的人,过了数年之后,外国的语言也会忘却。但是,外国语的发音与声调会作为身体的记忆巩固下来。知识与技能借助反复练习,有的可以得到巩固,有的不可能得到巩固。在学校里学习的运算方法、汉字与英语的单词等,持续不断地得到活用的经验是重要的。汉字和运算在开始习得之际,反复练习是有效的。但是必须认识到,一度通过反复练习习得了的知识、技能未必是巩固的。再重复一遍,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是通过经验才得以功能性地习得的。
这样说来,并不是说识记与背诵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识记与背诵对于学习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因为,可以借助肢体动作强化的方法来学习。艺术的技艺、学习的技法、运动的技能等文化型的模仿是学习的中心,没有识记与背诵就不能学习。不过,同时必须认识到,只要不是教本、字帖需要模仿的东西,识记与背诵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关于“基础学力”的另一个谬误就是这样一种教育观念:以为学力的形成是循序渐进地累积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教师和成人都被这种谬误所束缚。文部科学省也出于这种谬误将教育内容削减了30%。“儿童的学习一旦困难就回归基础”是学习的铁则。然而这里所谓的“基础”是“基本”(fundamental)的含义,并不是扎根“基础”(base)的意味。然而,多半的教师一旦碰到儿童学习困难,便降低教育内容的水准。可以说,这是教育上的极大谬误。
“学力”并不是靠单纯的累积形成的,而是借助高端引领才得以形成的。学过教育心理学的人只要想想维果茨基(Л.C.Bыгoтский)的“最近发展区”与“内化”的理论就可以明白,“学力”的形成并不是基于自己理解的水准,而是通过同教师与同学的沟通,认知自己当下的理解水准下并不理解的事物,并把它加以“内化”的结果。
在学习中需要的,并不是在儿童不理解的时候,先降低程度再自下而上地提升,而是通过伙伴与教师的帮助,模仿理解事物的方法并加以“内化”。学习是需要“冲刺”与“挑战”的。
诸多事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小学生在算术课中最难的是分数的运算。在学习分数运算的时候,许多儿童理解不了分数的意义和运算方法的意义。分数意义的掌握和运算意义的理解通常是从习得比例开始的。这次《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中被削减的内容有梯形与多角形的面积。实际上,梯形面积的教材是可以通过多样方法的交流,把课上得有声有色的。况且,重要的是,许多儿童学了梯形面积之后,才理解了三角形面积的求法的。学力不是靠低水平反复来累积的,而是靠高端引领才得以形成的。
自下而上地累积学力的教育观念,在“垫底校”的高中教师中是根深蒂固的。在都市部的“垫底校”高中就学的学生,几乎都是小学、初中阶段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因此,几乎所有教师都断定他们的学力程度相当于小学3年级的水准。然而,通过这些“垫底校”高中学生的意识调查发现,他们对学校的最大不满是“教学内容过分浅显”。他们迫切期望“高难度教学”。教师在拼命地追求“懂的教学”,学生却期待“不懂的教学”。
由于存在这种鸿沟,在都市部的“垫底校”高中就学的学生中有将近一半是中途辍学者。为了填平这种鸿沟,我要求协议合作的“垫底校”高中调查一下学生入学时的数学水准。结果发现,同教师的预想相反,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达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水准。不过,正答率呈减少趋势:达初一水准的有半数,达初二水准的有三分之一,达初三水准的有五分之一。这个结果可以作为学力需要高端引领的一种旁证。在这些学生上学的高中倘若能够实施同通常高中一样的数学教学,数学成绩本身或许仍然会停留于“差等”水准,但毕业时学力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达到初三的水准。“高难度教学”——许多学生的这种殷切期待是一种合理的要求。再重复一遍,学习是需要“冲刺”与“挑战”的。
美国“回归基础”改革的失败启示我们的第二个教训是,在后产业主义的“知识社会”里难以凭借“基础学力”就业的现实,在现代日本更加深重。综观上世纪90年代以降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就可以了解,追求“纯基础学力”的文部科学省的教育改革是何等的时代错误。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东亚型教育”奏效的产业主义社会业已终结,其典型的现象是金字塔型劳动市场的解体;是单纯劳动市场的崩溃带来的青年劳动市场的崩溃。
如今,中国工厂的工人工资只有日本的四十分之一。伴随全球化的进展,日本国内的劳动市场的底部受到外国市场的侵袭乃是理所当然的。其影响所及,是青年劳动市场受到最深重的打击。据劳动省(厚生劳动省)的调查,1992年的高中毕业生需求人数是一百六十四万人,1998年锐减为三十七万人,2001年再锐减为十五万人。在不足十年的期间里,青年劳动者市场的90%被消灭了。
生存于后产业主义社会(智能社会)的儿童所必需的教育不是“纯基础学力”的教育,而是能够应对知识的高度化与复杂化的、实现优质学习的教育。
倘若仍然执迷于文部科学省的“纯基础学力”,就会像上世纪80年代中叶的美国那样,尽管高知识水准的人才需求扩大了,但由于难以雇用“纯基础学力”水准的人才,只能招致大量的青年人加入失业大军的弃民化的结局。
无论哪一个时代,儿童与青年对时代的变化总是最敏感的。在儿童与青年之中蔓延的“厌学”现象是由于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之中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所致。
注释:
①同样是“勉强”两个字,在汉语中系“无理强制”之意,但在日语中却是“读书”、“用功”、“学习”的含义。佐藤学基于两者不同的文化内涵,把“勉强”的学习界定为应试教育支配下,高效率地灌输现成教科书知识点的内容,旨在应付升学考试的学习。但这不是真正的学习。真正的学习是一种对话与修炼的过程。他说:“学习,可以比喻为从既知世界到未知世界之旅。在这个旅途中,我们同新的世界相遇,同新的他人相遇,同新的自我相遇;在这个旅途中,我们同新的世界对话,同新的他人对话,同新的自我对话。因此,学习的实践是对话的实践。”课程改革的中心课题是,实现从“勉强”到“学习”的转换。即从应试教育的“勉强”的学习走向“活动式、合作式、反思式”的学习。参见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钟启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译本序。——译注
②森鸥外(1862-1922年),日本明治时代小说家、翻译家、军医。从事西欧文学的译介与评论,被誉为明治文坛的“巨匠”。著有小说《舞姬》、《青年》、《雁》、《阿部一族》等。——译注
③夏目漱石(1867-1916年),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英文学者、小说家。1905年发表《吾辈是猫》,接着出版《伦敦塔》,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地位。著有《虞美人草》、《草枕》、《三四郎》、《从今往后》、《门》、《道草》、《明暗》等诸多作品问世。——译注
④OECD的“阅读素养”(reading literacy)的界定是:“个体理解、运用及省思书面文本,以达成个人目标、发展个人知识和潜能,有效参与社会的能力。”因此,PISA2006的“阅读素养架构和评价设计”不同于一般成就测验强调学科知识的认知能力。PISA试题强调问题解决能力、跨学科知识的综合,突出高层次思考,着重阅读理解并寻找有用的解题线索,重视表达和沟通的能力及与生活情境结合。参见台湾课程与教学学会《基本能力评量之各国经验比较》2010年1月版(《课程与教学季刊》第13卷第1期)第23-26页。——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