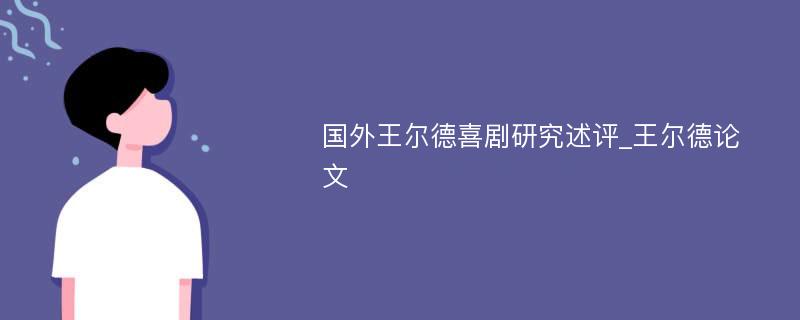
国外王尔德喜剧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尔德论文,述评论文,喜剧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1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94X(2007)04-0080-05
王尔德以其杰出的喜剧创作,打破19世纪英国舞台的沉寂,带来了英国戏剧的复兴,喜剧方面的成就是王尔德对英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王尔德一共写过4部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 s Fan,1892)、《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1893)、《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1894)和《认真的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1894)。这些剧作当时轰动英伦,王尔德也一度享有两部喜剧在伦敦同时上演的殊荣。喜剧给王尔德带来了最惊人的成功”,[1] 14它们至今仍有强盛的活力,是不少剧团的保留剧目,其中《认真的重要》为世界剧坛长演不衰的喜剧经典。
国外王尔德喜剧的研究成果颇丰。据米哈依尔(Edward Halim Mikhail)1978年编辑出版的《王尔德评论注释书目》(Oscar Wild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2] 10提供的资料统计,从1892年到1975年间,关于王尔德喜剧的研究成果多达871项。时至今日,人们从未停止过研究,新的成果仍不断出现。
以目前掌握的资料为依据,对一百余年来国外的王尔德喜剧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予以考察:1892~1899年为第一个阶段,1900~1969年为第二个阶段,1970年迄今为第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1892~1899)
这一时期,王尔德在人生舞台上历尽悲欢,生活极富戏剧色彩。4出喜剧的成功,使王尔德的声誉如日中天;一桩丑闻的暴露,又使他锒铛入狱,最终声名狼藉。生活的戏剧性变化,直接影响着他的喜剧在当时的命运。
1892~1895年间,随着4出喜剧在伦敦先后上演,英国掀起了一股评论王尔德喜剧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至少有20多家报刊登载评论文章,所载文章总数达到150余篇。《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首演后的两天之内,有14篇评论文章见诸报刊;《认真的重要》公演后的第二天,竟有12篇剧评出现在伦敦的报刊。《周日时报》(Sunday Times)、《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世界》(World)、《每日新闻》(Daily News)、《观察家》(Observer)、《时代》(The Times)、《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戏剧》(Theatre)、《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等报刊都及时刊登过论述王尔德喜剧的文章。
这些评论反映了同时代人对王尔德喜剧的看法,既是日后研究的珍贵资料,也代表了王尔德喜剧研究的最初成果。当时的评论者亲临剧院观看,对演出效果了然于心,因此,剧场观众的反映成为他们评剧时的重要参照。阿契尔(William Archer)分析《认真的重要》时着意提到:该剧演出过程中“剧院笑声如潮”;[3] 661895年1月4号《早间邮报》刊发的评论《理想丈夫》的文章,作者开篇便描述了此剧演出结束后,王尔德两次登台谢幕的情境,并强调:“不仅王尔德欣赏该剧的演出,而且观众也同样欣赏。”[3] 60可以根据自己在剧院的现场感受审视王尔德的喜剧,这是王尔德同时代剧评者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他们的评论往往及时、有针对性,无论对观众还是作者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在同时代人的评论中,一些知名人士的评价尤其引人注目。戏剧理论家阿契尔、剧评家沃克利(Arther Bingham Walkley)、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叶芝(W.B.Yeats)、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都是王尔德喜剧的热心观众和批评者,他们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代表性。这些名家一致肯定王尔德的戏剧天才,赞赏剧作中的机智,同时也指出在戏剧动作、人物形象刻画方面的不足,对剧中泛滥的机智也略有微词。阿契尔指出:“在现代英语戏剧中,王尔德的戏剧独树一帜,水平极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知识能力、艺术能力、戏剧天赋方面,后世戏剧家无人能与之匹敌。”[1] 144在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契尔认为剧中的机智有炫耀之嫌,并将它视为与“喜剧的优点随之而来的缺点”。[1] 145当时英国最有影响的戏剧评论家之一沃克利在论述《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时,一方面肯定该剧十分成功,“自始至终没有一刻使人厌烦”,[1] 119另一方面也指出它情节未脱窠臼,主人公的某些行动不够理性,机智的反论用得过多,显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立场。
由于同时代评论者深受维多利亚时代精神濡染,且对王尔德的生活、个性了解真切,因此评论时惯于从道德角度审视,常常将王尔德的个性特征与他喜剧创作的特点相联系,存在以人论文的倾向。论及创作态度,大多数评论者皆因剧作者的玩世不恭,断定他没有严肃地对待喜剧创作;分析喜剧语言,评论者总会涉及王尔德机敏的谈吐;探讨思想内涵,则多以道德价值为尺度。对此贝克森指出,19世纪后期的许多评论家“未能抓住王尔德独特的天赋,他们评判王尔德的成就时,局限在文学是道德启蒙的一种形式,其核心是真诚这样一个批评框架内”[1] 2。这种注重道德、以人论文的批评特征,打下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烙印,预示着王尔德喜剧在当时不可避免的遭遇——退出舞台。1895年,王尔德因同性恋罪被捕入狱后,他的狼藉声名影响到剧作的演出,风靡一时的王尔德喜剧随即淡出舞台,如潮的评论也因此销声匿迹。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1896~1899年长达4年的时间里,伦敦各家报刊上未出现一篇评论文章。
二、第二个阶段(1900~1969)
1900年,王尔德在贫病交加中告别人世,他生前的是是非非也随风而去,人们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痛惜。在他去世的第二天,英美一些报刊登出讣告。这些讣告都不约而同地提及王尔德的戏剧成就,并以不少篇幅评价了其喜剧。美国的《纽约时代报》(New York Times)、《时代》(The Times)及英国的《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登载的讣告中对王尔德喜剧的评价颇具代表性,我们可以视之为20世纪王尔德喜剧批评的开端。
从1901年开始,王尔德的喜剧作品被重新搬上舞台。在重演王尔德喜剧方面,圣·詹姆斯剧院经理兼演员亚历山大(George Alexander)功不可没。1902年,亚历山大在圣·詹姆斯剧院重新上演了王尔德的喜剧代表作《认真的重要》。此次演出虽然获得好评,但票房收入并不理想。几年之后,亚历山大分别在1909年、1911年和1913年3次重演《认真的重要》,并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此外,王尔德的另外3出喜剧也在他去世后不久重现舞台。
王尔德去世所唤起的痛惜之情,以及王尔德喜剧的重新上演,推动了王尔德喜剧研究。从1900年起,英美报刊上相继出现相关评论文章。这年12月8号,比尔博姆(Max Beerbohm)发表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8 Dec.1900)上的论文,是这一阶段的首篇王尔德戏剧专论。文中指出,王尔德“不只是一位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思想家,一位富于机智的人,一位文学风格大师”。[3] 69并认为王尔德的去世“对戏剧文学是多么令人痛惜的损失”。[3] 70比尔博姆的这篇评论,透露了王尔德喜剧研究的新动向——力图更加全面、深入地评价王尔德的喜剧,认识王尔德在戏剧史上的地位。此后,不断见诸报刊和收入论文集的王尔德喜剧研究论文,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这一趋向。蒙特格(C.E.Montague)的《王尔德的喜剧》(Oscar Wilde' s Comedies,Manchester Guardian,13 Apr.1908)对王尔德的4部喜剧逐一分析,显示了作者试图全面评价王尔德喜剧的努力;格林(Jacob Thomas Green)的《论戏剧家王尔德》(On Wilde as a Dramatist,Sunday Special,9 December 1900)、亨德森(Archibald Henderson)的《王尔德戏剧》(The Theatre of Oscar Wilde,Overland Monthly,1,1907)以及汉肯(St John Hankin)发表在《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1 May 1908)上的文章,都是对王尔德喜剧予以整体观照的上乘之作,重视文本分析是上述论文的共同特征。
在这一阶段,比较研究是当时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既有剧作家本人喜剧之间的比较,也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如赫瑞克(Land Herrick)的《一个显得重要的女人》(A Woman of Some Importance,Drama Magazine,New York,Apr 1930)着重将《认真的重要》同王尔德的其他3部喜剧进行比较,以揭示其创作的发展变化;格瑞格尔(Ian Gregor)的《喜剧与王尔德》(Comedy and Oscar Wilde,Sewanee Rewiew,Spring 1966)把莎士比亚和本·琼生纳入批评视野,在与他们的比较中展示王尔德喜剧艺术的独创性。福斯特(Richard Foster)的《作为模仿者的王尔德:再论〈认真的重要〉》(Wilde As Parodist:A Second Look at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Chicago:College English,no.1,Oct 1956)、瑞纳特(Otto Reinert)的《〈认真的重要〉的讽刺策略》(Satiric Strategy in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Chicargo:College English,Oct 1956)利洛克哈特(J.H.K.Lockhart)的《萧、王尔德与风俗喜剧的复兴》(Shaw,Wild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Comedy of Manners' ,Dublin:Hermathena,Spring 1968)等都是运用比较方法研究王尔德喜剧的佳作。虽然这些论文中的比较大多显得简略肤浅,但也体现了此间王尔德喜剧研究的开阔思路。
随着研究的深入,60年代出现了从心理角度研究王尔德喜剧的论文,其代表作首推甘兹(Arther Gans)的《王尔德社会喜剧中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 in the Society Comedies of Oscar Wilde,Modern Drama,May 1960)。甘兹此文从王尔德的创作心态这一角度,探讨同性恋与王尔德喜剧创作的关系,他认为:“显然,喜剧中隐瞒的罪恶及其希望社会认可、接受的诉求,是王尔德因同性恋导致的内心情境的反映。”[3] 129以此为出发点,甘兹进一步论述了王尔德喜剧中的自我冲突,其见解新颖独特,为日后的研究开辟了新路。
此外,随着王尔德作品的不断出版,不少名人或王尔德的生前好友为之作序。这些序言中对王尔德喜剧的精辟论述,是这一时期王尔德喜剧研究中极有价值的部分。戏剧评论家沃克利为《王尔德全集》(Introduction to vol.vii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New York,1923)撰写的序言中,简明扼要地分析了王尔德的4部喜剧,对剧中人物、情节、语言的论述都富有新意;诗人兼剧作家敦克瓦特(John Drinkwater)的序言(Introduction to vol.viii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New York,1923)则以莎士比亚、本·琼生和康格里夫的喜剧为参照,着重阐述《认真的重要》的独创性。为王尔德喜剧作序最多的是著名传记作家皮尔森(Hesketh Pearson),他先后为《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和吉尔伯特的〈忍耐〉》(Introduction:From" Bunthorne" to " Bunbury"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by Oscar Wilde and Patienceby W.S.Gilbert..London:Methuen,1952)、《王尔德的五部戏剧》(Introduction,Five Plays by Oscar Wilde,New York:Bantam Books,1961)和《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Introduction,Lady Windermere' s Fan by Oscar Wilde,London:Methuen,1964)作序。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也曾为好友王尔德的喜剧撰写序言。这些序言评价持重、公允,为人们解读王尔德喜剧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在这一阶段,一些王尔德研究专著中有关喜剧的论述或与王尔德相关著作中对王尔德喜剧的评论尤其值得重视,它们反映了此间王尔德喜剧研究的水平。1912年,兰瑟姆(Arther Ransome)出版了第一本系统研究王尔德作品的专著《王尔德:一种批评研究》(Oscar Wilde:A Critical Study London:Martin Secker),在第七章专论王尔德戏剧。在对王尔德喜剧的论述中,兰瑟姆注重王尔德的人格与剧作的联系,并将王尔德与康格里夫进行比较,显示了作者独到的批评眼光。其他专著如英格列比(Leonard Cresswell Ingleby)的《王尔德》(Oscar Wilde,London:T.Werner Laurie,1907)、苏利文(Vincent O' Sullivan)的《王尔德面面观》(Aspect of Wilde,London:Constable,1936)、本特利(Eric Bentley)的《作为思想者的戏剧家》(The Playwriter as Thinker,New York:Reynal,1946)、泰勒(John Russel Taylor)的《佳构剧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ll-Made Play,London:Methuen,1967)等都不乏对王尔德喜剧颇有见地的评论。如苏利文从戏剧与生活的关系分析王尔德的喜剧情境,并将王尔德与惠斯特勒(Whistle)、平内罗(Pinero)进行比较,阐述王尔德喜剧的创作目的与机智特征,令人耳目一新。
综观20世纪前60余年的王尔德喜剧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重视文本,注重比较研究是此阶段的主要研究特点。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视阈不够宽广,研究者很少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王尔德喜剧。在对王尔德喜剧的比较研究中,大多研究者仅就王尔德喜剧的某一方面与其他喜剧作家的创作进行对比,而且往往语焉不详,缺乏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
三、第三个阶段(1970迄今)
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以及王尔德传记、评论的大量出版,对王尔德喜剧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料收集日渐完备。1970年,贝克森(Karl Beckson)编辑出版《奥斯卡·王尔德:批评遗产》(Oscar Wilde: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其中收录了王尔德生前及死后一段时间里散见于英国报刊的王尔德喜剧评论文章,为我们了解王尔德同时代人对他喜剧的反应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78年,米哈依尔的《王尔德评论注释书目》问世,书中收集了1892年至1975年间英、美、德、法、日几国有关王尔德喜剧研究的成果目录,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来源;1982年,泰德曼(William Tydeman)出版了《王尔德:喜剧》(Wilde:Comedies,The Macmillan Press LTD.),这是第一本专门辑录王尔德喜剧评论的著作,此著囊括了从1891年到1977年王尔德喜剧研究的重要成果,通过这些成果,展示了王尔德喜剧研究的发展脉络,为研究走向深入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第二,注重宏观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众多研究者不再拘泥于对喜剧某一方面的剖析,而是将它们置于19世纪英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予以考察,力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观照王尔德的喜剧,伯德(Alan Bird)的《王尔德的戏剧》即是一例。伯德着重从19世纪后期英国的政治经济角度审视王尔德的喜剧,得出了不同寻常的见解。他认为:《理想丈夫》的结尾“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金钱、野心和腐败的胜利”。[4] 15090年代,适逢《认真的重要》和《理想丈夫》上演百年、王尔德入狱100周年,英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王尔德的喜剧再次在伦敦各剧场受到追捧。[5] 与此相呼应,对王尔德喜剧的研究也形成高潮,新的成果纷纷问世。鲍威尔(Kerry Powell)的《王尔德与19世纪90年代的戏剧》(Oscar Wilde and the Theatre of the 1890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唐诺休(Joseph Donohue)的《王尔德及其戏剧思想》(Wilde and The Idea of a Theatre)[6] 328以及拉比(Peter Raby)的《王尔德的社会喜剧》(Wilde' s Comedies of Society)[6] 118-126等都是于90年代面世的对王尔德喜剧进行宏观研究的力作。更值得一提的是,拉比在《王尔德和欧洲戏剧》(Wilde and European Theatre)[7] 143-160一文中,以欧洲戏剧大师易卜生、契诃夫的创作为参照,肯定王尔德喜剧的价值与意义,指出以往英国批评家对王尔德喜剧评论的局限,为人们准确评价王尔德在英国和欧洲戏剧史上的地位开启了新的思路。
第三,人们热衷于从文学批评的武库寻求可资利用的新的利器,以揭示王尔德喜剧中尚未引人注意的深层意蕴。由于王尔德的爱尔兰身份及其同性恋癖好,使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等时新的研究方法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仅以同性恋批评为例:在前一阶段,只有个别研究者论及同性恋对王尔德喜剧创作心理的影响,对喜剧文本中的同性恋倾向则未曾涉及。而在这一时期,随着同性恋亚文化及同性恋批评的流行,同性恋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成为王尔德喜剧研究的热门话题。贝伦德(Flanagan P.Behrendt)的《王尔德的性爱和美学》(Oscar Wilde:Eros and Aesthetics,London: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1991.)就是研究王尔德喜剧中的花花公子和同性恋迹象的专著。对王尔德的喜剧代表作《认真的重要》,更有不少研究者阐释其同性恋倾向,并视之为表达同性恋者双重生活体验的剧作。[6] 328-337这些具有创见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此期王尔德喜剧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此外,运用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等方法研究王尔德喜剧的有影响的著作或论文还有: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现代批评解释》(Oscar Wilde' s " The Importance of Be ing Earnest"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Chelsea House,1988)、拉比(Peter Raby)的《〈认真的重要〉:读者指南》(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A Reader' s Companion,New York:Twayne,1995)、卡普兰(Joel Kaplan)的《舞台上的王尔德》(Wilde on the Stage)、[7]249-275克维(Richard Allen Cave)的《王尔德喜剧的影响》(Wilde' s Plays:Some Lines of Influence)、[7] 219-245费利曼(Joel Fineman)的《文学的意义:〈认真的重要〉》(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8] 108-118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现代色彩,富有浓厚时代气息的当代王尔德喜剧评论。这些评论既展现了西方王尔德喜剧研究与时俱进的趋势,也给我们启示:出现在世纪转折点上的王尔德喜剧,是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王尔德喜剧研究是一个具有广阔学术前景的课题。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五”规划2005年度课题(编号YZ11—1)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