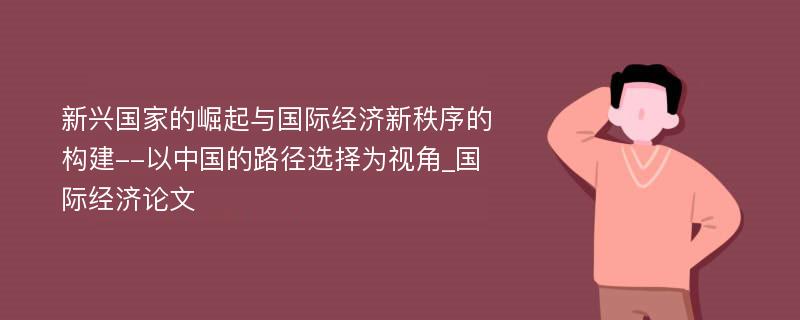
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新秩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中国学界对于国际经济秩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冷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陷入低潮,我国学界对国际经济秩序问题的研究亦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将如何对待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到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者也开始再度重视对该国际经济关系基本问题的研究。
二战之后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经济秩序立基的是所谓的“内嵌的自由主义”。①虽然这种自由主义承认各国政府以积极的角色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必要性,但其本体仍然是自由主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是“市场导向分配模式”的国际经济秩序。②例如,1947年缔结的《关贸总协定》就是一个以推行贸易自由化为基本宗旨的多边贸易法律体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开始盛极一时,在反映西方新自由主义观之“华盛顿共识”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最典型的例子是,相对于以往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协定》拓展了贸易自由化的范围,并大大强化了贸易自由化的纪律。
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始终存在着失灵的可能,失灵的主要情形之一是,过度的自由竞争容易造成贫富国家之间不公平的结果。为此,中国一贯倡导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③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国家异军突起,经济增长迅速,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④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构建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斗争态势的演进,⑤包括“特殊与差别待遇”传统路径的演变和“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新增路径的显现。而新辟这种路径,可能意味着正在推动继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一度潮落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再掀高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于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研究,立论基础实际上仍然沿用南北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没有变化,甚至越来越悬殊的笼统假定。无疑,忽视近年来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趋于缩小的事实,将无法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对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基本态势作出完整、准确的判断。
近年来,中国迅猛发展,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兴国家。因此,对于构建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态势的演进而言,中国又是所有新兴国家中最为突显的一个。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一般出现在世界大战之后或全球重大经济危机之后的节点上。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兴和增长的重心有进一步向新兴国家移转的趋势,这将成为新兴国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基点,同时也为中国的参与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显然,要促进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确当地把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斗争的基本态势是首要之举。
二、“特殊与差别待遇”传统路径的演变
如上所述,战后建立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2008年之后,虽然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膜拜自由放任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终结,各国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加强了政府干预,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难见有取代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以市场为导向的基本理念。
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首先遵循的是以实力决定竞争结果的逻辑,相应地,反映这种逻辑的用以构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直接规定以各国经济实力大小决定权责分配多寡的规则。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行的加权表决制就属此类。显然,这是一种法律上和事实上对发展中国家都不公平的规则。二是表面上规定对所有国家都实行相同待遇的规则,但因南北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实际上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实力享受同等的权利(或权力)和承担同等的义务(或责任)。例如,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为各国提供了同样的规则,但发达国家对该机制的实际利用率远高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在是否拥有大量的专家、丰富的信息以及充分的诉讼经验等决定利用争端解决机制能力大小的因素上,二者差距甚大。这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法律上平等、事实上不公平的规则。本文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上述两类规则统称为“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
无疑,这种“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的适用必然置贫弱的发展中国家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作为重构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起点,发展中国家一贯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主张制定区别对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对发展中国家作出有利的特殊权利义务安排的规则,以弥补其竞争实力不足的弱势,从而求得与发达国家间表面上不平等、实质上公平的结果。本文将此类规则称为“体现差别待遇之规则”。发展中国家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实际上立基的是“实质正义”。⑥尽管对实质正义的标准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保护弱者(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即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其公认的题中应有之义。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黄金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攻势凌厉,并颇有斩获,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包括:促成发达国家建立了以非互惠为主要特点之一的普惠制以及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了国际海底资源的“平行开发制”。
在这一历史时期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发展中国家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行动有所斩获是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经济基础的状况,即南北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极大失衡。仅以GDP为例,1960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GDP总量的比重为20:80,1980年曾一度上升到25.4:74.6,但1985年又退回到1960年的比值。⑦在经济实力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形下,穷国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既存国际经济秩序可谓“造反有理”——强烈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其正当性不容置疑,发达国家在道义上也没有足够的底气予以漠视,不作出应有的回应。
毋庸讳言,冷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曾一度潮落,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攻势趋于减弱。⑧例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后,遭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抵制,其理由是该公约规定的“平行开发制”妨碍了私人企业通过自由竞争来参加海底资源的开发。为了吸引这些发达国家加入该公约,发展中国家只得作出让步,于1994年达成了一个新的修正协议,更为强调国际海底资源开发的市场机制。⑨又如,在传统的《关贸总协定》框架内,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特殊与差别待遇”,采取的是一种“承担义务不对等”的模式,即发展中国家在立法上自始就无需承担与发达国家一样的义务,如实行普惠制以及允许发展中国家选择不参加有关复边协议,等等。然而到了《世贸组织协定》,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蜕变为“履行义务不对等”的模式,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只不过是设置过渡期之类的暂时优惠,最终仍需回归“正常的法律框架”。⑩
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攻势减弱的趋向,西方学界给出的主要原因是:在根本观念上,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战胜了“依附论”等发展中国家赖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想基础;在权力结构上,是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原来在美苏两大集团对抗中作为第三方可有的战略回旋空间。就此,我国学界多是简单地从“应然”的角度加以研究,提出正因如此故更有加强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显然,国内外学界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基础——南北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变化,尤其是从新兴国家崛起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攻势减弱的根源。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加快,总体上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近年来,全球出现了更为明显的财富“从北向南”转移的现象。据经合组织保守的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2000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GDP总量的比重达到了40:60,2010年上升至49:51,预计2030年将达到57:43。(11)近年来南北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中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态势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践行“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愿必然趋于下降,并开始主张按“发达”的程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例如,在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主张,“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不应与贫穷的“欠发达国家”享受同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而其中最为发达的那些新兴国家已到了毕业的时候,应当终结对其实行的“特殊与差别待遇”。(12)
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发达国家眼里,新兴国家已是“中产阶级”,不再是需要救济的“穷人”,它们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诉求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正当性。在发达国家经济实力趋于削弱,新兴国家经济持续上升的当下,对新兴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诉求,发达国家不但“无心”满足,可能还会更加认为自己“无力”为之。由此,新兴国家要推进符合实质正义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将面临更为艰难的局面。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要求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日渐艰难。例如,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就没有获得完全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实际得到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被大幅削减。(13)可见,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认为,中国虽然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因此,虽不至于要求中国完全放弃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但已主张应对中国的受惠加以限制。
“入世”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发展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新兴国家,且GDP总量跻身世界第二。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向发达国家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必然成为整个发展中国家阵营中最为艰难的一个。对当下中国而言,在重构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要求遭到了发达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制。发达国家提出现在已到了剥夺中国享受优惠待遇的资格,并进一步提高中国应负国际责任的时候了。由此可断言,中国在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传统路径上,已经进入了守势阶段。这种攻守态势的转变,皆因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否定。
针对中国主张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发达国家予以否定的理由是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一个超级发达的经济体,甚至是可列入几乎可与美国平起平坐、共治世界的“两国集团”(G2)。甚至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14)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认定中国事实上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巨大受益者。例如,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学者伊肯伯里认为,“中国已经发现通过在该开放性市场体制内的运作可以取得巨大的收益”。(15)按照这种说法,既然中国是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受益巨大的一个发达经济体,那么,如果中国继续主张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就将成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最大的“搭便车者”。(16)在发达国家看来,中国已不是一个“穷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也已不是一个“中产阶级”(一般的新兴国家),而是一个“富人”(发达的强国),一个“中产阶级”就不该再“领救济”(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遑论一个财富正在不断递增的“富人”。
对于发达国家发动的攻势,中国的做法是坚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虽然中国在GDP总量上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尚有1.5亿人口需要脱贫。显然,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只考虑总量而不看人均是片面的。假如以国家总量上的指标认定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并要求其承担超高的国际经济责任,那么,就会限制仍然处于不富裕甚至贫穷状态的多数中国人的发展权;只有以个体之人均计,多数中国人可享有的更大发展空间才不至于被压缩。对于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发达国家历来罔顾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标举个人的普世权利。现今,对于经济权利,发达国家却颠倒其惯有立场,以国家总量上的富裕为由限制个人的发展权,显然是在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之间对中国搞双重标准。
当然,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水平并非确定而不能改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多享权利”和“少尽义务”的幅度可以调低,但其底线是必须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称,不能超越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而任意剥夺或加码,这是中国在构建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之攻防战中,哪怕作为守势的一方也必须坚守的防线。
三、“平等与无差别待遇”路径的显现
进入新世纪,发展中国家集团中的新兴国家发挥自然资源丰富、年轻劳动力人口增长、国内政治经济稳定、积极引进外资以及消费人群扩大等优势,崛起速度相当惊人。统计表明,21世纪头十年,新兴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17.71%上升到2009年的24 22%。(17)据世界银行统计,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从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约45%;直接投资占全球投资总额的1/3;所持金融资产也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的2/3,主权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部分。(18)总之,当前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是,“新兴经济体在迅速崛起……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向着渐趋均衡的方向发展”。(19)
如前所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立基的首先是“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其强调以经济实力大小决定国家待遇的高低。以往,南北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悬殊,发展中国家适用这样的规则显然于己不利。然而,新兴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促成南北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北降南升”的变化。由此便产生了在“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适用上,发达国家是否平等与无差别地对待新兴国家,即国际经济领域的“形式正义”是否得到实现的问题。按照形式正义的要求,既定的规则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国家,不得厚此薄彼。
对新兴国家平等与无差别地适用此等“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的结果应当是,其从中获得的利益本应随着它们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而增加,即新兴国家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可获得“增量收益”。然而事实上,发达国家往往只顾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不愿让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做大做强,并用“主动出击”或“消极抗拒”两种手法——或实施限制,阻挠新兴国家取得更大的权益;或株守现状,拒绝对新兴国家实行权益再分配。此外,发达国家也可能会超越新兴国家的发展水平,通过拔高国际责任标准,阻碍它们的迅猛崛起。鉴于此,新兴国家在有关“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的适用上,向发达国家发起了要求获得“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攻势,且要求平等对待的呼声不断提高。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实际上大多仍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锁定于获得于已有利之“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传统路径,尚未对焦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日趋缩小及其对构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从而未能从另—角度考虑新兴国家在建立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过程中开辟的这一新路径。(2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除GDP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之外,2009~2011年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量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进口总量为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引进国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经济地位跃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主张“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下的“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方面向发达国家发起的攻势,当然可以达到所有新兴国家中的最大程度:即发达国家面临着依这些“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应给予中国与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相称之权益的强大压力。
(一)对于前述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表面上规定对所有国家都实行相同待遇的那些“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在要求得到“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路径选择上,中国应坚决反对发达国家损人利己,实行贸易、投资及货币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对中国适用这些规则本可获得的收益递增进行压制的倾向。
在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中,那些规定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规则多属于对各国均同样对待的规则,体现了全球市场在准入上的开放性和竞争上的平等性,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而且这些规定自由竞争的“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整体上将呈现出对中国越来越有利的态势。据统计,“入世”十周年,尽管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21.6%,总量增加将近5倍。此外,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扩大近145%,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高达40%以上。(21)中国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对外经济活动的迅猛发展,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这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国际经济体制运作的必然逻辑。既然如此,发达国家本该通过自我调适,化解这种外部竞争压力。然而事实却不然,发达国家出台了种种贸易、投资和货币政策上的保护主义措施,而中国成为了这些保护主义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和首要目标国。(22)
发达国家历来标榜自己尊奉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但这一切未必都像它们所说的那样真实,即在自己强大时,它们必然主张可自由地从中获益;而当别人也变得越来越强大,获益能力越来越强,并与自己发生利益分配冲突时,它们可能会罔顾平等竞争之市场规则,设置种种障碍,专门限制别人获益的自由。一些西方学者直言不讳,“虽然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设计和创造的,但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才是当之无愧的最大受益者。如果西方在某个时候断定中国已成为主要受益者,同时对西方越来越不利,那么西方很可能会变得更加趋向于保护主义,同时当前的全球体系也会被逐步削弱。”(23)
遇此情势,中国应当起而攻之,要求发达国家恪守基本的“平等与无差别待遇原则”,坚决反对贸易、投资和货币政策上的保护主义,(24)将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有关自由竞争的规则平等地、不加限制地适用于中国,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就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曾做过这样的评论,“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上,中国的作为令人有一个‘错位’的感觉。自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以来,从来就是发达国家推进自由贸易的。但现在不一样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国家的‘自私性’暴露无遗,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也自然成为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面对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25)其实,中国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和货币政策上的保护主义,担当起维护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大任,绝非一种错位的作为,而是向发达国家主张起码的“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之举。
(二)针对前述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国家经济秩序下直接规定以各国经济实力大小决定权责分配多寡的那些“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在要求得到“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路径选择上,中国应坚决反对发达国家不按这些规则行事,不以中国已有的经济实力为尺度,对中国实行少给权益、多加责任的倾向。
1.在权益的分配上,中国应坚决反对发达国家为维护既得权益,拒不平等与无差别地适用有关直接规定以各国经济实力大小决定权责分配多寡的规则,调高对中国的权益再分配比例之做法。
其一为发达国家为维护“既得利益”,拒绝平等与无差别地适用此类“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的情形。就金融领域而言,在现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美元处于“一统天下”的地位。肇始于美国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充分暴露了美元霸权体制下“利益美国独享,风险全球共担”的弊端。二战之后,美国的GDP曾一度占据世界一半。其时,作为历史的产物,如果说确立美元“一币独大”的地位尚有一定合法性的话,那么,时至今日,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已远非昔比,美元继续维持垄断地位的正当性不可能不遭受质疑。
按照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以各国经济实力大小决定权益分配多寡的规则,无论采取哪一种改革方案,有关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都应与其经济实力相对称。根据此类“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新兴国家凭借自身迅速成长的经济实力,它们的货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理应得到提高,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促进将人民币纳入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之中。(26)显然,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应属于平等适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并非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恩赐。
其二为发达国家为维护“既得权力”,拒绝平等与无差别地适用此类“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的情形。就全球经济治理的决策权分配而言,发达国家担心大权旁落,通常不愿给予新兴国家更大的参与权。(27)但按照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直接规定以各国经济实力大小决定权益分配多寡的规则(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加权投票制),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其参与世界经济决策的话语权应得到相应的提高;反之,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其参与世界经济决策的话语权则应相应地减少。
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国家快速兴起,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没有新兴国家参与治理,单靠发达国家自身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战胜这场危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发达国家不得不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包容性,重新分配全球经济治理的决策权,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中国等新兴国家。例如,2009年9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决定,包括11个重要新兴国家的“二十国集团”取代基本上为“富国俱乐部”的“八国集团”(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又如,2010年4月和11月,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分别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在这两大机构的投票权数提高最大,从原来的位列第六,一举超越德国、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然而,这些都是新兴国家要求平等与无差别地适用此类“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所得到的与自己经济实力相称的起码权力。(28)对于中国而言,也只是将参与有关国际公共机构决策的权力提升到与其国力相匹配的水平。(29)
今后,在构建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要求相应地增加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以实现基本的“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攻势将进一步加强。(30)
2.在责任的承担上,中国应坚决反对发达国家为抑制中国迅猛发展,超越此类直接规定以各国经济实力大小决定权责分配多寡的规则,拔高中国应负的国际责任的企图。
当然,所获权益的增加必然带来所担责任的加重。例如,中国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得到提高的同时,向这两大国际货币金融机构的注资也将相应地增加。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获得的只是与自己经济实力提升相称的权益,相应的,中国所需承担的责任也不应超越中国的现有经济实力。需要警惕的是,现在发达国家企图以中国得到这种有限的权益提升为由,要求中国背负过高的国际责任,甚至将中国推上“全球领导者”的岗位,承担连发达国家都无力承担的责任。“中国无意也没有精力谋求成为全球领导者”,(31)任何违背中国意愿,试图“忽悠”甚至强迫中国成为全球领导者,让中国超高地,而不是适度地承担国际责任的做法,显然都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违反了“平等与无差别待遇原则”。例如,美国前贸易代表施瓦布认为,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已启动十年,但现在仍然前景黯淡,根本原因在于该回合谈判继续沿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两分法。中国等新兴大国混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犹如“大象躲在老鼠背后”,以只能承担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义务为由,抵制其他国家提出的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要求。(32)事实上,近些年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和欧盟一直以中国等新兴国家贸易地位上升为由,迫使这些国家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作出超越其发展水平的过度让步,遭到了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一致拒绝。
在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一定要避免陷入因自身经济实力上升,原有的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路径被堵塞,当下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路径未被有效打开,而承担的国际责任却被发达国家以“中国责任论”为由不断推高的困境,从而陷入最不利的境地。
四、传统路径与新增路径的此消彼长:中国整体斗争态势的廓清
如上所述,传统路径上的坚守和新增路径上的出击,代表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基本发展态势。在传统的斗争路径下,发展中国家诉求“特殊与无差别待遇”,旨在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于己不利的“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然而,就“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路径选择而言,中国等新兴国家只是要求这些内容本身并不公平的“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能够平等地适用于自己,那么,以下三大疑问就需要加以澄清。
疑问之一:这种斗争新路径的开辟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出现了倒退呢?
事实恰恰相反。新兴国家开辟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斗争新路径,并不会排斥、消减乃至取代发展中国家延续传统路径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斗争,反而可对传统路径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首先从新旧两种路径斗争开展的层面分析,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和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分别指向的是规则的内容和规则的适用两个不同的层面。在建立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路径是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旨在以内容上于己有利的“体现区别待遇之规则”取代内容上于己不利的“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但这是一个长远的斗争目标,在其达成之前,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既存的多数规则仍然是那些“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对于此等“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新兴国家可以通过开辟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新增路径,先消除这些规则的不平等适用,从中获取相应的“先期利益”或“中期收益”;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持续平等地适用“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新兴国家还可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获得“增量收益”。例如,对于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权分配,新兴国家当然可主张“特殊与差别待遇”,要求打破现行反映市场逻辑的加权表决制之窠臼,不以经济实力大小论,给予发展中国家超比例的投票权。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2010年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决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虽然只是改善了加权表决制本身对新兴国家平等适用的状况,但新兴国家毕竟在获得公正的机会,参与这两个重要国际经济组织治理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即取得了“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下的“中期收益”。今后,随着新兴国家的进一步崛起,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进行新的投票权调整中,还应按照新兴国家经济实力上升的幅度,不断地调高它们的份额,这正是新兴国家依“平等与无差别待遇原则”获得“增量收益”的过程。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即使现在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传统斗争路径受到了发达国家的阻挠,仅凭借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而开辟的新增路径,也并不表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显现出了对新兴国家越来越不利的趋向。由于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增强,从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获益程度已大为提高,即便在构建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收益要少于以往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收益,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对新兴国家仍然呈现出越来越有利的态势。简言之,从以往的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到现在的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新兴国家可能只是边际收益收窄,并不代表着其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整体获益减少。例如,2009~2011年,中国的出口额已达世界第一,而1978年中国全年出口额只相当于2008年一天的出口额。(33)因此,1978年,即使中国诉求得到再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当时从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整体获益(属于“低开高涨”的情形),肯定不及2008年中国立基于“平等与无差别待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从维持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所获的整体利益(属于“高开低涨”的情形)多。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种认为冷战之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新兴国家而言趋于恶化的观点,难以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主张将中国等新兴国家立基于“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斗争分列出来,视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新增路径,还因为这样做可以赋予新兴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以更大的道义性。众所周知,在“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下,新兴国家要求得到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国家”应该得到的基本待遇,是反对发达国家在适用内容本身就不公平的规则时还要大打折扣的做法,而不是以一个“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要求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下发达国家给予的任何“接济”。这种防止因“法律面前不平等”致使自己起码权益遭到侵蚀的诉求,其正当性无可辩驳。
例如,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的一员,1988年成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采取的是集团投票制。因为当时经济实力弱小,在投票权的分配上,发展中国家集团获得的股份票数量虽然少于发达国家集团(比数约为40%∶60%),但是发展中国家集团所得的成员票(基本票)数量却多于发达国家集团,弥补了在股份票上的分配劣势,最终实现了南北两大集团的均分投票权,这一分配比例超出了当时南北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另者,2010年,在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内,新兴国家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了一部分投票权的让渡,使发展中国家在这两大机构中的投票权总数分别达到47.19%和45.5%。虽然发展中国家1988年和2010年在上述国际金融机构中都获得了更大的投票权,但两次行为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在1988年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成立时,发达国家还可以说在投票权制度上践行了“特殊与差别待遇”向发展中国家作了“让步”的话,那么,在当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下,2010年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向新兴国家转移投票权,完全是新兴国家立基于“平等与无差别待遇”应得的一种起码的权利,其中将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调高到第三位,也只是基本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际地位。
疑问之二:中国等新兴国家在这种路径选择下的斗争难度是否就一定小于以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路径下的斗争呢?
就以往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斗争路径与当下新兴国家路径选择相比较而言,考虑到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得出的结论却未必如此。有时,新兴国家在新增路径上取得进展比之以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路径上的斗争要更加艰难,它们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以求实现“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以往发展中国家以除旧布新为目的,开展了激烈的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种意在从体系外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变革的斗争具有极大的威胁性。然而,冷战之后,在发达国家看来,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强度趋于下降,已成为“体系内的改革者”。对于这些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国家,施舍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让它们多享一些权利或少尽一些义务,从根本上说,不会对发达国家构成实质性威胁。但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劫难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其日益繁荣的时代似乎已经逝去;而它们面对的新兴国家却活力不减,经济实力上升势头强劲。在发达国家对自身的衰弱深怀危机感的当下,任何对其既得利益发起的挑战,哪怕只是新兴国家主张的“平等与无差别待遇”,都可能使发达国家倍加敏感,从而在整体上增加新兴国家当前和今后开展这方面斗争的难度。(34)
其次,从争取的待遇性质来看,对于以往发展中国家要求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当时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即使予以满足,许多情形下也只不过是牺牲自己的一些具体利益,给予发展中国家相应的好处而已,如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实行普惠制等。然而,现在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所争取的不再是发达国家给予的“小恩小惠”,它们主张取得“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与发达国家争夺的是一些根本性的权益(如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本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决策权力等)。由此可能会动摇发达国家控制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根基,容易招致它们的强烈抵制;因此,新兴国家所进行的斗争即使只是要求获得“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也将困难重重。
最后,从斗争的深度来看,以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非常有限,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分获的权益本身很小,即使加上额外所得的“特殊与有差别待遇”,也不会危及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权,因而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这种诉求的顾忌较小。然而,近年来新兴国家实力大增,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当大的分量,所获权益也已今非昔比,这些新兴国家如要在此基础上依“平等与无差别待遇原则”继续深化构建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将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权益分配的比较优势岌岌可危。因此,发达国家对丧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的忧惧会越来越强,新兴国家斗争的边际难度也将随之不断加大。例如,目前,在如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方案中,可以增加新兴大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但任何新兴国家如要颠覆美元本位制,实现“去美元化”,撼动美国金融帝国的基石,则很难在短期内实现。
改革开放初期,发达国家最多视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追求“特殊与差别待遇”,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想“捞好处”的“搭便车者”而已。(35)然而,中国作为一个迅猛发展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只是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但改革方向直指发达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根本权益。这样做极易引发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内想“夺实权”、试图动摇发达国家优势地位的一个最有可能的“改朝换代”者。这就是说,当下中国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决不会比改革开放初期时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更加容易。
疑问之三:中国等新兴国家开辟这种斗争新路径会不会造成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的分裂呢?
的确,现今发达国家实际上试图采取三分法,把现有国家划分为“富人”(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新兴国家)以及“穷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三类,通过将其中相对比较发达的新兴国家与其他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达到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目的。例如,在2008年7月进行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就农产品补贴问题,美国对一些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做出了一些妥协,但是拒绝就印度、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正当关切做出应有的回应,从而导致谈判无果而终。其目的就是要让那些认为可从美国的让步中获益的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谈判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印度和中国。(36)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虽然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有渐趋平衡的趋势,但南北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差距依然存在。(37)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与发达国家单打独斗,都难有胜算。这就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传统的“南北国家”(穷国对富国,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之两分法,加强南南合作,整合力量,协同向北方国家发力。毋庸讳言,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其他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在防止丧失传统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和争取获得现行的“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两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新兴国家首先应相互协调,共同合作,在构建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集体发声。例如,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及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的形成及相互间合作的加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38)
另外,还应看到发展水平的差异及相互间合作的加强,也决定了新兴国家与其他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构建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存在着互补的利益: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实力甚至处于下降的状况。因此,对于这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更加需要也更有理由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但它们尚不具备经济实力通过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而获益;相反,中国等新兴国家因为“变富”而更难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但已积聚相当的经济实力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下的“增量收益”。可见,在追求传统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和现行的“平等与无差别待遇”过程中,两类发展中国家可以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共同受益。
总之,中国等新兴国家应支持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此举不但包括支持它们向发达国家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新兴国家自己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它们优惠待遇。例如,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免除债务以及减免关税等,就属此列。假如新兴国家不愿对其他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这部分责任,将会陷入被发达国家指责和其他贫穷发展中国家抱怨的双重困境。另一方面,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也应策应中国等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而中国等新兴国家一旦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治理权力,就能更加有力地支持其他贫穷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发展水平尚有差异的两类发展中国家在互惠互助的关系基础之上,只要相互策应,共同对外,就能结成一个牢固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合力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
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实际上只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界定为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诉求,而没有将新兴国家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行动包括在内,所以只强调新兴国家与其他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就此存在的共同利益,对于两类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利益则未予关注。实际上,这样的合作利益恰恰是加强南南合作、维系南方国家阵营内部团结的一个新的重要基础。
南北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状况的变动,决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态势的跌宕起伏。
以市场为导向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反映的是市场的逻辑,即按各国经济实力大小决定权益分配的多寡。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南北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实力非常低下,假如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地适用此等市场逻辑,则所获甚少;而且当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在“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下也并无多少“增量收益”可得,因此它们必然强烈主张以“权威分配导向体制”全面取代“市场分配导向体制”,(39)即废除“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全面代之以“体现差别待遇之规则”,从而掀起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第一次高潮。
在发展中国家中,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不断崛起,它们的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且其经济仍然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好比已从原来的小股东变成了越来越大的大股东,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可给它们带来比以往更大的收益,并且是越来越大的收益。对此,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战后西方国家创设的是“无知之幕”之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现代的国际秩序其实不是美国的或欧洲的,只不过因为历史的原因开始成为这样。它是一种更广泛的东西”,为中国等新兴国家日后的崛起提供了制度条件。(40)
因此,当下中国等新兴国家不再是一蹴而就地彻底革除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对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存在的公正性缺失的问题不断改革。从规则的构成角度来看,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由充当主体的“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和作为例外的“体现特殊待遇之规则”整合而成。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包括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继续推动“体现差别待遇之规则”的制定进程,即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诉求增加此类于已有利的规则,并加大这些规则给出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力度;简言之,就是要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构造中,通过消减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的成分,增强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体现差别待遇之规则”的成分,促使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的利益分配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崛起中的中国等新兴国家应更加着力改变现行“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的不平等适用状况,即开辟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新路径。对于构建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解,不但应继续涵盖传统路径之制定更多、更大程度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体现差别待遇之规则”,而且应包括反对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对中国等新兴国家不平等适用的状况。这就是说,新兴国家不应完全拘泥于对现行秩序下“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的改造,还要关注这些规则在适用层面的不公正问题。
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持续发展,新辟路径下“增量收益”和传统路径下“增量损失”的并发,也决定了建立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基本态势。中国等新兴国家实力的上升,意味着在“反映市场逻辑之规则”下的收益也应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对中国等新兴国家追求“增量收益”的压制,必然带来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建立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这条新增路径上发起强烈的攻势;反之,中国等新兴国家实力的上升,也意味着在“体现特殊待遇之规则”下的损失也在逐步增大,出现“增量损失”的情形;也就是说,伴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程度的提升,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地位和力度从逻辑上说也将趋于下降。这将在客观上抑制其他新兴国家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传统路径上发动的攻势,而作为经济最发达的新兴国家的中国,在这一传统路径上的斗争则可能陷入守势。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中国等新兴国家自此将失去主张“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资格,因为它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且发达国家应给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从来没有不折不扣地到位过,中国等新兴国家现仍然可以要求发达国家弥补这方面既存的实质正义之“赤字”。
另需强调的是,在现今建立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因许多贫穷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态并未得到改变,它们对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之传统路径的侧重和固守,与中国等新兴国家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之新增路径的开辟,从不同战线向发达国家发起攻势,结成的是一个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合作利益的共同体。
日后,中国实现“三步走”战略,无论是在总量意义上还是在人均意义上,均成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而且中国获得与自己发达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权益,不再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同时“平等与无差别待遇”也得到应有的保证。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构建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国是否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呢?届时,从利益的维度考察,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将大为有利。然而在国际法律过程中,各国追求的不仅仅是利益,而是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平衡。(41)因此,即使将来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国,也不会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会从公正的理念出发,秉持特有的“利以义生”、“见利思义”等传统价值观,继续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哪怕这样做会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中国仍会“舍利取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使它们的发展获得更为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
①“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约翰·鲁杰对战后这一阶段国际经济秩序构建基本理念的概括。(详见J.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79—415)之后这一概念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内嵌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被引用最为频繁的术语之一。(参见孙伊然:《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变迁:重建内嵌的自由主义?》,《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22页)
②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③2011年6月17日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重要演讲,重申中国致力于“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立场。
④2010年9月14日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变革”。
⑤2012年3月6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外交部长杨洁篪指出:“当前世界一大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这对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⑥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实质正义”和下文述及的“形式正义”之界定,参见H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3rd E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76;法学理论中有关这一对正义之分类,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5页。
⑦何方:《南北差距的新变化》(上),《世界知识》1994年第8期。
⑧B .Gosovic:《二十一世纪联合国将走向何方:改变抑或延续国际旧秩序》及徐崇利:《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潮落与中国的立场》,均参见《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年第2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20—25、34—46页。
⑨周勇:《国际海底“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困境与原因》,《国际论坛》2012年第1期。
⑩杰弗里·L.丹诺夫:《WTO贸易法公平吗》,《国际经济法学刊》2004年第1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25页。
(11)OECD,"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0:Shifting Wealth," Summary in English,2010,p.2.
(12)林灵:《试析多哈回合“特殊与差别待遇”谈判及中国相关立场》,《武大国际法评论》2007年第2期。
(13)《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8、9段。
(14)例如,美国皮尤中心调查表明:在14个被调查的国家中,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领先大国”的人数从2008年的22%上升至2012年的42%。(参见Pew Research Center,“Global Opinion of Obama Slips,International Policies Faulted,”June 13,2012,p.6)
(15)G.J.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87,January/February,2008,p.29.
(16)例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就声称:“中国是一个惯于搭便车者”,“这是西方当下与中国打交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引自Minxin Pei,“China Puts the World Off Balance,”Newsweek,vol.155,no.5,Feb.1,2010,p.7)2011年3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了其就“中国崛起”问题在全球所进行的民调结果,其表明,与2005年的调查数据相比,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持负面看法的发达国家受访者比例有比较大幅度的增加,该项比例普遍超过50%。这些受访者持负面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更多的是国际经济体制的“搭便车者”,而不是“利益攸关者”。(详见纪双城、徐盼:《英媒就“中国崛起”搞全球民调》,《环球时报》2011年3月29日,第3版)
(17)林跃勤、周文主编:《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13页。
(18)刘洪钟、杨攻研:《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经济学家》2012年第1期。
(19)在2011年3月7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答记者问时,两次强调了这样的观点。在2012年3月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杨洁篪再次强调“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将增强,国际力量的对比将向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
(20)最近一篇代表性论文见李滨、陆健健:《论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之正当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2期。
(21)参见2011年12月11日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22)在2012年3月23日举行的“2012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上,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指出,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且贸易摩擦形式不断地翻新,涉及的产业不断扩大,发起的国别也不断增加。
(23)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弱》,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56—157页。
(24)2011年4月14日胡锦涛主席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时发表了题为《展望未来共享繁荣》的讲话,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实现发展回合目标。”
(25)引自郑永年:《2009,中国作为新型大国开始改变世界》,《参考消息》2009年12月31日,第12版。
(26)例如,2011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访美期间中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中美双方认同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应仅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鉴此,美方支持中方逐步推动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努力。”
(27)杨泽伟主编:《联合国改革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28)例如,2011年4月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结束时发表的《三亚宣言》第15条就指出:“我们呼吁各方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峰会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目标,重申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应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29)S .Devi,"China’s Votes Grow to Match Its Power," 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7,2011,p.3.
(30)在2011年3月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继续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三个积极趋向之一便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趋向深入,提高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有关机构当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31)2011年10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是言。
(32)S.C.Schwab,"After Doha:Why the Negotiations Are Doomed and What We Should Do about It," Foreign Affairs,vol.90,May/June,2011,pp.107 — 109.
(33)法理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34)在2011年4月14日发表的《三亚宣言》中,“金砖国家”实际上只是表达了依基本的“平等与无差别待遇原则”,要求在全球治理结构中获得应有权力的呼声,即被发达国家视为“联合出手发出更大的声音,并颠覆世界传统的权力委员会”的威胁。(参见K.B.Richburg,“China,Other Developing BRICS Nations Seek Change in Global Economic Order,” Washington Post,April 14,2011)
(35)参见杰里米·T.帕蒂尔:《开放国门的铰链与门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参数》,陈志敏、崔大伟主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全球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33—261页。
(36)参见约翰·W.米勒:《中国称其有权设置高关税》,http://chinese.wsj.com/big5/20080729/bch133430.asp?source=whatnewsl,2008年7月29日。
(37)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指出:“有人说世界权力重心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看现在还谈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占据着优势。如果说世界权力重心有变化,我认为权力分配开始向相对公平、均衡的方向扩展,这对世界是好事。”(引自戴秉国:《中英两国合作是我们的唯一选择》,《环球时报》2011年9月30日,第14版)
(38)林跃勤、周文主编:《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发展报告:合作与崛起(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3、149—165、282—292页。
(39)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第1—29页。
(40)G.J.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vol.90,May/June,2011,p.61.
(41)对于国际法律过程之利益和价值两种维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参见K.W.Abbott and D.Snidal,"Value and Interests:International Legaliz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31,no.S1,2002,pp.141—178。
标签:国际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经济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