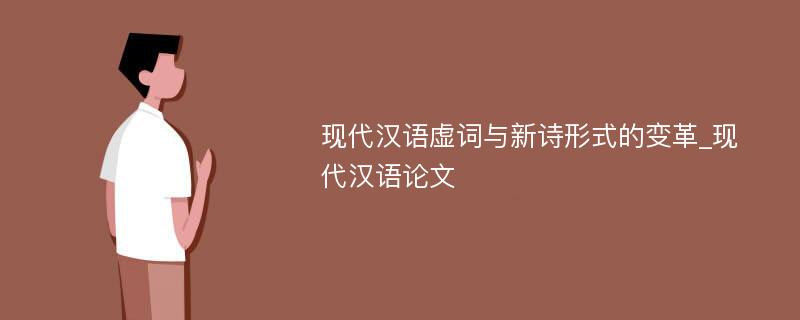
现代汉语虚词与新诗形式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词论文,新诗论文,现代汉语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将中国新诗与语言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成为一个新动向,但从现代汉语虚词的角度切入,却并不多见。其实,现代汉语虚词在中国新诗中大量运用,并直接影响了其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新诗真正从传统诗歌中突围而出,实现现代转型,现代汉语虚词功不可没。目前,对于现代汉语虚词与诗包括与新诗的关系,学界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或注重中国古典诗歌的虚词运用,或就某一诗人展开,相关探讨往往较为简略和随意,没有对现代汉语虚词和中国新诗的复杂关系及其转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讨,这为本研究留下了创新的空间。 一、现代汉语虚词入诗的历史语境 清末民初的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盛行,成为五四新文学产生的时代土壤,较大程度地影响了汉语诗歌形态的转变,给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提供了历史语境。1907年6月,在巴黎创刊的《新世纪》周刊第一期发表的《新世纪之革命》指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膨胀,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也有学者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科学思潮概括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①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基本改变了中体西用的观念,面向西方的欧化观念与思维形成了对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成为非常流行的新名词。有学者统计,“科学”一词在《新青年》里出现了1913次,《新潮》里出现了1245次,《每周评论》里出现117次,《少年中国》里出现2273次。②胡适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③新旧文人、知识分子不得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汉语文学包括汉语诗歌重新作出思考与选择。现代汉语白话书面语系统的规范化,就是在适应欧化语法体系的价值认同与知识的科学性认同基础上开始建构的。传统诗歌抒情写意的诗歌范式开始受到科学主义尊崇的理性思维范式的挑战,讲究严密逻辑性的欧化语法体系开始影响汉语书面语言系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汉语诗歌革新运动中提出的“我手写我口”、“言文一致”、“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等主张,是与科学求真的理性价值认同趋于一致的。梁启超在概括清代学术思想时认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④受科学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注重客观写实、率性求真、哲理感悟的诗歌表达方式影响了汉语诗歌观念、思维与形式的现代转换。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需要与之相对应的诗歌外在形式,或者说,外在诗歌形式的变化与选择体现的是诗歌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转换。 比如进化论之于胡适。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谈到:“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⑤为了使现代汉语诗歌表意明白、描述具体,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选择了对西方语言词汇、语法逻辑的直接借鉴。其中,包括对大量虚词的接受与借用。胡适认为,白话文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⑥他在词语的采用、句式的组合、自然的音节建构方面践行“言文合一”的诗歌理论,与传统诗歌重视实词搭配、遵守诗体格律表现方式明显不同。如《老鸦》、《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一颗遭劫的星》等,都使用了大量现代汉语虚词以尝试诗歌形式的变革。在对西方语言的借鉴中,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的大量运用,较大程度地破坏了古代汉语诗歌以单音节为主的结构表述功能,导致了白话诗歌文体趋向散文化自由体形式的选择。⑦ 又比如泛神论之于郭沫若。他的文学思想与世界观都是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物,泛神论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表达方式。闻一多便认为郭沫若的诗“富于科学底成分”,“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⑧郭沫若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是与泛神论融为一体的,他将抒情主体“我”与自然同化,赋予自我主宰一切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毁灭旧宇宙、创造新天地。这与诗人在现代科学观念影响下建立的新的世界本体观、时空观连在一起。《女神》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像《凤凰涅槃》、《天狗》、《晨安》、《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等,就有大量的现代汉语虚词,现代汉语虚词中的感叹词、语气词、助词、介词、连词等的大量使用,几乎构成“女神体”诗歌一个突出的外在标志。郭沫若认为:“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⑨郭沫若《女神》中大量外来词语的采用(包括直接使用科学词汇)、大量虚词的运用,体现的就是现代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都是科学思想与诗思打成一片的产物。 “五四”前后新诗的说理和写实之风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直接相关。诗歌对外来语汇的接受又最为敏锐与快速。汉语诗歌外在形式的变化,包括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正是诗歌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适应性选择。除了虚词的大量采用,诗行排列、分行、押韵的变化、标点符号的运用与现代诗歌意象的类型扩展等,都受到了科学思潮的影响。古代汉语诗歌格律化的形式规范,建立在实词对称、单音节韵律的平仄对应、句式整齐的基础上。汉语虚词偶尔入诗,也大多只是起到表达情感的辅助作用,不影响诗歌语义的表达,例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⑩《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雎》),“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伐檀》);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闻一多指出:“中国的文字尤其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句子连个形容词、动词都没有了。”(11)语言学家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指出:“汉人平常说话不喜欢用太多没有基本意义的虚词,它只是把事情或意思排列起来,让人去了解这两个事情或两个意思之间所生的关系如何。”(12)虚词的大量省略,使古代汉语诗歌语法显得灵活而松动,诗歌语言和句式也呈现出精练、简短的特征。因此,古代汉语诗歌往往不铺陈细节,而是剪除旁枝杂叶,省略语法的联系,直接指向事物中心。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是对英语、日语等诗歌语言词汇与语法体系的自觉借鉴。汉语与英语属于不同语系,汉语属于孤立语系,英语属于曲折语系。曲折语系更强调语言的语法逻辑关系,语言的表达往往突出和讲究事理逻辑、周严完整,时态清楚、字音一致等。孤立语系突出语言的直观,表意具有感性和模糊化的色彩。(13)日语是一种粘着语,需要助词与语尾的变化。(14)汉语的时态特征无英语那样的明显标志,这也成为现代汉语虚词中语气助词较多入诗的一个原因。特别是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基本与读音不一致,这就成为现代诗歌音节需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特点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语言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某些本体属性。 中国传统的文字属性与语言文化特质,遭遇了外来语言与文化的挑战,中国诗歌要顺应时代潮流,必须打破传统的诗歌语言与形式格局,建立一种多元开放的诗歌语言与审美文化系统。可以说,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大量加入现代汉语虚词,就是在科学思潮冲击、思想文化演进与文学审美变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与此相对应,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使用带来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特别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形式、诗思、审美的显著变化。 二、现代汉语虚词入诗引发新诗语言变化 语言是表意的工具,是思想的外壳,语言的变革直接体现了思想的更新。F.W.贝特森曾言:“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15)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语言大变革,首要地体现为现代白话代替古代文言的大趋势,其实质反映的是语言之雅与俗的新旧观念冲突。白话口语能否入诗,白话语言能否成为文学正宗,是新旧文学观念的分野。现代汉语虚词,像“的”、“地”、“得”、“了”、“着”和“啊”、“呢”、“吗”、“吧”、“哟”等口语词入诗,是带着平民主义与大众文学观念挤进贵族化典雅文学殿堂的。例如,当年胡适被守旧派诟病的第一首白话诗《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又如《山上》:“‘努力!努力!/努力望上跑!’//我头也不回,/汗也不揩,/拼命的爬上山去。/‘半山了,努力!/努力望上跑!’”口语化的语气词、助词、介词的入诗,体现的是大众化的平民意识,它们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理想与审美趣味,破坏了古典诗歌贵族化的审美雅兴与格律规范,也破除了诗歌与广大民众的语言障碍与观念隔阂。 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基本包括三类:一是由部分文言虚词转化而来的白话虚词入诗。汉语在语言变革的过程中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在一些文言虚词被淘汰的情况下,部分虚词被承继下来,直接适用于现代汉语的表述。如“而”、“则”、“与”使用范围扩大,这些文言虚词已转化为现代汉语虚词。二是现代口语中的虚词入诗,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语言入诗,体现的是“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言文合一”的新诗观念。生活语言入诗增添了新诗的原生态气息,符合平民化、日常化的审美趣味,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文言虚词如“之”、“乎”、“者”、“也”被“吧”、“啊”、“呢”、“哦”等现代口语化的一类虚词所代替,表现出更加丰富的情感和语气。叶维廉指出:“一如文言,白话同样也是没有时态变化的,但有许多指示时间的文字已经闯进诗作里。例如‘曾’、‘已经’、‘过’等是指示过去,‘将’指示未来,‘着’指示进行。……白话的使用者却在有意与无意间插入分析性的文字。”(16)这种大量增多的指示性文字、分析性文字主要就是虚词成分的运用,以表述时间的变化,建立事物间的关系或展示演绎性的逻辑。王光明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以现代言说性的语言作基本材料对僵死古文的反拨,是真实意识和本真生命的显身显影”。(17)由于文言虚词向白话虚词过渡,现代白话虚词和语言比古代文言更接近人生与大众,也更贴近现代人的情感与心理。现代汉语虚词在词义衍变、使用频率和语法结构的严密性等方面的变化,成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转型的重要因素。三是外来虚词的翻译与引入,扩大了新诗的语言资源,给现代汉语诗歌输入了现代气息与思想活力。梁启超认为:“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尽载之尽描之,此无何如者也。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18)如虚词“在”、“和”、“又”、“被”、“而且”、“如果”、“既然”等词语的翻译选用,极大地重构了现代汉语诗歌白话语言的语汇和语体方式,激活了部分汉语虚词功能的扩展与变化。如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被他认为是真正意义的新诗,诗歌较突出地使用了虚词“也许”、“和”、“但是”、“还有”等,清晰地表明了诗句的语义与情感逻辑关系。这与他受英诗句式影响有关,也与他自觉使用欧化的虚词、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细密的句法结构相关。 显然,大量现代汉语虚词入诗的作用不只是词汇的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了组织诗歌语言的词法、句法,有效促成了诗歌文法的变化。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19)鲁迅也认为,中国“向来作文的秘诀是避去俗字,删掉虚字,以为这样就是好文章。其实不精密”;“文与话的不精密,证明思路不精密……要话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就只得采取些外国的句法。这些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泡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但补偿这缺点的是精密”。(20)汉语词类关系的变化影响到整个语言表意系统。废名曾指出,古代诗歌“都是在诗的文字之下变戏法。他们的不同大约是他们的辞汇,总决不是他们的文法。而他们的文法又决不是我们白话文学的文法”。(21)词汇创新直接改变语言外部关系,语言的内在关系是由文法的意义来决定的,只有通过外部与内部的双重变革,才能使诗歌获得真正的现代品格。特别是大量连词或关联词构成的诗歌从句结构和复句关系,形成了现代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以行为句”的单一表意系统的明显区别。朱自清在总结新诗第一个十年时,认为周氏兄弟的诗“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另走上欧化一路”,“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22)古代旧体诗不强调文法,少用或不用虚词,以避免妨碍诗体的齐整或押韵。胡适等白话新诗派诗人的新诗则相反,有意使用大量现代汉语虚词。虚词的激增影响了诗歌语言词汇、语法体系和思维模式的更新,体现了古代诗歌“以字为中心”的诗思向现代诗歌“以句为中心”的诗思转换,这从外在与内在语言构造形式上对诗体进行了彻底革新。 三、现代汉语虚词与新诗形式变革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直接影响了汉语诗歌句法、体式、节奏等诗歌形式的变革。现代汉语虚词运用,在建构散文化的自由诗体形式中起了重要的标志性作用。 (一)现代汉语虚词入诗与新的诗歌句法的形成 现代汉语虚词使诗歌的句法更为严密,诗歌的句式排列自由度扩大,并把古代汉语诗歌以实词结构为基础的可对称性组织变为以白话口语为中心的松散性组织,这从根本上突破了古代诗歌固定的诗体结构规则,突出表现为“五四”以来白话文语体的散文化诗句在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运用。现代汉语诗歌践行的“言文一致”表意原则,需要句子成分较为完备、逻辑语义关系大体清晰,需要更多具备语法能力的现代汉语虚词承担诗句中的重要功能。 古代汉语诗歌建立在诗体格律固定化的规范之上,经常有语序错综、成分缺失和语法不严密等缺陷。因此,古代诗歌常回避诗句间的逻辑关系,省略对于逻辑推理不可缺少的介词和连词。如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就省略了指示方向的介词及动词。“鸡声”、“茅店”、“月”是意象叠加,形成并置的视觉感。其中的主客体处于一种交互关系中,整首诗形成多重的句法结构。“鸡声”既可当作时间状语理解,又可视为名词。其中有连词或助词的省略,“鸡声”、“茅店”、“月”或为并列关系,或为从属关系。古诗中虚词的省略,试图使诗歌意象间形成空间架构,实现实词间的跳跃、叠加、渗透、对照等多重非线性的诗意流动。这也是为了形式的对称工整与音律的平仄协调,这种建立在单个字或词语组合基础上的诗歌思维,呈现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字的思维”特征。现代汉语诗歌接受了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重视事物之间的关系,注重诗歌的内在诗意生成,把真切表现现代人复杂的情感思想和具体、生动、深刻的生活经验放在首位;在诗歌形式上不强调单个字或词语的个体蕴含,而突出诗歌形式整体的诗性建构,强调句与句间的组合关系,“旨在自由表达更为复杂的思想感情的句法形式主要是靠一些特定的句式和带有特殊虚词的句法结构来实现的”。(23)这种为了彰显内在诗意,大量借助汉语虚词,重视诗歌句子组合关系的诗歌思维,构成了与古代诗歌“字思维”相区别的现代汉语诗歌“句思维”的形态特征。像胡适的《“应该”》中有这样的句子:“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如果不使用虚词“也许”、“还”、“但”、“总”、“再”,则很难表达出诗歌完整而曲折的情感逻辑。又如郭沫若的《天狗》借助一系列语气词的变化与介词词组的重复叠加,构成内在情绪的紧张关系,形成整体上汪洋恣肆的宏大气势,借以表现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情绪。它的思绪表达与艺术美感不是局部的诗意显现,而是整体的诗意生成。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改变了汉语诗歌朦胧多变的句法关系,以散文化诗句形式作诗,这是突破古代汉语诗歌固定诗体形式的一个前提条件。 (二)现代汉语虚词入诗与现代汉语诗歌自由体形式的形成 现代汉语自由诗体式的形成,源于诗歌句式的自由变化与扩张。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形成了词组、短语和诗句容量的扩展。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与严密的语法逻辑关系相辅相成,部分虚词在短语或词组中构成修饰成分,拓展了短语或词组,形成句式的扩张,更加清晰地表达了主体的情感思想。 其一,在名词或其他词语前面使用介词,组成介宾短语,突出对实词的依存关系。如胡适《尝试集》中的“从”、“在”等介词的使用:“我从山中来”(《希望》),“老槐树的影子/在月光的地上微晃”(《十一月二十四夜》),“打我们的船边飞过”(《湖上》),这些诗句中使用的介词指明了时空关系的存在与变化,描绘了主体精微细致的现代感受,与西方语法结构中突出介词短语构成的状语成分有相通之处,也改变了古代汉语诗歌朦胧模糊的时空观念。现代汉语诗歌表示时空关系介词的大量出现,直接导致了诗句的散文化。如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他含着个十年的烟斗,/慢慢的从田里回来;/屋角里挂去了锄头,/便坐在稻床上,/调弄着只亲人的狗。//他还渡到栏里去,/看一看他的牛;/回头向她说,/‘怎样了——/我们新酿的酒?’”介词“从”、“在”、“到”、“向”的使用,点明了空间关系与主客体关系,用散文化、口语化的语言写出了一个农民从田里归来的日常家庭生活情景。这种确定关系的写法,对于现代汉语诗歌书写特定的具体情景有着极大的帮助。 其二,现代汉语诗歌中助词的使用,确定了句法中的从属或修饰关系,使词组、诗句增长,破坏了古诗固定的短语、句子结构和诗体形式。古诗中很少出现助词,现代汉语诗歌的使用则较为普遍。如沈尹默的《月夜》:“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第三行结构助词“的”和动态助词“着”的使用,改变了古诗固定的字数限制。“的”字限定了一种语法关系,属于口语化的助词,形成修饰性的从属结构;“了”、“着”表示动作行为的状态,在现代汉语诗歌中使用也较多。现代汉语“动词自身不能表示时间性”,(24)不像西方语言的动词有时态标志,因此需要在诗歌中增添结构助词“了”、“着”以及一些时间副词等,才能更明确地表示动作的完成或事态的变化与确定的语气。胡适在《你莫忘记》中应康白情的建议添加了三个“了”字,认为这样“方才合白话的文法”。(25)如刘半农的《情歌》:“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结构助词“的”、动态助词“着”及语气助词“啊”的使用,扩展了诗句的结构,很好地表现了抒情的效果。特别是语气助词的使用,其位置的灵活性使得诗体形式变换自由。又如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等,不仅大量使用“啊”、“呀”、“哟”、“哦”、“吗”等虚词,而且用叠音的语气助词“啊啊”、“哦哦”来直接抒发主体激扬的情感,使用位置多变,或位于诗行之首,或位于行末,或位于诗节之首单独成行,只依情感的表达,不求诗句的均衡。这些语气助词的使用,使诗行的形式变化多样,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古诗固定的诗体结构,摆脱了传统诗歌旧格调的束缚。 其三,副词在现代汉语诗歌中的大量使用,使诗句中的动词、形容词得到修饰,更加明确地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性质的时间、范围、程度等,使诗人的态度、感受、情感与思想得到完整传达或突出表现。如刘半农的《老木匠》:“他说了他就哭,/他抱了我亲了一个嘴;/我也不知怎么的,/我也就哭了。”时间副词“就”起到了两个动作之间的承接作用,两个频率副词“也”的连续使用,以及“也”、“就”的连续使用,令诗句的情感状态得到较好的显现。可见,副词的大量使用能在有限的形式中蕴含一定的逻辑语义关系,加强了诗句的口语化倾向。 其四,与介词、助词、副词在现代汉语诗句中的修饰性成分相比,连词在现代汉语诗句中多用于连接词组、短语或分句,能较明晰地呈现各种关系,是现代汉语诗歌自由运用单句、复句的关键性虚词。如郭沫若的《梅花树下醉歌》:“假使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运用了假设关系连词,连续引导两个单句与下一诗句结成一个复句,拓展了句子的容量。连词能包含较大的思想容量,使意义曲折连贯,能自由展示自己的思维过程及丰富的思想与情感。新诗中现代情感与哲理的增加,较多依靠虚词的使用,呈现出语言逻辑和事物关系。特别是具有议论性、思辨性、哲理性的诗歌常借助大量连词,能增强事物的逻辑语义关系。这类虚词在穆旦诗歌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穆旦的《赞美》:“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辞,溶进了大众的爱,/坚定地,他看见自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个复句因为连词“而”、“因为”的多次使用,容纳了更多丰富的内容和思想情感,使句子的长度大大扩展,即被分为九个诗行,这从根本上突破了古诗的诗句长度和诗体限制,解放了固定的诗体形式。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不仅拓展了诗句的长度和容量,还使大量的分行、跨行成为较普遍的诗句组织形式。由大量介词、助词、副词、连词构成的语法结构,改变了一句一行的传统诗歌句式规则。如胡适的《许怡荪》:“我把一年来的痛苦也告诉了你,/我觉得心里怪轻松了;/因为有你分去了一半,/这担子自然就不同了。”利用虚字重新组合诗句,连词“因为”的使用,使语法更为严密,形成了一个长复句,扩张了诗歌容量。如介词“把”,助词“的”、“得”、“了”,副词“也”、“就”等虚词的使用,突破了旧诗的文法,带来了单字排列的减少和词组使用的增多;诗句长短不一,使古代诗歌严整的诗句松动和变形。现代汉语诗歌在语法上受到西方逻辑化语言规则的影响,增加了大量抽象词汇和口语词汇,并利用词序或虚词调适了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虚词的使用令散文化的诗句化板滞为流动,形成了内在的顿挫抑扬、张弛跌宕的张力效果。 大量现代汉语虚词的入诗,拓展了诗句长短的自由度,形成分行、跨行为基础的散文化自由诗体,这是对古代汉语诗歌固定的一句一行、短语连缀式的句式结构与格律化文体的瓦解与破坏。 (三)现代汉语虚词入诗与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新构型 现代汉语虚词在诗歌中大量运用,改变了传统诗歌建立在实词基础上的音步组合规律,对现代汉语诗歌现代节奏的构型起到了重要作用。虚词的增加和使用反映了欧式语法的渗透,各种定语、状语、补语径直挂靠在主谓宾上,成分完备而句子变长,以上各方面都影响着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建构。(26)由于古代诗歌中虚词较少入诗,轻音也少,音步的组合仅为单音和双音音步;现代汉语诗歌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由于双音节、多音节词汇的激增,译音词、轻音及虚词的大量入诗,使得现代汉语诗歌音节形态增多。如介词“从”、“在”,以及结构助词“的”、“地”、“得”和动态助词“着”、“了”、“过”的进入,使得多音节音步剧增。比如胡适的《上山》:“我在树下睡倒,/闻着那扑鼻的草香,/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介词“在”和助词“着”、“的”、“了”及副词“便”的使用,使诗歌的音节拉长,形成“1|3|2||2|4|2||1|5|2|2”的自由组合方式。这种方式依据自然的语气,以口语化的虚词改变了古诗的格律规则。又如大量语气助词的进入,使得现代汉语诗歌的节奏组合更为自由。郭沫若诗歌较多使用语气助词,特别是位于句末的语气词的使用,有助于诗人情感的自由抒发,形成自然流畅的音响效果,在情感、气势、神韵、声韵的交融中给人耳目一新的美感。如《天狗》第一节:“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首诗中大量感叹词、助词和介词结构的运用,构成了情绪节奏与现代韵律节奏的交响。整个《女神》大量借助现代虚词,构成了以情绪节奏为主,又兼具多种节奏形态的自由开放的现代节奏形式。 现代汉语诗歌在对西方音节诗学的借鉴中,把古代诗歌重视平仄韵律的规则转向了重视轻重韵律的现代音韵节奏探索。胡适的“自然音节论”强调:“白话诗里只有轻重高下,没有严格的平仄……白话诗的声调不在平仄的调剂得宜,全靠这种自然的轻重高下。”(27)英语诗句多通过轻重音和语调的变化构成诗歌节奏,这与古诗严格遵守平仄韵律的规则不同。如胡适的《“威权”》:“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句末虚词“了”的弱读减少了声调时长,也改变了古诗多以重音节字结尾形成拖腔的现象。同时,句间虚词“的”的使用与其他实词,形成白话的自然语气和轻重感知的变化,突破了古诗单一、固定的平仄律。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也调节了声调的高低升降和语调的抑扬顿挫变化,形成散文化的自然声调和口语化的日常语调,这与现代汉语诗句的增长及对西方英语诗歌语调的接受有关。如胡适强调自然音节的形成,多用大量口语化的虚词,如句末常用轻音虚词“了”等,形成了自然舒缓的内在节奏和近乎自然的散文形式。郭沫若多用语气助词以及名词性非主谓句的偏正结构,形成了大量表示感叹语调的音节形式。譬如《晨安》:“啊啊!大西洋呀!/晨安!大西洋呀!/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大量助词的入诗,形成诗歌句尾反复呼应的气势和感叹的语调。 康白情认为:“我们底感兴到了极深底时候,所发自然的音节也极谐和,其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无不中乎自然的律吕。”(28)五四时期的现代汉语诗人一方面进行传统诗体格律形式的解构,另一方面也在自觉尝试建立新的节奏形式。胡适等人立足于语言节奏属性的“自然音节节奏”,郭沫若注重情绪和情感的内在律为主的“情绪节奏”,闻一多、陆志韦、徐志摩以西方音步或音尺为范式的“现代音节节奏”等,都自觉以大量现代汉语虚词的入诗来建构现代汉语诗歌节奏形式。 四、现代汉语虚词与新诗表意功能的嬗变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推动了中国传统诗歌抒情这一主要功能向叙事与哲理表现的多元路向转变,这是一种由“情”向“理”的现代转变趋向。中国古代诗歌以言情为本。汉代《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29)自魏晋时期起,诗学家“以情释志”,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感性维度。诗人“应物斯感”,见物起情、借景抒情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诗思方式。 古代汉语诗歌主情的诗思方式,力求精炼简略,以含蓄隽永为美。在语言选择上常省略各种关系词,尽量少用或者不用连词、介词、助词等。如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望庐山瀑布》),省略了介词“在”、副词“像”、助词“的”等,直接运用实词及比喻词。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省略了描述性的虚词,但为了表达的清晰也接着使用了副词“岂”和“应”,“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然而,在整体上古代汉语诗歌使用虚词仍然很少。尽量省略虚词则形成实词间词语的跳跃,一方面与古代汉语诗歌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理念相联系,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表意的含蓄。现代汉语诗歌为了实现“言文合一”的诗歌理念,在借鉴欧化的词汇、语法、逻辑、修辞时,大量使用各种虚词、代词、单复数词汇等,形成了句子结构的复杂化,使句子关系更加紧密,表意更为清晰周全。可以说,这一由传统诗歌的表意之“虚”到现代汉语诗歌的表意之“实”的转向,与现代汉语虚词的剧增与大量使用是分不开的。如周作人的《小河》:“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该句使用了助词“的”,副词“总”、“便”和介词“在”,构成了清晰的语义逻辑关系和散文化的语言形式,呈现出与古诗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散文则恰恰要在现实中寻找实际存在(Daseyn)的源流,以及现实与实际存在的联系。因此,散文通过智力活动的途径把事实与事实、概念与概念联系起来,力图用一种统一的思想体现出它们之间的客观关系。”(30)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改变了古典诗时空、因果关系的朦胧与模糊,以散文化的句法和语义连接方式,更明晰地表现了复杂的事理叙述和语意联系。 在现代诗歌语言中,外来虚词的使用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如“在”、“和”、“又”、“被”、“而且”、“如果”、“既然”等词语的翻译与选用,就极大地重构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关系。如郭沫若《女神》中大量的现代汉语虚词,显然受到惠特曼诗歌及日文粘着语形式需要助词与语尾变化的影响。特别是语气助词的使用不仅频率较高,而且变化多样,体现出不同情感状态的喷涌勃发。《凤凰涅槃》中“啊啊”的使用,不仅单列诗节的首行,甚至引导多个诗节,将诗人情感的抒发不断地推向新的高潮。《日出》中“哦哦”引导诗节首行诗句,并与其他诗节形成对仗,显示了诗歌回环跌宕的情感节奏和语形节奏。这种虚词的大量使用拓展了现代汉语诗歌情感的表现方式。葛兆光认为:“意象的密集化、凝练化,使得虚字逐渐退出了诗歌;语脉与意脉的分离,使得习惯语法破坏殆尽;声律模式的形成,使诗歌有了一个华美整饬的图案化格式;典故的运用及诗眼的推敲,使得古典诗歌尤其是近体诗有了精致而含蓄的象征意味。”(31)这种精致和含蓄的诗意表现与古代汉语诗歌“温柔敦厚”的抒情功能相适应,却不利于现代思想和哲理的明晰表达。现代汉语虚词的激增拓展了诗歌哲理功能的表现领域,实现了汉语诗歌发展的多元路径。 中国古代诗歌最为兴盛的是篇制短小的抒情诗,西方的叙事诗与哲理诗较为发达,西方诗歌具有史诗传统。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史诗“追求客体的全部表现”,所以叙事成分与哲理性体验较多;在语言形式上句子关系复杂,多用从句结构,这就决定了大量的介词和关联词语等进入诗歌。诗歌的丰富内涵和复杂事物关系的表现与虚词的大量入诗互为一体。许多现代诗人不再把情景交融视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开始追求一种具有理性体验特征的诗歌表达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古代诗歌的主情或感性的表达范式,起到了“以理正情”的作用。 现代诗人在使用现代汉语虚词表达情感或知性体验时,都有主体意愿和不同选择,但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体现出与古代诗歌感性抒情倾向的不同。早期白话新诗派诗歌,开始大量运用白话虚词,让语言接近白话口语,诗歌体现出通俗明了的说理倾向与纪实风格(周作人批评“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意在建立一种科学求真的新诗境界。朱自清说,新诗的初期,“‘说理’是这时期的一大特色”,“胡氏也许受了外来影响,但总算是新境界”。(32)继新诗“尝试期”之后,郭沫若的诗因其强烈的感情和奇伟的想象而自成浪漫一派。诗人为了情感的解放与书写的自由,在《女神》中大量运用语气词、助词、感叹词、介词等,形成了不拘一格、自由奔放的风格,而这种浪漫主义风格饱含着科学民主思想的主体精神的高扬,是人觉醒后被理性意识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的体现,科学理性精神形成了与内在现代诗意以及外在自由诗体的有机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闻一多说郭沫若的诗饱含着20世纪的动的、反抗的成分,“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33)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总体上呈现为以理正情、以理主情的现代色彩,打上了五四时期雄浑昂扬的时代烙印。 闻一多代表的新月诗派倡导“理性节制情感”,无论是表达个人的切肤之痛,还是表达民族的忧国之情,都能在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节奏中,巧妙调控虚词,显现出成熟的以理节情的艺术魅力。比如闻一多为女儿写的悼亡诗《也许》:“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这一节连续用的三个“也许”,既有表语气的作用,也有表情态的意义,同时起到了连词作用,“也许”在句子中三次重复与停顿,构成了舒缓的节奏,传达出一种忧伤哀婉的抒情之美。“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结尾这一节,采用了“那么……就……”的连词引导句式,表达假设语气,最后又用介词、语气词、儿化词(还有重叠词)形成舒缓平抑节奏,渲染静穆幽美的抒情意境。闻一多代表的以理节情的现代审美意趣,体现了现代汉语诗歌与古代汉语诗歌语言诗性表现力的有机融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派自觉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借鉴,呈现了一种新诗智性化倾向。卞之琳的新智慧诗,冯至充满了沉思和哲理的《十四行集》,中国新诗派重视经验传达的知性化诗歌,都明显表现出与中国古代诗歌主情传统的异趣。唐湜认为“诗就是情感”的说法早已过时,并引述里尔克的话说:“诗并非如人们所想的只是情感而已,它是经验。”(34)正如唐湜所言,40年代现代派诗人信奉诗是经验的传达,这使他们在创作中确定了情与理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在诗歌外在形式上大量采用连词特别是关联词语,大量的从句结构和复句形式构成了他们诗歌的常态。 穆旦的诗歌最有代表性。他较多地利用关联词语来表达他丰富复杂的人生经验与生命感受。比如《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在两个复合句式、一个假设的虚词关系结构中,表达了青春生命的苏醒与渴望,具有多种含义。又如《赞美》:“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个诗段集中运用介词结构构成排比句式,用连词“而”构成并列句式,突出表达诗人对艰难岁月中人民的关切与温爱,对大众苦难的忧戚与悲悯,最后的“因为”句式形成有力的转折,赞美伟大民族的觉醒与抗争。穆旦所代表的中国新诗派诗歌对现代汉语虚词的艺术化的成功使用,极大地增添了现代诗歌的知性内涵与艺术张力。 现代汉语诗歌虚词大量入诗,最积极的意义,就是打破了传统诗歌外在固有的格律,推动了诗歌文体与语言的解放,促进了现代汉语诗歌现代诗意的有效生成。在废名看来,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35)他认为,现代汉语诗歌与古代汉语诗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现代诗歌语言形式是散文的,而内容是诗的;古代诗歌外在形式是诗的,但内容是散文的。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的激增,使得诗歌语言具有更强的自我生殖功能、创造功能以及接受西方欧化语的融合性功能,使得现代汉语的运用在符合逻辑性、语法性等方面更为有效,能更具体、细致、明晰地表现事物的状态或主体情感体验。 现代汉语虚词表意功能的变化,直接带来了汉语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化。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是在汉语欧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古代汉语是一种突出的“意合”语言形态,不同于英语等欧洲语言重“形合”的特征,常常省略标明句子关系的词语,而倾向于通过句子之间的语意逻辑实现连接,这也形成了古典诗歌浑然融合、朦胧含蓄的独特诗美形态。这种以含蓄、朦胧、空灵的虚境之美为理想的审美趣味,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于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开始融入了求真写实的审美趣味。对这种由“虚”向“实”的转变,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使用功不可没。因此,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所指向的诗美倾向与传统诗歌有了明显的区别。首先,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追求的是诗歌形式与主体思想表达的一致性。如穆旦诗歌在关联词的大量使用中,形成了思想的深厚与审美风格的浑厚统一。唐湜说穆旦,“他的诗里很少中国人习惯的感性抒情与翩然风姿”。(36)袁可嘉认为,穆旦的某些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其构思和形象都有现代派的特色:肉感中有思辨,抽象中有具体”;“敏锐的知觉和玄学的思维,色彩和光影的交错,语言的清新,意象的奇特,特别是这一切的融合无间”。(37)穆旦的诗歌大量使用复句,客观上呼唤着关联词的参与,有意避免“意合”,体现了与古典诗歌之所谓的“朦胧含混美”的异趣。我们应看到关联词使用背后所延伸出的现代思想和精神,那就是注重生活多层次的立体表达,表现生活本身的真实与复杂,特别是个体生命的多样性体验。其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知性化诗潮中,凸显着严密性和逻辑性的关联词语,在思维上既体现着智性思考,在形式上又规约着抒情表达;同时,叙事性因素的增强使得关联词的使用更为自然,展现了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和范式,即对理性的强调和叙事的融入,这给中国现代诗歌带来了一种传统诗歌所缺乏的浑厚与坚实的理性抒情与知性美感。 在汉语诗歌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起到的作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然而,这一变革过程中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郑敏在1993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时,就对汉语诗歌语言变革作了一番沉痛的自我反省,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过激策略失之偏颇。她肯定古代汉语的诗性特点,指出新诗“语言的阻塞与困乏”的原因在于接受西方欧化语的同时扔掉了古诗语言的独特魅力。也有年轻学者对诗歌虚词的使用抱有异议,认为新诗、旧诗都应该尽可能地剔除或避免过多的虚词。还有学者以李金发诗歌中的虚词使用半文不白、与欧化句式扭结,偏离了艺术性和审美性作为失败的例子。 应该说,如何恰当地使用虚词,让虚词的使用符合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表达、增进艺术审美的效果,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即使是实词入诗也不能例外。古代诗歌中虚词运用虽然不多,但古人早对虚词功能有精要的表述。清代学人刘淇在《助字辨略》中道:“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清代另一学者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认为,“词中虚字犹曲中衬字,前呼后应,仰承俯注,全赖虚字灵活”。程抱一评价清代学者袁仁林的《虚字说》:“赋予虚字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上’的地位……他将实词和虚词之间的辩证游戏等同于激荡宇宙的虚与实的生机勃勃的运动。”(38)这种虚实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思想有一定关系。《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9)现代语言学家邢福义结合虚词的功能给虚词定义:“虚词是意义比较虚灵,不能充当句子基干成分的词。但是,虚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够配合实词造句,协助实词表达意义,帮助句子成分或分句表达关系,是汉语的重要的语法手段。”(40)早在1980年,新诗研究专家孙绍振已注意到虚词在诗歌建构中的作用,强调西洋诗歌不可忽视的优点:“那就是有比较大的思想容量和生活容量。这是因为它不回避诗句间的逻辑关系,不省略对于逻辑推理来说是不可少的介词和复合连接虚词。”(41)古今学者虚词之论,对我们理解古今汉语虚词与汉语诗歌的复杂关系不乏启示意义。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促进了汉语诗歌语言的转化、诗体的解放、诗意的深化与诗美的嬗变等。但它也带来了诸如诗歌语言的直白、诗体形式的散漫、感性抒情的淡化、知性表现的生涩与诗歌节奏声韵的无序等问题,这也是我们在顺应诗歌现代潮流变化的历史进程中,需要辩证反思和认真探索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审:王兆胜 注释: ①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1999年12月号,总第56期。 ③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1页。 ⑤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⑥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导言”,第24页。 ⑦王泽龙:《“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⑧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1113页。 ⑨郭沫若:《文艺与科学》,《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⑩本文引用诗歌数量较多,因篇幅所限,不在文中一一注明引用来源。特此说明。 (11)闻一多:《英译李太白诗》,《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6月3日。 (12)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3页。 (13)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与美学的汇通》,《中国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209页。 (14)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陈顺智、徐少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15)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16)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33页。 (17)王光明:《诗:聆听与言说》,《面向新诗的问题》,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 (18)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号,1902年6月。 (19)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0页。 (20)朱自清:《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74—175页。 (21)冯文炳:《谈新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22)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导言”,第3页。 (23)欧阳骏鹏:《现代诗歌语言研究的基本路径》,《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4)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25)胡适:《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四版自序”。 (26)王泽龙、王雪松:《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内涵论析》,《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27)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05页。 (28)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15日。 (29)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3页。 (30)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8页。 (31)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32)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2页。 (33)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第113页。 (34)唐湜:《论意象》,《新意度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11页。 (35)冯文炳:《谈新诗》,第24—25页。 (36)唐湜:《忆诗人穆旦——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 (37)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第11、15页。 (38)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39)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6页。 (40)邢福义编:《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 (41)孙绍振:《论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新诗基础论之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