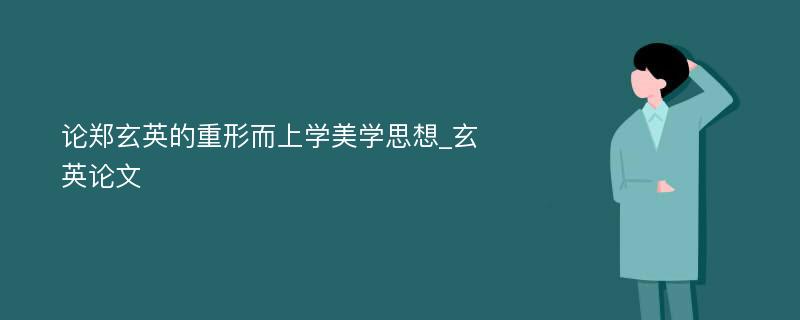
论成玄英重玄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思想论文,论成玄英重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58;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2)02-0140-06
成玄英,字子实,唐代道教重玄宗著名学者。陕州(今河南陕县)人氏,生卒年不详。曾隐居东海,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将其召至京师,加号西华法师。高宗永徽(650-655年)中流放郁州。期间,注疏《老》、《庄》,并撰述其他著作。“书成,道王元庆遣文学贾鼎就授大义,嵩高山人李利涉为序,唯《老子注》、《庄子疏》著录”[1]。其中,成玄英的《老子》注疏已散轶,散见于强思齐的《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和顾欢《道德真经注疏》中,今天可见的三个辑校本分别为:蒙文通《老子成玄英疏》6卷、严灵峰《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5卷、日人藤原高男《辑校赞道德经义疏》。而又以蒙本成书较早,严本次之,藤原本最晚,并对前两种辑校本均有指正辨难。另《道藏》本收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35卷,并收入清人郭庆藩《庄子集释》。此外,成玄英所注道教灵宝派《度人经》也收入宋人陈景元《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今《道藏》本及《正统道藏》均有著录。本文主要根据成玄英的老庄注疏对他的重玄美学进行分析。
一、以“空”代“无”——对道家美学思维方式的补偏救弊
成玄英曰:“至道微妙,体非五色,不可以眼识求,故识之不见。……体非宫商,不可以耳根听,……体非形质,不可搏触而得。”但“至道虽言无色,不遂绝无,绝无者遂同太虚,即成断见。今明不色而色,不声而声,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2](389页)至道幽微,既不可以感官感受,又“不可以心识之”[2](392页),要体会作为世界最高本体的至道,只有摆脱认知思维,才能重新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
就人类思维的一般特征而言,认知行为是有对象的。而有对象就意味着有客体与主体(物与我)之间的区别,将世界人为地分裂为主、客两个部分。主体不仅在认知过程中将物、我分开,而且将物与他物、类与他类区分开来,并为了更具普遍性完整性地把握客体,而冠名于物,将物概念化,却反而忽略了名(符号)背后的实(事物本身)。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深刻认识到认知思维中存在的问题。因而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2](468页)。不仅充分指出“小知”“好知”、“机心”对人类社会及生命本真造成的戕害,更以“为道”来消解认知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道家的美学思维方式分别通过无物、无我、物我两忘来实现。不但消除认知思维强加于物与物之间的差别,更进一步消解对象化的根源——自我意识,最终实现物我之间相互交融,消除一切界限,使心灵获得极大的自由,实际上是通过以直觉体悟为基础的非逻辑理性思维方式,来达到道家最高人生境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3]。
然而,道家的这种消解其实并不彻底。老子以“无”消除对象化的“有”,但这个“无”本身就具有对象化倾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21章),可见,道体本身就并非绝对的“无”。为了弥补理论上的不足,庄子针对老子的“无有”进一步提出“无无”,把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改造为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把老子道的形而上观念上升到体悟生命的道的形而上境界,在这一点上,庄子哲学进一步与美学思维打通。然而,庄子的“无无”仍然具有消解自我的不彻底性。《庄子·齐物论》中庄周化蝶打破了物我之间的界限,但这个我毕竟还是存在的,只不过自我在蝴蝶与庄周的互换过程中,位置变得极不确定而已。同样,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齐物论》)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模式来看,表面上似乎没出现主客体的对立,但事实上,是谁在从道的角度观物之无贵贱呢?隐匿的自我藏在道的背后,仍然高高在上地审视万物。正是由于对认知思维主体消解的不彻底性,道家美学没有实现真正的物我两忘,因而也就没能实现它所谓的最高人生境界、审美境界。目前学界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4]。
作为道教学者,不管成玄英是否已经清楚认识到老庄在美学思维方式上存在的缺陷,通过对道教祖经《道德经》、《南华真经》的注疏,他事实上已经借助佛教大乘空宗的“中观”思想,以重玄美学对道家美学思维方式进行了修正工作。
以中观的思想方法来看,现象与本体是统一的,整个世界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故无自性,虚假不真,根本不必区分现象与本质来确认其空。但这个空却并非无。它“非有非非有,非无非非无”[5],处于一种假号的存在状态。道家用“无”来消解主体,而佛教中观学说则不落窠臼,有无双遣,不执着于物,也不执着于心,既否定认知思维的主体,又否定我之外的一切事物的实体性,从而超越了心物、主客、有无的二元对立。
为了补救老庄因滞“无”而造成的美学思维上的偏颇。成玄英借助大乘佛教空宗的“空”来代替老庄的“无”。以摆脱因“滞”而带来的论述中的不彻底性。具体而言,成玄英对道家美学思维方式的补救是从以下几个层次展开的:
首先,针对道家的“无物”,他提出了“物境虚幻”[2](369页)。认为万物之间的差别实际是不存在的,人只不过是以自己的喜好来妄断事物的美恶。“一切苍生莫不耽滞诸尘而妄执美恶,逆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为恶。顺其意者必生爱染,名之为美。不知诸法即有即空,美恶即空,何憎何爱”[2](362页)。可见,世人所谓的美恶根本是不真的,诸法既空,又何来诸法的美恶?世俗的美恶如此,善恶也是这样。“善之与恶相去何若?顺意为善,违心名恶,违顺既空,善恶安寄?且唯阿出自一口,善恶源乎一心而忘者知其不殊,执者肝胆楚越,然有为之学,迷执者多,是非善恶之中,喜怒唯阿之内,适为患累之本,绝之所以无忧”[2](403页)。成玄英的论述可谓釜底抽薪。一方面,他沿袭了庄子《齐物论》的思想脉络,指出物无贵贱、美恶之分;另一方面,他又不落“以道观之”的窠臼,他所谓物无差别的原因在于万相皆空。他并不把自我摆到与道合一的位置上来审视万物,因而也就不会导致所谓主、客体的割裂。
其次,针对道家的“无我”,他指出人应该“空心惠观”[2](362页)。既然世间万物不过是虚幻不真的存在,即有即空,那么便知“喜怖之情皆非真性”。“是以达者譬穷通于寒暑,比荣辱于偿来,生死不扰其神,可贵贱之能惊也?”[2](386页)领悟到这一点,人便能“即心无心,而实有灵照”[2](367页)。
《道德经》称:“塞其兑,闭其门。”成玄英将闭塞之义注解为二。“一者断情忍色,栖托山林。或即塞闭其门,不见可欲。二者体知六尘虚幻,根亦不真,内无嗜欲之心,外无可染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见,极耳之所闻,而恒处道场,不乖真境,岂曰杜耳掩目而称闭塞哉。盖不然乎。见无可见之相,听无定实之声,视听本不驰心,斯乃闭塞之妙也。”[2](477页)可见,成玄英本人推崇的实是第二种闭塞之妙。因为只有第二种闭塞才是真正地做到了心空,境空,而第一种闭塞只不过通过与外境声色的强制隔绝来消除对心的干扰,与真正体道的境界还相差甚远。所谓“可欲者,即是世间一切前境色声等法,可贪染爱之物也。所言不见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体尘境虚幻,竟无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见闻而心恒虚静,故言不乱也”[2](366页)。
当人体会到世界的虚幻不真,那么即使不有意去闭目塞听,也能够处染不染,和光同尘。按成玄英的话来说就是:“既无可欲之境,内无能欲之心,心境两忘,故即心无心也。“[2](367页)
又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成玄英将“无”换为“空”,释为:“周礼考工记云三十辐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当其无者,厢毂内空也。只为空能容物,故有车之用。况学人心空,故能运载苍生也。又车是假名诸像和合而成。此车细析推寻,徧体虚幻,况一切诸法亦复如是。”[2](383页)诸法既空、我心亦空,不仅认知思维的主体我被否定,我之外的一切事物(诸法)的实体性也遭到彻底否定,经过这样的双重否定,达到了有无双遣的效果。同时,“物我皆空不见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自他平等不是已非物,故其德显著。”[2](410页)正是因为物我皆空,而实现了自他平等,我不是站在中心地位对他事物妄加审视、评断,才能实现真正的物我相融。接着,成玄英进一步提出“兼忘”的观点。他不仅继承了庄子坐忘的思想,以不断的忘却来摒除世俗之见,达到境智两忘,物我双绝,更要将忘却也忘却,以示不滞(不执着),也就是佛教所讲的破执。他说:“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执,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药还遣。于是唯药与病一时俱消,此乃妙极精微。穷理尽性。”[6](5页)境智两忘本来是对物我的否定,而将忘却本身也一并忘却则是要将否定本身也否定掉,空甚至要将自身也空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不滞,也才能达到精神上极度的自由和超越,从而在一种逍遥无碍的状态中体悟大道之美。
成玄英深刻洞见到道家滞于单方面消解认知思维主体而对于最终体道造成的阻碍,因而明确指出:“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6](4页)玄是非有非无,重玄则是非非有非无,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并且超乎有无,遣之又遣。成玄英在老庄注疏中将大乘佛学中观理论(如八不中道的双遣法)大量植入道教经典的注释,经过双遣双非的双重否定,以期最终证到重玄道果。
最后,为了实现彻底的精神超越,成玄英将重玄作为一种境界,建构了一个超乎天地之外的重玄至道之乡。他在《齐物论疏》中称:“六合者,谓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谓众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乡也。”[7]在这一超越了天地四方的重玄境界中,“万物云云,悉归空寂”。若“于重玄道中妄起分别”,则是“倒置”、“妄执”[7]。即使“根尘相逼,举眼色等相当也,仍以大慈之心虚察前境,则能所两空,物我清净,故一切诸法皆成胜妙之境也”[2](517页)。同时,“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能随顺世事而恒自虚通。此犹是孔德。唯道是从之义。道得之者,只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两冥,能所相会,道得之犹得道也”[2](412页)。至此,妙契重玄的我即是道,即是理,也即是物,道心与世界、至道融为一体,于是,在这个绝对空寂的重玄之乡中,万物都无分别无是非,事物以其本来面目示人,而不再是相对于主观认知的客体。生命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和展现,处于一种整体的动态融合状态,从而进入一种比道家的天地境界更高的审美境界——重玄妙境,真正实现精神上的自由无碍,天人合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成玄英的重玄美学不仅是“老庄哲学在佛学影响下的新发展或道家、佛学融合的产物”[8],也是对道家美学思维方式的一种补偏救弊。
二、“妙契重玄”——以重玄为美的人生境界
崇尚自然,以自然天成的东西为美是道家、道教十分鲜明的主张和特点,作为唐代著名的道教思想家,成玄英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但不同的是他的自然观念同样渗透着重玄的味道。
成玄英注“道法自然”一句称:“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之迹,故义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无所法,体绝修学,故言法自然也。”[2](419页)可见,在他看来,自然是道的本性,而“自然者,重玄之极道也”,“自然之妙理,所谓重玄之域也”[2](419页)。从成玄英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笔下的自然是以含有重玄妙理为特性的自然,而“妙契重玄”[2](519页)则是成玄英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
成玄英曰:“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徼妙两观,源于一道,同出异名。异名一道,谓之深远。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也。”[6](4页)此一“玄”字,从语义学上讲,是深远之貌,而从义理上讲,则指一种“不滞”的状态。按成玄英重玄美学的观点来看,自然不仅是玄,是不滞,无待;而且还是玄之又玄,是不滞于不滞,是一种精神上的彻底自由与逍遥,彻底的“绝待”,也是无不待。
重玄——美首先表现在重玄是一种彻底的空寂状态,它朦胧而难以把握、难以捉摸,因而呈现出一种神秘美、朦胧美。《庄子·大宗师疏》曰:“一者绝有,二者绝无,三者非有非无,故谓之三绝也。夫玄冥之境,虽妙未极,故至乎三绝,方造重玄也。”“夫道,超此四句,离彼百非,名言道断,心知处灭,虽复三绝,未穷其妙,而三绝之外,道之根本,所谓重玄之域,众妙之门。”[9]在成玄英看来,要达到重玄的境界,必须彻底否定三绝,即不光要绝有、绝无、非有非无,还要达到非非有非无。这样的状态至虚至寂,不可把握,不可触摸,不能以理性思维和语言逻辑显现,而正是在这种混沌和深远的玄思中,通过不断的否定,将领悟推向更深邃更绝妙的层次,通过非理性的体验和直觉,重玄妙境显示出它自身的难以言说的神秘之美。
重玄之美的最直接化身和显现就是成玄英不断提到的“圣人”。成玄英所谓的圣人,不是儒家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而是充分领悟到重玄妙理并能与至道相合的人。“圣人,即与天地合德之者也”,“圣人者,体道契理之人也。亦言圣正也,能自正,正故名为圣”[2](368页)。圣人妙契重玄,在他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真、善、美的融合与统一,也最有说服力地体现了重玄之美。可以说成玄英所谓的圣人的境界就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最高的审美境界。在成玄英的著述中,有很多关于圣人的描述,在他看来,圣人是体道之人,更是深谙重玄妙理之人。圣人契道的结果不仅使他们自己成为美的化身,美的典范,同时,在他们身上也寄托了普通人的人格理想。
首先,借大乘佛教般若“空”观的思想,成玄英说明俗人与圣人所谓的美有着真假的区别。俗人所崇尚和追求的感官、声色之美不过是以假相为美,“人不能无为,不能恬澹观妙守真而妄起贪求,肆情染滞者适见世境之有,未体有之是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睹死生之归趣也”[2](360页)。而圣人明白诸法皆空,所以能够收视返听,摒弃空幻的假相,追求真美——重玄至道之美。所谓“怀道抱德充满于内,故为腹也,内视无色,返听无声,诸根空净,不染尘境,故不为目也”[2](385页)。
正是由于俗人与圣人对美的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俗心滞有,司察是非,妄生迫遽;圣智空无,体知虚幻,恒自闲静。”[2](405页)俗人执着于物我分别,有无分别,这种分别之心令其不能看破世间万物“实相无相”,所以“滞于欲境,未尝休息”。而圣人“妙体虚假,”“不见是亦不见非”[2](406页),所以“圣人虚怀体道,故能乘两仪之正理,顺万物之自然,御六气以逍遥,混群灵以变化,苟无物而不顺,亦何往而不通哉?明朝彻于无穷,将于何而有待者也?”[3](280页)
作为宗教,道教一直以神仙为崇拜对象。神仙不仅是至道的实体化表现,同时也是集真、善、美于一体的至美的化身。与道教传统的提法不同,成玄英绝口不提神仙,而以圣人作为重玄至道的化身,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成玄英的重玄美学对于肉体成仙思想的消解和弱化倾向。而精神上的极度超越和自由无待成为重玄美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圣人只不过是“善修之士”,能够“妙体其空,达于逆顺,不与物争,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极道”[2](515页)。只要善修,便能炼性,并最终契道,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至于对肉体是否不死甚或成仙,则存而不论。这种有别于传统道教的新思想不但促进了道教从人的内在本性,即“不灭的心性”中去寻找人与道之间可以契合和沟通的本质,以期解决肉体不死与道的永恒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从客观上讲,也导致了“以身为炉鼎,心为神室”的道教内丹学的迅速发展。
与传统的道教神仙相比,成玄英所谓的圣人由于道契重玄,而更加强调其精神自由、适性逍遥、崇尚自然的一面。圣人的自然不仅是不滞,不追求,而且是连不追求本身也不追求,处于一种彻底的无待状态。成玄英曰:“学人虽舍有无,得非有非无,和二边为中一,而犹是前玄,未体于重玄理也。此虽无待,未能无不待。此是待独,未能独独。”[21(533页)而“圣人能行所两忘,境智双遣,玄鉴洞照,御气乘云,本迹虚夷,有何病累?”[2](520页)所以,只有深谙重玄妙理的圣人才能实现无不待,处于一种独独的状态。由于圣人与重玄至道相合,所以不仅其自身实现了极度逍遥,而且在这种连不追求本身也不追求的绝对自然无为的状态下,圣人对于世间万物反而具有生养宰育之功,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成玄英曰:“圣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时,动寂俱妙,凝照潜通,虚怀利物。遂使四时顺序,五谷丰登,人无灾害,物无天枉。圣人之处世,有此功能。”[3](283页)
成玄英笔下的圣人没有生死、穷通的分别,也没有是非、有无的分别,所以能够无为而无不为,无待而无不待,在绝对空寂的深远玄思中体悟到重玄至道的真谛,以灵性与神性的存在方式来代替感性与理性的存在方式,并最终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种妙契重玄的人生境界才真正体现了“圆融无碍”的大道之美。
三、“一中之道”——美育中的重玄之思
成玄英认为人从领悟至道的根性来讲,天生就有着秉赋的差别。“上机之人智慧聪达,一闻至道即悟万法皆空,所以勤苦修学,遂无疑怠。中机智闇,照理不明,虽复闻道,未能妙悟,若敛情归道,即时得空心,絻涉世尘,即滞于有境,与夺不定,故云存亡。下机之人根性愚钝,闻真道玄远,至言宏博,心既不悟,谓为虚诞,遂生诽滂,拊掌笑之”[2](454页)。正是因为人的秉赋相差甚远,领悟至道之美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所以美育教育、也即修炼指导,在成玄英的整个论述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成玄英的美育思想首先是从对世俗审美观的批判开始的。成玄英认为“诸法即有即空,美恶即空,何憎何爱?故庄子云:毛嫱孋姬,人之所美。鱼见深入,鸟见高飞。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以斯所验,岂有美哉?故知世间执美为美,皆则恶而已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2](362页)世俗之美不仅是空美、假美,而且它还是非永恒的,随人的情绪、好恶而发生变灭。所以圣人才要“诱导苍生,令归真实。释散其怀而破嗔疾也”[2](369页)。
作为隋唐之际释道融合的先锋,成玄英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因而毅然摒弃了道教中讲究世俗快乐、享受现世幸福的一面,而力主禁欲。他沿袭老子以来的道家思想对感官欲求的鄙弃态度,不但以佛教空观釜底抽薪地视世俗之美为假美,更从修道的角度指出了执着于假美的危害:“人不能内照真源而外逐尘境,虽见异空之色,乃曰非盲不视,即色是空,与盲何别?”“心耽丝竹,耳滞宫商,不能返听希声,故曰聋也。庄子云:非唯形骸有聋盲,夫智亦有之。”“耽贪醪醴,咀嚼膻腥,不能味道谈玄,故曰口爽。”这些感官的享受以及对“难得之货”的贪欲都“于修道行中大为妨碍”[2](385页)。成玄英从修炼的角度指出:“魂性雄健,好受喜怒;魄性雌柔,好受惊怖。惊怖喜怒损神,故修道之初先须拘魂制魄,使不驰动也。”[2](380页)
然而,“众生欣爱声色,情染极深,如饥人享太牢之馔,悦美色之甚,又如春日登台,眺望林野,畅适其心也。”[2](404页)为了避免尘境对初学者的干扰、诱惑,就必须将自己彻底排除于世俗的审美活动之外。成玄英借鉴佛教的说法,提出了意业净、口业净、身业净的修持方法。具体而言,就是要修道人对尘境和欲望始终保持畏惧之心。“修道学人惧于世境意业,如冬涉川水,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业净”。“又畏尘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邻闾里知闻也,此明口业净”。“学人应须敛励身心,勿得放纵,犹如宾对主不可轻躁,此明身业净”。通过这样对身心欲望的严密防范,“三业已清,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华归实也”[2](392页)。
尽管以强制身心的方式,实现了闭门塞兑,但这毕竟是有心的表现。既然有所恐惧,有所逃避,那么实际上还是被所逃避的对象所束缚,得不到真正的逍遥,所以还是一种滞,不符合重玄美学的要求。“正真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此即妄起攀缘,乃为流动,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虚通,妙绝分别,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性齐,死生一贯,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险而常安临,大难而无惧,故无畏也。今乃起心分别,乖于本心,诸所施为,动之死地,故可畏也。”[2](480页)所以,成玄英重玄美育的下一步便是要消除分别之心。“修道行人必须处心无系,不得域情狭劣,厌离所生,何者?夫身虽虚空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耽爱亦不可厌憎。故耽爱则滞于有为,厌憎则溺于空见,不耽不厌,处中而忘中,乃守真学者也。”[2](520页)有鉴于此,他将无分别作为“治身之楷式”,并称其为“深玄之大德”[2](508页)。从修身的角度讲,要想适性逍遥,便须外忘一身,内忘一心,完全泯灭作为我的分别知见,而成玄英从重玄美育的思路出发,更进一步提出兼忘的思想。不仅要忘身忘心,还要将忘记本身也一并忘记,所谓“筌蹄既忘,妙理斯得”[2](434页)。
通过以上的步骤,遣境遣智,遣去物我分别,使“外无可欲之境,内无可欲之心,恣根起用,用而无染,斯则不闭而闭,虽闭不闭”[2](422页)。可谓得“一中之道”的精髓。最后,成玄英自己在注老中清楚地展示了他美育教育的重玄思路:“众生初从化起修者,必有心欲于果报也,既起斯欲,即须以无名朴素之道安镇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无名之朴,亦将不欲,非但不得欲于有法,亦不得欲此无名之朴也。前以无遣有,此以有遣无,有无双离,一中道也。不欲以静天下,自正静息也,前以无名遣有,次以不欲遣无,有无还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谓探幽索隐穷理尽性者也。”[2](442页)
通过“一中之道”的表述,成玄英为他的美育思想打上了重玄美学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美学之思始终是统一于重玄学的总体思路之下,并始终围绕着玄之又玄的虚极之道展开,呈现出条分理析、层层推进的特点。
总而言之,成玄英的重玄美学以“空”代“无”,解决了老庄滞“无”在美学思维方式上造成的偏颇,他所构造的重玄妙境作为最高的审美境界、人生境界反映了修道者的终极追求,而圣人的妙契重玄更是大道圆融无碍之美的具体展现。同时,作为宗教学家,出于对体道、修道的关注,成玄英在他的著述中始终贯穿了重玄美育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有对道家思想的补偏救弊,也有对传统道教思想的发展创新,充分体现出援佛入老、援庄入老的特点,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涵,对于后来道教思想中哲学思辨色彩的加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受其重视修性的思想启发,道教内丹学也获得了迅猛发展。
[收稿日期]2001-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