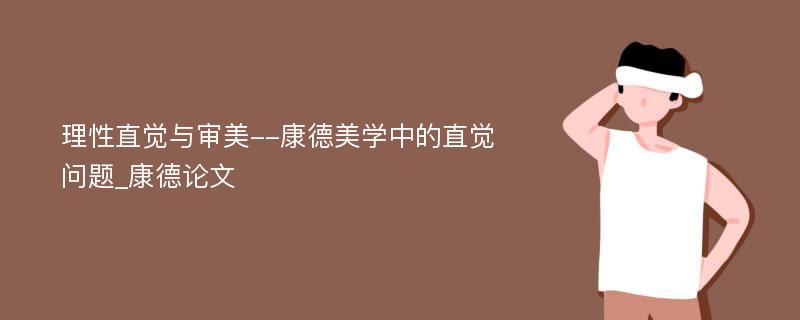
智性直观与审美判断——康德美学中的直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观论文,学中论文,康德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智性直观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于此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康德本人却明确主张,人类只具有感性直观能力,不具有智性直观能力。那么,他的这一范畴何以仍然被后来的哲学家所重视呢?我以为秘密就在康德的美学之中。通过对于审美经验的探究,康德实际上变相地肯定了人类的智性直观能力,并对这种能力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这一范畴的认识论地位。
一
从哲学史上来看,智性直观这一概念并不是康德的发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者,都主张人类具有智性直观或理性直观能力,并且将其视为最高级的理性能力①。那么,康德为什么要颠覆这一传统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只具有感性和知性这两种认识能力,其中感性是被动的、接受性的,知性则是主动的、自发性的。因此,如果知性能够直观,那就意味着知性能够通过自己的直观创造出对象,因为如果对象在直观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知性就变成接受性的了。这就是说,智性直观乃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能力,这种能力显然是人类所不具备的。用康德的话说,“一种知性,假如在其中通过自我意识同时就被给予了一切杂多,那么这种知性就会是在直观了;我们的知性却只能思维,而必须在感官中去寻求直观”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德宣称:“我们的本性导致了,直观永远只能是感性的,也就是只包含我们为对象所刺激的那种方式。相反,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就是知性。”“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只有从它们的互相结合中才能产生出知识来。”③
尽管康德否定人类具有智性直观能力,但却不妨碍他对其做进一步的思考,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能力本身并不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在做出“直观永远只能是感性的”这一断言的时候,特意在前面加了“我们的本性导致了”这一修饰语,也就是说只有对人类这种存在物来说,直观才只能是感性而不能是知性的。反过来,如果一种存在物具有比人类更高级的本性,那就完全可能具备智性直观能力了。那么,人类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康德认为,人类是一种不独立的存在者,它必须依赖于其他现成的存在物才能存在,因此,人类只能被动地直观现成存在物,而不可能主动地创造存在物。反过来,如果一种存在物具备了无限性,那么它就不需要依赖于其他存在物,相反,其他事物却是由它创造出来的,因而也就具备了智性直观能力。正是因此,康德宣称:“这种智性直观……看来只应属于原始存在者,而永远不属于一个按其存有及按其直观(在对被给予客体的关系中规定其存有的那个直观)都是不独立的存在者。”④这里所说的“不独立的存在者”显然是指人类,而“原始存在者”则是指神或者上帝。《圣经》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便是这种智性直观的典型例证。
通过把智性直观归结为神或上帝才具有的直观能力,康德就把这一范畴从认识论之中排除出去了。然而在《判断力批判》中,他的这种立场却发生了动摇,因为他把反思判断力说成是一种智性直观能力。按照他的说法,“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即使它作为先验的判断力先天地指定了惟有依此才能归摄到那个普遍之下的那些条件)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⑤。从这段话来看,反思判断一方面是一种直观行为,因为按照康德的观点,直观就是和对象直接发生关系的能力,既然反思判断是直接从特殊对象出发的,因此当然就具有直观性;另一方面,反思判断又是一种知性行为,因为它不是像感性活动那样只是产生个别表象,而是要寻找某种普遍的法则和规律。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自然就使反思判断成了一种智性直观活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重新肯定了人类的智性直观能力。叶秀山就曾经指出:“我们都知道,在知识论里,康德否认有‘理智性的直观’的存在,因为他从二元论立场出发,认为理智与感觉各有来源,所以知识不可能是绝对的,所谓‘绝对知识’(形而上学)只是一种‘理念’,而‘理念’是找不到直觉作根据的;但是,我们觉得,在情感判断领域里,在鉴赏判断中,在对美的欣赏中,康德应该承认‘理智的直觉’的合法权利。”⑥杨祖陶更是明确宣称:“反思判断力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就是从特殊中去发现普遍,或把普遍本身看做是特殊的,这就超越了他一贯强调的直观与知性的对立,使反思判断力成了一种‘直观的知性’或‘知性的直观’。”⑦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康德本人却似乎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在谈到目的性判断力时指出:“我们的知性是一种概念的能力,即一种推论性的知性,然而对它说来,在自然中提供给它并能够被纳入它的概念之下来的那个特殊的东西可能是哪些以及如何各不相同,这却必须是偶然的。但由于属于认识的毕竟也有直观,而一种直观的完全自发性的能力就会是一种与感性区别开来并完全不依赖于感性的认识能力,因而就会是在最普遍含义上的知性:所以我们也可以思维一种直觉的知性,这种知性不是(通过概念)从普遍进向特殊并这样达到个别,对它来说自然在其产物中按照特殊的规律而与知性协调一致的那种偶然性是不会遇到的,这种偶然性使我们的知性极其难于把自然产物的多样性纳入到知识的统一中来;这是一件我们的知性只有通过自然特征与我们的概念能力的非常偶然的协和一致才能完成的工作,但一种直观的知性就不需要这样做。”⑧从这里可以看出,康德把知性区分为推论的和直观的两种形式,这与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直观区分为感性的和智性的正好相对。不过,康德在认识论中否定人类具有智性直观能力,在目的论中同样否定人类具有直观的知性,这从他把“我们的知性”称作“推论性的”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这里,直观的知性同样不为人类所有,而是属于原始存在者的,因此他又将其称为“原型的知性”。由于知性的直观和直观的知性完全是同一种认识能力,因此认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重新肯定了人类的智性直观能力,显然是一种不应有的误解。
那么,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何在呢?我以为这是由于上述学者把两种不同的智性直观混为一谈了。我们把反思判断力视为一种智性直观能力,这只是就这一概念的传统含义而言的,与康德所赋予它的独特内涵有着本质的差别。在传统哲学中,智性直观指的就是不经思维和概念而把握一般对象的能力,比如柏拉图主张理念或真正的存在是被“心灵之眼”(即理性)直接“看”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矛盾律等逻辑公理是自明的,笛卡尔强调几何学的公理是被精神清楚明白地领会的等等。在这些哲学家看来,智性直观是心灵先天所具有的一种认识能力,它能够使心灵直接领会到许多自明的真理。康德则不同,他认为智性直观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能力,它能够通过直观创造出对象,而不仅仅是把握一般对象。当然,这两种直观能力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着一定的交叉之处。康德认为,智性直观是一种把握本体或物自体的能力:“如果我们把本体理解为一个这样的物,由于我们抽掉了我们直观它的方式,它不是我们感性直观的客体;那么,这就是一个消极地理解的本体。但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非感性的直观的客体,那么我们就假定了一种特殊的直观方式,即智性的直观方式,但它不是我们所具有的,我们甚至不能看出它的可能性,而这将会是积极的含义上的本体。”⑨从这段话来看,康德认为对本体的理解包含两种方式: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本体不是感性直观的对象,因此对人类来说是不可知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本体则是智性直观的对象,因此对神来说就是可知的。就此而言,康德对智性直观的理解与柏拉图显然有一致之处,因此当他宣称人类不具有智性直观能力的时候,意味着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的智性直观理论。
不过,康德的这一立场并不彻底。尽管他认为人类只具有感性直观能力,但他对感性活动的理解较之传统哲学却要宽泛得多,在一定程度上把智性直观也包含在内了。具体地说,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一向把数学或几何学的公理视为直观活动的结果,康德其实也认同这一立场,只不过他认为这种直观是感性的而不是智性的。他认为:“一切有关空间的概念都是以一个先天直观(而不是经验性的直观)为基础的。一切几何学原理也是如此,例如在一个三角形中,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这决不是从有关线和三角形的普遍概念中,而是从直观、并且是先天直观中,以无可置疑的确定性推导出来的。”⑩康德之所以把几何学归结于感性直观,是因为在他看来,几何学的概念和定理所涉及的主要是空间关系,而空间则是他所说的先天直观形式之一(另一种是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并没有彻底否定传统的智性直观,他所否定的只是作为创造性能力的智性直观而已。因此,当他把反思判断力说成是一种智性直观能力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立场。
二
现在的问题是,反思判断力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智性直观能力呢?对于这个问题,康德通过对审美鉴赏的探究进行了解答,因为审美鉴赏一方面是从个别表象(特殊)出发的,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普遍性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普遍性的法则,因此是一种典型的反思判断。
那么,审美判断究竟为自己找到了怎样的普遍性法则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长期困扰着美学家们的理论难题。英国经验主义美学把审美归结为一种趣味,而趣味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很难提出普遍性的要求。所谓“趣味无可争辩”,意味着审美鉴赏只具有相对性,不具有普遍性。休谟就曾明确指出:“在很多能证明趣味的多样性的事例面前,你们双方不仅会承认美与价值都具有相对性,而且会认为它们存在于人的愉悦感之中——这种愉悦感乃是特定的对象在特定的心灵中结合心灵的特定组织与构造而生成的。”(11)在这里,审美鉴赏的相对性是由情感和心灵的主观性和个别性造成的。康德同样认为审美鉴赏与客体及其概念无关,只与主体的情感相关:“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象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12)但他认为审美判断的主观性并不必然导致其相对性,因为主观性并不等于个别性,从主观的情感出发所做出的判断,只是不具有客观的普遍性,但却可能具有主观的普遍性:“一种不是基于客体概念(哪怕只是经验性的概念)之上的普遍性完全不是逻辑上的,而是感性上的,亦即不包含判断的客观的量,而只包含主观的量,对后者我也用普适性来表达,这个术语并不表示一个表象对认识能力的关系的有效性,而是表示它对每个主体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关系的有效性。”(13)那么,审美判断为什么会具有主观普遍性呢?康德将其归结为一种可以被普遍传达的内心状态。在他看来,审美经验由于不涉及概念,因此各种认识能力(主要是想象力和知性能力)就处于一种自由游戏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由这表象所激发起来的诸认识能力在这里是处于自由的游戏中,因为没有任何确定的概念把它们限制于特殊的认识规则上面。所以内心状态在这一表象中必定是诸表象力在一个给予的表象上朝向一般认识而自由游戏的情感状态。……诸认识能力在对象借以被给出的某个表象上自由游戏这一状态必须是可以普遍传达的:因为知识作为那些给予的表象(不论在哪一个主体中都)应当与之相一致的那个客体的规定性,是唯一地对每个人都有效的表象方式。”(14)
然而问题在于,认识能力的游戏状态何以会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呢?事实上游戏所导致的恰恰是一种相对性和个别性的内心状态,因为想象力可以对感性表象进行任意的变形和组合,知性能力则可以把表象与任何可能的知性概念联系起来,比如想象力可以把一朵白云设想为一只绵羊、一堆棉花,知性能力则可以将其当作天气变化的征兆,或者视为空气污染的证据,如此等等。这样一来,主体的内心状态就会变幻不定,何来一种普遍的可传达性呢?康德的解释是,任何知识都必须是普遍可传达的,因此与之相应的内心状态也必须是普遍有效的:“如果知识应当是可以传达的,那么内心状态、即诸认识能力与一般知识的相称,也就是适合于一个表象(通过这表象一个对象被给予我们)以从中产生出知识来的那个诸认识能力的比例,也应当是可以普遍传达的:因为没有这个作为认识的主观条件的比例,也就不会产生出作为结果的知识来。”(15)在这里,内心状态被归结为诸认识能力之间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当各种认识能力形成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才会产生相应的知识。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尽管不会形成关于对象的知识,但却仍旧会出现这种可以普遍传达的内心状态,因为诸认识能力在自由游戏的过程中仍会形成一定的比例。
不难看出,把认识活动或规定判断中的内心状态引申到审美判断当中来,在逻辑上是一个巨大的跳跃。正是为了完成这一跳跃,康德引入了“共通感”的概念。“共通感”本是西方思想中的常用词,指的是一种健全的知性,也就是健全的心灵所共有的知性能力。康德则认为,除了这种健全的知性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健全的感性”或“健全的情感”,也就是健全的心灵都具有的情感反应能力,从而保证健全的主体在面对同一个表象的时候能够做出共同的情感反应,因此就构成了鉴赏判断的普遍原则:“鉴赏判断必定具有一条主观原则,这条原则只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念,却可能普遍有效地规定什么是令人喜欢的、什么是令人讨厌的。但一条这样的原则将只能被看作共通感,它是与人们有时也称之为共通感的普通知性有本质不同的:后者并不是按照情感,而总是按照概念、尽管通常只是作为依模糊表象出来的原则的那些概念来作判断的。”(16)他甚至认为,这种健全的情感比健全的知性更有权利享有“共通感”之名,因为它是真正诉诸感觉的,后者则依赖于常识和模糊的概念。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共通感”究竟是否存在呢?事实上审美判断经常面临各种分歧和争议,人们面对同一个审美对象经常会出现不同甚至对立的情感反应,这似乎表明共通感是子虚乌有的。对此,康德坦率地承认共通感的理念是一种主观的预设,并无任何客观的依据。但他认为,这种预设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先在的理念,主体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就可以预先使自己处于他者的位置,从而消除个体差异对判断普遍性的影响:“人们必须把共通感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感觉的理念,也就是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这种评判能力在自己的反思中(先天地)考虑到每个别人在思维中的表象方式,以便把自己的判断仿佛依凭着全部人类理性,并由此避开那将会从主观私人条件中对判断产生不利影响的幻觉,这些私人条件有可能会被轻易看作是客观的。做到这一点所凭借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判断依凭着别人的虽不是现实的、却毋宁只是可能的判断,并通过我们只是从那些偶然与我们自己的评判相联系的局限性中摆脱出来,而置身于每个别人的地位;而这一点又是这样导致的,即我们把在表象状态中作为质料、也就是感觉的东西尽可能地去掉,而只注意自己的表象或自己的表象状态的形式的特性。”(17)不难看出,康德在此求助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感性论思想。按照他的说法,“在现象中,我把那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质料,而把那种使得现象的杂多能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形式”(18)。这也就是说,表象是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质料诉诸感觉,因而必然导致个体差异;形式则是主体先天的直观能力,因而不存在个体差异。主体在进行审美鉴赏的过程中,只要排除构成审美对象的质料因素,只关注对象的形式,就可以消除审美判断的个体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判断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直观能力。由于它的对象是被给予的感性表象,因此不同于神才具有的创造性的直观能力;同时,它所寻找到的普遍原则又只具有主观性而不具有客观性,因此也不同于传统哲学所说的智性直观。总之,审美判断力只是一种反思能力而不是认识能力,它只能用来把握主体自身的内在机制,而无法获得关于外在世界的客观真理。康德把审美鉴赏归结为这样一种纯主观、纯形式的反思能力,就使审美经验丧失了任何把握真理的认识功能,同时也使他的美学染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色彩。
三
如果反思判断只具有这样一种主观的反思功能,不具有客观的认识功能,那么它就无助于确立智性直观在认识论上的地位,因为自古以来,智性直观就被看作一种高级的认识能力。不过正如朱光潜所说,“在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中没有哪一部比《判断力批判》显示出更多的矛盾,也没有哪一部比它更富有启发性”(19)。我们认为,这种矛盾性和启发性在他对审美判断的理解上有着集中的体现。正是通过这种内在矛盾,康德揭示出了反思判断力的多重内涵,从而为确立智性直观的地位铺平了道路。
按照康德的定义,反思判断应该只涉及个别表象而不涉及概念,因此它只能通过反思寻找到某种主观的普遍原则,而不可能通过认识获得任何客观知识。然而在对审美判断的分析中,他却发现审美对象经常是与概念相关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把审美对象划分为两种类型:“有两种不同的美:自由美,或只是依附的美。前者不以任何有关对象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为前提;后者则以这样一个概念及按照这个概念的对象完善性为前提。前一种美的类型称之为这物那物的(独立存在的)美;后一种则作为依附于一个概念的(有条件的美)而被赋予那些从属于一个特殊目的的概念之下的客体。”(20)不难看出,这种划分的依据就是美与概念的关系:自由美与概念无关,依附美则与概念相关,因此,自由美是纯粹的,依附美则是不纯粹的,前者在审美价值上必然高于后者。问题在于,康德所说的自由美在审美经验中是极为罕见的,他能举出的例子只有花,自由的素描,无意图地互相缠绕、名为卷叶饰的线条等寥寥几个,除此之外的所有审美对象都或多或少与概念相关,因此都只能归属于依附美。更重要的是,自由美的审美价值实际上远远低于依附美,因为任何具有健全的审美修养的人,都不可能不承认一幅自由素描的价值抵不上一幅经典的画作,装饰性的线条只有与特定的含义结合起来,才能具备真正的审美价值。康德自己也把美的理想说成是人的形象,却又认为这种美不是纯粹的而是依附的,也就是说,理想的美竟然只具有较低的审美价值,这岂非咄咄怪事?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清楚地说明康德划分审美对象的标准是站不住脚的,毋宁说他颠倒了审美对象的等级:真正的美恰恰是与概念相关的,至于那种与概念无关的自由美,只具有附属性的意义而已。
事实上,康德自己也在不断地偏离原有的立场。他在美的分析部分坚持美与概念无关,但在崇高的分析部分却宣称:“美似乎被看作某个不确定的知性概念的表现,崇高却被看作某个不确定的理性概念的表现。”(21)这里的知性概念和理性概念之所以被说成是不确定的,是因为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并不与某个确定的概念相关,而是与某种不确定的一般概念相关:“正如同审美的判断力在评判美时将想象力在其自由游戏中与知性联系起来,以便和一般知性概念(无需规定这些概念)协调一致:同样,审美判断力也在把一物评判为崇高时将同一种能力与理性联系起来,以便主观上和理性的理念(不规定是哪些理念)协和一致,亦即产生出一种内心情调,这种情调是和确定的理念(实践的理念)对情感施加影响将会导致的那种内心情调是相称的和与之相贴近的。”(22)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一般概念”,也就是未做具体规定的概念。康德认为,这种不确定的概念同样可以唤起主体的某种内心情调,从而赋予审美判断以普遍性。
对于自身立场的这种矛盾,康德其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他思想的内在矛盾,而是审美判断的二律背反特征的体现,矛盾的丽个方面其实是审美判断的正题和反题:“1)正题。鉴赏判断不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因为否则对它就可以进行争辩了(即可以通过证明来决断)。2)反题。鉴赏判断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因为否则尽管这种判断有差异,也就连对此进行争执都不可能了(即不可能要求他人必然赞同这一判断)。”(23)他为这个二律背反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正题和反题中所说的“概念”其含义是不相同的:前者是指确定的概念,后者则是指不确定的概念,也就是说,审美判断虽然不以某个确定的概念为依据,却要以某个不确定的概念为依据,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无论这个解释是否能够令人满意,其关键之处在于康德明确承认审美判断是以某种不确定的概念为依据的。那么,究竟什么是不确定的概念呢?康德认为就是指“关于现象的超感官基底的概念”,也就是某种超验的理性概念。理性概念之所以是不确定的,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可规定的:“鉴赏判断必须与不管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发生关系;因为否则它就绝不可能要求对每个人的必然有效性。但它又恰好不是可以从一个概念得到证明的,因为一个概念要么可能是可规定的,要么可能是本身未规定的同时又是不可规定的。前一种类型是知性概念,它是可以凭借能够与之相应的感性直观的谓词来规定的;但第二种类型是对超感官之物的先验的理性概念,这种超感官之物为所有那些直观奠定基础,所以这个概念不再是理论上可规定的。”(24)这样一来,康德的意思就变成:审美判断虽然不以知性概念为前提,但却是以理性概念为前提的。
理性概念何以会成为审美判断的前提?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说过:“我把理念理解为一个必然的理性概念,它在感官中是不能有任何与之重合的对象的。”(25)这也就是说,理性概念根本不可能转化为被直观的感性对象。然而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却认为艺术天才的想象力能够把理性概念感性化。按照他的说法,“诗人敢于把不可见的存在物的理性理念,如天福之国,地狱之国,永生,创世等等感性化;或者也把虽然在经验中找得到实例的东西如死亡、忌妒和一切罪恶,以及爱、荣誉等等,超出经验的限制之外,借助于在达到最大程度方面努力仿效着理性的预演的某种想象力,而在某种完整性中使之成为可感的,这些在自然界中是找不到任何实例的;而这真正说来就是审美理念的能力能够以其全部程度表现于其中的那种诗艺”(26)。想象力为什么会具有这种神奇的功能?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对此做过一定的探索。在他看来,想象力能够把先验的知性范畴转化为可以直观的图型,从而使其能够与感性表象统一起来。不过,他特别强调图型与形象不同,因为形象具有空间特征,图型则只具有时间特征,这意味着想象力并不能真正把知性概念感性化。在《判断力批判》中,他的这一立场则发生了改变,因为在他看来,天才的想象力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创造性的,这就使其能够把超验的理性概念转化为可直观的感性形象。
当然,这是就艺术创作而言的,对审美鉴赏来说,则意味着审美表象可以反过来被看作理性概念的象征。康德认为,图型和象征乃是把先天概念直观化的两种方式:“一切我们给先天概念所配备的直观,要么是图型物,要么是象征物,其中,前者包含对概念的直接演示,后者包含对概念的间接演示。前者是演证地做这件事,后者是借助于某种(我们把经验性的直观也应用于其上的)类比,在这种类比中判断力完成了双重的任务,一是把概念应用到一个感性直观的对象上,二是接着就把对那个直观的反思的单纯规则应用到一个完全另外的对象上,前一个对象只是这个对象的象征。”(27)在这里,康德把图型看作对概念的直接演示,象征则是对概念的间接演示。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图型所演示的乃是知性概念,因此可以做经验的运用;象征所演示的则是理性概念,没有任何经验对象能够与其完全符合,只能借助某种经验对象来加以类比,因此必然是间接的。
通过把审美对象看作理性概念的象征,康德就把理性概念引入了审美判断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审美判断不再是纯粹的反思判断,而是包含着规定判断的某些因素,因为审美判断看起来是从个别表象出发的,但这表象却同时是理性概念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审美判断为自身寻找到的普遍性原则,就不仅仅是主观的内心状态,同时也是客观的普遍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审美判断反过来变成了规定判断,因为在审美判断中被把握到的理性概念,并不是由知性自发地生产出来的,而是通过直观被给予的。然而无论如何,这都表明审美判断并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反思能力,同时也是一种客观的认识能力。沿此思路推论下去,就会通向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和本质直观理论,因为如果理性概念可以通过直观被给予,那么知性范畴就同样可以成为直观的对象。因此我们认为,康德对于审美判断的分析尽管是一种美学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为智性直观在认识论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当然,这里所指引的还只是康德与胡塞尔在直观学说上的关联,实际上康德关于创造性想象力的理论,直接促成了费希特和谢林的智性直观理论。
注释:
①有关智性直观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演变过程,可参见邓晓芒《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载《文史哲》2006年第1期)以及倪梁康《“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思想中的不同命运》(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2期)。
②③④⑨(18)(2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第52页,第50页,第226页,第25—26页,第278页。
⑤⑧⑩(12)(13)(14)(15)(16)(17)(20)(21)(22)(23)(24)(26)(27)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第261页,第29页,第37页,第49—50页,第52—53页,第75页,第74页,第136页,第65页,第82页,第95页,第185—186页,第186页,第159页,第200页。
⑥《叶秀山文集·美学卷》,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728页。
⑦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11)大卫·休谟:《论道德与文学》,张万利、张正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19)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