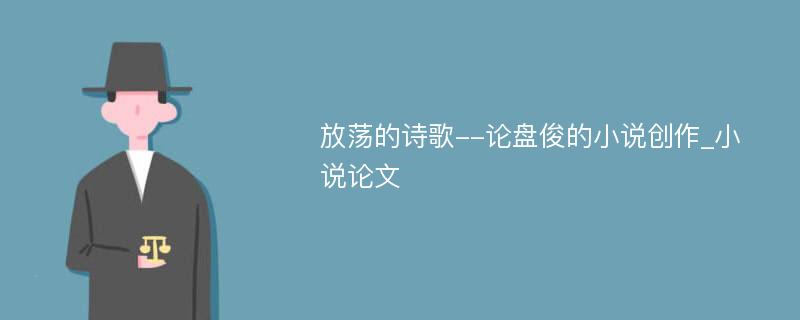
恣情的诗意——论潘军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意论文,小说论文,潘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1)01-0078-05
潘军在1980年走向文坛之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现代派色彩,但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小镇皇后》、《篱笆镇》、《墨子巷》、《红门》等不少中短篇小说的格局基本上没有跳出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们的圈子。现实主义是其创作的底蕴。只是到了中篇小说《白色沙龙》才出现了转机,透出了令人欣喜的灵气和神韵。而长篇小说《日晕》则已完全摆脱了现实时空的限制,任凭作家自由驰骋,思绪跳荡而散漫,但“跳荡而不飘忽,表面看似散漫而有着内在隽永的韵律”。(注:唐先田:《长篇创作的新尝试:评潘军的〈日晕〉》,《清明》1988年第3期。)
潘军在1993年是一位先锋派小说家,在当年的《钟山》的先锋派小说大展中,他就是重要的一位。他的小说浸染着先锋派,特别是新历史小说的叙事色彩。
对于历史的叙述,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对历史的记述,如《三国志》,它尽量保持与历史本相的一致;另一种则是对历史的“演义”,用某种观念来重新阐释过去曾经发生的事实;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则以“历史趋势”来叙述与构想历史,所以历史于是成为一个符合“趋势”的因果前定的链条。作为先锋派小说家的潘军在叙述历史时对既有的历史叙述法采取了非常明显的反叛的姿态,如同对待“黔之驴”一样的嘲讽和戏弄的态度,他总是尽量使“历史”(真实-本事)与叙述分离,证明了历史不仅仅是“历史”本身,而且也是一种叙述的结果,而正是多视角的叙述(主体)使历史离开真实越来越远,真相越来越成为永远不可谛视的永恒之谜。能指碎片或者说本文之网,“延异”了可能隐藏的意义,本文成为纯粹的能指游戏,“语言主义”分散了或者说消解了中心,这样的文本操作体现了先锋派对于“习惯”中的语言之后的意义的怀疑甚至谋杀。长篇小说《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的故事由现实、回忆、想象三块组合而成,依照惯常的叙述,这三块最后应当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意义,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谌容的《人到中年》都是多视角叙述,但始终是围绕一个中心,或者说是在确定一个“事实”。但潘军在文本中把应该被确定的“英雄”一再置于被“疑问”的处境:叶家有两个少爷都可能是英雄“郑海”,但打开英雄的墓,却发现棺材里有六根指骨,分明是叶老爷的义子六指。确定的“意义”在此被以疑问的形式延迭。前来给墓碑揭幕的专员林重远自称是“郑海”的战友;既然“郑海”可能是子虚乌有,那么这个“战友”又从何而来。“意义”再次被抛出叙述之外。故事接下去更是离奇:在青云山上,林专员遇见了一个老樵夫,他们一见如故,便常常在山上的亭子里下棋,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就是当年的叶家兄弟。几天后,人们发现林专员死了,老樵夫也从此消失了。“郑海”的墓碑一夜之间被铲平,成了一块无字之碑。“意义”至此被彻底埋葬。所指就这样不断被提及,但最终却没有明确的指向,文本也因为脱离所指而成为叙述游戏。
历史是什么?潘军在写作《流动的沙滩》时,曾引用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克洛德·西蒙的一段话作为题记: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我们始终是在流动的沙滩上行走。他似乎告诉你,历史就是那种确实存在的但又是不可确知的宿命般的悬念。它在发生作用之前会给你暗示,但真正发生的时候还是令你措手不及、令你不可思议、令你心惊胆颤。人作为主体却被那种神秘的力量主宰,这不但让人沮丧而且让人恐惧。恐惧是人的本能之一,它是存在的本质。当叔本华在讲述“西西弗斯神话”时,他所传达的不仅仅是人的韧性而且更是人对于被控制的刻骨铭心的恐惧。《和陌生人喝酒》(《上海文学》1998年10月号)中仍然笼罩在这种神秘的气氛中,陌生人A的婚姻波折是通过他的自述、我的转述、她的证实和我的亲眼所见来逐段展开的。在这展开的故事中,阅读者最急于了解的是主人公离婚的真实原因,这构成了作品的情节,但同时这正是作品所播散的焦虑情绪的集中所在。他的离婚的真实原因被一再地“落实”,但在每一次落实的当下,阅读者就马上感觉受到了欺骗,因为那还不是“历史的真相”,真相一再地被“迁延”,那导致A夫妻离散的两张交响乐的票到底是谁送的?“很长时间以后,我突然明白了许多。我想这件事做起来并不难,而且做事者早已是胸有成竹了。或许这就不是个玩笑”。那么,是否是那个最终和A共结连理的大提琴手呢?同样是不得而知。“真相”被掩埋了,而且可能永远不会被揭示。真相永远不可被确知,人的言说可能每一次都接近,但每当接近时却发现接近的并不是“真相”,而是一个新的假象。当真相不可被确知的时候,所有的对真相的言说都成为了语言游戏。当人的两脚总是蹈在虚空中,你还能宁静而安详地活着吗?当历史被虚无化的时候,人的存在难道不是一场荒诞?这个短篇小说与长篇《风》保持着一致的叙述格调。这种历史怀疑主义和对叙述形式的迷恋即使在风格有所改变的后来也一直被保持着。
这样的叙述与日本导演黑泽明的影片《罗生门》和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采取了同样的叙述策略:通过摇镜头式的动荡不定的叙述,不断地变换叙述视角,使故事彼此交叉,又彼此消解,割裂叙述与深度意义之间的联系,使故事本身呈现出神秘莫测和闪烁不定的“故事本能”,一座让读者头晕目眩的结构迷宫。而历史/真相因多种可能性的呈现,而被拆解,分割,且只停留在可能性阶段,或部分真实阶段。阅读主体只能窥见“部分”,当他因此而迷惑或无所适从的时候,正好承认了作者的“历史不可知论”。
这样的能指游戏,揭示了被“习惯”了的叙述背后的所隐含的真理。这样的叙述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红色古典主义”时期的“中心主题论”和故事因果链及其对阅读主体的强迫性主宰的强烈反拨,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也诱导阅读主体参与历史和思考历史。同时,陌生化和对交流的拒绝,不但拓展了艺术和读者的想象空间,也非常确切地传达了现代主义的生存理念。马尔库塞说:“艺术有义务让人感知那个使个人脱离其实用性的社会存在与行为的世界——它有义务解放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一切范围的内心的感觉、想象和理智——有了那种自主性才能使艺术脱离既定事物的欺骗力量,自由地表现它自己的真实。因为人和自然是由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构成的,它们被压抑、被扭曲的潜能只能以一种具有疏隔作用的形式表现出来。艺术的世界是另一个现实原则的世界,是疏隔的世界——而且艺术只有作为疏隔,才能履行一种认识的职能:传达任何其他语言不能传达的真实;它反其道而行之。”(注:潘军:《基调与意味》,《上海文学》2000年8月号。)潘军和先锋小说拒绝文本与阅读的交流,正体现了他们对于生存“疏隔”的理解。
至1997年,潘军仍然喜欢在文本中设置“谜团”,仍然喜欢用第一人称“我”自由自在地叙述故事,仍然喜欢设置精巧的结构。但显然,他已经没有了当初操作结构游戏的热情和沉浸游戏中的那份愉悦了。中篇小说《三月一日》(《收获》1997年第3期)是作家表达游戏疲累的作品也是他走向写实的过渡性的文本。这是一篇典型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梦的解析”。三月一日“我”在城市里失去了做梦的能力,却具有了窥视别人梦境的能力。究其原因文本语义上起源于一次“突然事件”——车祸。在事件中,“我”获得了意外的快乐,但更不得不接受被一切人排除在外的焦虑。这是“局外人”的孤独和清醒。窥视是城市的功能化和物质化压抑之下的结果,而要重获做梦的能力、流泪的能力,一句话人的能力,唯一能够救赎的惟有那记忆中的“风筝”,但风筝就在“我”异化——被汽车撞死——的时候也死了。“我”的假死与风筝的真死,看上去是宿命的因缘巧合,但正是这种“巧合”揭示了其中的必然联系,记忆中的田园爱情的死亡,才使人彻底丧失了人之性。“我”在旧地重游中找回了旧梦,也重获做梦的、流泪的能力,摆脱了在现实中做人的尴尬,但记忆可以救人于一时,还可以救人于一世吗?风筝的没有翅膀,暗示了一个必然的忧伤的结局。被作家在《风》中所摒弃的叙述的中心——意义,终极关怀重又回到他的文本之中。文本的样式是卡夫卡《变形记》式的,但潘军只走了现代主义的“前半生”,他把“后半生”留给了沈从文,留给了中国式的伦理乌托邦。
《秋声赋》(《花城》1999年第4期)在叙事上更趋于平实,几乎没有了《风》中的激进的叙述花样。它是一个大体的戏仿乱伦结构,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故事,小说一开始就利用安徽土语爹爹和北方话爷爷之间的语义模糊(北方话称祖父为爷爷称父亲为爹爹,而安徽土话却正好相反)设置了一个“谜团”,暗示主人公旺可能在伦理上出现的混乱。情节果然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潘军就如同他一贯的做派一样,设置线索让你向那个向度展开你的思索,但至最后总是让你的想法落空(这一点还保持着1993年代的顽皮和狡猾)。他让主人公在爷爷与爹爹的角色中历险,最终却让主人公回到伦理所赋予的角色责任上。这种“逆转”说是意料之外,但对于经常读潘军小说的读者来说,却又在意料之中。他总是在具有刺激性的题材的边缘游荡,但终究还是要匡扶他的“思无邪”的道德准则。他的叙事也由最初的“不可信任”而走向平实和“可信”。
引起较大反响的中篇小说《重瞳》(《花城》2000年第1期),潘军对“历史”——被书写的历史如《史记·项羽本纪》一如既往地持怀疑态度。它通过项羽的自述,来叙述故事。由于是自叙形式,它能够很好地深入内心发掘人物心灵的“真实”,对历史进行还原。这里的叙述人项羽,他是历史全程的在场者,使主人公既在当时又在现在,一种全知视角,和历史时间和当下时间的对照使作品呈现出历史反思的特点。叙述人项羽,担任着角色和叙述者的双重责任。但这种讲述方式与此前的长篇小说《风》是同样的,“项羽”与“我”都是隐含的作者,读者很容易看出作者的意图。只不过,由于题材的限制,《风》讲述的当下时段的故事使作者可以以“我”直接参与,而《重瞳》讲述的是过去时段中的故事,“我”要成为角色之一已不大可能。因此可看出潘军叙述的特点,“我”,隐含的作者尽量参与故事,并成为其中的角色,而不喜欢以纯粹旁观者的姿态叙述。就是《秋声赋》中的叙述人“我”已经被抽干为完全的平面皮相,但仍然存在于文本之中。现代主义文学对自我的迷恋在潘军的小说中可见一斑。潘军尽管通过叙述人“项羽”表示了对历史/既存的书面或口头历史的怀疑,但与《风》显著不同的是他却给出了一个确定的“历史”,《风》只将“历史”/真相消解,对它的重建并不在意,而在此历史却已显山露水,历史当事人的直接叙述,实质上已经重构/重建了“历史”。
这种在焦虑之中的重建欲望在潘军的2000年的创作中越来越强烈了。话剧剧本《地下》(《北京文学》2000年第1期),在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诞时空中展开故事,地震后的倒塌的大厦里的两组人物:一对不是夫妻的男女,两个同一单位的同事。一对男女在现实中婚姻各各不如意,当环境被压缩后在一种“假名”的情况下,慢慢化解了现实/地上的人与人的隔阂,产生了美好的感情;同样一老一少两个同事之间,现实/地上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经过地下的被迫交流,相互解除了“代沟”。当他们被救出时,人们不禁要留念地下的生活。这部话剧的结构和风格都极其类似于1980年代的实验话剧,诸如《两个人的车站》《WM》。剧本的结构是现代主义的,但表达的倾向却是古典的。作品的结构很精致,但缺乏潘军此前小说叙述的灵气和才气。这部作品结构形式是荒诞的,但有着很明显的人文关怀,即对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关注。也就是说作品的价值倾向被指向了一个“中心”,一个确定的中心。特别是在这一文本中露出了在《秋声赋》中业已存在的、在《坦白与手势》中被扩大的那种为了消解焦虑和安慰灵魂而表现出的“和解”的愿望。这种和解是“十八岁离家出走”的先锋派对于“家”的回归,是对于父亲、母亲以及情人们所在的故乡的再体认,是对于那种温柔善良和残忍无聊的文化的再次融入,更是对于浓缩了这一切的历史文化的作为过来人的宽宥和承认。
潘军的小说在文本的表层有着一股放荡不羁的作风,他任意地玩弄历史,别出心裁地拆解和组合文本,有时甚至企图借助图片来参与故事的叙述,如《坦白与手势》;他的语言在一些时候是玩世不恭的,甚至是粗俗的;但这正是他的浪漫的诗意所在,它极其生动地传达出了一个负才傲气的当下知识分子的狂狷的个性。在潘军狂荡不羁的作风中蕴含着他对现实/历史和生命的感悟和省察:忧虑中的及时行乐,狂欢中的惊悸和震颤。他的《风》《流动的沙滩》《结束的时候》和《南方的情绪》等一批作品具有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故事摇曳动荡,而语体却在透明中包孕着无尽的张力。而他的更多的创作却一直处于“现代主义”与“可读性”之间(他自己称之为“两套笔墨”),处于清晰与模糊之间,处于顽皮戏谑与诚挚深刻之间,视野开阔、恣意纵横但又不失绳范,轻松嬉戏的语言却极寓穿透力和隽永的诗意,具有现代主义的探索精神而又不乏古典的情怀,喜剧式的叙述中有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历史沧桑感。而如《小姨在天上放羊》《去茂名的路上幻想一顶帽子》等篇,篇幅短小却有诗一样的意境,把一些令人失望和感伤的故事叙述是美妙得让人感动。特别是《三月一日》和《重瞳》将变幻不定的故事举重若轻地落足于典雅的意象“风筝”和“虞美人”上而又如蜻蜓点水般轻盈,真是风流尽得。他在这些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所“拍”下的“生活点滴”很有惊鸿一瞥的艺术效果。正像他对电影的理解一样,“他的每一个设计都非常的精致和不同凡响,但看上去又那么漫不经心,以致于你很难找到雕琢的痕迹”。(注:马尔库塞:《美学的方向》,转引自绿原译《现代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潘军的小说显然是一种主观化的作品,他习惯以自己的视点来加以观察。在他的小说中,这种称作导演主观视点的角度通领了全局。但他的作品又明显打着纪实的烙印。他的叙事是主观叙事,流露的却是纪实风格。在叙述的时候,如一些评论家所发现的,他从不做专门的心理或景物描写,而是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将主体的情绪化入叙述语言和作风之中,在一种漫不经心之中达到风度最调谐状态。
从上述的潘军小说的编年式解读来看,作家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文体/语言叛乱到回归传统叙述的过程。这也与当下的先锋小说的创作趋向是一致的。先锋派的领袖人物余华自从《活着》发表后,又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几乎是义无反顾地走回了终极关怀的意义中心之中。潘军也不例外。他的叙述出现了平实化的趋势,《坦白和手势》的《蓝》《百》两卷就是这样的文本,虽然他仍然醉心于虚构/荒诞时空的设置,同时他的平实之中却化入了现代主义的叙事因子。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见到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的影子,但中国的现实主义精神仍是他的底蕴;这样不但使他的故事好读,同时也使他的作品获得了现代主义的深度,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结构上的。汪晖在评价余华时曾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我还很少见到有作家像余华这样以一个职业小说家的态度精心研究小说的技巧、激情和他们所创造的现实”。(注:汪晖:《(余华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序言》,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潘军也是这样的一个职业小说家的写作态度,他认为“文学是生活的需要”,(注:潘军:《坦白——潘军访谈录》,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文学有着赤子之心,在创作中对小说结构的“漫不经心”中的精心营构,对语言的“看似无意”的推敲锤炼,对小说诗意的醉心,都使他显示出职业作家的老练和专业精神。对于潘军可以这么说:他算不得先锋小说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他确实是先锋小说告别仪式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正因为潘军的创作,才使先锋小说没有显得那么草草收场,而有了一个辉煌的结局。
收稿日期:2000-0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