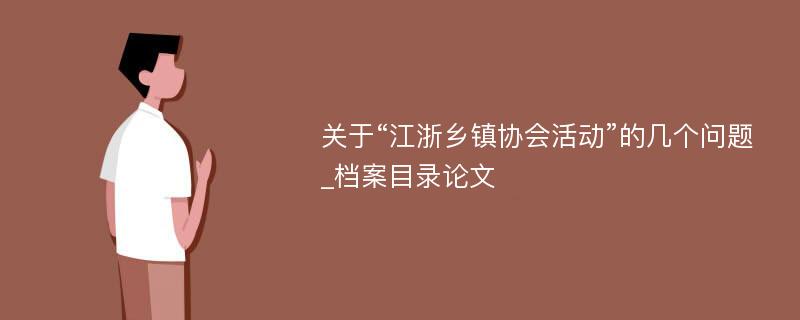
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乡会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江浙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秋到1928年夏发生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从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开始,被人为地发展成一个政治事件,不但波及到各学校的领导、联共(布)中央监委、当时在那里的中共代表团、共产国际,一直惊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最高领导,最后由联共(布)中央监委直接出面干预并作出明确的决议。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决议并未得到尊重和执行。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和中共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中,留在苏联的继续受到政治迫害,回到国内的则成为王明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的真实经过和有关机构的处理,史学界已有人作过论述,此不赘叙。本文对该事件的几个问题再作些探讨。
一、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起因
所谓“江浙同乡会”这个组织是根本不曾存在的,但是这一事件无疑是存在的。如果给这个事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不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起以完全莫须有的组织,即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中国学生为审查对象的、人为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完全是由于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生中一些无原则纠纷,被其中一些宗派意识浓厚的人加以利用,恶意攻击,然后被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有关领导大肆渲染,最终酿成为一起骇人听闻且后果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第一,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生的情况,尤其当时苏联的政治环境都是非常复杂的。中国学生的来源十分复杂,除了共产党派遣的之外,还有国民党、冯玉祥、私人或者团体派来的,甚至还有张作霖派来的。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倾向。当时苏共党内的“反派别斗争”正激烈地进行,很多学生也开始用联共(布)式的政治斗争方式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他们所在的学校管理混乱,某些领导(例如米夫)水平低下,作风恶劣,加上当时生活的困难,在学生中出现很多矛盾和纠纷。此外,当时中国革命正发生急剧历史性的转折,1927年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的失败在中国学生中引起的震动和困惑是可想而知的。当时联共(布)中央监委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曾作了深入的分析:这些中国学生太年轻、很多人原来是团员或国民党员,他们到苏联以后才加入共产党,社会成分不一、地方主义和乡土观念严重、中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建设历史短、中国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中山大学(即中大)原来斗争历史复杂以及学校党的工作太弱、拉狄克任校长时期学校工作混乱、学生生活困难等等。他认为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源是“中国学生中间为争夺影响的各派相互的斗争”(注: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495,目录154,卷宗343。)。
第二,当时在苏联(主要是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出身经历和个人素质各不相同,有的是有高度党性的久经考验的中共早期领导干部,但更多的人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地方观念;有的是大学教授,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学校的政治工作和管理都很不到位,许多消极现象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进一步发展和流传,以致过去所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某些人身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良作风,如派别林立,拉山头,明争暗斗,热衷于逢迎巴结上司、打小报告、追逐名利,这种情况在中大和东大十分严重。这里只引用方绍原1928年7月31日写给项英的一封信来说明。那一天项英去给学生们作报告,他趁机写了这封信并请项英转交中共中央代表团。信中说:“我自抵莫都之后,几及一载,除了从书本中和教室内学得一点理论之外,其余对党的生活,同志间的关系,只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拉拢,互相攻讦,互相猜忌,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好者所不屑有的行动,而我们的同志居然行之若素,毫不以为可耻。此种现象,在孙、东两大里,盖已成为狠(很)普遍的公开的秘密了。”这里的同志关系“向如一盘散沙,毫无党的整个利益的结合,只有利用封建式的私人情意的联络”。(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
第三,中国留苏学生中的纠纷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酿成这样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其直接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的学校领导(主要是米夫)听信少数派性严重的学生的诬告,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处理中国学生中的内部矛盾,从而使无原则纠纷政治化,激化了学生中的矛盾。米夫自己也承认,在接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处负责调查这一事件的美尼思的情报和一些中国学生的告密信后,他没有将这些情况通知有关部门就擅自处理,并在中大的全校党员大会上作了“严重的报告”,把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定性为“反党”、“反革命”的“派别活动”,从而在学生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二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处在对这一事件所进行的调查中,根据未经证实的材料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并据此对有关学生作了开除和遣送回国的错误处理。许多学生不服,连续上告到中共代表团、联共(布)中央监委和共产国际,直至苏联的最高领导斯大林、莫洛托夫,致使事情越闹越大。三是当时在苏联的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向忠发迁就由他和米夫煽动起来的在学生中反“江浙同乡会”的过激情绪,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把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当事实来处理,武断地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二、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的组织
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在反对者的一片讨伐声中变得神乎其神,似乎它的组织“比中国共产党还健全”,有人甚至在匿名的告密信中列出了一张“组织系统表”:最高机构是“中央干事会”,下设“宣传部”、“组织部”、“宣传煽动部”,还有“军事组”、“侦探组”、“翻译组”和“交通组”,各校都设有支部,还注明了联络的详细地址及负责人的名字。这个组织同第三党、蒋介石、冯玉祥以及联共(布)的“反对派分子”都有联系,有多渠道的经费来源。而且还详细说明了它的四个阶段的“工作计划”、八条工作方法,还有“反第三国际的理论”等等。在有的告密信中甚至列出了各部门的负责人名单。笔者从档案中看到许多份不同的“江浙同乡会名单”,其中最多的一份竟列出了129人的名字,而有的文献甚至说这个组织的人数有150多人。在这份名单中有“正式会员”、“名誉会员”,还有“同情者”,而且其成员早已经超出江浙两省的范围,例如被诬为“同乡会”骨干的周达明是贵州人,陈启科和左权都是湖南人。最莫名其妙的是,从所看到的文件中还出现了两个朝鲜人的名字。(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6。)
那么,这样一个严密的组织到底是否存在呢?在笔者所查阅到的大量档案资料中,无论是从当时的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中国学生的申诉、诬陷者的告密材料,还是大量的会议记录和调查、有关领导机关的正式决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都无法证明这个组织的存在。
首先,在笔者所看到的几十份署名或者不署名的告密信中,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的存在。这里举出一份揭发这个组织详细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计划的告密信为例可以说明。这封6页32开纸的信,密密麻麻用蓝色钢笔写满了中文蝇头小字,它既无署名也无日期。作者在信的最后附有这样一个“声明”:“这个书面的报告是我亲自直觉(接)的或间接得来的材料,关于间接材料的一部分,我只可以负责使我自己相信,但我不能在公开方面对于这部分消息负责,希望对于以后有人直接送来的消息,则还是与直接知道消息的人问谈,这样对于工作进行上较为有效,因为这是群众方面知道的消息,在事实上很难确定到底是谁说出的谁看出的。”可见,这个写告密信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否存在。更可笑的是,还有一个署名“无名氏”的举报人,看见一个“同乡会员”正在抄一本小书,是“工作计划”,他看到有很多条文,而且许多“同乡会员”都轮流在抄。后来的一天,“当着一个学生如获珍宝似的拿给了米夫”,以为破案的证据总算拿到了,可是翻译一看,原来是1926年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3。)
其次,1928年6月5日向忠发和苏兆征代表中国代表团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也没有拿出任何确凿的证据说明这个组织的存在。8月3日雅罗斯拉夫斯基质询米夫:“你认定在中大有互助会的组织吗?”米夫答称“我不肯定”(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7。)。8月17日,就连坚持不同意撤消这个案件并参与处理这一事件的苏兆征和周恩来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也只是要求对陆贻松致周策、胡士杰、朱茂榛的信,周策致胡士杰和刘仁寿等人的信进行核实,因为这是能够证明该组织存在的“严肃的文件”。但是他们承认,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多月,“这个组织到底是有还是无,谁也不知道”。还承认“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这个组织和国民党、第三党及反对派的联系。(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米夫本人6月在中大讲话时也矢口否认了“江浙同乡会”组织的存在。
第三,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在前面所引的《报告大纲》中,他明确指出,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对这些中国学生提出来的罪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和第三党或国民党的关系,最主要的证据就是蒋经国收到家里的汇款问题,许多揭发材料都说蒋经国和他父亲之间依然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家里先后给他寄款达6次之多,总计从那里领得1000多美元的款项。为了了解这方面的事实,雅罗斯拉夫斯基把蒋经国等人找到联共(布)中央监委单独谈话,他们全都否认同第三党和国民党右派有任何联系。蒋经国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到,他的母亲确实给他寄过300元钱,但这是在1927年他同自己的父亲蒋介石的关系破裂之前的事,他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政治意义。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报告大纲”中指出,“关于这个会的组织上之存在是绝对没有确实证明的,也更无材料可以证明它现在仍然存在”。“我敢断定,谁也没有看见章程,章程是没有的……这些同志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许多材料所“根据的都不是事实,而是猜想、谣言和不正确的报告”。他甚至激动地质问道:有人说,“江浙同乡会”的组织机构比中共都健全,“根据在哪里?一点都没有!”最后他还气愤地加了一个“附注”说:中国人动则用“同蒋介石有关系”来骂反对他的人,“应当用党的名义宣布停止这些事,不论是哪一派的同志,他都要对党负有严格的责任”。
第四,近年来出版的大量资料和回忆录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盛岳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是“王明虚构了‘江浙同乡会’”(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35页。)。陈修良在回忆录中也指出“‘江浙同乡会’是一件完全虚构的假案”(注:见《怀念战友孙冶方》,《上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此类事例还有一些,不再一一列举。
三、中国学生中的派别斗争面面观
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的许多学校,如东方大学、中山大学、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军事院校等,都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学生,据档案记载,到1928年初总数已经有1500人之多。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党派,出身经历和文化水平都各不相同,到了异国他乡自然要发生新的组合,有按地域的,有按情趣的,也有按政治倾向的。如果是在政治宽松的环境中,这些事本算不得什么,但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些原本很自然的事也都人为地和当时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搅和在一起,并无情地打上政治的烙印。
在苏联的中国学生中的派别很多。就政治观点来说,不但有共产党,而且还有国民党,而国民党又有“左”、右派之分。就地域来说,当时所谓的“同乡会”也不少,据档案记载,除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之外,在中大还有人提到“西北同乡会”(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此外,在旅莫支部中从法国回来的大部分是四川人,他们之间互相关照,于是又有许多人议论纷纷。后来就出现了所谓的“党务派”和“教务派”。中国学生中派别之多可以想见。
首先,这次反所谓“同乡会”的斗争是一次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其斗争的目的是不严肃的。在中国革命面临历史性转折的关头,所发生的事件竟然不是围绕革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引发的。学生们大多是对学员的待遇和毕业分配的去向不满,反对那些和学校领导关系好、职务高(如翻译或留校当教员)、领得的薪水多、待遇好而且群众关系不够好的学员。前面引用的方绍原7月31日在致项英的信中还写道:“哪一次不是因私人得失才引起来的同志纠纷”。就斗争的目的而言,尽管反对所谓“同乡会”的人指责其同国民党和第三党的“勾结”,但这丝毫不表明这场斗争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1927年4月两党关系破裂,当时在苏联的国共两党党员几乎同声谴责蒋介石,蒋经国更是利用各种场合抨击蒋介石。不久,一些右派学生就被遣送回国。据米夫说,1927年前后,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国民党员在学校的中国学生中并“不孤立”。国民党叛变后,曾清洗了三四十人,但并没有发生大的矛盾。(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7。)
其次,这场斗争的方式也是极不正当的,甚至是卑劣的、荒唐可笑的。一是扣帽子,用最可怕的政治帽子压人、吓人、整人。什么“国民党”、“第三党”、“取消派”、“联共反对派”……不一而足。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培吾1928年4月14日致“中委”的信。作者煞有介事地分析了“同乡会”产生的“客观条件”,但是除了劈头盖脸的一大堆帽子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他指出的客观条件是:国内由于国民党的胜利有许多人叛变,在莫斯科也同样会有人叛变;是旧中共领导破产的产物;是旅莫支部的机会主义表现;是联共党内反对派破产的产物;“是一切反动分子、取消派、改良派、伤心派等等的汇合体”,所以,这个“同乡会”就是另一个“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反动的”。很多学生对于这种乱扣帽子的现象都极为不满。8月17日邵世柱在给代表团的信中要求尽快解决问题。大家整天生活在“满城风雨”之中,“许多人的胸部都被‘大帽子’压弯了,然而他还不知到〔道〕那里来的‘大帽子’。假使你们再不能同我们彻底解决,我敢说倒不如早些回国做点实际工作好。”(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二是写告密信,捏造事实,诬陷同志,躲在角落里用暗箭伤人。有些人为了诬陷别人,不择手段地去跟踪、盯梢,甚至扣留、私拆、偷看直至抄录别人的信件。有的告密信的作者毫不隐讳地说明他们得到这些情报的手段。一封用着重点注有“秘密文件”字样的告密信,说明是“朱务善由专差送给周达文的信(从原信中摘要出来)”;有一份用圈点注明的“秘密文件”,自称是“最早发现的关于江浙同乡会文件——列宁格勒江浙同乡会负责人给在莫斯科同乡会活动分子的信”;还有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部分文件”(其中有许多是他们揭发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名单),大多是一些从32开或64开的小本子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字迹潦草的字条,信的内容叫人不忍目睹。例如何尚志(他写的这类信件有四五封之多)在致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所在的单位许多人也是“同乡会”的支持者,当他们野营时,常有中大的人来,“组织他们”“在森林里谈话”,然后就“三五一伙地总是讨论与野营无关的问题”。信的最后特别说明“我请您特别注意下列同志”,接着列出了8个人的名字,最后又加上一句:“上述同志是这个派别的‘积极分子中的积极分子’,其他的人没有必要都写。”1928年7月30日王培吾等三人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专门告发胡锡奎和胡建三是“同乡会”的“可疑分子”,他们的可疑之处是:近来他们两个每天“回来很晚”、“不知在何处”,“每个房间里都没有他们”。晚饭后他们就又“一前一后地在树林子对面会齐,或一东一西在树林子南面集中,然后走的很远,甚至十九点钟方回”。这种现象经常发生,他们开始“怀疑起来”,“于是就留意他们的行动,乃每晚见之,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他们原来就是“公认”的同乡会的“嫌疑犯”,“现在又有这些事实,所以我们确信他们两个至少也是江浙同乡会的同情者。在中央还正在调查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将我们亲眼所见公目所闻(原文如此——引者)的事实,供献给中央,以万(备)参考。”三是在找到所谓的“证据”之后,就开始无限制地上纲上线,用恶毒的语言对同志进行攻击。为了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有那么多的人向有关部门建议,要求将自己的同胞开除、流放、直至枪毙。一位署名“江西代表”“87号”的学生认为,“同乡会”的成员都是些“土豪劣绅资本家子弟”,“他们怎么能够革命?”应当把他们“枪决”,“不客气地一个一个铲除出去,这就是我希望的意见”。信的最后用“中共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口号结束;郭雨苍在给代表团的信中也斩钉截铁地呼吁:“对于这个组织的领袖们,应该是毫不怜惜地处以死刑,最低限度应该要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去”;在野营中的张国庶利用军官给的10分钟假的时间匆匆忙忙地写了一封信,经王明之手转交中国代表团。他要求把董亦湘开除,米夫太“懦弱”,这样会“遗党以祸根,这种懦弱是应该对党的前途,对革命的前途负责任的!!!”郭寿华除要求严厉惩处这些人外,还提出以后要“派工农子弟及对党忠实者”出国。(注:以上均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此类档案甚多,不再列举。
在这种气氛之下,中国学生的情绪就可想而知了。正如当时有人所说,简直是黑云压城,昏天黑地。1928年2月,“反动组织”“江浙同乡会”的事件传来,大家都噤若寒蝉。屈武听人说他也成了这个组织的成员,立即去找向忠发作口头声明,但还是放心不下,又向党组织写了一份书面声明。3月11日又向中共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写了一份长篇声明,检讨自己对所谓的“江浙同乡会”问题认识转变的三个阶段:从开始时的否认,到听了米夫讲话后“怀疑也许有这个事实”,但矢口否认自己和这个组织的关系,直到最后“当然相信是有这种组织了”。屈武还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最后用“一切小组织从布尔什维克的党中滚出去!”“共产党是我的家室!”“共产主义是我的生命!”“为生命和家室和敌人决战而死是我的职责!”等五个口号结束。在用中文写的这份“负责声明”中,屈武把“小组织”写成了“小织组”,把左权和陈启科的俄国名字也弄颠倒了,可见当时他的心情紧张到了何等程度。(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无怪乎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时屈武吓得几乎要得精神病。(注:参见《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400页。)
第三,这些中国学生在过去“党务派”和“教务派”的斗争中有各自的倾向性,但这次事件和过去的斗争没有实质的联系。过去“党务派”和“教务派”的斗争是同学校里联共党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而“江浙同乡会事件”完全是在中国学生中进行的斗争。斗争双方的阵线并不很分明,有的人显然是积极反对“同乡会”的,可是他们也被许多告密者写进了这个组织的黑名单(例如何尚志)。有的人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莫名其妙”地被列了进去(如张师、傅汝霖、陈浪沙等)。在中共代表团就有关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处理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中曾明确指出:“江浙同乡会”的大部分成员并不是过去的“党委会派”,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同这些派别作斗争的,还特别提到俞秀松、周达明、董亦湘。还认为“江浙同乡会事件”和过去的党委会派是两个不同的案子,不能混为一谈。(注: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致联(布)中央政治局的信》,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米夫在书面回答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有关问题时也明确表示,他不认为“江浙同乡会事件”涉及原来的“党委会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斗争。
历史资料证明,把围绕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斗争和过去的“党务派”与“教务派”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正是王明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在1928年7月14日的大会上,正是王明在对向忠发的讲话所作的“补充”里提到,去年由于米夫去中国,学校里只留下阿哥尔副校长和书记,事办不过来,发生了许多纠纷,才出现了“教务派”与“党务派”的斗争,“埋下了”这次斗争的种子(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3;另见王培吾1928年4月14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显然,王明在这里俨然以超然于“派别斗争”之外并以当时政治上很时髦的“反派别斗争”的姿态出现,其实不然,他恰恰是这些派别斗争的始作俑者。
第四,在这场斗争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坚持原则、敢于伸张正义的同志,他们同那些严重危害革命事业的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俞秀松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参加过五四运动、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人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尽管当时蒙受了不白之冤,异常苦恼,但他依然刚直不阿,拒绝向恶势力屈服。1928年3月初在中国学生中进行了一场争论,他说道:“现在我非常痛苦,也非常激动。我想骂中大的同志是混蛋!在中大那里是一团糟,而且出现了极为‘过分的作法’!我今天就去米夫那里!”他又说:“我已经全对米夫说了,莫斯科绝对没有派别组织,这是可耻的杜撰!这是卑鄙的臆造。我坚决反对这样做!我承认我和董亦湘等人是好朋友,过去是,现在都是。我必须声明,我同陈独秀关系很好,我和他自始至终有良好的关系,我反对他的不正确的路线,但是他是真正的典型的中共的领袖,中共这样的领袖很难找。我坚决反对那种专门有意地把某个人抬举到中共领袖的位置上,陈独秀被撤职以后,在中共内部任何人也不能成为领袖,只有集体领导。”档案记载,他把“最后这段话重复三遍”。最后他说:“现在在中大完全没有同志的关系,这是不给人以新的出路!”俞秀松在7月29日还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主席团,信中说:“关于我个人和所谓‘储金互助会’或‘江浙同乡会’的关系问题,本来我已经和几位中央同志谈话时声明过:我私人问题,将来候你们有暇时详细报告。但现在此问题既已决定在最近10天内解决,那么我应该在未解决前向本党报告的。请你们决定时日通知我向党报告。中共党员俞秀松。”(注:以上均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面对众人的无端攻击,他旗帜鲜明,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应有的光明磊落的品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还有一些受到无端诬陷的同志也冲破重重的压力坚持斗争,胡士杰、尤赤、陈启科、左权和郭景惇等人,在得知被开除并将遣送回国之后,多次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去上访,但米夫均以“有病”为由拒绝接见。四个星期之后他们又写信给联共(布)中央监委,要求他们彻底审查。7月22日,他们又去联共(布)中央直接找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时正在召开共产国际会议没有找到。然后又到联共(布)中央监委。这些问题没有查清就要将他们遣送回国并开除党籍,他们再次要求中共代表团以党的利益为重,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给予解决。周达明1928年3月7日致米夫的信指出,应当让那些最认真的同志进行最谨慎的调查,在组织未作结论,尚未查清时不允许把问题转向群众,在学生中散布这个问题是完全不正确的。在没有材料证明这个组织的存在、它同第三党的关系等就宣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是反革命(我是指向〔忠发〕同志),这不仅不能弄清问题,反而会坏事”(注:《丘古诺夫(周达明)致米夫的信》(1928年3月7日),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
应当承认,最后联共(布)中央监委之所以作出一个有原则性的正确的决议也是与他们坚持斗争分不开的。
四、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处理结论和后果
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结局,可以说是既有明确的结论,但又不了了之。
之所以说当时关于这一事件曾经作出过结论,是因为在1928年8月10至11日联共(布)中央监委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曾经就所谓的“江浙同乡会”问题正式作出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由中央监委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亲自签署。决议指出:联共(布)中央监委“没有材料确认过去和现在存在过任何固定的组织”,并确认指控这些中国同志是“反党”、“反革命”,同国民党右派军阀有联系和支持谭平三的“第三党”、“夺取中共的领导权”等政治目的“是没有根据的”。该决议的第四条决定“同时撤消”有关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案件。决议还指出,米夫根据未经核实的材料就在学生大会上公开宣布存在秘密组织,并没有向“任何一个相应的党的机构”提出这个问题的“作法是错误的”。这项决议在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协商后正式报请共产国际监委会同意。(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21。)另据档案记载,共产国际监委还于1928年9月10日专门就“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案件”作出一项决议,正式批准联共(布)中央监委1928年8月10至11日作出的决议。并于1929年9月22日正式通知中共中央。(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6。)
总之,当时的联共(布)中央监委确实就有关“江浙同乡会事件”作出了决议,而且这项决议应该是有效的。因为在中共旅莫支部解散以后,在苏联的所有中共党员一少部分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其余的全部转为候补党员,从隶属关系上说,联共(布)中央监委就此作出决议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说“江浙同乡会事件”,是有结论的。
但是,实际上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处理确实又是不了了之。因为雅罗斯拉夫斯基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并准备为这个事件平反,他希望“在尽力依照中共代表团的意思,求得一个最无偏见的结果,求一个最完全的会商”。可是在和中共代表团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矛盾。最后由于联共(布)中央监委特别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坚持,在连续开了11个小时的会之后于8月11日还是通过了为“江浙同乡会事件”平反的决议,宣布撤销这一案件,对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予以平反和恢复名誉。联共(布)中央监委的处理方式是符合原则的,结论也是正确的。至此,这一事件本应该就此了结。但是由于参与处理这一事件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这一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根据现有的材料就可以证明这个组织是“存在”的,是“对党秘密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些重大的分歧对于执行中央监委的决议是十分不利的。由于当事人原来就是中共党员和中国学生,这些人以后大部分都回到了中国,因此实际上对这个曾一度酿成轩然大波的所谓“政治事件”的处理也就从此再没了下文。但从有关档案中可以知道,这一事件及其处理经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是应该了解的。因为:第一,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都在莫斯科,他们当中有些人不但了解而且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处理。第二,据档案记载,1928年8月8日雅罗斯拉夫斯基曾致米夫一封信,内容是让他答复中共中央来信询问的几个问题,这至少说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有关情况(注:《米夫致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1928年8月8日),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7。)。第三,在1928年8月11日联共(布)中央监委的决议出来后,也曾正式决定将这件事通知中共中央。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是很严重的。
第一,中国学生中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乡土观念依然存在,而且学生中的无原则纠纷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苏共党内的斗争激化,中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使革命同志之间的正常关系被破坏,搞得人人自危。有些人继续以“左”的面貌出现,极尽打击陷害同志之能事,这种状况在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时期达到了顶点。1928年3月15日,胡世杰、朱茂榛等五人给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信中指出,我们对革命的忠诚是由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不用自己申诉。信中痛斥那些挑拨同志关系,对同志恶意中伤的人是“误党的内奸”,“党必须特别注意并肃清这些野心家在党和群众中的影响”。当时受到株连已接到通知被遣送回国的张师也给共产国际和中国代表团写了一封充满悲愤之情但又坦荡激昂的信:“党内同志长此以凭空的罪名互相挤压,这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至少也成了些微的阻碍。我从未曾在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的刀斧之前畏缩不前,也未曾顾虑到!只愿以自己的生命,为世界革命之前躯而牺牲!派我回去,我已准备好一切!准备着与我们阶级的敌人作殊死战!准备着在不久的战场中去表示自己对党对革命对列宁主义的忠诚。余不赘。”(注:以上均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
第二,错误地处理了一批对革命赤胆忠心并曾对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好同志,二些人当时就被取消了继续学习的资格,背着有严重历史问题的黑锅回到了国内。还有一些人虽然留在了苏联,但是随着苏共党内斗争的激化和斗争方式的扭曲,他们又作为“托派”而受到打击,继续受到政治迫害,留在苏联的周达明等人也被打成“反党阴谋集团”。1930年,在苏联的中国学生中有“托派嫌疑”的人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劳动改造。(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74 卷宗321。)
第三,后来王明一伙正是在米夫的支持下篡夺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并全面推行“左”倾路线,同时也把苏联党内斗争的“经验”带回国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正如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他们把所有“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86~987页。)1928年3月7日周达明在为自己的申诉中就曾指出,毫无根据地对同志进行伤害,“如果这类不健康的现象、非常有害的状况不结束,如果把它运用到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去,可以说会造成巨大的不幸。它无疑将成为党内的巨大的消极因素”。不幸,以后发生的事实证实了他的预言。
第四,由于这一事件在中共党内始终没有作出一个正式的结论,以至后来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及其同伙仍然继续把参加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同志作为一项严重的历史问题,当作“托派”进行残酷打击。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一到新疆他们就立即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写信,密告在新疆的所谓“托派”的活动情况。声称这里的许多人都有“反革命嫌疑”,其中第一个就是俞秀松。就在王明、康生到达新疆后的一个月后,12月下旬,俞秀松等人被捕入狱,1938年6月25日被押解苏联,并死在那里。据档案记载,直到1940年,苏联内务部对一位在苏联的中共党员进行调查,还说王明曾指控他是“积极的托派分子”。尽管这个人在中大学习时的政治鉴定相当不错,但是另外有一份材料说他“好象加入过”“江浙同乡会”,是曾被列入了“嫌疑分子名单”的,在调查中竟然还有人作证说,“在中大时的一次会上发言,曾反对该校领导和反对过王明”。1930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74 卷宗321。)
“江浙同乡会事件”作为革命队伍内部的一次严重内耗,给革命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令人深思的。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特别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内耗给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估计不足。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的洪流中才能荡涤自己身上的污垢,它也不可能脱离中国革命的进程去搞自身的建设。我们从这一事件看到了30年代以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并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可怕魔影,其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是党内30年代严重的“左”倾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灾难性后果之前的一次预演。正如后来周恩来所说:在“那些是灾难性的年月,好同志成了无谓的牺牲品”(注:转引自〔英〕韩素音著《周恩来和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1页。)。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国外,但是它在中共党史上造成了永远无法消除的恶劣影响,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