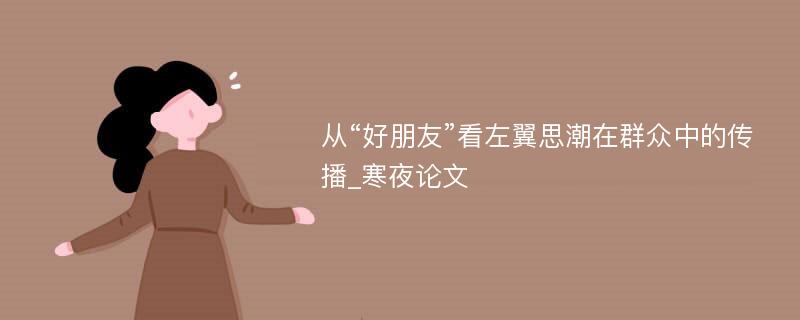
从《良友》看左翼思潮在大众层面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大众论文,思潮论文,良友论文,层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良友》作为一份大型综合画报,也是中国第一份结合新闻报道的图片杂志,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众人纷说“公共空间”和“媒体霸权”的今天,研究它在现代中国的作用力也许会对当下有所启发。在它存在的二十几年间,左翼色彩日益浓厚与突出,批判功能也随之不断加强。然而这种来自左翼的力量在什么层面起作用,是否真正具备影响力,到底拥有多大的操纵能力都是值得玩味的。细致的考察也许会对此有所发现。
一、《良友》的空间
1926年2月15日,《良友》画报在上海出版第一期。无论从时间、地点、刊物形式还是阅读人群来说,《良友》都具备了天然的高容纳力。“编者的目的,是要包罗万象,力求能使各种读者各取所需。”(注:马国亮:《良友忆旧——家画报与一个时代》第7页,第121~12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月。)在当代中国的传媒形势下,不进行读者细分的杂志会令人担心其销量,然而作为中国第一份大型画报,《良友》的营销策略显然是成功的,在它的第一百期纪念特刊中,刊出了“本志读者一斑”的系列照片,其读者从家庭妇女、职业女性、工人、黄包车夫、小职员、学生乃至社会名流无所不包。《良友》自豪地宣称自己“无处不在”,“无人不读”。《良友》的空间首先是读者所圈定的。
《良友》初生时,中国的传媒并不发达,尤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旧中国的报纸,要想做一个记者,对平民百姓出身的人来说,那是很难的。上海的报纸记者,不是流氓的徒弟,就是同资本家或富豪有关系,有政治背景的人。”(注:袁殊:《对〈文艺新闻〉及〈记者座谈〉的回忆》,见《传播学研究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报纸尚且如此,以杂志而兼有新闻性,而且以中立为原则,不介入权力之争,没有明确的意识指导的更是相当之少。在杂志界,同人杂志占据了数量的绝大部分,它们或致力于宣扬小团体的理想,或有志于大众启蒙,还有不少只为自娱自乐。这些杂志不以销量为目标,因而内容大多“自说自话”,难以作为大众嗅觉的风向标。而占据了销量大部分的则是休闲娱乐性的杂志,以发售言情、侦破和武打为主要内容。这类杂志至今面目雷同,缺少时代感。但是《良友》不同,“伍联德常向西人书店买几期回来研究参考,所以盘桓在伍联德脑海中的就是在中国尚未有人想到过的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新闻画报。”(注:赵家璧:《重印全份旧版〈良友画报〉引言》,1986年9月。相似的意思,余汉生在第53期《良友画报》中也曾提及。)
伍联德确实实现了他的设想。《良友》不仅以图代言,囊括了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具有追踪新闻时事的能力。如果说它第一期的时人照片还只是模仿当时通行的做法,那么之后的要闻报道,时事述评等栏目的相继设置则显然具有了明确的新闻意识。它不谈古只论今,搜罗了大量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从政府行为、闻人行踪、娱乐报道、奇闻轶事到文艺写作无所不包,其栏目设置和现在的许多新闻类杂志十分相似,充分证明了这种设计的合理性。它的办刊思想及其成功也决定了杂志的整体风格是庞杂、丰富、兼收并容的,善于捕捉大众的敏感点,具有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难怪阿英认为,在现存的画报中,富有历史价值的无过于《良友》。(注:同上书,第6页,第28页。)
然而,《良友》无所不包的风格,以图片为主的叙述方式也使得它缺乏深入剖析的能力。它的新闻是扁平化的,强调的是知识而不是事件。因此《良友》的新闻报道像要人行止和各地风光介绍,背后缺乏意识的拽撑。初期的《良友》文字苍白,经常只作为图片的讲解和连缀出现。周瘦鹃接手后,开始有了小说连载,文学成分加重,但他的“礼拜六”气息和《良友》的新闻综合性显然并不投合。虽然之后接任的主编梁得所遵照伍联德的思路奠定了《良友》的风格基础,定下了“包罗万象”的基调,然而周瘦鹃的趣味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良友》的文学部分,或许这也并非出于周瘦鹃本人的影响力,而是当时的大众趣味所决定的。相当时间内,卢梦殊、叶鼎洛等人的创作代表了《良友》的文学方向,并且在以后的《良友》一直占据着一定的分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良友》中出现多少字句铿锵,观点鲜明的深度报道。出于中立的原则,它也不便于在势力均等的情况下对其中一种倾向显示出太过于迎合的姿态。它是一面很尽职的镜子,而且为了自身的生存,始终避免成为《白雪公主》里那面饶舌的爱评论的镜子。不过也正因为此,它所反映的事实才更具有参考意义和时代特征。当它明显倒向某一方时,后人可以由此得知这一方的势力已经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至于对它的倾倒不再具有“帮凶”或“帮闲”的危险。而它发出某种呼声的时候,也基本上可以认定这种声音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规避当局的指责,是一种普遍性的民意。
虽然《良友》的销售状况非常好,而且一直和当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用简单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说它是当时主流舆论的传声筒则很不确切。事实上,《良友》一直以热卖作为它的最大目标。是否受到大众的欢迎,是它最为关切的问题。在《良友》周年纪念或其他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期数上,编者照例要在杂志上讲几句,无论是伍联德、梁得所、余汉生还是马国亮,说得最多的就是杂志的受欢迎程度。他们反复表示要将杂志办得人人爱读,并举出种种具体措施,从印刷机器到栏目设置到号外都有全套的设想。在这些文章的结尾,总有一些带有炫耀性的数据以表明杂志在销售上的成功。显然,大众的接受是生产《良友》者所最关心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特别是伍联德总是在表明希望杂志卖得再多些的愿望之后,还会告知杂志另有宗旨,那就是教育大众,普及知识,使人家具有丰富的常识,健康的心灵,以及完备的道德。这项宗旨与其说是对民众教化起到了作用,不如说是《良友》的自我约束,把它和其他一些庸俗小报区分开来。同样是增长销量,《良友》希望自己并不低劣恶俗,而是具有一定的都市品位。
因此《良友》的大众路线更多地可以被视为市民趣味和政治文化气氛的结合。它所反映的思潮已经经过了市民社会的漂染,少了些许理想主义的光辉和理性思辨的深沉,却突显出了日常生活的含混和对趣味的强调。人们从生活经验出发,追求生活以外的东西,《良友》体现了这种追求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友》的空间是开放的,它容纳得下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它的空间又是有限的,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和它只有少部分的兼容。精英的气味在这里十分淡薄,由精英所传播的一切如果具有了足够的力量则会在《良友》有所显示,只是已经丧失了启蒙的原意。《良友》是被启蒙的,出于吸引大众的需要,它只表现较为成熟的思潮。
二、左翼的渐进
1926年2月,国父孙中山逝世不足一周年,国共合作尚未破裂,陈独秀与汪精卫联手抗衡蒋介石,政治形势微妙复杂,一日三变,然而对于老百姓来说,气氛上还维持着表面的宁静,呈现出短期的开放与容忍。这对一份力求丰富的大型画报而言,是极好的创刊时机,正是有材料而少约束的时段。《良友》既然自称是新闻性周刊,它对政治就不可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回顾一下第一期的内容,就会发现除了艺术、娱乐和休闲之外,政治人物的图片着实不少:有一方大豪(孙传芳)、新贵(行将取代孙中山领袖地位的蒋介石)、风云人物(宋子文、吴铁城、许崇智等),还有刚被暗杀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这个人物名单包括了各方面具有实力的政治势力,从中甚至可以窥见中国今后十几年的风云变幻。从名单的选择上来看,《良友》的确是一份本身无所倾向的大众杂志,它的标准是要有足够的知名度或者说是显赫度。平常百姓对于要人总会感到某种兴趣,《良友》的图片正是从迎合大众的角度编发的。到第十四期,《良友》还索性做了一个“中国现代闻人录”,收罗了更多的闻人照片,其中除了政界要人外就是著名学者,如胡适与蔡元培等。基本上,在1928年以前,共产党根本很少被提及。这与其说是《良友》排斥共产党,倒不如说是共产党当时尚未成熟到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还没有成为有力者,因此没有引起大众画报的注意。
但没有提共产党,不表示其中没有左翼意味。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是和孙中山、国民党、北伐等名词联系在一起的。《良友》16期中设有专题报道五卅惨案纪念日的活动,照片里的横幅上醒目地写着:“要报仇雪耻的人快来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的革命尚未与共产党的活动等同起来,民众更多地联想到国民党左派的革命行动。在含义上总是会与左翼相关的“革命”在现代中国是一个相当富有吸引力的时尚话题,《良友》作为新闻性的期刊,从来没有忽视关于革命的报道。创刊以来的第一次号外就是关于国父孙中山的,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他“革命的一生”。(注:同上书,第6页,第28页。)该号外一版再版,号称销行十万册,即使有些水分,销量也是十分惊人的。后来的《北伐画史》也达到销售几万册。充分说明民众对于革命的关注。第14期和34期还刊出了烈士纪念专刊,纪念的是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廖仲恺、宋教仁等。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所纪念的革命烈士在今天仍然被正面提及,这种评价的一致性显示出中国二十世纪革命意义的延续性。
1928年之后,“赤匪”在《良友》的出现频率开始上升。虽然《良友》自称没有任何党派背景和政治倾向,从经济上也的确没有接受任何政治势力的援助,然而它与当时的政府显然保持着“主旋律”的一致性。1928年的中国政治空间,由于蒋介石的强硬执政,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良友》中所透露的意识形态是国民党右派一手包揽的,肉体的屠杀配合主流舆论的导向,使得普通大众将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良友》对于“赤”的口诛笔伐是自觉自愿的,27期的《写在卷头》是指责女红阻碍女性解放的,开头就写道:“红,红,红,中国女子赤化了几十年,遗害之深,不亚于共产党的赤化。”显然,“赤”在当时非但没有得到普及,反而令人畏惧。第24期刊登了李炎生的《迷途》,这是一篇小说体的说教文章,充斥了大段的对话以阐明观点,俨然两党辩论,而国民党则占据了道德和正义的高地。没有资料表明这是一篇出于授意而刊载的小说,虽然它与《良友》整体面貌格格不入。但是在这篇小说的开头,有一段《编者的话》,明确表明了编辑的倾向性,其中写道:“……以广州共党祸乱做背景,用小说体裁指斥共党的错误,而描写这纷乱时代的青年思想之苦闷。”刚刚形成较为稳定的政局形态的国民党政府非但代表着合法,也代表着合理。难怪《良友》每期末页都会出现的歌曲中,会有梁得所作词,借用外国曲目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还特意用括号注明“国旗歌”。无论如何,共产党开始产生了影响,比起1928年以前的从未提及,最起码《良友》中开始出现了有关共产党的报道和词句。
然而到了三十年代,情形有所不同了。“红色的三十年代”,“赤”成为了时尚,《良友》随着读者的兴趣把眼光向左转了。需要说明的是,左翼思潮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党派理论。三十年代“红旗漫卷大地”卷来的是人们对更合理的社会模式的向往,是“革命”所带来的冒险刺激与英雄认同,和五十年代的“红旗飘飘”所弥漫的共产党理论霸权并不相同。《良友》及其代表的普遍大众所感兴趣的是左翼风潮而非党派理念。只不过,将左翼和党派完全区分开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之所以产生左、右两翼本身就表明着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当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屠杀开始,“左翼”在普通人心目中可能只是指国民党左派,当时可以互相抗衡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共产党只是“赤匪”。而十月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红军的胜利所引起的震撼是具有重大作用的,《良友》中关于苏联的逐渐增多的报道足以说明问题。
三十年代的左翼显然是指和共产党有关的政治方向,国民党左派只是作为它的延伸而存在。同时,左翼又是一直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这从《良友》提及宋教仁和廖仲恺的时候总要特别注明“国民党左派”一词可以观察到这种微妙的差异。三十年代和革命建立联系的是国民党的反对党——共产党。由此,在大众含糊的认识中,共产党、左翼、革命这几个从学理上讲并不等同的概念被画上了等号。国民革命政府在民众的心目中已经不再革命。第59期的《编后话》写在国民会议闭幕后:“民国以来,我们听闻过许多的消息,可是一年等一年,好在中国人脾气够涵养,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也可以活下去。”对政府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出言还算止于牢骚。而62期的《编后记》则更出言不逊,当时正是1931年那场影响深远的大洪水之后,《良友》写道:“在我们国家里,有负着保护人民的使命者,干着践踏人民的勾当;拿救命钱去做杀人的开销。”杀的是什么人,略具历史常识的中国人大概不难明白。“赤党”不再是理所当然该杀的对象了。
真正把具有党派色彩的左翼文化带入良友的契机,是郑伯奇的加盟。(注:《良友》从1932年第65期开始刊登虚舟的社论。马国亮回忆为1933年初,应是记忆有误。)郑伯奇化名虚舟,每期一篇言词犀利的新闻评论使得《良友》忽然变得具有锋芒了,虽然他没有将社评写成明显的宣传文字,但其中透露的倾向性则为《良友》抹上了一层红色。如中苏建交后欢呼,对法西斯的分析都带有明显的导向。
他的加入,不仅影响了《良友》编者的思想,也直接导致了刊物言论的方向转变。马国亮自己也承认,“郑伯奇的到来,朝夕相处,他的思想对我和赵家璧两人都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他,我们也认识了鲁迅,以及左联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周起应、沈端先(夏衍)等等。”(注:同上书,第120页。)这起码使得《良友》的组稿范围扩大到了左翼文化阵营。从65期开始,文学性在杂志中进一步加强了,“新感觉”的都市风格被逐渐削弱,而主要撰稿人则大多来自“左联”。仅以75期的文字目录为例,虚舟《早春的低气压》,鲁彦《恋爱行进》,郑伯奇《革命作家巴塞比》,袁殊《春曦之诞》以及何家槐《追》。个个都是左翼阵营的作家,“赤风”怎能不影响《良友》的风格?另外,郁达夫、穆木天、黎烈文、楼适夷、周楞伽、洪深、茅盾等人都是《良友》的撰稿人,其他不能一一例举。从83期起,《良友》设有一个“良友人影”栏目,通常会刊登一些和《良友》关系密切的供稿人和编辑的剪影和简介,而第一期的“良友人影”中就有穆木天。在对他的介绍里甚至还有一则小小的逸闻趣事,足以说明穆木天和《良友》办刊人私交的密切程度。另外,良友图书公司里的许多人如赵家璧、孙师毅(注:孙师毅曾与夏衍合作《新女性》剧本,甚至列席参加“文委”的会议。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64~18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等都和“左联”中的主要负责人关系密切,这不能不影响到《良友》的整体风气。1933年赵家璧主编的《良友丛书》几乎全是左翼作家的文集。
不仅是编辑内部的转变,社会对于文学的期望也已经有所改变。魏南潜在第89期的《悼庐隐女士》一文写道:“如果是大众的呐喊,或者是压迫的反抗,甚至血和刀,你向她索取这些,她会教你失望的,批评者说:庐隐是始终脱不掉女性感伤味的个人主义者……她早就停滞在五四的路上了。”对于庐隐的评价事实上反映了当时文学价值的取舍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郑伯奇的加盟,也会有另外的机遇出现。于是在《良友》中出现了有趣的景观,屡次在开头几页的新闻图片版中刊出“剿匪”实录,后面的文学栏目里出现的却是左翼作家在做小知识分子的呻吟,影剧通报里还有左翼理论家在鼓吹新上映的剧作。甚至出现了王家城《清炖肘子》这样以古讽今的小说。(注:这篇小说讲一位钦差大人曾到某地视察,对当地的清炖肘子念念不忘。他又一次路经该地时,正值大饥之年,根本无猪可食。地方官为了讨好上司,竟用小儿臂膀代替猪肘进献。文中借小儿母亲之口进行了大量的控诉。)虽然恋爱和社会素描仍然是《良友》文学部分的主题,但“觉醒”、“大众”、“压迫”、“反抗”等左翼词汇频频提醒着读者的眼睛。《良友》早期温婉的风格已经被左翼的特质所改造,在气质上出现了转变。
三、左翼在《良友》中
不过,《良友》既然有本事将新闻变作图片集,它也可以对左翼进行改装。和《北斗》、《沙仑》等刊物相比,《良友》当然不具备造反的野心,也无意进行任何宣传。它将左翼存在的缘起和意义一概过滤,摒弃了一切理念化的东西,仅留下了一些富有吸引力的姿态。吹到左翼劲风的《良友》保留了青年的朝气,可是却不问这股劲头能够干成什么大事;它体现出拯救者的同情心,却省略了为穷人而奋斗的理想;它吸收了先锋的风气,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勇气。来自左翼思潮的公平和正义思想渗透入了《良友》的大部分栏目,它由此抱怨穷人的处境,民主的缺失以及国家的贫弱,但它对未来的向往和大部分普通中国人一样,只中意于目的地。第89期赵家璧在介绍赫胥黎的小说《乌托邦》时写道:“乌托邦并不存在于赫胥黎的小说里,可实现的乌托邦,却就在这个地球上。”“实现的乌托邦”显然是指苏联,这个参照物本身是左翼带来的,但《良友》从来没有涉及到如何在中国实现乌托邦的具体实践。《良友》中的左翼是大众心目中的左翼,简单而平面化,来自革命的刺激结合美好未来的设想就足以构成趣味和道德的最佳传媒搭档,《良友》不需要更多更为沉重的理念。
《良友》是以销量为目标的,即便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得不局限于大众的接受力,更何况它与执政党一直保持着互不侵犯的关系。对于一本已经有相当知名度,风格比较成熟的杂志,左翼阵营也没有试图对它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众所周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媒体进行宣传可以说是“左联”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许多“左联”成员后来都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当年如何争夺报纸和杂志的阵地,但似乎很少有人提及《良友》。在这一点上,为《良友》撰稿的左翼作家大都和杂志保持着默契。左翼作家们大多很好地掌握着分寸,从未出现过像《迷途》这般露骨的宣传。其中最富有倾向性的是出现在77期中吴家盛的《县官与犯人》,文中写道,官:“混蛋!你知道你是共产党么?”犯人:“前年老爷你叫我加入的,为何不知?”这篇寓言式的小文章算是最有勇气的了,明确写出“共产党”三字,并将这一词组放在可同情的一方,可是它也只是为共产党的处境不平,并没有进行党义教育。
《良友》最为大胆的一次举动是刊出了丁玲的手稿,附语中有“系女士失踪后”的字样,算是间接地报道了丁玲的被捕。此事引起了当局注意,成为马国亮日后写回忆录时抗议“白色恐怖”,表明“跟上时代的步伐”的证据。(注:马国亮:《良友忆旧——家画报与一个时代》第7页,第121~12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月。)丁玲的失踪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引起了文艺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十年以后,丁聪在《小说半月刊》上为丁玲作漫画,注解中还特别提及此事。报刊杂志反应激烈,议论纷纷,是一个极好的新闻卖点。《良友》对丁玲事件的处理显示了它的典型风格,既抓住大众的注意力,又不涉及“主义”之类的重大话题。事实上,从用词来说,《良友》算是相当温和的了,只说其“失踪”,还是只在附言里简单注明。《女声》等杂志都直接使用了“被捕”的字眼。不过《良友》利用它的图片优势,刊出手稿,当然特别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
在捕捉大众的敏感点上,《良友》比“左联”更进一步,当“左联”还在试图以“阶级”对抗“国家”的时候,(注:为了对抗国民党所提的民族主义文艺,共产党提出“工人没有祖国”,“阶级斗争高于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见《告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出版。)《良友》已经将穆木天作为“东北来的作家”隆重推出,从直觉出发,将救亡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为左翼找到了一个能够在大众心目中立足的最具合法性的点。《良友》中激进一些的文字大都和民族救亡有关,这种激进无论在对付审查还是激发大众上都是安全的,《良友》当然会经常表现出这种姿态。
《良友》为左翼找到的另一个立足点是对“大众”的关注。“大众”在现代中国的涵义相比现在要狭窄一些(注:本文所用不带引号的大众一词,是当下所通用的意义,指不掌握权力的普通百姓,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中。),它仅代表着底层劳动人民,没有或者很少量地受过教育,靠体力劳动维持艰难的生活。由于当时相对稳固的阶级(温和的说法曰阶层)划分已经形成,这一人群在整个社会中具有独特的生存方式,也带有鲜明的识别印记。当他们被他者提及时,所表现的态度正好符合中国社会的思潮转变。受到左翼影响之后的《良友》不但把镜头和笔触频频投向“大众”,并且转变了观看的视角,将好奇的旁观变为混杂着尊敬与同情的复杂的拯救者心态。这种情绪带有明显的左翼知识分子烙印,也是以后42年延安文艺整风的重要由头。35期的《良友》尚用看风景的态度拍摄纱厂女工,署以“自做自吃”的标题,而73期的“时代女性”专栏就将劳动女性作为时代的楷模,赞美“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80期楼适夷的《纺车的轰声》以报告文学的体裁写“资本主人对纺车女工的压迫”。74期马国亮《债主》把乞丐小儿当成自己的债主,因为“他是债主,他是最大的债权人。他没有该在路边伸手向人们乞讨的义务!”在《良友》的漫画栏目里更是频频出现“大众的素描”,“劳工神圣”已经成为它的老调。
无论是谈及“国家”还是“大众”,《良友》都巧妙地利用了左翼的批判功能,针砭时弊,为民请命。它很好地把握着尺度,不触及过分敏感的话题,不谈论具体的事件,不评论政府的行为,在流水账一般的新闻报道里,它绝不进行附带的评价。可是在另一些栏目里和句子里,它的不时稍显锋芒,表现出社会正义感。对于大众来说,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保守为主的小小激进是最令人心安理得的,也是一份大众杂志可以采用的明智态度。
左翼作家在《良友》写恋爱,写风光,写上海,写剧评,是从抵抗外侮,劳工神圣,为穷人抱屈以及感伤焦虑的情绪中体现自身的倾向。虽然这些文字的左翼气味隐藏在作品的深处,但是还是可以被明白地分辨出来。具有意味的是,《良友》上最具有典型左翼气质的小说是73期杜衡的《寒夜》,这篇小说讲述一位穷困潦倒的人负债累累,为激愤无奈的心情所逼,半夜在街头踯躅,身上最后的两毛钱出于破罐子破摔的心态给了紧追不舍的乞丐,棉袍被人抢走,想回小客店却没了车钱。小说的末尾想死的主人公忽然情绪高涨起来,暗示着他想通过模仿乞丐和强盗的方式继续生存。小说通篇弥漫着感伤、愤懑的情绪,主人公敏感而易于激动,虽然描述的事件非常黯淡,可是语气却保持着高调。而这些正是左翼小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作品气质。虽然杜衡没有在作品中点明主人公的身份,可是那些富有情感的思维方式只能属于小知识分子,难怪万籁鸣所作的插图里为主人公穿上了一件长袍。小说看不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最后也没有安排主人公拿起武器反抗万恶的旧社会,但《寒夜》中标志性的构思、情节,特别是带有自传色彩的情绪,深得左翼文学的个中三味。由杜衡这样一位身份微妙的人物来作为《良友》左翼文学的代表并非出于偶然。在意识和文学之间只存在着极为狭窄的一线空间,仅供架设一条细钢丝,以杜衡为代表的左翼边缘作家就行走在这条钢丝上,力图保持平衡。他们的努力使得作品更富有文学意义,而左翼作家如果不写宣传性的故事,就只能通过社评、剧评和散文中的一些蛛丝马迹来表现自己的主张了。
《寒夜》中所显出的左翼影响正是《良友》的绝好写照。左翼不是通过自己的主义,而是通过气质的感染存在的。左翼在《良友》从来没有被对象化过,对象化的反而是国民政府的行为。左翼在《良友》是作为潜在的背景出现的,没有被大声喊出来过,事实上也不需要特别说明,它在作家名单里,在丛书名录里,在栏目设置里,在编者的话里,在社论里,在电影介绍里。只不过这种影响由于过分平面化而多半有些变味,夹杂进了娱乐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时尚的展示。不过与其在到底是大众决定了左翼的传播,还是左翼思想影响着大众的趣味之间作出选择,不如说这中间存在着一股合力,两者互相需要,互相影响,互相修改。《良友》的目标是赢利,因而它的封面永远是美丽女郎,如果与时俱进的大众要求来点儿振奋人心的东西,那么《良友》就让女郎拿上武器。正如81期整张彩页的插图中所绘的那样,一位美丽娇艳的裸体女郎一手持大刀,另一手放出闪电,《良友》为它题名《反抗》。《良友》中的左翼就是女郎手里的大刀和闪电,就是图片的标题,不得不承担起一定的装饰作用。既然大众接受的口味就是如此,责怪《良友》传播不力,歪曲理念就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能因为女郎手里的大刀没有杀伤力而全盘否认它的意义。如果说杜衡们的困境是在文学与意识之间保持平衡,那么《良友》的难题是在如何让娱乐与意识达成统一,其结果是不得不两头都做些牺牲。较之当今将新闻、纪实与评论都全面娱乐化的报刊电视,《良友》还算得上是一本正经杂志,最起码它从未以他者的眼光看待左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