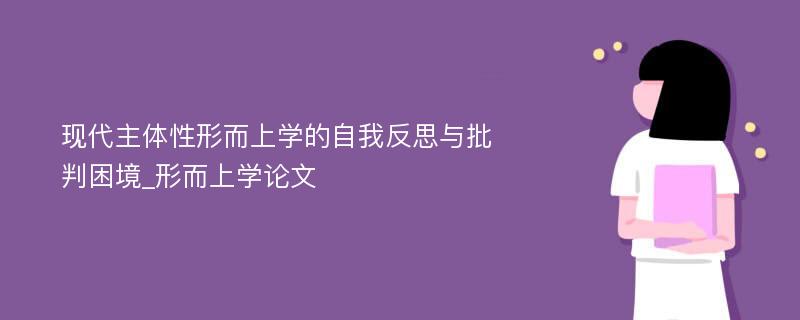
自我的困境——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之反思与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形而上学论文,近代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来,主体和主体性成了我国哲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与现代西方哲学竭力批判和解构主体概念相反,我国哲学界则是一片高扬主体之声。此种状况,耐人寻味。
尽管人们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哲学概念,但哲学的基本概念却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空洞符号,而是浸透了种种历史内容和现实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是概念决定了使用者的思想,而不是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和别的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殚精竭虑地要通过改造乃至生造一些术语和概念来避免传统思想的束缚。既然主体和主体性概念起源于近代西方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那么,批判地反思这两个概念在近代西方哲学中的兴衰和困难,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界不为无益。
一
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笛卡尔的任务是“将人理解为自我确定的自律(Selbstgesetzgebung),以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1] 笛卡尔及其后继者们将cogitatio(思)解释为将事物作为眼前的现象来把握。 这种把握占有了存在者,将其置于完全的确定性中。给这种现象以无条件确定性的, 是为它奠定基础的主观“立场”, 即作为主体的自我(ego)的确定性。 一切东西置于其上犹如置于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从那时开始,形而上学向其崩溃运动,即向一个时代运动,在这个时代中,自由的人的主体性扩张为意欲意志(Wille zum Willen),要求完全支配世界。
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这种诠释虽然有很高的启发意义,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它只适用于笛卡尔的前两个沉思,却难以用于解释《沉思》进一步的发展,和在那里进行的存在论转折。笛卡尔发现,如果我清理自己的思想,向自己弄确实我的生存(Exsitenz),那么就会遇到一个特殊的概念,即无限。这是唯一一个不能从我自身而来的概念,因为它超出了我有限的主体性。我然后发现,并不只有我存在于世,还有他者,它的无限性包围着我,把我送进此在。这他者的概念显明自己是一切概念中最真实者,比我思的直觉更明证,更可靠,在我自身中比我自己来得更早。我思的真理是我被思。列维纳把笛卡尔这种理论向度的倒转称之为“存在论革命”。
笛卡尔把这个无限的他者与存在神学(Ontotheologie )的上帝视为一体,它占有最高原理的位置,而曾经占有这个位置的自我,则被赶走了。我思在先只是表面上的,完全是一种暂时的在先,只是为了展开思路的需要。但现在要维持这种立场就难了,因为笛卡尔将现象的确定性建立在人主体的立场上。不求助于上帝的真实性,我思自我幽闭症式的明证本身仍是封闭的,无法确定世界的实在性。
不仅如此,也许自我本身就不能给它自己的生存牢固地奠定基础。无疑,我自己在我思中的直观不能怀疑。我思,我在,这是确定无疑的。但笛卡尔进一步问道:无疑能“多久”?如果我作为自我只是思维的存在物,那么它的确定性与思维的意识是一样的,每当我说“我存在”,或在思想中领会这句句子,我思的真理就被确定了。[2] 但我一停止思我,我就不再意识到我和我存在。问题在于,在笛卡尔看来,“我生命的时间”本质上是不连续的。因此,我绝对的确定性只是存在于瞬间的闪现中,转瞬即逝。我必须在后来的瞬间重新开始我的自我意识,[3]重新把握我的存在,越过虚无的断裂重新找到我。但是, 如果我在每个瞬间又完全消失了,如果我在我已成碎片的时间延续中不能保持起码的自我同一性,自我固定性,我能认出自己,重新认同我吗?我闪现的断断续续的片刻决非我自己。
实际上,笛卡尔的我思所缺的是人格(Personalitaet), 即康德给这个术语定义的,“不同时间中我的同一性意识”。如果我无论是在我的过去,还是在我的将来都不能将我成就为我自己,我在现时现刻(它只有通过我的过去和将来才有意义)对自己的再把握也会受到损害。主体的即刻性意识是个矛盾的概念。一个如此破碎的、断断续续的我思的意识必然要求一个“外在真理的保证”。由于其缺陷,我思自己必须求助于上帝的担保。正是时间使自我的直接呈现产生了问题。我的时间的断裂性,它也是我有限性的标志,使我不能将我作为我存在的基础。不仅我在时间中的此在,如一切有限的实在一样,以一个由上帝的因果性而不断的重新创造为前提,而且还要求不停更新的东西,每次都在我的我性中证明我。
我思所有的路都导向上帝,但无限的概念的思想也是从我思中显现出来的。如果这个概念先行于有限,即我自己的概念,那么这也是在我之中发生的。我在我绝对的孤独中找到无限的入口,虽然它超出了我的把握能力,但这个先验的概念仍是我的概念。我思以上帝为基础,上帝以我思为前提:笛卡尔的论证在此似乎陷入了困难。但这种许多人强调的循环却无疑是源自自我在虚无与存在,自我与他者,有限和无限“中间”的特殊处境。这种循环其实反映了近代主体性哲学本身的吊诡:主体要给自己奠定一个确实可靠的基础,但其可靠性却一直动摇不定,它无法不逸出自己去寻找自己外在的可靠性根据。这样,自我不能不像围着自己尾巴打转的狗一样,拼命要抓住自己,却怎么也抓不住。那条引诱它疯狂打转的尾巴,就是时间。
正是时间明显地动摇了我思的确定性,使它无法将自己作为绝对的基础。要解决这个困难,重新予主体以形而上学的尊严,似乎只要将我思从时间中解放出来,宣称自我的无时间性就可以了。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讨论同一性问题时认为,同一性概念必然要和某种实体观念,如一棵树或一个人联系在一起,才有用。使我们说某个特定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在于它是的那个东西。只要那个特定东西的种种变化仍是那种东西的特性,是那种东西的概念允许的,那么尽管有种种变化,那个特定的东西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一棵树多年后尺寸大了许多,但仍是同一棵树,因为那种变化正是树的特点,是树的概念允许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有隐蔽的实体来保持事物的同一性。但问题在于,什么变化是允许的,同一性的标准在哪里?正是在这里洛克没有继续走下去。虽然他看到了实体概念的无用,但仍保留了它。这使他陷入混乱。
洛克把人分为实体人(man)和人格者(person)。 他认为实体人的同一性在于他的生物组织。他把人格者定义为“有理性和反思,能认自己为自己。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是同一个思维的理智存在者。”人能认出自己是由于意识,而意识与思维不可分,思维对于意识是根本性的。也就是说,洛克通过“实体人”和“人格者”两个概念将人区分为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和理性意义上的人。只有人格者才是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者。人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就在于他们能认出他们的行为是他们所为。这包括两层意思:1.在做的时候意识到正在做什么。2.能记住曾做过。因此,洛克说人格者的同一性标准与实体人不同,他的同一性标准是意识。“只有意识能使人人成为他所谓‘自我’,能使此一个人同别的一切有思想的人有所区别。”[4]
更确切地说,人格者的同一性标准是作为记忆的意识:“如果我同样意识到,先前曾见到方舟和挪亚的洪水,去冬看到泰晤士河底泛滥,在现在又在这里写作,则我便会确信现在写作的我、去冬观察泰晤士河泛滥的我、和以前观察洪水为祸的我,是同一的自我,……这个正如现在写此论文的我,是和昨天从事写作的我是同一的我自己一样(不论所谓我是否是由同一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实体形成的)。”[5]但是, 仔细想想,就可发现记忆不能是个人同一性自足的标准。因为记忆可能有错,如果只以自己意识为参照系的话,这错甚至都没法发现。其二,一个人说他记得,实际上却不一定。其三,想象和做梦的内容一旦成为记忆后,记忆根本无法作为自我认同的唯一标准。庄生梦蝶的故事足以说明记忆不足为同一性标准。
也许是预感到记忆不足为同一性之唯一标准,洛克提出了精神实体的学说,以说明人格各种性质可以历经时间而终能九九归一,以及它们聚合为一个空间的领域。但是,按照洛克的经验主义理论,我们的知识限于事物的性质,而不可能对实体有任何认识。但如果无论感觉还是内省都不能认识实体于万一,那么精神实体又如何能作为同一性的标准?此外,如果记忆是同一性的唯一标准,它与作为人格存在论基础的实体又是什么关系?事实上,经验地诉诸记忆或实体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自我同一性问题。
比起洛克,休谟在这个问题上要干脆得多,也彻底得多;但也离问题的解决更远得多。休谟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精神实体的学说。精神实体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在自己那里找到一个独一无二和简单的“自我”。休谟非常简单有效地论证说,他在自己那里找不到这个自我。既然它缺乏证明,那么关于人格同一的信念就是错误的。人只是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的一束或一组知觉。休谟说他在自己中只能发现知觉。这样,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考察人们(包括他自己)如何“假定我们自己在我们一生的全部过程中拥有不变和不间断的经验”。
休谟认为这是由于人们没有区分一个在假定时间的变化中保持不变和连续的对象的概念(同一性的原型),和存在于前后相继中,由一种密切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几个不同对象的概念所致。我们混淆了这两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精神的惰性,它使我们满足于它们表面的相似。我们把同一性给予变化的事物,实际上并无明显这么做的理由,结果是既然找不到这样做的根据, 就发明一个, 这就是形而上学关于实体和自我(self)的幻想。但这都是空洞的解决。虽然在人的思想、感觉、记忆间有充分的相互联系来解释我们为什么错误地把统一性赋予人,实际上却找不到统一一个人的东西。“关于联系着对象的同一性的一切争论都只是一些空话,实际上仅仅是部分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某种虚构或想象的结合原则而已。”因此,“关于人格同一性的一切细微和深奥的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只可以看作是语法上的难题,不是哲学上的难题。”[6]
二
经验主义关于个人同一性的结论使康德看到,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以经验的方法来论证和解决。自我不能通过经验和在经验中,而是相反,只有超越经验,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和给自己奠定确实可靠的基础。构造现象世界的主体自己不能是现象,它不是与经验的意识有关,而是与先验意识有关。先验意识先于一切经验,使之可能。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只不过就是我思,它能伴随我的所有表象,[7] 是一切知识的最高条件。只有经验的我才像一切现象那样在时间中,而先验的我则不然。康德将先验的我规定为一个“纯粹、原始、不变的意识,”[8] 一个“恒常的我”[9]。 康德试图通过区分经验的我和先验的我来驱走使我思之明证动摇的时间性这个邪恶的精灵。
就像近代的大部分哲学家那样,康德比笛卡尔还要笛卡尔。他从同样的基本立场出发,要将它重新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他批评笛卡尔没有将作为纯思的主体作为理论中心,从而混淆了先验意识和我的内在直观意识。通过将我思规定为先验意识或先验主体,康德的批判实际上已经开始将主体上升为纯我和绝对精神。统觉由于它的构造功能被视为现象世界可能性之条件。一切现象“统统在我,即我的同一自我的规定性。”[10]“如果我取走这个思维的主体,全部物质世界(必然)因而被消灭,因为它不过是我们主体感性的现象和同样一种表象而已。”[11]
这样,只要康德划定的现象与本体的界限被取消,主体就能因此成为存在者的根据。它将不再只是“自然的形式统一”的发动者,而且也是物质实在的创造者,我和世界,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转化在其创造中的上帝的逻各斯。[12]这个绝对的主体性,因为始终只是与自己有关,所以不应与一个经验的个人的个别意识相混淆。它必须是一个普遍的主体,或一个直接的主体间性,如黑格尔说:“一个我,那是一个我们,一个我们,那是一个我。”康德在这里为黑格尔铺平了道路。
尽管康德的先验主体逻辑上可以预期到近代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体性,但那却不是康德自己的想法。《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把普遍、自足的绝对主体贬为先验假象和形而上学的幻相。康德对于笛卡尔独断论的批判同样也适用于费希特、黑格尔或费尔巴哈,甚至也适用于他自己的先验意识的学说,就它已预期了一个绝对主体的学说而言。这都是由于《纯粹理性批判》包含了一个存在论的不一致。
从《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开始,康德事实上就在两个非常不同,甚至是矛盾的先验主体概念之间摇摆。在“先验分析论”中,重点是放在主体的自发性,它的主动的综合活动上。但“先验辩证论”却又夺走了它的构造功能;它是“(意识的)纯粹形式,”[13]“一切表象中最贫乏的”,“一个内容完全空洞的表达式我”[14]。我思形式的抽象只表达了一个重言式句子我=我。它的谓语也只是分析(而不是综合)判断,只阐明这个抽象同一性之逻辑涵义,却不让我们认识实在的事物。如果我思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它就不可能彻底与它给予形式的东西分离。因此,坚持非时间性的先验意识和处于时间中的经验意识间的本质区别是不可能的。康德在这一点上犹豫不决,但他的第三谬误推理批判最终做了决定:我们决不能决定是否我思不像其它思维那样,同样处于流转之中。[15]时间性的邪恶精灵并未被驱走,批判仍陷入它试图要解决的笛卡尔的困境。关键是外在世界的现实性和我的同一性的关系究竟为何?
但批判本身隐含的另一种倾向却使它和笛卡尔的想法更为接近。按照康德二元论的存在论立场,也可以得出下列推论:因为主体是它知识的作者,它不能把握存在。自我不能在其存在中把握自己,因为关于我所是的本质“什么也不能给予思想”[16]。这样,我将自己规定为我思,碰到的却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作为现象,我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逃离自己。每当我以为我在我中找到了我,又认出了我,认出我怎样存在时,我陷入了先验假象。其实假象的原因在于硬要将我思与作为现象的我分开,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内在形式,试图在这样的分裂中像把握物自体那样来把握自我本身。人们抓着一个空洞的形式来套实际的现实,然后把这个形式主体的(分析)逻辑谓语变为一个实在主体的(综合)现实特殊性。因为重言式的分析判断与感性直观的条件没有关系,人们就试图不管时间来规定主体的生存,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时间的“主体本身”(Subjekt an sich)的辩证假相。
但这决不是说康德以主体自身现实的存在为前提,因为现象与物自本的区别在康德那里不是两个不同对象领域的区别,而只是两种认识方式的区别:服从感性直观的被动接受的自发性和理智直观的绝对自发性的区别。理智直观不是根据存在者来规定,而是通过一个创造活动从自己产生。因此,“人……自己不能……认识他自身是怎样的……,因为他没有创造他自己。”[17]我不能把握主体本身,这是我有限性的标志。它并不表明在经验的我后面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我,而只是提醒我笛卡尔的真理:我不是自己的原因,不存在我的自我构造或自我建立。形而上学的主体是纯粹理性的幻相。但一个不能知道自己为何而只是一个形式的自我,它的可靠程度决不会超过笛卡尔的我思,当然它也无法完成我思想要完成但却不能完成的任务。
三
康德关于先验主体的正面规定与阐述充分暴露了近代形而上学主体观念的不足,而他对围绕着自我的四个谬误推理的批判却进一步揭示了近代形而上学主体哲学的种种错误观念。康德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些批判来使他的主体概念建立的可靠的基础上,但在我看来他是在解构近代主体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预示了主体在本世纪的死亡。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害怕面对一个空洞的主体概念,总急于要通过理性的谬误推理来填补主体的空白,这就产生了独断论的“理性心理学”。“理性心理学”的第一个谬误推理是把自我或我规定为实体。根据第一批判的“先验分析论”,实体范畴指的是在时间中作为一切变化基础的固定存在的东西。如辩证地将它用于主体,就会产生“我的自我客观固定不变”的假象,[18]产生我的去时间化。理性心理学从这种在时间中固定不变的假象中独断地得出外在于时间的固定,“(灵魂)本身超越生命的固定不变。”形而上学的实体—主体首先就是不死的灵魂,一个自主、自足、绝对的存在者。这个存在者有能力确立自己,能在其自我确立中继续存在下去,抗拒时间中此在不停的变化。它能在时间中保持不变,是因为它是由自己确立自己,它已经存在于自身之中。一切行为的主体都是实体,而实体在绝对主体中完成自己。
自我成为主体后,就避免了它的有限性,在持续存在的幻觉下否认自己的时间性条件。它声称从它自己、通过它自己而持续存在,而不是被与外部事物和一个立法的他者的关系所改变。康德将这样的主体视为理性的谬误推理,视为先验假象。“一个自为作为主体的东西的概念,不能作为单纯的谓语存在,也不能依靠自己拥有客观实在,……因此,如果在实体的名称下指一个可以被给予的对象;如果它成为知识;它必然有一个持续不变的直观,……作为基础。但是现在我们在内直观中完全没有这样持续不变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在思维中保持不动,我们就缺少必要的条件将实体的概念,即自为存在的主体概念用于作为思维存在的自我,这样结合起来的实体的朴素性就完全取消了这个概念的客观实在性。”[20]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主体根本没有与实体划等号的根据。不死的灵魂、绝对主体、人格的同一性,都有没有意义的表达。
其实,康德的主体概念除了逻辑和语法意义外,没有什么剩下,它只有在实践的层面才能得到。虽然“先验分析论”给了主体性一个突出的地位,但“先验辩证论”又加以否定。康德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为了避免时间的“骚扰”和“破坏”,主体必须空洞化,主体不能与人、个人、自我相提并论,因为主体不是人,先验主体性不能还原为人的经验实在性。批判不是人类学,在先验层面上,话语不能是关于现象,关于人的。自我(Ego )并不必然是主体:主体的存在不是自我特殊的存在方式。作为主体,我不再是我自己。但是,康德以后的哲学家一方面觉得康德的主体概念过于空洞,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打通,来充实主体,于是就将先验意识直接作为对象意识,主体通过将自己对象化来构造对象,对象化是主体性的本质。许多后康德哲学家就是这样来解释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以这种思路看,主体不像谢林讲的,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是绝对的主体性与对象的客观性恰好重合。如果主体试图通过自己的强势行动把自己强加给自我,它就失去了他的我性。这样,主体的形而上学就是一种客观主义。先验主体性通过对象化和剥夺自我的我性和单一性同时在解构主体本身。
康德倒是看到了将先验我的形式视为对象的危险,因为这样势必使我消失在对象中。但如果我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既不在我的现象,也不在我的先验形式被把握,那么我究竟是谁?“先验辩证论”明确告诉我们:我不能认识我是什么。那么我是否能至少确定:我存在?康德的思想能否讨论自我的此在,以阐明我思和我在的关系?令人惊异的是,康德在这一点上立场依然没变。他认为我思与我在的关系是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我思”的句子直接表达了一个“此在”,它“本身已得出了一个给定的此在”[21]。但是,此在意味着经验个人的特殊、个别、独一无二的存在。一百个塔勒可以分析出一个塔勒的存在,但作为非个人的、普遍的先验形式的我思,却是分析不出作为此在的自我。否则,它将重蹈笛卡尔的覆辙,而这正是康德要竭力避免的。按照康德的思想,自我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既不是现象,也不是物自体;既不是单纯经验的,也不是纯粹先验。但这样的自我在康德的体系中找不到它的位置。那么剩下一途就只有将它解构。
如果我思可分析出我在,即我思维地存在着,那么,我是谁(什么)?我只是我自己此在的感觉,直接的自我感觉,没有心理内容和情感色彩,虽然在时空中。《判断力批判》明确指出,感觉最终是物质性的东西。[22]但是,我思的存在来源于一个不是经验、几乎是下感性的(untersinnlichen)感性,一种先验的感受, 像是自我生命躯体那样的东西,却要在人类机体所有现象的具体性和自我表现上来感受。这个个别性以时空条件为前提:如果一个自我的“纯理智表象”只是一个“我”的物质表象,那么通过它给予我的就不是我所是的那一个自我。但自我的单一性不只是所有存在者中一个特殊存在者的单一性,他人中一个特殊个人的单一性。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既不是现象,也不是物自体;既不属于感性世界,也不属于理性世界的东西,只能在一切世界的观念性和现实性还原的终点被把握。它谜一般的此在只有在其同一切不是它自身的东西的根本区别中被把握。在我对我(Ichheit )的准知觉中,我感到我不同于所有别的东西,我将自己体验为一切存在者的他者。好象我是存在本身,是一个和单一。我的区别感是第一明证,无条件的真理,直接揭示一个存在的确立。就是这种感觉在原始的统觉中伴随我所有的表象,给世界的表象,尤其是我自己独有的世界表象,打上我的印记。对于康德来说,这种自我中心论的区分是最终的,不可还原的,是世界的零点。他者的他性,存在或上帝,都从这个自我一中心向我显示。
但是,也没有什么比原初的感觉更棘手,更不稳定的了。它不但没有达到通向可靠的确定性的道路,反而不断遮蔽自我—真理,使自我论区别日渐消失,陷入它特定存在的不断遗忘的运动中。在一个客观世界划一的空间和时间中,我将自己表现为他者中的一个,社会躯体中的一分子,大全中的一小块,众多身体中的一个身体,存在者中的一个存在者。但是,自我区别是确立别的此在的前提这一点没有变。为了融入社会中,或者消失在客观性中,我必须已经开辟了一个视域,它们能作为与我有别的东西向我显示。我必须从我的区分感觉出发,给我世界的意义和他者的他性。在此意义上,说“一切都是我的现象”,和“我同一自我的规定性”[23]没错。问题是要更准确地分析现象不同的构造模式,指出老的自我的存在意义是如何,即通过“在我之中”我的感觉的何种变化出现。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思考经验中给予的自我事实的多样性,和试图描述他共在的结构。
自我区分已经隐含了一种与和我有别的东西的关系,它以“没有一个非我的自我是不可想象的”(胡塞尔语)为前提,或者以海德格尔说的“此在本质上本身就是共在(Mitsein)”为前提。然而,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既然以自我为中心,就不可能再揭示自我在其原始的敞开中是如何消失为存在和他者,客观化或实体化自身,从而摆脱先验假象。相反,作为单一者和有区别者的自我是形而上学的假象,它表明自我论区别的瓦解。通过非法越出它的我性,形而上学的假象将自我的单一性上升到超验的普遍性,上升到类主体的抽象。事实上,近代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无法保证自我的单一性,因为自我的单一性是与时间密不可分的;可是,在将时间引入自我问题等于消除自我的情况下,形而上学宁可让它变为一种超验的东西,无论这是叫纯我,绝对精神,类存在,无产阶级,还是超人。反讽的是,尽管所有这些假象毁掉了单一自我,但它却给了它们它的身体和生命的假象。
另一方面,即使坚持自我是感觉,进一步分析问题也不少。我是这个自我(Ego),这个自我的特殊同一性就是我自我的存在。 但这本身难道不也是假象?自我存在的确定性,自我性(Selbstheit)的确定性可能只是又一个版本的、更难揭破的假象,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我生存的感觉中。但我(Ichheit)并不是自我(Selbstheit), 我不可还原的存在的感觉并不无条件地指:每当我感到我存在时,与我自己同一的那同一个我存在。我们只是在瞬间流逝的显现中感到自己,但能在不连续的瞬间流逝中一直认出自己和保持确定的同一性吗?康德认为,人格假象就是由此产生的。康德对人格假象的批判是:我的同一性规定不是综合的,而是纯形式和分析的,它只是表达了统觉中我=我的逻辑同一性,“完全不证明我的主体数的同一性。”[24]那个在一切思想中都出现的同一性之极(Identitaetspol)不是持续存在的直观。它不是无时间的,
而是全时间的(
allzeitlich ),或“贯穿时间的”(durchzeitlich)。它和现象之我一样是暂时的, 它将现象之我带入一个形式。自我就此被确立,在每一瞬间认同自己。
但是,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我决不能确定我重新找到了自己,在我的自我(Selbstheit)中重新把握了自己。把自己规定为感觉,就是把它固定在时间性中,使它的情况更麻烦,而且个别化需要感性直观的条件。如果感觉不处于时空中,它就不再是感觉,就不再是我所是的这个单一的自我。自我论区别将消失。自我(Ego )的时间化是它单一性的条件,却也一下毁了它的自我性(Selbstheit),使之无名。如果我是自我(Ego),我不再是我自己。如果我每个瞬间都裂变, 我不再真是一个个人,我不再是人格(person)。也许是在非人格中中立的本质本身,但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本质。
康德对付时间精灵的法宝是区分先验的我和经验的我。先验的我在时间中的同一性的规定是先天有效的,因为它的意思是“在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全部时间内,我意识到此时间属于我之自我的统一性,所以说这全部时间在作为个别统一的我中,和说我以数的同一存在于一切时间中是一样的。”[25]康德认为,当自我意识是时间意识时,自我(Ego )就可以免除时间的瓦解了。因为这时时间必须具有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品格,因而是一个划一的系列。而自我的同一性归根结底是靠时间的先验性来保证的,但它的同一性不是那种勉强在不同时间保持不变,而是指它本身具有的先验性,即它是先验的我。但如果自我认同的根源在一个先验的我,那么自我还剩下什么?单一性,个别性只属于经验的我,但它们是先验的假象。近代形而上学拼命要突出我,抓住我,以我为基础,以我为出发点,但如果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我就是我”的空洞形式,那它岂不是建立在沙滩之上?而它的全部努力最后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造成近代哲学的这个悲剧的因素有很多,但时间问题无疑是个重要的因素。当康德将时间先验形式化,以将其纳入主体的控制时,他实际上是在将时间非时间化,即剥夺了主体的时间,使主体成为无时间的。这也是先验主体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他以为这样可以保证主体的无限性,却不料实际上宣告了主体必然死亡的命运。人必然要在存在中,即在时间中理解自己,剥夺人的时间性,也就是在消灭人。时间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只有在存在中、而不是在意识中,人才能真正把握自己,海德格尔最终揭示了这一真理。
注释:
[1]Heidegger,Nietzsche,Pfulligen,1961,Bd.2,S.147.
[2][3]Descartes,Mediations de prima philosophia,Lat.dt.,hg.v.L.Gaebe,durchges.v.H.G.Zekl,Hamburg,1977.S.46/47(Med.II,§6)S.44/45,(Med.II,§3).
[4]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310页。
[5]同上,第316页,译文有改动。
[6]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3页。
[7][8][9][10][11][13][14][15][16][18][19][20][21][23][24][25]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B 131.A107,A123,A129,A383,A382,A355,A364,A429,A363,B415,B412F,B418,A129,A363,A362.
[12]参看R.Kroner,Von Kant bis Hegel,Tuebingen,1921,Bd.1,S.60f.
[17]Kant,Grundlegung zur Metaplysik der Sitten, AkademieAusgabe,Bd.IV,S.451
[22]Kant,Kritik der Urteilskraft,Akademie Ausgabe,Bd.V,S.277.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康德论文; 笛卡尔论文; 同一性论文; 主体间性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纯粹理性批判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