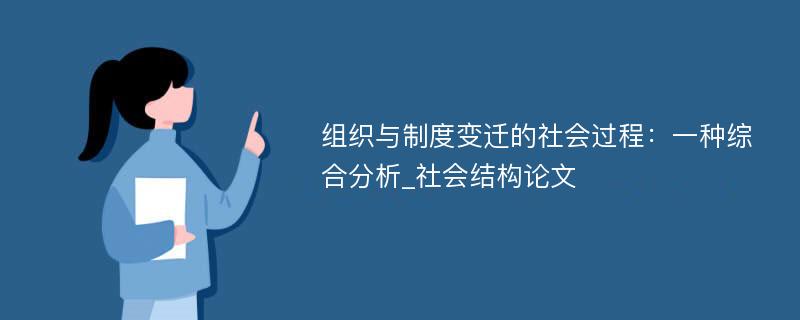
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种拟议的综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拟议论文,综合分析论文,过程论文,组织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西式的现代性猛烈地渗透、撞击和攻占传统的中国社会以来,这个社会就始终陷入在被迫的动荡和主动的变革之激流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始终作为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把合理合法的标尺。无论是旨在彻底颠覆现有社会结构的革命或变革,还是在中国社会基层曾经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和改造运动,且不说其立场和方法如何,都是符合“变”这一基本精神及其主流话语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虽说社会变革的方式少了那种革命性的颠覆色彩,但其参照现代化模式彻底改造社会体制之流弊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改革已经成为了一种占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老百姓进行日常判断所依据的价值形态。
我们所要考察的“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变革和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在这样一个改革成为社会惯性或习惯、改革本身作为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时代里,“变”(change)成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常态(regularity)。这样的常态或常规性,从根本上说并不具有一种实质性的涵义,许多社会现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变化和变迁,并不具有具体的、实在的意涵,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变而变”这种形式上的动力促成的。但变迁已经成为我们社会首要的形式规定。因此,要考察这些年来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首先必须对变迁本身做深入的思考。换句话说,在没有充分理解变迁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之前,我们尚不能奢求去直接找到组织变迁的具体内容或是制度创新的具体项目。若究其实质内容,则首先要看看这个所谓的“变迁”都有哪些形式上的特征:或许,政府推动变迁的坚决程度,人们的意识中渴望变迁的迫切程度,变迁一词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合法化程度,以及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变迁实际发生的速度,会对组织和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产生更为实质性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中国组织变迁的研究,一开始就会面临一种困境:在这样一个在变动中融汇着各种复杂因素、且各种复杂因素时刻处于无穷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必然会面临现有的理论解释力不足的状况;而就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变迁格局和态势,很难让我们有可能针对一种具体组织形态做长期的结构性的考察。换言之,我们曾经刻画的某些组织形态的结构性因素,也往往会在变迁之潮中迅速地流失或转移掉,继续成为有待观察和刻画的新的因素。因此,要想对中国社会组织变迁过程进行一次完整的结构性考察和形态学分析,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工作。这样一来,我们的组织变迁研究就要换一种有别于静态上的结构性考察的思路,它并不囿于刻画和描述组织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或者是对制度安排及其社会行动效应的分析,而是要从组织的内部,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去寻找其在社会变迁意义上的逻辑规定性。
超越类型学,意味着超越类型学的分析前提,即面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变迁与创新,我们很难用一种特定的制度模式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而应该回到构成社会组织之特质的一个更原初的起点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超出制度主义或类型学的研究范式,去寻找一种更切入社会组织性质的范畴。超越类型学,也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地回到事情本身上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在变迁过程中,不同的组织既有其本土的生长基础,同时也主动或被动地吸纳了外来的制度因素,套用马克思的观点,中国的社会组织既有它的原生形态,又有其次生形态,甚至还夹杂着许多成型或不成型的制度移植的形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克服纯粹的类型学所带来的各种局限。
从上述角度出发,在分析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时,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制度的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的内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使一种制度在渐进的状态下逐步地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第二,把嵌入性看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第三,承认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第四,强调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硬核与保护带的互动:组织和制度分析的一种维度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个理论系列中各个理论结合而成。其结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硬核”,表现为某种非常一般的、构成纲领发展基础的理论假说;(注:比如哥白尼纲领的“硬核”是行星的公转和自转,牛顿纲领的“硬核”是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硬核”是唯物史观。)一是“硬核”周围的保护带,不仅包括各种辅助假说,还包括初始条件时所依据的假定以及观察陈述。当“硬核”遇到反常或否证的时候,即当科学研究纲领与观察实验资料有矛盾的时候,就要调整作为保护带的辅助假说和理论,以保护“硬核”不受否证。(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保护带调整可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可导致进步的问题转换,说明这个研究纲领是成功的;另一方面,也可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说明这个研究纲领是不成功的。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是每一个环节都能预见新的事实,事后在人们知识生产的实践中能够得到证实。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有两种方法: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是告诉科学家哪些研究途径应该避免,告诉他们不应该干什么。它具体要求科学家们在科学研究纲领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修改或触动其“硬核”,任何修改“硬核”的企图都是等于放弃整个科学研究纲领。正面启发法是告诉科学家们应该遵循哪些研究途径,表现为一些关于如何改变、发展科学研究纲领,如何修改、精炼保护带的提示或暗示,它是人们预先设想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研究方向、次序或政策。正面启发法中有三个功能。首先,它决定科学家对所研究问题的选择。科学家们在提出第一个理论或模型时,他们已经预计到会有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其次,通过建立辅助假说“保护带”来消除反常,保护“硬核”。最后,由于任何科学研究纲领一开始总是陷入反常事例的包围中,所以,通过正面启发法可使人们集中精力,按正面启发法所规定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日趋复杂的理论或模型。在这里,正面启发法使人们能不依赖已知的反常,而且先于这些反常而采取行动。(注:查尔默:《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8-97页。)
一个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必须具有严谨性,从而有可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确定的纲领;其二,能够导致新现象的发现。一个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在进步的和退化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竞争中,科学家们总是趋向于参加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这即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这样,当科学研究纲领处于前进的时期,它就有足够的启示指导的能力去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当它处于退化的时期,其“硬核”在经验和逻辑的压力下,也可能破碎,但是,新旧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仍可以有某种嫁接的关系。
在科学研究纲领中,拉卡托斯强调了“证实”新预见的证实作用。他认为,只有新的事实最终得到证实,知识才能增长,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才能持续地进步,并在与对立纲领的竞争中战胜对手。与此同时,拉卡托斯也提出了一个摈弃理论的标准。当一个新的理论较之原来的理论具有超量的信息内容,而且这一事实通过检验得以确认时,原理论就会被抛弃,并被新理论代替。拉卡托斯强调指出,威胁某种理论生存的不是否证和反驳,而是另一种理论,一种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有超量内容的理论。
依此理论出发,我们来观察组织和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制度看作是在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得到认可和强制执行的、并内化为相应的社会角色的某些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和取向。单位作为一种制度,即具有这样的特征。这些行为规范,融于人们在单位中所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之中,调整着单位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和保证了单位成员间的社会互动,并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互动的最基本的组织和制度的结构条件。从理论的角度看,一种制度主要具有四种结构性要素(注:Hermann Korte und Bernhard Schaerfer (eds.),Einfahrung in Hauptbegr iffe der Soziologie.Opladen,1995.J.A.Schülein,Theorie der Institution,Opladen,1987.H.Schelsky,Zu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r Institution.Zur Theorie der Instittution,Duesseldorf,1970.W.Powell and Dimaggio (eds.),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1.制度建构的主导思想(Leitidee),或这种制度建构的意识形态。这种主导思想或意识形态被人们所内化、所承认以及被正式地确定下来。2.制度中所规定或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这种社会角色在制度或组织中行为的内在规定性。3.制度中的规则和行为规范,依此来定义人们在一种制度或组织中交往与互动的方式。4.制度中被物质化或形象具体化的象征(Symbol)和设置。
那么,在制度的这四种结构性要素中,哪一种又是最核心的要素呢?从理论上讲,这四种结构性要素在抽象层次具有差别,意识形态的抽象层次最高;其次是规则和规范,再次是社会角色,最后是象征符号。随着系统复杂程度的增加,整合系统的机制也必须更抽象。(注:N.Luhmann,Social Systems.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由此看来,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最有可能成为制度最核心的要素,其次是规则和规范。也就是说,处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结构,最核心的结构性要素可能是不同的。对于总体社会而言,或者是试图代表总体社会的政治组织而言,意识形态,即第一种结构性要素,可能是最核心的制度要素。而对处于中观层次的组织,一种被人们所认可、被内化或者被强制执行的规则和行为规范,即第三种结构性要素,是制度的结构性要素中最核心的东西。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理解,这里所指的这种组织和制度的硬核与保护带究竟是什么。组织和制度的硬核,应该是从根本上决定组织和制度区别于其他的组织和制度的特征属性,它类似于DNA的特质,从根本上决定着组织和制度的性质以及这种组织和制度与其他组织和制度的区别;同时,它也是组织和制度中稳定的和深层的内涵,从根本上抗拒变迁,而且就其自身的性质来说也不易发生变迁。(注:N.Luhmann,Ansdif ferenzierung des Rechts.Frankfurt am Main,1981.N.Luhmann,Soziologische Aufklaerung.Opladen,1982.E.E.Lau,Intention und Institution.München,1978.R.Lepsius,Interessen,Ideen und Institutionen.Opladen,1990.H.Hartmann,Funktionale Autoritaet.Stuttgart,1964.)因此,组织和制度硬核具有隐含性(深藏在日常的组织行为和制度表述之后)、抗逆性(面临灾变性环境变化时也不会轻易妥协)和稳定性(不会因为时空的延伸、内外的变故而数变其身)等三个基本属性。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制度的硬核。一方面,制度的硬核主要是指制度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化(institutionalized culture),一种被特定制度深刻影响和内化的文化。这种制度的硬核包括某种制度安排的合法性、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所有制形式。制度文化不完全是一种信仰,更确切地说是人们实际行为过程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另一方面,制度的硬核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取向。这种制度化的行为取向可能隐含在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中,也可能通过一种合法化的程序固定下来。在一个国家所有的单位组织和制度中,各种不同的角色有着特定的行为规范,人们在其中的资源分配与消费有着特定的规则。这种组织和制度内有着各种不同的机构设置以保证规则的实施。人们认同这些规则,在其中社会化。通过一定的程序和仪式,这些规则被合法化,要求人们强制性地执行,并以此来区别于其他非国家所有的单位组织和制度,进而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内核。
由于制度的硬核具有隐含性、抗逆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所以,一般的改革所涉及的只是制度的表层或表现,其内核常常被厚厚的一层保护带包裹着,维护着。而制度的保护带主要是指围绕在特定制度周边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或直接对应的组织行为和规范。所谓保护带的调整,主要是指人们相应地改变政策、行为、规范以及局部的制度安排,以期达到保护制度的硬核不受外部变化或压力的影响,维护自身免被改变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制度是规则,而组织则是这些规则限制下的集体行为,是制度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指的是特定组织和制度的硬核从量(quantity)和质(quality)两个方面逐渐发生变化的过程。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
首先,这种变化来自于宏观环境的压力:1.支配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及其连带的失范效果。2.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3.全球化的压力及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和制约。其次,这种变化来自于外部的压力:1.示范效应。在和外界环境比较的过程中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了不满意和相对剥夺,从而愈来愈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2.模仿机制。改革开放使人们更容易了解和感受新鲜的和更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在模仿过程中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学习的愿望和对现状的不满意。最后,这种变化也来自于组织和制度内部愈来愈强烈的改革要求:1.当一个组织内部社会团结程度较低、运行状况也不理想的时候,组织和制度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2.不同所有制状态下组织之间的竞争以及这种竞争所造成的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上愈来愈大的差距,也迫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依照各自不同的角度产生愈来愈强烈的要求变迁的呼声与动力。
组织和制度的硬核不可能在上述压力下即刻发生变化,最先做出反应和变化的是这种组织和制度的保护带。或者说,保护带在这种压力下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不断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路径依赖所造成的一种行为惯性;一是行为的嵌入性,因为人们的行为,哪怕是一种自身极力想要改变的行为,都难以摆脱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人们主观上想要调整的组织和制度的保护带,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行为之路径依赖和嵌入性的影响。组织和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就是在不断受到这些影响同时也不断试图摆脱这些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注:从逻辑上讲,调整保护带所带来的结果有三种可能。首先,调整保护带的策略成功,此时,制度硬核得到成功保护;第二,调整保护带的策略只获得部分成功,使制度硬核部分直接暴露在外在环境的直接压力之下;第三,调整保护带的策略完全失败,全部制度硬核均暴露在外在环境压力之下。当制度硬核面对环境压力时,它可能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而发生渐进性变迁(这是本文所要考察的情形),也可能由于制度硬核表现得过于刚性而无法适应,因灾变而消亡,整个制度安排发生革命性变革。)
嵌入性: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环境
嵌入性理论的提出,归功于三位学者: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White),以及怀特的学生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当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将其研究兴趣与热情倾注到讨论制度的构成和起源、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及需求与供给时,却往往忽略了在特定社会中产生这种制度的社会结构与环境。嵌入性的理论恰恰是在这个方面为制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波拉尼首先指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一个社会的联合与稳定的过程紧密相联。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一种由社会定义的功能……由此产生相应的价值观、激励机制和政治形态。在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被制度化。……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注:K.Polanyi,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odberg (eds.),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al Life.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2,p.34.)。在这里,波拉尼首先提到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对非经济的结构与制度的依赖。或者说,人们对某些经济行为与模式的选择,从根本上来看,往往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所影响的结果。
在分析市场产生的社会过程的时候,怀特指出,市场是关系密切的企业通过相互观察彼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结构,而且,市场亦通过这种重复关系而自我复制和再生。市场的供给则是生产厂家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怀特认为,生产商们在一开始就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他们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特别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所以,生产商的社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营和价格信息。其次,处于同一网络中的生产商相互传递信息,并相互暗示,从而建立和保持一种信任关系。按照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约定和信任,人们从事着生产与经营。最后,市场制度事实上产生于同处一个网络圈子里的生产商,而不是生产商按照凭空而起的市场制度来行事。换言之,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规则的反映。
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发展了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他和他的同事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经济行为从内容和方式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会受到其行为发生的那个社会环境及其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定的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Mark Granovetter once said that:"we suggest that 1.economic action is a form of social action; 2.economic action is socially situated,and 3.economic institutions are social constructions."In Granovetter,Mark and Richard Swodberg (eds.),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al Life.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2,p.6.)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批评了关于人类行为概念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over-and under-socialized conceptions of human action)两种极端观点,因为它们忽略了人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格兰诺维特进一步重提“嵌入性”,深入地说明波拉尼的观点,并明确指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网络,信任则是嵌入网络的机制。从根本上说,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产生有效率的互动。总之,在格兰诺维特那里,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和互动往往产生在间接或直接的相识者或熟人之间,嵌入性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信任,而非信息。(注: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1360-80.Mark Granovetter,Getting a job.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Granovetter,Mark and Richard Swodberg (eds.),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al Life.)另外,按照刘世定的理解,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的讨论涉及了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是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的行动的视角,即以“嵌入性”挑战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关于人的行动的基本假设;一是在“嵌入”的具体内容上,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基本要素,从而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领域引入进来。这两个层面,正是格兰诺维特和波拉尼的有别之处。在波拉尼那里,一方面,他提出问题并没有达到人类行动之基本假设的抽象程度,另一方面,波拉尼注意到的只是嵌入制度,而不是人际关系网络。(注:刘世定:《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72页。)事实上,嵌入性的研究不但要弄清楚嵌入性为什么会存在,而且还需要深入分析嵌入性对经济行动与制度的影响,以及嵌入性的构建问题。
上面,我们从硬核与保护带之互动作用的角度分析了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指出制度的内核本身具有抗拒变迁的特征,组织和制度通常会在保护带不断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不过,这里尚未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制度与组织变迁的结构环境。中国目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其目的都是为了重新调整组织关系和制度安排,合理规范政府和企业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行为,重新定义人们在新的制度中行为的不同条件,并由此提高组织行动效率,顺利实现制度目标及其社会整合效果。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创新和变迁离不开我们现实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资源所能提供的条件。亦即任何一种制度总是要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中。制度设计得再合理,若不能成功地嵌入到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之中,或者说,倘若制度创新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遭遇到强烈的“排异反应”,那么,这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则最终不可能带来效益,也不可能为这个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和发展。那么,一种新的组织和制度嵌入社会结构环境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抑或这种新的组织和制度是怎样逐步嵌入到社会的结构性环境之中的呢?
首先,如上所述,这种创新与变迁的动力来自于宏观环境的压力,以及人们在对外部环境或群体示范与模仿的过程中自身改革与创新的要求。但是,外部制度以及人们行为的规则不可能简单地拿来和照搬,更多的是要按照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环境做出相应的修正和改变。对外部制度移植的修正和改变,我们称之为“制度变通”,它是一种旧的制度安排嵌入到新的社会结构环境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其次是制度适应。如果说制度变通是指一种已有的移植来的外部制度安排或规则逐步嵌入到新的社会结构环境的过程,那么,制度适应就是指,当这些外部制度成功嵌入本地社会结构之后,人们的行为逐步地适应这些制度或规则的变化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制度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具有主导作用;个人行为“嵌入”于制度、并被制度所塑造和指引,因而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在根本上离不开对制度的理解,个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因变量。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方面,一旦某种制度建立起来,它就能够规定人们进一步的行动。制度规范行为,在这里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意味。人们在特定的组织中必须遵守这一制度规范,否则就会因违规而受到组织规章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惩罚。制度按照角色和情境的关系确定人们行为的适当性,既包括对情境和角色的鉴别,也包括对某种情形下适当行为的确定,它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据此可以界定个人的适当行动、个人和情境之间的关系,制度促使个人去反思:当下是什么样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下,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较合适?这种角色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样的?”(注:J.March and J.Olsen,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9,p.160.)在个人做决定的时候,他的问题不单是“怎样扩展我的利益”,而是根据我的位置和责任,在此情境中,判断什么是我最适当(正确)的反应和行为方式?在多数情况下,规则和程序(即制度)是清楚明确的,个人总是跟随惯例,按照惯例的要求采取行动,个人的行为是被动的,是不断适应的过程。(注: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然而,另一方面,在制度的制约下,人们在组织中行为的适应,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在更多的情境下,同时还表现为一个积极学习的过程。(注:M.Douglas,How Institutions Think.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6.)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价值认同,人们对新的制度、新的规范与规则会逐渐由被动的适应转换为主动的学习和接受。在这样一个社会过程中,人们逐渐被社会化,逐渐接受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及其知识图式,建立组织行动中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力图使其变成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并最终使这种制度的安排“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嵌入”到人们自身的行为结构之中,变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和自身行为结构的一部分。所以,理解制度适应,需要考察上述结构化过程的这两个角度。(注:A.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London:Polity Press,1984.)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一种制度真正嵌入到了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之中时,这种制度同时也就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文化的烙印,形成为一种互依互存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形成起码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在一种组织和制度创新的初期,当这种组织和制度能够成功嵌入到社会结构中时,这种组织和制度就能够借助于这种相互的整合推动自身的发展,使其创新与变迁得以深化。其次,当一种组织和制度发展到了一定时期,需要进一步实现创新与变迁的时候,这种制度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高度整合,则会给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带来极大的障碍。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嵌入性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功能,是非常有益的。总之,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自我设计的社会过程,它客观上要求这种组织和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结构环境也必须发生变迁。
路径依赖:组织和制度的惯性
由制度经济学家诺斯首先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注:D.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Norton,1981.D.C.North,Transaction Costs,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San Francisco: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1992.D.C.North,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in U.Maeki,B.Gustafsson and C.Knudsen (eds.),Rationality,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New York:Routledge,1993.D.C.North and R.P.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同时参见柯武刚等《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年);程虹《制度变迁的周期》(人民出版社,2000年);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年);彭德琳《新制度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孙立平《从市场转型理论到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中国书评》1995年第7、8期。
)主要是描述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和将来所实施的制度、人们过去的行为对现在和将来的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这种理论告诉我们,一种现存的制度及其所塑造的人们的社会行为,都会具有一种“惯性”,一旦采取了某种制度,贯彻了某种社会行为,进入了某种特定的路径,那么,这种制度或行为就会形成一种惯性,为人们进一步的路径选择制造出一种依赖结构。按照诺斯的说法,即人们过去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决定着他们现在或将来的选择。
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主要有两种极端的形式:
“路径依赖Ⅰ”。是指一旦某种独特的组织发展轨迹确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强化这一轨迹。某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和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及其配套制度,从而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
“路径依赖Ⅱ”。是指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这样,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追加投资,只会强化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这种制度只能鼓励进行简单的财富再分配,却给生产活动带来较少的报酬,也不鼓励增加和扩散有关生产活动的专门知识。
诺斯认为,除这两种制度变迁的极端形式外,还有其他一些中间性的情形和方式。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情不自禁地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或者,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正反馈的轨道,迅速优化;或者,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继续下滑,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无法自拔。在这里,诺斯进一步分析指出,决定制度变迁的轨迹有两个因素,即收益递增和不完全市场。随着收益递增和市场不完全性的增强,制度就会变得愈来愈重要,自我强化的机制才会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根据诺斯的分析,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的机制取决于以下四种表现:(注:D.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第一是初始设置成本。即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第二是学习效应。适应新的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迫使组织和组织成员积极地学习,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和适应发展与生存的需要。第三是协调效应。通过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进而实现协调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他正式规则及其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和协调这项正式规则发挥作用。最后是适应性预期。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种维持现存制度的不确定性。
在分析路径依赖形成的原因的时候,诺斯指出,主要有四个共同的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路径。第一个因素是报酬递增。当一种新的制度实施能够产生社会成员普遍报酬递增的效果时,人们采用和认同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就愈大。第二个因素是不完全市场。市场的发育愈不完全,人们愈不可能在经济行为之前掌握准确和全面的信息,制度变迁的轨迹就会愈呈现出发散和不可预测的状态。第三个因素是交易费用。市场和信息愈不完全,交易费用的成本就会愈高,制度的绩效就会因此变得愈低。也正是由于高昂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使大量无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锁定”状态长期存在。第四个因素是利益因素。一个社会中的利益集团从现存制度中所得到的资源或好处愈多,则其要求维持现状的呼声就会愈高,要求制度变迁的驱动力和积极性就会愈低,阻碍这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会愈大。
在前两节里,我们谈到了制度的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的内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使一种制度在渐进的状态下逐步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其次,我们指出任何一种制度都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结构性环境,总是嵌入其中。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一种制度和组织嵌入到它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以后,人们行为方式和取向的变化会遵循什么样的规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人们对行为方式做出选择以后,他就很可能会按照其既定的选择模式一直选择下去,这种惯性会在随后形成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强化已经选择的行为方式。而如果在这时选择其他的行为方式,则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成本。因为人们的行为方式被社会化的程度愈深,在人们随后的互动过程中受到这种行为方式影响与制约的程度就愈深,可能性也愈大。
人的行为如此,组织和制度的行为亦如此。当一种制度和组织嵌入到它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以后,它首先要面临很多的选择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这意味着,在制度和组织变迁的过程中,一旦这种组织和制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就会很强势地沿着已经选定的路径继续走下去,这种组织和制度的既定方向也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发展进程中得到强化。换句话说,一种制度与组织的初始选择对这种制度与组织变迁的轨迹和将来发展的方向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一旦有了明确的选择,该组织和制度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有人把这种路径依赖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方面,这种路径可能会通过惯性和动能产生所谓的“飞轮效应”,推动一种制度和组织朝着一种正反馈的方向去变迁与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路径可能会通过惯性和动能触发一种负反馈机制,从而造成制度与组织陷入或锁定在一种死循环(doom loop)的状态之中,最终导致组织无效或停滞状态。(注:L.Zucker,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nn.Rev.Sociol.1987,13.M.Yang,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ness in a Chinese Socialist Factory.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9,no.22.B.Womack,Transfigured Community:Neo-Traditionalism and Work Unit Socialism in China.China Quarterly,1991,no.126.A.B.Weiner,Lehrbuch der Organisationspsychologie,Muenchen,1981.I.Sezeleny,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Toward a Synthesi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vol.101:1082-1096.David Stark,Path Dependence and Societies Strategies in Eastern Europe.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992,6:17--54.Andrew G.Walder,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2,vol.57:524-539.)
上述制度行为的惯性对于制度与组织的变迁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和规则制约下,制度可以增加社会、经济交换行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减少非规范社会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此同时,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和规则,制度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使组织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这些功能使得制度在正确的初始选择过程中能够积极地推动制度的良性循环与变迁。另一方面,一种新的规则或规范能够得以制度的形式出现,必然是交易各方共同选择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这种共同选择和相互妥协根植于各方在这种体制选择中实现了各自投入—收益之间的均衡。与此同时,制度的价值还在于它能够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一种稳定的长期服务,人们可借此对社会经济互动做出长期的预期,并由此产生安全感。制度行为的惯性对其变迁的推动与制约的双重作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制度的初始选择与影响这种初始选择的条件(初始条件)的重要性。
从改革以来中国制度与组织变迁的初始条件和过程来看,我们一直较为注意依托现有经济、社会组织进行边际制度创新。同许多其他经济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的变迁与改革不同,中国的组织变迁不是简单地采取开放市场,通过社会经济组织自由竞争来催生市场体系发育,更不是抛弃既有组织结构,另起炉灶,用全新组织来推动变迁和拉动改革,而是充分利用了原有计划体制中既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依托长期积累起来的组织和制度资源,通过有序的边际组织创新的方式来稳步推动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回顾多年来中国改革与变迁的历史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新生的经济组织几乎都是直接、间接依托原有国有经济与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延伸、嫁接、脱壳成长起来的,不少乡镇、村级政府基层组织以及城市的管理领导往往是组织转型的双重领导者。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许多在转型中新生的市场经济组织一旦达到某种规模,也要挂靠或寻求某种政府组织保护,向原有的组织性质靠拢。依托既有经济组织推进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改革的摩擦阻力,降低制度创新的风险,低成本地利用传统组织和制度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法制与信用关系淡薄,个体承受力较低,民间组织发育严重不足的国家,只有依托业已形成并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各级政府组织、国有与集体经济单位,才能避免大的被动与震荡,稳定推动改革深入。(注:参见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陈孝兵《路径依赖与体制变迁》,《新东方》2003年第4期;王小鲁《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3月20日;刘伟《转型经济中的国家、企业与市场》(华文出版社,2001年)。)在这里强调这一点,依然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制度与组织变迁的初始条件与基础。理解了这一点,就能进一步理解目前我们制度与组织行为的惯性。因势利导地利用这种行为的惯性,则是我们的组织和制度变迁难以规避和不可选择的策略、前提与条件。
意识形态: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
在一般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一种信仰体系,一种世界观,是一种系统的价值观念和规范(norms)。若从承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的角度看,意识形态是一种由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所倡导和推动的主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若从略带保守主义倾向的社会理论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则是一个社会通过价值整合来实现社会存在基础的集体意识。(注:E.Durkheim,The Division Labour in Society.Trans.by W.Halls.N.Y.:Free Press,1984.)因此,意识形态不仅被赋予更广泛的心理和文化涵义,而且通常还和人们社会化的过程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
1.意识形态可以影响和左右人们的利益表达。占支配地位的群体通常通过社会化的暗示和明示的方式,传递着他们的观念和世界观,再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化载体,通过各个不同的角度或方式,反复论证和宣传一种观点、主张和世界观,使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这样的观念意识,或者用它们来论证和归纳自身的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注:分别参见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A.Etzioni,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61。)。2.意识形态可以影响和左右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众所周知,社会化有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化的载体,并始终作为一种主导和主流的思想文化形态。接受某种意识形态,更多表现为一种主动、积极的学习过程。通过这样一种价值认同过程,社会成员总是潜移默化地承认现行支配秩序的合法性,将通行的世界观内化为自我的世界观,用通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为自我制定行为的取向和标准,从而完成自我塑造和实现的过程。3.意识形态可以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意识形态既可以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也可以成为阻力。意识形态可以用来指明社会变迁的新方向和新秩序,也可以使那些未预计到的变迁合法化。意识形态可以团结社会,也可以激励人的行为。意识形态本身作为一种承认的政治,造就人们自我实现的价值(注:L.Robert,Perspective on Social Change.Boston,1977.)。4.意识形态可以节约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各种行为费用,可以通过价值认同的方式使决策过程简化。(注: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53页。)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与他人的社会经济交往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一种相应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可以是公众的共同约定(common consensus),也可以是具有特定行为方式的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简化的认知图式安排;共享同一意识形态的人群会对相似事件做出类似的反应,这种共同知识的形成有助于合作,使达成共识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并形成比较确定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注:T.Cheek and T.Saich(eds.),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New York:ME Sharpe,1998.L.Buss,Lehrbuch der Wirtscha ftssoziologie.Berlin,1985.)。5.意识形态可服务于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能够定义和改变人们行为的取向和偏好。有的学者把意识形态的内在约束称为“价值权力”(注:S.Lukes,Power:.A Radical View.London:Macmillan,1974.),具有定义和改变人的行为偏好的功能,可以将一种由制度强制形成的“必须”(have to)规范转换成为一种靠人们自觉地去遵守的“应该”(should)规范。当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否应该遵循规范而犹豫不决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非制度化的行为规范被内化的程度,即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注:从这个角度,诺斯也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会选择投票而不是按照狭隘的个人主义行事(搭便车),是因为他接受了投票是公民光荣义务的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从而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个人计算行事。如果社会普遍信奉的某种意识形态决定性地塑造了个人的荣辱观、义利观、幸福观,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就能形成对产权的重要保护和产权界定中的重要机制。)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稳定性特征。有些学者把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来源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当一种意识形态为集体中多数人接受后,符合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往往被看作是合乎理性的行为,而挑战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则往往被看作是非理性的行为;其二,一旦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后,个人的意识或信念就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其三,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个别人或少数派很难改变主流意识形态。(注:P.Battigalli and G.Bonanno,The Logic of Belief Persistence,Economics and Philosophy,1997,13:39-59.)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意识形态对一个社会的变迁,对一种制度的变迁,对一种组织中的行为与观念的变迁,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意识形态在制度和组织变迁与创新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按照吉登斯的归纳,有以下三点:1.把局部利益表现为整体利益;2.否认矛盾存在,并对矛盾进行演变;3.通过具体化的方式使现状合法化。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合法化的工具,是行使权力保障和掩饰局部利益的媒介。换言之,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有利于某些群体的意义环境,同时掩盖了这一意义系统的统治本质。在多数组织中,意义体系表现为故事、笑话、礼仪、备忘录、会议等形式。所有这些组织实践都是再现或重组组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的符号形式。他指出:“分析符号秩序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就要考察含义的结构是如何调动的,从而使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合法化。……从机构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反映符号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维持统治形式的……从这一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识别将含义同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巩固统治者的利益的最基本的结构要素”。(注:A.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London:Polity Press,1979,pp.188,191-192.A.Giddens,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Berkeley:Uni.of California Press,1981,p.170.)
在一种制度与组织的变迁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如上所述,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逐步代替旧的制度安排、一种新的行为规则逐步取代旧的行为规则的社会过程。在这一社会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新的制度安排和行为规则必须或必然要代替旧的制度安排和行为规则。对所有制度改革和创新者提出这个变革的理据,都是必需的步骤,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诘难创新者的“理据困境”。对于所有墨守成规的人来说,这种被诘难的理据困境是不存在的。然而,恰恰在处理理据困境的时候,意识形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从合理性(变革的理性依据)、合法性(变革的秩序依据)和合情性(变革的情感依据)三个方面为制度变革和创新提供支持。
如果所要变革的制度或所要创新的制度,是属于整个制度安排中的保护带,也就是说,新旧制度不具有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矛盾,那么,处于硬核位置上的意识形态就可以为这些制度变革或制度创新提供合理性依据。此时,依据意识形态而走出理据困境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制度变革或创新是意识形态的更完美、更确切的表达;二是制度变革或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借助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信念,对意识形态的总体承诺,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的理据困境中的合理性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诉求,并不排除其他价值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诉求。事实上,借助于意识形态,新制度在整个社会中被接受的范围、程度和速度都将大大加快,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阻力,从而顺利实现旧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的平稳过渡。
其实,人们接受新的制度安排与行为规则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些安排和规则不断得到内化或社会化的过程。制度安排和设计提供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系列行为规则,同时还有许多隐藏在这些行为规则背后的价值系统。只有让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这种价值观念,并自觉地把制度设计的行为规则变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成为其自觉行为的一部分,这种制度的创新才能真正融入人们的社会行为结构,也才能真正嵌入其社会结构和环境当中。因此,一种制度变革的理据困境还存在合情性的维度,需要对社会情感的诉求。事实表明,公众对制度变革和创新的情感反应往往与制度的变革成败有着密切关系。这期间,意识形态往往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人们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能够相信一种新的制度结构更合理、更合法、更公正,在这种前提下自己和他人的收益会更多、福益更大时;当人们把这种规范和信仰最终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幸福感的评判标准时,他就会情不自禁地认同和参与其中,由此激发出来的热情和效益都将是巨大的。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同时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力,一种能够激励人们创造、降低制度创新成本的生产力。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成为了成功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小结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总体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变迁时期,“除旧布新”、“厌旧喜新”,是一种个人意向,一种社会潮流,恰如涂尔干当年针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描述:
人们渴望各种新奇的东西、未知的享受和不可名状的感觉,但是这些新玩意儿被认识以后,它们便失去了一切乐趣。从那时起,突然发生最危险的挫折,人们就无力承受……老是等待着未来和死盯着未来的人,他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鼓励他去忍受现在的痛苦,因为过去对他来说只是一些亟待度过的阶段。使他能够欺骗自己的是,他总是想在不久的将来找到自己还未曾遇到过的幸福……无限的欲望像一种道德的标志每天都显示出来,而这种欲望只能在反常的和把反常当作规律的意识里产生。(注:E.Durkheim,Suicide.Trans.by J.Spaulding & G.Simpson.Glencoe:Free Press,1951;p.256.)
本文所论及的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就发生在这样一种将反常作为常态的变化处境之中,人们经常用变革的欲望来催促一切组织和制度的改造与转型,而社会改革的最终基础,恰恰也具体化在每个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过程之中,落实在每个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效果之中。不过,相比于由变迁激发出来的人们的求新欲望,任何一种具有整合能力和团结效应的组织,任何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系统,在内在结构上总会表现出一种抗拒变迁(resistance to change)的倾向。一方面,制度变迁的这种滞后性,保证了在社会及其结构的急剧变迁中,人们的行为不至于完全处于一种迷茫和混乱的失范状态;另一方面,这种滞后性对一个社会的改革和变迁也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强大阻力。所以,当一个组织和制度发生变迁与创新的时候,一定会有其内部与外部的深刻原因,使这个组织和制度不得不发生相应的变化与变迁,以适应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以及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要求。
有关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上文已做了概括。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通过制度移植来实现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观念,在方法论上是基于制度主义的类型学基础,将这一夹杂着不同因素的变迁过程诉诸于制度类型的比较和参照,而形成这一观念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对中国自身组织系统之制度化不足的基本判断,因此,对于比较和参照意义上的制度类型来说,现实社会中的制度改造和组织建设都是依照示范效应和模仿机制的原则展开的。就此而言,无论是政府推动所构成的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重要动力,或者是组织和制度改造和更新自身结构的要求,都源自对不同制度类型的认识、比照和选择。
然而,通过检讨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不仅仅是组织本身的系统变化,改革一种制度,也不是依靠单纯的制度移植或更替就可以一蹴而就,一个组织和制度的形成、生长和变迁,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组织结构及其制度模式内在的构造或重构过程,而必须考虑到组织嵌入其中的整体社会的结构性环境,也必须考虑到组织自身的路径依赖的惰性,不考虑这些,在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具体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拔苗助长”的效果,有可能使一些本来有本土社会基础并能够自发生长的组织系统受到破坏。
因此,撇开制度类型学的研究架构,从组织和制度更根本的规定性出发,来考察其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才能把握住它最具生命力的脉搏。就此而言,特别是就变迁已经成为社会存在之最终正当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来说,将变迁分析作为组织结构或制度类型分析的前提和基础,才是我们在理论上的根本要务。简言之,有关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组织形态变迁的研究,必须在方法论上诉诸于研究范式的变迁。
在这个意义上,考察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还需要重视一个及其重要的理论维度,即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社会团结的程度指的是一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水平,它可以反映出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主观感受和认同状态,以及组织成员彼此间的整合程度。所谓团结,既是指社会群体或组织的聚合状态,同时也是指社会群体或组织的一种固体化的、结晶化的过程(solidarization)。特别是在社会变迁的情境中,通过团结来考察群体或组织,不等于说用一种现行的、定型的制度模式进行度量。相反,团结这一概念所要考察的,正是一个社会组织自身结晶化的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制度晶体,这样的制度并不是先前设定的,而是团结的结果。因此,团结是先位的,没有了团结,一切制度都无法实现其成型的过程,亦即根本不会产生制度建设的空间。就中国目前的组织研究而言,社会团结的概念恰恰提供了真正能够将制度成型过程纳入进来的研究空间。
也只有以上述研究作为理论突破口,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之社会过程的研究,必须超越制度类型学的研究范式。如果我们以变迁作为研究起点,通过考察社会变迁所连带形成的结构效果,将组织系统与其嵌生的生态学环境联系起来,对组织与制度的基本结构、形态及其演化过程加以考察,才能超越类型学所依靠的比较和参照的理论模式,回到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现实逻辑上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设想: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形式特征,即变迁的方式、速度及其范围,在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具体社会过程中,具有决定组织形态和制度架构的实质性意涵;换言之,变迁的上述形式规定性,直接决定了中国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实际效果和方向。今天,许多组织或其他社会形式有可能因为变化太快而失去生长的机会,反过来,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制度模仿,一些表面上符合变迁意识形态的改革,一经完成制度移植的过程,反倒使其内在的活力丧失殆尽。中国的社会建设,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只有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民情,耐心地寻找适于这一结构性环境的制度建设的条件,我们才能摆脱百年来从革命到革命的怪圈,建设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
标签:社会结构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科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