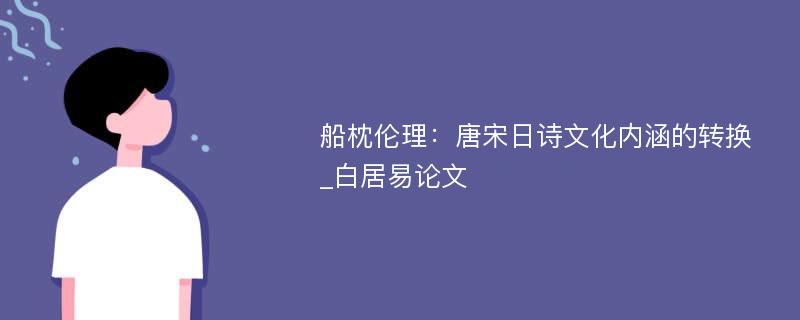
午枕的伦理:昼寝诗文化内涵的唐宋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诗文论文,伦理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昼寝诗,一般指以昼寝行为为题材创作的诗歌。中国传统诗歌中描写昼寝,最早场景始于对闺闱中女性的色艺情貌进行描绘。中唐之际开始出现描摹士人昼寝的诗歌,到宋代大为盛行,并且其他文体及绘画中都有大量表现。本文主要论述从中唐开始兴起到宋代蔚为大观的这类以士人昼寝为题材的诗歌,试图通过对唐宋士人昼寝诗的兴起和流行作较全面的检视,考察其如何克服儒家传统礼仪和道德压力而兴起,如何由个别创作逐渐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其表现的文化和思想内涵怎样逐渐成型,诗意空间如何得到提升和深化,在儒释道不同的创作语境中各自传递怎样的意义而又互相影响,并希望通过对昼寝诗文化内涵的考察,窥见唐宋文化转型的一个侧面①。 一 从闺闱到轩窗:宋前昼寝诗的流变 《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夫子对宰予昼寝的严厉谴责:“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②孔子对昼寝异乎寻常的态度,曾引起许多“昼寝”何解的讨论,但中唐前几乎都释为“昼眠”,释“寝”为“眠寝”,并未过多引申③。不过夫子的态度无疑对后代士人描写寝卧内容有所影响,行止有礼、起卧有时本是深受儒家礼仪文化熏陶的士人牢记的行为原则,《礼记·檀弓上》就以为白日寝居于内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④。唐前描写士人昼寝较少见,即使描写,也带有嘲谑意味,如《后汉书·边韶传》记边韶因昼日假卧遭到弟子嘲笑,若非他才捷学博,引经据典为自己辩护,恐怕免不了“懒读书”的形象⑤,可见昼眠并非美谈。因此,唐前诗歌几乎没有描写士人昼寝的,其他体裁中也极少见。例外的有陶渊明描写自己理想的闲居生活: 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⑥ 描写夏日昼卧的闲适趣味,颇具出尘之意,成为后人对陶渊明形象的经典想象之一。但其所写昼寝并未马上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回应,且北窗高卧在宋前基本上只是隐士符号,与士人的日常行为还相去甚远。 不过,当诗歌表现范围扩大,笔触进入到日常内室时,将闺阁中眠寝的美人作为审美对象,倒不乏其例。尤其齐梁之际,陈设于内室的寝具、器物及居于内寝的女人的行住坐卧引起诗人兴趣,女人昼寝也作为诗人审美对象,如沈约“寒闺昼寝罗幌垂,婉容丽色长相知”⑦。又如萧纲《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帐,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⑧ 描写女性昼眠的声容情貌,细致入微。最后强调所咏乃良家女子,则颇具意味:即使流行绮艳诗风的萧梁宫廷,吟咏女性昼寝,还是会引起诗人内心焦虑,昼寝于内,专注于女性情貌之美,让人感到道德不安,所以特别强调并非倡家,以免更显不堪。 中唐前写及眠寝,基本以女性为对象,同写梳妆、歌舞一样,只是将女人声容色艺作为审美对象,场所限于闺闱之内,环境不外绮帐雕床、玉簟银钩之类,所写不过是佳人的闺中情绪,昼寝并没有特殊文化内涵。女性恒居于内,昼日眠寝,在儒家观念里比士人更容易被宽容。倒是对欣赏者的批评严厉许多,因流连内闱绝非君子行为。如唐梁锽《观美人卧》,清人赵执信就斥责“直是淫词,君子所必黜者”⑨。自古皆将这类昼寝诗归于艳诗一类,在士人诗教观念里是“绮丽不足珍”的。 中唐情形逐渐发生改变。此时,诗人开始将昼寝作为诗歌描写题材,且其对象不再限于内闱美人昼寝,也开始离开儒家以昼寝为非礼懒惰的叙述语境。日本学者大桥贤一将中唐出现的昼寝诗分描写女性、隐者、士大夫、僧人四类⑩,除描写女性的属上述传统昼寝诗范畴外,描写僧人和隐士昼寝的诗歌均较少见,且对象特殊。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描写士人昼寝的诗歌,此种昼寝诗逐渐增多,至宋代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首位大规模描写士人昼寝,并张扬其慵疏闲适趣味的是白居易,其专咏昼寝情味的便有《禁中小卧因怀王起居》、《隐几》、《春眠》、《春寝》、《睡起晏坐》、《晏起》、《昼寝》、《卧小轩》、《昼卧》、《晓寝》等诸多诗篇,咏闲居之事而描写昼寝者更不在少数。如其《春寝》写春阳和煦,且无公差,于是自午及未,昏昏而寐,自得之乐从平淡诗语中流泻出来,且直言少健日“甘寝常自恣”而毫不以之为非(11)。又如《昼寝》: 暑风微变候,昼刻渐加数。院静地阴阴,鸟鸣新叶树。独行还独卧,夏景殊未暮。不作午时眠,日长安可度?(第791页) 夏日庭院薰风南来,鸟鸣相间,午睡的风味自然是令人舒心安乐的。以上两诗中诗人描写的昼寝对象已由闺闱佳人转向自身,其场景从帷幕深掩的内闱转向了清风徐来的庭院,风格也由婉丽香软转为清淡疏放。最重要的转变在于脱离了昼寝非礼的思想语境,为之注入安贫乐道、不营名利的生活美学。因此,陶渊明北窗高卧时就已表现出的疏慵自放、欣然自得的审美趣味在白诗中不断强化,渐渐形成昼寝诗的另一种面貌: 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眠。棉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闲居》,第527页) 食饱拂床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惰性,亦足傲光阴。(《食饱》,第693页)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第639—640页) 在饮酒、读书、弹琴、品茗渐已成为诗人笔下表现生活雅趣的重要内容时,白居易常将昼寝与诗酒琴茶并举,将之纳入闲适生活的组成部分,极大地开发了其审美趣味:昼寝是案牍劳形的官吏生活中难得的休闲解脱之法,是仕途遇挫时抚慰心灵、清畅情性的良药。“人间有闲地,何必隐林丘”(《赠吴丹》,第474页),这与白居易“中隐”思想是一致的,忙里偷闲、疏慵昏眠成为可以标榜的趣味,并常用以表现自己不慕名利的精神境界。白氏曾以《咏慵》标榜自己的慵懒(12),恐怕是夫子未曾想到的吧!正是在这种思想转变下,昼寝诗的场景成功地发生了转换(13)。 二 焦虑和辩解:北宋昼寝诗的矛盾面向 北宋文官社会成熟,科举制度进一步严密和科举取士范围的扩大,对文治的强调及对文官的礼遇,为士人实现白居易理想的“中隐”提供了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宋初白体诗尤其白居易闲适诗的流行也是内在的必然。在此背景下,昼寝成为诗人描写优游卒日的生活场景时常出现的内容。北宋描写昼寝极普遍,诗人们不但继承了白居易昼寝诗的主题和思想转向,在诗中传达宠辱不惊、淡泊自守的生活态度,甚至以“乐睡”、“嗜睡”命名亭台轩榭——如王禹偁“睡足轩”(14)、晁补之“卧陶轩”(15)等,显示出对这种生活态度的认同和偏爱。因此,北宋许多昼寝诗都表现出白诗那种清淡疏放的风格: 别院帘昏掩竹扉,朝酲未解接春晖。身如蝉蜕一榻上,梦似杨花千里飞。嗒尔暂能离世网,陶然直欲见天机。此中有德堪为颂,绝胜人间较是非。(苏舜钦《春睡》)(16)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宛转愁。(王安石《午枕》)(17) 这几例都继承白居易昼寝诗,以平易浅切的语言营造自然清新的意境,传达淡泊自守的精神。 不过,北宋士人安闲地享受昼寝时,并不只有舒适惬意的满足感,另一类型的昼寝诗显示出他们的焦虑不安,这种不安源于圣人和儒家传统谴责懒惰所带来的压迫感。诗人描写昼寝的清闲兴味时,常露出焦虑,对自己偏爱悠闲的生活趣味感到紧张。例如苏舜钦《夏热昼寝感咏》由昼寝而自省,不但用前贤爱惜光阴的事迹告诫自己,自责“奈何耽昼寝,懒惰守坏垣”,而且回顾了少年时勤勉进取,然“文章竟误身”以致“闲困尚有待”、“不寝徒自烦”,昼寝是仕途蹭蹬后无奈的选择,为午寝找到理由(18)。邹浩《午枕有感》思路也基本与此一致,也由昼寝而自省自警,不但以反思表达积极进取的态度,还努力解释耽于昼寝的原因是睡思潜牵,即使茗饮再三也无法驱逐。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会焚膏续昼,以救往失(19)。不过,诗人们虽极力表达戒懒的意愿,其描写昼眠部分怡然自乐的情趣却无法掩盖,与其内省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张力。更值一提的是两位诗人都曾在另一些昼寝诗中单纯描写昼寝之适,显得悠然自得,如苏舜钦“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一两声”(20)、邹浩“睡乡天地肃秋风,日日欣随宰我踪”(21)等。 圣人教训、儒家礼仪传统无法置之不理,但实际上士人的人生理想、日常生活和审美趣味自中唐以来渐渐发生转向(22),为昼寝在传统和现实的矛盾中寻找弥合点,消除因矛盾带来的焦虑感,是北宋士人描写昼寝时难以逃避的问题。通过解释、自警、劝诫表示自己并未叛离传统教导,当是试图消除焦虑的一种表现,但这也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无法否认对昼寝清闲趣味的喜爱,上举两位诗人便是明证。诗人必须寻找新理由,以便比自警能更彻底消除焦虑感。于是,出现了对经典教诲作新解释的言论: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学者多疑宰予之过轻而仲尼贬之重,此弗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昼夜居于内,昼居于内,则问其疾,所以异男女之节,厉人伦也。如使宰予废法纵欲,昼夜居于内,所谓乱男女之节,俾昼作夜,《大雅》之刺幽厉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贬之?然则寝当读为内寝之寝,而说者盖误为眠寝之寝云云。(23) 这条解释极有意味,刘敞辨证“寝”当释为内寝,引《礼记》“君子不昼夜居于内”与之印证,将孔子言论上升到人伦大节的高度,则宰予不是眠寝非时和懒惰废学的问题,谴责针对的不是昼寝行为,而是其场所。上文曾讨论昼寝诗的场景转换,即离开内闱转向外庭。那诗人们这种清雅的昼寝行为,是否应受谴责?刘敞没在辨证中揣测圣人观点,但他通过诗歌给予了会心的答案。他自己使爱昼寝且爱写昼寝诗,《公是集》仅卷四以昼寝为题便有《昼寝三首》、《昼寝上府公》、《六月二十六日西阁昼寝》,皆正面描写昼寝。如其《昼寝三首其一》以“圉圉为潜鱼,因之乘波流。翻翻为飞鸟,爰以凌空游。在己孰是非,于物任沉浮。观化悟独乐,真伪竟悠悠”(24)形容昼寝感受,毫无不安迹象,反而充满怡然物化的逍遥之乐。这种安然是否源于他对经典的新解,笔者不敢断定,不过周密《齐东野语》专论昼寝的言论会让这种判断更有说服力: “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枕边”,丁崖州诗也;“细书妨老读,长簟惬昏眠。取簟且一息,抛书还少年”,半山翁诗也;“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西窗无夕阳”,放翁诗也;“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吴僧有规诗也;“老读文书兴易阑,须知养病不如闲。竹床瓦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吕荥阳诗也;“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蔡持正诗也。余习懒成癖,每遇暑昼,必须偃息,客有嘲孝先者,我必以此自解。然每苦枕热,展转数四。后见前辈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问何意,公云睡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语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隐号睡仙,其亦知此乎?虽然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字当作画字,盖夫子恶其画寝之侈,是以有朽木粪墙之语。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尝著《启颜录》,意必戏语也。及观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诛,若然则吾知免矣。(25) 此材料引前人之说,解“昼寝”为“画寝”,将孔子的指责转向“恶其画寝之侈”。与《七经小传》不同,《齐东野语》目的不在辨证词义,而在为昼寝辩护,他先列举数位诗人的昼寝诗和事迹,自陈是为了在面对嘲讽自己慵懒的他者时“自解”。材料隐含这样的意味:昼眠是可与知者言的美妙之事,不应被嘲讽,至于夫子的指责,那只是不知睡味者的误解而已。“若然则吾知免矣”,透露出作者的真正意图,以上所有都不过是为自免找到解释——他需要消免焦虑感,且他所列举的诗人、新型的时代文化也一样,需要能消弭焦虑、将新的生活状态合理化的解释:这种解释符合现实的生活美学,且不叛离传统。 三 自适与梦想:昼寝诗的诗意提升和文化内涵 上文论述宋代昼寝诗通过自省和经典新解来消解焦虑,这是在昼寝行为外寻找合理性的努力。同时,诗人也通过赋予昼寝行为本身以独立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为自己昼寝和写作昼寝诗的行为取得合理性。白居易昼寝诗中,昼寝所显示的自身的“闲”、“懒”就已具意义: 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名利近,无复长安心。(《食饱》,第693页) 诗中言闲居昼睡的好处:畅情性,傲光阴,息灭名利仕进之心。这种贪闲好懒与勤苦劳瘁的长安生活并无是非之分,只不过是各自适意而已: 缅想长安客,早朝霜满衣。彼此各自适,不知谁是非。(《晏起》,第714页) 高位者权势煊赫,却要付出辛苦和忧惧的代价,而闲居适意,正是昼寝的意义所在,况其意义不限于此: 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全胜彭泽醉,欲敌曹溪禅。(《春眠》,第525页) 睡中了然无虑,摄心正念,可参禅,可悟道,则睡与觉有何区别?白居易赋予昼寝一种淡泊名利、息心歇虑的精神内涵。 宋人昼寝诗在白居易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对昼寝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了更深挖掘。首先是适意的内涵在宋诗中被提高到心灵自由层面,摆脱外累,不但不汲汲于名利,而且遭遇困境时能随运委化,不为外物所牵,能安眠便体现出这种自由心灵。宋人追求心灵自适,较白居易更强烈,这是士大夫人文旨趣与理性精神的一种体现。周裕锴认为宋诗的“自适”在于“化劳心的苦吟为娱心的闲吟”、“化钟情的酸楚为乐易的闲暇”、“化执迷的怨怒为戏谑的调侃”(26),宋代昼寝诗对“闲”的反复吟咏便体现出这种精神意蕴。如王禹偁仕途失意时,便以安眠为心灵安顿之所,作“无愠斋、睡足轩以玩意”(27),他正是以无愠和安眠表达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由心灵,其《睡》诗也说昼寝“不入荣名客,还宜放逐臣,东窗一丈日,且作自由身”(28)。 失意时写昼寝诗表现自己身为事所拘心灵却安闲的境界,在宋代十分普遍,苏轼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苏诗言及昼寝之多不下百处,且几乎都写于外放杭州、被贬黄州和岭南时,昼眠表现的心灵自由纯粹、自信坚定的意义,在其诗中能得到直观证明。他写谪居适意,常言“睡蛇已死”: 且倒余樽尽今夕,睡蛇已死不须钩。(《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29) 睡蛇本亦无,何用钩与手。(《谪居三适·午窗坐睡》,第2286页) “睡蛇”为佛教概念,比喻烦恼困扰、心绪不净。“烦恼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30),睡眠属于没有烦恼、心灵纯粹的人,苏轼曾作《睡乡记》,认为不仅“内穷于长夜之饮,外累于攻战之具”者,连大禹、商汤、武王、周公等贤圣也无以入睡乡(31),为安眠限定了特别的意义,即心无所累、心无所惑。不但如此,苏轼在白居易基础上进一步提纯了昼寝诗,他极少在诗中通过议论性语言来描述昼寝所展现的生活趣味和精神境界,而是通过艺术描写、意境烘托,完成了“睡乡”优美情境的塑造,给人直观审美感受,而非理性价值判断。因此,苏轼在谪居失意时所作昼寝诗,多具旷达纯粹之美: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其四》,第478页) 鸣鸠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泼眼明。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春日》,第1331页) 对比白居易诗中对闲适自在的判断选择,苏轼昼寝诗意境优美自然,睡境的美好从诗境中自然流露出来,这正是其自由无碍的高尚灵魂的优美外化。东坡睡诗为昼寝注入的这种内涵,完成了昼寝诗思想和诗意空间的提升。宋人普遍接受昼寝的这种意义内涵,认为心地清凉自能成眠,昼眠安寝在逆境中尤可标榜。如东坡因睡美而惹怒执政的轶闻: 东坡海外《上梁文口号》曰“为报先生春睡美”,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32) 不为贬谪所动,安眠如常显示的精神力量令政敌感到极大的压力。纪昀说:“此诗无所讥讽,竟亦贾祸。盖失意之人作旷达语,正是极牢骚耳。”(33)从原诗看,苏轼未必有牢骚,不过无讥讽正说明不在乎,其旷达在政敌看来是一种毫不妥协的精神,就如汪师韩所说:“自写酣适,本无怨刺,乃遭执政之怒,岂以安于所遇,反不足以惬忌者之心耶?”(34)一睡而力量至此,不论记录真实性几何,在记录者看来,诗中显示的那种精神和人格魅力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宋人对安寝睡乡的内涵有普遍认同,所以许多人都写有此类昼寝诗以明志。如李纲《晏起》:“何如谪堕溪山里,钟鼓不闻春睡美。先生梦觉本来齐,更与睡乡重作纪。”(35)愿接续苏轼为睡乡作记,可视为贬后宣言。另如翟汝文《睡乡赋》、张九成《读东坡谪居三适·午窗坐睡》等,都接续苏轼的叙述语境。而更多诗人通过具有单纯明丽意境的昼寝诗,表现了对其审美趣味的认同。 宋人除在昼寝诗道德内涵和诗意空间上有所提升外,在其所可表现的个人情志方面也有开拓。有一类昼寝诗,因昼寝写昼梦,因梦及思,凡思亲怀旧、归隐还乡之情,往往可通过昼寝诗表达。因此,昼寝的意义不仅在于道德上的纯粹心灵,还常寄托着诗人们的真实理想和情绪。黄庭坚《六月十七日昼寝》: 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啮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36) 任渊注黄诗说:“此诗……言江湖之念深,兼想与因,遂成此梦。”(37)因有沧洲之思,才有江湖之梦,经由马啮草声刺激,使午枕成为“实现”这一梦想的媒介,现实的辗转辛劳与梦境的悠然形成强烈对比。因思成梦在传统诗歌中并非新鲜构思,不过昼寝诗通过写梦而有所寄托,构成其另一种类型,宋代这类昼寝诗并不少见。如张耒《道榻》:“谁惊午枕江湖梦,风落晴窗柏子干。”(38)与黄诗同一机杼,写昼寝而有江湖之梦,然为现实喧响所惊,不得不脱离梦境。又如唐庚仿黄庭坚诗而作的昼寝诗: 雨余热喘殊喊呀,坐翻故纸腰足麻。铺陈枕簟搴青纱,倒床不复知横斜。梦魂飞扬远还家,故人见我一笑哗。须臾睡觉衙鼓挝,墙头瞑雀声槎槎。(39) 官居辛苦,吏职相萦,不如昼眠一梦能与家人团聚,聊解归思。又如“试拂横床供昼寝,且容幽梦绕清江”(40)、“坐对禅房花木,梦成午枕江湖”(41),均以昼寝兴江湖之梦,起林壑之想,慰倦游之怀。 当然,宋人昼寝诗并未像笔者分析的一样,将道德内涵、审美趣味和情志寄托区分得如此清晰,他们只是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昼寝诗创作,使其思想意蕴更丰富,意境更纯美圆熟。北宋中期后,昼寝诗基本表现了自由、自适的精神追求,沿着白居易、苏轼、黄庭坚开创的诗境进行创作,此时很少再有自警类昼寝诗,可见昼寝的意义内涵渐趋稳定,昼寝诗基本成型了。 四 卧图与诗偈:宋代关于昼寝的释道传说和艺术表现 翻检昼寝诗,可发现诗中常有对睡与觉、梦与醒的关系叙述,并总表达这样的观念:睡与梦者表现为无所思虑、无所知觉的天然纯真,而觉和醒者则表现为有所烦恼、有所挂碍的智巧机变,睡与觉、梦与醒的真正界限和得失无法辨识,甚至互相转化,因此睡与觉所对应的昏昧或清醒在诗歌中常表现为反常状态。这种思想体现了庄、禅两方面的影响:《庄子·齐物论》中通过南郭子綦隐几、庄生梦蝶等寓言,将昏昧与清醒、梦幻与真实间的界限模糊了,《齐物论》的寓言也成为昼寝诗常用典故;禅宗常将“困来则眠”的无知觉和反常姿态作为禅悟的机缘和表现,以与醒的烦恼界和日常状态形成鲜明对照,故而有“梦里惺惺”之类的说法和禅师以睡、懒悟道的记录。“是醒是醉人莫测,非梦非觉中了然”(42)是宋人对“睡”与“觉”关系的一致体认。胡寅《清寐记》说: 其不寐而寐也,犹日之韬乎夜;其寐而不寐也,犹月之隐乎昼。开目闭目,幽显混融。鼾息雷鸣,而本心澄默;灵台焕照,而四体嗒然。殆进乎晦息之随,而超乎昼寝之表矣。(43) 鼻息雷鸣却本心澄然,体现了宋人对眠寝本质的认识接受了传统的庄子思想和流行的禅宗思想的影响。 宋代不但昼寝诗创作繁荣,士人眠寝图也广为流传,其中最典型的是以陶渊明北窗高卧为题材的图画。如赵幹《北窗高卧图》,绘“松亭掩帘,一人北窗高卧,童子倚栏看鹤”,宋高宗题诗“林间无事可装怀,昼睡功劳酒一杯。残梦不能全省记,半随风雨过东街”(44)。 除士人对昼寝的精神涵义有所体认外,宋代道、释两家均有以眠寝为悟道行为的传说和艺术创作,其中以大量的眠寝题材绘画和题画诗偈最流行,不但可与士人昼寝诗相映成趣,甚至影响着士人创作。下面以陈抟和四睡图为例。 陈抟事迹在北宋已流传很广,宋代关于他善睡、嗜睡的传闻和睡诗记载不少,如《诗话总龟》: 陈希夷先生每睡则半载或数月,近亦不下月余,赠金励《睡诗》云:“常人无所重,惟睡乃为重。举世皆为息,魂离神不动。觉来无所知,贪求心愈用。堪笑尘中人,不知梦是梦。”又曰:“至人本无梦,其梦本游仙。真人本无睡,睡则浮云烟。炉里近为药,壶中别有天。欲知睡梦里,人间第一玄。”(45) 陈抟隐武当山……多闭门独卧,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户试之。月余始开,抟熟睡如故,尝对御歌曰:“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铺地,震雷掣电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鼾睡。闲思张良,闷想范蠡;说甚孟德,休言刘备,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争如臣,向青山顶头,白云堆里,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但一觉睡!管甚玉兔东升,红轮西坠。”(46) 材料反映出宋人对陈抟眠寝的认识:以眠寝为养生的道家修养之法;以眠寝为入世对立面,眠寝是出世的自适的人生追求的象征;以睡的能知玄体道与人世醒的“不知梦是梦”对比,睡是大智若愚、心灵澄澈的境界。总之,其“睡”虽非仅是昼寝(一睡数月),却为宋人昼寝观念提供了一个来自道教的依据。陈抟的典型形象是高卧避世,北宋就有相关绘画和诗歌流行,如晁说之《昼寝看壁上陈希夷》(47)、谢薖《题陈先生华山高卧图》(48)均是诗画相辅行世的例证。因为陈抟“睡仙”形象的流传,宋人昼寝诗中常以对他的希慕来表达情志,如陆游《午梦》、《新晴午枕初起信笔》便是极显著的例子。 南宋后至元代,陈抟高卧的形象广为流传,不但有大量高卧图和题画诗流行,马致远更改编为杂剧,使高卧与避世的紧密联系更深入人心。 禅宗同样有大量睡图和诗偈赞颂,和道家陈抟形象、士大夫津津乐道的陶渊明北窗高卧形象相映成趣,其中流传最广的即睡布袋及四睡图。这里以四睡图为例略作分析。 相比陈抟高卧事迹,寒山等“四睡”形象作为绘画题材出现和流传相对较晚,就笔者所见,北宋似尚难见相关绘画和诗偈(49),但南宋时四睡图和相关诗偈赞颂却大量涌现,昼寝诗的流行和昼寝文化内涵的逐渐成型,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所谓四睡图,指寒山、拾得、丰干和一虎相与枕藉而眠,南宋以下许多禅师有关于四睡图的诗偈赞颂: 善者未必善,恶者未必恶,彼此不忘怀,如何睡得着。恶者难为善,善者难为恶,老虎既忘机,如何睡不着。(无准师范《丰干寒拾虎四睡》)(50) 一等骑虎来,两个挨肩去,松门外聚头,辊作一处睡。梦蝶栩栩不知,孰为人孰为虎,待渠眼若开时,南山有一转语。(石田法薰《四睡图》)(51) 从上引诗偈赞颂来看,以四睡图为代表的禅宗睡图和昼寝诗偈,基本以人虎相安而眠之毫无关防、毫无知觉的状态表达禅悟状态,这与士人昼寝诗中以眠寝为自由心灵的象征有相似之处。但禅宗睡图和诗偈,不及士人昼寝诗那样具有丰富多样的意蕴,从上引诗偈也可看出。四睡图在士人中亦有流传和影响,如林希逸“多少醒人作寐语,异形同趣谁知汝。四头十足相枕眠,寒山拾得丰干虎”(《四睡戏题》)(52)便为此类。 禅宗其他睡图及相关诗偈,基本也与四睡图一样,表现在睡与觉、梦与醒的转化中体悟禅机。要之,虽然道释和士大夫对昼寝文化内涵的体认略有差异,但其互相影响,不可分割,共同促进了昼寝题材的文学和艺术创作在宋代的流行。 本文通过对唐宋以来以士人昼寝为题材的诗歌进行考察,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中唐时以白居易为典型,对昼寝所代表的道德意义和生活态度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从而影响了昼寝诗创作,场景由内闱向外庭,对象由女性向男性,题材由单一描写女性色艺情态向描写士大夫闲适生活情趣转变。宋代文人生活的变化和诗歌写作的日常化,使士人对白诗中的昼寝文化产生兴趣,昼寝诗大量创作,但来自传统的教导使其在表现闲适疏慵的生活趣味之外,还带着思想上的焦虑感,因此北宋许多昼寝诗表现出描写安于闲适又不时自警的矛盾现象,还有对宰予昼寝进行新解来寻找昼寝合理性的现象。 经过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诗人对昼寝诗思想内容及审美趣味的诗意提升,昼寝诗终于摆脱道德意义方面的缺陷,获得了新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同时,士人和道教、禅宗都有以昼寝为题材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虽然各自对昼寝内涵的体认略有差异,但互相影响,共同促进了昼寝题材的文学和艺术创作在宋代的流行。 ①关于昼寝诗研究,国内已有沈金浩《宋代文人的午睡昼寝及其审美心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第75—79页),归纳宋代昼寝诗流行和文人审美心理的关系,部分观点具开创意义,但其审美心理和原因分析较陈旧;另日本有大桥贤一《中国古典詩における昼寝について——唐代を中心に》(筑波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筑波中国文化论丛》2002年,第59—78页),寻绎昼寝描写在唐前文学作品中的流变并将之分为四类,对本文写作颇有启发,但其以唐代为中心,不涉昼寝诗在此后的重要转变。 ②刘宝楠撰、高流水校点《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7—178页。 ③关于“宰予昼寝”主要有以下几说:(1)昼眠说。如何晏解、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朱熹《四书集注》等作此解。(2)画寝说,以“昼”、“画”形近而误。或为绘画寝室,如韩愈、李翱《论语笔解》,周密《齐东野语》等持此说;或为绘画寝庙,周亮工《书影》持此说。(3)昼居内寝说。如王楙《野客丛书》、刘敞《公是先生七经小传》作此解,今人更因此引申为昼御即男女白日同房说(赵建伟《“宰予昼寝”与古代禁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3期)。 ④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校点《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2页。 ⑤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册,第2623页。 ⑥陶渊明《与子俨等疏》,逯钦立校点《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8页。 ⑦沈约《四时白纻歌·冬白纻》,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册,第807页。 ⑧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40—1941页。 ⑨赵执信《谈龙录》,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谈龙录》合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⑩参前揭大桥贤一文章。 (11)谢思炜撰《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册,第606页。下引白诗均出此本,随文出注。 (12)《白居易诗集校注》,第2册,第554页。 (13)此处并非说描写女性昼寝完全被新昼寝诗替代,不过到宋代这种写作传统主要被词分担,昼寝诗则更倾向于白氏式的描写男性昼寝行为。 (14)沈虞卿《小畜集序》:“咸平初来于齐安……作竹楼、无愠斋、睡足轩以玩意。”(王禹偁撰《小畜集》,《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75册,第1页) (15)黄庭坚《卧陶轩》:“为晁无咎作。”(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册,第239页) (16)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8—79页。 (17)李壁笺注、高克勤校点《王荆文公诗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1页。 (18)《苏舜钦集》,第38—39页。 (19)邹浩《道乡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21册,第171—172页。 (20)《夏意》,《苏舜钦集》,第68—69页。 (21)《午枕觉怀世美》,《道乡集》卷七,第224页。 (22)关于唐宋文化和思想转型,可参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3)刘敞《公是七经小传》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第33页。 (24)《公是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第432页。 (25)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26—327页。 (26)周裕锴《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27)沈虞卿《小畜集序》。 (28)王禹偁《小畜集》,第52页。 (29)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册,第1617页。下引苏诗均出此本,随文出注。 (30)鸠摩罗什译《遗教经论》,《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影印本,第26册,第286页。 (3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372页。 (32)曾季狸《艇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10页。此处苏轼写春睡,虽非昼寝,但其所言睡眠意味,与其昼寝诗内涵一致,即以安枕为自由心灵的象征。 (33)苏轼撰、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四○,清同治八年韫玉山房刻本。 (34)汪师韩《苏诗评选笺释》卷六,转引自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纵笔》诗集评部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71页。 (35)李纲《梁溪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563页。 (36)(37)《黄庭坚诗集注》,第2册,第403页。 (38)张耒撰、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41页。 (39)唐庚《昼寝效鲁直》,《眉山集·眉山诗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289页。 (40)谢逸《夏日》,《溪堂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508页。 (41)周紫芝《书淳师房六言三绝其一》,《太仓稊米集》卷一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第121页。 (42)陆游《醉眠曲》,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册,第1085页。 (43)胡寅《清寐记》,《斐然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第748页。 (44)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6—1377页。 (45)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卷四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0页。 (46)《诗话总龟》卷四七,第461页。 (47)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8册,第173页。 (48)谢薖《竹友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597页。 (49)寒山题材绘画的演变,可参崔小敬《寒山题材绘画创作及演变》(《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 (50)宗会、智折等编《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五,《大藏新纂卍续藏经》(以下简称《卍续藏》)第70册,河北省佛教协会2006年版,第270页。 (51)妙因、至慧等编《石田法薰禅师语录》卷四,《卍续藏》第70册,第350页。 (52)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