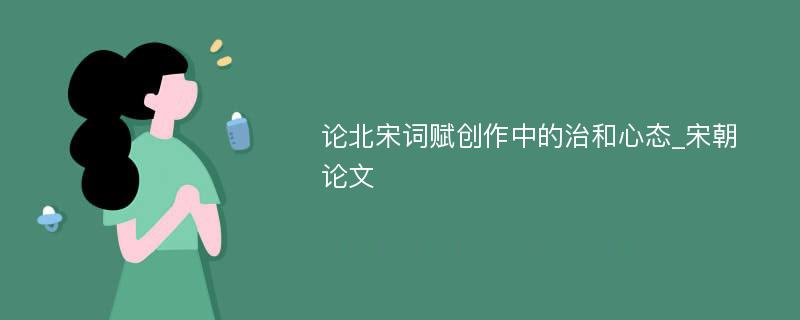
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平论文,辞赋论文,北宋论文,心态论文,真仁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5-0021-04
宋初文学深染五代风气,太宗以来大力推行崇文守内的政策,重学风气渐趋浓厚。随着重学空气的形成和国家趋向繁荣,杨亿、刘筠诸人追慕晚唐李商隐,追求华丽富雅、雍容典赡的骈体文风。这种文风适于表现当时的治平气象,也为文人施展才学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当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方兴未艾的真宗到仁宗亲政这段时期,这种文风在文坛上影响甚钜。在辞赋创作方面,晏殊、夏竦、胡宿、宋庠、宋祁诸骈文高手广泛挹取前人芳润,创作了一批反映治平心态的优秀作品。
所谓治平心态,是指在太平环境中形成的以优游不迫、纵逸闲雅、细腻深婉为感情基调的心理态势。其形成与有宋的国策密切相关。宋从开国,守内的国策已基本确立,特别是两次征辽失败后,军事上更趋保守。真宗承多年之积弊,好功而厌战,无力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景德元年(1004)与辽订立“澶渊之盟”以钱帛换取和平之后,又与西夏如法炮制。于是,天下似乎太平了。巧佞的大臣乘机兴风作浪,真宗也借机要在烂疮疤上敷粉,以掩饰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东封泰山,四年(1012),又于山西宝鼎祭祀地祇,人为地构筑一幅盛世图画。这时,各地祥瑞纷纷出现,为封禅大典烘托气氛。真宗以来的太平气象造就了文人们平和细腻的心理素质,西昆体诗,柳永、晏殊的词,或遣愁怀,或咏盛世,均流露着雍容闲雅的情绪,传达着盛世之音。黄裳在《书乐章集后》曰:“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1] (P120)
在大唱盛世颂歌的氛围中,颂美赋作大量涌现,影响及于仁宗时期。何薳《春渚纪闻》曰:“人臣作赋颂,赞君德,忠爱之至也。故前世司马相如、吾邱寿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吕文靖公、贾魏公则尝献《东封颂》,夏文庄公则尝献《平边颂》……。今元献晏公、宣献朱公遭遇承平,嘉瑞杂遝,所献赋颂,尤为多焉。”[2] (卷6)宋初的田锡就曾大力提倡这种雍容典雅的文风,至刘筠、杨亿随成风气。仁宗以来的西昆后进之一晏殊也大力提倡治平文风。这一时期,在辞赋创作中流露着雍容气象的作家有晏殊、夏竦、胡宿、文彦博等人。夏竦于大中祥符三年(1011)作的《河清赋》、魏震作的《瑞木赋》、杨亿作的《天禧观礼赋》等是颇为典型的颂美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刘、杨诸人的创作说:“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升平,春容典雅,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
晏殊今存完整的赋4篇,另有残赋5篇;夏竦存赋12篇,多为律赋;胡宿存赋5篇;文彦博存赋19篇,以律赋居多。晏、夏诸人的赋充斥着颂美太平的治平之声。晏殊的《皇子冠礼赋》、《西掖植紫微赋》、《亲贤进封赋》均是润色鸿业之作,通过典雅的文辞和对庄严的礼制的描写以体现太平气象。文彦博的《天衢赋》、《土牛赋》、《玉鸡赋》、《汾阴出宝鼎赋》等描写都邑之文制、典礼、祥瑞以体现太平景象,等等。真、仁时期,北方的边患基本解除,澶渊之盟以后的承平景象给赋家们以极大的鼓舞。真宗时期,辞赋创作中颂美之声叠起,逮仁宗朝,余绪犹盛。如果说宋初的颂美赋倾向于取法魏晋征实赋风,在颂圣时有所节制,那么,真仁时期的颂美赋则广泛运用汉大赋虚构夸张的手法,体现出雍容大度、富丽堂皇的台阁习气。宋初向内收敛的心态渐为优游闲雅的治平心态所代替。
夏竦的《河清赋》和《景灵宫双头牡丹赋》作于刘太后摄政时,其风格已与宋初颂美诸赋大不相同。在《河清赋》中,作者充满激情地赞美了大宋的太平之治,赋曰:
洎我国家秉皇图,宣帝力,尊百神,朝万国,光明乎遐绝,馨香乎霄极。禅云亭而广厚,玉简即封;祀汾睢而颂祗,鸾旗未饬。西人清候而望幸,六官戒期而励弈。爰荐祉而炳灵,滟澄波之湜湜。徒观其祥风荡漾,非烟蒙幂。浮休气于川上,泛荣光于岸侧。失汹涌之黄流,湛清冷之素液。银潢之景横秋,帝台之浆映月。江练初静,壶冰乍释。鉴秋毫及纤尘,露金沙与银砾。神鱼龙马,泳深渊而不隐,紫阙珠宫,扩洪流而可觌。合济渎兮安辨,委沧溟兮竞碧。
夏竦描绘了一幅黄河转清、千里澄碧的祥和景象,像是奏响盛世的颂歌。溢美的言辞不再有所节制,而是充分宣泄。其实,真、仁以来虽然边患暂时平息,但困扰国家的种种危机并未得到解决,赋家们的颂美太平只是为了迎合当朝或慰藉自己的太平奢望而已。《景灵宫双头牡丹赋》是应制之作。赋中说:“伊牡丹之淑艳,实造化之鸿英。杂五色以交丽,间千叶以敷荣。结紫心而函实,散黄蕊以传馨。干扶疏而四擢,枝绰约以相承。……萌琪珠之璀璨,藉瑶草之葱青,润五云之滋液,对六羽之威灵。”通过描写牡丹的高贵华丽,以体现国家祥和的气象。夏竦喜欢用典使事,以增加颂美内容的雍容典雅情调,但他用典不大冷僻,常常一生一熟、一浅一奥相互为对,因而,他的赋既典雅含蓄又明白练达。他不是凭借文辞的渊奥,而是通过弘阔张扬的笔势来体现太平气象的。据范镇《东斋纪事》卷3载:夏竦不满杨亿的晦涩文风,称其文章“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时人认为夏竦之文“譬诸泉水,迅急湍悍,至于浩荡汪洋,则不如文公也。”这说明骈体文、赋风在夏竦手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主要是通过追求一种迅急湍悍的气势,以体现出雄视古今的治世豪情。
胡宿的赋除《正阳门赋》外,其余均是律赋。《正阳门赋》作于仁宗时期,作者突破了宋初赋尊法晋赋的征实倾向,采取铺陈夸张的手法,借以表现宋王朝强盛的气势。这篇赋创作的背景是朝廷增饰正阳门以兴太平之象。对于增饰正阳门,胡宿既没有像西汉大赋那样,对宫观极尽夸张以突出其气势,也没有像东汉大赋那样,强调循礼而动,奢不可逾,俭不可侈,而是师法西汉萧何劝汉高祖增饰宫观的论调,不壮丽无以威万国而服诸侯:“谓皇居之偪下,方万乘之尊严;谓宝俭之过中,非四方之表则。乃帝阍之峨峨,图天象之奕奕,一开一阖,于以顺乎阴阳,不壮不丽,何以威乎戎狄!”儒家是崇尚节俭的,但也不主张土阶茅殿般的过分节用,而是要依礼而行。胡宿为增饰正阳门找到了合乎儒家礼制的理由,即不壮丽则无以威万国、顺阴阳。这样,把宫观的壮丽和儒家的礼制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为适应承平享乐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何晏的《景福殿赋》赞美魏明帝的大兴土木所依据的理由即是萧何的论调,胡宿此赋很可能受到何晏赋的启发。赋的主体部分是对正阳门的铺张描写,作者细致地描绘了正阳门结构之工巧:“宝篆鸾飞,耀煌煌之金刻;荣檐虬耸,壮翼翼之瑶京。崒兮天党,屹若神行。丽谯横互,磴道阶升。六梁布藻,烟瓦摇青。云疏洞开,璇题彪列,蔼若鲜云,蔽婵娟之素月;镂槛周施,彤栏钩折,宛在半空,横连蜷之雌霓。”这样细致入微且充满动感的描写显然是师法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技法。作者还夸张地描写了正阳门的飞动气势:“觚棱上拂,隐日月之回环;辇道相过,瞰烟云之明灭。……形半起而还正,势将翔而复抑。跂而望之,若太阳御六龙,升扶桑而耀色;迫而察之,若威凤将九雏,下丹山而接翼。东虬兮西兽,交镇兮左右;南箕兮北斗,夹照兮前后。”表现出远承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表现王朝气魄与威势的用心。可见,仁宗以后颂美赋不再崇尚内敛平和的艺术效果,而是趋向于表现王朝宏阔壮大的气魄。不过,赵宋王朝过分强调文治,因而,这种气势的发露是有所节制的,赋的结尾,胡宿赞美赵宋行王道以致太平的美政,以儒家的仁政思想收缩这种飞动的气势,从而体现出优游不迫的韵致:“功崇则业大,德盛则礼尊。斯干咏于周家,落成百堵;建章营于汉代,丽极千门。况乃业包海岳,道格乾坤,逾苍姬之拓统,超金卯之集勋,抚和旷俗,惠养齐民。秋毫皆出帝力,率土莫非王臣。”胡宿视眼前的形势为旷古未有的治平,因而虽然缺乏总揽古今的豪情,但也不失“安以乐”的自得之情。这一时期的颂美赋还直接描写帝王,如文彦博作于天圣三年(1025)的《圣驾幸太学赋》。这篇赋文词丰赡,章法井然,集中描写了仁宗的循礼而动,优游容与,展现了太平天子的风采。
晏殊、夏竦等人的赋还流露着追求享乐的闲逸情怀。对男女之情的关注,对艺术的重视,均反映了士大夫对平静安闲的生活的玩味,对要妙宜修的心理的深刻体会。柳永词的羁旅之愁、狂欢之态、离别之思,晏殊词中流露的对时光流逝的无奈、闲愁萦心的痛苦,何尝不是承平环境中的心理体验。这时期的赋与词表现的情绪波动,不是肝脾靡烂的、呼天抢地的悲恸,而是基于典雅的情感基础上的闲淡隽逸的情感冲动,是太平时期对生活的仔细品味。这样内容的赋同样是太平之黼黻。夏竦的《周天子宴王母瑶池赋》表现了对享乐的追求。神遊天上,极尽情欲之欢,这是游仙诗经常表现的主题,它反映了人性中追求情欲满足的一面。夏竦的这篇赋极写纵乐天上的美好:“修城而美锦千两,供帐而轻绡万重。广乐嘉成,编舞霓裳之曲;流霞互举,争传马瑙之钟。是何云雨驰魂,笙篁饰喜。倦敛霞袂,慵凭玉几。”赋中还写了周穆王与西王母的悲伤离别,并各自歌咏以抒怀,这就为享乐涂上了一层高雅情趣,更投合当时士大夫的享乐心理。他们所追求的不单纯是官能上的满足,还有心理上对悲欢离合的体验。可以说,此赋与柳永词在表现男欢女爱上是相通的。夏竦的《放宫人赋》同样表现了对男欢女爱悲欢离合的体验。据《春渚纪闻》卷5记载,此赋作于作者12岁时。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更能说明对悲欢离合的情感体验是当时社会普遍的心理需求。赋中写宫女离别宫苑的心理极为传神:
莫不喜欢如梦,心摇若惊。踟蹰而玉趾无力,眄睐而横波渐倾。鸾镜重开,已有归鸿之势,凤笙将罢,皆为别鹤之声。于是银箭初残,琼宫乍晓,星眸争别于天仗,莲脸竞辞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步缓而回廊缭绕。嫦娥偷药,几年而不出蟾宫,辽鹤思家,一旦而却归华表。
作者对宫人的心理体会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具有美感,体现了当时欣赏幽约心理的审美风尚。
当然,追求享乐之等而上者是在艺术的境界中陶冶心灵。晏殊的《飞白书赋》、《御制飞白书扇赋》通过对书法艺术的赞美以寄托高雅超逸的情怀。所谓“飞白”,是一种特殊风格的书体,它的主要特征是笔画中夹白。它不同于枯笔,枯笔是端际露白,或时黑时白,而飞白则是丝丝夹白。这种书法艺术极具美感,对书者的技艺要求也极高,这正可以作为盛世生活的一种高雅点缀,因而深受当时人青睐。晏殊的《飞白书赋》叙述了“飞白”书体产生、发展变化以及兴盛的过程,尤其传神地描写了创作飞白书法的境界。书者临砚挥翰的心态是:“若乃宫砚沉碧,山炉泛清,恣冲襟之悦穆,指神翰以纵横。”书者与笔势完全融为一体,线条传达着书者的思想感情、个性特征。再看飞白书法之美:“空蒙蝉翼之状,宛转蚪骖之形。斓皎月而霞薄,扬珍林而雾轻。曳彩绡兮泉客之府,列纤缟兮夏王之庭。仙风助其缥缈,辰象供其粹凝。”“飞白”书艺具有如纤云蔽月、岚绕珍林般秀美典雅的特点,体现着盛世承平的高贵气象,反映了承平社会中人们的某些审美特征。当时,上至皇室,下至臣僚纷纷挥翰,创作飞白书法。太宗、真宗、仁宗均精于飞白。晏殊的《御书飞白书扇赋》即是颂美御笔之作。此外,晏殊讨论“飞白”书艺的言论尚有《谢赐飞白书表》、《御飞白书记》。可以说,君臣蜂起钻研“飞白”书艺,的确体现着身心通泰的承平心态,如游丝流水、长风轻云般的飞白书艺也可作为承平心态的一个象征。
治平心态在辞赋创作中还表现为对远离世俗尘嚣的闲散淡逸的情韵的追求。晏殊仕途平坦,处身于承平之世的真宗、仁宗时期,居官显要而了无建树,品茶、饮酒、狎妓、赋诗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名副其实的“太平宰相”。春残花谢,日斜燕归,往往引发他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和对野逸生活的向往,四时美景被赋予了闲散淡逸的情韵。他的《中园赋》寄托了优游于太平盛世的风流闲雅。赋中描绘了理想的野逸生活:
寓垣屋于穷僻,敞林峦于蔽云。朝青阁以夙退,饬两骖兮独归。窈蔼郊园,扶疏町畦。解巾组以遨游,饬壶觞而宴嬉。幼子蓬鬓,孺子布衣。啸傲蘅畹,留连渚湄。或捕雀以承蜩,或摘芳而玩蕤。食周粟以勿践,咏尧年而不知。琴风飒飒以解愠,田雨滂兮及私。
这段文字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所表达的情调十分相近。陶渊明幻想着插身于太平之世,作一个羲皇上人,而晏殊以一种悠闲心境细细品味着鼓腹而游、叩壤于途的美感。置身于天和景明,人与自然亲和的境界中,花鸟草木自来亲人,陶渊明幻想中的境界,晏殊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了。晏殊还在赋中展示了园中瓜果蔬菜的勃勃生机:“尔乃坛杏蒙金,蹊桃衒碧。李杂红缥,柰分丹白。”“历钟山之菘韭早晚,吴郡之苋茄紫白。织女耀而瓜荐,大昴中而芋食。匏瓠在格以增衍,藜藿缘阴而可摘。”晏殊对园圃美景的层层铺叙,景象叠生。瓜碧茄紫的豆棚园圃给人以置身上古太平之世的种种幻想,自由舒展的菜蔬果木,处处体现着远离尘世、人与自然万物相亲相融的闲适情韵。园中的虫吟鸟鸣更增添了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调:“鹪匪陋于荆棘,鷃无营于钟鼓。顺时律以弄吭,乐天和而命侣。燕溢溢以交贺,鹊翛翛而告语。”置身于这样的境界中,枯燥冗长的生活变得情韵盎然,具有了审美价值:“谈王道于樵子,接欢歌于壤父。……日复论名花于君子,兴瑶草于王孙。采家臣之秋实,歌上瑞之丰年。资旨蓄以仰冬,撷众芳而錬颜。至若严客幸临,良辰是遘。载掃危榭,爰张宴豆。蒙山骑火之茗,豫北酿花之酎。或秋弈以当局,或唐弓而在彀。”这样的生活不离日用百物之俗杂,而又充满高雅的情趣。晏殊的这篇赋描绘了理想的丰腴生活图景,展示了如沐春风般的舒展闲逸的治平心态。
晏殊善于状物,其景物的描写舒缓纡徐,从容不迫,体现出闲雅的气度。他的《雪赋》描绘了雨雪霏霏中的闲淡心境。以虚静之心映物,万物便显现出丰富的情韵。赋中对雪花的描写十分传神:“初晻暖以蓬勃,倏森严而悄寂,随蠛蠓以汎汎,径抉摇而奕奕。乍拂庑兮萦树,忽穿窗兮逗隙。厌丛竹之虚籁,点乔松之秀色。委严穴以含垢,赴波澜而灭迹。兽族处兮休影,鸟归棲兮接翼。原野漫其一平,羲舒为之双匿。”心静意迟,雪花也充满了灵淑之气,飞舞跃动的姿态似乎在礼赞存在的美好。在“倾身无希声,在目皓以洁”的意境中,流注着投身于自然怀抱中的融融暖意。赋的后半部分,描写了雪天不同的人物活动,显然是受到江淹《恨赋》、《别赋》的启发。在邃馆曾台,彤墀紫闼,人们在对饮赏雪,联句赋诗;在藻扃绣户,金屋兰堂,有人在端居悯默,惨别悽伤;在穷漠塞北,行者在艰难地跋涉;在边鄙之地,使臣在杖节怅望;在春意融融的暖国,稑穜在瑞雪的霑溉下生长。这种种的景象与钱惟演《春雪赋》之悯农伤己的情怀不同,它是作者的意识在自由地流动,是一次审美的心理历程,是闲散的心灵在体认美的艺术境界。钱钟书先生评价晏殊说:“他跟当时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作者以及宋庠、宋祁、胡宿等人不同,比较活泼轻快,不像他们那样浓得化不开,窒塞闷气。”[3] (P13)这段话虽是评价晏殊诗歌特色,用来评价他的赋也同样合适。晏殊没有刻意在字面上堆叠金玉锦绣,而是以活泼灵动之笔描绘了一幅幅富于承平气象的画面,风流蕴藉,温润秀洁,展现了闲雅淡逸的富贵心境。
文彦博的一些赋也以状物为工,与晏赋同一旨趣。他的《金苔赋》依据王嘉《拾遗记》的一段记载,描写晋惠帝时宫苑中特异的金苔。文氏深得汉大赋状物之旨趣,多角度地描写养尊处优的金苔舒卷自如的风致:“萦流荇而细细,缭舒荷而漠漠。……风团而或谓能铸,浪飐而多虞自跃。……东篱之菊兮,瞻我而失色;北堂之萓兮,对吾而不芳。”这种优游自得的态度与当时达官贵人的闲在气度深相契合。赋的结尾,曲终奏雅,指出金苔一类的人物不能指邪斥佞,排难解纷,于世无补,西晋的覆灭即是前车之鉴。赋中的金苔可以说是治平心态的一个形象化身。文彦博的《鸿渐于陆赋》师法唐赋描写飞鸿肃然从容的姿态十分传神,也颇能体现台阁风气。
总之,晏殊、夏竦等人的创作,或抒发盛世豪情,或表现享乐情绪,或发露承平心境,均体现着雍容典雅的特点,是那个承平时代一部分文人心理的真实写照。他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社会潜藏的危机,或不愿触及现实弊病,在政治上均无大的建树。在祥气氤郁的承平景象中,他们细心品味着生活的美好,体会着身心通泰的闲雅境界,并通过辞赋创作将这种种感受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