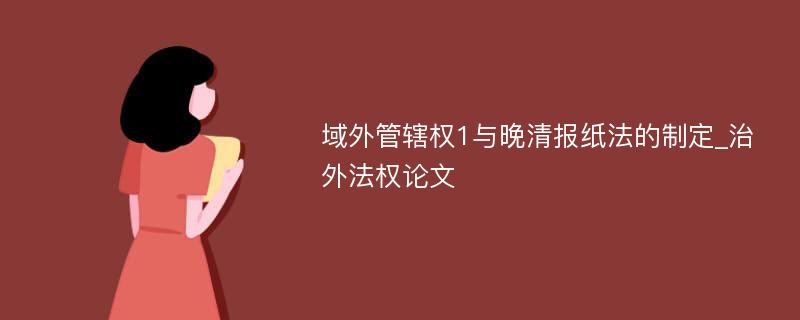
治外法权①与清末报律的制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外法权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政府制定报律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清廷欲有效管制包括租界在内的全国所有的报馆及其出版行为,另外就是预备立宪在法制建设上的需要。这两个因素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报律的制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为了配合清政府收回租界的治外法权。清末出版的报纸大多数在各口岸城市的租界之内,尤以上海最称繁荣,这些报馆大多数是国人所办,但多为“洋旗报”,②清廷要有效管理这些报馆,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租界独立的管理制度。租界当局对辖内报馆一般采取保护措施,给予基本的出版和言论自由权。租界当局之所以要按照西方的制度对报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大致出于两个动机,一是维护租界“文明”制度的形象,二是维持租界的治外法权。清政府在面对租界报馆随意报道朝廷秘密信息和肆意评论朝廷官员和政策得失的时候,往往因报馆托庇于租界“文明”治理制度而无法追究责任,由此体会到的主权丧失的危害比其他交涉事项更为明显而直接,因为报馆的揭露和批评还事关朝廷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颜面。如果制定一部西方式的“文明”报律,既能实现对租界报馆的有效管理又有助于收回治外法权,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1902年以后,这样的好机会曾一度出现。 西方人在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制度和观念,其中就包括了出版自由的理念。马礼逊1833年用英文在《广州志乘》上发表过一篇《论印刷自由》的文章,称上帝赋予的思想与言论自由权属于天赋人权,没有一条人立的法律可以取消。③这种典型的英国新教出版自由理念在西方各国均被奉为公理。西方人既然在租界内援用他们所称的文明制度,也就要对新闻出版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费唐法官曾指出,租界“文明”制度主要体现在它的“平民自治”,这种制度的运转需要依赖舆论,所以言论自由必不可少,这是工部局必须认真考量的因素。④既然如此,对于在租界内注册出版的报刊,无论其为外国人或中国人所办,租界当局都应待以宽容的态度。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胡道静论及上海报纸的繁荣,引外人著作探究其原因,认为大致有二:其一为商业发达,其二为“能够得到外国租界地的掩护,在相当的限度内获得言论自由权”。⑤费唐法官也指出,上海的报纸皆设立于租界,而且“为保证官署之不干涉,并保障其职员不受迫害(指清朝时代而言)起见,各报纸之作为外人财产注册者,即非全数如此,亦占大多数”。⑥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办报托庇于外人,主要是为了换取租界“文明”制度的保障,租界制度中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自然是报人最为看重的。上海为清末中国报界的模范之地,中国凡有租界之地大多学习上海经验,而报馆最多的地方又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所以全国报界的情况与上海大致相同。“苏报案”主事人章太炎、邹容没有受到重罚,是因为外国律师为他们作辩护时主张思想言论自由权,主持审判的外国人也支持这个理由。⑦而清政府决定封闭《苏报》并缉拿主笔,则与官府得知其不再是日商注册有很大的关系。⑧继《苏报》而起的《国民日日报》言论也较激烈,但是清廷也仅能做到禁阅、禁邮,⑨原因在于它以英商名义在英国领事馆注册。⑩总体而言,外国租界在一定限度内为当时中国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护,这是事实,虽然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11) 外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几乎涵盖所有租界内的事务,清政府甚至对租界内中国人的事务也不能完全行使主权,朝廷上下因此深感主权丧失的祸害。甲午以后,治外法权问题越来越严重,诚如某御史所言:“此后十余年中,虽内政竭力整顿,外权且日进而无穷。若复因循苟安,坐待法权之侵夺,则逃犯不解,索债不偿,赴愬多门,人心大去,无论治外法权不能收回,恐治内法权亦不可得而自保矣。”(12)在缉拿主笔和封闭《苏报》的过程中,张之洞等人便想借“苏报案”收回公共租界工部局历年来攘夺去的主权,以便今后再遇到缉拿匪犯之时便于措手。(13)而恰恰在治外法权问题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肯相让,势在必争。对于这一点,地方督抚也了然于心。(14)英美等国为维护租界内的治外法权,往往把矛头指向清廷残酷的法律。实际上,自同光以来,西方人关于中国律例野蛮残酷的指责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此清廷也有清醒的认识。(15)有识之士也早就提出要改革律法,以符合西方律法,以便于赢回主权。(16)正因为法律制度对内政外交都很重要,尤其与治外法权的收回有莫大的关系,清政府才下决心着手修订刑法、民法、商法以及报律等各项法律,以使大清的法律能够“中外通行”。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就提出要制定报律,目的之一就是对付租界内的报馆。他明确指出:“凡在洋人租界内开设报馆者,皆当遵守此律令。各奸商亦不得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黄议论,于报务外交,似不无小补。”(17)对于外国人办的报纸他还不敢直接提出也要管理,“在洋人租界内开设报馆者”显然仅指中国“奸商”。当然,康有为当时提出要制定报律主要是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舆论,以利于他的维新变法事业,上引文字也并非专门针对租界的治外法权。管学大臣张百熙在1901年提出要办官报以对付租界报纸舆论之时,也曾提出过要制定报律,他提出的“粗定报律”只是几种禁令而已。(18)清廷此时对于制定报律尚无紧迫感,就在张百熙提议制定报律的这一年,清廷修订了《大清律例》,仍然沿用了中世纪性质的刑律盗贼类中“造妖书妖言”这一条对违规的报纸言论进行定罪。(19)在“苏报案”中,这一刑律遇到了公共租界“文明”制度的抵制,也同时遇到了治外法权的阻梗。清廷原来的想法是要将章太炎、邹容弄到南京,以便处以极刑,租界当局最初并不知情,“苏报案”初起时,法、美、俄、德、荷、比等国公使均赞同将《苏报》主笔等人交给清方,只有意大利公使反对。(20)但是知名记者沈荩恰在“苏报案”期间遭清廷杖毙,在华的外国使领官员对清廷的行为深表不满,不肯把苏报案犯交给清政府,其借口就是担心交出后这些人会遭到清政府“重典”处置,有伤他们所认为的“公理”。(21) “苏报案”后,清廷开始考虑制定报律,这当然不是单一的举动,而是清廷试图重建法律体系以适应现实环境的整体设计中的一项。 清政府的法律不能完全适用于租界,主要原因是外人指责其“残酷野蛮”,因此朝廷和地方政府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处理发生在租界内的许多争端。参与处理“苏报案”的地方督抚等官员对于争回或补救主权都曾想了办法,(22)但是最后还是按照工部局的意思办结此案。法律是一国之本,正如负责修律的大臣沈家本所言:“国家既有独立体统,即有独立法权,法权向随领地为范围。”(23)从西方法理而言,这是属地主义,沈家本等人对此也十分清楚。更何况租界本属中国领土,西方各国一直都予以承认,他们对中国政府在租界内治理华人的主权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异议。(24)但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了使自己的管理权不致丧失,坚持对所有租界之内的外侨和中国居民予以保护,尤其对出版言论自由给予特殊的照顾,他们认为这事关“外人素持公理之名誉”。(25)清廷深知外人的此类借口,所以在庚子事变结束之后即宣布实行新政,欲以较为“文明”的政治制度来治理国家,以博得外人“文明”之观感,以示不再与外人所持“公理”冲突。另一方面,张之洞等人在力行新政的时候,对国家主权的丧失深感不安,时时不忘收回治外法权。就在1902年,出现了一次收回治外法权的机会,这就是清廷在与英美等国重新协商修订通商条约的过程中得到了一项正式的许诺:只要清政府使自己的法律体系符合西方“文明世界”的通则,列强可以放弃治外法权。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清廷首先与英国议定了新的通商条约,其第十二款曰:“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26)次年,清廷与美国、日本议定的“通商行船条约”也都有这一条款,文字也相同。(27)稍后与葡萄牙签订通商条约也有此内容。清廷在中英通商续约正式签订之前就下发了一道谕旨,明确指出:“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自裨治理。”(28)很可能是清廷这样公开表态之后,英美等国才同意将前述放弃治外法权的条款添入条约。在修约过程中,张之洞、吕海寰、盛宣怀等人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他们坚持要求列强放弃治外法权,上述条款才得以写入条约。(29)此后,清政府成立了法律馆,开始收集翻译西方各国和日本的法律汇编及法律书籍,着手制定西方式的法律。尽管清廷修律有主动改变旧有法律体制以符合新政思路的因素,(30)但是列强同意在中国法律“臻于妥善”之时放弃治外法权仍然是一股重要的外力,对当时主持修律的大臣而言是直接的动因。(31)因此之故,沈家本等人在奏折中屡称修律是为收回治外法权计,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其他官员。(32)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光绪也认可此说。(33) 与此同时,新闻出版方面的律例也开始着手制定,并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首先推出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专门的报律则由商部、巡警部酌定,由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议定之后形成了报律草案。(34)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报律草案在交给相关部门商议时遇到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治外法权因素。清廷修改法律本来就有收回主权的打算,因此在修订各种法律时都考虑到了外国的因素,(35)这也是各种法律的制定大多有外务部参与复核的理由,报律的制定也是如此,因为外务部是对外交涉的政府部门,而报馆与外国人控制的租界关系密切。也因为这样,当时任江苏巡抚的陈夔龙要求朝廷饬外务部专门与各国公使商定与报纸、电讯等言论事务有关的法律专条。(36)法部尚书戴鸿慈在议论制定法律办法时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编纂“文明世界”的法律最晚,集各国先进法律之大成,容易形成世界上最完备的法典,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法律的适用性如何。他认为施行新法律存在四方面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外国扩属人主义与内国属地主义相冲突”。(37)因此主张从长计议,认真研究讨论,绝不能草率。他的这一看法也体现在民政部奏定《报馆暂行条规》的奏折中。报律四十二条草案本来已经成稿,但是民政部却认为该草案与租界和沿海商埠有关,需咨送外务部仔细研究对策。(38)光绪三十三年底,民政部在奏定报律时,再次提到了七月份之所以没有正式出台报律的具体原因,一是“以事关法律,非详加讨论不易通行”,其二即租界外埠问题的困扰。民政部在奏折中说:“且以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开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订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纷歧,转多窒碍。迭经咨商外务部体察情形妥为核覆,旋准覆称:各项法律正在修订之际,尚未悉臻完善,若将此项报律遽为订定,一时恐难通行,似应暂从缓议等因。用是审慎迟回,未敢率行定议。”(39)因此,《报馆暂行条规》仅仅是报律草案的删节版,主要是为了应急试用,所以没有关于租界的内容。(40)从上引的这两份奏折来看,民政部在制定这部报律时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是对租界内报馆应如何管理。这涉及到治外法权问题,一旦条文不当将引起外交纠纷,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要请外务部协同复核。二是各项法律正在制定过程中,尚未“悉臻完善”,报律须与各项法律保持一致,才能在整体上完善法律体系。民政部和外务部的此种考虑显然是由于新的通商条约中有这方面的规定,一旦没有达到列强所认为的“文明”标准,就会影响到治外法权的收回,这是修律官员不敢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清廷制定报律确实指望它能起到实际的作用,对租界内报馆的控制能得到加强。比如,民政部在制定报律的时候特别参考了香港新定的“报律”,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条:“无论何项人等,凡在香港境内刷印售卖或分送各项报章、书籍及一切报告、说帖,其宗旨在摇惑中国人心,酿成变乱,或使人民因此犯罪于中国者,得处二年以下之监禁或五百元以下之罚金。”他们看到之后如获至宝,认为这与现定报律草案有关条款大略相同,一旦颁布施行之后,“有意外之交涉,亦可援引比照以为杜绝徇庇之计”。(41)由此可见,清廷在制定报律时的谨慎、犹豫主要受到租界治外法权的困扰,他们害怕报律不完善、不“文明”会影响到收回主权的大计;他们既想有效管理租界内的报馆,又非常担心报律的实行会引起“交涉”,晚清从朝廷到地方政府,最怕的就是与列强发生“交涉”。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定一部报律竟如此凄凄惶惶,真难为了这些官员!如果没有外国租界和治外法权的因素,仅仅是为控制报馆或者是为预备立宪而制定报律,何至于此。 然而,正式颁布的《大清报律》(包括宣统二年出台的《钦定报律》)并没有明确的关于租界报馆的条款。但是细绎条文,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内容与租界因素有关。第一,《大清报律》对报馆开设地点没有做出特别规定,只需登记出版地址即可。这表明该报律也适用于租界;第二,报律第二条规定,可以充当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者须是“年满二十岁以上之本国人”。这就是说,第一:外国人不适用于本律;第二,凡合法登记的中国人,无论所办报馆是否在租界,都要受《大清报律》的管辖。清廷制定报律原来就是想“俾各馆一体遵循”,隐含的意思就是租界内的报馆也不能有例外,因此民政部特别与外务部各堂官悉心筹定,巧妙地避开了报馆开设地点的问题,又把外国人排除在外,让他们继续享受治外法权。在开始制定报律的时候,江苏巡抚陈夔龙曾指出:“凡通商口岸开设华字报馆者,勿论华股、洋股,悉应遵守中国报律。”并且提出中国有自行处治权,外人不能干涉。(42)他虽未明指外国人也应受报律约束,但是至少明确要求任何资产性质的报馆都要纳入报律管辖范围,“洋旗报”和外资报馆自然也包括在内,这对租界治外法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事实上,《大清报律》在草案中确曾添入有关租界内报馆的条款,但是在送各外国公使审阅后未获认可,于是又删去了这些条款,这才得到外国公使的认可。当时的一些官员对此非常不满,但又无可奈何。(43)因此,修律官员在条文中只对“国人”的办报资格加以条规,对开办地点也故意模糊,避开租界,他们以为这样至少对租界内的中国人办报可用新的法律加以约束。然而,修订法律大臣在条文中隐含的对租界报馆的管辖空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外国人既然不受《大清报律》的约束,本国人如要办报就可以直接请外国人出面作为发行人、编辑人和印刷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大清报律》还是《钦定报律》,对租界内“本国人”所办的“洋旗报”也仍然无法控制。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911年,两广总督张鸣岐就革命报刊挂洋人牌子一事咨询民政部应如何办理,民政部不能决,转咨外务部,外务部答曰:“报馆既挂洋旗,则吾国报律不能适用。因吾国领事裁判权尚未收回也。”(44)由此可见,租界报馆事务不仅管理内政的民政部无法也不敢管理,就是负责对外交涉的外务部也不想惹事,政府行政部门如此,政府制定的《大清报律》和《钦定报律》对租界内的报馆而言也就形同虚设了。 从报律四十二条草案到《大清报律》再到《钦定报律》,除了把保护言论自由权的条款剔除之外,(45)清末的报律至少在形式上是越来越“文明”了,这与清廷创建新法律体系的精神基本一致,(46)这其中有立宪政治一步步高涨的背景,可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来因素的逼迫。(47)其实,最早提请清政府制定报律(press law)的恰恰是英国人。早在同治五年(1866年),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因传教士所办的《广州新报》屡有诽谤中国官员的现象,建议中国政府对此采取法律行动。总理衙门不愿多事,遂由恭亲王照会英公使阿礼国,要求英方按照英国的法律处理中文报纸的诽谤行为。英国人也确实在上海制定了两项有关报纸的规则:英国人未获执照不得在中国出版中文报纸;英国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出版的报纸中如有诽谤行径,即视为违法。(48)由于清政府对租界涉外事务不愿与闻,更不愿管理,希望外国人自己去处理类似报纸诽谤之类的事务,于是把管理租界报馆的权力拱手让予外人,外人也就按照总理衙门的意思收下了这份意外之礼。在恭亲王照会阿礼国的时候,上海的中文报纸只有英商开设的《上海新报》,其他口岸租界也只有外国人办的少量报纸,朝廷和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一定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中国人也会在租界里开设报馆,而且越来越多,更没有预料到这些报馆居然敢肆意讥评官府乃至指斥乘舆。 当外国租界当局的管理权限越来越大,以至于本国政府对租界内自己的臣民也无法有效控制的时候,朝廷才知道主权的丧失已到了危害其合法统治权的地步。而当租界报馆的揭露性报道和讥评危及朝廷名誉和权威之时,他们才想起要制定报律,希望以西方式的“文明”方式来控制舆论,以争回自己曾经随意放弃的治理权。殊不知,当甲午、庚子以后,列强对于积弱已久的清朝政府早已视之蔑如,远不如在所谓“同治中兴”年代那样还愿意在洋务方面帮清廷一把。此时的列强只知道维护既得权利,哪里会真愿意当中国法律制度“文明化”之后就放弃治外法权。最早向外人“索议”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的张之洞,后来就对沈家本等人所持的修律以收回治外法权的想法不以为然,他认为条约中外人的承诺本身就是已失法权的明证,而“所谓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十字,包括甚广”,一旦贸然举行,很可能造成许多法律上的困境。(49)张之洞言下之意是,政府所修的法律无法达到列强所定的“皆臻妥善”标准,因此也无法完成收回治外法权的任务。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刘廷琛则认为,收回领事裁判权“首在国势强盛,次须审判公平,若于此二者锐意经营,成效昭著,不患无收回之一日。若国势如故,审判如故,而谓持摹仿之空文,收法权之实效,殆必无之事”。他把修律官员按照西方标准修订的法律视为“摹仿之空文”,主要是指这些法律无助于收回治外法权。他认为这样做反使中国原有礼教扫地,于是社会混乱,匪徒蜂起,外人将得到借口以行并吞之策,“则人将治我,尚何裁判权可收乎?”(50)张之洞和刘廷琛等人为保存传统礼教而反对修律,固然属于守旧思想,但是他们对于列强的许诺不以为然确实是出于实际的观察。即如报纸管理,租界当局在“苏报案”之后就提出“工部局有权检查及管理租界内华文报纸,并列入土地章程附律第34款”之建议,因北京公使团反对而未果。(51)很显然,租界当局在经过“苏报案”之后,感到有必要通过正式条款加强对租界报业的控制,以此对抗清政府的主权要求,这种企图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维护其治外法权的效力。至于中国法律是否能达到西方所谓的“皆臻妥善”,也即“文明法治”的境界,在当时看来是遥遥无期的。即使是二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治下的民国,费唐法官在研究了租界治外法权的情况后也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设使法治之在中国,尚未树立至一种程度,而使普遍人民之行使个人权利以及履行市民义务,均得有充分保障,则一旦将治外法权废除,势必令现有市制之命脉破坏无余。盖社会内之重要部分,倘不复享有一种行动自由,如治外法权之现所赋予者,则公共租界内地方自治之平民制度,将终止其效用。”(52)这就是说,中国的法律尚未“臻于妥善”,为保护租界内自由权利起见不能取消治外法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按照西方标准制定的包括报律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其“文明”与否的标准是由西方列强来界定的,只要西方列强不认可这些法律,借以收回治外法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清政府所制定的报律之所以在后人看来在某些条款上较为“文明”,并非清廷真的具有宪政意识或现代法律意识,修律大臣们只是参照了西方的标准来装点法律,主要是为了让列强满意,以利于收回租界的治外法权。换言之,假如没有修订一部“文明”的法律以收回治外法权这一前提,清廷是否会汲汲于制定一部稍具现代特征的报律,恐怕还在两可之间。 注释: ①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的概念学界有争议,但是由于清末官方两个说法并用,所以本文不作区分,为行文方便使用“治外法权”一词。 ②所谓“洋旗报”就是请外籍人士挂名为出版人注册登记,出资者、编辑者和经营者均为中国人。这样挂“洋头”卖报纸,为的是避免清政府的管理,可享受到租界内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 ④《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无出版社信息),1931年,第446页。 ⑤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一期(1934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219-220页。 ⑥《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第467页。 ⑦参见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1-73页。 ⑧《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八日探员志赞希赵竹君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中称:“遵查苏报初办,挂日商牌,沪道询小田,不认,即无外人保护。刻已拿到主笔三人……该报即可封闭。”《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09页。 ⑨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一期,1934年,第261-262页。 ⑩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59页。 (11)胡道静在述及此事时曾说:“事实证明这种诳语不能否认,真是一件堪痛恨的事。”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一期,1934年,第220页。 (12)《御史吴钫奏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23页。 (13)《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428页。 (14)《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两江总督魏光焘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中称:“彼系争界内之权,实非惜各犯之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433页。 (15)光绪三十二年沈家本、伍廷芳等奏:“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藉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卷二百四十四“刑考三”,考九八八二。 (16)陈炽在甲午战争前就指出,中西律法相比,西轻而中重,每当交涉案发生时,纠纷就难以解决,于是“泰西领事诸官,乃得操会审之权,不复以与国相待”。因此建议“斟酌其间,变通尽利”。陈炽:《庸书·刑法》,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6页。康有为在戊戌年痛感“吾国法律太苛,监狱污秽,外人惊恶,故不能收回治外法权”,因而提出改革法律审判监狱之法。见康有为:《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军折》,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1页。郑观应指出,中国如不改革律例,则不能列于教化之邦(也就是文明之国),因此要“与外国一律”,改用外国刑律则“外国人亦归我管辖,一视同仁,不分畛域”。郑观应:《盛世危言》,辛俊玲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13-215页。 (17)康有为:《请定中国报律折》,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34页。 (18)张百熙的“报律”有四条:一、不得轻议宫廷;二、不得立论怪诞;三、不得有意攻讦;四、不得妄受贿赂。此外则宜少宽禁制。见方汉奇、谷长岭、冯迈:《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编年》(六),《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4辑,第226页。 (19)参见张宗厚:《清末新闻法制的初步研究》,《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3辑,总第8辑,第195-196页。 (20)张簧溪:《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380页。 (21)《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432-435页。 (22)张之洞提议免去死罪以求租界当局交出主犯,他认为这是为争取主权的权宜之计。袁树勋则提出补救主权的两个办法:由地方官审讯,给案犯法外之仁;照会各公使,申明和约及会审交犯章程,以后不得援以为例。参见《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432、435页。 (23)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刑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6页。 (24)1862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之后曾有“自由市”之动议,但是英国公使、领事均反对,英国政府也反对。英公使谓:“中国政府未尝将统治去本国人民之权放弃,英国政府也未尝要求对于中国人民行使其保护权”,并表示对“外侨以办理市政为名而侵犯中国主权的企图予以警醒,不使得逞”。1864年3月25日,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在一封信中指出:“此间多数外侨,有一错误观念,即以为公共租界可视为外国领土,并可漠视中国政府于纷纷迁居租界之数十万华民之管辖权。”北京公使团对英国的这一观点没有异议。参见《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第175-176页。 (25)《字林西报》的一篇评论,转引自张簧溪:《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381页。 (26)《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六款》(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四日),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919页。 (27)中美商约是第十五款,中日商约是第十一款。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083、5086页。 (28)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4864页。在光绪二十八年的四月初六日的这道谕旨之后不久,清政府就与英国鉴定了新的通商条约。 (29)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奉旨与英国议定商约的吕海寰、盛宣怀曾将议定商约条款的过程奏明,其中说到“治外法权、筹议教案、禁莫啡鸦”三款(分别是第十二款、第十三款、第十一款,而奏折中将治外法权放在最前,可见他们对这一款特别重视),是张之洞等人向英使马凯“索议”入约的,而英国方面在此之前有承诺。吕海寰等对这三项非常重视,认为“皆我补救国计民生要图,幸就范围,实有裨益。”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4950页。 (30)参见高汉成:《晚清法律改革动因再探——以张之洞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系为视角》,《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1)光绪三十二年沈家本、伍廷芳等奏:“……夫西国首重法权,随一国之疆域为界限,甲国之人侨寓乙国,即受乙国之裁判。独于中国不受裁判,转予我以不仁之名,此亟当幡然变计者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领事裁判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之仁政之要务,即修订之宗旨也。”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卷二百四十四“刑考三”,考九八八三。伍廷芳等在另一奏折中也直言“修订法律本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宗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卷二百四十四“刑考三”,考九八八五。 (32)如《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奏修订法律宜妥慎进行不能操之过急片》(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谓“夫法律之所宜修订者,本欲收回治外法权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37页。光绪三十四年,学部对新刑律表示反对,指出修订法律大臣制定新刑律“所注意者,只收回治外法权一事。”认为即使为了收回治外法权而采用西法,也不能弃旧律精义于不顾。参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卷二百四十七“刑考六”,考九九二○。 (33)光绪三十二年的一道谕旨谓:“饬于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告成后,即将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克期纂订以成,则领事裁判权可以收回。”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卷二百四十四“刑考三”,考九八八四。 (34)王学珍:《清末报律的制定》,《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 (35)刑法、民法是最显然的,宪法也要考虑治外法权的因素。达寿在一份奏折中曾指出:“若宪法颁布,一国之中常有两种法权,则宪法为无效。此治外法权所急宜收回之证也。”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四册,卷三百九十三“宪政一”,考一一四三二。商法也是如此,吕海寰在光绪三十一年奏称:商埠不得不开,但是需要先谋主权,商律为收回治外法权之要领,必须中外一律始能预先防患。参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四册,卷三三四“四裔考”,考一○七五四。 (36)参见《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报纸电讯集会演说宜范围于法律之内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50页。 (37)另外三个困难是“安常守故,见小欲速”“旧法积久弊生,新法弗便于私”“法理精微,莫明解释”。见《法部尚书戴鸿慈等奏拟修订法律办法折》(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1页。 (38)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729页。 (39)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818-5819页。 (40)据民政部奏,《报馆暂行条规》是为了对付流弊日甚的报馆,而且与拿办《中华报》主笔彭贻孙等人有关。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729页。而前此的《报章应守规则》是京师巡警总厅制定的,具有地方性质(实际上准行于京津地区)。参见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57页。 (4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819页。 (42)参见《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报纸电讯集会演说宜范围于法律之内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50页。 (43)参见王学珍:《清末报律的制定》,《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第232-233页。 (44)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编年》(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5页。 (45)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奏定的“核定报律四十二条”中有关于言论自由的表述,这就是第三十三条:“凡照本律呈报之报纸,除本律所定禁例外,准其有言论自由之权。”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二册,卷一百十九“职官考五”,考八七九九。但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正式颁布的《大清报律》中这一条被删去了。 (46)光绪三十四年,宪政编查馆在覆奏沈家本等人“编定现行刑律折”中指出,朝廷庶政咸新,以前禁止的都渐次放开,“结社集会、发行报纸之类均非旧时律例所能限制。”因此与新法不合的各种事务都应该改革。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卷二百四十七“刑考六”,考九九三三。 (47)沈家本在刑律草案告成之际上奏说,制定西方式的法典是国际竞争的需要,“中国介于列强之间,迫于交通之势,盖有万难守旧者。”各国借口中国法律制度未能完善,因而用领事裁判权削弱中国主权,因此不能不改革司法制度。参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卷二百四十五“刑考四”,考九八九一。在《宪政编查馆大臣和硕庆亲王奕劻等奏为核定新刑律告竣请旨交议》一折中,宪政编查馆认为,颁行新刑律有诸多益处,其中之一为符合预备立宪以“保卫人权”并赞助“国民主义”,另一目的则为“裨益外交”、“用同一之法律,以收法权。”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卷二百四十五“刑考四”,九八九三。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则认为宪法与收回治外法权直接相关,他指出:“宪法既定,则宜收回治外法权。然中国之刑法、民法俱未规定,将来发布宪法,实多困难。日本收回治外法权虽在发布宪法之后,而制定刑法、民法则在发布宪法之前。若宪法发布,一国之中常有两种法权,则宪法为无效。此治外法权所急宜收回之证也。”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四册,卷三百九十三“宪政考一”,考一一四三二。 (48)Natascha Vittinghoff,"Readers,Publishers and Officials in the Contest For a Public Voice and the Rise of a Modern Press in Late Qing China(1860-1880)," T'oung Pao,Second Series,vo1.87,4/5(2001),p.407. (49)参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卷二百四十四“刑考三”,考九八八七。 (50)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册,卷二百四十八“刑考七”,考九九三七。 (51)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25页。 (52)《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二卷,第297页。标签:治外法权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晚清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