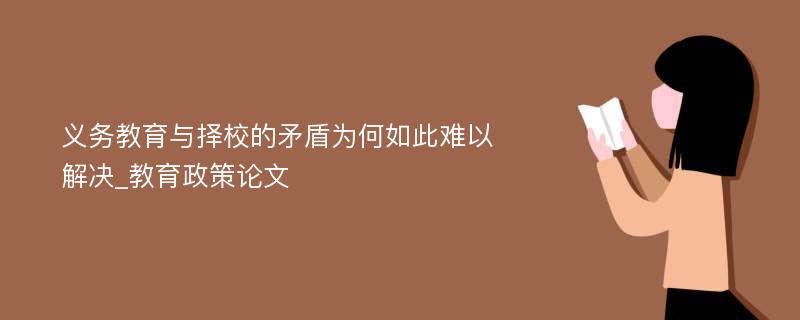
化解义务教育择校矛盾为什么这么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务教育论文,择校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一般解释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不均衡,导致了学校间的办学差异。这样的分析虽然具有合理性,但当前我们需要更加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不均衡是不是导致择校问题的唯一原因,如果是,政府为什么会长期采取这种倾斜性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如果不是,还有哪些因素加剧了义务教育学校间的择校矛盾,这些因素间又是如何作用的,其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笔者认为,从现实来看,我国义务教育领域的择校矛盾是由政府、市场和人情社会等因素相互卷入、共同作用、彼此强化的结果。本文拟将义务教育择校问题根植于当代中国学校间横向分层与分割的背景中,从政府、市场和人情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分析义务教育择校矛盾的发生机制,以期为深入理解引发义务教育择校矛盾的复杂机制提供“新的认识图谱”。
一、学校间横向分层与分割的普遍性事实
学校间横向的分层与分割,指在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同一层级的学校内,存在着由于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育质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度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性和层级性,造成学校间的“好中差”之分。
现代学校间的横向分层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制度设计的学校分层。二是自然演进的学校分层。三是主观建构的学校分层。学校间的横向差异,既具有相对客观的标准,诸如师资的数量和结构差异、校舍面积、设备等数量化指标等,也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体现为大众心理、公共舆论、社会观念和民众期待对学校间差异的影响。一方面,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学质量和办学特色影响着公众对学校的认识、判断和选择;另一方面,持续广泛的公众认识和民众判断构成了具有弥散性的公共舆论和大众心理,这种大众心理抬高了“名校”的声誉和地位,加剧着人们的择校需求和择校冲动,它“具有孟德斯鸠或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意涵,即制度的作用已经完全扩展到人们的意识形态、思维图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一种全社会的风习”[1]。尤其是对于广大“非专业”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不但缺少判断学校优劣的专业知识,也缺少对学校之间差异进行判断的充分信息,“从众”、“跟风”就成为了他们体认学校质量和差异的主要方式。这也可以解释国家在中小学取消了“重点学校”的称谓以后,为什么这些学校还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这不但是因为这些重点学校以往积淀的优越师资和良好的办学条件在持续发挥作用,更因为民众对他们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认可度和公共舆论倾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中小学办学条件、硬件设施、师资条件并不比某些“名校”差,甚至是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名校,但家长和学生依然对名校趋之若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名校在社会中长期积淀的优越感和信任感,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判断能力和判断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名校成为了一个主观建构的、可感知的“社会符号”,其“符号效应”不仅诱导着家长的选择趋向,也对教师、校长有着强大的选择驱动力。正是这种名校的“社会符号效应”对优质生源和优质师资的吸引,不断加剧了其与一般学校的办学差异。
二、义务教育公共治理中的“市场失灵”
一是择校供需关系的“市场错位”。当前,义务教育“以钱择校”行为中的供需关系,正在由“家长选学校”倒置为“学校选家长”。正是这种错位的供需关系制造了义务教育市场的“虚假繁荣”。其发生机制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义务教育择校行为主要发生在家长与私立学校之间,我国义务教育的“以钱择校”行为主要发生在家长与公办学校之间。其基本表征是,少数优质中小学利用自身的办学优势,在正常的招生名额之外,划出有限的招生指标,通过高额收费的方式,在家长中制造了激烈的竞争关系。
二是公共治理关系中的“市场僭越”。这主要是指,市场机制在义务教育公共治理中已经超越了其基本职能,发挥着市场之外的“特殊”功效,产生了教育公共治理的“副作用”。众所周知,无论从对国际义务教育治理经验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公共教育治理理论思考的角度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载体主要是私立学校,即通过私立学校间的竞争,提高学校的办学特色,为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机会,以弥补公办学校由集体选择的办学体制和就近入学的招生政策带来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办学体制僵化和学生选择性不够等弊端。相对于私立教育机构的选择性功能,公办中小学则承担着提供基本教育服务、维护教育公平、均衡教育资源的重要职责,即政府是基础、市场为补充,这就是政府与市场在公共教育治理中的边界划分和功能定位。
在以择校为特征的市场机制中,出现了市场边界的越位和功能的异化。其主要表现为,市场不再是政府的补充,而是少数地方政府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因为,当择校的供需关系发生在家长与公办学校之间时,市场的竞争关系就不是发生在私立办学主体之间,而是发生在少数优质公办学校与多数薄弱学校之间。其作用机制是,地方政府将少数优质资源进行市场包装,并利用家长对优质学校的渴求心理,进行“有组织”的出售和交易。
将这种交易称“有组织”地出售,是因为这样的交易不是基于自由竞争的家长选择,也不是基于“价高者中标”的市场规则,而是将选择的决定权落在了学校的管理者和政府手里,择校的对象、缴费的数额甚至是缴费的方式,都受到权力的制约和限定。这样的市场机制不但不能实现对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办学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反而为名校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制造教育差距提供了体制基础。这不但让名校实现了为政府创收的特殊功效,还严重挤压了民办中小学的发展空间。因为,名校享有着国家配置的优质办学资源,并且可以以低于“成本”的方式向社会进行“出售”,这让一般的民办中小学“望尘莫及”,从而加剧了其办学危机。正是这种市场机制的僭越,使得中国义务教育治理主体中,除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外,出现了一个与政府有着庇护/依附关系的特殊的“第三者”,这就是那些通过政府倾斜性政策打造的“公办所有、市场投入、非公非私、名公实私、名私实公”的“假民办”。“‘假民办’的出现,不仅使得其成为当代中国义务教育治理中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具有特殊优势的竞争主体,也使得其成为当代中国诸多教育问题的主要‘肇事者’,如愈演愈烈的中小学择校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乱收费、教育腐败等问题”。[2]
三是存在于义务教育学校内外的“隐形市场”。这主要是指,在当代中国义务教育办学实践中,存在着一个与“择校市场”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和互相强化的教育市场,这个教育市场依托于“以钱择校”的社会背景,同时以潜在、隐形的方式,强化、支持和推动着择校矛盾。这就是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以帮助中小学生争夺名校名额为诱导,广泛存在于义务教育学校之外的形形色色的培训市场。诚然,这里并不是不加区分地将所有的校外培训机构都界定为加剧义务教育择校冲突的“隐形市场”,而是特指那些由校内外教师“相互配合”、体制内外的管理者“彼此合作”而构成的、导引并加剧着家长择校行为的相关培训机构。
三、教育政策的“新特殊主义”运行逻辑
“特殊主义”是相对于“普遍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美国学者帕森斯将两者看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野的重要标志。他认为,如果行动者按同一个标准对待所有其他的行动者,就是普遍主义行为模式;如果对不同人采用不同的标准就是特殊主义行为模式。[3]这里的特殊主义,主要是指社会成员根据环境和情境的特殊性,将交往的规则限定在与自己有着特殊关系的人身上。“特殊主义的价值观是古老的,它曾经并且现在仍旧凝聚着一个个部落、群体或社区,促成着一种特定的信任、互助与交换。”[4]
借用“特殊主义”这一视角分析中国的教育政策,可以看出,教育政策的运行也经历了一个从“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转换历程。传统教育政策的“特殊主义”运行模式具有“服务少数人利益、满足特殊人需求”的“对人不对事”特征。与此对应,现代教育政策愈来愈具有了普遍主义的运行特征,即现代教育政策坚持“对事不对人”的立场,在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各个环节遵循“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教育政策的普遍主义运行方式,是现代教育政策的典型特征,并具有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公信力的重要功效。因为,普遍主义的教育政策可以让相关利益主体对照教育的普遍规则和一般规范,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教育方式,以取得可期可盼的教育结果。例如,按照志愿和分数录取的高考政策、按照学区和户口的就近入学政策、按照科研成果和教学工作量的职称评定政策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殊主义在当代中国教育政策的运行中已经走向了终结,相反,在某些领域,其正在以普遍主义的形式重新登场。这种重新的登场既具有传统特殊主义的特点,又赋予了现代普遍主义的外壳,使得其特殊主义的运行更加隐蔽和“诡秘”。笔者将这种根基于传统、依托于现代的教育政策运行的“新特征”称之为“新特殊主义”运行逻辑,并进一步扩展为一切在普遍主义规则的“掩护”下,对教育政策进行的变通、抵制或扭曲,以实现部门或个人特殊利益的教育政策运行方式。诸如,对教育政策“雷声大、雨点小”的象征性执行、对教育制度“按需所用”的选择性执行,以及与上级政策“貌合神离”的替代性执行等。教育政策的“新特殊主义”运行方式,对义务教育择校矛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通过对现有教育政策的“为我所用”,强化了名校与薄弱学校的“区隔”状态,营造了择校的氛围和冲动。义务教育学校间的办学差距主要表现为优质师资的差距,促进优质师资的合理流动成为缩小教育差距的有效手段。而当前在一部分地区优质教师的流动常常流于形式,其根本原因是由名校、名师甚至是少数官员等组成的“利益联合体”对教师流动政策的“变相抵制”。之所以称之为“变相抵制”,是因为这种抵制是以“支持教师流动”的姿态和面貌为掩护的。这在某些地区表现为“点缀性”地安排个别名师做“象征性”交流,甚至是仅仅安排少数普通教师或年轻教师做“应付性”交流;更有甚者,有些官员和学校还以“教师过多流动破坏了‘学校的文化传统’”为借口,公开地“抵制”教师交流制度。
潜藏在这些“抵制”与“变相抵制”行为背后的逻辑是:名校、名师和地方官员这一紧密的“利益联盟”对名校声誉的眷恋和对名校特权的维护。因为,名校地位的维护,对于帮助他们获取部门或个人的“特殊”利益具有“实质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深化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触动部门利益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异常艰难。此外,地方政府在施教区划分中享有的充分“自由决定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少数官员根据个人的需要和喜好划分学区的倾向。甚至个别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迁建名校、名校办分校等方式,与开发商“合作”,制造出“新的学区房”。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享受学区房价格上涨所带来收益的同时,广大的家长群体成为实际的埋单者,而使得这种部门利益得以实现的机制是:政府“放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这一“冠冕堂皇”的政策追求。这种将普遍性规则置于前台、特殊主义规则潜藏在后台;以普遍主义方式为手段、特殊主义利益为目的的“新特殊主义”政策运行,降低了教育政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扭曲了教育的公共性品质,使得“在有关教育改革的言论中总会出现一些虚夸、虚幻乃至虚伪的‘修辞’,行动中总会出现一些唬人、蒙人乃至忽悠人的‘作秀’,从而形成一些‘假象’”。[5]
其次是通过对现有教育政策的“变通”与“改造”,服务于特定群体的择校需求。这种“变通”与“改造”的动力来源于中国人情社会特有的关系网络。费孝通将传统中国的人情关系称为“差序格局”;杨国枢将这种关系网络概括为“家人讲责任、熟人讲人情、生人讲利害”;黄光国则将其类型进一步划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6]人情社会复杂的“差序格局”,常常使得“家人关系”在教育政策的运行中受到了特殊的照顾、“熟人关系”列为优先关照,“生人关系”则容易成为“普遍主义”竞争规则的“失败者”。这也成为了我国义务教育择校中“条子生”、“招呼生”屡禁不止的社会基础。
可见,在“名校”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标识和一种身份的人情社会背景下,那些掌握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公共权力的干预或人情交换的方式,将自己或熟人的孩子安置在名校就显得“合情合理”和“顺理成章”。而使得这种以“人情交换和权力庇护”为特征的择校现象得以发生的机制是少数地方官员对义务教育政策的变通与变革。例如,依托于国家的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名校招收的择校生不得超过一定比例”的规定。这“不超过一定的比例”,实际上为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既得利益者的择校行为预留了空间。“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凭借自身优势条件,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7]再如,利用“国家义务教育的免费政策”和“制止教育乱收费”的政策规定,制定出“择校收费的数量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是“取缔义务教育择校收费”的政策规定。不难发现,对于那些深谙人情逻辑、与名校或地方官员有着“家人关系”和“熟人关系”的家长而言,这是一个既可以保证他们的孩子进入名校学习,又可以让他们少花钱甚至是不花钱的“双重利好”政策。
以普遍主义教育政策为掩护,以服务于特殊人群、满足特殊个体或部门特殊利益的“新特殊主义”教育政策运行逻辑,正在将政府、市场和人情社会等多种力量持续不断地卷入到驳杂的利益纠葛和复杂的择校冲突中,这种彼此间的裹挟和卷入,造成了政府职能的错位、市场机制的扭曲和人情关系的异化。三者的交互作用,成为了引发和加剧义务教育择校矛盾的“长效机制”。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当代义务教育择校矛盾有着深厚的体制根源、驳杂的利益纠葛和复杂的引发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讲,变革这些体制基础、消解这些引发机制、理顺这些利益关系,已经超越了择校政策本身,甚至是超越了教育政策本身。但无论如何,继续冷静而深入地对引发当代中国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复杂因素进行分析和思考,对于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化解义务教育择校矛盾的政策措施具有前提性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