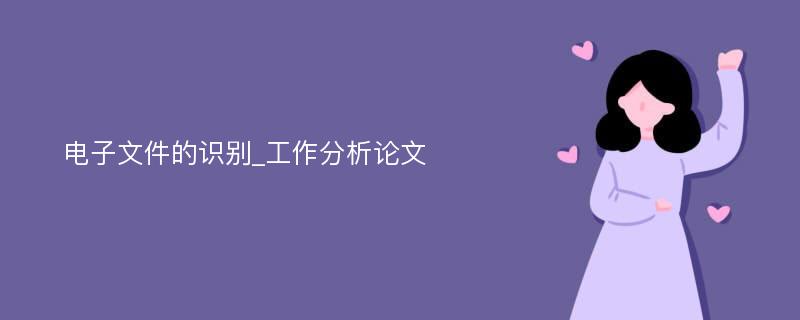
电子文件的鉴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鉴定论文,文件论文,电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美鉴定文件、处置文件的方法在电子文件时代已经行不通了,在接收进馆后再对文件进行鉴定,对电子文件来说是不适宜的。有人提出,鉴定电子文件时应该对事务职能及过程进行分析,而不是对个别文件、案卷或系列进行分析。有些国家对档案鉴定方法进行了改革,采用的方法是“职能鉴定法”,而非“内容鉴定法”,这引起了专家们的争论。加拿大档案工作者特瑞·库克(Terry Cook)对于这种新方法的理论和哲学背景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职能鉴定概念来自于德国联邦档案馆前任馆长、国际档案理事会前任主席布姆斯(Booms)教授的理论。布姆斯指出,社会而非历史学家或文件形成者决定了档案的价值,因而也决定了档案的重要性和档案的保管期限。这要求档案工作者鉴定文件时必须从社会角度进行考虑。布姆斯1991年提出,档案社会价值的鉴定最好不要通过研究社会基础活动、公众意见来直接进行,而应通过了解主要文件形成机构的职能来间接进行。档案工作者应当对文件形成部门的职能进行有效的分析,从而把文件需要和文件本身联系起来。
库克说,布姆斯的理论更坚定了加拿大国家档案馆1989年决定采用“新”的宏观鉴定战略的决心:以前档案鉴定重点着眼于文件的内容,着眼于反映公众意向、用户需求和历史研究趋势,现在着眼于更为广泛或“宏观”的文件的背景联系。这种联系通过文件形成机构的职能、计划、活动、办理情形表现出来。库克根据布姆斯的理论阐述了他的档案哲学思想和战略方法。
库克认为,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采用了组织职能研究模式,鉴定的重点在于文件的形成者,因为文件的形成者和与之联系的机构反映了组织间的综合职能和社会活动。这点类似布姆斯所说的从抽象的社会职能到具体的以来源为基础的组织职能的“直接转换理论”。库克提出,国家档案的鉴定应以背景联系为基础,以来源为中心,而不应以内容为基础,以历史文献工作者为中心。
德国马尔堡档案学院院长安杰莉卡·门内-哈里茨(Angelika Menne-Haritz)教授阐述了档案鉴定方法的发展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档案理论与来源原则研讨会上,她对战后德国鉴定方法及政治关系做了概述,并对以往挑选文件的标准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回顾。她对鉴定中的情报价值和证据价值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指出人们对于谢伦伯格提出的情报价值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她认为,职能鉴定理论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也不是非和电子文件鉴定联系在一起不可的理论。
德国档案工作者协会1957年的年会指出,由于行政管理职能的扩大,档案工作者不能再按老办法来鉴定文件,而应该根据职能的重要性来鉴定、保管文件。以此会议为标志,德国档案界形成了“按文件产生者划分级别原则”,鉴定已不再是只对文件本身进行鉴定。由于文件越来越多,档案工作者担心自己会成为纯粹的行政管理者,从事历史研究会成为他们的专业责任。因此,人们希望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决定文件形成机构的重要性,通过处置所有不怎么重要机构的文件来减少大量的纸质文件。门内-哈里茨认为,电子办公系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必担心会淹没在大量的纸质文件中,但如果我们不制定一个指导日常工作的基本原则,那么可留作鉴定的文件就微乎甚微了。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档案鉴定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制定适合鉴定电子文件的原则。电子文件管理经验使我们的认识得到了提高。开展鉴定工作,并不是为了减少文件的数量,而是为了使档案更有说服力,更利于研究。门内-哈里茨强调,档案工作者不要把文件鉴定局限在评价已经产生的文件上,而应该把重点放在确保重要的职能活动都用文件记录了下来。对于档案界存在的有关职能鉴定理论的争论,门内-哈里茨提出要“停止争论,开始行动”。
面对挑战,档案工作者必须积极参与文件的产生、分析和鉴定工作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沿用传统方法的档案工作者很不适应诸如此类的工作,要成为胜任职责的档案工作者就必须对形成文件的机构及其文件性质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库克一样,门内-哈里茨的结论是,职能鉴定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来源原则。她指出,人们通常认为来源原则是整理、著录文件的方法和手段,不是鉴定的基础,完全否定其对鉴定的作用。职能鉴定法是不同于以来源原则为基础的鉴定方法,但是二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件反映了其形成者履行职能的社会活动,而不同的文件产生者对社会变化的影响不同,因而对文件产生者职能的评价实际上也就是对相应的文件做出的评价。鉴定需要来源原则,但其外延必须大于归档原则、整理原则、研究原则,我们需要来源原则作为一种工具,以共同的职能来源为基础来分析、反映主要社会活动。文件只有经过著录和鉴定才能得以利用和理解。文件的情报价值决不会,也不可能会真实地反映或代表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门内-哈里茨认为,档案工作者只不过是掌握了某种理论或方法工具,能准确揭示信息的来龙去脉,因而可以使档案的证据作用得到发挥的专业人员。
档案工作者不应只重视简单的信息,而应重视信息的来龙去脉,这是档案工作者的职责。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其他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得不做这些工作。他们通常关心证据性,却在不经意间破坏了文件之间的背景联系。结果,历史的延续性会因证据的丢失而中断。
美国国家档案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第一代信息资料数据库,他们采用了传统的电子文件鉴定方法。
1990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将电子文件的鉴定与其它类型文件的鉴定区别开来,指定电子文件中心负责电子文件的鉴定。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同一单位电子文件的鉴定不同于其它类型文件的鉴定。相反,将电子文件鉴定工作交由电子文件中心来完成实际上是为了将鉴定工作交由高级专业人员来进行,其原因简单一点说,就是该中心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将电子文件鉴定工作交由电子文件中心来进行的作法拓宽了对所鉴定文件的背景联系信息的理解。这样做,在鉴定时不仅可以全面看到同一机构形成的有关文件以及产生文件的法律基础、组织及其职能等方面的背景联系信息,而且可以从机关之间和整个政府活动的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电子文件。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样做并没有贬低来源原则和尊重全宗原则的作用,需要明确的是,文件产生和保存的相关背景联系信息经常和越来越多地超越了组织机构的界限。这种超越可能来自于许多个方面,包括机构之间的合作,一个机关对另一个机关的专家、资源和能力的依赖,对特定的政府职能和共同责任领域的法律托管,以及某些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武装冲突等。
除了以职能为基础对电子文件进行鉴定的愿望之外,许多人提出,要在电子文件真正产生之前就开始对它进行鉴定。一位澳大利亚专家写道:“有价值的文件需要在这个阶段鉴定,以便使(计算机)系统中包含有管理和确保这些文件保存下来的程序。”
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格里格·奥谢依(Greg O' shea)认为,为了能够对档案文件进行保护,需要在文件生命周期开始之前进行干预,对于电子文件来说,干预的时机最好在系统开发阶段。这一要求使档案工作者在文件生命开始时或生命周期内不再是消极的观众。强调干预以确保有价值的电子文件不被丢失,不仅仅是一个鉴定文件的战略方法,而且也是整个档案工作的战略方法。与文件智能控制、保管、利用和保护相关的传统思想和作法都需要重新进行全面检讨。在信息时代我们能够继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也需要如此。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斯蒂芬·爱丽丝(Stephen Ellis)和斯蒂夫·斯塔基(Steve Stuckey)说,所有政府活动及与之相关的文件都必须进行鉴定。鉴定不是对文件本身进行评估,反映职能活动的文件保管系统是鉴定的间接对象。
荷兰国家档案馆对这种鉴定方法表示赞成,即根据文件在政府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来确定其保管期限并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在鉴定电子文件时首先要决定,对于其履行的职责和任务来说什么过程是至关重要的。然后,选择、记录和鉴定出来的信息就要努力去反映该职责和任务的实质。一般说来,再现机关重要职能所需要的信息就是需要保存的文件。
荷兰王国档案馆长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在有关电子文件的一个会议上也赞成按照职能鉴定文件的理论。在档案鉴定领域,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向职能鉴定方法的转移。如上所述,理想的状况是,档案馆从电子文件产生时就介入了,或者更早一点在信息系统策划和开发时就已经介入了。这就意味着鉴定的重点是政府机关的职能和活动,而不是电子文件本身。电子文件的性质和数量使得鉴定工作有必要向更高更抽象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不是文件的本身,而是产生文件的背景联系。
荷兰有一个鉴定和移交500千米文件的工程。霍夫曼的同事彼得·豪斯曼(Peter Horsman)在对这个工程进行总结时说,如果某项职能没有对一个活动(例如一个值得用文献记录的活动)产生影响,那么由它产生的文件就没有保存价值。文件的证据价值是由职能价值派生的。豪斯曼说,这个工程的鉴定方法是建立在对机构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文件的分析上。
澳大利亚档案馆接受了这个新观念,认为按照职能对文件进行鉴定是鉴定电子文件的非常重要的方法。格里格·奥谢依说,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档案工作者共同发展了这种理论,称之为“职能/逻辑鉴定法”。
澳大利亚移民和民族事务部采用了职能鉴定法,该部用于管理电子文件的计算机系统被分成职能和行政管理两个系统。文件鉴定被限定在该部的职能系统内。把职能作为挑选文件标准,并对文件进行著录,从而确定其保管期限。在以职能为标准的情况下,通过对系统和应用软件的改进,可以继续扩大系统收录电子文件的时间跨度。从广义上来看,职能比管理文件的系统更加稳定和可靠。从宏观角度看待机关和职能,可以通过机关的独特的核心职能对机关全部文件进行鉴定,而不必考虑其形式。
比尔曼·海德斯托姆(Beaman Hedstrom)的观点与其他职能鉴定论者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传统的考察和划分文件期限的方法已不适用了。在只有1-3%的文件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情况下,人们要对100%的文件进行考察和鉴定,费时费力,不够经济。人们应该只鉴别那些需要保存的少量文件,并且鉴定的重点应该放在对文件的鉴定上,而不要对机构活动的鉴定上。档案工作者不可能掌握组织结构和职能知识,而且过分细致地处置文件会给公众留下档案工作者只是廉价的文件收发者而不是管理者的印象。
澳大利亚企业档案工作者也参加到了讨论中来。他们提出,档案鉴定应该建立在职能和工作过程分析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个别文件、案卷、系列的基础上。现在电子系统可执行复杂的任务,且形成了比较复杂的文件,更细致地对文件进行处置是必要的。幸运的是,近年来系统设计中的技术工具可以运行更为精确的处置程序,它有助于我们保管那些有必要长期保存的文件。
对于这种争论,查尔斯·道拉斯(Charles Dollass)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目前国际档案界有关电子文件的鉴定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方法,另一种是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德国的理论家所说的“职能鉴定学派”。理论家的争论最后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按照职能对文件进行鉴定应侧重于文件本身还是文件内容。美国的方法选择了后者,其理由是档案馆保管文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之能够为研究者所用,在这种情况下,文件中的信息内容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美国的做法反映了美国档案界和史学界的历史联系,以及档案价值对于学者的潜在性。相反,以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为代表的所谓“职能鉴定学派”根据职能对档案进行鉴定,它采用从上到下的方法,先对政府重要职能进行鉴定,然后再对这些职能产生的文件的行政和文献联系进行分析,最后对最能满足证据要求的文件进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