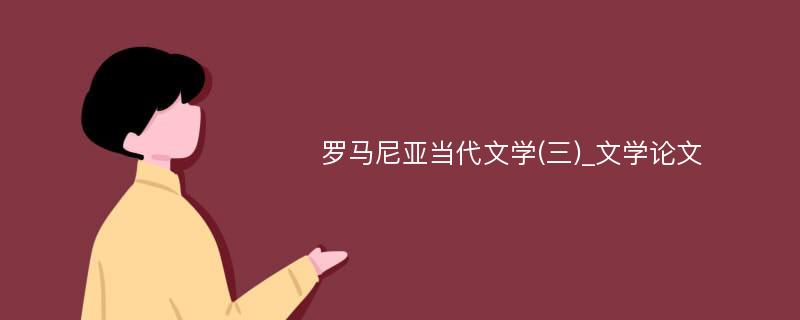
罗马尼亚当代文学(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尼亚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之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节 小说
作为一种体裁,罗马尼亚小说起步较晚。自19世纪中叶出现于文坛后,经过依昂·斯拉维支、依昂·克里昂格、依昂·卢卡·卡拉迦列等作家的努力,小说题材和表现手法得到丰富和完善,但就现代含义的小说而言,直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才逐步成熟起来。一些作家立足本国实际,吸取世界文学精髓,推出一批为国内外小说界瞩目的作品。利维乌·列布里亚努于1920年至1932年的短短12年中出版了《伊昂》、《绞刑森林》和《起义》三部长篇小说,用现实主义手法深刻揭示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农村生活和社会风貌,为罗马尼亚文学增添了瑰宝。切扎尔·彼特雷斯库一生致力勾勒20世纪罗马尼亚社会画卷,发表了《黑暗》等几十部作品。卡米尔·彼特雷斯库除从事戏剧活动外,在小说创作上也独树一帜,强调小说的“新结构”,发表了《爱情的最后一夜,战争的最初一夜》等优秀作品。霍尔坦西娅·帕帕达特—本杰斯库注重人物心理分析,推出《巴赫音乐会》等代表作,为罗马尼亚心理小说的发展揭开了序幕。乔治·克林内斯库既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又是优秀的小说家,巴尔扎克式的《欧蒂丽亚的秘密》是他享誉小说界的成名之作。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作品浩繁,自1904年首次发表作品起直至1961年辞世,始终在小说园地辛勤耕耘,为罗马尼亚文学留下了宝贵遗产。由于他们的努力,罗马尼亚小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20多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某些西方国家走过的近百年的路程。在作家基本队伍的构成、题材开拓的广度和深度、创作技巧的继承和借鉴、小说流派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价值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水平。可以说这一代作家为罗马尼亚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年8月23日后,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 文学也急剧被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这无论是对文学本身还是对作家队伍,都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和震撼。文学需要转轨,作家面临严峻的抉择和适应问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小说家,除利维乌·列布里亚努于1944年逝世外,均跨入了社会主义年代,大多继续从事写作。这批作家在法西斯猖獗的日子里,一直坚持民主进步立场,为反对黑暗势力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但这并不意味他们的文艺观和创作手法也符合新制度的需要。战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及相关文学在罗马尼亚根基不深,康斯坦丁·多布洛几亚努—盖利亚和亚历山德鲁·萨希亚是这方面的理论家和小说家,可他们的作品影响面相当窄,几乎被文学界所忽视。至于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这批作家来说更是陌生。且不说文学的党性、阶级性、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就是题材也有特定的范围,只限于战前地下斗争、“8·23”武装起义、民主改革、 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和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等。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作家们都得一切从头做起,以便顺应形势需要。首先文艺观念必须革命化,然后还得摸索能够表现新题材的创作手法。如何把艺术个性和政治标准完满结合起来,是每位老一代作家面临的课题。缺乏思想准备和缺乏生活体验是两大难点,再加上没有正确的文学批评加以引导,所以他们在这种探索和尝试中虽有成功之处,但更多的却是痛苦的教训。
就时间分野来讲,1944年8月至1947年底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 战前的文艺思潮和流派仍能有所表露。扬·马林·萨多维亚努发表了《布加勒斯特的世纪末》(1944),佩特鲁·杜米特鲁和马林·普雷达分别出版了《尤丽迪丝》(1947)和《大地相遇》(1948),但由于局势的动荡,这些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此时,以革命面目出现的极端倾向也开始抬头。这股潮流在理论上对马克思文艺观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在实际运用上则不问青红皂白,对革命胜利前的文学艺术成果一概否定,动辄加以罪名。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老一代小说家利维乌·列布里亚努、扬·佩特罗维奇、扬·布勒特斯库—沃依内什蒂等受到无端攻击,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被封存,不许同读者见面。当时把持文学阵地的大多是武断专横的新闻记者、末流作家和党的活动分子,他们从一开始就严重伤害了新生文学的健康发展。
摸索、适应阶段,亦可称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大致从1948年延续到1960年。在此期间,文学界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坚实传统,大批作家为形势所迫匆匆学习有关方面著作,往往不得深入消化即用以指导创作,造成了文学艺术政治化、创作手法模式化、现实生活图解化等一系列错误倾向,而当时的导向更是以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把文学创作引入误区。因而,这一阶段围绕反法西斯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规定题材创作的作品大多缺乏生命力,例如:扬·克卢格鲁的《我下令开枪》(1948)、《钢与面包》(1952),欧塞比乌·卡米拉尔的《雾》(1949 )、 《基础》(1951),扬·帕斯的《锁链》(四卷,1950—1954)等,出版后没过几年就被人们淡忘了。这类作品的失败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有些现象值得人们深思,诸如以政治代替艺术、创作脱离生活、套用外国模式、限定创作手法、划定文学禁区等等。尤其是有些新生事物未待沉积澄清,在深层情况和发展趋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就立即配合宣传进行创作,必然导致一些肤浅作品出笼,不能真实反映现实。尽管这一阶段小说创作存在严重弊病,但是几经磨练和探索,毕竟也产生了一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作品。其中有扎哈里亚·斯坦库的《赤足》(1948)、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的《马蹄铁尼古拉》(1952)、乔治·克林内斯库的《可怜的伊瓦尼德》(1953)、马林·普雷达的《莫洛米特一家》(第一卷,1955)、蒂图斯·波波维奇的《陌生人》(1955)、佩特鲁·杜米特鲁的《家庭纪事》(三卷,1956—1957)、卡米尔·彼特雷斯库的《一位杰出的人》(三卷,1953—1957)、埃米尔·加兰的《勃勒干大平原》(1954)、欧金·巴尔布的《坑》(1957)等。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创作同战前的小说传统接了轨,作家本人能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分析和对待他们各自熟悉的历史、农村、知识界或贫民区等各个方面的原始素材,从而使他们的艺术个性得以发挥。尤其是老一辈作家,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
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1880—1961)是老一辈中名望甚高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坚持进步立场,1937年右翼势力和亲法西斯刊物曾向他发起攻击,暴徒们在大街和广场上公开焚毁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同知识界许多名人一道,对法西斯战争持反对态度。1944年他的爱子战死疆场,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罗马尼亚全国解放后,他积极投身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历任大国民会议主席团副主席(1948 —1961)、作家协会主席(1949,1956)等重要职务。由于突出的文学成就和社会活动,曾获金质和平奖章和列宁奖金。他在罗马尼亚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1950、1955和1960年均为他组织过全国性的祝寿活动。1961年萨多维亚努逝世时,著名作家乔·博格扎在悼词中称他是“罗马尼亚文学的斯特凡大公”。的确, 他对现代文学的功绩不可磨灭, 在5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100多部作品,含历史题材、农村题材、 集镇题材、风光渔猎题材四大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是《安古察客店》、《斧头》、《吉德里兄弟》等。1944年前,萨多维亚努的创作风格已经定型,他的传统主义在小说界有广泛影响。他崇尚历史,崇尚大自然,对农、牧、渔、樵和小镇风情十分熟悉,对此他习惯用讲述故事的语调予以徐缓的静观描绘。在他的作品中,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他主张人类应该回归自然。因而萨多维亚努的人物经常是从属自然融于环境的,而不侧重性格的突出,人物只是整个构图的一小部分。他虽然也创作过《泥棚户》一类反映农民遭受奴役的小说,但感人之处仍是氛围。可是1944年后,新的文学必须有革命内容,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是创作的主旋律,在这类斗争和变革中,人应该占据首要地位。这些新的要求是萨多维亚努的创作风格所不能适应的。迫于需要,他必须重新学习,但要突然改变他自己所熟悉的创作题材、艺术风格乃至语言,并非一件易事。因而他1944年后的作品往往显得幼稚拘谨,情节的安排倾向模式化,从整体上看没有完全达到战前的艺术水平。
1946年他出访苏联,回国后出版游记《万花筒》。该书从机场、旅馆、街景等若干侧面记述了观感,赞颂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活。由于是走马观花,且接触的方面相当窄,有些段落只是为了赞扬而赞扬,难免显得十分勉强。1948年他发表《小帕乌纳村》,这是他在新的文艺导向指引下进行的初次创作尝试。小说讲述几个年轻人在分得村边土质低劣的田地后凑到一起商量,决定成立互助组。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很快这个互助组成了荒原中的一面旗帜。作者的意图是想通过这个故事突出农民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同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描绘河沼地区的特有风光。但是作品问世后,却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只写农民的自发行为,集体劳动组织中没有干部的干预,没有党的领导。1949年萨多维亚努发表长篇小说《米特里亚·珂珂尔》,故事一开始就从阶级角度对一户农民家庭的四个成员进行了剖析。一方是正直的父亲和二儿子杜米特鲁,绰号米特里亚·珂珂尔;另一方是生性贪婪一心想当富农婆的主妇和他们的长子磨坊主吉察。这母子俩和地主串通一气,对前来磨面的农民进行盘剥。双亲死后,兄长为了独占田产,把弟弟米特里亚送到地主家当长工。接下去,故事的发展脉络基本按照特定的模式予以安排。米特里亚在地主家里挨打受气做苦工,每餐吃的是发了霉的玉米糊,多次反抗都没成功。后来他被送上反苏战场,被俘,在俘虏营中受到教育,接触共产党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回国后参加武装起义,在驱逐德军的战斗中负了伤。接着是复员回乡,找到受尽折磨的恋人,结婚、生子,按照党的指示进行土地改革。由于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符合当时的文艺导向,所以出版后立即得到普遍赞扬,被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楷模。但是从多视角观察,故事对那一段历史的反映缺乏深度,有些情节概念化,政治说教多于艺术感染,平面式的人物显得呆滞。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完全失去了萨多维亚努所特有的艺术风格,所以若干年后就被批评界彻底否定了。此后,又有几部小说陆续问世。《花之诱惑》(1950)以社会主义运动为背景,通过渔民生活描写了一群出没芦苇荡的穷人和对现实不满的革命分子。这部小说是在《水的王国》(1928)的基础上,用新时代的观点改写而成的。《铁喙》(1951)讲的是杜米特拉克受富农指使,企图谋害进步农民的故事。《创业多瑙河》(1954)讲述前地下党员波波维奇工程师领导一批人在多瑙河谷创建国营农场的事。此外,这一期间他还创作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米瓦拉之歌》、富于寓言色彩的《东方幻想》、爱情故事《丽莎维塔》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萨多维亚努在不违背现实题材的情况下,逐步恢复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历史小说《马蹄铁尼古拉》(1952)。故事取材于16世纪下半叶伊昂大公在位时的摩尔多瓦公国。为了振兴趋于衰败的国家,伊昂大公严厉镇压了贪官污吏,动员人民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但是以叶列米亚·莫维拉为首的贵族却与外敌勾结,把他杀害了。伊昂大公的异父兄弟尼古拉(绰号马蹄铁,因他能用双手轻易折弯一块马蹄铁)和亚历山德鲁在人民的支持下,奋起为兄复仇。一次,他们避难老臣家中,兄弟俩同时爱上了他们的仇敌莫维拉的女儿,由此导致了爱情悲剧。后来,他们协同哥萨克人击败土耳其操纵的大公部队。胜利后,尼古拉下令处死叛徒莫维拉及其同伙,其中也有他的生身父亲佩特列·根日,但是他并不晓得往昔的实情。在那权力频繁更迭的年月里,尼古拉不久又被波兰人杀害了。这部小说的前身是《肖伊木家族》(1904),但它的文学价值却远远超出它的前身。浓重的历史色彩、独特的乡土气息、感人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使这部小说成为萨多维亚努最后一部十分成功的作品(获国家文学奖)。
卡米尔·彼特雷斯库(1894—1957)也是战前已经名扬文坛的老一代作家。他自幼失去双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双耳部分失聪,长期过着清贫生活。外界的严苛环境造就了他孤僻、顽强、进取的性格,尤其是对文学的专一精神,使他在小说、戏剧创作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解放后他立即投身革命,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创作和其他社会活动。为了表彰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1948年他被选为科学院院士,此后获一级劳动勋章和多种文学奖。战后,他除发表中篇小说《付出生命的人们》(1949)和描写知识分子问题的短篇小说集《象牙塔》(1950)外,占突出地位的是多卷本小说《一位杰出的人》(三卷,1953—1957),共2000多页,第3卷没有全部完成。这部小说以大量笔墨描写了1848 年革命领袖博尔切斯库的生平和活动,可贵的是在不失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他也用艺术手法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彼特雷斯库曾经提倡小说创作的自白体和日记体,严格要求原始素材的准确性。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他更是一丝不苟,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研究参阅了大量资料,创作过程中正确处理了艺术中的真实与杜撰的辩证关系,因而他得以用娴熟的笔调勾勒出19世纪中叶罗马尼亚的社会面貌。农村的黑暗与赤贫是促使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彼特雷斯库从社会、经济、民俗等多种角度探索了这一问题,写得相当透彻真实而且丰满。如果说瓦杜—勒乌村在他的笔下是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那么布加勒斯特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都市生活。在那里,冬季白雪皑皑,夏季人潮如流,秋季送来阵阵葡萄香。入夜,形形色色的市民聚在街边的芦棚下饮酒谈天,直至黎明。而那些巨贾显贵则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一场赌局可以持续几天几夜,赌资少则数千金币,多则动用家财地产,动荡的社会似乎同他们根本无关。主要历史人物的描绘都以资料为基础,每个形象都刻画得细腻入微,有血有肉,言谈举止跃然纸上。人物的服饰,甚至房屋、庭院、家具等微末细节无不渗透出历史的准确性。当然,受50年代文风的影响,他对部分贵族人物也采用了脸谱化的表现手法,把他们描写得形似恶魔。而小说中的俄国人,不管其政治倾向与历史功过,一律被视为救星和朋友。又如,有些革命者的演讲过于模式化简单化,这也是小说中的一处败笔。
解放初期的历史题材小说还应该包括扬·马林·萨多维亚努(1893—1964)的作品。这位知名的戏剧家兼诗人在小说园地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布加勒斯特的世纪末》(1944)是一篇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扬库出身卑微,可他雄心勃勃,不择手段搞垮了他的主人巴尔布男爵,一时间平步青云,身价百倍。而旧时代的贵族面对新兴资产者的严酷挑战,却一步步走向衰败。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得十分细腻,个性鲜明,尤其是心态得到充分透视。在19世纪末叶的时代氛围中,房舍、街景、室内装饰等都描写得恰到好处。《扬·中图》(1957)是《布加勒斯特的世纪末》的续篇,描述了扬库的孙子的成长过程和情感经历,故事跨越20世纪初、1907年农民大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工人运动等几个重要历史阶段。这部作品对社会变革的描写有些概念化,人物的心理透视也不如前者那样深厚。作者的原来设计还有第三部,即《扬·申图的成功》,以期形成三部曲,可惜没有完成。(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