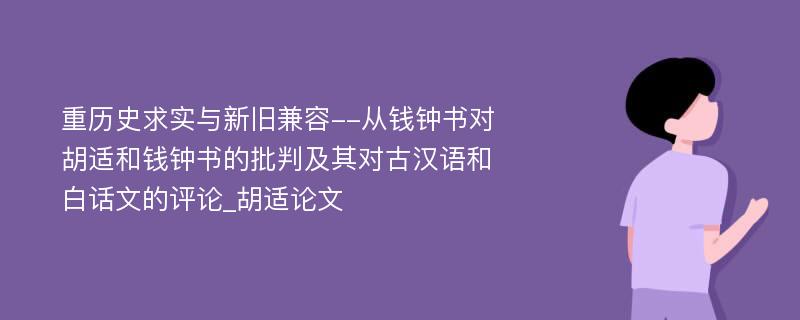
重史求实、新旧兼容——从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批评及对文言与白话的评说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文言论文,白话论文,求实论文,新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钟书在给同学好友郑朝宗的信中曾明确表示:“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①受此影响,把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在时间上打通古今,在地域上打通中西,在学科上打通文史哲各人文学科的“打通说”已成“钱学”研究者的共识。其实“打通”是钱钟书对自己治学方法、经验和心得的高度抽象概括,并不能代替他在研究具体问题时所坚持或采用的方法和原则。或许,打通中外古今及各个不同的学科,也只有钱钟书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师能够敢想敢做而且做得成打得通。本文结合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有关批评,来探讨钱钟书重史求实、新旧兼容这一具体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一
由于家学渊源,青少年时的钱钟书已经打下国学的牢固根基。上中学时就“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甚至开始为父辈学者的书作序②。交游问学于唐文治、钱穆、徐景铨等老派学者③,以旧体诗与当时的文坛名宿陈衍酬唱应和,并与其纵论天下文章之得失,遂成为学术上的忘年交。陈衍对他有“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志”之誉④。其父钱基博也公开称赞:“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学诚)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⑤如上种种记述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钱钟书当时就是一个远离新文学而沉湎于旧学的旧式学者,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除家学和传统旧学外,钱钟书因为接受了严格的新式学校教育和受域外文化的影响,无论在学术视野还是在理论、方法与创作上,都已经超越了父辈学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秦氏小学和东林小学期间他所接受的还是旧式的传统教育,那么自入桃坞中学后,他就开始接受严格的西式教育了。这不仅培养了他的外语能力,而且也为他接受西方的治学方法和思想观念奠定了基础⑥。此后他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更得以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西方学术思想。清华的华籍教师如王文显、吴宓、陈福田、叶公超等均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而外籍教授温德(R.Winter)、瑞恰慈(I.A.Richards)等均是西方声名显赫、能成一家之言的学者。他们的言传身教,使钱钟书获益匪浅。瑞恰慈是把西方现代新批评理论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教授的文学批评课程对钱钟书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钱钟书高度评价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认为“确是在英美批评界中一本破天荒的书”⑦。他还征引瑞恰慈的观点来解释“俗气”的本质:“批评家对于他们认为‘伤感主义’的作品,同声说‘俗’,因为‘伤感主义是对于一桩事物的过量的反应’(a response is sentimental if it is too great for the occasion)——这是瑞恰慈(I.A.Richards)先生的话,跟我们的理论不是一拍就合么?”⑧就是在清华就读期间,他发表了《一种哲学的纲要》、《休谟的哲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哲人或思想的文章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落日颂》两篇专门关注新文学的书评。可见钱钟书在与旧派学者交游酬唱的同时,眼睛也在关注着世界的文化思潮与新文学的发展动向。下面先从他对胡适的批评来分析他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二
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揭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此后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史》和《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等,或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发展建设进行规划,或为其存在的合理性寻求历史的根据并进行理论的辩护。可以说胡适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理论资源。钱钟书比胡适小十九岁,当胡适蜚声文坛时,他还是一个跟从伯父读书识字的少不更事的孩童。到他才华横溢在文坛崭露头角已经是“五四”落潮后的20世纪30年代,胡适早已是文坛名宿。年龄和志趣的差距使两人虽曾谋面但却没有直接的深入交往。据杨绛回忆,钱钟书在合众图书馆查书时遇到过胡适,两人就旧体诗的话题有过简短的交谈。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前到上海造访他留美时的老同学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钱氏夫妇应陈衡哲之邀参与了在任宅为胡适举办的“家常tea”。由此可知,钱氏夫妇、任氏夫妇和胡适曾有一次亲近而随意的聚谈。此后钱钟书还参加了一个送别胡适的宴会⑨。然而,对胡适而言,他所了解的钱钟书的才名是在作旧诗上,这和他反对旧诗提倡白话诗的志趣是相悖的,志趣的不投使他无法接受钱钟书成为他的忘年交。对钱钟书而言,以他恃才傲物的个性,自然也不会主动攀附胡适这一文化名宿。况且钱基博曾明确警告儿子:“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⑩此外,钱钟书对胡适的语言和文学革新的一些态度和做法是持保留意见的,曾点名或不点名地对胡适多有批评。
首先看钱钟书对胡适的作史方法和态度的批评。胡适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用从“死文学”到“活文学”的发展变革的逻辑来描述五十来年新旧文学过渡的短暂历史。他站在文学进化与革新的立场上,认为“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11)。他以否定和批评的态度把清末很有影响的诗文家王闿运和同光诗派一带而过,而高度赞赏写诗颇具散文化倾向的诗人金和。他说:“王闿运为一代诗人,生当这个时代,他的《湘绮楼诗集》卷一至卷六正当太平天国大乱的时代(1849—1864);我们从头读到尾,只看见无数《拟鲍明远》、《拟傅玄麻》、《拟王元长》、《拟曹子建》……一类的假古董;偶然发见一两首‘岁月犹多难,干戈罢远游’一类不痛不痒的诗;但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纪念这个惨痛时代的诗。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都是因为这些诗人大都是只会做模仿诗的,他们住的世界还是鲍明远、曹子建的世界,并不是洪秀全、杨秀清的世界;况且鲍明远、曹子建的诗体,若不经一番大解放,决不能用来描写洪秀全、杨秀清时代的惨劫。”(12)“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作诗如说话。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歌(如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作诗如说话’的趋势。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近代学宋诗的人,也都犯这个毛病。陈三立是近代宋诗的代表作者,但他的《散原精舍诗》里实在很少可以独立的诗。”(13)胡适在书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的两个诗人是金和与黄遵宪。他说:“这个时代之中,我只举了金和、黄遵宪两个诗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有点特别的个性,故与那一班模仿的诗人,雕琢的诗人,大不相同。”(14)并特别称赞金和“确可以算是代表时代的诗人”(15),“故他能在这五十年的诗界里占一个很高的地位”(16)。对此,钱钟书阐述了自己作史的立场与原则,并不点名地对胡适提出批评,他说:“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体制悬殊。一作者也,文学史载记其承邅(genetic)之显迹,以著位置之重轻(historical importance);文学批评阐扬其创辟之特长,以著艺术之优劣(aesthetic worth)。一主事实而一重鉴赏也。相辅而行,各有本位。重轻优劣之间,不相比例。掉鞅文坛,开宗立派,固不必由于操术之良;然或因其羌无真际,浪盗虚名,遂抹杀其影响之大,时习如斯,窃所未安。反之,小家别子,幺弦孤张,虽名字寂寥,而惬心悦目,尽有高出声华籍甚者之上;然姓字既黯淡而勿章,则所衣被之不广可知,作史者亦不得激于表微阐幽之一念,而轻重颠倒。试以眼前人论之: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者,湘绮一老,要为大宗,同光诗体,亦是大事,脱病其优孟衣冠,不如伏敌堂、秋蟪吟馆之‘集开诗世界’,而乃草草了之,虽或征文心之卓,终未见史识之通矣!”(17)这里钱钟书区别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各自的特点和职能。文学史重的是记述作者在文学发展史上对某时代的文风或文体的贡献及承先启后的作用,并以此来标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文学批评重的是揭示某些作家作品独特的风格特点,并评判其艺术的得失或优劣。文学史重的是历史事实而文学批评重的是鉴赏,两者各有各的职能,但又相互借鉴、相辅相成。史家要注意两者在文学史中所占的位置轻重的比例是不能等同的。对于那些曾蜚声文坛、开宗立派的大家,当然不必仅看其主张或方法有多么高妙;然而也不能因为现在看来他没有做出真正的贡献而浪盗虚名,就抹杀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反过来说,对那些名声并不显赫但却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的小家别子,读其作品惬心悦目,在某些方面确实高出了那些声名极大的大家。只是名声很少人知,给人们的影响自然也就不会广了。作史的人也不要执著于揭示隐幽精微事理并加以大书特书,以致轻重颠倒。文中的“湘绮一老”即王闿运,“伏敔堂”指的是江湜的《伏敔堂诗录》,“秋蟪吟馆”即指金和的《秋蟪吟馆诗钞》。因为江湜的诗不用典故,纯用白描,曾有人把他和郑珍、金和并称,所以钱钟书把他和金和并提。“集开诗世界”是指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诗中推崇杜甫开辟了诗歌的新领域所说的“子美集开诗世界”。钱钟书认为就晚清文学来说,王闿运和同光诗派都开宗立派,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以其模仿的毛病就认为他们不如江湜、金和的诗有革新开创的意义,于是在写史时不予重视,这种做法虽然或许表明为文者的用心和识见不同凡响,但终不能说是对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表述或评判。钱钟书坚持的是“信”,是一种重史求实的态度;胡适着眼的是“变”,追求的是“成一家之言”的独特性或创新性。两者难为轩轾。
再看钱钟书对胡适革新文学的某些理论、做法及学术上的疏漏所进行的批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把“不用典”标为改革文学的八项主张之一。虽然钱钟书也反对那种“无一字无来处”的“典癖”,认为那样会使作品叫人读起来“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18),但他对胡适明确提出“不用典”的主张是持保留意见的,他说:“词头,套语,或故典,无论它们本身是如何陈腐丑恶,在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的性质跟一切比喻和象征相同,都是根据着类比推理(Analogy)来的,尤其是故典,所谓‘古事比’。假使我们从原则上反对用代词,推而广之,我们须把大半的文学作品,不,甚至把有人认为全部的文学作品一笔勾消了。”(19)在论骈文的利弊时,他指出用典的实质和作用:“骈体文两大患:一者隶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骈语,两语当一语,叠屋堆床。然而不可因噎废食,止儿之啼而土塞其口也。隶事运典,实即‘婉曲语’(periphrasis)之一种,吾国作者于兹擅胜,规模宏远,花样繁多。骈文之外,诗词亦尚。用意无他,曰不‘直说破’(nommer un objet),俾耐寻味而已……末流虽滥施乖方,本旨固未可全非焉。”(20)胡适为白话文学寻找理论根据写了一本《白话文学史》。他站在平民主义文学的立场上,认为古典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作品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写成的,所以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对此钱钟书在讲旧传统和新风气的代兴时说:“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这种事后追认先驱(préfiguration rétroactive)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21)此外,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醒世姻缘传》,胡适为此写了三万余字的考订文章——《〈醒世姻缘传〉考证》,考证出其书的作者西周生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谈林纾的叙述和描写的技巧时认为白话作品完全可能具备“古文家义法”。引林纾同时人李葆恂《义州李氏丛刊》里的《旧学盦笔记》记有关《儒林外史》的笔法俱从太史公《封禅书》得来。钱钟书在注释中说:“李氏对《儒林外史》还有保留:‘《醒世姻缘》可为快书第一,每一下笔,辄数十行,有长江大河、浑灏流转之观……国朝小说惟《儒林外史》堪与匹敌,而沉郁痛快处似尚不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年二月十六日:‘阅小说演义名《醒世姻缘》者……老成细密,亦此道中之近理者’……这几个例足够表明:晚清有名的文人学士急不可待,没等候白话文学提倡者打鼓吹号,宣告那部书的‘发现’,而早觉察它在中国小说里的地位了。”(22)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认为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举例说“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23)。这里胡适是引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句子。原文是“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文中的“媰”,指妇人妊身。胡适对此字理解有误,钱钟书批评说:“林纾原句虽然不是好翻译,还不失为雅炼的古文。‘媰’字古色烂斑,不易认识,无怪胡适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轻藐地说:‘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大约他以为‘珠’是‘珠胎暗结’的简省,错了一个字,句子的确就此不通;他又硬生生在‘女’字前添了‘其’字,于是紧跟‘其女’的‘其母’变成了祖母或外祖母,那个私门子竟是三世同堂了。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24)
以上是钱钟书对胡适革新文学的某些理论、做法及学术上的疏漏所进行的批评。这些就某些理论或做法上的批评表明了两人不同的个性和志趣,而指出个别学术上的疏漏对胡适来说当然也是白璧微瑕。钱钟书这种略带嘲讽的行文方式,表明了其喜欢臧否人物的个性。
三
如果说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揭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的话,那么周作人就是以《人的文学》一文确立了“五四”启蒙文学的性质与走向,成了“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家之一。钱钟书比周作人小二十五岁。就所见的资料来看,二人未曾谋面。钱钟书对周作人有公开的批评,未发现周作人对这些批评有所回应。
周作人于1932年3—4月间在辅仁大学作了系列讲演,后依据讲演的记录稿整理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该书旨在用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寻找历史依据。其核心观点就是:言志派与载道派两种文学潮流的起伏消长,构成了全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曲线;而“五四”新文学的源流则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公安派”(25)。他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明代公安派文学潮流作了比较,结论是两次运动的“趋向是相同”的;认为清代八股文和桐城派文学都属于“遵命文学”过了头,于是引起“不遵命的革命文学”,也就是新文学运动。明末的文学是新文学的“来源”,而清代八股文学、桐城派古文所激起的“反动”,则成了新文学发生的“原因”。他特别比较了新文学的主张与明末公安派的类同点,认为两者都属“言志”的文学,或者叫“即兴的文学”;认为胡适的“八不主义”和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及“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其精神趋向是一致的。钱钟书认为周作人此书存在根本概念上的错误:“周先生根据‘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来分派,不无可以斟酌的地方,并且包含着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一个很大的问题。‘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有如周先生和其他批评家所想者。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诗’是‘诗’,‘文’是‘文’,分茅设蕝,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文以载道’的‘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的近世所谓‘文学’;而‘道’字无论依照《文心雕龙·原道》篇作为自然的现象解释,或依照唐宋以来的习惯而释为抽象的‘理’,‘道’这个东西,是有客观的存在的;而‘诗’呢,便不同了。诗本来是‘古文’之余事,品类较低,目的仅在乎发表主观的感情——‘言志’,没有‘文’那样大的使命。所以我们对于客观的‘道’之能‘载’,而对于主观的感情便能‘诗者持也’地把它‘持’起来。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片面的真理;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悖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与他们平时的‘文境’决然不同,就由于这个道理。”(26)钱钟书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有其自身的文体特点及渊源流变,和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概念是不同的两套体系,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周作人受西方文艺学概念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术语的含义分辨不清,和西方文艺理论概念强行比附。钱钟书强调“作史者断不可执西方文学之门类,卤莽灭制,强为比附。西方所谓 poetry非即吾国之诗;所谓drama,非即吾国之曲;所谓prose,非即吾国之文;苟本诸《揅经室三集·文言说》、《揅经室续集·文韵说》之义,则吾国昔者之所谓文,正西方之verse耳。文学随国风民俗而殊,须各还其本来面目,削足适履,以求统定于一尊,斯无谓矣”(27)。中国传统文学在区分文章类别特征的基础上约定俗成地形成一套文类体式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讲文章“体制”和“品类”。所谓“体制”,传统文论中也称“体格”或“大要”,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文体”或“体裁”。各种文体都各自有其严格的规则或体式,形成分门别类的文学样式。各种文体的规则或体式不能混用或杂糅,否则就叫“失体”。“得体”与“失体”是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所谓“得体”,就是诗、文、词、戏曲、小说等体裁严格区分,不能相杂。钱钟书举例说:“譬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皆谓《眉庵集》中七律联语大似《浣溪沙》词,又如章炳麟《与人论文书》谓严复文词虽饬,气体比于制举。”(28)也就是说明代杨基《眉庵集》中的律诗写得像《浣溪沙》词,严复文词虽然整齐,但风格体式上有科举考试的策问应答之气,这在王世贞、朱彝尊和章太炎等人看来都是“失体”。如果体裁分得如此细致明确,那么为什么又有“以文为诗”的说法呢?对此,钱钟书认为:“不知标举‘以文为诗’,正是严于辨体之证;惟其辨别文体与诗体,故曰‘以文为诗’,借曰不然,则‘为诗’径‘为诗’耳,何必曰‘以文’耶?且‘以文为诗’,乃刊落浮藻,尽归质言之谓。”(29)按钱钟书的看法,正是由于细别文体与诗体,所以才有“以文为诗”的提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诗”就径直“为诗”,又何必说“以文为诗”呢?这就是“体制”,是属于形式的范畴。那么“品类”又是指的什么呢?“品类”则指各种体裁尊卑的排定和题材内容的分等,是从作品体裁形式、题材内容以及体裁形式是否完美即“得体”或“失体”等角度来评判作品的尊卑高下的一套规则或标准,既关涉到内容又牵涉到形式。一般说来,“文(古文或散文)以载道”,“文”的地位最高;“诗以言志”,诗的地位次于“文”;“词”号“诗余”,又次于“诗”;“戏曲”、“小说”则更下一层。并且同一种体裁,也因其题材和内容而分出尊卑。各种体裁相杂即叫“失体”,词写得像诗,就是“失体”,并不能因诗的品位高于词而词写得像诗就变得“尊”起来。钱钟书举例说:“《苕溪渔隐丛话》记易安居士谓词别是一家,晏殊、欧阳修、苏轼词,皆句读不茸之诗,未为得词之体矣。又譬之‘文以载道’之说,桐城派之所崇信。本此以言,则注疏所以阐发经诂之指归,语录所以控索理道之窍眇,二者之品类,胥视‘古文’为尊……姚鼐《述痷文钞序》顾谓‘古文’不可有注疏语录之气,亦知文各有体,不能相杂,分之双美,合之两伤;苟欲行兼并之实,则童牛角马,非此非彼,所兼并者之品类虽尊,亦终为伪体而已。”(30)这里李清照强调词的文体特点,认为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词都是句读不整齐的诗而不能算是词;姚鼐提示“古文”不能因为考虑“文以载道”而写得像注疏语录,均是强调文体特点即不能“失体”。就“品类”的尊卑,钱钟书举例说:“一体之中,亦分品焉;同一传也,老子、韩非,则为正史,其品尊,毛颖,虬髯客则为小说,其品卑;同一《无题》诗也,伤时感事,意内言外,香草美人,骚客之寓言,之子夭桃,风人之托兴,则尊之为诗史,以为有风骚之遗意;苟缘情绮靡,结念芳华,意尽言中,羌无寄托,则虽《金荃》丽制,玉溪复生,众且以庾词侧体鄙之,法秀泥犁之诃,端为若人矣!此《疑雨集》所以不见齿于历来谭艺者,吴乔《围炉诗话》所以取韩偓诗比附于时事,而‘爱西昆好’者所以纷纷刺取史实,为作‘郑笺’也。”(31)就是说,同一体裁其品类的尊卑又因题材不同而不同。如同一传记体裁,来自正史的老子、韩非则尊,来自传奇小说的虚构的毛颖,虬髯客则卑;同一诗体,其内容写国事民生的则尊,写缠绵悱恻的男女私情的则卑。倘若只是绮靡艳词,那么就是温庭筠的《金荃》丽制(32),李商隐复生(33),人们也会因为是堆积词藻、品格低下的庾词侧体而鄙夷。法秀禅师所怒斥的下地狱的,正是这些人啊(34)!历来谭艺者不屑于提起王彦泓的艳诗《疑雨集》,吴乔《围炉诗话》拿韩偓的诗比附于时事,喜欢西昆体诗的人纷纷引用史实,为西昆体诗作笺注,这就是个中原因。
传统的文艺理论,论文的就仅谈文,说诗的就只论诗,基本上没有把各种文体沟通综合产生像西方的“文学”概念。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局限,然而也是它的特点。自古以来,作者本着这样的特点而创作,论者本着这样的特点而欣赏或批评:“昔之论者以为诗文体类既异,职志遂尔不同,或以‘载道’,或以‘言志’;‘文’之一字,多指‘散文’、‘古文’而言,断不可以‘文学’诂之。是以‘文以载道’与‘诗以言志’,苟以近世‘文学’之谊说之,两言抵牾不相容,而先民有作,则并行而不悖焉。”(35)钱钟书在与西方文论比较中进一步揭示古代文论的文体特点,并批评近代一些人对中西文学概念强为比附而造成的认识上的混乱。
多年以后,钱钟书又旧话重提,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用浅白易懂的语言和一系列形象生动的比喻,进一步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个别文体的职能,并非概括‘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说不出的‘志’。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于是那两句老话仿佛‘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斥的命题了。”(36)我们把钱钟书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论述放到一起,便于读者比较赏析,从中也可以领略其早年“凌云健笔”、晚年老而更成的文章风格。当他晚年看到一些对中外文学传统都一知半解的人在大谈“比较文学”时,就不无讽刺地想起小学里的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37)
四
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这两个“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的发起人或奠基者多有批评,又喜作旧体诗且与旧派学人交游密切,那么他是不是沉湎于旧学而对新文学和白话文有成见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其实他是古今贯通,新旧兼容的。无论新文学、旧文学或文言文、白话文,他都以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来分析其优劣得失,而不怀门户之见采取绝对肯定或否定的过激态度。他的这种治学原则与态度在他发表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与张君晓峰书》中表现得尤为清楚。该文主旨就是讨论文言与白话的优劣的。他认为:“苟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骖驔比美,正未容轩轾。”(38)文章从阅读欣赏、文化史及应用的角度来考量文言与白话的优劣。针对有人从阅读欣赏的角度认为白话比文言容易理解并否定文言使用典故的情况,钱钟书说:“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听途说之资。往往钩深索隐,难有倍于文言者,譬之谈者力非文言文之用典故,弟以为在原则上典故无可非议,盖与一切比喻象征性质相同,皆根据类比推理(Analogy)来。然旧日之典故(白话文学中亦有用典者,此指大概),尚有一定之坐标系,以比现代中西诗人所用象征之茫昧惚恍,难于捉摸,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39)所以“难”不是文言的根本特点,“易”也不是白话的本质特征。因此“以难易判优劣者,惰夫懦夫因陋苟安之见耳;彼何知文艺之事政须因难见巧乎?”(40)就文化史的角度来考量,钱钟书认为:“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41)针对有人以文言文简洁而判定文言优于白话的情况,钱钟书引《养一斋诗话》来批评说:“文章各有境界,宜繁而繁,宜简而简,推简者为工,则减字法成不刊典。”(42)针对有人认为不读文言,则不能了解和体会传统文化的观点,钱钟书批评说:“老师宿儒皓首穷经,亦往往记诵而已,于先哲之精神命脉,全然未窥。彼以版本考订为文学哲学者,亦何尝不以能读古书自诩于人耶?”(43)他以辩证的观点认为文言、白话可以通过互动互补而达于融合之境,他说:“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Elasticity)不少。而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44)这不但是钱钟书对文言与白话的态度,也是他对古典文学与新文学的态度。正是这种客观包容而又辩证的治学态度,使他能文言、白话皆擅,不但能写出《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学术巨著,而且能以“融文于白、化西入中”的白话文体创作出《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这样独具风格的新文学作品。
以上就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批评及对文言与白话的评说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胡适和周作人当时都以批判旧文学并创建和发展新文学为己任,其立论或观点带有强烈的改革求变的“五四”时代特征,而钱钟书则是在“五四”落潮之后,站在纯学术的立场,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出发评判问题,表现出重史求实和新旧兼容的治学特色。
注释:
①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②(37)《杨绛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147页,第141页。
③参见钱钟韩《我所了解的唐文治先生》(《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3页),钱钟书《哭管略》七律二首(载《国风》半月刊1934年7月第5卷第1期)。
④钱钟书:《石语》,《钱钟书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78—485页。
⑤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载《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3月第4卷第6期。
⑥桃坞中学是一所由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校长由外国传教士担当。主要课程都用英语授课。据陈次园回忆:“这里,不会讲英语的最好免开尊口。听吧,连早操、军训、游戏、吵架……都用英语;中国地理教科书却用美国人诺顿著的原版西书;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美国校长梅乃魁要亲执教鞭正它几个星期;初一年级第一次小考后,凡英语不及格的,一律退到补习班去。”(陈次园《一些回忆与思索》,载《昆山文史》1990年第9辑)。
⑦钱钟书:《美的生理学》,载《新月月刊》1932年12月第4卷第5期。
⑧钱钟书:《论俗气》,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11月4日。
⑨杨绛:《怀念陈衡哲》,《杨绛作品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223页。
⑩钱基博:《谕儿钟书札两通》,载《光华半月刊》1932年11月第1卷第4期。
(11)(12)(13)(14)(15)(16)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集第184页,第188页,第207页,第207页,第190页,第192页。
(17)(27)(28)(29)(30)(31)(35)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载《国风》半月刊1933年10月第3卷第8期。
(18)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19)钱钟书:《论不隔》,载《学文》1934年7月第1卷第3期。
(20)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74页。
(21)(22)(24)(36)《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190页,第292—293页,第299—300页,第191—192页。
(2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2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33—52页。
(26)钱钟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载《新月月刊》1932年11月第4卷第4期。
(32)《金荃》即《金荃集》,温庭筠词集,今佚。
(33)玉溪,永乐水名,唐李商隐尝隐居之,号玉溪生。
(34)泥犁之诃:《扪虱新话》曰:黄鲁直初好作艳歌小词,道人法秀谓其以笔墨诲淫,于我法中,当坠泥犁之狱。鲁直自是不作。佛书泥梨耶,无喜乐也。泥梨迦,无去处也。两者皆地狱名。或省耶迦字,只作泥梨,一作犁。又阿鼻,无间也,亦地狱名。
(38)(39)(40)(41)(42)(43)(44)钱钟书:《与张君晓峰书》,载《国风》1934年7月第5卷第1期。
标签:胡适论文; 钱钟书论文; 文学论文; 古文论文; 周作人论文; 文学改良刍议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儒林外史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白话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