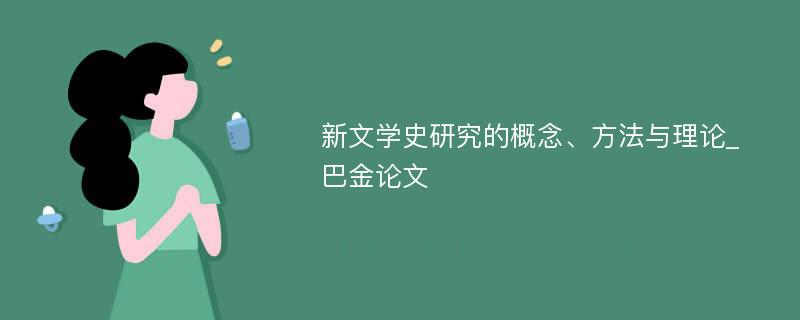
新文学史研究的观念、方法和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史研究论文,观念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3-0134-05
百年来,新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新文学史编撰方面成果丰硕,极大促进了学科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年);程光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和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等。①回首百年新文学,如何在已有基础上,从观念、理论和方法上寻求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研究空间,是当前摆在新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一、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一直较少人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儒教“不具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1]性质比较特殊。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我们也有自己独特的宗教问题。其中,任继愈先生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有不同于欧洲的独特的专横独断宗教——儒教,中国的儒教经常以反宗教的姿态出现,它猛烈地抨击佛教和道教,致使很多人误认为中国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黑暗的神学统治时期,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2]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在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时曾触及到儒教问题。当时孔教会提出要把孔教定为国教,遭到以陈独秀、蔡元培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坚决反对。陈独秀认为“国教说”既缺少学理上的依据,又践踏了信仰自由的原则,只不过是为了给袁世凯的帝制复辟造势,因此,荒谬至极。[3]蔡元培指出,尽管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或孔子的学说成了儒教,但孔子本人不是宗教家,而且随着科学的发达,宗教必将消亡,因此应该以美育代宗教。
在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下,“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具有明显的反宗教意向,胡适说:“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4]但是,科学与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追求的是“真”,强调的是“疑”,怀疑与批判是科学发展的永恒动力,而宗教追求的是“善”,强调的是“信”,主张“因信得救”,因此,从根本上讲,科学与宗教是很难互相取代的。其次,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以揭示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为宗旨,科学本身并不含有价值意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将科学视为超越了具体知识领域的无可置疑的信仰对象,坚信人类只要有了科学,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这种“独尊科学”的态度与“独尊儒术”一样带有准宗教的色彩。“五四”时期,有很多知识分子一面呼唤科学与民主,一面又独断地相信自己把握了超绝真理,所谓“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5]这种褊狭的做法,与允许怀疑、可以讨论、强调宽容、尊重理性的科学品质相去甚远,它打的是科学的旗号,显示的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气”。[6]正如罗素在分析近代学者与中世纪学者之不同的时候所指出,科学要求理性裁断,“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信念,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7]
“五四”时期的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地集中在政治、文化、道德、封建迷信层面,未能充分注意到儒教的准宗教特质,但“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却会因为对生活在传统文化阴影下的国民性批判而触动儒教这根神经,无论是鲁迅小说对“礼教吃人”主题的挖掘、曹禺话剧对专制家长的批判、巴金小说对现代孝子的双面人格的揭示、还是周作人散文对“三纲”伦理的解构等,都让人们看到儒教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和精神桎梏是如何的深远和沉重。
以鲁迅为例,“礼教吃人”的主题之所以在创作中表现得十分深刻和沉痛,正因为他写出了礼教背后的宗教力量,绝非一般作家所可企及。上世纪40年代,梁漱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之路。”[8]作为宗教的代用品,礼教在传统中国一直享有神圣、绝对的崇高地位,它一方面给信奉者以终极的精神安慰和圣洁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使那些违背礼教律令的人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不得喘息。祥林嫂就是这样的典型。抢亲时候她拼命抗争,脑袋都被打破了,但内心深处认同的还是社会主流观念和偏见,还把它作为绝对价值,所以一旦不能遵从,就有很深的罪恶感。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但是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礼教罪感却可以使原本无罪的人在沉重的“心罚”中走向死亡,而且得不到任何同情和怜悯。这是鲁迅继《狂人日记》对“吃人的老谱”的揭露后,再一次对“吃人”文化的深度发掘,其意义绝不在《狂人日记》之下。
无独有偶,《雷雨》中周萍自杀亦与礼教罪感密切相关。蘩漪不了解周萍的苦衷和心结,一心想赶走四凤,她没有想到,即使没有四凤,周萍也很难维持与她的关系,周萍离开她绝非见异思迁,因此她越是不断向他提起他们的过去,企图唤起他的温情,周萍就越恐惧,越跑得快。周萍的痛苦在于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与父亲好不好没有关系,而自己的乱伦行为恰恰违背了这一绝对的道德律令。如果不是这种带宗教色彩的罪感,他完全有可能像父亲周朴园一样在伪善、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度过一生。周朴园比他坏得多,但无论是30年前包修江堤时故意淹死2200个小工并从每个小工身上骗取300块黑心钱,还是大年三十晚上为了赶娶门当户对的小姐导致刚生下孩子才三天的侍萍离开周家跳河而死等等,这些罪恶都没有和礼教的神圣价值挂钩,所以他还是场面上人物,还能道貌岸然教训人。
对于生活在传统阴影里的中国人来说,礼教罪感就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尽管在新文学史上除鲁迅、周作人外,很多作家并未在意识层面意识到儒教问题,但是,他们的写作却让世人看到,对儒教的深刻批判和解构,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能够产生经久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儒教的角度探讨新文学史,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作家的创作和思想,从而更深入地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和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亲近宗教的作家虽然很多,但真正皈依或信仰某一宗教的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作家都声称是无神论者,对于这些作家,儒教的潜在影响和精神束缚比有形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更大。夏志清曾尖锐地提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9]问题,引起学界广泛争议。笔者认为,倘不抓住儒教问题,泛泛而谈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得失关系,很难对转型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宗教性这一敏感而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做出深入、有价值的判断。
二、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
就新文学史研究而言,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研究也是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研究领域。考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晚年大都不在现代文学时段里,研究现代文学的认为,他们的晚年写作属于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的又认为他们是现代作家,因此,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如周作人、郭沫若、老舍、巴金、冰心、梁实秋、苏雪林等)解放后仍在创作,但是他们的晚年写作却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盲区。以上世纪80—90年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为例,无论是周作人、冰心、郭沫若,还是曹禺、丁玲、沈从文等,传记的重点几乎都放在解放前,头重脚轻的现象十分普遍。相对而言,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研究中,研究鲁迅的成果比较多,如199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彬彬的《鲁迅:晚年情怀》和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林贤治的《鲁迅最后的十年》等就是较早从事现代作家晚年研究的成果,而这显然与鲁迅主要生活在现代文学这个时段里分不开。另一方面,有些作家虽然活跃在当代文坛,但其创作却不仅仅属于当代文学,比如杨绛,她比张爱玲大10岁,上世纪40年代即以话剧创作称誉文坛,但除了研究中国现代话剧的学者,很少人把她视为现代作家,正如人们提到张爱玲时总觉得她是现代作家一样;与张同年出生的汪曾祺,情况也类似。
近年来,现代作家晚年写作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老舍的自杀之谜、曹禺的苦闷以及冰心、巴金、孙犁、杨绛、汪曾祺等老作家的散文等,但除了孙犁、曹禺等少数个案外,绝大多数研究不是从晚年写作的角度切入的,也没有明确的“晚年研究”意识。2005年前后出版的《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丁玲的最后37年》、《沈从文的最后40年》、《郭沫若的最后29年》、《郭沫若的晚年岁月》、《晚年孙犁研究》等著作,使这一现象有所改观。现代作家的亲人、友人、学生的回忆资料的陆续出版,如韦韬与陈小曼的《父亲茅盾的晚年》、梁秉堃的《老师曹禺的后半生》、傅光明与郑实采写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陈明的《我与丁玲五十年》、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等,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现代作家的晚年生活提供了更充分的材料。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王富仁教授文章《重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晚年的研究》引起学术界对中国现代作家晚年研究的重视和关注,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个案研究多,宏观整体的研究少;普及性传记读物多,有深度的学术专著少;单部的晚年作品研究多,比如巴金的《随想录》研究、老舍的《茶馆》研究,但把晚年写作纳入作家一生的整体创作中进行透视的少;另外,对新整理、出版的现代作家的晚年作品,如周作人晚年翻译的古希腊及日本文学作品、张爱玲晚年小说《小团圆》以及遗稿《重访边城》等研究不够,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不多。
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研究是新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式成立的时候,除了鲁迅、朱自清等少数作家已经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程,或像徐志摩、闻一多、郁达夫、梁遇春这样英年早逝者外,绝大多数作家还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己的文学活动,因此,从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全貌的角度来说,忽视他们的晚年写作是不科学的。其次,晚年是作家创作生命的最后阶段,深入研究晚年写作,有助于揭示出作家早期创作中一些潜在的变量或隐而未现的危机和局限。以巴金为例,解放前,巴金无情地批判觉新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不是“文革”,他绝对不会相信自己也会信神拜神,成为无神论时代典型的“宗教人”。在写作《随想录》的时候,巴金对自己分析得越深入,就越是惊讶原来自己身上也有觉新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1981年在谈《寒夜》和《激流》时,他写到:
“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自己。”[10]“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11]
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苟活麻木等确实是“文革”时期巴金与觉新十分相似的地方。但巴金是旧制度的坚决批判者和毫不妥协的战斗者,觉新是旧礼教的殉葬品,巴金爱的是国,觉新爱的是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怎么会有如此神似的思想和人格表现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20世纪中国,对绝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来说,国就是家的放大,忠就是孝的延伸,巴金爱国正像觉新爱家,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时代,一个是封建时代的孝子,一个是新社会的忠臣,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都与儒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前者在明处,后者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而已。“文革”使巴金发现束缚觉新心灵的儒教伦理也钳制着自己的思想,这使我们对巴金早期创作的贡献和局限有了新的审视眼光。
研究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还可以收获在普通的文学史研究中不容易发现的很多启示。有的作家在晚年迎来了新的创作高峰,如冰心、巴金、孙犁、杨绛等,但也有的晚年笔耕不辍,虽作品多却影响不大,奠定他们文学地位的仍然是早年的创作实绩,如郭沫若、茅盾、丁玲、杨沫、刘白羽等,他们逐渐被人疏远,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同时,如何看待中国现代作家解放后的创作,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主要以回忆录、散文、旧体诗、读书笔记、翻译著作或学术研究等文体为主,如孙犁就认为,作家晚年不宜写小说,散文是最适合老年的文体,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继续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说张爱玲的晚年杰作《小团圆》技巧成熟、思想深刻,令人刮目相看。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写于1987年,当时76岁,但宝刀不老,笔力温婉遒劲,意蕴深长,是当代文坛的重要收获,当然从总体上看,现代作家晚年写得最多最好最有韵味的还是散文。
在某种意义上,晚年写作,也是人生的终端写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无论是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周作人的“寿则多辱”、巴金的“忏悔”、还是老舍的天问“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几乎都可以视为现代作家留给后人的文学遗嘱,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现代作家的心灵密室,甚至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地使被传统的研究模式所遮蔽的现代作家更生动、更立体地浮现出来,因此,就新文学研究而言,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频繁的政治运动、不公正的命运、日渐衰退的生命力以及难言的个人隐痛等,使很多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面临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生死的大限也使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有时候更敢讲真话,无论是冰心晚年“有些烫手”的散文,杨绛走到人生边上的“鬼神质疑”,还是韦君宜晚年的“思痛录”等,不仅使他们个人创作更上一层楼,更使我们看到真正的作家可以被打倒,却不会被打败。
“晚年写作”研究有它的难点,首先是如何界定晚年的概念。国际卫生组织认定晚年指的是65岁以上的人。但有些现代作家在65岁以前已经离开人世,比如鲁迅、穆旦、赵树理等,因此,“晚年写作”主要是指现代作家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写作。其次,“晚年创作”不等于“后期创作”。晚年主要是指一个作家正常地走完人生道路的人生最后岁月,对于那些英年早逝的作家,比如徐志摩1931年由于飞机失事离开人间,终年34岁;庐隐1934年难产而死,终年36岁;郁达夫1945年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等,他们的后期创作就不属于“晚年写作”。最后,当代作家即使已到晚年,因为还没有走完人生全程,他们的晚年写作还在进行中(如王蒙),是否要纳入晚年写作的研究视野也值得商榷。
三、新文学经典的现代解读
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近年来也被纳入高校通识课的课程建设。但实际教学情况不容乐观。首先,很多学生对为什么必须学习人文经典并不是很清楚,只凭实用主义的立场认为什么有用就学什么,而文学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在很多同学心目中,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不如古代文学如唐诗宋词优美,又不如外国文学名著深刻,加上中学有些老师对现代文学作品食而不化的讲解,很多同学对中国现代作家有一种缺少了解的偏见和隔膜,读不懂,也不感兴趣,少数极端的甚至认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已经过时了。其次,很多老师对作为通识课的经典导读与作为专业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区别不清,把作为通识课的经典导读上成了普及版的专业课,既没有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也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普及和传承。
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新文学史研究中加强现代文学经典的人文价值研究。虽然什么是经典,学术界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但经典至少是能经得住时间考验、能够常读常新魅力无穷的作品则没有疑义。用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的话说:“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在新文学史上,凡是经得起现代阐释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公认的经典作品,比如鲁迅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诗歌、曹禺的话剧等,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如何认识和理解它们的经典性,却需要研究。经典在阐释中生存,阐释是经典获得不朽生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再伟大的经典作品,如果被禁止阅读、禁止阐释、禁止研究,它就不仅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甚至其合法性价值也会被怀疑。在新文学史上,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现代名家的复活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新的世纪,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应该特别着力挖掘它内蕴的永恒人文价值,比如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的刻画,就特别具有深长的历史意味。一般人都知道压迫会激起反抗,但是鲁迅却发现,压迫并不一定都会导致反抗。“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12]在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压迫不深才使反抗成为可能,所以,最坏的专制是让人连反抗的欲望都不会产生的专制。[13]鲁迅所刻画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就是生活在这种最坏的专制制度之下的可悲而又可悯的中国人的心灵史诗。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他对暴君、暴政、暴力对中国人心灵的扭曲的批判是力透纸背的,他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忧虑是感人至深的。再如冰心散文对“母爱”的歌颂,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坚定信念,今天看来,也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20世纪中国,有那么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写母爱,但是影响都超不过冰心?这绝不是仅仅因为冰心文笔优美,风格温柔,名气大,而是因为冰心笔下的母爱,有两个核心特质,是其他作者没有看到或没有充分表现的,即母爱的伟大在于:它是无条件的,是包容一切的。我们不需要证明或争取、不需要刻意掩饰什么或张扬什么,就可以获得母亲的爱,而人世间很多的爱却是需要我们努力争取或证明才能获得的。母爱是我们在童年时期能够获得的最好的礼物,只有在母亲的身边和母亲的怀抱,我们才能安然享受这种无条件的“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母子之间彼此相爱,却又互相损害,这种扭曲的“爱”不知道在人世间造成了多少沉痛的不合与磨难。在新文学史上,张爱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恰与冰心相反,她与母亲的关系之所以那么疏远,正因为她母亲从一开始就不能接受她的木讷、不美和不活泼,尽管她的成才几乎是母亲一手培养出来的,但是,她的存在,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肯定,直到完成传世杰作《小团圆》,张爱玲才真正解开心头的疙瘩,实现与母亲的精神和解。
人文教育的起点是生命关怀,它的宗旨是对人的存在的无条件肯定,它的目标是培养有文化、有教养、有民主价值观的、身心和谐的现代公民。借助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学经典,我们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思考生命、真理、人性、公正、正义、爱、同情、善良、自由、美等,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无论是曹禺话剧对独断专行的中国式家长的塑造和压抑人性的中国式家庭弊端的揭露、巴金小说对婆媳矛盾的表现、老舍小说对贫穷对人的精神剥夺的深度表达、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牧歌情调,还是张爱玲小说对现代都市人善于调情却找不到爱情的审视,钱钟书小说中自由相爱却又吵架不断的“夫妻吵架”现象的生动表现,等等,均是能够激起现代读者特别是大学生的对话欲望和阅读兴趣的永恒话题。如果说在文学史的专业课教学中,我们要侧重解析作品的文学史地位,那么在通识课教学中,我们更应该有当代意识和对话精神。
①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程光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标签:巴金论文; 鲁迅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新经典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作家论文; 宗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