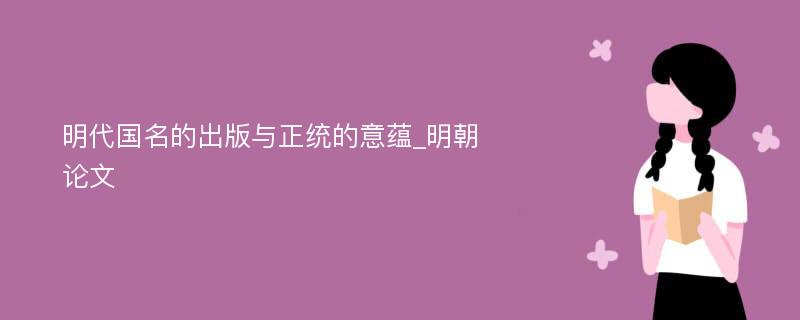
明代的国号出典与正统意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典论文,国号论文,正统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2—0052—06 一 明代国号与明教、白莲教无关 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偏安一隅的创业霸主,还是一统天下的开国皇帝,在开基立业的过程中通常会竭力建构政权的正统性以强化其统治基础。历代统治者建构正统性的手段通常包括建立国号、确定“德运”、①颁布历数、制礼作乐等一系列蕴含着传统宗教观念与古典意识形态的符号性手段,因此讨论明代的国号问题理应从正统建构的角度入手。然而对明代国号问题进行过深入探究的史学名宿吴晗、杨讷及陈学霖却分别选择以明教或白莲教作为考察明代国号出典和蕴涵的线索。 1941年,吴晗就明代国号问题提出了在中外史学界影响深远的观点。②他指出前代国号“或以初起之地名,或因所封之爵邑,或追溯其所自始,要皆各有其特殊之意义”。然而关于明代国号的出典与蕴涵,不但《明实录》、《明史》诸书语焉不详,明清学者亦从未涉及。他认为明代国号应与韩山童父子的“明王”称号有关。韩氏父子信奉的是早已与明教混合的白莲教,而“明王”的出典正是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朱元璋曾“为明教徒”,“因明教而建国,故以明为国号”。③在此后出版的《朱元璋传》中,吴晗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他指出朱元璋麾下诸将“都是明教徒”,选择出自明教经典的大明作为国号,是为了显示“新政权是继承小明王的,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应该同舟共济。④ 1983年,杨讷在探讨元代白莲教的文章中对吴晗明代国号出于明教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吴晗因白莲教、白云宗与明教具有共同特点即断言三派混合的论证方式“颇欠周密”。因为不管明教与白莲教存在多少相似之处,“只要明教还信奉摩尼佛,它就不会同崇奉阿弥陀佛的白莲教混合”。不止如此,明教在元代不但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教派,而且还获得了元廷的承认。上述事实表明,吴晗认为白莲教与明教混合的观点无法成立,“明王”亦与明教无涉。杨讷进而指出“明王出世”的口号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所谓“明王”即是阿弥陀佛。他还援引经文“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其光明所照”,“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期望以此为据论证明代国号的出典是《大阿弥陀经》。至于朱元璋选择大明作为国号的用意,杨讷认为是为了向民众表明新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光明世界的到来,同时也是“对自己出身佛徒的一个纪念”。⑤2009年,陈学霖鉴于杨讷的观点没能赢得应有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往往“仍然延续吴晗的错误”,特意撰写长文重申杨讷的主张。⑥ 杨讷及陈学霖的贡献在于更正了明代国号出于明教经典的误解,但他们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越吴晗的研究思路,即以韩山童父子所信奉的宗教为线索探求明代国号的出典及蕴涵。或许正是由于研究思路的限制,杨讷、陈学霖的观点仍然留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首先,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已经将白莲教定性为异端教派并公开否定了弥勒佛的存在,因此他在洪武元年(1368)诏告天下的国号不可能出自白莲教经典。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在对张士诚政权发动总攻时颁布了《平伪周榜》(按:又名《讨张士诚令》)。⑦榜文云:“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⑧所谓“不幸小民”,“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表明朱元璋认为部分民众不能觉悟白莲教教义的荒诞,误以为真有弥勒佛。正像杨讷明确指出的那样,元末的白莲教徒普遍持有弥勒转世的信仰,⑨因此在至元二十六年公开将白莲教斥为“妖术”并断然否定弥勒佛之存在的朱元璋不可能选择与白莲教有关的国号。 其次,所谓朱元璋试图掩盖与韩林儿的隶属关系或担心他人亦利用白莲教或明教取明而代之的假说,不能抵消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六年公然否定弥勒佛的存在与明代国号出自白莲教或明教经典之间的矛盾。吴晗虽然对明教与白莲教的关系有所误解,但他却比杨讷、陈学霖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上述矛盾。⑩可惜的是,吴晗并没有就此改途易辙,而是试图设法弥缝其论断的漏洞。吴晗为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时“深斥弥勒之传说”与洪武初年严禁白莲教及明教的行动提供了两个理由:第一,朱元璋担心如果白莲教继续流传,“则后来者人人可以自命为明王,为弥勒,取明而代之”;第二,朱元璋受刘基、宋濂等儒士的劝说,决定摆脱与白莲教的干系,即吴晗所谓“隐去旧迹”。(11)姑且不论朱元璋少年时因饥荒而被迫为僧并没有坚定的佛教信仰,(12)参加红巾军的行动也不能表明他崇奉白莲教。即使笔者相信朱元璋打击白莲教的原因确如吴晗所论,仍然无法接受吴晗、杨讷等人的观点。因为,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吴晗还是杨讷,都假设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为了争取明教或白莲教信众的认同。然而,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六年斥白莲教为妖术并断然否定弥勒佛的存在,洪武三年更严禁白莲教及明教。(13)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就算白莲教或明教信徒相信明代国号出自其所信奉的宗教典籍,仍然不能由此对明廷产生认同。 明代国号既然与白莲教、明教无关,那么明代国号究竟典出何处,又具有什么样的正统意涵呢? 二 正统建构与明代国号的出典及蕴涵 创立国号是建构王朝正统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探求明代国号的出典理应从承载着当时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典入手。检儒家经典《诗经》有《大明》之诗,《易经·乾卦·彖传》有“大明”之文。(14)那么明代国号究竟典出何处呢?笔者认为是后者,因为其中同时出现了元、明两代的国号。《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15) 关于元代国号取自“乾元”的问题下文将会展开讨论。笔者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元、明两代的国号不但同出一典,而且上下文相连。一云“大哉乾元”,“乃统天”;一曰“大明资始”,“时乘六龙以御天”。这绝非偶然。 在考察朱元璋为什么要在元代国号出典《易经》的同一段文字中选择国号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宋金以后建构王朝正统性的政治理论“五德终始”说日趋没落,国号对于塑造王朝正统性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的历史情境。在元代以前,国号在王朝正统性建构中的作用远不及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的“德运”。自秦、汉以至宋、金,历代统治者无不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视为极其重要的建构正统性的理论工具。这主要是因为“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相生或相克为基础建构的循环理论,它在意识形态层面为新兴王朝提供了取代旧王朝的正当性。然而,自北宋中期以来“五德终始”说遭到了彻底的批判。率先发难的是欧阳修。他指出以五德相克的循环论来解释王朝更替实乃荒诞不经的游方术士之言,实际上正统王朝并非此仆彼起,延绵不断,而是存在着正统断绝的时候。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基础。不止如此,欧阳修还将道德因素置入评判正统的价值体系之中,试图以道德论取代“五德终始”说成为新的解释王朝兴替的政治理论。(16)至南宋,朱熹进一步完善了欧阳修的上述观点,从而形成了新的正统理论。南宋以后,理学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被宋儒贬抑的“五德终始”说在宋金以后一蹶不振。(17)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元代统治者不再讨论本朝的“德运”问题,(18)改以国号彰显王朝的正统性。至元八年,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改国号为“大元”,并诏告天下。诏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盖因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肆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伸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为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资尔有众,体予至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19) 引文首先强调建立含有美好意蕴的国号以继承古代圣王次第相传的正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上古三代圣王皆按上述方式建立国号。接着指出,自秦、汉、隋、唐以来,历代君主背离古制,“不以义而制称”,或“因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不免有遭人非议之嫌。本朝承继上古三代之传统,“称义而名”,取《易经》“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清代史学家赵翼敏锐地认识到元廷建立国号的方式是以复古为革新,创造了以儒家经典文义建立国号的新传统。因此,他特意标出“国号取文义,自此始”。(20)需要指出的是,元世祖将国号由大朝改为元朝是利用儒家传统经典建构本朝的正统性,而不是像萧启庆所说的那样“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文化化”。(21)否则元廷就不必诏告天下,制造刻有国号“大元”的钱币,(22)甚至派遣使者至高丽宣布“建国号曰大元”。(23) 现在回到朱元璋为什么选择与元代共享国号出典的问题。当明朝创立之时,“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功能趋于消解,因此明廷并没有确定“德运”的举措。正如陈学霖所说,朱元璋政权虽然在与群雄逐鹿之际因依附于韩林儿的大宋政权而宣扬“火德”,但在明朝建立之后,并无“讨论德运,推定行序”之举。后人以为明朝为“火德”,纯属误解。(24)需要追问的是,朱元璋为什么不沿袭秦、汉、隋、唐建立国号的方式呢?这主要是因为秦、汉、隋、唐的国号或取自其封地之名,或采用其爵邑之号,朱元璋虽然亦拥有的吴王封号,但这个封号不但在名义上受之于韩林儿而且与张士诚的封号别无二致。(25)因此,为了建构本朝的正统性,朱元璋采用了元代以复古相标榜的建立国号的新传统。 朱元璋选择与元代共享国号出典的举措亦与明廷“承元”而不直接“继宋”的正统策略有关。元明之际的主要矛盾不是族群冲突,元末民变首领韩山童号称宋徽宗八世孙主要是为了强调其自身的正统性,未必有强调族群矛盾的意图。红巾军的著名口号“贫极江南,富称塞北”亦仅侧重于凸显江南与塞北在资源分配层面的矛盾。(26)与此相应,朱元璋政权在《谕中原檄》之前未曾提出强调族群矛盾的口号。(27)《谕中原檄》中虽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语,但其目的却并不是要强调族群冲突从而将少数族群彻底驱逐,(28)而是要激发中原民众的华夏认同,避免其“反为我仇,挈家北走”。(29)钱穆、姚大力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族群冲突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他们指出元明之际的士人与民众“华夷观念”淡薄,仅将元明兴替视作“一次改朝换代而已”。(30)上述情况表明,明廷采取“承元”的正统策略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 明廷“承元”的正统策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了元朝作为宋朝继承者的正统地位。第二,洪武三年七月明廷完成了《元史》的修纂,这进一步确立了元朝的正统地位。(31)第三,洪武六年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这不但标志着明廷建构的包括上古帝王与汉、唐、宋、元的正统王朝谱系正式形成,(32)而且再次体现了元朝的正统地位。 朱元璋在与元代国号出典相同且上下文相连的文字中选择国号与明廷“承元”的正统策略息息相关,其目的在于象征性地展示元、明之间的正统嬗替。明代国号所具有的这种象征意义与明廷“承元”的正统策略一道为明廷统辖宋代版图之外的地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因为明朝的疆土除了辖有两宋故地之外,还辖有曾属于元朝但不曾属于宋朝的大片疆域。虽然这些土地大部分是汉唐故土,但明朝若在正统谱系上“继宋”而不“承元”,无疑会削弱其在不曾划入宋朝版图的东北、甘肃、云南等地区的统治基础。 朱元璋宣布国号为大明的《初即帝位诏》既宣告了明廷“承元”的正统策略也暗示了明代国号的正统意涵。鉴于著名学者陈学霖对上述史料有不同理解,下面就此展开讨论。《初即帝位诏》虽有不同版本,但与明代国号相关的内容基本相同。为了使讨论更具针对性,本文使用陈学霖展开分析的《皇明诏令》本。兹征引原文如下: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告终,帝(按:昊天上帝(33))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蛮夷,各处扰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皆已勘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俯徇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34) 陈学霖在对上述文本进行仔细分析之后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朱元璋强调天下取自群雄之手,“亦无表示新朝是继承蒙元而来”;第二,诏书并未透露国号“大明”的“取义”。(35) 陈学霖的上述观点存在着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首先,诏书已经明确指出了宋、元、明之间的正统承继谱系。所谓“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意在表明元朝取代宋朝的正统地位是昊天上帝的安排;元“运亦终”之后,“(朕)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云云,显示元、明之间的正统嬗替亦是上天的安排。诏书强调天下取自群雄的用意只是为了建构取代元朝的合法性,即元朝并非明朝所灭,明朝获取的是早已被群雄攘夺的天下。(36)其次,诏书虽未直言国号的出典及蕴涵,但并非没有透露相关讯息。因为《易经》是中国古代知识精英熟知的儒家经典,元代国号取自《易经》亦是诏告天下的事实。因此,元、明两代国号出于《易经》中上下文相连的同一段文字并不是不易察觉的事实。与此同时,诏书中明确宣布了宋、元、明之间的正统承继关系,这也就暗示了明代国号具有象征元、明之间正统嬗替的意涵。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明代国号的出典与正统意涵之所以数百年来隐没不彰与明中叶以后族群中心主义抬头有关。因为在明初的历史情境中,元、明两代的国号同出《易经·乾卦·彖传》与明代国号具有的象征元、明之间正统嬗替的意涵,对于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精英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他们无需为此枉费笔墨。明中叶以后,随着族群中心主义的日渐高涨,士人群体开始否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并炮制出形形色色的有关国号的传说以期掩盖明代国号具有的象征元、明之间正统嬗替的意涵。然而,正如陈学霖所说,这些传说对国号问题的解释“都不能成立”。(37) (感谢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张帆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所谓“德运”源于战国思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该学说认为宇宙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组成,名为“五德”或五行。“五德”或五行按照相生或相克的原理构成了依次循环的变化规律,这一规律为解释自然变化与王朝更迭提供了理论基础。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册,第404-617页;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辩》,第5册,第617-630页;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55-64页;Benjamin I.Schwar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50-382. ②吴晗是中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其明代国号出于明教的观点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自不待言,国外学者亦往往认同吴晗的见解。Edward L.Farmer,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the Reorder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Era of Mongol Rule,E.J.Brill Leiden,1995,p.32. ③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原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载北京市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418页;引文见第382—383,409、414页。 ④吴晗:《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42页。 ⑤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93年,第213—214页。 ⑥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0期,2009年),载陈学霖:《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引文见第28页。 ⑦关于《平伪周榜》的颁布时间,参见杜洪涛:《〈弇山堂别集〉所载〈平伪周榜〉勘误——兼论其颁布时间》,《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3期,第137—141页。 ⑧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15页。 ⑨杨讷:《元代的白莲教》,第212页。 ⑩杨讷亦曾征引《平伪周榜》(按:又名《讨张士诚令》),却未曾注意到所引史料与其观点的矛盾之处。陈学霖在重申杨讷观点时,亦未曾察觉上述矛盾。杨讷:《元代的白莲教》,第214页;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第1—35页。 (11)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第415页。 (12)关于朱元璋出家的经过,其亲笔所撰的《皇陵碑》记之尤详。碑曰:“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修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可见,朱元璋是被迫出家,并没有深厚的信仰基础。正如陈高华所说,朱元璋“对佛教宣扬的天堂地狱和修来世之说,并不尽信”。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皇陵碑》,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433—434页;陈高华:《朱元璋的佛教政策》,载陈高华:《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13)《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37—1038页。 (14)《大明》是《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的第二篇。此诗首先揭示天人感应之故,接着追述武王生有圣德并非偶然,最后描绘武王伐商而一统天下。关于其主旨,《诗》序以为是“文王有明德,故复命武王也”;清代学者方玉润则认为是“追述周德之盛,由于配偶天成也”。笔者认为,此诗名“大明”,含有圣德昌明之意,以此作为国号出典亦非不可。然而,笔者在综合考虑元、明两代国号同出《易经·乾卦·彖传》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后,仍然认为明代国号的出典应为《易》经。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7—480页。 (15)高亨:《高亨著作集林——(第二卷)周易大传今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0页。 (16)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 (17)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载陈学霖:《宋史论集》,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25-173页;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论“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2—106页。 (18)元廷拒绝讨论“德运”问题固然与其自身汉文化水平不高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五德终始说已经不再是建构王朝正统性的必要手段。 (19)陈高华点校:《元典章》卷1,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20)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0页。 (21)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载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页。 (22)杨敬民:《珍奇的元代国号钱》,《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4期,第10—12页。 (23)(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国书刊行会1977年版,第416页。 (24)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载陈学霖:《宋史论集》,第48页。 (25)据《明史》,张士诚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称吴王”。张廷玉:《明史》卷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页。 (26)丁国范:《元末社会诸矛盾的分析》,载南大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3页。 (27)在颁布《谕中原檄》的前一年(按:至元二十六年),朱元璋在《平伪周榜》中不但没有痛斥张士诚投靠元朝反而指责他对元不忠。如“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别达丞相,谋害杨左丞(按:以上二人皆为元朝官员)”;又如“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江浙丞相达失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5,第1616页。按:笔者对引文进行了必要的更正。相关文字考订,参见杜洪涛:《〈弇山堂别集〉所载〈平伪周榜〉勘误——兼论其颁布时间》,第137—141页。 (28)《谕中原檄》明言:“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程敏政:《皇明文衡》卷1,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32册,第2页上。 (29)程敏政:《皇明文衡》卷1,第2页上。按:《谕中原檄》针对的只是中原臣民,因为同在至正二十七年颁布的讨伐浙南等地的檄文中并没有以“恢复中华”相号召。关于《谕中原檄》的相关分析,参见杜洪涛:《“再造华夏”:明初的传统重塑与族群认同》,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7-10页;关于讨伐浙南的檄文,参见《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甲寅,第388页。 (30)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载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56页;钱穆:《读明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载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第235—236页;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载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262页;引文见第262页。 (31)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十二月命宋濂、王祎等纂修元史,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同年八月基本修成。洪武三年二月再次开局补修顺帝朝史事,洪武三年七月全部修成。《宋濂目录后记》,载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677—4678页。 (32)《太祖实录》卷84,洪武六年八月乙酉,第1500—1501页。关于明廷建构的正统王朝谱系,参见杜洪涛:《“再造华夏”:明初的传统重塑与族群认同》,第10—13页。 (33)据《太祖实录》的相关记载可知“帝”为“昊天上帝”。《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乙亥,第477页。 (34)《皇明诏令》,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册史部,第35页。 (35)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第12—13页。 (36)这种论说只是一种倾诉策略,不必与事实完全相符。 (37)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第14—16页。标签:明朝论文; 朱元璋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明教论文; 元朝论文; 易经论文; 白莲教论文; 明史论文; 吴晗论文; 大明论文; 五德终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