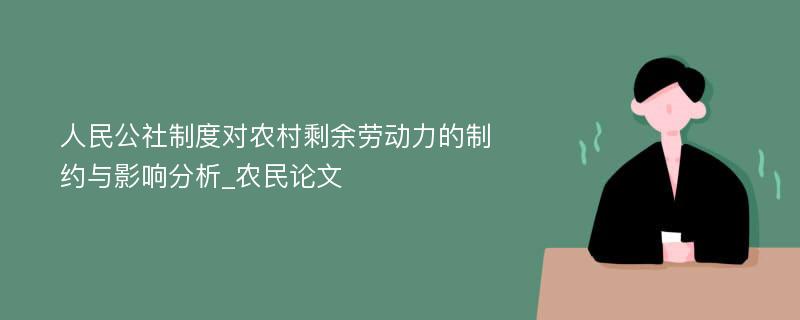
试析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制约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公社论文,剩余劳动力论文,体制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民公社时期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模式,包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经济上的计划管理和分配体制,社会层面上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及人民公社制等。这种大政府的高度控制与全面干预体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及其流动影响深远。本文拟以人民公社体制下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切入点,着重论述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素及其后果。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体制内的积存
人民公社时期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使得农村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劳动力剩余积淀严重。研究表明,重工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明显低于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重工业每亿元投资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只及轻工业的1/3(注:李同文主编:《中国民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现状与未来》,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以固定资产增长与劳动就业岗位变化脱节为例:1978年与1952年相比,我国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增长22.7倍,年均增长12.9%;工业部门劳动力仅增长3倍,年均增长5.5%,而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却增长4.8倍,年均增长6.2%;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增长5.7倍,年均增长7%。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工业从业者未能随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而相应增长,为解决就业造成结构性困难。从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看,1978年,中国工业所占比重达44.8%,已具有人均GNP3000美元以上的中等发达国家特征,而从劳动力结构看,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70.5%,是人均GNP200美元以下农业国家的典型特征(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3年第7期,第4、3、4页。)。
据我国学者计算,1952~1978年,我国工业资本积累吸纳新增劳动力的理论数字为17113.7万人,实际吸纳8097万人,少吸纳劳动力9016.7万人,这意味着二元经济一端的工业部门实际吸纳劳动力不及理论数字的1/2(注: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页。)。在工农产品“剪刀差”减掉了农村6000亿元人民币的同时,高速行进的工业化却并没有吸纳农民,使农村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以1978年和1965年相比,城市人口增加了4200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从18%下降为17.9%;而农村人口却增加了1.9548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从80%增加为82.1%(注:周尔鎏、张雨林主编:《城乡协调发展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农民在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的过程中,却没有分享到城市工业化的成果。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排斥在工业大军行列之外,其结果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有限的耕地和单一的粮食生产项目上,忍受着隐性失业和生活贫困化的痛苦,农村经济发展步履维艰。据估计,整个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新蓄积了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注: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它直接构成了农村劳动力日后大规模流动的原动力。
其实,我们从当时农业生产率的滞缓中也不难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压。据统计,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按不变价格计算,1975年比1957年还低11.6%,到1980年也不过提高了15.8%(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3年第7期,第4、3、4页。)。这说明,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人口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压力增大,劳力投入密集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出现内卷化,投入与产出的边际效益渐趋于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已经出现了大量剩余,他们处于不充分就业的半失业状态,或重复劳动,或窝工、怠工。
农村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既已承受了超负荷的就业压力,而剩余劳动力作为一种具有流动倾向的“势能”,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问题是为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剩余劳动力转移才如泄洪般地得以释放?何者阻碍了这一流动?换言之,是什么因素掩盖了劳动力的剩余?
二、超稳定结构下的“全民就业”
1、执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决定了不允许在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农民入社,土地产权关系亦随之而变,土地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为实现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的农村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政治上农民翻身做主人,整个社会则被单位化和组织化,再加上浓重渲染的劳动光荣思想,批判不劳而获或劳心不劳力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这种局势下可谓全民就业,没有失业现象和乞丐,极少流动人口,自然也就无剩余劳动力可言。
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相呼应,我们建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满足其需要的体制和制度,如中央集权体制、计划管理和分配体制、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管理体制、统购统销制度、城乡隔离制度、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等。在上述体制和制度的影响下,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农村非农产业被压制,农村人口城市化被阻止,城市被建成强大的计划体制堡垒。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失误,使我国在1949~1978年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逻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性、有持久效应的转移是微弱的,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52年的87.5%下降到1978年的82.1%,年均仅下降了0.25%,农村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88%降为76.1%,年平均也仅下降了0.56%,而同期农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却由45.4%降为22.9%(注:《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并没有带动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的下降,表明了我国工业和城市吸纳过剩农业人口的能力相对很弱,无法拉动并刺激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和流动。总之,这一时期的农村社会稳定是政治体系强控制的结果,这种强控制势必窒息农村经济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抑制农民作为“经济人”的经济冲动,从而严重削弱农业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首先,在国家采取的严格限制农村居民流向城镇的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农村社会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僵硬的身份壁垒和极低的社会流动率。国家禁止农户向城市自由迁居,严格限制农民异地活动。不仅城乡之间的界限难以逾越,就是农村的不同社区之间,这种身份壁垒也是长期存在的。对所有的农村人口来讲,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公社社员。除联姻、过房、承继等情况外,这种社区身份也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不仅人员流动极难,其他社会资源的流动也同样如此,农民不但不能携带自己入社时的土地和耕畜退社,而且,甚至不能携带他自身退出这种体制。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人民公社化制度下,农民没有分化,没有流动,没有迁移,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只有农民、渔民、山民和牧民的区别。经济学家赫彻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语中的:公社制下的农民既没有“退出权”,也没有“喊叫权”,他们留在体制内不是出于对集体的忠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注: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8期。)。
其次,公社体制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第二个层面,即为禁止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公社化的严密组织下,农民就是农民,农民只能呆在农村,不能随便外出,也不能干不属于农业范围内的事情。否则,就是不老实,不本分——用那个时代的话说,就是搞“资本主义尾巴”。“不堵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所以资本主义尾巴是要随时割掉的。浙江的桐乡一度出现:自留地、饲料地不准搞“五秧”等商品生产;限制农民家庭饲养家禽数量;社员不可以出门做生意等等,有的社员甚至把一个鸡蛋拿到集市上出售要看“主义”,卖给供销社的是社会主义,卖给城镇居民多卖一分钱就变成“资本主义”(注:俞宗泳:《桐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载中共桐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的足迹——建国后桐乡地方党史专题选编》(征求意见稿)。)。这些极“左”的东西,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的改善。笔者在浙江桐乡和江苏盱眙的访谈也印证了这一点:“只要你种点瓜,养点小鸡、小鸭,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小瓜还没有生,就把藤给你拔掉,鸡也有规定,每一户只能养2只,检查队每天晚上都要去看的,只要你养了3只,就给你抓走一只,剩下的2只还得是留着过年时吃的,是产品才行,农民自己留一点,种一点就不成,就是‘资本主义尾巴’,你说你怎么去搞经济作物?”(注:2002年10月15日对桐乡市河山镇政府宣传部长的访谈实录。)“我的父亲是当时沙岗村的第一任书记,听我父亲说,在整个50~60年代,农民只能种地,干其他的不行。文革时,我们种点经济作物叫做资本主义尾巴,所以当时的社会大气候决定了农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出路。”(注:2002年11月6日上午对盱眙县沙岗村第六任书记的访谈实录。)于是在超强的压制下,“白天,你可以看到田地上有一大堆一大堆的人在‘大呼隆’——集体耕作;夜晚,你可以看到一家至少有五六个人甚至是七八个人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吃饭,然后悄无声息地躺下,等待第二天黎明就要敲响的上工钟声。广袤的农村大地一片寂静,没有欢声,没有喜乐。老实巴交的农民日复一日地在那块由50年代土改时划定的属于村庄所有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着,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天,指望着能有一个好收成”(注:陈文科等著:《中国农民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便成了公社体制下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2、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制度勾销了流动的需求
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及实物配给制的计划分配体制简化了人们的利益需求,汩没了基于需求之上的差序结构,自然也就消泯了流动之源。按照社会学的社会流动理论,“社会流动与社会阶层化乃是一体之两面。不过,在逻辑和时间上,社会阶层化应先于社会流动。因为有了社会阶层,才能有社会流动。”(注:许嘉猷:《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4页。)但在城乡隔绝的二元体制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流动管道被堵塞,成为封闭性的社会。与此同时,农村公社体制则以成分均一、结构单一的社会结构特点,从生产到分配的各个环节都试图取消社会分化与分层,从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斩断了流动之源。
需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动力,但满足农民需求的分配机制却从某种程度上扼杀了这种需要。在平均主义严重的公社内部,矛盾是十分突出的。江苏省盱眙县1956~1960年5年的收入分配结果调查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表一所示):
全年分配劳动力全年产值与实分数
年 小队
度 名称类别
人口
劳力其 中 占分配
实分数
个数 非包工 劳动日
总产值
元占产值每劳力平均 每人平均
一太平高产13872 7479
9665
615563.6
85.48 45.18
九新民一般11761 6509
7521
535771.2
87.81 45.78
五林山低产11557 5908
5727
486284.8
85.29 43.99
一太平高产1457110336 1551 15 11981
725660.5
102.19 50.00
九新民一般13359 9485 202821.6 8781
6407 73108.59 48.17
五林山低产11757 7802 105413.5 6432
5523 85 96.89 49.88
一太平高产1467010609 426942.213156
771558.6
110.21 52.84
九新民一般1376010609 501347.211381
738064.8 123 54.89
五林山低产1225710324 5270 51 8984
632470.3
110.94 51.83
一太平高产1768010448 346733.110125
418141.252.26 23.75
九新民一般14665 9461 2839 30 7317
378451.758.21 25.91
五林山低产13054 8165 231728.5 7001
326746.660.50 25.13
一太平高产1877615355 401026.118639
844045.1
111.05 45.18
九新民一般1466212166 396132.513688
669148.8
107.92 45.82
六林山低产1325310636 297327.911233
584952.1
110.35 44.34
资料来源:《关于桂五公社林山大队落实1961年、“三包一奖”工作情况的报告(1961年)》,盱眙县档案馆105-1-18。
由表一我们可以看出,集体公社内部分配工作上的平均主义错误倾向是十分严重的,集体成员多劳却并不能多得,生活水平都差不多,高产队甚至低于低产队的平均生活消费水平。1959年的分配结果显示,高产队太平每人收入23.75元,相反,一般和低产的新民和林山两个小队的每人平均收入均在25元以上,比太平小队平均高2元左右,显然,集体公社内的分配是极其不合理的。
这种平均分配制度的极端形式便是“吃大锅饭”,人们都叫做“敞开肚皮吃饭”的时期。“大伙一天都吃5~6顿——可那年地里根本没有多余的收成!所有的收成都已交给了集体,个人家里空空如也,聊无存量。结果,人们饿得睡不着觉,有的病了,有的老人顶不住,死了。村子变得一片沉寂,似乎大伙全死了。如此下来,村民再也没有心思为下一季粮食下种了。由于管理权在公社手中,陈村的收成和其他8个村的一样,都给送进了集体大锅。看来别村的农民恐怕也都没心干活,陈村人非常怀疑自己今后的劳动能不能得到回报。于是,陈村的农民开始任土地抛荒,宁可到山坡上扒找野食,或者索性缩在家里少出工耗力气,默默地疗其饥苦。”(注:陈佩华、赵文词、安戈著,孙万国等译:《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泽东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村农民的悲惨遭遇也可以说是公社化时期农村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流动既缺乏理论上的合法依据,又受到制度和体制上的制约,并被从需求层面的硬性安排中抽掉了流动的动力,其结果便是农村充当剩余劳力蓄水池日益不堪重荷,以及流动势能的与日俱增,必然会反过来对农村和整个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与冲击。
三、流动势能的积累与潜不安因素的滋长
一般而论,稳定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但从逻辑上讲,并不是只要稳定就有助于发展,从根本上看,稳定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目标,“发展是一个社会中最终的目标。没有发展,任何一个社会迟早要走向崩溃。稳定是一个社会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也是发展的一项重要制约条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种类型的稳定,即发展的动态性稳定和阻碍发展的迟滞性稳定(注:徐勇、张厚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前一种稳定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动态平衡,而后一种稳定则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的高度控制实现的,它往往以牺牲发展为代价。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稳定便属于后者,是政治体系对乡村社会强有力控制的结果,这种控制几乎掌握着农村的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心理资源,支配了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典型的全能控制特征。其结果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评价的那样:“1958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窒息了农业经济活力,使农村经济长期停滞徘徊,动摇了稳定的基础
建国以后,包括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农业经济从总体上看还是呈增长趋势的(1959~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除外),但进入人民公社时期以后,农业生产增长,尤其是农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减慢,一直到1977年也没有达到1957年的水平。农业的停滞直接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农村未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状态,农民始终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以数据为证:1957年农户人均纯收入73元,1978年为133.6元,其中从集体分得的约为88.5元,年递增率为2.5%,扣除物价因素,仅为1.4%。至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50元以下的占27%,40元以下的占16%。同一时期,全国农村人均口粮占有量反比1957年减少4斤。其中旱粮地区人均口粮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19%,水稻地区人均口粮4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18%,全国约有1.4亿农村人口处于半饥饿状态(注:肖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我们从县志上随处可找到这样的材料,如浙江省的《新昌县志》记载:由于搞“大跃进”运动,随之掀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县28万人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推广亩产万斤粮的所谓“经验”,又搞全民伐木、烧炭炼钢运动。瞎指挥、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泛滥,农村生产力一再受到破坏。1960年人均口粮比1958年减少139斤,农村出现饿、病、逃、荒现象……(注:新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包产到户文存》(内部资料),第6页。)江苏省的《泗阳县志》也载:大跃进期间,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影响,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村一度形成生产靠贷款,吃粮靠供应,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局面,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外流现象严重(注:《泗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泗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农业增长的缓慢,固然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导向有很大关系,但从农业发展自身来看,以强制性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则是制约农业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制度性因素。“公社化实际上使农民变成了农村的‘无产者’,这一种祖祖辈辈繁衍于农村但是却‘无产’的状态,使中国农民中的许多人,从‘公社化’那一天起,心里就埋下了一份不安,这不安渐渐麻痹以后,又演变为一种普遍的依赖的惰性……种什么,怎样种,种多少都要‘公社化’,农民不可能在耕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时获得什么真正的劳动的愉快。农民在田间相互比赛的劳动热忱,以及在地头休息时的愉快情形,其实都只不过是人为煽动的热忱和即兴一时的愉快。秋收以后,当大批的粮食被收缴,农民们仅仅剩下口粮时,他们的失落感是难以形容的。”(注:梁晓声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人民公社以其高度控制和深度渗透为特点的组织方式,束缚了农民的自由,限制了其自然转移与流动。由此,导致农民的生产热情下降,直接妨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明明是土地减少了,劳动力大量增加了,村里的农民却仍然一年四季地“忙”,有时还要开早工、夜工,这些都是集体生产制度难以维系的症结。1978年平均每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仅2008斤,比1952年的1893斤只增加115斤,增幅为6.1%。如果按产值看,1978年平均每一个劳力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636.2元,与1952年的506.3元相比仅增长25.7%,平均每年递增为0.9%。1952年按人均产值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为1∶8.3,到1978年这一比值剧增至1∶17.5(注:《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167、180页。)。强控制下的联合劳动窒息了农业经济活力,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并进而阻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2、城乡差距拉大,剪刀差陷农民于共同贫穷之中
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被强制性地划分为两大地位悬殊的社会群体,且二者之间的沟通与流动渠道被人为堵塞,使得城乡在就业机会与收入分配方面的鸿沟加大。据有关专家测算,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和乡村人均收入比大约在1.08∶1左右,1955年大约在2∶1左右,而到了70年代末,包括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各种明贴暗补在内,城乡人均收入比据不同学者测算演变成了3∶1,4.9∶1,5∶1和5.9∶1(注:段若鹏等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二元结构的强度还可以用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比来衡量,美国著名数理统计专家库茨涅兹的研究表明,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中国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竟高达6.08倍(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3年第7期,第4、3、4页。),为世界各国所仅有。此外,中国农业与非农业从业人员间的隐性经济与社会差距也非常大。据估计,这类差异有几十项之多,主要表现在住房制度、粮食补贴、副食品供应、能源供应、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等方面。
在城乡差别扩大的过程中,国家通过强迫征购和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身上大约剥夺了6000亿元人民币(注:Tiejun Cheng,1991,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Hukou)System in China,Paapers of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a,November,13:p.8。)。这6000亿元对于当时中国农民的生计来讲是个什么概念呢?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全国农民整劳力的日平均工资只有5、6角钱,如果6000亿元由8亿农村人口均摊,每人要摊750元;如果再除去老人和儿童,仅让3亿劳动力平摊,每人要摊2000元。以日工资6角钱计算,每人要白干3300多天,差不多要10年。也就是说,在实现集体化的20年中,中国农民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无偿劳动。
3、阻碍了农村社会正常的分化与流动,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引起了普遍不满和消极抵抗
禁闭式的公社体制取消了社会流动与利益分化,进而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劳动效率低下,人心思动。在平均主义严重的集体化时期,劳动低效率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对1949~1957年间山西省101个合作社5种不同作物所需的劳动量,以人头小时为单位作了大体上的统计,发现在这8年之内劳动生产率综合指数下降了5%(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443页。)。对50年代和60年代粮食投入—产出关系的研究也表明,“投入的增长快于产出的增长。总要素的生产率在1952~1957年间下降了6%,而在1957~1965年间则下降了8%。中国农业在投入—产出比例关系方面的成绩是低劣的。”(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443页。)虽然动员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但农业总要素的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原因何在呢?
对剩余劳动力的封闭与不合理使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以江苏省的盱眙县为例:入社后土地利用率提高了,复种面积扩大了,粮食也收得不少,但是耕种工夫却比入社前差了。重要的是社员“对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上认识不明确,做活毛糙。贪数量,抢工分而不顾质量。”另据对冼庄的调查,锄工亦大不如从前,“过去锄过的玉米,土质发黑(锄得深),根部像坟堆,现在锄田既浅又平,而且锄得不干净,有时锄得不适时,对比起来,过去锄一脚要抵现在锄二脚。”不仅如此,队干部对生产劳动管理也缺乏经验,在合理支配劳力、公平确定报酬、评工记分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点,小段作业计划、组包片、户包、定额管制、分级计酬等都没有推行,做活还是大呼隆,工分是死分死计。
因此,窝工、费工现象很普遍,劳动效率很低。现在社员做一天半到两天,才抵上单干时做一天的活。单干时晚上拔秧,白天栽秧,现在拔栽分开,有时拔一天还不够一天栽的。过去耕田,天麻麻亮就下田,现在太阳出才下田(注:《盱眙县新湾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情况的初步调查》,盱眙县档案馆105-1-7。)。又如对浙北乡村陈家场在1965~1980年15年间的历史考察:在生产队的全年实际用工中,竟有一半属于窝工(如表二所示)。
表二陈家场四个年度的窝工数(注:曹锦清、张乐天等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年份
全年实际用工总数
全年有效用工量窝工总数窝工的比率
196515441 8832
660943%
197021688 9636 1205256%
197522138 11936 1020246%
198024469 11993 1247651%
在退社自由被取消之后,窝挤在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内,农民又用种种特殊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抗议,如“工分挂帅”(是指社员在生产劳动中只顾拿工分,不顾劳动质量的现象)、“搭便船”(主要是指让别人捎带干活,自己也可以轻松地与他人拿一样的工分)、损公肥私、追求体制外收入(主要是指农民外出打工或其它家庭经营收入)等(注: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4、引发政治危机与信仰危机
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村的停滞徘徊意味着农村政治不稳定因素的累积。人民公社未能使中国农民摆脱贫穷落后,相当部分农民仍然存在着基本的生存问题。据中国社会统计资料显示,1952~1978年,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从62元增加到132元,26年间仅增长1倍(注: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而在城市现代化突起的对照下,农民的心理失衡便会越来越重,这不利于农村的经济建设,也不利于农村的长治久安。
早在退社自由还没有被取消时,集体中的小农就时而做起退社的梦。尤其在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这种状况更为严重。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6年12月向中央的汇报:“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浙江省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浙江省发生了20余起社员殴打社干部的事件。”(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队问题》,1956年12月6日。)江苏省的《泰县志》记载:1957年4月,全县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不少地方违背自愿原则,各项政策没有妥善处理,加上风、涝、病、虫自然灾害,82.7%的社减产,引起社员强烈不满。塘湾区穆庄、港口区河南、泰西区复兴等农业社相继出现社员退社事件,5月迅速蔓延至全县各区,直接参与的农民49582户,遍及94个乡的609个农业社(注: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泰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江苏省的盱眙县也是如此:据对十里营乡淮峰社的调查,看大势,顺大流,采取中间态度的社员占34.4%,对社不满、思想动摇者占到了6.5%,坚决要求退社的也占到了0.2%(注:《盱眙县淮峰社各阶层人民对合作化的态度等问题的调查报告(1957年)》,盱眙县档案馆105-1-7。)。由此可见,对农民实行高度控制与剥夺的公社体制已经激起了农民的抵制和反抗,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把这种对实践中社会主义模式的体认等同于马列主义,从而对人民公社体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方向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产生疑虑,造成在基层党组织成员和社员之间出现思想混乱,引发信仰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孕育了冲破旧体制的巨大能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一种具有流动倾向的“势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政、经、社、教合一的公社制度难以为继,束缚与圈囿农村剩余劳力洪流的闸门终将开启——要么是国家主动有计划地从闸门泄洪,因势利导;要么就是势积而发,冲堤决坝,一发而不可收拾。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实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战略,无疑顺应了这一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种正确的必然选择。
标签:农民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农村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剪刀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