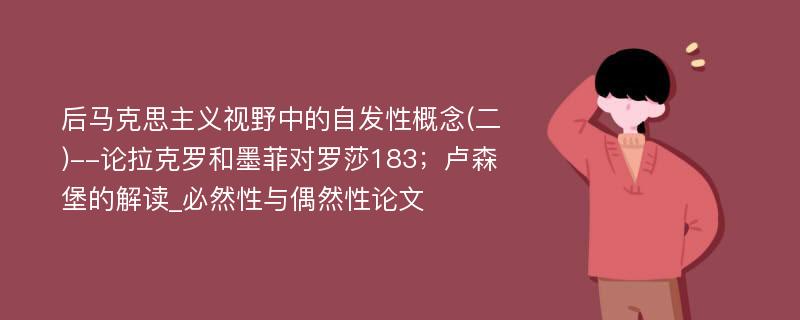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下)——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183;卢森堡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森堡论文,视域论文,自发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克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016-07
可以肯定地说,罗莎·卢森堡确实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阶级的真正统一不是静态的、理论性的、“事先”决定好了的,而是在革命风暴的具体过程中形成的。这一观念是她阐发激进政治行动主义或行动优先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拉莫正是“猎取”了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念,并以此作为其发挥所谓偶然性的建构逻辑的张本。不能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根本没有建构主义的因素,也不能说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的表述中没有给偶然性任何空间,关键在于,在一个怎样的理论构架中、怎样的分析范式中处置它们,并将这种建构性引向何方,将这种偶然性看得有多大?从拉莫的主观愿意出发,他们当然希望偶然性逻辑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起得作用越大越好。但事情并非总是随人心愿,更何况人为地“篡改”的事实也与“自发性”的本义不相符。因此,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拉莫的行文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大起大落”现象:他们先是振振有词地确证罗莎·卢森堡触到了偶然性逻辑,并且这种逻辑俨然已发挥了它特有的功效。这似乎让人依稀产生一种朦胧的期待: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接合逻辑宛如发育完好的胎儿就要分娩而出。然而,就在令人激动的时刻即将来临的一刹那,拉莫突然吹响了哀伤的号角:本来要发出第一声啼叫的婴儿却由于某种原因而胎死腹中。
对于拉莫的这种“跌宕起伏”手法,诺曼·杰拉斯无比愤慨。在他看来,拉莫对罗莎·卢森堡的“表扬”不仅不地道,而且原本就是一个歹毒的阴谋,这岂不是先把罗莎·卢森堡抬升到最高点,然后又突然丢开手吗:“这个表扬,罗莎·卢森堡不要也罢,因为它不过是指责罗莎·卢森堡犯了二元论错误的序幕”[1] (P61)。拉莫当然不会承认他们在“暗算”罗莎·卢森堡,更不会承认他们故意悬设了一场虚惊。按照拉莫的解读,问题出在罗莎·卢森堡身上:她使出浑身力气拉满了大弓,最后却没有将箭发射出去!既然已经把象征的多元决定看成是统一种种斗争的具体机制,那么,“自发性的那种逻辑看来似乎意味着作为其结果而出现的统一主体类型(由于不是在多元决定过程之外被决定了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不确定的”[2] (P11)。质言之,如果断定政治主体的统一是在具体斗争过程之中生成,而不是在斗争之前就严格地决定了的,那在理论上,这种统一是何种统一应该是未确定的,“但是,问题出现了,因为,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多元决定的这一过程却构成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统一:阶级统一”[2] (P11)。即是说,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主体统一的性质或类型已经没有变化的余地,已经别无选择,已经不言而喻,它是铁定的,它一定是阶级统一。在拉莫看来,问题正出在这里:为什么就是“一定”的呢?“为什么就不能超越阶级的局限从而导致部分一致的主体统一类型(它的基本规定是大众或民主)的建构呢”[2] (P11)?
拉莫认为,恰恰在这个地方,罗莎·卢森堡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在革命的多元决定过程之外业已铸就的基本事实,那么,无论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都不外乎是这种已形成的统一性的对等表达(或者说是既定图式的一种演示),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无须谈论革命主体的阶级特性问题,它本身根本就不成问题,因而也就根本没有所谓建构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政治主体的统一是在多元决定过程中具体构成的,那么,这种统一自然不能脱离自己得以型构的过程,可是,它缘何在构成之前就已完全成形了呢?显然,过程本身的始源性的生成能力与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形成了一种难解的紧张对峙关系,而罗莎·卢森堡又不愿有所偏废,不肯舍弃任何一方。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罗莎·卢森堡宁肯自己一再阐发的自发性逻辑受到阻滞而断然不肯放弃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呢?换言之,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拉莫指出,尽管罗莎·卢森堡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思考过)多元决定过程所构造的主体一致性与主体的阶级立场之间何以必然“重叠”这一问题,但是,从她的思想背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所深信的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保证”了革命主体的主体性与其阶级性的天然一致和完全重合。即是说,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蕴涵的必然性逻辑为自发性逻辑提供了一条必须接受的“路线图”——自发性逻辑无论怎样自主“跳跃”,它终究跳不出必然性逻辑的“掌心”。正缘乎此,拉莫不无感慨地说道,“结果,自发性逻辑的创新作用看起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地限制”[2] (P12)。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拉莫的解读中,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不再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悖论,不再是铁的必然性与主体干预之间的矛盾,而是政治主体统一性构成中的建构性与先验规制之间的两难困境。
从满怀兴致地“发现”自发性的意义“超出”,到略带败兴地叨唠自发性的“受限”,表面上看,拉莫似乎生出了无穷的遗憾,平添了浓浓的忧愁,因为那个女革命家竟然在最丰收的地方造成了严重的饥馑,还有比这更让钟情于“所指超出能指”的后马克思主义骑士惆怅的吗?还有比这更让心系自主建构的“霸权接合实践”的后马克思主义旗手郁闷的吗?然而,这终究是拉莫的一种高超的书写策略:就在这艰涩难行之处,将要峰回路转,将要柳暗花明,将要妙笔生花,将要奏响他们对罗莎·卢森堡解读中最为“华彩”的乐章——即著名的“双重空场(a double void)”说。如果仅有意义的“超出”而没有意义的“限制”,就不可能形成“双重空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拉莫对罗莎·卢森堡进行的是“双重解读”——既解读出了意义的“剩余”,又要解读出了意义的“贫困”。
“双重空场”源于“限制”作用。在拉莫看来,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自发性逻辑所受的限制,首先表现在它起作用的范围被紧紧地“圈定”了——它只用于说明一种特权式的主体统一性,即阶级统一性,似乎不可能会有其他类型的主体统一。然而,之所以说自发性逻辑受到了限制,不仅仅是因为其运作领域的封闭性,在更重要的意涵上,是它起作用的方式受到了极大限制。这才是最根本的限制,正是这种根本限制导致了“双重空场”的出现。“自发性逻辑和必然性逻辑并没有作为两个具有各自独特性并且互有积极助益的原则而会合起来说明某种历史情景,相反,它们作为两个对立的逻辑,通过互相限制对方的作用而发挥各自的作用”[2] (P12)。偶然性逻辑与必然性逻辑终于会合了,然而却是一次尴尬的会合,宛若交汇的两股溪水,虽然共流在同一河道,却依然泾渭分明。而在拉莫眼中,它们不仅难以融合,而且还互相敌视和排斥。由于彼此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它们各自的独特性被这种消极的同一所吞噬。“自发性逻辑是一种象征逻辑,因为它恰恰是通过瓦解每一种原本的意义而发挥作用。必然性逻辑是一种原本意义上的逻辑,它通过固定所确立的意义而起作用——恰恰因为它们是必然的,所以这种由固定所确立的意义消除了任何偶然变异的可能”[2] (P12)。
必然性逻辑和自发性逻辑作为两个对立的原则不能融合在一起,只能“通过互相限制对方的作用而发挥各自的作用”——即每一方都是在完全取消对方之后才在这一已“绥靖”的区域发挥自己的作用——这表明,这两种逻辑互相“蚕食”的方式决定了两种逻辑的区域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换言之,两种逻辑之间的边界经常处于来回的移动之中,犹如夏至时太阳的直射点向北移到北回归线,冬至时则移到南回归线。这就是拉莫所谓“两种逻辑的关系是一种边界关系(a relation of frontiers)”的含义。正是这种“边界关系”导致了“双重空场”的出现。从必然性逻辑一方看,逻辑的双重性与可决定/不可决定的二元对立是一回事,必然性逻辑君临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不可决定”之事。而自发性逻辑所以冒了出来,就是因为必然性逻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发挥作用,一俟必然性逻辑产生预期的功效,自发性必当了无踪影。这是“可决定”之缺席,是必然性逻辑的空场——“一重空场”。
从自发性逻辑一方看,“历史必然性”所以要呈现,是要通过建立固定的意义来限制自发性逻辑的象征作用,它无视自发性的真正效果,强硬地把固定的意义加之于自发性逻辑,这种强加彻底否定了任何偶然性。换言之,必然性逻辑之所以要起作用是因为自发性逻辑起不到“名副其实”的统一作用。必然性逻辑是在自发性起不到“必要的”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的。必然性逻辑在自发性逻辑的“零作用区”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俨然是自发性逻辑的“缺陷”。“此一限制,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局限性(缺陷)”[2] (P13),因为在自发性所在之处,某种主体性一致似乎是建立起来了,但这还不能保证它一定就是阶级的统一性。因此,为了确保主体性与阶级性的重叠,必然性逻辑就要在自发性逻辑这里“现身”,以便使“不可决定”之事变成“可决定”之事。这是“不可决定”的隐身,是自发性逻辑的空场——“二重空场”。
拉莫认为,这两种逻辑互相限制的独特性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并非显而易见,“它之所以不是直接明显可见,是因为这两个明确且不同的解释原则被认为是汇合起来了”[2] (P13)。确实,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既有自发性逻辑,同时又有必然性逻辑,表面上这两种逻辑好像是汇聚了,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融通与会合。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性”导致了“双重空场”的出现,同时,也正是这种“二元性”表面的交汇使“双重空场”变得模糊起来,“然而,使这种空场不可见,并不等于填补了这一空场”[2] (P13)。
在拉莫看来,“第一重空场”是一种真正的空场,它实质上是必然性链条的开裂,是必然性逻辑的退场。但是,第二国际的正统派理论家们则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不相信必然性会面临崩溃。因此,他们或者根本看不到自发性,或者说不愿谈论自发性,或者认为自发性顶多表明必然性还没有发挥它一定要发挥的作用,质言之,即便承认自发性的存在,它也只能被视作必然性缺位的一种症候。然而,罗莎·卢森堡不回避和否认自发性,她率真地发出了关于自发性到场的第一声惊呼。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是无畏、睿智和严肃的。只有承认这一空白,才能为一种替代逻辑的确立廓清地基。
比较而言,“第二重空场”是一种伪空场,它是由篡夺或者说涂改而形成的。事实上,自发性已经建构了主体的统一性,但自发性辛苦取得的成果最后还是被归结在必然性的名下,自发性虽然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没有得到正当的定位;必然性其实并没有起到建构统一机制的作用,但它却堂而皇之地盗用了自发性的成果,这实质上是一种僭越和篡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把本来没有阶级特征的斗争或运动形式也赋予一种严格的阶级性质,从而错失了把自发性逻辑加以合法化和理论化的可能性。自发性逻辑作用被抹杀,这种空场成为自发性在场情况下的“隐身”,它象征性地“在”,但这种“在”最终被遮蔽和隐匿。因此,这种空场是在场的“非在场”,是一种更加晦暗不明的空场。只有标示出这一空场,才能恢复自发性的本来面目,才能使自发性从“蒙难”中解脱出来,才能名正言顺地光大自发性逻辑的积极成果。
在拉莫眼中,第二国际所有正统理论家都着力于遮掩空场,以使人们睁大眼睛也看不见有什么“空白”和“破绽”,从而继续维持必然性的神话,确证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不过,将空场隐藏和遮盖起来并不等于空场被填补,并不意味着空场的真正消失。掩饰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无能,是对暴露空场的回避,是可占据空场之物的缺乏,是制造“填料”的失败。如果没有空场,就不会有对空场的掩盖。而且,如果没有空场,也就不会有对空场的填补,这恰恰是拉莫探察空场的全部用意所在:空场的掩蔽之揭秘就是解构,空场的填补之完成就是建构。就此而论,空场对于拉莫来说,也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他们既需要解构的空场,同时也需要建构的空场。
罗莎·卢森堡天才地触碰到了自发性逻辑,旋即又束缚了自发性的“手脚”。而在拉莫看来,这是令人十分叹惋的。但无论如何,作为第二国际反修正主义的最英勇斗士,作为第二国际最激进的左派,作为坚守暴力革命立场始终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恐怕也只能如此。而拉莫却不肯仅仅如此,他们不愿像罗莎·卢森堡那样“保守”和“功亏一篑”,他们要尝试着移动必然性逻辑与自发性逻辑之间不稳定的边界,这就是为诺曼·杰拉斯所诟病的“边界实验(experiment of frontiers)”。
既然两种逻辑关系是一种“边界关系”,既然两种逻辑的“边界”不固定,而且“双重空场”就是边界稍稍移动的效应,那么,如果将这种移动扩大化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必然性逻辑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以至于两种逻辑不再表现出一种表面的交叉关系,而是必然性逻辑的全面覆盖,那么,“明摆着的抉择就在于:不是资本主义通过它的必然规律走向无产阶级化和危机,就是这些必然规律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产生作用”[2] (P13)。这种最大程度地扩大必然性逻辑的作用范围,其实等于完全取消了自发性逻辑的作用,这是低于罗莎·卢森堡水平的一种视界。因为,正是由于罗莎·卢森堡承认自发性的作用,她才能够把在资本主义社会平静的、“正常”的、议会时期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分离,特别是各种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看成是资本主义国家“人为的产物”。反过来说,在自发性起作用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故意制造的分裂就会顷刻瓦解,各种“分开的、完全独立的形式之间的人为界限也被一扫而光”[3] (P95)。可见,自发性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起着一种证伪主体立场必然分裂的重要作用。可是,如果一点也不承认自发性的作用,那么,主体立场的破碎与分散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呢?果真如此的话,岂不是不能有效地证伪主体立场分裂的虚而不实吗?岂不等于要承认主体立场分裂的永恒性吗?宁可守望着主体立场的分裂,也不肯承认在必然性逻辑之外能成就政治斗争的一致性的可能性,唯一的选择就是眼巴巴地等着终有一天必然性逻辑会奇迹般地突然起作用。要么是严格的统一性,要么是一盘散沙式的支离破碎,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拉莫看来,无非是“所有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观念所固有的零和博弈(the zero-sum game)”[2] (P13)。边界向着增大必然性领域的方向扩展所带来的这种“零和博弈”,显然是十分糟糕的结局,既然如此,移动还不如不移动。
顺便一提的是,诺曼·杰拉斯在讨伐拉莫的著名论文《后马克思主义?》中,曾指摘拉莫错误地“炮制”出了这个僵硬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拉莫在反批评中申辩说,他们并没有证明也绝对不打算承认这个“非此即彼”,相反,他们是用“归谬法”来揭露这种“非此即彼”的荒谬性:“我们的本意在于指出,除非马克思主义话语完全是决定论的(即是说,仅仅在我们实验的假想情况之下),否则杰拉斯所提及的那种刻板的选择就不会出现。与杰拉斯的指责正好相反,我们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描述为逃避这种‘非此即彼’的决定论逻辑的持续努力。”[4] (P95)从文本上看,拉莫的自我辩护无疑是成立的,因为拉莫所以要玩边界游戏,不是要证实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存有这种意义上的“非此即彼”,而在于说明,由于她引入了自发性逻辑,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非此即彼”。拉莫断定诺曼·杰拉斯何止是断章取义,简直就是“错误引证”。他们冷嘲热讽地写到,这个诺曼·杰拉斯的做法印证了一个特别的“非此即彼”:他“要么是不诚实,要么就是不负责任”[5] (P171)。
拉莫利用诺曼·杰拉斯在“细节”上的疏忽,狠狠地反抽了诺曼·杰拉斯一记耳光。但不管怎样说,诺曼·杰拉斯还是值得同情的,他在细节上犯了错误,并不等于他奋起反击拉莫全然没有道理,因为拉莫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歪曲了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原初意义,这一点在拉莫朝相反方向的移界游戏中清晰地表现了出来。如果自发性逻辑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以至于使必然性逻辑退出社会的地平线,那情形又会如何呢?拉莫曾欣然指出:
如果我们把边界推向相反的方向,推到政治主体的阶级性质失去其必然特征的地方,那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就完全不是虚幻的了:它是第三世界社会斗争所具有的多元决定的原创性形式。它构建出了与严格的阶级界线毫无关系的政治同一性;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无情地驱散了某种阶级接合的必然性质这一幻象;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崭新的斗争形式,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新的政治主体性形式超出社会和经济范畴的界线不断地出现。霸权概念正好出现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受到分裂的经验以及不同斗争和主体立场之间接合的不确定性所支配。它将在见证了必然性范畴退出社会地平线的政治话语中提供出一种社会主义答案[2] (P13)。
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发性逻辑的作用范围,其实就等于彻底取消了对自发性逻辑的限制,给予自发性这个“无名之师”一个正规编制,并任其占领所能够占领的地盘。拉莫自认为,这种扩展完全符合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所蕴涵的建构主义“本性”,是对这一本性的释放与张扬,是高于罗莎·卢森堡水平的一种视界。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自发性虽然被承认和肯定,但不仅空间狭小,而且如螟蛉一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最终却被误以为是“蜾蠃”的义子。罗莎·卢森堡一边大声疾呼“行动在先”,为自发性的出场鸣锣开道,一边又不容置疑地引入必然性逻辑来“支撑门面”,把自发性的所作所为视为必然性的“表达”,从而使她陷入“两难困境”。在拉莫看来,不扩展边界要陷入“两难困境”,而扩展必然性逻辑的范围却会更糟,所以,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扩展自发性的边界,将它推到极限,推到必然性逻辑完全消失的地方。唯有如此,自发性逻辑的独自的构成性作用才不至于被遮蔽,才能充分展示它特有的风采,才可能在必然性崩溃之下重树左派政治斗争的信心。如果说上一次边界移动实验是通过把必然性的作用推到极端以揭露它的荒谬性;那么,这一次则是将自发性逻辑复归其实然状态,从而展示它原本可能达到的功效。如果说上一次实验导致“非此即彼”的僵硬对立是一种虚幻;那么,这一次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则是不断出现的“原创性形式”。如果说上一次的移界游戏是令人沮丧的零和博弈;那么,这一次则是硕果累累的喜人丰收。从拉莫轻快的笔调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对于眼前“景象”的欢欣与畅意,不难感受到他们对于偶然性的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动局面的嘉许与赞誉,不难感受到他们对政治主体统一性的崭新建构态的“激进想象”与殷殷寄托。
可以看到,也正是在对这一实验结果的鉴赏性描述中,拉莫自然而然地引入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这一概念出现的领域只能是偶然性充分起作用的领域,即是说,偶然逻辑的边界向外极端扩展是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呈现的必要条件。拉莫假设:如果罗莎·卢森堡进行如此扩展,那么,她就会得到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而事实上,罗莎·卢森堡根本就没有进行如此“扩展”,因为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做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是拉莫自己执意要做如此“扩展”。因为他们乐于将自己归属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名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与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显然具有很大的区别,一如斯图亚特西姆所评价的那样:拉莫“被自发性概念所吸引,这一概念形成了他们的‘激进民主政治’的某种模型;区别是:拉克劳和莫菲看到没有必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加工它,或者一种设想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为这种自发性所必需。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倾向性在如下意义上是明显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连接被割断,而使霸权以一种自由无羁的方式运作为目标,在此一方式下,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之其上的那种强制。”[6] (P14—15)
罗莎·卢森堡无疑是第二国际的激进左派,不过,在拉莫看来,她还远远不够“激进”——因为她没有将自发性逻辑的范围加以“激进地”扩展。从所谓的“边界实验”中,我们可以翻然悟出拉莫所谓的“激进民主”中的“激进”并非意味着革命立场的“激进”,而只是表示对偶然性的“激进”态度:“要接受根本的偶然性”[5] (P171)。拉莫疯狂地把自发性逻辑的边界无限制地扩展,这诚然是一种极端,一种激进主义。然而,这种激进主义在最大程度地消解罗莎·卢森堡的“教条式的僵化(the dogmatic rigidity)”的同时[2] (P11),也最大程度地远离了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激进主义诉求。套用齐泽克的说法,这俨然是一种反激进的激进主义。
拉莫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阐释建立在两个基本事实之上:一是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的热切关注与积极肯定;二是罗莎·卢森堡承认,在自发性这里最终可以达成主体的统一性。从这两方面看,拉莫与罗莎·卢森堡无疑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两方面构成了拉莫与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共同“底面”——没有这种重叠共识,拉莫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就丧失了起码的学理依据,就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就成了彻头彻尾地“顺嘴胡诌”。如果说,拉莫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尚有某种合法性,那么,这种合法恰恰恰是基于拉莫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正当性和历史担负的确证。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拉莫的理论努力并非要真正回到罗莎·卢森堡那里去,他们不会满足于复原自发性概念的历史本真性,严格说来,他们也无意于从事这种复原。因为,在对解构立场的坚守之下,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绝对固定不变的意义,根本就不相信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稳定与对称的关系。既然他们倡导“所指超出能指”,那么,自发性这一能指被打破、被超出也就是题中之义了;既然他们倾心于意义的增生与流动,那么,自发性概念的意义溢出罗莎·卢森堡所设定的边界也正符合他们的支撑性观念——“任何既有的话语都不可能完成最后的缝合”[2] (P111)。拉莫认为,他们的这种观念与那些激烈消解在场形而上学的当代思潮——分析哲学中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现象学中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后结构主义对符号的批判——是完全契合的,正缘乎此,他们尤其推崇德里达对意义核心和先验性所指的颠覆与解构:“先验性所指的不在场无限扩展了意义的领域与作用”[2] (P112)。
在拉莫看来,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先验性体现在两个节点上:其一是,自发性源于旨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之中,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取得政权始终是革命的灵魂;其二是,自发性的作用在于达成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革命主体的统一只能是阶级统一。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由于这两点,罗莎·卢森堡才是罗莎·卢森堡。消除这两种意义的先验性所达到的结果自然就是:后革命的自发性概念和非阶级的主体统一性。就前者而言,是实现了自发性的领域置换;就后者而言,是实现了自发性的功能替代。抛弃了罗莎·卢森堡最为重要的东西,当然也就谈不上忠于罗莎·卢森堡。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在《康德书》中对康德认识论所作的存在论分析视为是对康德的背离,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拉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本义。从革命的自发性到后革命的自发性,从严格的阶级统一到超出阶级限制的非阶级统一,这是罗莎·卢森堡根本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也根本不是罗莎·卢森堡所想要的东西。拉莫视为罗莎·卢森堡的缺陷的东西,拉莫认为罗莎·卢森堡给自发性设定的严格限制,恰恰是罗莎·卢森堡不愿丢开,也从未想要丢开的东西。对罗莎·卢森堡而言的客观历史规律,对拉莫来说却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教条;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是必须坚守的原则,对拉莫来说,却不过是要抛弃的局限性。罗莎·卢森堡宁愿牺牲性命也“咬定不放”的东西,拉莫竟轻松地、毫不痛惜地放弃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曼·杰拉斯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气头上的诺曼·杰拉斯也说了一些错话,有时甚至发错了脾气。他认为,拉莫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解读是有意栽赃陷害,旨在显示“罗莎·卢森堡关于群众罢工的真正观念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不一致的”[1] (P61),其“罪恶意图”在于由此暗示: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这里潜伏着后马克思主义的强烈萌动,或者说,从罗莎·卢森堡这里可以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实际上,诺曼·杰拉斯的这种忧虑完全是多余的。拉莫将他们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解读置于全书的开端处,并不是径直把罗莎·卢森堡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按拉莫的看法,“在把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还原论的视域之内,接合意义上的霸权完全是不可思议的”[2] (P68),而罗莎·卢森堡并没有脱出这个视域。可以断定的是,在拉莫的心目中,罗莎·卢森堡并不是一个在某些地方越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界线的人,她不像葛兰西那样能被看成是一个“分水岭”,她的自发性概念也不是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的雏形。
但是,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与霸权概念又存在着相关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可贯通性。否则,拉莫绝不会以解读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为起始。然而,这种相关性和贯通性却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它晦暗不明、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只有借助“解构式地运作”,通过拉莫如此这般地“解读”,它才能一显尊容,露出“庐山真面目”。这颇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从不言之中、从有意无意的掩饰之中、从一个个的闪避之中诊断出深藏的原痛与创伤。实际上,拉莫原本就没有想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这里侥幸地挖出一个“大金矿”,他们十分清楚,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拱心石依然是“历史必然性”。他们只是想探测“必然性之石”的裂缝、断层、褶皱与罅隙,想通过“历史必然性”这面破碎的镜子“折射出”新的社会逻辑。新的社会逻辑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还没有正式出现,它只是拉莫眼中的镜像。此时,不仅霸权没有真正出场,就连霸权的逻辑也只是以异化的形式显现。
拉莫以罗莎·卢森堡为开端,不是因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罗莎·卢森堡最早使用霸权概念,而是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必然性逻辑与偶然性逻辑以戏剧化的方式遭遇了。这两种逻辑的突然碰撞,并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结果。唯一吸引拉莫的东西,就是碰撞后留下的那道裂痕,即必然性的创口,也是偶然性发出声响的通道。值得指出的是,在拉莫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解读上,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的态度全然不像诺曼·杰拉斯那样激烈拒斥和怒不可遏,而是表现出一种十分平和与宽容的姿态。西姆倒不在意拉莫是否歪曲了罗莎·卢森堡的本义,而是看重他们的阐发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否与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某些方面契合,是否在理论视界的转换之中实现了“旧义”在改变了的背景之下的诠释学重塑。西姆也认为,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自发性概念所蕴涵的偶然性逻辑暗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卢森堡是为数不多的直面偶然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的一个,并且我们发现她以一种比其他人更严峻的姿态在思考这种不连续性。一般讲来,偶然性作为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因素被古典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允许偶然性进入社会均衡因素之中就是暗示:马克思主义小于(达不到)一个思想总体,并且它的运作逻辑在某种有意义的方式下是有缺陷的。偶然性甚至使问题进一步变得晦暗不明,因为它暗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机器所施加的控制的缺乏,或者,更令人忧虑重重的是这种控制的无能[6] (P14)。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拉莫以罗莎·卢森堡为开端的原因所在:其一,罗莎·卢森堡通过自发性概念天才地触碰到了霸权逻辑,尽管这一逻辑没有得到如拉莫所想象的那种展开,但是,在拉莫眼中,它毕竟是卢森堡思想天空中闪电般骤亮的一瞬。其二,自发性的确认及其人为限制,形成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而“双重空场”更是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以鲜明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对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典范性意义。按拉莫之见,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几乎所有理论家都遭遇到了这个问题,尤以罗莎·卢森堡最为突出。其三,在罗莎·卢森堡这里,霸权逻辑并没有填补起由于必然性链条的断裂而形成的空场,此时还谈不上霸权概念的真正出场。因此,所谓的概念谱系学只能是一种“隐匿的考古学”,它的任务只是揭示霸权逻辑被遮蔽和抑制的苦难历程。在罗莎·卢森堡这里所发生的,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那里,因此,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分析,具有一种统领性的作用。
可以说,拉莫把罗莎·卢森堡置于开端处,既不是为了表明罗莎·卢森堡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不是为了表明他们要步罗莎·卢森堡之后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拉莫非常明白,由于罗莎·卢森堡拒不放弃某些东西,所以她还不够资格被称作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由于拉莫抛弃了太多的东西,所以他们担心自己是否还有资格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拉莫将罗莎·卢森堡置于开端处,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愿景: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那里发现一点后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而让坚定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拉莫那里保留些许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如此一来,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但总归还惦念着马克思主义,或许正如西姆所说的,像拉莫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还存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怀旧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