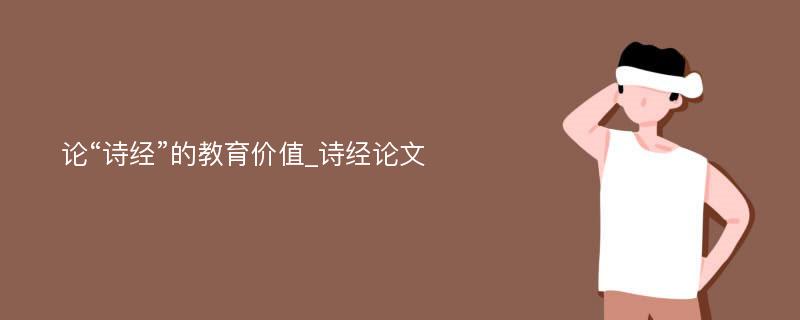
《诗经》教育价值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10)03-0054-05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同时也是教科书,从先秦到清末被士人讽诵研读。《诗经》所具有的教育价值是其两千年被当作官方教材的基础。
一、《诗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价值
(一)先秦时期的全面修养教育价值
先秦时期,《诗》是瞽矇学习诗乐演奏的教材,是国子成才的教材,也是孔门弟子的修身教材,具有全面修养的教育价值。
国子学习《诗》是基于一种实用的态度和目的,它在人生修养上具有“导广显德”的价值,也是外交礼仪的教科书。《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使士亹辅导太子箴,士亹请教申叔时,申叔时为他开列了包括《诗》在内的一串教课目录单,并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
《诗》也是周代贵族子弟的重要学习科目。在《礼记·内则》中规定了国子的学习课程,其言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
作为“六经”教科书之一,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诗》是人生修养的第一步。孔子对《诗》之教育功能的经典论述是:“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强调了学习《诗》的多方面功能,包括人的个性品质、社会性和知识能力的发展。在孔子看来,《诗》具有全面的教育价值:人生的、美学的、礼仪的、交际的、知识的,是全面的人生修养教科书。
(二)汉唐时期的政治教化价值
汉代的《诗经》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价值。闻一多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①。
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诗》上升为“经”,并被认为是蕴含着圣人微言大义的作品,具有政治教化的重要作用。
汉昭帝时,昌邑王淫乱暴戾,郎中令龚遂谏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悦。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顾王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汉书·武五子传》)“人事浃,王道备”是独尊儒术的汉代统治集团对《诗经》的理解。将“三百五篇”当谏书,所以释《诗》教《诗》尽用美刺,通过理解《诗》中的美刺来达到统一人心的目的。
汉代教《诗》重政治讽谏。郑玄在《诗谱序》指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董仲舒认为在位者用六经来教化民众,六经各具不同的作用:“《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春秋繁露·玉杯》)。
唐朝孔颖达在主持《毛诗正义》编撰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汉儒的诗教观,同时也有所发展。在《毛诗正义序》中,孔颖达表示编撰《毛诗正义》的目的是“对扬圣范,垂训幼蒙”,即阐发古圣先贤的经文,对民众进行教化。孔颖达进一步发展了汉代的政治教化价值:“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若政运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诗歌是人情感的自然表现,所以具有感发人心、教化民众的作用:“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毛诗正义序》)。因此,“《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使开悟也”(《尚书正义》卷三)。就是说,学习《诗经》可以生长人的志意,使人开悟,从而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同时调和人的性情。
(三)宋以后的伦理道德教化价值
宋明理学重视人的自我修养,将《诗经》看作伦理道德教化的教科书,因此《诗》教重内心感化,重视对人情感的作用。朱熹开始用《诗》治心,认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读之“使人法其善,戒其恶”(《诗集传·序》)。在学《诗》上,他重视对《诗》的沉潜讽咏,强调对《诗》的个体体认,通过体认《诗》中之理,达到影响人的伦理道德意识的作用。
朱熹认为《诗》的产生是情感作用的结果。“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诗集传·序》)人感物而动,有欲而思,思化为言,言所不能尽者,借《诗》来表达。诗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与人的思想最接近,具有感人心性的教化作用。“《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诗》是圣人所感,可以教化民众。“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同上)。朱熹重视《诗》对人感情的作用,进而主张对人实施伦理道德教化。
(四)明清时期《诗经》教育价值的异化
在《诗经》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当和选士制度相结合之后,其价值就逐渐偏离了教化与修养的方向,而成为选拔人才与求取功名利禄的工具。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形式来考试《诗经》,这是一种程式化的文体,有多项严格要求,需要在熟练掌握《诗经》经注的基础上体会理解,加以发挥,组织成篇。所以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诗经》学习就以写《诗经》八股文为主。由于功名利禄的吸引,很多人完全为应科举而学习《诗经》,从而出现了很多以应试为目的的《诗经》著述。
明清科举考试时期,《诗经》逐渐异化为单纯的“场屋之资”,在俗儒士子眼里,其获取功名的价值超过了人生修养的价值。这显然是《诗经》教育价值的一种异化。
从先秦时期的全面修养价值,汉唐时期的政治教化价值,到宋以后的伦理教化价值,《诗经》的教育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正是这种随时代而变的教育价值,适应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各个时期都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
(五)现代的文学教育价值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古史辨派将《诗经》拉下了儒家经典的宝座。胡适说:“(《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②。自此之后,《诗经》的教育多定位于文学教育中的一部分——诗歌教育。
诗歌具有的情感性、易读性、趣味性、艺术性等特点,使《诗经》具有了广泛的教育价值。诗是诗人感情冲动的结果,是灵感的产物,是语言的精华,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更能感发人心,引发人美好的情感。《诗经》的语言整齐押韵,朗朗上口,读起来给人以快感,学习这种诗的语言,可以增加我们对汉语的敏感性,感受语言之美。同时,《诗经》具有丰富的文学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如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意象和氛围的使用,写真的艺术表现方式,均可以使学《诗》者得到熏陶修养。
二、《诗经》不变的教育价值——温柔敦厚
随着历史的发展,《诗经》的教育价值经历了多次转变:从全面修养到政治教化,再到伦理道德教育,一直到现代的文学教育。在变化的同时,《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又具有历两千年而不变的特征,从外在形态来说,即为三百零五首诗的文本。分析其内在原因,在于这三百零五首诗所蕴涵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功能。通过《诗》的教化功能使人的精神气质变得“温柔敦厚”,塑造了中国人趋于平和、宁静、含蓄、内向的心理气质,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
《礼记·经解》中记录了孔子对《诗》的教化功能的概括: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孔颖达对“温柔敦厚”的解释为:“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礼记正义》卷五十)此处“颜色温润”、“情性和柔”,正是对人的表情和性格的描述。孔氏认为《诗》的特点是“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而“温柔敦厚”是指民众接受了《诗》的教育之后的精神状态。
但是,如果把握不好《诗》教的度,也会出现问题,这就是“《诗》之失愚”。郑玄对“失”的解释为“失谓不能节其教者也”,指教化不当的情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诗》教不节制,就会超过“温柔敦厚”而变得“愚”。《诗》教的最佳状态是“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郑玄解释说:“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孔颖达疏解此句曰:“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礼记正义》卷五十)。在这里,孔颖达明确指出,以《诗》“化民”、“教民”,也就是讲《诗》的教育,即“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
当《诗》与揖让周旋、进退如仪的礼乐活动密切配合,熏陶于其中的子弟就易于养成温良恭俭让的品性。儒家《诗》教的目的,就是通过教化,使民众都形成“温柔敦厚”的性格,在社会上形成“温柔敦厚”的民风民俗。
“温柔敦厚”是一种温润如玉的君子风度。《秦风·小戎》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温柔敦厚”代表了一种君子风范,有像玉一样温润含蓄的气象,含蕴无穷而又温文尔雅,颜色温润而又情性和柔。同时“温柔敦厚”又被儒家解释为一种中和的礼乐精神。《诗》教中蕴涵着礼乐精神,《礼记·乐记》说:“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朱自清对“温柔敦厚”作了深刻的分析:“‘温柔敦厚’是‘和’,是‘亲’,也是‘节’,是‘敬’,也是‘适’,是‘中’。这代表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儒家重中道,就是继承这种传统思想”③。
《诗经》始于《周南》终于《商颂》,体现了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其“温柔敦厚”的教育价值是超越时空的。《诗经》两千多年中一直作为儒家经典进行传授,其中包含了恒常不变的精神,适应了不同历史时代的背景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④。
注释:
①《闻一多全集》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6页。
②胡适:《谈谈〈诗经〉》,《古史辨》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页。
③朱自清:《诗言志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④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序》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