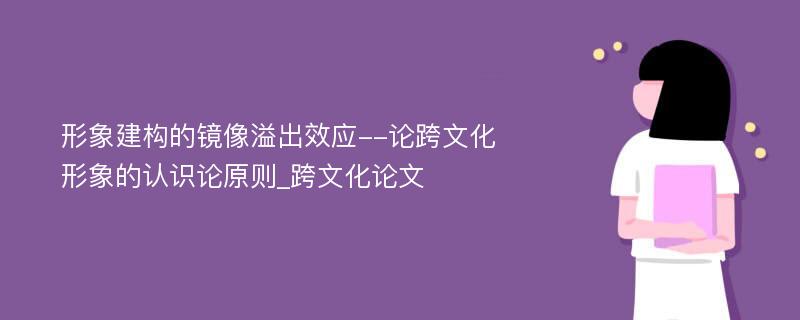
形象建构的“镜像—溢出”效应——论跨文化形象学的认识论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认识论论文,镜像论文,效应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3)04-0011-06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异域“中国形象”建构,是周宁教授过去十余年研究“中国形象”的一贯性学术努力的成果。本文以他的《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为例,探讨其有关异域“中国形象”建构之研究的一些学理性问题,从康德的知性范畴论出发,在认识论高度上总结“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中所体现的八条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涉及西方(主要是西欧与北美)的“中国形象”研究,同时也涉及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流动的问题研究。
一、形象建构的“镜像”效应: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认识论原则
一国在自身的文化和话语体系中建构他国的“形象”,这种努力目的并不在于满足求知欲或者科学探索的需求,而在于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本国文化,在比较当中看到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象建构的“镜像”效应(the looking-glass effect)。①对于西方而言,从1250年开始,它们就不断在想象当中与中国“邂逅”。它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其说是为了从知识增量的角度去描绘事实,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它们对自身的观照。针对该效应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借鉴康德的知性范畴论,[1]从判断的量、质、关系、模态这四个角度来审视与其相关的原则。
第一条原则——“想象动机污染”(the principle of pollution by imaginary motivation):所有有关他国形象在本国话语体系当中的表达,都受到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该国语境中占主流地位的想象动机的污染,这种动机既可以是意识形态式的,也可以是乌托邦式的。
此处所指的想象动机,其实指涉的是周宁对曼海姆所提出的一对概念的阐发。在曼海姆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有一个想象性的内在逻辑起点,它要么是意识形态式的,要么是乌托邦式的,[2]其区别在于想象动机与现实秩序之间的关系:如果它是辩护的、去肯定现实秩序,那就是“意识形态”;如果是颠覆的、去否定现实秩序,则可称之为“乌托邦”。
“想象动机”乃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出发点。一国把他国作为一个“他者”在文化上进行建构,这种建构努力本身应当从“话语社会学”或者“知识权力学”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从方法的层面上来讲,这要求我们既要关注单个具体文本的内容,又要在不同文本之间建立一种整体性的关联,“发现某种知识与想象类型以及由不同类型构成的、具有断裂、转型与连续性的话语谱系”。[3]这样的一种“话语谱系”,就是一种能够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作者的不同文本都整合在一起的“超文本理念”(ideal beyond text),让我们“发现某种知识与想象类型”,并构建一个整体、连贯的分析视角。而进行这种整体性构建的目的,是在于揭示这种“知识与想象类型”是一种渗透着权力的知识体系和话语类型。其间,知识借由想象引导,而想象又和权力勾连在一起。[4]如此一来,不同文本在同时代的观念体系中,一定是首先服从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想象动机;正是在受到动机污染的前提下,这些文本才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共同建构出某个关于“文化他者”的形象。因此,这第一条原则,主要是从方法论上为周宁的整个研究定下基调,限定他看问题的方式、分析的角度和理论的走向。
第二条原则——“事实无涉”(the principle of non-relevance to facticity):一国对于他国的形象建构,既然都只是被想象动机污染的“主观”描述,那么,这些描述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对他国的“客观”再现和“精确”描述。因此,这种形象建构与事实无涉。
既然每种“想象”都有其原初的“动机”,那么,我们可以推论,被这种“想象动机”污染的“形象建构”,其本身是否符合事实,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都已经变得不相关了(irrelevant);相关的是要符合这种动机。周宁所做的中国形象研究,其理论假设是“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5]这种“文化他者”,并不是从符合论的前提出发来进行的一种假设性建构。
显然,西方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文化他者”而对之进行建构的过程,本身首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这个建构“符合”事实或者中国存在这一“本体”,而是首先要服务于“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6]周宁一再地表明,他并不关注这些异域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是否反映了事实,他关注的是这些中国形象作为“他者”而存在于主体关于自我意识的思考当中所具有的相对意义与价值。按照这种观点,主体之意识,是以意识到他者之存在为基础的,所以“我思故我在”(ipso factum,ipso cognitum)应当改写为“他者故我在”(ipso factum,ipso alterum)。因此,周宁在此并非从事实层面上来关注这些中国形象是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恰恰相反,他首先就意识到,社会的现实是外在于我们知识之外的“自在之物”(Ding an Icht),只要它进入到思想层面,只要我们通过语言和思维来对其进行表达(representation)与描述(description),那么,从那个被表达的时刻开始,它就蜕化成携带着自我之想象动机烙印的“畸形的小孩”。[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宁之所以首先从“价值”的层面上进入跨文化中国形象学这样的一个场域,其理论承诺(theoretical commitment)带有鲜明的“事实无涉”之特征。
第三条原则——想象动机“具体情境”(the principle of contextual contingencies):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于他国的形象建构既可能具备单一性,也可能具备多样性,可以是单一的“乌托邦式”或者“意识形态式”想象,也可以两者兼有,其情况要视具体社会—历史情境而定。
对他者的想象动机有两个: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在周宁看来,这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其地位取决于上升集团与现有秩序之间一致或者冲突的关系。[8]当这两种动机在人类生活当中具体表现出来之时,存在四种不同的组合情况:头两种情况是“排他式”(exclusive)或者“独占式”(dominating)的,即在某时某地,只存在某种动机,另外的动机则隐退或者潜伏;后两种情况则是“包容式”(inclusive)或者“兼容式”(compatible)的,即两者可以互相包容,具体哪一方占上风或者两者的权重比例则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意识形态为主、乌托邦为辅”或者反之,或者两者相对均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状态,达致了一种暂时性的平衡或妥协(modus vivendi)。
纵观历史,欧洲对中国的最初想象是“大汗的大陆”,这表现的是欧洲当时萌芽的世俗资本主义精神,在这种想象当中,欧洲寄托了一种“对商业财富、王权统一、感性奢侈的生活风格的向往”。[9]随着开明君主专制主义理想的出现,欧洲则在制度的层面上来想象中国。欧洲的哲人构建了一个“孔教乌托邦”,借此表达对欧洲君主专制的失望、对限制君权的现代立宪主义的展望,和对一场摧枯拉朽的大革命的期望。在125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乌托邦式想象”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到了启蒙时代,则是“意识形态式想象”时代的来临。西方需要一个“停滞的帝国”作为其进步大叙事的“他者”,此时的中国,被意识形态化为一个“野蛮、落后和东方专制”的帝国。[10]
相比于文艺复兴前后和启蒙时代的这种“单一化”想象方式,在后启蒙时代,则更多的出现一种“乌托邦—意识形态”互相交织的局面。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虽然在大部分时间中“意识形态式想象”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乌托邦式想象”并未完全消失,在浪漫主义时代,又变成了“审美艺术期望中的、带有浓厚‘中国情调’的审美乌托邦”。相比于这一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转型,“孔教乌托邦”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中叶,是在左翼文化的批判浪潮中开始的。此时的中国,变成了左翼运动理想的“红色圣地”。[11]在周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想象方式的强弱关系和组合情形。
第四条原则——“主观置信”(the principle of subjectiv berredung):某一个历史时期一国对他国的形象建构,尽管与事实无涉,都被接受这一建构的个体或群体认为是真实的。这样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表达,置换了现实中的那个“他者”,唯有被建构出来的“形象”才是真实的。
结合上述的三条原则,既然一种形象建构本身是受到“想象动机污染”的,与事实无涉,且符合不同组合的想象动机“具体情境”,那么,可以推论这种“中国形象”的有效性必定是只能限定在建构者自身的领域之内,换言之,这样的一种建构,只对西方而言是有效的。如果这种建构拿到中国,不一定会获得当地知识界和普通老百姓的认可。这样一种区分,可以借助韦伯的一个概念来阐明。在韦伯看来,存在一个“主观”言之正确和“客观”言之正确的区分,前者针对宗教/信念,后者针对科学探索;前者指既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证伪的一些信念;后者指运用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力求探索客观的知识[12]。我们在这里运用到的“主观置信”,指的就是韦伯谈到的“主观”言之正确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无关乎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假”,而只关乎认识论意义上的“主观置信”,即信念持有者本身只要在主观上认为自己的信念是“真”的,那么,该信念就是“真”的。这个“主观置信”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他对不同的“信念”做了区分,一种是“确信”,是某件事对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效;而另一种“置信”,则只是“在主观的特殊形状中有其根据”,并不是对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因此,“置信”不符合康德的“客观”标准,而只能是一种主观上的“幻相”。[13]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形象上的“主观置信”,和康德的“置信”存在一个根本区别。在康德看来,虽然这种“主观置信”具有私人有效性,但是其本身是不能传递的,即这种观念没有办法在有理性的人之间进行传播。相比之下,周宁笔下的跨文化形象学,却是要为我们揭示,这样一种仅仅在主观上有效的“形象建构”,是如何借助霸权、技术和网络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传递、传播和流动。这就是我们在下面一节要讨论的内容。
二、形象建构的“溢出”效应:西方“中国形象”跨国界流动的认识论原则
如果西方的“中国形象”建构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作为它们现代性、自我和优越感的一个“他者确证”(other-corroboration)②,那么这可能会是一种无害或者最低伤害(minimum hazard)的行为。因为,这仅仅涉及西方“自我”本身,是一个西方“自我”在建构了一个邪恶、落后、愚昧的中国“他者”之后的一种“精神胜利法”(ideational triumphalism)。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它与事实无涉,那么,无论是西方将中国建构成一个人见人爱的白马王子,还是一条亟待屠杀的恶龙,这些形象都只限定在西方自身知识体系之内。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为西方与之搏斗的对象,而且,也仅仅在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之内,西方才赋予了这些形象生命与存在。③但问题的关键是,当西方赋予了这种形象建构以生命和存在之后,这种形象就具有了它自己的行动逻辑,它借助权力的联系、技术的力量和传播的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影响和型塑着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这样的一种效应,我们可以称之为“溢出”效应(the spill-over effect)④,即形象建构突破了其母体文化的限制,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叠加和整合效应,最终形成一张全球性的形象建构网络。
这样的一种“全球化”视角下的“溢出”效应,是周宁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一个突破和延伸。“东方主义”讲述的是西方如何去构建“他者”,来对自我进行确证。这种“东方主义”其实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涉及“主观有效性”(subjective validity),即只要对于观念持有者本身而言具有有效性即可。在加入“全球化”的视角之后,周宁为这种“东方主义”开放出了一种扎根西方但同时又是超越西方、形象建构跨国界进行流动(a transborder communication of images)的“溢出”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方的“中国形象建构”就不再仅仅具有地缘限定(territorial particularity)的特征,而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这种现象的核心在于,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所生产的“中国形象”不仅仅是在西方国家内通过媒体和学术被大众以及知识界消费,同时,还借助大众传媒的新技术向全球扩散,形成了一张“中国形象”的全球网络。
第五条原则——“西方建构之霸权”(the principle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construct):所有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建构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中国形象”建构的影响。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主要择取了三个国家——俄罗斯、日本和印度,来研究这一西方“中国形象”如何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在这三个国家中,它们本国的“中国形象”都无一例外地以西方建构为摹本。以俄罗斯为例,其中国形象的知识与价值都来自西方,俄罗斯全盘接受了西方建构出来的“中国形象”[14];在印度,因为政治上与中国相互竞争的需要和文化上亲美的倾向,印度也基本上是根据西方建构的“中国形象”来看中国;日本的“脱亚入欧”,这个“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与“欧洲”对立面的“野蛮、落后、专制”的代名词,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则自然成为“亚洲”的换喻,所谓“脱亚”就是“脱华”。[15]因此,在日本,其中国形象同样脱胎于西方的建构。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在非西方国家建构“中国形象”的背后,潜伏着“西方建构之霸权”的幽灵,它宰制和主导了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想象和形象建构。
第六条原则——“形象差序”(the principle of a differential mode of image approximation/distanciation):所有非西方国家中的“中国形象”,都是对西方性的靠拢和对东方性的排斥。这些“中国形象”要确认的是本国与西方的距离有多近、与中国的距离有多远,肯定本国当中贴近西方、可被称之为“现代”的那些元素,否定那些贴近中国、可被称之为“传统”或者“落后”的元素。
这样的一种“形象差序”实际上是和上述第五条原则中的西方霸权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差序”之所以成为所有非西方国家都逃避不了的宿命,因为西方现代性把所有国家都纳入了它自己建构起来的世界历史体系当中。所有的国家都似乎必须按照西方设定的“发展道路”来前进,实现“形象差序”的方式,则是通过“自我东方化”。该概念包含了一对相反但是相辅相成的面相,即“自我西方化”与“自我去东方化”,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加入一个东方国家之间的“彼此东方化”,这正好对应于康德所提出来的“正、反、合”的范畴体系构想。以印度为例,印度在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念秩序中同时在“去东方化”(按照西方的尺度来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西方化”(以西方为范例来进行文化改造)。同时,这一过程还包含了“东方”内部国家的“彼此东方化”——互相比较谁更“东方”、谁更“西方”,从而确定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和否弃。[17]尽管周宁没有严格地按照康德的“正、反、合”来剖析“东方化”的三个维度,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把“自我西方化”、“自我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这三个元素糅合在一起,集中进行了论述。而且,这不仅仅是印度单个国家的问题,其他亚洲国家也会出现类似的行为。[18]
第七条原则——“合谋”(the principle of collusion):非西方国家对西方“中国形象”建构的接受是缺乏反思的,忽略自身在智识上进行批判、甄别和建构的必要性。这样的一种“前反思接受”,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事实上构成了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中国形象”问题上的“合谋”。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形象”就是西方霸权一厢情愿的产物,好像光靠武力、胁迫(coercion)和暴力就可以把这种形象深入人心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恰恰相反,西方霸权要想真正在地方具备有效性,并广为人接受,还需要当地文化和知识界的主动接纳。上一条原则当中的“自我西方化”、“自我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其实已经从规范的层面上限定了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和中国的态度。既然非西方国家唯西方马首是瞻,那么,“爱/恨屋及乌”就变成了一种自然的选择态度。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态度,而在于这种态度带来的格局,即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进行有意或者无意的“合谋”(collusion),实现了“中国形象”被刻板化,并在非西方国家当中有效、迅速地传播。比如,在俄罗斯,其思想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内容总是在复述西方的论述,而忽略那个“领土之邦”的中国[19]。这种“不认真”和“简单复制西方表述”实际上是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在传播“中国形象”过程当中的通病。它既表现了非西方国家在面对西方“舶来品”之时那种缺乏批判和甄别的“移植品格”(transplant quality)[20],同时也显示了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合谋。
第八条原则——“多元排除”(the principle of plurality exclusion):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对“中国形象”建构的霸权性力量,加上非西方国家的“合谋”,形成了一种“中国形象”本质化的全球性格局。这种格局排斥了多元“中国形象”建构的可能性,消除了人们对于一个可能不同于西方“中国形象”的中国的想象力,并且扼杀了所有旨在挑战西方“中国形象”建构的努力。
从上述的几条原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性构筑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象话语体系,在该体系中,西方建构的“中国形象”占据了霸权的地位,在其他的国家内得以传递,使得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必须按照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体系来审视自身的“东方性”,看清自身的“位置”,并明确自身前进到“两方性”的距离和方向。这样一个“整体性”的体系,以“世界历史”为主、“中国形象”为辅,既表达了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捍卫,同时也“污名化”中国,将其作为西方的“大他者”加以“陷害”和“诬陷”。这样的一种“整体性”体系,其本身排斥了多元,把我们对现代性、世界历史和中国形象的想象,都限制在一个狭隘的框架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周宁注意到,一方面,虽然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圈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异,但同时,这些中国形象又“在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表现出的越来越强烈的同一化倾向”。[21]
在笔者看来,“跨文化形象学”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它为我们审视形象建构开放出了一个既针对表达又针对传播的视角,笔者称之为形象建构的“镜像—溢出”效应,其内容包含了八条各自不同但在逻辑上层层递进的原则。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建构“中国形象”当中所包含的这种“镜像—溢出”效应,我们才能从批判和警醒的角度对这种形象建构进行一个更为深入的考察和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形象学本身不仅仅只是为了批判;恰恰相反,它为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和建构开辟了空间。
收稿日期:2013-05-05
注释:
①“镜像”效应一词主要是受库利的启发,参见Charles Horton Cooley,Human Nature and Social Order,NY: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2,p.64,136,152,198。
②本概念相对于“自我确证”(serf-corroboration)而言。
③这一看法乃是受克尔凯郭尔的启发,他认为生活与小说当中都充满了各种形象,正是我们通过阅读或者经历、通过精神上的各种“搏斗”,才赋予了这些形象以生命和存在。见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卷),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④这一概念源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功能主义学派,由该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创立。参见E.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London,Stevens,1958,p.283; L.N.Lindberg,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10。相关理论评述,参见Xi Lin,"Neofunctionalism Revisited",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2(3)。
标签:跨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认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镜像理论论文; 知识体系论文; 他者论文; 周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