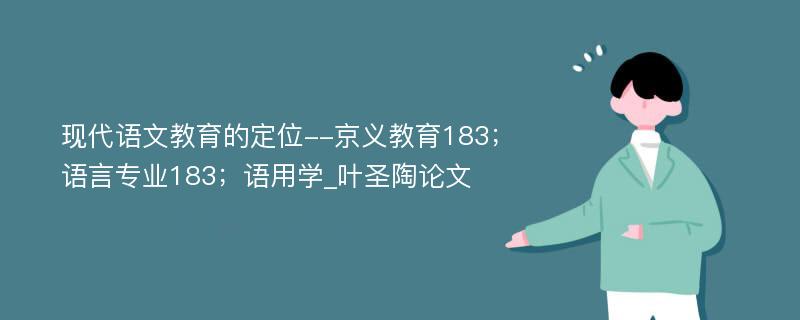
现代语文教育的定位问题——经义教育#183;语言专门化#183;语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义论文,语文教育论文,语言论文,语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德格尔说:“历史学的课题既不是仅只演历一次之事,也非漂游于其上的普遍的东西,而是实际生存上存在的可能性。”[1]历史是多种可能性中实现了的一种。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这种已经实现的历史可能性,而是在历史的岔路口上,是什么东西决定历史走上了它最终走上的这条路。 一、“总体性教育”的残留: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之迷 (一)“经义教育”与“总体性教育”:传统语文教育的两大特征 “经义教育”是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个特点。正如顾黄初、李杏保所指出的:“古代各类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研习儒家经典。”[2]张隆华则概括为“道”:“学习者从学儒学,到学汉学、理学,都是学这个传统的‘道’……所谓重‘道’,就是重儒家这个正统观念。”[3]9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语文教育可以直接称之为“‘道’教”。在这里,所谓“道”,具体表现为儒家典籍的经义名理,所谓“‘道’教”,就是儒家典籍的经义名理教育,因此可以称之为“经义—训诲教育”:以儒家典籍义理为内容或载体,以训诲儒家正统观念为目的。 “一身而数任”是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古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识字教学还是‘国学’常识教学,无论是读书作文,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常常是扭合在一起的……学语文,也就是学思想、学社会、学自然,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古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文、史、哲不分的,甚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不分,学伦理、历史、哲学,学科学、技术,也就是学语文。语文教育始终是一身而数任的。”[3]6笔者曾称这种“一身而数任”特征为“内容泛化”,顾黄初、李杏保称之为“混合式教学”,刘国正则称之为“总体性”。 “经义教育”这个特征是着眼于古代语文教育的“内在价值取向”(目的和内容)概括出来的,第二个特征则是着眼于古代语文教育岣“外在形态”(语文教育的存在形式)概括出来的。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第二个特征,即“总体性”特征,是由第一个特征,即“经义教育”的内在需要决定的:经义本身就是综合的、百科全书式的、无所不包的。因此,以“经义—训诲”为价值取向的经义教育,则必然呈现一种“总体性”的特征。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现代语文教育就是在反经义教育中诞生和发展的。但是,遍览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著作,我们发现,现代语文教育与传统语文教育在外在形态(即语文教育存在形式)上的关系,一直在人们讨论的视野之外。 历史常常是这样,它把自己的规定性深藏在匆忙和纷繁芜杂中,任人们在黑暗中摸索。只有等到历史拉长成为一段背景,人们才可能意识到历史中的某一步的重要性,回过头来去寻找历史中的这一刻,以及隐藏在这一刻中的历史规定性。20世纪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回眸历史,把目光停留在传统语文教育与现代语文教育相揖别的那一刻。我们想弄清楚的是,现代语文教育作为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反叛,它是从哪一个层面切入的,它是在哪一种意义上的反叛,这种历史的选择如何注定了“历史的遗忘”。直言之,现代语文教育反叛了什么,又保留了什么,它为什么会有所保留,它为什么会保留这些“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对现代语文教育意味着什么。 (二)白话文教学:只反“经义教育”,不反“总体性教育” 郑国民认为:“从文言文教学转变成白话文教学,这就是传统语文教学向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艰难过程。可以说,关于语文教育的所有方面都和这个问题紧密相关。”[4]3由于论题本身的限制,他主要是从现代教育这个角度来讨论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的选择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文言和白话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首先并不是作为一个语言问题提出来的,也不是作为一个语文教育的问题提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提出来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以“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为主要标志的现代语文教育,是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言与白话并不仅仅是一种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之别,也不仅仅是一种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别,文言与白话负载了深厚的历史内容和文化内涵。在历史的“那一刻”,“文言”被当作了传统,“白话”被当作了现代,“文言”与“白话”的抉择,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抉择。 “文言文教学的灵魂是‘代古圣人立言’,记诵古圣人之文,揣摩古圣人之道,束缚个性,禁锢思想,脱离社会和日常生活实际,空耗岁月,枉费精力”,[4]所以现代语文教育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和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反文言立场,必然使它把主要的变革力量集中到对“圣人之言”的摈弃和批判上,而把主要的建设力量放在新文化基本义理即“科学”与“民主”的阐释和弘扬上。“文言文教学”的千年历史负担,造就了“反文言”“反圣人”的历史艰难和文化阻力;“白话文教学”的现代内涵和广泛的生活基础,深深吸引住了现代语变的历史视野。这两股力量钓合力,把现代语文教育推到了一个思想文化的风口浪尖。而现代语文教育在“反传统文化”和“建设新文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深深滞阻住了它对自身的反省和审视:现代语文教育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反叛,除了在“义理”层面的反叛之外,除了对“圣人之言”的反叛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面的反叛?反了“经义教育”,那么与之相联的“总体性教育”是不是也应该一同予以反叛呢? 现代语文教育是从“反文言”这一层面切入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反叛的,它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反叛是在“反封建”意义上的反叛,它主要是在语文教育的文化内涵、社会基础、意识形态、政治倾向等方面的价值重构。一本现代语文教育史著作在总结“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的意义时说:“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争,对于语文教育来说,是一场根本性的论争,是教学要不要切近生活、要不要为实用服务的论争。”[5]12“白话文的应用与推广,看来只是一个语言形式问题,但‘五四’时期白话文与文言文在特定范畴的斗争,毕竟关系到与思想内容革新和与人民大众紧密相连的积极作用和实际意义,因而交锋甚为激烈。”[5]84这段话反映历史的“那一刻”的真实情形:它主要是从“切近生活”“为实用服务”“思想内容”“与人民大众紧密相连”这样的意义上来思考语文教育、影响语文教育的。这种历史选择的艰难性和与时代的高度响应注定了它的历史“遗忘”:它主要是关于语文教育内容方向的指导思想的改革,而把语文教育本身存在形式的改造和革新任务遗忘在一边。历史的结局是:百年语文教育,我们从“反文言”出发,成功地摧毁了经义教育(“道”教)传统,但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总体性”特征却予以了保留。其结果,是去除了总体性教育的思想文化基础(经义教育,“道”教),但却保留了经义教育、“道”教的存在形态。近一百年来,这种保留从没有进入过被审视、被反省的范畴,人们一直把它当作从来如此因而天经地义的事物,并把它指为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认为它“适应了语文教育的综合性,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或者指为“传统语文教育中值得我们后人重视的经验”,作为现代语文教育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语文教学的基本特征,被写入各类语文教学论著作。 (三)义理教学:传统语文教育在现代语文教育身上留下的“胎迹” 现代语文教育对“总体性教育”传统的保留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为经义教育留下了“后门”,留下了形式可能性。 百余年来的语文教育,一直存在一个“课程性质”之争。这个所谓课程性质之争的实质就是为语文课寻找立足点从而获得定位。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一而再、再而三构成对语文课程定位冲击的,都是来自经义教育传统。经义教育就像一个阀门。只要打开“经义教育”这个阀门,语文教育就立刻生发出定位问题。这种冲击之所以发生,而且有效,首先是因为语文课为它留下了“课程形式的可能性”。这种课程形式的可能性,就是“总体性”特征:正是因为对传统语文教育“总体性”特征有意无意的保留,现代语文教育在课程组织方式上为“经义教育”留下了复辟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体性教育”实际上就是经义教育的残留,它的身上必然地带着经义教育的气息和通向经义教育的引力。“经义教育”与“总体性教育”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它们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造就了整个20世纪语文教育的悲欢离合。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把现代语文教育对传统语文教育“总体性”特征的保留,称为现代语文教育的“胎迹”。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是语文课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的历史,这段历史之所以这么艰难,这么曲折,历经这么多的磨难,原因之一(甚至是首要的原因),就是它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带着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总体性胎迹”。在我看来,从传统语文教育的娘肚子里带来的这种“总体性胎迹”,在源初性意义上决定了20世纪语文教育的历史走向、整体面貌甚至某些细节。正如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也许就隐藏着他今后人生道路的某些信息,预示或预设着他整个的人生走向,甚至决定了他的人生命运。但在现代语文教育诞生的那一刻,即传统语文教育与现代语文教育揖别的那一刻,人们却并不知晓。那一刻,它是作为“历史之迷”存在着,并在历史中继续着它的旅程。破解这个“历史之迷”、打破“总体性”束缚、中止它在现代语文教育中的延续、实现语文教育的“语言专门化”,这样的艰巨使命,历史地交给了叶圣陶和他的朋友们。 二、语言专门化:语文教育的“独当其任” (一)语言的觉醒: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笔者在2000年曾撰文对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历程进行过一种宏观概括: 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呈交错状同时发展着两种理论或主张,一种就是“语言本位的语文教育观”,它逐步摆脱与儒家经义的黏着状态,逐步把在古代语文教学中处于次要和幕后地位的语言内容推到前台和主体位置,使之成为语文教学的主体构成;另一种就是“义理本位的语文教学观”,它继承了古代语文教育的载道传统,坚持以思想义理为语文教学的主内容,虽然“道”的具体内容不断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以思想义理内容为语文教学的本体构成这一基本原则却始终得以肯定和保持。这两种理论和主张交错发展,它们的比重变化和发展曲线,决定着现代语文教学的悲欢和兴衰。但就其总的趋势来看,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这就是由传统的义理本位教学向语言本位教学不断发展、推进和演变。[6]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条线索并不是一开始就明朗化的,恰好相反,在现代语文教育揖别传统语文教育的那一刻,“语言”还遮蔽在“反文言”“反封建”“反经义教育”的时代浪潮中。作为“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语言的觉醒”是从叶圣陶开始的。 这是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即从“反经义教育”到“语言专门化”。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个过程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实际上是通过以叶圣陶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得以实现的。 “课程不是天经地义的存在,而是同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之中形成的‘社会构成物’。”[7]换句话说,现在“这个样子”的语文课,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天然就有的,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信念和原则选择的、建构的,它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它有着这样的目标而不以那样的目标为目标,它有着这样的课程内容而不以那样的内容为内容,是人们根据一定的需要以及人们对母语教育的认识决定的。世界课程史和课程比较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明。并不是从来就有一门“这样的”“语文”课,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语文”课。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三艺”(逻辑、语法和修辞)到中世纪被废止,在文艺复兴时期则重新发现,到了经院哲学时期则成了语法学,到了现代,则呈现一种各不相同的状态。有的直接以“英语”“法语”来称呼,有的则称之为“语言艺术”或“语言交际”,有的则称之为“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或“美国文学”,而其中的实质性内容,也是各自不同、相差很大的。实际上,西方的现代母语课程范围不仅包括语言、文学,还包括戏剧、传媒、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的有关方面,有的学校干脆把它分解成写作、新闻、语法、文学、科幻小说、电影、戏剧、演讲等许多名目,分成若干不同的课来教。课程是在一定的信念和背景下由人们建构的,不同的信念和背景就会有不同的建构。 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现在称之为“语文”的课至少有四次历史选择。第一次就是从“反经义教育”到“语言专门化”,第二次就是从“国文”“国语”到“语文”,第三次就是语言、文学分科实验,第四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文课”“革命文艺课”。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对语文教育的一次选择,一次基本立场的变更。就以从“反经义教育”到“语言专门化”为例,“反经义教育”只是意味着对传统语文教育文化内容、文化取向的摈弃,而“语言专门化”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存在形态”的变革,即从“总体性教育”转向以语言为专门领域的教育。而前者(反经义教育)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到后者(语言专门化)。比如,“五四”以后,一些思想文化界的革新派,鉴于语文教育中封建复古势力依旧顽固,因而特别强调在语文学科中开展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他们往往采用自编讲义,课文按思想内容、按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编组,在语文课里带领学生讨论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劳工神圣、妇女解放、儿童至上等文化观念。正如顾黄初、李杏保所指出的:“新旧两派人物,他们要张扬的‘道’显然是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但他们在语文教学上所坚持的做法却有共同之处”。[2]这个共同之处都是“义之教”,都是“总体性教育”“混合性教育”。从内容上来说,“道”不同,但从形式上来说,都是“‘道’教”。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文课”“革命文艺课”,它们在课程存在形态上,与传统语文教育是完全一致的,即“总体性教育”,换一句话说,即换了“义”的“经义教育”。现代语文教育起源于“反经义教育”,但“反经义教育”的核心是反“经之义”,并没有反“义之教”,如果将此“经”换为彼“经”,比方换成“民主与科学”之“经”,“自由与平等”之“经”,还有“劳工神圣、妇女解放、儿童至上”之“经”,“政文”之“经”,“革命文艺”之“经”,则同样拥有了“反经义教育”的基本特征。 总之,“反经义教育”不一定走到“语言专门化”,“反经义教育”可能仍然停留在“总体性教育”的领域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对有关论者的以下判断持保留态度:“白话文运动的作用表现在语文教育方面,使语文教育从此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使它从几千年来历史所赋予的各种使命的缠绕中挣脱出来,承担起了本学科所应该承担的独特任务,即学习掌握语言文字这个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传统语文教学向现代语文教学转变的主线,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的转变过程,也是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逐渐明确的过程,语文教学从此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征途。”[4]这段论述将“反经义教育”“白话文教学”直接接植于“本学科所应该承担的独特任务,即学习掌握语言文字这个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从而将“反经义教育”“白话文教学”直接等同于“语言专门化”,似可商榷。白话文教学只反“经义”“‘道’教”,不反“总体性教育”,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真正使语文教育“从几千年来历史所赋予的各种使命的缠绕中挣脱出来,承担起了本学科所应该承担的独特任务,即学习掌握语言文字这个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样的历史功绩,是由叶圣陶和他的朋友们花了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才完成的。是他们实现了现代语文教育的“语言专门化”,并以“语言专门化”为核心,完成了“语文科”作为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中的一门独立课程的合法化论证和价值揭示。 (二)反“经义教育”更反“总体性教育”:叶圣陶的历史功绩 通阅叶老关于语文教育的全部论述,笔者更坚定了在拙作《言语教学论》中的以下论断: 叶圣陶把语言文字教学与思想义理教学的关系提高到涉及语文教育本质(是不是语文课)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并鲜明地肯定了语言文字在语文教学中的主体位置。尤其要指出的是,这种研究是在关于语言文字与思想义理的关系的辨析中展开的,在传统教育思想中占绝对主体地位的思想义理(即“道”)让位于过去始终作为附庸地位的语言文字(即“文”)这样的意义中展开的。这不仅需要深刻的研究,同时还需要极大的思想魄力。叶圣陶在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他以较系统的理论,总结并明确了现代语文教育由义理本位向语言本位演进发展的趋势,并使之上升为一种语文教育思想确立下来,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下半个世纪的语文教育。[8] 与其他现代语文教育家一样,叶圣陶是反经义教育的。1942年,他在为其主编的《国文杂志》写的发刊词里写道:“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书中内容背到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9]87叶圣陶是从“生活的需要”这样的意义上反“经义教育”的。同样从“生活的需要”出发,叶圣陶确立了“国文科的专责”在“运用语言文字”:“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9]2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叶圣陶把重点放在反“总体性教育”上。 叶圣陶既反对“经义教育”,又反对“总体性教育”,这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这一点,奠定了叶圣陶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叶圣陶不止一次地强调:“站定了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这是对于国文教学的正确的认识。”[9]89直到晚年,他仍然告诫语文教育工作者:“能真知语文教学之为何事(如何以须教学生阅读,何以须教学生作文之类),而不旁骛耳。”[9]744叶圣陶关于语文教育的论述,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正面阐释“语文教学之为何事”,一是批判语文教学的种种“旁骛”。站在叶圣陶的位置上,他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守住语文教育的防线:一是防止语文教育对“生活的需要”的背离,一是防止借“生活的需要”糐生出对“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的背离。前者是防“经义教育”的复辟,后者是防“总体性教育”的复辟。现在来看,对经义教育的警惕是成功的,但对“总体性教育”的警惕则始终处在艰难中,时时有被全线突破的危险。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深切地理解上述引文的真正价值。 三、“语用”的崛起:现代语文教育的第二个岔路口 (一)二难选择:留在“语言专门化”的道路上还是退回到“总体性教育” 得益于叶圣陶等人的坚守,现代语文教育在艰难中仍然“站定了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百年语文教育,我们可以大致理出这样一条“语言专门化”的道路:起源于20世纪初的白话文教学,成形于1935年夏丏尊、叶圣陶的《国文百八课》出版,而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颁布标志着这样一个教学体系的基本完成,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中得到了强化。 然而历史的诡秘在于,它同样也向我们呈现,伴随着这个历史过程的也是语文教学逐步走向“工具主义”“技术主义”,并逐步脱离“生活的需要”,走上一条与当年叶圣陶所批判的“旧式教育”相同的道路:“现在的国文教学训练出来的学生,国文程度实在不足以应付生活,更不用说改进生活。”[9]90这句对20世纪40年代语文教育的批评,几乎可以原封不动拿来批评当代的语文教育。 20世纪末由《北京文学》发起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对近半个世纪来语文教育领域里工具主义、技术主义泛滥的种种情形,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这些批判在逻辑上都指向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选择:语言专门化的道路。 现代语文教育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继续在“语言专门化”的道路上走下去,似乎看不到光明。伴随着“语言专门化”一起走过来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泛滥,已经对语文教育产生了伤筋动骨的侵蚀。在当下这种历史语境中,这种选择明显是弱势话语。另一种选择是从“语言专门化”的道路上退回去,退回到“总体性教育”的老路上去。然而它的“倒退姿势”让这个时代的人们天然有一种警惕,而且经义教育曾经负载过的“道”教取向,也让许多人心生忌惮。近几年来,在反工具主义、技术主义的浪潮中,在某些方面,语文教育已经重新开启了“经义教育”的阀门。“总体性教育”的传统以各种新兴的名词和概念回归到语文教育之中。对它的质疑之声,可以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当下语文教育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泛语文”“泛人文”现象,更加深了人们对“总体性教育”的警惕。 (二)从语言要素到语言功能:现代语文教育的语言学基础 现代语文教育走到了21世纪,走到了第二个岔路口。在第一个岔路口上,历史舍弃了“总体性教育”,选择了“语言专门化”。历史不可假设,历史是一个存在,站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上,我们可以思考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存在,我们可以在下一个岔路口上作何选择? 我们回到“语言专门化”概念。所谓语言,有两个本质。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说:“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看法,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这就是语言的语言学与言语的语言学。”[10]所谓“语言的语言学”,它着眼于语言各要素的描述与分析,把语言理解为一套知识系统;所谓“言语的语言学”,它着眼于语言的功用,把语言看作一个功能体。对语言的第一个本质,大家的认识比较充分,对语言的第二个本质,大家的认识并不那么明确。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皮特·科德在《应用语言学导论》里说:“传统法认为,语言是一个‘语言的’语言学概念。它似乎很少关心‘适合性’这一概念,也不考虑语言行为对不同社会环境作出反应的方式。而现代语言教学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它较多地从社会的角度来对待语言,并且重视语言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交际功能问题。”[11]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是要教这套“语言的语言学”知识给学生呢,还是把语言的功能教给学生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岔路口”。 现代语文教育,才走完了自己的第一个岔路口,才完成了第一次岔路口上的抉择。现代语文教育应该在第一个岔路口的正确的抉择的基础上,及时在第二个岔路口作出另一个正确的抉择,那就是语言功能教学。 百年语文教学主要是把语文课当作知识课来教,其主要的思路是:语言由哪些要素构成,它们各自有哪些特征,如何辨析它们。于是我们有了文字、语音、词汇、语义、语法、修辞等的教学。这种知识教学被不断扩大化,泛化到文章知识、逻辑知识、文学知识、文化常识等,于是形成了所谓“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八字宪法”。因为这种语文教学把注意力放在语言的要素上,我把这种语文教学称为“语言要素教学”。 在对这种语言要素教学的深刻反思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倾向。章熊在“言语思维”和“言语技能”两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王尚文、洪镇涛则从语言心理学的角度辟开一条道路,提出“语感教学论”,并开展了扎实的实践探索。李海林、李维鼎、余应源则从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辨析中找到一线理论生机,提出“言语教学论”,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这些研究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学理论基础,这就是功能主义语言观。功能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通俗地说,语言是“做事”。章熊的研究是着眼于“做事”的技巧,王尚文、洪镇涛着眼于“做事”的能力,李海林、李维鼎、余应源着眼于所做之“事”本身的性质和结构。总之是着眼于语言的功能重构语文教育的学科基础。这种从功能主义语言观出发的语文教育研究,为现代语文教育开辟了在“总体性教育”和“语言要素教学”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语言功能教学”。 (三)“语用教育观”:现代语文教育价值的重新定位 “语用”最初是作为“语用学”的概念进入我们的视野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课程性质”中提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用”作为“语言文字运用”的简称,开始作为一个语文教育的专门术语,逐渐被大家接受。《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那一个命题,也就被人们称为“语用教育观”。[12] 作为“语言文字运用”简称的“语用”概念与语用学中的“语用”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有区别。但它们的实质是一致的,这个实质即:它们都是关于语言功能的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用教育观”集中蕴含了从“总体性教育”向“语言专门化”转化,又从“语言要素教学”向“语言功能教学”转化的全部历史成果。它既保留了“语言专门化”的正确选择,又在“语言专门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再一次转型。 “语用教育观”的提出是历史为现代语文教育给出的一个机遇。它在历史的这一刻提出,以这种方式提出,也许带有偶然性,但它内含的课程价值意义则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在学理上它响应了近现代语言学研究从结构主义向功能主义的进化,在实践上它总结了语文教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它是历史进化观在语文教育上的具体体现。 从“总体性教育”到“语言专门化”,现代语文教育在第一个历史岔路口的选择是正确的,但这是一个没有走到位的选择。它是现代语文教育必经的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它的第一个历史功绩是:奠定了语文课程的“独当其任”和“专责”,确立了语文课程在现代教育体系的合法性地位。它的第二个历史功绩是:它为“语用教育”提供了历史可能性。因为没有“语言专门化”,就没有在“语言专门化”基础上的“语用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专门化”导入了“语用教育”。“语言专门化”的历史意义,只有把现代语文教育史拉长在这样一个长卷中,才能看得清楚。 “语用教育”既是对“语言专门化”的深化,又是在现代语文教育的第二个历史岔路口的再选择。站在第二个岔路口上,它是对“语言要素教学”的反拨。但站在第一个历史岔路口上来看,它与“语言要素教学”一起,防守着现代语文教育向“总体性教育”复辟。它是“语言专门化”历史使命的达成,又是“语言专门化”道路的有力开拓。如果没有“语用教育”,“语言专门化”就停留在“反经义教育”的中途,“语言专门化”的意义就夭折了。更严重的是,现代语文教育就时刻处在经义教育复辟的危险中。 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关于定位问题,分歧多于共识。“语用教育观”的提出,为现代语文教育的定位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达成共识的机会。但愿这一次,我们不会辜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