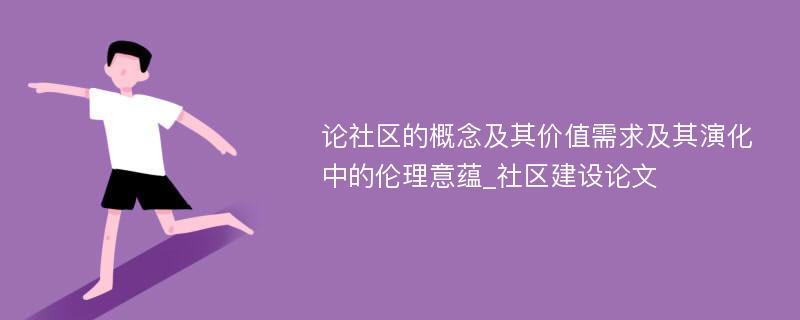
论社区概念及其演进中的价值诉求和伦理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伦理论文,概念论文,价值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5—0163—0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必须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建设。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实现社会基层民主、社会管理、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协调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那么,如何理解社区,以怎样的价值理念来构建社区,在理论上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词源学意义上的社区表明,社区也是一种道德的存在,任何社区都包含着这一社区特有的共同价值和伦理要求
社区一词进入学科领域,源于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Ferdinand Tonnies),以他于1887年发表的著作《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为标志。其中德文Gemeinschaft一词可译作共同体、团体、集体、公社、社区等,表示一种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藤尼斯提出与社会相对应的社区这一概念,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藤尼斯在该书中指出,“社区”是基于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记忆等,以及基于血缘、地缘和心态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在社区中,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包括感情、传统和共同联系在内的自然意愿,其特点表现为人们对本社区的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而“社会”却不同,社会是基于人们的理性意志和主观利益之上的理性意愿而形成的组织,其特点是人们没有或很少拥有认同感、情感中立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片面交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藤尼斯提出的社区概念逐渐引起西方社会学家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罗·密斯第一次将藤尼斯的著作翻译成英文,他起初将其译著命名为《Fundamental Concepts of Sociology》(《社会学的基础概念》),后又将其译为《Community and Society》(《社区和社会》),首次将英文中的Community与德语中的Gemeinschaft相对应。英文单词Community源于拉丁语Communitas,有“共同性”或“社群性”、“联合”或“社会生活”、“地域性”等意。
1933年,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将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成“社区”一词,融原文中的“社群性”(社)和“地域性”(区)两个意义于一词。应该说如此翻译不仅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英文原词的要义,还保留了德文Gemeinschaft的基本含义,即“社区”不仅仅是一种“地域社会”,而且还是具有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共同体。
通过对“社区”一词的历史追踪,不难发现“社区”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价值诉求和伦理意蕴。“社区”被创设出来,不仅表征着一种空间的地域特征,更主要的是强调了它是一种由共享的价值利益和共同的道德承诺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或社群。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价值诉求和伦理意蕴会有所不同,正如戴维·米勒所言,每个社群都以其成员的特殊信仰而区别于其他社群。但无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社区如何存有差异,社区都会表现为一种道德存在,其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建立在维护共同利益基础上的道德不仅能有效地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还能有效地促进成员间的交往与合作,从而形成“某种超越于个体和私人关系网的社团感,以及特别的一种对社群存续休戚与共的义务和贡献感”①。
二、从“社区”的定义看,伦理和价值观上的某种共同性是社区最为核心的特征
100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社区”的内涵不断丰富,其外延也不断扩展。从藤尼斯到现在,人们对“社区”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定义也多种多样。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希拉瑞(George Hillary)对各种“社区”定义进行了统计,发现共有94种不同的定义。
藤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和社会》一书中最早使用社区一词,是为了用社区和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说明社会变迁的趋势。他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人们加入这样的团体不是自己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血缘和地源自然形成的。这样的共同体逐渐向异质人口组成的、由社会分工和契约联系起来的、缺乏感情和关系疏远的社会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藤尼斯对社区充满深情的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西方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和忧虑,反映出一种对传统社区精神的呼唤和向传统的欧洲乡村社区模式的复归”②,更表达了他对传统社区人伦关系的怀念和向往。
后人对社区概念的理解和定义较之藤尼斯的原初定义有了很大不同,更多的学者已不再把社区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社会共同体,而倾向于认为社区也是当代社会最基本、最广泛的社会单元和社会学分析单位。不同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赋予它许多涵义,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如我国学者费孝通从社区的功能和地域空间相结合的角度对社区的定义是:“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家庭、民族)或社会组织(机关、团体)聚集在一地域里,形成一个生活上互相关联的大集体。”③ 无论从哪种角度下定义,“社区”一词总有一些共性的基本特征为人们所认同,如地域性、社区的人际互动、共同的约束等,其中最为核心的特征是社区一定是一个充盈着深厚的感情、道德的承诺等伦理意蕴的共同体,即这一地域性人群必须具有伦理和价值观上的某种共同性,没有这一特征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也就不能使社区从一个“大社会”里分出来而相对自成一体的必要和可能。社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大社会”的组成部分,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微观的、动态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包含有自然地域、群体、组织制度、规范、机制等因素,属于社会的基本层面,具有满足人们共同需要的基本设施和功能。这一“共同体”不仅具有一整套维护自身形象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涉及社会形态、组织模式和人际互动方式的价值判断和偏好的选择,而且还拥有公共的资源和财富,如土地、矿藏、林木等资源,以及各种社会和集体福利与公共性事业。因此,社区内任何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失,必将同时牵动另一部分人和整体的利益,这种利益上的互相牵制与影响,更多来自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调节。正如戴维·米勒在其《市场、国家和社群》中所言,这种公共利益还涉及某些基本的人际原则,如诚实、无私、奉献等。迈克·沃尔泽也指出,人类不仅拥有共同的需要,而且拥有关于共同需要的观念。④
三、社区社会化到社会社区化的变迁,标志着人类对传统社区人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复归
藤尼斯写作《社区与社会》的时代正是欧洲工业化、都市和现代化大发展的时代,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浪潮打破了前工业化的社会共同体形式,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原有的家园惨遭破坏,人口流动加剧,物资交换的范围扩大、频率加快、手段和途径日益多样化,社区的基本福利和安全保障方面的效用大大降低,突如其来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巨大变迁摧毁了社区群体成员的首属关系,也打破了存在于社区成员间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中,“社会”这种现代城市组织源源不断地从“社区”那种村社组织中分化出来,社区被社会所取代。人们在这种变迁面前别无选择,而且人们也正是在这种社区不断为社会所取代的过程中极不情愿地被带入了工业文明时代。藤尼斯正是发现了这种社会转型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组织的分野,从而运用“理念型”方法构建起“社区—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分析架构,从而为诠释以工业化和都市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过程构建了一个理论平台,也预见了社区社会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路径。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化的进程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人类生活从农村社区走向城市社会的过程。那么,在物的法则驱使下所构建的理性社会是否让人们得到极大的满足呢?回答是否定的。现代化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资利益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人们在享受社会进步成果的同时,孤独感、不安全感却时常困扰人们的心灵;人们在理性增强的同时,情感却贫乏了。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所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以期对现代化发展的路径进行修正,也为一些后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对现代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人类社会出现了从社会向社区回归的发展趋势,可以称之为社会社区化或社会人文化的发展趋势,这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二次选择”⑤。这种从社会向社区的回归,是源于人们发现了现代化进程中所缺失的东西,那就是传统社区的人伦精神和人文法则。社会社区化这种对社区人文的复归,实质上是对传统社区那种充满温情的人伦关系的复归,人们向往那种由自然意志和传统价值取向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人们彼此共享某种经验、感情和价值,并共同营造满足人们共同生活的美德和价值追求。
社会社区化就是要使社会的理性法则回复到社区的人伦精神和人文法则,是要告诫人们,在坚持物的理性法则的同时,更应高扬人文法则;在建设人类的物质家园的同时,还必须保护和关照好人类的精神家园。
四、当前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必须坚持和谐的价值理念,以社区的伦理构建作为社区建设的核心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才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此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社区理论研究和社区实践探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我国的社区建设正处于“社区社会化”和“社会社区化”同步进行的阶段。一方面是一些较落后地区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正在经历着由社区向社会的迈进;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已进入到发展后期,与现代化建设相伴而生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充分暴露,急需加大社区建设的力度来消减各种社会问题,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有序的发展。不仅如此,由于地域的差异,在同一个城市中也会出现社区社会化和社会社区化同时进行的局面。这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反思的结果,所以,无论是社区社会化还是社会社区化,都表明社区建设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为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开展,民政部于2000年颁布实施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是繁荣基层文化生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措施,是巩固城市基层政权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⑥
21世纪的中国,在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的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然而社会转型也给城市社区建设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分化、地区差别、城市大量“农民工”的涌入、城市人口老年化问题、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问题等。另外,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也对城市社区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社区的责任越来越重,功能不断强化。第一,随着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单位组织的机制被打破,城市居民大量地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从企业和政府中剥离和分离出来的一部分职能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式管理模式来承接;第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不到位、跟不上,随着社区成员异质性程度的加大,其成员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亟待提高;第三,由于政府职能的下移,社区还要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化服务的职能;第四,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社区建设“要求各家各户打开自家封闭的大门,走到社区这个大家庭中来,重新发展社区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把疏远的人际关系拉近,使扭曲的或被异化的人性复归”⑦。所以,社区还担负着重新培养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社区凝聚力的重任。
传统社区,人们祖祖辈辈长期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由于地缘和血源关系彼此有着一种对自己故乡认同、喜欢和依恋的情感,社区成员间形成了以亲情、邻里情和伙伴情为代表的首属人际关系,社区成员间彼此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正是由于社区的这种社会黏着的特性和成员所拥有的强烈的社区意识,才使社区成为人们向往的“家”。这个“家”不仅是社区成员物质意义上的家园,同时还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今天讨论社区建设,并不是要回到原来的传统社区时代,而是要将传统社区的伦理精神移植到当今中国的社区建设中来,并赋予它以现时代的精神和伦理内涵。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区伦理精神是推动社区建设的精神动力,引领社区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社区成员追求主体自觉和人格价值的动力,具体表现为社区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和共同崇尚的伦理观念和人伦精神。由于社区的管理和运行关涉千家万户和每一个成员的利益,还有社区中的组织、企事业单位、管理机构、群众团体以及公共的资源和财富,如土地、矿藏、林木、水等资源与各种社会和集体福利、公共性事业,因此社区伦理建设必然包括用于调整社区成员之间、社区成员与社区内组织之间、社区成员与自然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准则。当然,社区的伦理理念和规范必定是与社会主义伦理规范相一致的,是社会主义伦理规范在社区中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当前当以和谐作为社区建设的价值理念,建立一套维护社区这一“共同体”的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坚持政府指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合理配置社区资源,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素质和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将社区建成为人际关系和谐、人人奋发向上、个人安居乐业的摇篮,这样才能依靠社区的力量消解各种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为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收稿日期:2006—07—10
注释:
① 于海:《三个角度看社区》,《社区》2001年第2期。
②⑤⑦ 夏国忠:《社区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24、26页。
③ 转引自夏国忠编著《社区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④ 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⑥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0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