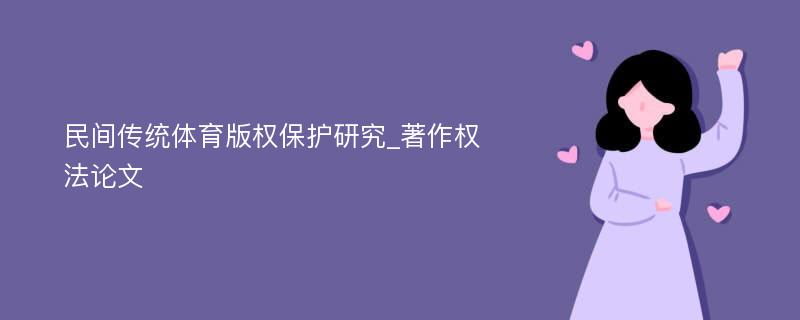
民间传统体育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作权论文,民间论文,传统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6-03-26
中图分类号:G80-05;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98(2006)04-0001-04
民间传统体育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体育全球化趋势使得民间传统体育在现代体育运动的冲击和融合下,面临着被遗弃、吸收或肆意改造的严重危机。民间传统体育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的基本识别标志。保护民间传统体育,不仅关系着传统体育资源最丰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体育大众化”(sport for all)的现代体育发展观念所倡导的。借助法律制度保护民间传统体育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民间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智力成果和文化遗产,具有著作权的某些属性,人们寄希望于著作权制度对其进行保护,但传统体育的特殊性与现有著作权保护体系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冲突。因此,研究如何对传统著作权制度进行某些变革,以适应保护民间传统体育的现实需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民间传统体育的特征
民间传统体育(traditional sport or folk game)是指一个民族或地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开展的具有修身养性、健身娱乐、竞技表演等特色的体育活动形式。如第7届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中的花炮、珍珠球、木球、蹴球、毽球、龙舟、秋千、射弩、陀螺、押加、高脚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等就是典型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
民间传统体育是与现代体育相对而言的。现代体育是指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近代体育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体育运动形式,[1] 它是西方体育以其强势对各项民间传统体育进行同化和改造后形成的。现代体育的典型代表是奥运会体育项目。民间传统体育同现代体育一样,具有健身性、群体参与性等特点。民间传统体育的独特性在于:
地域性。民间传统体育只在一定的地域内存在,受区域环境、自然条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影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间传统体育的活动方式,具有本民族或本地区的显著特征。如“达瓦孜”源于两千多年前的西域,汉代传入中原,主要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盛行。而现代体育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出于公平竞争的需要,在表现形式、比赛规则等方面要求公平一致,体现出很强的共同性。
文化遗产性。民间传统体育是在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提炼出来的,保留着本民族或地区最原始的文化,通常是一种宗教或文化的表达工具而不带有商业目的。如射弩比赛源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有悠久的用弩历史,尤其是广西、贵州的瑶族,云南的傈僳族、怒族、苗族,四川的彝族,至今仍用弩狩猎,并以弩作为装束和定情的信物。而民间体育比赛中使用的弩与国际比赛用弩的区别是,弩、箭为竹、木质料做成,比赛时不许装瞄准器。而现代体育则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身心发展的需要,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商品化等特征。
娱乐观赏性强于竞技性。民间传统体育把体育融汇于宗教礼仪、生产劳动、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之中,并与音乐、舞蹈等民间文化艺术形式紧密结合,从而体现出较强的娱乐观赏性。如秋千就是我国许多民族喜爱的观赏性很强的传统体育项目,秋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种类较多,例如阿昌族、苗族就喜欢打形状似纺车的4人秋千和8人秋千,土族喜欢打用大马车轮子做成的轮子秋。而现代体育更多地强调“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竞技原则,以竞技运动中的超越自我、战胜对手为直接目标,突出地体现为竞技性特征。民间传统体育的开展大多不需要专门的场地设备和环境条件,而现代体育对场地、设备等外部条件的要求较高。
2 民间传统体育适用著作权保护的国际立法趋势
民间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而传统文化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始,才作为受保护的客体出现在一些国家的著作权法(也称“版权法”)之中。目前已有约50个国家对于民间传统文化采用著作权制度进行保护,一些地区性的版权条约和国际版权公约也对传统文化保护做了规定。
多数版权公约和各国版权法在明文规定保护传统文化时,并未单独列明对民间传统体育的保护。如《伯尔尼公约》第15条规定仅使用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名称,而未具体指明是否包括传统体育在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1976年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突尼斯版权示范法》中,将民间文学艺术定义为“在本国境内由被认定为该国国民的作者和民族集体创作,经世代流传而构成文化遗产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全部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从这一定义看,并没有把“民间传统体育”排除在外。1982年在日内瓦通过《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方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以下简称《示范条款》),进一步将民间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划分为4类:第1类为语言形式,包括民间故事、诗歌、谜语;第2类为音乐表现形式,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曲;第3类为动作形式,包括民间舞蹈、戏剧和各种仪式的艺术形式;第4类为以物质材料体现的形式,如雕刻、雕塑、陶器、乐器、建筑形式。[2] 根据《示范条款》,民间传统体育即属于第3类动作形式的民间传统文化。
明确将传统体育纳入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立法出现在非洲。自20世纪50年代起,非洲一些不发达国家率先提出了保护本国民间文学艺术的主张,禁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任何不适当的利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非洲一些不发达国家先后通过国内立法和区域性条约的形式确立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在较早的“跨国版权法”中,保护民间文学的“非洲知识产权组织”认为:“受版权法保护的民间文学包括: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以非洲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为基础的、代代相传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技术等领域的传统作品。”1977年签订的《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班吉协定》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至少应包括6类:
(1)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的文学作品,如故事、传说、寓言、神话等;(2)艺术风格与艺术作品,如舞蹈、音乐、手工艺品等;(3)宗教传统仪式;(4)传统教育的形式,如传统体育、游戏、民间习俗等;(5)科学知识及产品,如传统医药品及诊疗方法;(6)技术知识及作品,如冶金、农业技术。[3] 明确将民间传统体育列入民间文学艺术中加以保护。
总体而言,国际上关于民间传统体育的著作权立法主要出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法律文件和非洲一些不发达国家签署的公约中,尚未成为主流趋势。[4]
3 民间传统体育与著作权制度之协调与冲突
著作权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财产权,保护客体是智力成果。[5] 而民间传统体育是人类的智力创造成果,具有身份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和地域性特征。因此,民间传统体育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能够成为著作权的客体。但民间传统体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主体的不特定性和群体性、保护期限的永久性等,这又使其与著作权制度之间产生明显的冲突。
3.1 民间传统体育的著作权属性:两者的协调
以《伯尔尼公约》为代表的著作权国际公约和各国的著作权法都规定著作权的保护客体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作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作品的含义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当具备“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两项条件。因此,民间传统体育只有具备以上两项,才能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3.1.1 民间传统体育的独创性
所谓独创性(originality),在著作权法发展早期曾存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标准:英美法系要求的“独创性”指作者独立构思并运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完成作品,而非抄袭。如美国规定独创性的典型案例是1903年Bleistein案件,在该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版权保护不能仅限于优秀的艺术作品,试图评估原始创作的艺术价值不仅超出了版权法范围也超出了法官的能力。只要作品符合法定的版权作品种类,并且由权利主张者创作完成,也就是说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就具有独创性。”[6] 而大陆法系的“独创性”标准较高,如德国要求作品应当具备一定的创作高度和水平。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两大法系的独创性标准出现融合趋势,都认为“独创性”除了要求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之外,还应当具备最低限度的创作性,即质和量的统一,同时不同作品的独创性标准也应有所区别。
以独创性标准来衡量民间传统体育,不难发现:民间传统体育是由不同的创作群体在其独特的历史传统、民俗风情、地理环境、社会心理、审美视角和表现手段等因素影响下创作的结果,每一群体的体育表达形式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具有高度的个性,呈现出较高的独创性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著作权所保护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表达形式。因此,具有独创性的仅指传统体育的表达形式,而并非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过程中的素材或任何工具。使用同样的素材或工具创作出的传统体育形式,只要能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和个性,就符合了“独创性”要求。如同样是摔跤,满族摔跤和蒙古族摔跤在服饰、规则和方法上就各不相同。又如湖南桃源县流传几百年的“板龙灯”舞龙活动,龙身由厚为寸许的木板连接而成,结点插有龙骨,粗为锄把大小,板上各装有4盏内燃蜡烛的小灯笼,板身亦以布为饰,舞龙人肩杠木板,手握龙骨,齐步如飞。同时板龙灯还可用于争战,以鼓、角、旗为号,板龙灯可立即化整为零,其木板、龙骨皆为武器。1995年中央电视台曾对该县的板龙灯作过专门报道,被誉为舞龙中之奇葩,其鲜明的个性完全符合著作权法的“独创性”要求。
3.1.2 民间传统体育的可复制性
可复制性也称可固定性(fixation)。民间传统体育多数以口头等非物质的形态存在于民间,存在于集体或个人的记忆之中,是“未固定的表达”,但能否因此而排斥著作权保护?笔者认为,民间传统体育只是未固定的作品,并非不能固定。如何理解作品的“可复制性”?“可复制性”是指作品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加以固定,指的是一种属性,而非现实状态。如果必须是固定后才能保护,那么口头作品就被排斥在著作权之外了。曾经有国家规定作品必须固定之后才能受到著作权保护,但都已先后修改法律,将“固定”仅作为司法程序的要求,而非获得著作权的前提。《伯尔尼公约》第5条也禁止各成员国对版权保护提出形式上的要求。
在古代就已经有人通过绘画、雕塑等方式将民间传统体育记录下来,而如今借助文字、录音、录像等手段能更加便捷地对民间传统体育进行复制、出版、发表、播放、展览。如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记录和整理了民间流传的上百项传统体育,这些均表明民间传统体育具有可复制性。
因此,民间传统体育可以纳入著作权保护体系中。
3.2 民间传统体育和著作权制度之冲突
著作权制度产生只有300年的时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以保护作者利益、鼓励创新为目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和信息化时代出现的电脑软件、域名等新兴客体也纷纷提出保护要求时,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就难免暴露出很多缺憾。民间传统体育与著作权制度之间存在的冲突主要体现在:
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和群体性。传统著作权法中的权利主体一般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而民间传统体育由一个地区或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创作而成,最初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但经过世代的加工完善,创作者的个性特征逐渐淡化甚至消失,演变为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作品。权利主体一般为群体或难以溯本清源确定作者,因此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群体性权利,难以直接适用现行的著作权制度进行保护。[7]
权利范围的设定。权利范围的宽窄决定了对民间传统体育的保护水平。如果保护过严,将阻碍民间传统体育的传播;而过低的保护水平,也不利于保护权利主体的正当利益和鼓励权利主体进行再创作。传统著作权法对作者的权利范围设置较广,多数情况下作品的传播权控制在作者手中。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民间艺人的陆续去世,一些民间传统体育正面临着失传或消亡的危险。如果完全依照著作权法的保护,将不利于民间传统体育的繁荣和发展。
保护期限的永久性。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经济权利都有明确的保护期限,超出保护期的进入公有领域可被自由利用,如《伯尔尼公约》规定对经济权利的保护期不少于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民间传统体育历史悠久,经历了长期积累和传承而得以延续,远远超出保护期限的限制。因此,民间传统体育难以适应著作权保护的期限要求。
4 民间传统体育的著作权保护制度设计
著作权制度以鼓励创新为基本目标,因此著作权制度本身也随实践的发展而呈现出创新趋势。近年来各国将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域名等新兴客体纳入著作权法体系中,对传统的著作权制度进行了许多发展。基于民间传统体育的著作权特性和保护要求,我们应当在不改变著作权制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两者相冲突的内容加以适当的改造,主要涉及民间传统体育著作权的权利主体、权利范围、权利期限等问题。
4.1 民间传统体育的集体著作权人制度
随着民族运动的兴起和民族权利意识的增强,集体权利的构建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它在保护文化传统、习俗、历史等文化遗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保护文化遗产权等基本人权的要求。[8] 因此,应当在著作权法中增设民间传统体育的集体著作权人相关规定,确认和保护民族或群体享有民间传统体育的著作权。实践中,民间传统体育的著作权归属主要存在3类主体:
第一,某个民族或群体,对本民族或群体自身的传统体育享有集体著作权,如瑶族的打陀螺、高山族的放风筝、布朗族的藤球等等,应当由本民族对其传统体育享有著作权;第二,传承人对其加工和创新的部分享有著作权。在民间传统体育继承和发展过程中,传承人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搜集、整理散落民间的各种素材,通过艺术加工、整理和创新,使民间传统体育得以保存并不断充实提高。加工、整理和创新均属于创造性劳动,由此产生的作品为演绎作品,传承人应当对其享有著作权。如著名的太极拳有陈式、杨式、孙式、吴式等多种流派,传承人对其独创的部分应当享有著作权;第三,民间传统体育在无明确的民族或群体时,著作权应归属于国家,如中国象棋、中国气功等。
虽然确定了权利主体,但仍未完全解决其保护问题,因为在缺乏权利行使机制的情况下,事实上的权利主体往往不能及时行使权力。尤其是民间传统体育中,群体受到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单纯赋予权利往往不能有效保障它的行使。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当由国家或法律授权的民间组织(NGO)来具体承担行使和保护民间传统体育著作权的职责,如国家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协会或单独组建的体育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4.2 著作权保护的权利范围
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可以分为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大类。为了促进民间传统体育的繁荣和发展,在精神权利方面应予以严格保护,而经济权利方面则加以适当的限制,达到促进民间传统体育发展和维护权利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4.2.1 精神权利
民间传统体育的权利人应当享有的精神权利有:署名权(或称注明来源权),行使署名权能够强调民间传统体育的归属,权利人有权在民间传统体育的传播中标注自己的名称,或要求其他使用人在公开传播时以适当方式注明其出处,防止混淆。如太极拳的传播中,要根据不同派别分别注明陈式、杨式、孙式、吴式;保护完整权,禁止任何对民间传统体育的歪曲、篡改,如在向公众传播的过程中发生的损害起源地或流传地及群体声誉的曲解、篡改或其他贬损;修改权,指权利人对传统体育形式进行改造的权利。
4.2.2 经济权利
经济权利是指权利人通过民间传统体育的复制、出版、公开表演等传播形式,或者依法许可他人进行上述传播,从中获取报酬的权利。财产权利主要包括许可使用权、复制权、翻译权、传播权、改编权以及获得报酬权等。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民间传统体育能否像一般作品那样授予权利主体不受限制的经济权利?
笔者认为,民间传统体育的经济权利应当受必要的限制,区分使用方式的商业目的和非商业目的。如果他人对于传统体育的使用和改编是出于推广或提高民间传统体育的艺术水平之目的,则要求使用者事先取得许可及事后支付报酬,可能妨碍民间传统体育的发展。此种非商业目的使用,应当对权利人的经济权利作出限制,即无需事先经过同意,但可要求支付报酬。若将民间传统体育改编成电影、电视并用于商业用途,虽然这种改编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播民间传统体育的作用,但也有可能出现“搭便车”的行为,此时权利人享有完全的许可使用权和改编权,事先必须经过许可并支付报酬。
4.3 民间传统体育著作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民间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过程,它的主体即民族或群体不会消亡,蕴涵的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也不会消亡。因此,对民间传统体育的保护期限应不受限制。我国2003年7月制定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第29条已经规定“国家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不受限制”。在著作权法中应当对此作出特别规定。
5 结论
民间传统体育具有著作权客体的基本属性,应当通过对传统著作权制度的某些适应性改造,将民间传统体育早日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著作权制度能解决民间传统体育保护的全部问题,根据民间传统体育的特点,出台专门性的保护立法仍是十分必要的。
标签:著作权法论文; 著作权保护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艺术论文;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论文; 民间文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