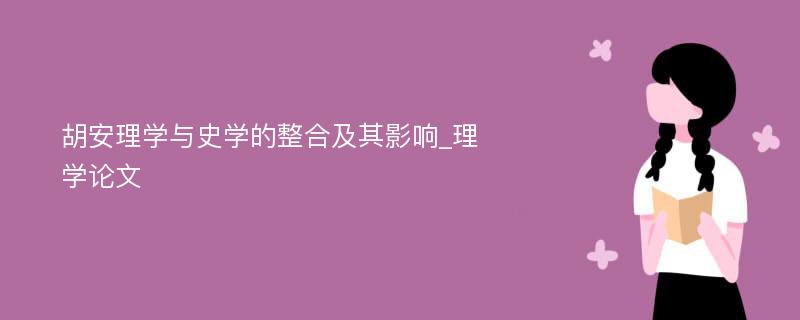
胡安国理学与史学相融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理学论文,胡安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安国私淑洛学而昌明于宋室南渡之后,其功不下于杨时。这个功不仅在于他在形式上下开湖湘学派,而且更在于他把史学引入理学,对于洛学的整个内倾化起到纠偏作用,为南宋儒学的建设引入新的思想内容与方法,并对南宋儒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胡安国(1074-1138年),字康侯,学者称武夷先生,原籍福建崇安。北宋入仕后除荆南(今湖北)教授,入为太学博士,提举湖南学事。南渡以后为高宗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因论故相朱胜非误国,反对高宗重新起用,遂落职,休于南岳衡山,著书立说。
胡安国与程门高足谢良佐、杨时、游酢辈义兼师友,在两宋之际以私淑洛学自任。胡安国膝下三儿,胡寅、胡宁、胡宏,以及侄儿胡宪,均从胡安国习二程洛学,“并以大儒树节南宋之初”(《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全祖望案语),由此而成湖湘学派。
从对理学的继承而言,胡安国主要是接受了洛学的精神,尤其是程颐的思想,强调主敬与致知并重,胡安国讲:“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求养之道。”(转引自胡寅:《斐然集》卷二十五《先公行状》)将致知与主敬并重,意味着胡安国坚持了外向推拓与内倾涵养并重的思想路数。胡安国于壮年时曾读佛书,后来则加以摒弃,这导致了他在思想上,在对待并重的致知与主敬两者中,更倾向于以外向性的致知作为内倾性的涵养的基础。胡安国在给曾几的信中写道:“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毕现,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同上)南渡以后,胡安国在呈献给高宗的《时政论》中,将这个思想表述得更完整,他讲:“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必本于方寸。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同上)强调致知在诚意之先,肯定“学以能变化气质为功”(同上)。
按照胡安国“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意”的思想,致知的外向求学与主敬的内向诚意,其实是正心之两翼。因此以心为体,以致知与诚意为工夫,而致知又为诚意之基础,构成了对二程理学消化以后的胡安国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尽管非常简单,但却也很清楚。胡安国自己由于将主要精力投注在致知上,没有将他的思想作进一步的展开阐述,然而他对心体的标示与致知诚意的推重无疑影响到了后来胡宏哲学思想的建构。
二
胡安国因为处身于两宋祸乱之间,其志在经邦济世,故他的致知很自然地落实在历史兴替的研究上。换言之,史学的兴趣在胡安国那里明显地居于主要位置,纯性理的哲学思考成为次要的工作。这一学术上的取向也决定了湖湘学派与道南学派的区别。
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研究,无不以经学为基础。宋学虽由疑传进而疑经,但其目的只是为思想的自由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在方法上超越汉唐经学传统,并不是也不可能尽弃经学。宋儒治经,往往根据自己的思想关注来作选择。一般而言,重治道者取《周礼》、《春秋》;重性理者取《易》,同时又将《大学》、《中庸》两篇拈出,再加上《论语》、《孟子》,以此作为各自的思想资源。胡安国所选择的是《春秋》。
胡安国在《春秋传.序》中说:“近世推隆王(安石)氏,按为国题,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逆乱肆行,莫之过也,至此极矣!”据《先公行状》载:“初,王介甫以字学训经义,自圣千圣一致之妙。而于《春秋》不可偏旁点画通也,则诋以为‘断烂朝报’,直废弃之,公……研索玩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之《春秋》,慨然叹曰:‘此传心要典也。’”据此,胡安国重视《春秋》,是因为王安石废弃《春秋》。按王安石重视《周礼》确是事实,但却并没有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加以废弃。
实际上,胡安国潜心于《春秋》,诚与《春秋》的性质相关。孟子讲:“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春秋》记载的是天子之事,而孔子留意于其中的是由其事而见其义,即所谓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通过标示其义,而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换言之,《春秋》是一部以历史而见证国家管理思想的著作,既适合思想家引来作为阐发自己思想的载体,同时又可使思想家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时避免空论。而胡安国以为,赵宋之祸,正是因为“乱伦灭理”,丧失了治国之“义”,故他治《春秋》,便是要藉此以针砭时政,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卷二七《经部·春秋类二》)
因为《春秋》史事与义理并蓄,故后来治《春秋》者便有偏重。《春秋》三传中,《左传》取事,《公羊》、《谷梁》取义,汉以后的古、今文经学家也沿袭了这种偏重。宋儒以义理见称,各家多以义理说《春秋》。胡安国虽然“事按《左传》,义采《公羊》、《谷梁》”(《春秋传·序》),但终因意在时政,故实未能“一一悉合于经旨”(《四库全书总目》语)。对此,朱熹曾多有指正。(详见《朱子语类》卷八十三)当然,对于《春秋》管理国家的基本思想,即《庄子·天下》所说的“《春秋》以道名分”,胡安国则把握得非常准确,并作了反复详尽的发明。《先公行状》称:“盖子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讨乱贼,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术,必再书屡书,恳恳致详。”这个宗旨,正也是理学所要确立的价值体系于现实中的贯彻。对此,朱熹持有同样的认定。朱熹讲:“《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正因为此,故朱熹虽对胡安国《春秋传》的牵强附会多有不满,他自己也因为《春秋》疑难甚多、未必字字有义而终生不愿强为之疏解,且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徒费精神于此,但遇需要时,终究取胡《传》为多,他讲:“某生平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 (同上)胡《传》为后世科举所重,也正是因为它对《春秋》思想的把握与理学的精神合若符节,而不是因为胡《传》本身的学术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讲:“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于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遂独用安国书。”胡《传》对《春秋》史事的解释虽多有牵强,如朱熹所言,而且事实上,胡安国欲藉《春秋》研究实现经济之志具有很大的理想性,但是,胡安国于历史中求义理的治学路径对南宋理学的建设却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这个意义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洛学内倾化的纠偏。洛学自拈出“天理”,标示出价值本体以后,如何体认与践履这个价值本体,成为关键性的问题。二程提出用“主敬’取代周敦颐的“主静”,目的是既要在形式上使儒家的工夫区别于佛家,更要在内容上持守儒家直面生活的本质。但在程颐指出进学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以后,如何来落实“格物”,成为程门弟子的问题。然而程门弟子在探索“格物”的问题上,无不取内倾化的向度。其结果,严重者直接在思想上混同儒佛,如游酢;其次则使洛学转向心学,如程门再传的王苹与张九成;最好的也只能是如李侗那样涵养成“沛然行其所无事”(《延平答问》)的气象。洛学的这种内倾化影响是非常大的,即便是有胡安国这样极重史学倾向的家学影响,胡安国的侄儿胡宪(字原仲,号籍溪)的学术风格,与李侗仍是非常相近。这种内倾化对于南宋儒学在心性方面的精深细微的阐发与实践,即挖掘价值本体的成立依据,以及据于其上的道德认知与实践,当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但是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即价值建构与认同中的主体性张扬,促使相对性的巨幅增长。这种相对性增长的直接结果,便是消解理学家“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建构普遍价值的努力。胡安国将史学引入理学,将价值的建构设定在历史事实的检讨上,这对南宋儒学的建设不仅具有克制内倾过度的作用,而且其本身便足以构成南宋儒学构建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与思想内容。
其二是对南宋儒学由价值兼而成为知识的一个有力推动。毫无疑问,儒学就其宗旨是要追寻价值本体并加以体认与践履。但是洛学的严重内倾化,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宗旨单纯地凭藉纯个体性的自觉来达到,这不仅会造成如上所说的相对性泛滥,而且事实上也不足以使儒家的宗旨成为社会民众的努力方向。朱熹评价大程子宏大、小程子亲切,正是指出大程子只言涵养虽具气象,却不及小程子致知格物来得方便,示人以门径。因此事实上,整个宋代儒学的建设,在追寻价值本体的同时,也在努力使之知识化。换言之,宋代儒学在确立“道”的同时,也在建构“学”,《四书》的形成及其重要性超过《五经》,便是这种努力的体现。只是,儒学的知识体系虽然是以“经”为本(《四书》是其体现),但“史”却也是儒学整个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门类,在很大程度上,“史”印证着“经”。
应该看到,寓褒贬于史事之中的史论,即于经验性的事实中来印证价值,一开始便为宋儒所喜爱,这从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新五代史》起就已十分明显。但是历史学家的史论,终与哲学家的史论有很大的区别。史家的史论重在史实,所欲陈述的思想寓于其中,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可谓典型代表,《春秋》本身其实也是这样的著作。而哲学家的史论却重在借史事言思想,史事当然要真实,但这种真实主要是要把握住大的方面,至于细节上的出入常不以为然。胡安国的《春秋传》便是如此。不仅胡《传》,胡安国长子胡寅所撰《读史管见》也是如此。胡寅撰《读史管见》,正是因为他觉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议少”,故“用《春秋》经旨,尚论详评”。(胡大壮:《〈读史管见〉序》)因此,《读史管见》之得失,与上文谈到的胡《传》之得失,是一样的。陈振孙论《读史管见》,以为“宏伟严正,间有感于时事。其于熙、丰以来,接于绍兴,权奸之祸,尤拳拳寓意焉”,亦因此,“晦翁《纲目》亦多取之”。(《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别史卷》)而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胡安国之传《春秋》,于笔削大旨,虽有发明,而亦颇伤于深刻”,胡寅秉承家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论以为:“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王应麟《通鉴答问》谓‘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诚笃论也。又多假借论端,自申己说,凡所论是非,往往枝蔓于本事之外。”(《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九《史部·史评类存目一》)然而,对于哲学家而言,人类历史的意义,决不在历史的陈迹本身,而在于历史是人类精神发展的见证,历史只是因为人类精神的存在而获得意义。因此,对历史的衡定,决不是让人类的精神苟且迎合已为陈迹的事实,而是要以人类的价值确认对历史作出批判。胡安国的《春秋传》,包括胡寅的《读史管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南宋儒学所追寻的价值,铺设起基于经验性事实(历史)之上的知识。它的作用,虽不及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但方向是一样的。
总之,将史学引入哲学的玄思,从而使哲学的思辨获得史实的支撑而不流于为玄想而玄想,使哲学得以落实在现实的人类生活并以为指引,以及为价值铺设源自史学的知识基础,这个工作就南宋儒学而言,无疑是由胡安国所开启的。
三
胡安国引史学入理学,对南宋后来的儒学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胡安国的儿子中,长子胡寅、次子胡宁都承继家学,对历史研究情有独钟。长子胡寅,前文已言及。次子胡宁,协助胡安国作《春秋传》,同时又自著《春秋通旨》。三子胡宏虽然由史学转入性理,使湖湘学派的精神为之一变,但胡氏史学理学相融的努力却在湖湘学派之外得到了继承。
这个继承主要是两家,其一是闽学,其一是浙学。而极有意思的是,继承胡氏史学理学相融路数的这两家,由史学中所呈现出的“道”却又截然不同。
关于闽学对胡氏的继承,钱穆作有详解。钱穆指出,朱熹曾于胡氏闽中故居侍坐于胡寅,并得以读到胡安国的《通鉴举要补遗》,“朱子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心有不足,乃见延平。是朱子理学启自延平,史学要与衡麓胡氏一家有关系”。(《朱子新学案》之五十三附朱子通鉴纲目及八朝名臣言行录)这便是说,朱熹的理学思想虽由道南一脉开出,但朱熹的学术研究之重史学却多由湖湘学派所启发。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史学的重视,其重要性在他本人,尽管尚不足以与其哲学思想的创建相比,但是同样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由于朱熹精于考证,史学的素养与学问的扎实远非胡氏所可比肩,因此,朱熹在以史阐道的过程中,虽然宗旨在追寻与建构价值,但是他对学生却给予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使得依托于理学的史学在门弟子那里足以演成自足的学术研究。换言之,史学与理学的相融,对于朱熹的影响尚不足以使他偏离哲学,但对于朱熹后学渐离哲学思想的创造而转入历史学术的研究却是意义重大的,它为理解朱熹理学在南宋后期的知识化发展至少提供了某种契机并指出了某种路径。
胡安国史学理学并重相融的特征对浙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胡安国门下有曾几、薛徽言。曾几传吕大器,即是吕祖谦的父亲;薛徽言传子季宣,再传陈傅良。这意味着胡氏湖湘学对浙学最重要的两支金华与永嘉的学术都有润泽之功。相比之下,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其家学渊源的影响或重于胡氏的影响,婺学终也以文献之学而闻名,表现出比较纯粹的史学特征,学术对于现实的思想性关照并不那么强烈,与胡氏有比较大的距离。但是永嘉薛季宣、陈傅良治学却是与胡氏的学术思想取向一脉相承,这个取向便是全祖望所谓“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宋元学案·艮斋学案》)。
胡氏史学理学之相融,不仅范导了永嘉的学术取向,而且由于这种治学宗旨的一致性,加之学术渊源以及个人活动上的因素,使得永嘉对湖湘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前文已言及,胡宏治学,重理学而轻史学。胡宏生前对胡安国的学术立场虽是继承,但学术思想不再通过史学来传达,而是直接由哲学来阐述,对于兄长胡寅之学则明显表示不满。至张栻,“只说五峰说底是,致堂说底皆不是”。(《朱子语类》卷二十)这意味着湖湘学在其成熟期是明显地以理学为核心,胡安国史学理学相融的学术路径被搁置。但是后来张栻死后,“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胡季随亦从之问学”。(《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作为胡宏的儿子,胡季随于张栻之后的湖湘学派中地位甚高,且颇自尊大,而能受业于陈傅良,足可想见永嘉与湖湘的关系了。
闽学与永嘉学虽然同受胡氏史学理学相融的影响,在史学理学并重的学术范式上有大的推进,如两家都精于考证,使与理学相融的史学摆脱了胡氏那种义理化程度很高的状态,得以发展出实证性较强的史学,为理学构筑了良好的知识平台。但是闽学与永嘉学终究有大的不同,闽学仍沿袭胡氏的基本思想取向,寓褒贬于史实之中,价值追寻与论证、建构仍是其核心,整个学术思想的重心在伦理哲学;而永嘉学固然承袭胡氏史学理学相融的学术思想范式,但基本思想取向却有大的改变,薛季宣、陈傅良不关注史实的褒贬,而重在考量制度的绩效,有效性制度的继承与创建成为其核心,整个学术思想的重心在政治哲学。正因为这种不同,所以永嘉学在文本上也有所取舍,不同于胡氏。胡氏重《春秋》,而永嘉重《周礼》。至于永嘉学与闽学的分歧,自然也便明显地凸现了出来。在闽学,历史成为人类价值理念的表证;而在永嘉,历史所昭示的却是人类开物成务的进程。所见者既相异,所立者必不同,两家最终要在思想上形成交锋,既必然,亦应然。
标签:理学论文; 永嘉学派论文; 胡安论文; 春秋传论文; 四库全书总目论文; 朱熹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读书论文; 读史管见论文; 国学论文; 周礼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宋朝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