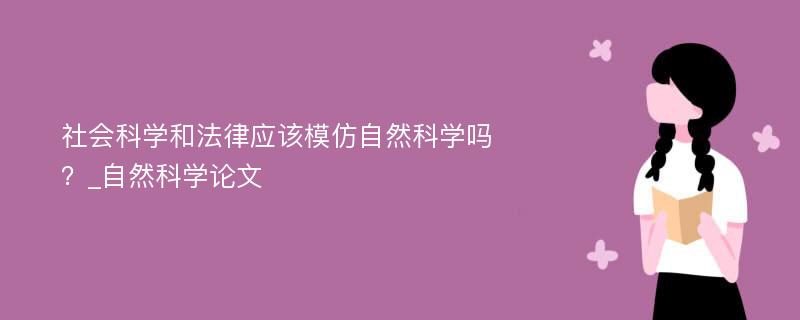
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的现代化历程之中,自然科学无疑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而在中国全力追求现代化的今天,几乎一切都要向自然科学看齐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信条。这样的意识可以见于“社会科学”这个词汇本身——虽然人们曾经试图把社会、经济、政治等学科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但是,久而久之,大家都几乎没有例外地采用了“社会科学”这个词,而且习惯性地把其中各个学科和法学都与“科学”相提并论,在国内尤其如此。这种倾向可见于学术管理人员的思想,当然也可见于各个学科的专业人士。 本文的目的首先是要说明“社会科学”和法学与“自然科学”的多重不同。当然,这不表示笔者提倡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完全隔离,拒绝任何借鉴,而是面对当今“科学主义”——认为关乎人间世界的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同样追求普适规律——的强大威势,更需要澄清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本文之所谓的“科学主义”所指不仅是哲学史中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等影响强大的思想,而更是由于科技在现代世界中所起到的有目共睹的广泛作用,它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无比的威信,从而促使人们认为其方法不仅适用于物质世界,也适用于人间世界。本文强调的则是,唯有认识到两种世界的不同,才有可能有限和有效地借助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来认识真实的人间世界。 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 (一)研究对象的不同 首先,应该说明两者研究对象的关键差别。人是个具有意志、理性、感情的主体,而不是物体,而人间社会是由如此的主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因此,尤其是在实践生活(区别于理论建构)之中,明显在客观性之外更具有主观性,在普适性之外更具有特殊性,在确定性之外还具有模糊性和偶然性。而关乎物质的研究,则只需考虑其客观性和普适规律性。固然,自然科学在其现代发展中,似乎日益关注特殊性,譬如,划分为众多不同的领域/次级学科,分别具有其不同的研究对象、规律和方法,但是,总体来说,自然科学仍然强烈倾向普适主义和纯粹的客观主义。这一倾向,在自然科学的第一个系统化的现代成果牛顿力学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其基本信念是:第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在于研究者并永恒存在的,不带有主观因素;第二,认为自然世界是被几个关键普适规律所支配的;第三,认为关于自然世界的命题与判断可以由可确定的几个基本公理的组合、应用推理出来,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玻姆[Bohm],1971[1957]:130-132;寇恩[Cohen],2002:57-58) 人们多认为,社会研究的最高目标应该是追求、模仿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主义。殊不知,正是普适和特殊以及客观和主观的并存实际才足以说明人与物质世界的不同。其中关键不在于排除特殊而简单偏重普适规律,而在于同时看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并存以及其间的异同和互动。关乎真实人间世界的抽象应该同时照顾到普遍和特殊,而不是把两者简单化约为其单一方面。这也是为什么现有的不同学科共同组成了一个从普适主义到特殊主义的连续体,其两极是普适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特殊主义的人文研究,而社会科学则正居于其间。 (二)研究对象背后的基本关系的区别 自然科学所界定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人类意识之外的自然世界。在自然科学看来,这一研究对象背后起主要作用的主导性规律,是确定性的因果规律。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寻找自然现象中促因(cause)与后果(effect)之间确定性的因果规律,逐渐成为自然科学最重要的任务。对这些因果规律的发掘与认定,逐渐被视作理性(rationality)的重要能力。(冯·赖特[von Wright],1971:2-3)这一特征,在自然科学的核心——物理学那里尤为显著。而物理学中,牛顿力学最早得到系统的发展与严密的数学化。这和牛顿力学本身特别适合处理一对一的确定性因果关系(一个原因对应一个后果,而且这种对应关系是确定性的)有很大的关系。牛顿力学的对象——物体的运动,特别适合用一对一的确定性因果关系加以把握。(Bohm,1971[1957]:5-6,12,34) 在人间社会,当然也有较为明确的一对一因果关系存在,但是,重大的历史现象(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革命、中国近20年的“隐性农业革命”,见黄宗智,2014b,第3卷:第2章;黄宗智,2003[1995];黄宗智,2014b,第3卷:第5章),多源自几个不同来源和半独立的历史趋势的交汇或交叉,在社会经济结构性因素之外,还有源自人的主观意志的抉择,也有实践世界中的无穷的特殊性和模糊性;在确定性的因果规律之外,还存在偶然性;而源自实践中的偶然性的长期积累,更可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对理解人间社会来说,要逼近真实不能从确定规律和抉择、客观与主观、必然与偶然、普适与特殊等二元双方中简单做出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在于看到两者的并存和相互关联。 (三)普适与有限的规律 相应的不同是,物质世界与人间社会间的“规律”性质的不同。前者追求的是确定化、普适化的真实——是能够在实验室里重建设定条件并且没有例外地证实(或证伪)的规律,但在人间社会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条件,最多只能探索到有限真实的有限规律。在我们从经验作出概括和抽象化的过程之中,只能希望达到一种局部有限的真实,而不是普适的、完全确定的,可以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来证实的真实。即便是在现今追求高度“科学化”(形式化)的法学和经济学领域中,也会承认法律/经济是不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无条件地普适化的:譬如,把美国法律不加选择地完全照搬、实施于中国,或把来自美国经验的经济规律不加选择地完全适用于中国。 在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科相对最偏向特殊主义。今天在国内,历史学科尤其带有强烈的完全特殊化倾向,其主流几乎拒绝任何抽象化(概括),只求忠于史实,只求精确“真实”地“反映”、“重建”史实,因此导致了(批判者所谓的)史学的“碎片化”。但这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科学影响的国外历史学科很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学科已经广泛采纳了社会科学众多的方法和理论。这种倾向尤其可见于经济史、社会史、家庭史、人口史等领域,并创建了认识上重要的突破。但这并不等于简单地采用科学主义、简单地追求绝对化的规律、简单地模仿自然科学,而是有限定界限的抽象化、规律化和理论化。 其实,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譬如中国革命,既不可以仅凭叙事来理解,也不可以仅凭社会经济结构来理解,而是要兼顾两者,既要掌握长时段的结构性变迁,也要认识到关键人物的意志和抉择。也就是说,兼顾结构与能动、普遍与特殊、规律与偶然,而且更要看到两者间的互动。中国革命史充满抉择与结构间的张力、相悖以及适应的例子。(例见黄宗智,2003[1995]关于“土改”和“文化大革命”的论析)譬如,适当结合倾向特殊主义的叙事史学和倾向普遍主义的社会科学化史学,要比简单依赖任何单一方更能解释中国革命。 (四)一统的规范认识和多元的理论 自然科学领域较多地认同于单一理论/规范认识。即便如此,仍然会呈现由于规范认识危机而导致的“科学革命”。正如库恩(Thomas Kuhn)说明的,科学界一般倾向于大多数专业人士都接纳同一规范认识(paradigm)的常态,要到积累了众多违反规范认识的经验证据之后,才会形成一种范式危机,最后导致规范认识的修改和重组。(Kuhn,1970[1962])我们可以用以下的例子来阐释库恩的这个论点:17世纪-18世纪,物理学的规范认识是以牛顿运动定律为核心的。在这一规范认识下,物体的运动,可以用严格确定的一组微分方程来描述。给出恰当的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我们可以推算物体在此后任一时刻的运动状态,特别是该物体的位置(position)与动量(momentum,质量与速度的乘积)这两个描述物体运动状态的关键变量。而物理世界的全部现象,最后均可化约、归结到由这样确定性规律所左右的物体的运动。①追求这样带有确定性、可预测性、一对一因果关系的普适规律迄今仍然是(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的主要内涵。 但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微观领域物理实验手段的发展,科学家逐渐发现,在原子层面这样的微观现象领域,物体(粒子)的运动状态存在内在的、固有的不确定性,因此相应的物理理论,只能以几率(probability)来刻画粒子的运动状态。这种非确定性的运动规律,一个最广为人知的表述就是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亦即粒子位置与动量无法同时确定,同时,这一不确定性是可以通过一个数学不等式来描述的。②到20世纪30年代,可以精确分析微观物理现象的量子力学的基本框架已经被建立起来,其基本精神便是对牛顿力学规范认识的否定。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的转变,正是一种由实验领域新发现的积累否定原有规范认识,并且在实验与理论的相互刺激下,催生出新的规范认识的典型历史经验。③今天,牛顿力学的自然观甚至被批评为一种机械主义的决定论(Bohm,1971[1957]:64)。但是,以几率和不确定性为主的科学观至今仍然没有渗透社会科学,其“主流”仍然强烈倾向之前的牛顿力学的世界观。 物理科学的常态是统一的规范认识,而社会科学,正因为其主题以及其性质的不同,不会趋向同样的统一性。而且,社会科学完全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够以普遍有效的可重复的实验方法,对理论/规范认识进行检验和约束,从而保证在整个学术圈中规范认识的一统性。长期以来,社会科学更多倾向一种天下分而不合的常态,在形式主义理论的主流之外,有众多其他影响较大的非主流理论与之对抗(例如,倾向特殊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和实体主义,当然也包括与形式化的新自由主义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后者同样带有强烈的普适主义冲动)。如此的现象是我们这里要论证的社会科学与物理科学实质上的不同的佐证。而这个社会“科学”的“特征”说明的不是其不足,而正是社会与物质世界的实质性不同。 人们其实凭直觉就能相当广泛地认识到,在人们追求的真、善、美之中,唯有“真”应该是部分由科学研究主宰的,而“善”与“美”则明显是特殊化的,不能普适规律化。其实,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即便是在“真”的领域,人与人间社会也与自然世界十分不同,部分原因是“善”和“美”一定程度上也是人间社会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其中占据一定重要性的动因。这也是为什么试图建立科学主义认识的形式主义理论一般都排除关乎“善”与“恶”的道德伦理,而与之对抗的后现代主义和实体主义则倾向强调道德伦理在人间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下面还要讨论)。 对我们拒绝科学主义的人来说,社会科学的多元常态是正面而不是负面的。正是其多元常态使我们可以在科学主义化的形式主义主流传统之外找到更多、更有洞见的理论资源,赋予我们可资借用的非主流资源。 (五)意识形态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从意识形态——背后有政权推动的理论——的作用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不同。在后者之中,可以说绝少见到“左”和“右”之分。这当然和其研究对象的不同直接相关:追求物质世界的规律一般谈不上什么政治意识。而社会科学则完全不同,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会涉及到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几乎都是与社会科学理论交搭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左右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学术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已经完全(再次)占据社会科学中的主流位置的原因。马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同样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都是试图掌控所有不同社会科学学科(包括历史学)的理论。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会看到对其的众多多元化反应和抗拒。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则由于原来的马列主义和改革中舶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并存,几乎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等的多元化理论的局面——当然,仍有不少“禁区”。 以上各项不同说明,我们不该也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不能简单地模仿自然科学、简单地运用其理论和方法于社会科学。 二、方法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简单拒绝自然科学及其方法。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具有一整套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正因为其更可以确定、统一认识,更可以规范化、规律化,更可以凭借能够重复的实验对理论进行检验,更可以较好地结合归纳与演绎方法。其精确性以及对经验证据的尊重是值得我们社会科学界学习的,但绝对不是要像有的机构和学科的管理人员那样要求无条件地模仿和援用。简单地模仿其实会导致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研究,硬把人间社会现象物质化——也就是说,把人间社会简单化和片面化,从而导致科学主义的错误,乃至于意识形态化的认识。 (一)演绎与归纳 在科学的认知方法中,比较广为应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抽象化:一是对经验证据的归纳(induction),也可以说是从具体证据来提出抽象概念(abstraction);二是根据演绎逻辑的推理(deduction)以及与演绎推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理体系(axiomatic systems)来建立普适化和绝对化的真理。前者是对经验证据的概括和论析,应该是通用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下面还要讨论);后者则是一条充满陷阱的途径。 演绎逻辑的典范是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学,这也是西方文明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个传统,被普遍认为是西方文明所独有和特别突出的文明财富。它今天被广泛认可为西方现代哲学学科的核心。譬如,今天美国的主要高等院校哲学系都以形式化、甚至数学化的演绎逻辑为其主要方法,并拒绝纳入没有同等传统的其他主要文明传统(包括中国、伊斯兰、印度文明)的哲学,坚持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结果是美国全国排名最高的哲学系普遍只教西方哲学,排除其他文明的哲学思想,使它们全都被置于诸如“东亚语文”、“近东语文”、“南亚语文”等系,在正规的哲学系里占不到一席之地。④ 今天演绎逻辑推理被广泛用于(自以为是社会科学中最“硬”的)经济学和法理学。尤其是经济学,广泛要求经济学从设定的公理出发,用数学化推理来表述和“证明”。而法学则要求,像韦伯强调的那样,把法律条文完全整合于演绎/法律逻辑。在美国的主流“古典正统”法学传统,即由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1870年-18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开启的传统中,非常有意识地把法学等同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坚持法学可以同样从几个“公理”(axioms)出发,凭演绎逻辑而得出一系列真确普适的定理(theorems)。在兰德尔那里,所采用的方法是从案例出发,但目的不是从众多案例的经验证据来归纳出不同的法律实践,而是凭借演绎推理来从选定的案例建构一个自洽和普适的理论和法则体系。⑤(见Langdell,1880:1-20关于合同法的论述)由此树立了美国法学的主流“古典正统”,更奠定了美国法学界普遍采用的训练和教学方法。其把法学“科学化”的意图的影响今天仍然广泛可见于美国的主要法学院——譬如,它们所采用的“法学科学博士”学位(J.S.D.,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制度,被设定为各法学院的最高学位。 在中国,形式主义经济学今天已经占到绝对的主流地位。其中,在新古典经济学上添加了产权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尤其巨大(下面还要讨论)。至于形式主义法学,部分由于中国学者对演绎逻辑感到难以接受或陌生,并更习惯使用“实用道德主义”思维,⑥则尚未占到与形式主义经济学同等的近乎霸权地位。但是,在全面引进西方的形式主义法律条文的大潮流下,其所附带的形式主义逻辑起到更大影响只是迟早的问题。此外,我们更可以指出,要清醒地做出不同的抉择,中国法学界非常需要掌握美国的“古典正统”法学理论以及德国的“形式主义理性”法学理论背后的形式化逻辑基本思维——这是本文重点讨论兰德尔和韦伯的原因。 归纳加上演绎方法之被广泛援用于社会科学,其本身无可厚非,因为社会科学的认知过程同样包括从经验得出概括,由经验证据得出抽象化的概念,而后从抽象化的概念试图加以推理来延伸。但是,在实际运作层面上,演绎逻辑之被用于社会科学其实常常变成一种简单的从贴近经验的抽象跃进到理想化的“理论”。即便是深奥如韦伯的理论建构,也展示了这样的倾向。首先,他把西方法律历史抽象为倾向“形式主义理性”的演变,突出形式逻辑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具有一定经验证据基础的抽象化概括。(Weber,1978[1968]:784-880[第iv-vii节],韦伯关于法学的论述集中于他的第8章,第641-900页,其中第4[iv]到第7[vii]节[第784-880页]是其历史叙述部分)但是,他进一步把其建构为四大法律类型中的一个(Weber,1978[1968]:655-658),而后更试图论证它是西方独有的、日趋完美的趋势。最终,由于其逻辑体系和形式主义方法本身的驱动,把它论述为一个完全由逻辑整合的自洽体系,与其他的类型形成非此即彼的对立。由此,一再坚持形式理性法律乃是四大法律类型中唯一充分体现现代“理性”的法律传统,唯一真正理想的类型,而其他文明的传统则基本全是非理性的,亦即现代西方的反面的“他者”。(关乎中国的论析尤见第818、845页;亦见黄宗智,2014c,总序,第1卷:001-018;黄宗智,2015;赖骏楠,2015)也就是说,从原先的有限归纳跃进到普适规律和理论。如此的论述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名副其实地成为“理想(的)类型”(ideal-type)。读者明鉴,这里我们需要清楚区别抽象化和理想化:前者是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但后者则是脱离和违反实际的跳跃。 这里,可以再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为例。他从新古典经济学设定的“人是理性经济人”以及“纯竞争性市场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农作物市场被认作最佳的例子之一)的两大前提“公理”出发,由此来论定劳动力的过剩不可能存在。他的出发点和与他同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W.Arthur Lewis)是完全对立的——后者特别强调的则是(主要是第三世界)农业中“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现实。当然,舒尔茨也曾经用其在印度走马观花获得的经验数据为其论点提出“经验证据”,即在1918年-1919年的异常流行性感冒疫症中,有8%的人受到感染,而农业生产因此显著下降。他论述,如果真的有劳动力过剩,那么8%的人受到感染便不会导致生产的下降。(Schultz,1964:第4章)在逻辑上,如此的论析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事实是,疫症感染不会同样程度地影响每个农户的8%的劳动力,因为有的农户没有感染,而有的则全家感染,由此影响总产出。但舒尔茨并不在乎这样的经验实际,因为在他的思维之中,设定的公理和其推演才是关键:如果市场经济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那么,劳动力“过剩”便不可能存在;如果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便不可能为“零价值”而劳动。对劳动力过剩做出如此的定义,本身便是一种仅凭演绎逻辑得出的定义;论者所言的“过剩”,其实多是相对的过剩而不是“零价值”的绝对过剩——后者只是舒尔茨凭其设定的公理来拟造的稻草人。舒尔茨所模仿的正是简单的、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演绎:如果出发点的公理是真实的,而其后的演绎推理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必定也是真实的。在舒尔茨那里,所谓的经验证据,说到底只是一种装饰;演绎逻辑才是一切的关键。(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b,第3卷:第9章)与其对比,韦伯的视野要宽阔得多,并且带有较深的历史研究,虽然最终同样强烈倾向形式主义化的理想建构。 但是,真实的人间社会是不可能像几何学那样凭几条公理来化约的,其经验证据也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确定性,更不可能抽离出可以完全控制的具体条件,经过可复制的实验来证实,而又通过演绎推理达到一种普适化的认识。在不可能做到如此的推演过程的实际情况下,试图建构绝对和普适的理论,只可能要么是像韦伯那样从抽象化跳跃到理想化,要么是像舒尔茨那样从设定的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公理”推演出不符实际的“定理”。 演绎逻辑的典范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在其几何学体系中,首先给出的是一组最基本的“定义”(definitions)。这些定义界定了点、直线、平面等等这些几何学将要处理的最基本的对象。紧接着这组定义的,是五个“公设”(postulates,第一公设是“从任意一点出发可向任意一点做一条直线”)和五个“一般观念”(common notions,第一个一般观念是“和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它们彼此亦相等”)。⑦“公设”和“一般观念”一起,形成作为推理前提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此后任何一个涉及具体几何问题的命题,都可以通过对概念、公理和其他(由概念和公理推导出的)已知命题的组合运用,推导而出。(林德伯格[Lindberg],1992:87-88)譬如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和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便可由基本的公理推导而出。⑧这是一个在设定的前提条件下的数学—逻辑世界中适用的方法,一定程度上适用于物质世界,但用于人间世界,只可能是脱离实际的建构。 正是出于模仿这样的典范的动机,高度形式主义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便设定类似的公理:如“理性经济人”和“纯竞争性市场”,而法学则设定个人权利的必然性前提。而后,两者都由所设定的前提公理出发,凭借推理来得出其自身认作普适的定理。上述兰德尔关于合同基本定理的论析便非常有意识地模仿这套方法。在科学主义的大潮流下,正是因为试图把数学世界中的演绎推理用于社会现象,促使这些学科的“主流”采用如此的理论建构进路。 之后,进一步(像兰德尔领导的哈佛法学院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的芝加哥经济学系那样)制定,所有本学科专业人士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训练,由此形成强大的制度化力量,把本学科专业人士全都推向接纳其设定的前提。如此,更促使本学科大部分人员都把其前提公理和被推演出的定理认作普适的真理,要么把其认定为真实世界的必然状态,要么更简单地把理想化的状态等同于真实世界的实际。 但是,上述的理论前提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建构,绝对不是什么跨时空的普适规律。我们只要看到人们的实际性质,由此出发,便不可能简单地设定人只是简单的纯理性经济人主体。正如上面已经说明,人明显不是简单的“理性人”,也是“感性人”,更可以是遵循道德理念的人。在其实际生活(实践)和人际关系之中,一般都不会遵循单一清晰的逻辑,而是错综复杂和模糊的逻辑。把人简单设定为一个完全理性的个体,完全没有感情化、道德化或偶然化的主体,再把如此的设定当作给定不证自明的“公理”,其实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建构,绝对不是符合人间世界实际的普适真理或规律。 如果从真实的人间世界出发,我们其实更需要把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作为前提,从人们的“实践”/实际行为而不是其理想化的理论建构出发。那样,便不可能制定形式化/理想化的公理,也得不出其后的一系列由演绎推理得出的定理。譬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市场,都是与政府权力密不可分的,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政府政权建立、维护、干预、控制。从实际存在的市场出发,便不会得出(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竞争性市场的理想化建构。同样,符合实际地设定人既是理性人也是感性人,其实比简单的“经济人”建构更能解释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多次危机——它们其实多与迷信必然增值和盲目逐利(贪婪)而不是理性抉择相关。在法学领域同样,如果从法律的实际运作出发,便会看到舶来的法律条文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重新理解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实。譬如,在产权法律领域,其实家庭(及其人际关系)的“权利”一直是主要的,在现、当代则和舶来的单一个人的权利并存。而且,“家庭主义”的产权并不一定劣于个人主义的产权法理,其间差别不在真实与否,而在道德价值抉择。(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5;黄宗智,2014c,第3卷,附录二:285-297) 这里要进一步说明,在社会科学领域,演绎逻辑应该被当作一种用来达到有一定界限的认知或洞见,而不是终极真理的手段。譬如,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就局部真实来建构一个模式,用以进行模式化推理,目的在于探寻出某种被忽视的逻辑关系,借以阐明某种有限的概括。这其实是理论家们常用的手段,但也是常被其门徒或后人错误理解的手段,把其等同于普适规律。 在经济史领域,一个能够阐释这样的方法的例子是农业经济理论家博塞拉普(Ester-Boserup)关于人口增长与农业劳动密集化的模式。她指出,人类的农业历史是一个趋向越来越劳动密集化的过程——从二十五年一茬的森林刀耕火种到五年一茬的灌木刀耕火种,再到固定耕地的三年两茬的“短期休耕”,而后一年一茬到一年数茬。从这样的基本经验概括出发,经过逻辑论析,说明其中的关键在于人地关系的演变:如果有无限的土地,刀耕火种是劳动投入最少的方法,要在一定的人地压力之下才会采用下一步的种植方法。也就是说,人地压力推动了农业的演变。(Boserup,1965;亦见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她的理论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得到珀金斯(Perkins,1969)很好的量化阐明(虽然多半是一种巧合)。这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其所采用作为手段的逻辑推理方法,才能适当地认识到其洞见,而不是错误地把其等同于超越时空的普适规律。 再譬如,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E.Anthony Wrigley)指出,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的关键不同在于其使用的能源的不同,从有机能源如人力、畜力到“基于矿物的能源”(mineralbased energy,如煤炭)。其间的主要变化是,单位劳动力所产能源扩增了许许多多倍(一个矿工一年能够挖掘200吨的煤炭)。(Wrigley,1988:77;亦见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这是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概括,其洞见在于清晰有力地说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间的关键差别。在普遍援用源自工业经济的经济学理论于农业经济的今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限)理论。在(户籍)农民仍然占总人口大多数,以及小家庭农场仍然占农业生产最大比例的中国,尤其如此。这并不是说瑞格里给出了一个永恒的规律,譬如,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地力的有限性问题,土地其实和人同样也是个有机体。但他的理论毫无疑问地在其所限定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洞察力。(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 另一个有效创建有一定界限的理论的例子是农业经济理论家恰亚诺夫(A.V.Chayanov)。他根据家庭作为一个(农业)生产组织单位的基本经验实际出发,凭借数学化演绎推理,说明其与一个雇佣劳动的企业单位的众多经济行为上的不同,同时又返回到经验证据中去验证。他得出的是一系列关乎两者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行为的强有力洞见。例如,在人地关系的压力之下,两者的经济行为逻辑十分不同,一个以消费需要为主,一个以盈利为主。这也是从经验概括到理论抽象再到经验的有效认知方法的例证。在小家庭农场仍然是农业主体的中国,这些理论洞见尤其关键。和瑞格里一样,这并不是说恰亚诺夫打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规律——譬如,他并没有考虑到家庭生产单位在商品化/市场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而是说,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并且特别适用于中国。(Chayanov,1986[1925];亦见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 在法学领域,我们可以从法社会学、法律实用主义、批判法学、后现代主义以及实践理论等非主流西方理论传统吸取认识,但不容易找到直接适用于中国实际的理论。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国自身近百年来的法律实践(区别于舶来的条文),看到许多兼顾条文和社会实际的创新性尝试。但是,在目前西方法理占据绝对话语霸权的情况下,较难看到系统的法理概括和建树。笔者近25年来关于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法律实践研究所特别关注的正是这些实践中的法理创新实例,包括经过一定程度现代化的传统调解制度(尤其是法庭调解),比较独特的当代婚姻—离婚法、考虑到赡养的产权法、侵权法的特殊适用等。笔者在中国古今法律和其实践中看到的是与西方十分不同的,结合道德理念和实用考虑,兼顾抽象和具体、普世和特殊的法律思维方式。它完全可以主导中国今天的法律。(黄宗智,2014c:第3卷) 其实,无论是法律还是经济领域,中国的实践早已远远超前于其理论,其中的众多创新都尚未得到中国自身的理论概括,更不用说现有的西方理论了。在经济领域,中国改革期间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显然如此。在法学领域,现阶段我们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实践中的创新进行适当的理论概括。如此的探讨一方面可以说明中国在韦伯理论视野中的悖论性,一方面可以说明中国创建符合自身国情的法律体系的可能道路。韦伯的理论显然不足以概括中国的实际。(黄宗智,2014c,尤见第1卷:总序) 虽然如此,我们如果从认知手段的角度来理解韦伯的类型学,仍然可以看到其洞见,即从经验实际抽象出“形式主义理性”类型,能够展示一些特定条件间被忽视的逻辑关系——譬如,高度形式化和专业化的法律体系可以(但绝不必然)成为一种防御外来权势侵入法律领域的力量。如此的理解十分不同于简单把这种法律等同于唯一的、普适的“现代”“理性”法律,并把其他文明传统的法律简单等同于非理性的他者。我们必须清楚区分韦伯类型学作为认知手段的价值,以及将其类型学作为真实世界的超越时空的写照或必然的指示的谬误。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多年前已经从一个内部人的角度论证:许多经济学学者会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建构等同于真实,把数学化/简单化的模式等同于真实,从而把真实世界等同于理想化的理论。(Hayek,1980[1948],尤见第2章,亦见第3章、第4章)其实,这些理论并不是如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对外在世界的绝对把握和客观再现,而只是经济学科这一系统内部所建构出来的“知识”的集合。这些知识被接纳为“真”,是因为它们的创制符合了学科训练体系的规范性方法。舒尔茨便是很好的例子。同样,许多法学家都经过类似的形式主义训练,并同样简单地把形式理性法律等同于唯一“真正”的“现代”法律。 把博塞拉普和舒尔茨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博塞拉普的设定前提是历史经历: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不断增长的人口;其结论也限定于人地关系,并且是具体的历史经验。其模式所起的作用是指出(之前人们所没有清晰地看到的)历史经验之中的逻辑关系,适当地、有限地使用演绎推理于从经验归纳出的抽象。而舒尔茨则不同,其出发点是理论前提(公理),而后加上适合其前提的经验装饰,由此得出的结论其实只不过是根据其原先的前提的演绎,其实是循环的论证。两种理论间的差别是:一是从经验到抽象再到经验的理论化,一是从前提到经验再到前提的理论化/理想化。这是个关键的差别。 从中国的法律实践经验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不简单是韦伯凭其理想类型所突出的非理性“卡迪司法”,而更具有韦伯所没有认识到的“实用道德主义”逻辑。至于现当代的中国法律,其给定实际是,中国古代法律传统、革命时代的立法传统,以及舶来的西方法律三大传统的必然并存,而韦伯建构的片面化的形式主义理想类型则明显把西方和中国都简单推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对理解现当代中国法律来说,韦伯的理论只能是有用的对话对象,绝对不是其真实的写照,也不可能是其必然走向的指示。 更有进者,形式化的理论,正因为其高度简单化和绝对化,对当权者来说,特别适合被采纳为统治意识形态,而一旦被政权设定、推广、强加为统治意识形态,便不可避免地会被更进一步简单化和庸俗化。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的帝国主义的借口正是把偷运鸦片进入中国建构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的国际关系大原则,而把鸦片战争建构为西方“文明”进入“野蛮”中国的战争。而今天,同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被广泛作为“软实力”的武器来应用于全球霸权的争夺,运用于跨国公司无限制地在全球逐利的借口和辩护。(当然,今天独立自主的中国可以设定条件来利用全球化资本和市场。)19世纪的形式主义国际法(当时中国根据其自身脱离实际的道德化思维习惯而接纳了“万国公法”的翻译)同样,把其适用限定于“文明”国家,对“野蛮”的中国则使用了凭侵略战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赖骏楠,2014)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绿色革命”便是由农业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政权所推动的一种意识形态,其依据则是上述舒尔茨的理论。当然,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理论话语的表达与社会、政治实际背离的例子——“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便是一个就近的例子。(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03[1995]) 无庸赘述,要贴近真实,我们需要对这样的理论和话语建构具备来自历史知识和意识的警惕和自觉。要借用科学方法,需要有同样的自觉,认识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那样,方有可能真正认识到人间社会的实质,而不是其形式化/理想化了的建构。那样,才有可能适当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不至于被其误导为高度简单化或意识形态化的认识。 (二)演绎与归纳之外的第三方法 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⑨指出,人们十分惯常使用的推理其实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一种凭借经验证据推导出来的合理猜测。譬如,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球都是同一壶里的球,也知道此壶里的球都是红色的,那么,如果从壶里拿出一个球来,它必定是红色的。这是演绎推理,在设定的条件下,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我们并不知道壶里所有的球都是红色的,而是经过从壶里拿(抽样)出好几个球,看到它们都是红色的,由此推测壶里的球多半全是红色的。这是归纳,有一定程度(几率)的可信性,并且可以经过反复实验而证实。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红色的球,并知道旁边壶里的球全是红色的,凭此猜测,这个球多半是从该壶里拿出来的,那样的推测,既不同于演绎也不同于归纳,仅是一种合理猜测。这是一个不可确定的猜测,因为这个红球很可能另有来源。⑩在自然科学领域,这样的因果猜测等于是个初步的假设,可以通过演绎推理来设定相关假设而后通过实验来验证。皮尔斯把这种理性猜测称作“abduction”,即尚待精确化、确定的合理猜测,而不是相对较可确定的归纳(induction),更不是可以完全确定的演绎(deduction)。皮尔斯指出,这样的猜测其实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理性推理,也是医学诊断中的一个常用方法,其实是自然科学设置初步“假设”的常用方法。他争论,这样的合理猜测乃是演绎和归纳之外的第三科学方法,其实是科学认识中的第一阶段,之后才会进入演绎推理和归纳实证。“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乃是三者的并用,不仅是演绎和归纳。(11) 皮尔斯没有区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我们看来,社会科学领域关乎因果关系的理论很像这样的合理猜测。它有点类似于探寻杀人凶手。我们要做到的是,尽可能严谨地找出佐证(譬如,附近并没有别的可能红球来源),尽可能达到较高程度的说服力、可信力(plausibility)。但同时,与自然科学不同,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推测一般是不可能完全确定的,是会有错误的。我们可以凭借演绎推理和对所有可用证据的归纳来尽可能提高这种推测的正确几率。但是,十分关键的是,需要承认我们不能达到绝对真实,因为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设定同样条件的实验来证实我们的推测。我们更不应该像形式主义理论那样,把自己的推测设定为给定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再凭演绎推理来建立定理和整套普适理论。那样的话,只可能是对真实世界的严重误导。(12) (三)计量 与以上论述紧密相关的是计量方法的应用。计量本身无可厚非。首先,量的概念可以起到把我们的经验证据精确化的作用。具体数字和比例要比“很多”、“较多”和“很少”、“较少”精确。即便是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地方/社区的内部,我们也常常需要知道,我们注意到的现象在该处到底具有什么程度的普遍性。更有进者,“量”能够让我们更精确地说明自己从质性经验证据得出的概括/抽象到底具有什么程度的普遍性。譬如,我们从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历史研究或某一微观社区(如自然村)的田野调查得出的经验证据,把其概括/抽象为概念之后,可以通过计量来有效地估计其到底带有何等程度的普遍性——是只限于某种类似的特殊条件的地方或村庄?还是具有更宽阔的普遍性?其实,像这样的量化经验证据,是对我们从经验得出的抽象概念的适当延伸的有用方法。它是一种有效结合特殊主义和(有界限的)较普遍适用性的研究方法。量化既是一种延伸,也是一种限定的手段。 另一种量化研究是在充分掌握质性知识之后,发现不被人们注意到的问题,既可以是根据质性认识而发现的问题,也可以是通过不被人们注意到的数据(或者通过对常用数据的重新理解)来发现广为人们所忽视的认识。以新近的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为例,他通过使用过去鲜为人使用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记录和数据(之前多依赖家计抽样调查数据,不具有跨越代际的历史深度)初步证实,在最近的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最富裕的1%的人所占的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在美国从不到30%扩增到约34%,在欧洲则从不到20%扩增到约24%。之前,从1810年到1910年,同比扩增非常显著,在美国从25%扩增到45%,在欧洲则从约51%扩增到约63%。此后,一度趋向较平等的分配,但在1970年之后,税收率大规模下降,导致分配不公重新上升。(Piketty,2014:349,图10.6) 检视最富裕的10%的人所占的社会总财富比例,结果同样:在美国,1810年不到60%,到1910年增加到80%,之后下降到1970年的约64%,而后再次攀升,到2010年的约70%。在欧洲,从1810年的约81%增加到1910年的90%,之后下降到1970年的约60%,之后再次攀升到2010年的约63%。(同上) 皮克迪解释说,以上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的回报率一般要高于经济增长率。在主要是农业经济的时期,增长率一般低于1%,而资本的回报率则达到4%-5%。这样,长期下来,继承大量资本者越来越富,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增长率显著上升,达到3%-4%的地步,而同时,由于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累进税率较普遍地提高(在美国最高超过70%),分配趋向平等。但之后,累进税率降低,经济增长率也降低,财富不均再次回升,导致1970年后40年的持续攀升。 据此,皮克迪呼吁,各国政府需要再度采纳较高额度的累进税率,甚或是新的“资本税”税法,不然,社会将重蹈覆辙而趋向越来越不公平。(Piketty,2014:347-358;亦见崔之元,2014对Piketty,2014全书的论析) 此书引起很大的轰动,主要是因为其上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精细计量研究,对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带来了强劲冲击,可以说很好地展示了计量研究所可能发挥的威力。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甚至写道,皮克迪证明了不平等趋势这个事实,是个“值得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a Nobel Prize-worthy contribution)。(Summers,2014)其实,皮克迪著作的关键不仅是精细的计量,更是独立思考与创新,而不是不加思索地接受主流“权威”理论。 但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不是这样由经验证据和与其紧贴的概括出发的计量,而是另一种计量,即从给定的形式化理论并由其产生的时髦“问题”出发,由此定下某一“假设”,而后搜集数据来证实该“假设”。上述的舒尔茨便是一个例子。又譬如,从市场化和私有化必定会导致更高效率的理论前提出发,由此来估计私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的各种要素的生产率(或要素的综合生产率),借此来试图证实自己已经认为是给定的真实前提。如果数据不符合原先的假设,则指出现实的不足,得出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运作尚不够完善的“结论”,凭此来提倡进一步朝向早已被理想化了的“理论”和其前提条件的改革。一个就近的例子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试图通过计量研究来“论证”国有企业必定是低效的,据此拒绝任何混合所有制,要求完全的私有化。(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殊不知,中国国家(包括地方政府)在改革期间的发展中,其实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且,在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中,中国作为后来者,其实只有通过国家机构在资源和资本等方面的特殊优势方有可能和世界先进的大规模跨国公司竞争。(见黄宗智,2010,2012)形式主义的计量研究其实多是一种理论先行的“研究”,其实质是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其推理其实已经包含在其当作前提的公理体系之中。它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数据游戏,而且高度意识形态化,与真实世界无关,但今天却是我们常见的“科学”“研究”。 那样的研究,究其根源,最终还是来自对形式主义理论的盲目接受,把其等同于普适规律,试图借助计量来“科学地”“证明”自己已经认为是给定的真理。这是没有真正求真动机的“研究”,是不会有创新性发现的研究,也大多是可以利用、雇佣他人——如研究生——来不经批判思考做的经营式“学术”。 另一种常见的计量研究不带有(自觉的)理论意识,是简单来自对数字和对(误解了的)科学方法的盲目信仰。用于历史学科,那种计量常常缺乏基本的质性知识,使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士对其所提的问题和所追求的答案要么觉得完全不靠谱,要么觉得再明显不过,但这种研究的组织者却往往能够凭借科学主义的包装而获取资助,由此组织一批学生来为其“项目”“打工”。 以上两种研究如今常被学术管理者认作“科学”的研究,并直接影响到其所支配的项目资金的“发包”。(关于“项目制”的论析,见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其根源在于对科学主义的迷信,错误地把人间社会等同于物质世界。 三、兼顾普适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社会科学 (一)形式主义理论为什么会成为“主流”? 在物理科学里,演绎和归纳是相互证实和推进的。这是因为其所研究的物质世界本身是带有可确定的规律性的。由归纳得出的规律,以及基于这些规律建构起的理论体系,时时刻刻都需要接受可重复的实验方法的检验。上述的牛顿力学便是如此,至今仍然适用于一般生活中的物质世界。其后的量子力学的建立同样是由归纳和演绎相互刺激而促进的所谓“范式革命”。 我们可以根据光量子理论——这是通向量子力学的关键一步——的形成来更具体地说明物理学中理论与实验、演绎与归纳之间相互刺激的关系。在1905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提出此理论之前,物理学主流将光理解为一种连续分布于真空中的一种电磁波。由此,光所携带的能量,也被认为是在空间中连续分布的,并且可以无限细分为任意小的部分。这是与一般物质(例如水、金属、空气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般物质被认为由大量离散的原子构成,该物体所携带的总能量,则是构成它的各个原子的能量的加总,是不连续分布的,不能被无限细分。这种光的波动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光学现象,例如光的衍射和散射。(Einstein,1998[1905]:177-178) 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实验进展,尤其是黑体辐射(13)与光电效应(14),却与上述光波动理论存在明显的矛盾。黑体辐射实验数据显示,辐射源向外散发的光束所携带的能量是不连续的。光电效应实验数据显示,光与金属板上的电子之间进行的能量传递,同样是不连续的。(蒂尔[Dear],2006:142-143)基于这些实验的启发,爱因斯坦提出将光同样视为一种由基本的单元——光量子构成的物理对象。(15)由这一新的光量子理论出发,立刻可以推理而知,光在辐射和传递过程中,其所携带的能量也是离散的而非连续分布的。由此,光量子理论及其数学计算可以很好地解释黑体辐射与光电效应的实验数据。此后该理论不断被新的实验证明其有效性,并成为后来一些重要的工业技术,例如激光、半导体和光纤通信等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支柱。上述光量子研究是“真正”的现代科学方法的例证。它很好地展示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特征:合理猜测加上演绎和归纳的相互刺激和支撑(及其相关数学计算)。同时,也可以被视作自然世界的一种支配性规律的例证。 由于科学主义的巨大威势,社会科学从来没有放弃过试图得出像物理科学那样的关键性普适规律。但是,人间世界,正因为其与自然世界在本质上的不同,其实际是由对立的二元或多元所组成的,既带有逻辑性和可确定性,也带有悖论性、偶然性、特殊性。而演绎逻辑最基本的要求则是从设定的公理出发,通过严密推理来建立定理。它是一个带有严厉的自洽性要求的方法。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所有的定理都必须在逻辑上符合原定的定义与公设和公理。它不允许例外、不允许悖论、不允许模糊或偶然。因此,在人间社会中,仅凭演绎得出的普适公理,必定会和从实际得出的归纳带有一定的张力、背离、矛盾。两者是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相互证实的。这是为什么形式主义经济学在追求普适规律的驱动下,强烈倾向摆脱归纳而单一依赖演绎来设定片面化、理想化的前提“公理”,而后试图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学凭借推理来建构其普适规律。这也是为什么形式主义理论长期以来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尤其是侧重特殊的理论,如实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强有力挑战。 但如此的挑战却没有导致类似于物理科学界那样的范式革命。部分原因是,关乎人间社会实际的归纳不可能带有和物理世界同样的确定性——因为在人间社会中,不可能通过实验来复制指定条件而证实可确定的规律,它不可能对形式化理论带有同等的挑战力。因此,面对相悖的经验实际,形式化理论仍然有余地来坚持争论,其形式化理论本身是正确和真实的。如果当前的归纳不符合其理论推理,这要么因为其归纳是错误的,要么因为经验实际尚未达到其必然发展到的状态。形式化理论惯常借助“反事实的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来卫护其理论:如果某一经济体能够更高度市场化,就必定会呈现理论所预测的现象;如果它具备更完全的私有产权,便必定会更像理论设定那样更高度发展。(关于反事实推理的进一步讨论见黄宗智,1993[1991]) 但是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多次危机——最主要的当然是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2008年的金融海啸,都完全没有被经济学家们所预测到,实际上完全违反其主流理论所设定的图景。这其实是形式主义经济学试图追求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规律和可预测性的失败的明确实证。但是,虽然如此,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之后,形式主义经济学仍然能够对其理论略作修改和补充而卷土重来,再次以其形式逻辑化的理论来占据学科的主流。在法学领域,韦伯—兰德尔型的形式主义同样,在经过众多经验研究和其他理论传统——如历史法学、法社会学、实用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实践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一再强有力挑战其普适意图之后,凭借科学主义和演绎逻辑的强势再次成为其学科的主流。(详细的论析见黄宗智,2014a) (二)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本文强调,研究真实人间世界的社会科学,不应该从形式主义理论出发,因为其所设定的前提公理只可能是抽离人间真实世界的高度简单化、片面化和理想化的设定,而且,由于形式逻辑的驱动,必定会把整套理论逼向排除悖论和相反的实际,进而绝对化和普适化。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摆脱由形式主义理论主导的认识方法而从实践出发,也就是说从紧贴真实世界的经验出发,而后由此概括/抽象,再凭借推理来发现特定经验现象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再返回到经验中去检验,如此不断往返,方才能够避免演绎逻辑的理想化驱动,方才能够兼顾特殊和有限度的较宽阔适用性。这是为什么本文在上述的例子中一再强调从经验/实践出发,避开形式化理论那样的普适主义驱动。(详细论析见黄宗智,2015)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陷入简单的特殊主义的泥沼之中。特殊经验的碎片化叙述虽然能够澄清个别史实的真伪,但不可能就此提高到抽象化的认知层面。认识不应该只停留在像搜集邮票那样的堆积,而是必须配合抽象化概括。事实和概括的适当结合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认识。 但仅此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试图尽可能把研究得出的发现朝向更宽广的含义推延,甚或对其因果关系做出合理猜测——是有限度的扩延和理论化,而不是绝对化和普适化。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同时照顾到特殊性可能包含的可以被有限度扩延的适用性,以及有限扩延的适用性所包含的特殊性,如此方有可能从特殊的经验积累中挖掘出真正的洞见。 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人间世界一系列的并存二元因素:如客观与主观、普适与特殊、理论与实践、抽象与经验、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等。我们的研究应该尽可能兼顾二元双方,起到双方间的媒介、连接作用。而演绎主义则因为其排除特殊性和偶然性而强烈把我们的思维推向在二元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在上面看到,韦伯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真实世界是个二元(多元)并存和相互作用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做的是使用能够兼顾两者的认知和研究道路。(详细论析见黄宗智,待刊,尤见导论) 更有进者,我们绝对不该放弃理论领域,让它变成完全由形式主义主宰的天下。历史告诉我们,形式化理论,尤其是被政权所采用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理论,是具有极大威势的(核)武器。正因为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理论高度简单化,当权者多倾向于采用其为意识形态,由此更壮大了其威势。我们需要做的是,从真实世界的视角来与之进行对话、质疑,并提出不同的、更贴近真实的有限度理论。对习惯把自身设定为特殊主义研究的历史学学科和区域研究来说,此点特别关键。我们需要认识到,正是从经验出发的研究才是最有资格提出理论洞见的研究,绝对不可放弃自身在理论界应有的发言权。 (三)有限的理论vs.普适的理论 笔者在上面列举了几个有效的兼顾(有限定条件和范围的较宽阔的)适用性和特殊性的理论的例子。人间世界和历史固然包含无穷无尽的特殊事实,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扎实、深入的研究来察觉特定经验现象之间的逻辑/因果关联,而凭借有限度的推理来精确地说明这些关系,进而把原先从经验证据得出的抽象概念进一步延伸、推广,由此形成具有一定洞察力的局部的/有限的适用性的理论。而后,返回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其真确性,如此不断往返。如此的理论的目的不是普适规律/理论,而是局部和有限的抽象及其延伸。其威力在于对相似历史现象/实际之下的适用性,而不是简单的普适性。 也可以说,我们要提倡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是一种结合(倾向特殊化的)实践研究和(倾向普适化的)理论抽象,在特殊中探寻更宽广的(有限)适用性,在理论中探寻能够兼顾特殊的概括。对待质性和量化研究,我们同样提倡兼顾两者,结合使用。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都必定要这样做,研究者完全可以也应该各自追求其所最喜欢或做得最好的一种研究。虽然如此,面对真实世界的无穷多元和复杂性、偶然性,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多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和学科来逼近真实及其所包含的逻辑关系,而不是试图把其化约为形式化普适理论/规律。笔者认为,这样才是面对人间世界的实质性所应该使用的真正的“科学方法”。 这里,有的读者也许会联想到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的所谓“中层理论”,它在专业人士中影响非常之大,描述了其学术实践中比较普遍试图采用的方法。默顿争论,宏大的(关乎全社会系统的)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障碍,因为它们是不可论证的,只会导致无谓的争执,而他之所谓的“中层理论”则是可以论证的,也是可以积累的。(Merton,1968:第2章)这里,他所强调的结合经验证据与理论概括的方法和我们提倡的研究进路具有一定的交搭性。 但是需要说明,不同的首先是,默顿没有明确提倡我们这里所说的从经验证据到概括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他也没有探讨演绎逻辑在形式主义理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我们为何需要把它们置于一旁。同时,他的设想最终仍然是一种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设想,认为人们可以凭借众多中层理论的积累和“巩固”(consolidate)而逐步形成全面完整的理论,由此来建树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规律/理论。(Merton,1968,尤见第2章)而我们则认为,如此的理念本身便是错误的。我们提倡的是另一种研究,即从人间真实世界的多元、悖论、模糊性出发,承认绝对化普适理论/规律之不可能,但同时,不是完全拒绝普适主义的演绎逻辑,而是排除其绝对化和普适化驱动,而把其当作手段来运用于发现真实世界中特定条件下的逻辑关系,借此来建立局部的但是具有洞见的有限适用理论。 我们的用意并不是要完全拒绝形式主义大理论。首先,因为它们原先(在其形式化和普适化之前)多含有一定的洞见。排除了其夸大的包装,便能看到其洞见。只要我们不把它们当作给定、全面的真理,完全可以从他们得到一定的启发。同时,如果适当配合对其提出挑战的非主流理论,会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譬如,从两者的交锋点来提出问题。最后,如果是像韦伯(和马克思)那样极其宽阔的理论,与之对话会有助于拓宽自己的视野。 这里提倡的方法的关键在于追求特定经验条件和界限下的理论。其实,今天的自然科学方法的重点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再是追求几个关键的支配性普适规律。伴随大量有限规律的发现,更重要的工作是对各个规律的适用范围的精确限定。库恩之前所谓的“规范认识革命”其实更多是一种叠加性而不是颠覆性的发现:牛顿力学仍然适用于相当广泛的领域之内,例如人类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建筑与工程设计;而在物体速度接近光速以及处理宇宙中极大宏观尺度的时空现象时,则需用相对论代替牛顿力学;在极为微小尺度的原子层面,则需应用量子力学。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下,自然世界日益被视作拥有无限丰富的侧面。科学家最多能够构建有限的理论和规律来把握自然世界某些侧面的性质,而无法做到将自然世界的无限复杂化约、还原为几个普适规律。(Bohm,1971[1957]:31)也许,正是限定条件下的有限规律的探寻,才应该是我们社会科学所应该借鉴的自然科学方法。 以上的论述中已经举了一些具体例子,这里我们可以加上科斯(Ronald H.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来进一步说明此点。他精辟地指出,之前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极少考虑到“公司”(firm)的运作逻辑,只考虑价格以及供给与需求。在一个像20世纪美国那样高度市场化、法规化和公司化的经济世界中,作为一个逐利体,公司的“交易成本”特别关键——诸如信息、交涉、合同、执行、验收以及解决纠纷等在交易中所必定涉及的成本。如此的交易需要一定的法规制度环境,不然,交易会变得非常混乱而其成本会变得非常昂贵。科斯由此做出推论:譬如,公司的组织逻辑是要做到最低的交易成本——它会借助扩大公司自身的规模和功能来尽可能降低其交易成本,直到其边际成本变成大于凭借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同来进行同样的行为的成本。这套理论(科斯自己说他21岁的时候便已经说明其基本轮廓)原本显然是一个具有特定条件和经验根据的概括,也用上了逻辑推理。(Coase,1988,1991) 与科斯相似,诺斯(Douglass C.North)的出发点是在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市场机制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之上,对其做出了以下的修改和补充:在市场交易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创新,而稳定和有保障(“高效”)的产权是创新的主要激励动力,由此才会推动其他相应的制度变迁,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则没有考虑到私有产权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North,1981,尤见第1章、第2章;亦见North,1990,尤见第13章)这也是带有一定经验条件和根据(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法规制度)的见解。 1997年,诺斯与科斯共同创建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North,1993,Addendum,2005)在两人的诺贝尔奖金象征资本以及一定程度的科学主义的推动下,试图把(只有私有)产权(才会推动经济发展和创新)设定为其普适规律,由此来解释所有的发展与欠发展经济现象。正如诺斯自己说明,他出身于(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一般比较侧重特殊),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都在追求解释经济为什么发展和不发展(也就是说,普适的经济规律)。正是由于那样的深层冲动,促使他试图把自己原先的(有特定条件的、有限度的)洞见建构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普适规律,配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建构,由此来分析历史上所有的相关经济现象。他争论,历史上最高效的产权“制度”是稳固的私有产权,在竞争的环境下,它会取代低效制度(虽然如此的变迁也可能会被独裁、专制的制度所妨碍),由此推动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体的高度发展。(North,1993;North,1981,尤见第3章)在他实际的经济史研究中,虽然论述得非常复杂和多元,甚至不可捉摸,但其核心其实主要是凭借其设定的普适规律(虽然是自我表述为尚待证实的理论假设),来阐释西方的成功发展经验以及其他地方的欠发展经验。最终,其实和舒尔茨一样,其经验论述成为一种只是为了突出其所设定的普适规律的装饰。两人的研究最终其实同样是前提先行的理论演述。 其结果是一个由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形式主义法学合而为一所组成的理论体系,同时凭借两者来建构其“新制度经济学”的“普适公理”。说到底,它也是一种类似于韦伯那样的自我正当化、普适化理论,等于是说明现代西方优越性的必然。之后,它又被“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采纳为其意识形态而进一步绝对化、庸俗化。在中国则更被其信仰者当作绝对真理(“天则”)来使用,据此一再提倡全盘私有化,拒绝任何混合产权制度,拒绝任何国家干预,要求完全引进被理想化了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全盘西(美国)化。 我们认为,要认识到科斯和诺斯真正的洞见,我们需要把他们返还到其原先有限度的、贴近真实世界的概括,剔除其后的简单化、绝对化、普适化和最终的意识形态化。后者只可能衍生出没有独立思考的伪学术和伪科学。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对普适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要具备来自历史和理论知识的警惕。我们反对的是理论先行/决定的研究;我们要提倡的是从问题而不是给定答案出发的学术研究。由此,方有可能认识真实世界。 (四)公理设定还是价值抉择? 最后,需要说明,我们绝对不是想要提倡一种纯回顾性的学术,因为我们认为,学术应该带有改善我们的世界的关怀,应该带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我们要清楚区别公理设定和价值抉择这两个不同的前瞻方法。我们上面已经看到,形式主义理论的一个惯用手段是把其(实际上是)价值的抉择建构为价值中立的科学公理,例如,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和法学理论中的个人权利。前者归根到底其实是西方源自启蒙时代的关乎理性的理念,不是什么“不证自明”的普适公理;后者则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关乎人的灵魂的永生性的信仰,同样不是一种属于绝对真实的范畴。而在中国文明核心的儒家思想之中,并没有设定这样的公理的冲动,其核心理念明确来自关乎人间社会的道德伦理,而不是模仿自然世界的普适公理,也不是来自关乎死后来生的宗教信仰。 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具有很重要的不同后果。把理念设定为普适公理,会促使人们把自己原先带有一定特殊性的价值抉择普适化为绝对真理。结果是,原先的价值抉择被赋予了科学和绝对真理的“公理”标签,甚至进而(像韦伯的理想类型那样)完全拒绝道德抉择,把道德归类为带有强烈“非理性”的“实体主义”。正因为如此,驱动了一系列的排他抉择,包括把西方文明普适化和绝对化,把非西方文明排斥为非理性的他者。 中国传统中的道德抉择则很不一样。它的出发点是关乎应然的道德抉择,不是科学主义/自然主义中的普适公理/规律;它不带有从公理演绎出普适真理的冲动。它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不同。正是出于如此的思想体系,中国文明更能容纳不同的理念和道德抉择,不会像西方文明传统那样强烈倾向排他的普适化,把自己等同于唯一的真理。也就是说,它不带有同等的科学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它不会导致形式化的科学主义理论。 两大文明之间这方面的不同最终是关于“真”与“善”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现代西方科学文明强烈倾向于把道德抉择排除在“真”之外,强烈认为“真”完全归属于科学,并在近、现代世俗化的大趋势下,强烈把“善”划归宗教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更特别提倡和自然科学同样完全价值中立的学术。这也是本文所谓的“科学主义”的部分内涵。而高度道德化的中国文明则不然,一直把“真”和“善”并置于人间社会,认为缺一不可(虽然也附带有一定程度的把“善”等同于“真”的冲动),不像现代西方文明那样,把两者推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其实,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大师康德,早已对此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论析,提出“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概念,把其作为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pure reason)和实践之间关乎道德价值的关键媒介。这就是他著名的“绝对命令”——“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16)——的用意,要求以此为标准来在众多带有一定特殊性的、指导行为的道德价值中做出“理性”的抉择。(17)笔者认为,儒家的“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与此带有一定的共通性,今天仍然在调解制度中被广泛援用,足可用来指导我们今天的道德价值抉择。(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5) 笔者自身的道德抉择可以说是谋求普通人民的福祉,虽然并不排除其他的价值抉择(如求真、求实、求乐趣)。在我们看来,坦率表明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佯装不可能的价值中立,才是诚挚的学术,才是对我们研究的对象和我们的读者的尊重。如此的价值抉择会影响我们的志趣和问题意识,但并不影响我们学术的求真和求实。在我们看来,完全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学术理念既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错误的理念。其实,那样的设定本身便是一种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选择。我们认为,学术研究不仅必然带有价值取向,而且应该带有如此的取向。我们追求的不仅是要认识到人间世界的实然,也是怎样去改善这个世界的应然。 我们认为,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是结合演绎与归纳缺一不可的方法,但社会科学和法学的形式主义理论,在科学主义的驱动下,一贯偏重演绎。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真实的人间世界的二元性和多元性、悖论性和矛盾性、规律性和偶然性,其经验证据几乎必然(起码部分)违反演绎逻辑所要求的一致性和自洽性。正因为如此,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形式主义理论最终只能依靠(从设定“公理”来推论定理的)演绎方法来建构其所追求的普适规律。那样,只可能成为片面的、违反实际的理论建构。为此,我们提倡的是,从真实世界的经验证据的归纳出发,借用合理猜测与推理来挖掘特定经验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来发现符合实际的洞见和建树有特定条件和界限的理论,而后再返回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那样才是真正科学方法的恰当使用。同时,在选题方面,研究者完全可以坦诚地表明自己的道德价值抉择,而不是像形式化理论那样,试图把自己的研究包装为完全价值中立的科学。价值抉择并不影响求真、求实的研究,反倒是科学主义的价值中立标榜才会真正误导读者和研究者本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摆脱科学主义而适当结合归纳、合理猜测、演绎和道德抉择来认识真实的人间世界。 *本文原稿由黄宗智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述,高原(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后转入社会经济理论与历史研究)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述,而后共同修改写成。感谢白凯、赖骏楠、彭玉生、余盛峰和张家炎的详细阅读、批评和建议。 注释: ①对牛顿力学及确定性机械论的一个简洁总结,参见Bohm,1971(1957):34-35。 ②与不确定性原理相关的实验,及该原理的数学描述,参见Braginsky and Khalili,1992:2-11。 ③关于量子力学这一新“规范认识”的形成,一个简明的介绍可参见Dear,2006:142-148,其中包含了促进量子力学形成的主要实验现象与理论探索。 ④这是笔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主持中国研究中心时试图向哲学系介绍、引进中国哲学专业教授的亲身经历。 ⑤兰德尔其实著作极少,他的影响主要来自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开启的教学方法。虽然如此,一篇能阐明他的观点和方法的例子是Langdell,1880:1-20,这是关于该书所选编的合同纠纷案例的导论。亦见Grey(2014:第3章)关于兰德尔的细致分析。 ⑥这是笔者对中国法律思维的总结表述,见黄宗智,2014c,第1卷:第8章,亦见第3卷:第8章。 ⑦关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定义、公设及一般观念的详细内容,参见Heath,1908:153-155。 ⑧此定理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Euclid's Elements)第1卷中的第47个命题,其具体证明参见Heath,1908:349-350。 ⑨皮尔斯、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一般被视作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三位大家。詹姆斯是皮尔斯的同学,杜威则曾师从皮尔斯。关于皮尔斯的最好的简短介绍是:Burch,2014。 ⑩这是Burch(2014)给出的阐释性例子。 (11)譬如,见Peirce,1998:第16章(即其1903年在哈佛讲解实用主义的第七讲)。皮尔斯著作极多,已发表的约有一万二千(印刷)页,另有约八万页未曾发表的手稿,涉及面极广,从数学、逻辑、语言到历史和经济(其全集尚在整理和陆续出版的过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写作带有较严重的“初稿”气味,文字有点晦涩,思路有时也比较混乱。同时,其本人长期从事应用科学(大地测量)的非学术职业。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更侧重实用。今天,他被比较普遍认为是实用主义传统中最具有创见的哲学家。 (12)近年来,哲学学术界纠结于试图通过演绎逻辑来确定皮尔斯关乎合理猜测的概念,从“最简单的解释是最佳解释”这一“定理”出发,试图把合理假设到确定规律的过程形式化,并逐渐把合理猜测(abduction)改述为“最佳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Douven,2011)我们认为,对社会科学来说,如此的追求没有实用意义,其实是违反社会科学所应该研究的真实人间世界的基本性质的形式主义追求。 (13)黑体指的是一个完全吸收而不反射任何外来电磁波的物体。但同时,该物体仍会向外散发电磁波,称为黑体辐射。因此,测量该物体(黑体)向外辐射电磁波的实验数据,能够排除那些并非来自该物体的外来电磁波的影响,从而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个物体向外界辐射电磁波的机制。 (14)光电效应指的是光照射在金属表面上激发出电子的现象。 (15)实验现象的启发在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理论的原始论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可参见该论文的开篇部分(Einstein,1998[1905]:177-178)。 (16)这是邓晓芒(2009:6)的翻译。 (17)O'Neill(1996)一文是关乎康德这方面思想特别清晰和有见地的解读。标签:自然科学论文; 科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科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公理系统论文; 学科排名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