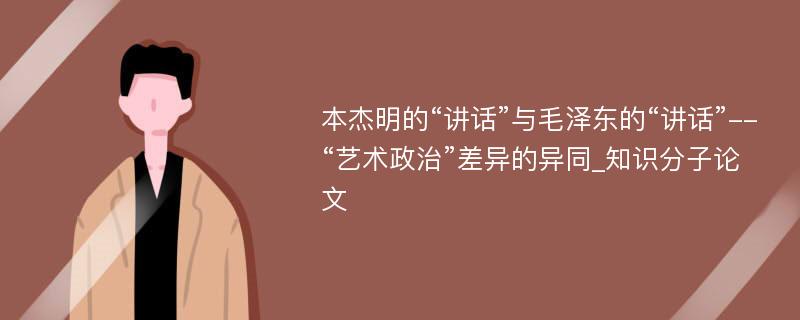
本雅明的“讲演”与毛泽东的《讲话》——“艺术政治化”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讲演论文,讲话论文,政治论文,艺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雅明虽写过大量文章,但作为“讲演”的文章似不多见,所以本文所谓的“讲演”,指的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所的讲演》。毛泽东一生中有过多次“讲话”,但一说到《讲话》,肯定是专指那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我之所以把这两个文本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文本,它们都蕴含着“艺术政治化”的战略方案,而其中呈现出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也颇耐人寻味。
把本雅明的“讲演”看作“艺术政治化”的产物是毫无问题的,因为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一文的结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这便是法西斯主义所鼓吹的政治审美化。共产主义对此所作的回答是艺术政治化。”①此后,“艺术政治化”便成为本雅明左翼激进思想的一个凝练表达。这种思想虽散见于多篇文章中,但以《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呈现得最为集中完备。毛泽东的《讲话》似乎要更复杂一些,但革命功利主义的思路,“文艺服从于政治”的主张,无疑也让这个文本散发出更多的“艺术政治化”的味道。因此,把《讲话》纳入“艺术政治化”的问题框架中加以考察,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而通过本雅明的“讲演”审视毛泽东的《讲话》,再借助毛泽东的《讲话》打量本雅明的“讲演”,或许能在两个文本中“看到”一些为人所忽略的东西。
仔细分析本雅明的这篇“讲演”,我们发现其中涉及三个维度:技术之维,作家之维和大众之维。它们既并行不悖又相互支撑,构成了“艺术政治化”的不同声部,并最终汇成了一种交响。
(一)技术之维。本雅明是从诗作政治倾向、文学倾向和文学品质的关系、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等讨论进入到相关问题之中的,但他进入问题的角度却与众不同。他把“技术”这一概念当作“一个辩证的切入点”,认为“文学倾向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倒退之中”。②这就意味着单纯讨论政治倾向与文学倾向等等关系显得空洞,而应该引入技术之维深入探讨。其后,本雅明果然亮出了他在技术层面的看家本领,通过丰富的例证加以阐释说明。比如,他把苏联作家特列契雅科夫(Sergei Tretiakov)界定为“操作型”作家。又以苏联报纸、行动主义(Activism)和新即物主义(New Objectivity)为例,说明“无论一种政治倾向显得多么革命,只要作家只是在态度上而不是作为生产者与无产阶级休戚与共,那么它就只有反革命的功能”。③论述过程中,他又引入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发明的一个概念——“功能转变”,进一步论证改变生产机器的重要性,④由此也引出了本雅明想要呈现的最重要的范例:布莱希特的“史诗剧”(Epic Theater),以便与他此前所写的《什么是史诗剧》(1931)中的相关论述形成一种呼应。凡此种种,都可说明他对技术的看重。
本雅明对技术大唱赞歌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本人在媒体工作的经历,他对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先锋派的迷恋,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对他的影响等等,都可能培养出他对技术的浓厚兴趣。于是,从技术的视角去观照艺术(文学),便成了他这一时期思考问题的一个兴奋点。当然,这种技术迷狂也曾被人定性为“技术决定论”而遭到批评,但相比较而言,沃特斯(Lindsay Waters)的分析或许更耐人寻味:“同本雅明一样,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仅仅是方法。技术是一种展现方式’。而且,海德格尔表露出这样的希望:‘如果我们留意这个,技术的本质的另一个领域就会对我们敞开。这是一个展现真理的领域。’这种对于技术的理解打乱了旧的主体性和客体化这一使主体得以认识和欣赏‘客体’的方法。技术一枪击毙了陈旧的认识论并取而代之。‘从长远的意识来看所存留下来的东西不再是与我们对立的客体’。”⑤这段文字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或许可以把技术看作主体(作家)与客体(受众)之间的一个中介。但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进入另两个维度之中。
(二)作家之维也就是知识分子之维,因为作家与知识分子是本雅明交叉使用的概念。在这一维度上,有两个新的动向值得注意。首先,本雅明把作家看作生产者,这既是对作家的重新定位,也是对作家的降格处理。由此,本雅明就让作家走下了“创造者”的神坛。这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在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看来,作家主要是一个生产者,与其他社会产品的生产者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浪漫主义把作家当作创造者这一概念——认为他像上帝似的,凭空地、神秘地变出东西来。有了艺术创作全凭个人灵感这种想法,就不可能将艺术家看成扎根于某个历史时代、选用一定材料加以创作的工人。”⑥如此看来,让作家走下神坛,其实就是让作家落地——落到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地面。这当然是为作家祛魅,然而在其背后,显然也隐含着本雅明更深的用意。而这种用意又与第二个动向紧密相连:让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休戚与共。
本雅明是在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和革命等思维框架中形成这种动向的。他在“演讲”的开篇即划分出两类作家,第一类是“从自主性和自由的立场出发要求创造的资产阶级作家”,第二类是能够认识到“当前的社会处境”促使他做出为谁服务之抉择的作家。⑦“资产阶级的消遣文学作家不承认抉择”,但他“还是在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较为进步的作家确实承认这种抉择,他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时,其决定便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这样,他的自主性就不复存在了,他的写作活动如今依据的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利益。”⑧在本雅明的划分中,特列契雅科夫、布莱希特等作家显然属于第二类作家,他把这类作家树为榜样,显然是要争取更多的资产阶级作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向无产阶级阵营,从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因为这是阶级斗争与革命事业的需要。如此看来,把作家命名为生产者,让他们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便是在解除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顾虑,这样他们才能够轻装上阵,在走向无产阶级时少一些精神负担。由此再来琢磨此文“题记”所引的费尔南德(Ramón Fernandez)的那句语录——“应当把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来,并让他们意识到二者的精神姿态和作为生产者的处境是一致的”⑨,我们才能够看出本雅明的良苦用心。本雅明是位引用大师,正如《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题记”中引用瓦莱里的文字隐含着该文的论述主题一样,⑩《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的“题记”引用也隐含着他的战略方案:争取知识分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可与工人阶级的生产等量齐观。大概只有这样,他们在被“争取”的过程中才能心悦诚服。
进一步追问,把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其用意何在?这就涉及了“讲演”一文的第三个维度。
(三)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大众之维是一个比较隐秘的维度。如果说技术之维和作家之维是明线,大众之维则是暗线。之所以如此,不光是此文在大众的维度上所论不多,而且即便有所触及,也需要通过语词和语义上的转换我们才能心领神会。然而,在其他文章中,本雅明对大众问题却有深度思考,它们构成了理解“讲演”一文的必要注脚。比如,在《苏俄作家的政治分类》(1926)中,本雅明认为对于苏俄作家来说,“第一要务是接近大众。心理特点、语词选择和表达方面的精致只会让公众畏缩不前。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表达而是信息,不是变化而是重复,不是技巧精湛的作品而是激动人心的报道”(11)。这种观点与“讲演”中对特列契雅科夫的论述构成了一种互动。而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大众也是本雅明论述的重要维度,他甚至在此文的“跋”中写道:“现代人日益加剧的无产阶级化与大众的日趋形成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法西斯主义试图组织新生的无产阶级大众,却不触动大众努力废除的所有制结构。……法西斯主义借其元首崇拜强迫大众屈膝臣服,这种对大众的侵害与对机器的侵犯极为相似,后者也被打压进膜拜价值的生产之中。”(12)考虑到“政治审美化”的评估与“艺术政治化”应对方案的提出正是以上语境的产物,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应对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便是要与法西斯主义争夺大众。
如果在这一背景上再来面对本雅明的“讲演”,大众之维也就开始显山露水。此文固然没有使用“大众”一词,但本雅明却让“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频频亮相。在我看来,它们基本上可看作大众的同义词,或者看作“不在场”的大众的修饰语。而当本雅明认为苏俄报纸已克服了资产阶级新闻的缺陷,读者随时可以成为合作者、写作者、描述者和起草者时,这既是对苏俄报纸的夸赞,也是对新型大众的期待。同理,本雅明之所以对布莱希特的史诗剧赞赏有加,关键也在间离、中断等等技术能对观众产生一种震惊效果,这其实也是对大众麻木心理的一种刺激。如果说资产阶级的传统戏剧是让大众沉醉其中,那么,布氏史诗剧则是让大众警醒起来,从而对大众产生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很难夯实,但起码在本雅明的想象与描述中,它的威力不可谓不大。
简要梳理了这三个维度之后再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答案也就明朗了。在本雅明的规划中,资产阶级作家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要被打造成“生产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阶级斗争、革命事业的需要。而他们要胜任这一新的角色扮演,又必须被“技术”武装起来。只有经过了这种生产工具的革新,他们生产出来的作品才能有效地作用于无产阶级大众。而我之所以把技术看作中介,是因为通过它可以消除主体(作家与知识分子)和客体(大众)之间的对立关系,使他们结成神圣同盟。本雅明固然只谈到了“文学形式的巨大重铸”,(13)但从他论述的思路中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当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能动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之后,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局面即已形成,这岂不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重组、重铸和重新融合?而“艺术政治化”方案的落实,也许就蕴含在这种充满激情的乌托邦想象之中了。
毛泽东的《讲话》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为比较方便,我也把《讲话》中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三,以便对应本雅明“讲演”中的三个维度。
本雅明的“讲演”以“技术”作为其出发点,而无论从哪方面看,群众(大众、人民)既是《讲话》最重要的关键词,也是它展开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据笔者统计,《讲话》中“群众”单独使用76次(包括“广大群众”6次),与它组成的相关词组及使用次数是:“工农兵群众”11次,“人民群众”11次,“革命群众”2次,“劳动群众”1次。“大众”单独使用6次,相关词组的使用次数是:“人民大众”23次,“工农兵大众”、“工农大众”与“社会大众”各1次。而“人民”则单独使用51次(包括“劳动人民”5次,“革命人民”3次)。据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考证,“民众”和“大众”(对应于德语词die Massen)均为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译文中喜欢使用的翻译概念,而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民众”一词在汉语里的价值得以提升,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文章中,它被赋予解放革命主体,或者至少是具备了革命素质的人群的含义”。同时,“毛泽东经常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组成‘Volksmassen’(人民大众),为此他不是使用‘民众’这个词,就是使用词组‘人民大众’或者‘人民群众’。毛泽东对‘Volksmassen’(人民大众)的定义与对‘Volk’(人民)的定义没有丝毫区别。”(14)而笔者查阅国内权威的《讲话》英译本,无论是“群众”还是“大众”,都译成了“the masses”;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人民大众”,又都译成了“the masses of the people”。(15)这也意味着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群众”或“人民大众”在《讲话》中如此声势浩大,自然与毛泽东的核心命意有关。在“引言”部分,他就特别提出了“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而在“结论”部分,他又把“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看作一个中心问题,由此展开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关键论述。(16)这种论述如今已被人在接受美学的层面做出了全新解读,但如此定位,也就把《讲话》中的“接受者”(群众)看成了单纯的文艺受众。而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群众”首先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其次才“蜕化”为“读者”或“接受者”,衍生为文学艺术意义上的术语。由于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工农大众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也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所以像马克思、列宁等人一样,毛泽东自始至终也一直把“群众”看作革命的主体。作为革命主体,群众虽然也有缺点,也是受教育的对象,但一方面毛泽东更多看到了群众的长处,以至于《讲话》及相关文本有“袒护”群众之嫌;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眼中,知识分子的诸多缺点又更加醒目,无法容忍。两相比较,群众的缺点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无论是在《讲话》还是别的文章中,毛泽东对群众都是高调表扬,很少有疾言厉色的批评。比如,在《讲话》前后,毛泽东便有许多论述群众的名言,它们在“文革”期间曾作为“毛主席语录”广为流行。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7)这种美化乃至圣化和神化群众的思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始终,也构成了他的群众观。
《讲话》中关于群众的论述实际上便是毛泽东群众观的产物,只不过他在许多问题上说得更加明确。在对“人民大众”的界定中,毛泽东把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看作“最广大的人民”。而文艺之所以要为这四种人服务,是因为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兵士既来自工人农民,又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同盟者”。(18)在这里,人民的等级秩序是围绕着他们在革命和革命战争中作用的大小建立起来的。由此看来,毛泽东在这里所论述的“接受者”与其说是文艺受众,不如说是革命主体。或者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人民大众是革命主体,他们才拥有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受众的资格。
群众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成为被服务的对象,所以有了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提炼和概括;群众的文化水平又决定了不能把文学艺术只做成“阳春白雪”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有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分析。甚至“文艺服从于政治”这一提法的登场亮相也与群众有关:“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体现出来。”(19)在这里,政治之所以还要借群众之名,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群众是“政治正确”的。
与对群众的高扬相比,毛泽东对作家艺术家则完全是另一种看法。而这种看法也隐含着诸多症候,值得仔细分析。
在《讲话》中,毛泽东对作家艺术家的称谓是多种多样的,据笔者统计,这些称谓及使用次数分别为:“文艺工作者”28次,“知识分子”26次,“文艺家”16次,“作家”10次,“文学家”、“艺术家”各6次,“文学家艺术家”连用4次。而在使用较多的几个称谓中,“作家”主要是在强调其身份(出身)或来源的语境下才使用(如“革命作家”3次,“党员作家”1次,“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2次,“革命根据地的作家”2次),“文艺家”的使用情况也是如此(“革命文艺家”6次,“无产阶级文艺家”2次,“抗日的文艺家”1次,“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反革命文艺家”等6次),“知识分子”的使用则更耐人寻味:除“引言”中的6次另当别论外,“结论”部分的20次中有17次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词组或相关语境下使用的。而“文艺工作者”则或者作为中性词单独使用,或者作为褒义词确认其归属(“我们的文艺工作者”10次,“革命的文艺工作者”3次,“党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各1次)。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呈现如上统计情况,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作家艺术家等等并非毛泽东看重的称谓,知识分子及其限定又主要呈现的是负面的联想,这与它所关联的被改造语境非常吻合。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所推出的都是一个崭新的说法:文艺工作者。
本雅明把作家看作“生产者”(producer)富有深意,毛泽东把作家定性为“工作者”(worker)也意味深长。查《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使用过“工作者”词组的文章只有四篇: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的讲话中曾用过“模范工作者”(2次);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曾用过“艺术工作者”(6次);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曾用过“文化工作者”(3次);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中曾用过“党报工作者”(2次)。这种使用频率及使用量意味着如下事实:《讲话》之前,毛泽东对“工作者”一词的使用并不热衷;“文艺工作者”虽经过了“艺术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铺垫与准备,但它的首次且大面积使用确实是从《讲话》开始的。而文艺座谈会结束后的第六天(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做报告,第三部分内容又名为《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20)这可看作是对此称谓的进一步固定。从此往后,“文艺工作者”便成为中共官方的正式说法,一直沿用至今。
“文艺工作者”并非毛泽东的发明,因为早在1936年6月,鲁迅、巴金等63人就发表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21)1937年1月,一份名为《文艺工作者》的刊物也在上海创刊(仅出两期便停刊)。(22)这至少说明,迟至1930年代中后期,“文艺工作者”就已在文艺界的左翼人士中开始使用。种种迹象表明,《讲话》中的“文艺工作者”之说既是毛泽东对此前“艺术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化用,也是对左翼人士说法的进一步借用。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一种革命文艺新话语的诞生。在这种新话语机制中,即便“文艺工作者”还没有完全取代“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等称呼,但与后者相比,前者不但获得了一种至尊至荣的地位,而且被赋予一种新的意涵。这种新意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虽然“文艺工作者”被直译为英文(literary and art workers或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时显得怪异,以至于后来《讲话》被“输出”时中国的英语专家们不得不尽量避免直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意译为“作家和艺术家”(writers and artists)(23),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文艺工作者”却具有新的气象。李博分析过“工作”(work)与“劳动”(labour)进入汉语之后的异同,并梳理了“劳动者”从日本“旅行”到中国的过程。他认为:“由于在整个中国的革命运动时期里,中国工人阶级从数量上看非常微弱,所以‘劳动者’这个中国概念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自然就比对俄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要。毛泽东经常同时使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24)可见,毛泽东把“文艺家”定位成“工作者”,一方面使作家艺术家的文艺活动性质更接近于“劳动者”,这就消解了文艺活动的神秘性;另一方面意在增加作家艺术家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因为一旦能够转化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就不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们的工作也具有了“劳动”的意味,或者他们起码在心理上可以把自己视为与“劳动者”一样的阶级了。
其次,在知识界的“五四”话语中,知识分子大都是以“启蒙者”的姿态或身份出现的,这意味着在这场中国的“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是启蒙的主体,而民众则是启蒙的客体。但在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革命叙事中,他固然已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但知识分子启蒙失败的原因则更是他在意的一面,并形成了“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25)的看法。如果说在1939年毛泽东还只是停留在这种口头的呼吁,那么三年之后他却是要通过《讲话》落到实处了。于是,“文艺工作者”的定位便显出了它的威力和魅力:通过概念转换,它不知不觉地驱散了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神秘光晕,破除了知识分子那种高高在上的启蒙心态,以便使他们更好地投入到毛泽东重新命名的“启蒙运动”之中。(26)因此,看似小小的概念转换,但在其背后却隐含着一种政治策略。因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便开始了从“启蒙者”到“工作者”位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其实就是从神圣到凡俗、从精英到平民、从精英主义到大众主义的过程。
当然,要完成这一过程,仅仅靠概念的转换是远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要触及知识分子的灵魂,于是便有了“思想改造”。(27)在“引言”部分,毛泽东在把“大众化”解释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之后,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呈现了思想改造和感情变化的过程。(28)而在“结论”部分,毛泽东在进一步呈现了知识分子不爱工农兵的感情、姿态和处于萌芽状态的文艺后指出:“这些同志的屁股还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29)笔者在这里特意引用《讲话》初版本中还未删改的句子,是为了说明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情感转变的问题上,毛泽东既有循循善诱的现身说法,又有暗含威严的调侃讽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可谓用尽了心思。
但是,文艺工作者若想写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还须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即语言问题。
虽然《讲话》中论及语言的地方不多,但毛泽东在《讲话》之前已有幅度不小的论述,《讲话》中他似乎无意进一步重复这一话题。比如,《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毛泽东谈论过艺术技术和技巧,而谈论的重心则落到了语言那里。在《反对党八股》(1942)中,“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成了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而“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讲话》延续了这一思路,并把向群众学习语言提到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的高度加以认识:“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30)
单独来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我们甚至可以在“学在民间”的层面阐发其微言大义。但是,一旦把语言问题还原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框架中,事情也许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中,学习、掌握进而运用群众语言进行创作,既是文艺工作者接近群众、深入群众的有效途径,同时又可让它反作用于自身,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如此说来,毛泽东在嬉笑怒骂中让文艺工作者去学习群众语言,固然首先是为了普及与提高的需要,但同时也是逼使他们清除其知识分子话语系统,代之以大众话语系统(从而也是革命话语系统)的过程,一旦这个新的话语系统进驻他们心中,即意味着他们已被新的语言机制所操控,也意味着被语言操控的思想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已呈现出毛泽东《讲话》与本雅明“讲演”的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不光体现在大的思路走向上,而且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操作细节上:本雅明把作家定位成“生产者”,毛泽东把作家定性为“工作者”。本雅明认同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背叛自己的阶级,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转变自己的阶级立场。本雅明以特列契雅科夫为例,力论作家不能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要投身其中;毛泽东不断呼吁文艺工作者要到群众中去,深入生活,他甚至以法捷耶夫的《毁灭》为例,论证越是为群众所写的作品就越有世界意义。(31)本雅明把“功能转变”奉为至宝,毛泽东把“思想改造”看作重中之重。本雅明强调“技术”,那既是生产工具,也是革命的手段;毛泽东则更看重“技术”中的“语言”,转换整个话语系统因而成为知识分子大众化的前提条件。本雅明把“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挂在嘴边,“大众”因而成为他思考相关问题的隐秘维度;毛泽东则让“大众”或“群众”频频亮相,“群众”因此成为他进入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凡此种种,都意味着这两个文本穿越了时空隧道,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互动。
然而,若是仔细辨析,我们马上又会发现这种相似无法掩盖其相异之处,大体而言,这种相异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雅明一直是在技术的层面做文章的,而由技术引发的生产工具、生产器械等相关论述虽然富有新意,也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说到底依然算是知识分子的迂阔之举。尤其是当他不去过问作家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而只关注作家是否能作为生产者出现时,也就为他的理论留下了许多漏洞。因为他谈论的是作家的技术,却拒绝谈论作家的“屁股”和“脑袋”。而当技术被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时,人(作家)就有可能被淹没。因此,有人指出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极其不辩证”(32)。因为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毕竟无法与物质生产等量齐观,这就意味着一旦让艺术与生产力挂钩,情况立刻就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当本雅明说出“对于那种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来说,技术进步就是其政治进步的基础”(33)之类的话时,他对技术进步与政治进步的关系显然理解得过于机械了。
如果说“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本雅明那里是“物”,那么在毛泽东这里却是“人”。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说过一句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4)从此往后,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维度去考察人、分析人、改造人便成为其固定思路。抗战期间,他又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35)这其实是把由技术形成的“物”放在了一个次要位置。《讲话》虽然谈论的是文艺问题,但依然沿用了这种思路。所以,与文艺创作中的物(语言)相比,他的思考重心不光是落在了人(文艺工作者和群众)上,而且落在了人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和“脑袋”(灵魂深处)上。这种路数当然要比本雅明的方案更有效果,但是也必须指出,当毛泽东把革命文艺看作“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36)时,他就不但把文艺工具化,而且也把为这架机器工作和服务的人“物化”了。
其次,由于重视物,本雅明就只能在“功能转变”上做文章。而这里所谓的“功能”指的是生产工具的“功能”,所谓的“转变”应该是消除生产工具中与生产者相敌对的因素,把它转变到有利于生产者(从而也有利于接受者)的方面来。而借助于“中断”、“间离”等写作技术和舞台技术,布莱希特也确实做到了“功能转变”。因为根据本雅明的分析,史诗剧并非让观众沉浸于感情(即便它很煽情),而是让观众通过思考,与自己的处境形成一种疏离。而且,笑常常是思考的触机,“特别是大笑引发的隔膜的震动往往比灵魂的震撼能给思考提供更多机会,史诗剧只对大笑的场合慷慨大方”(37)。而当本雅明如此解释时,他的落脚点已走向了观众。这种观众并非一味纠结于情感世界的观众,而是借此装备了反思机制的大众。这种大众是否真正存在也许还值得商榷,但起码在本雅明的想象和期待中,他已高估了大众的接受水平与能力。或者用毛泽东的话说,本雅明所做的事情是用特殊方式“提高”大众。
与本雅明相反,因为毛泽东更看重人,所以他便在“思想改造”上下工夫。而通过“思想改造”,也通过深入生活和“典型化”(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功能转变”)的表现手法之后,文艺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38)表面上看,以“思想改造”始,以“环境改造”终,毛泽东的革命目标要比本雅明的革命理想更为远大,而后来《讲话》催生的革命文艺也确实让群众“惊醒”和“感奋”起来了,但这种文艺显然重在激活群众的情感机制,以便让他们在眼泪和怒火中形成阶级仇和民族恨,却最大限度地取消了群众的反思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雅明所追求的受众效应在毛泽东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例证之一是,布莱希特虽然在其晚年对毛泽东情有独钟,但他的戏剧观和戏剧实践却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鲜有影响。究其原因,或许在于他的戏剧革命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存在着某种抵牾。
第三,无论本雅明如何为作家祛魅,“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依然是主体。换句话说,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二元格局中,前者是施动者,后者是受动者。而施动的目的是想尽办法让后者“动”起来,从而或者成为布莱希特戏剧那种能动的观众(反思者),或者成为苏联报纸那种积极的读者(合作者或写作者等)。因此,他对技术装备的焦虑和痴迷并不是让作家以此享受消遣,而是让他们有了更好的发动群众的武器。另一方面,虽然本雅明希望知识分子走到工人阶级阵营之中,但他并没有要求他们消灭自己的思想,泯灭自己的个性。而且他也清楚,“左翼知识分子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只能是本阶级的叛逆”。(39)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角色扮演既接近于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同时又保留着知识分子所固有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因此,我们不妨说,本雅明的设计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化大众”,或者起码可以说,他在“化大众”与“大众化”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
然而,无论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都是在“知识分子大众化”的思路上展开其思考的。于是,在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面前,知识分子只能是客体,是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从而无限接近人民大众思想感情的改造对象,而改造的成功与否不但要看其是否清除了自己的语言,而且还要看其是否废除了冷嘲热讽的“鲁迅笔法”。所有这些,其出发点都在于人民大众。当知识分子从“屁股”到“脑袋”,从思想到行动都能工农化后,他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才能大众化。而如此一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启蒙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也便荡然无存了。这正如高华所言:“毛泽东的新话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40)因此,尽管“大众化”如其英文所译的那样首先是一种“大众风格”(a mass style),(41)且在《讲话》的语境和逻辑中合情合理并能自圆其说,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大众化”却演变成了“知识分子被大众同化”。
第四,以上的种种不同最终都会在“艺术政治化”的归宿上聚焦,于是一者形成了“介入文学(艺术)”,一者造就了“遵命文学(艺术)”。
本雅明思想中虽然有多种维度,但受布莱希特影响,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11条提纲成为他们共享的理论资源。于是本雅明拥有了具有浓郁政治实践色彩的战斗姿态和理论主张,这种姿态和主张被后人概括为“介入”,它的集大成者当首推萨特。大概正是这一原因,把布莱希特、本雅明与萨特捆绑在一起批而判之,就成为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批判“介入文学”的固定思路。而他之所以要批判,原因之一是他担心萨特与布莱希特的文学实践有可能变成“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42)今天看来,这种批判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它也以“艺术自主”的名义封杀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与社会批判精神。实际上,本雅明等人虽然在特定的年代中陷入到了一种政治迷狂之中,而“介入”也确实对文学艺术构成了某种损害,但是他们那种主动出击的姿态,与法西斯主义死磕的理念却依然值得保护。因为在强权面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若想有所作为,除了以笔为枪之外似乎别无选择。这当然只是权宜之计,然而只要政治还在干预文学,文学干预政治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文学在敢怒不敢言中成为犬儒主义的俘虏。
“遵命文学”是鲁迅的说法,他曾把自己的《呐喊》戏称为“遵命文学”,意指当年他在“文学革命”感召下写出了一些“革命文学”。但他马上解释道:“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43)《讲话》的本来用意是要让文艺变成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这样,以阶级和人民的名义来定性文艺就具有了某种正义性和合法性。但是,由于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由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成为《讲话》的重要理论资源,更由于党派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已经“接管”文艺从而形成了高华所谓的“党文化”,(44)因此革命文艺最终果然变成了鲁迅所谓的“遵命文学”。而鲁迅的否定之词也变成了一种既成事实,因为《讲话》让人遵奉的显然是领袖意志和党的律令。而当《讲话》精神被当作金科玉律在毛泽东时代贯彻落实之后,“艺术政治化”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本雅明所意欲对抗的“政治审美化”,与此同时,“大众化”也变成了阿多诺所一生警惕并长久批判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区别只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遵”的是商业、资本和资本家之“命”,而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遵”的则是革命、政党和领袖之“命”,于是前者生产出了商业大众文化,后者制作出了政治大众文化。而它们在生产、消费、宣传和传播等环节的策略却极其相似。
由此看来,在“艺术政治化”的道路上,本雅明与毛泽东从几乎相同的起点出发,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终点。若是继续追问成因,显然涉及二者更为复杂的思想根源。而这一层面的解读我在这里已无法展开,当另文论述。
①[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第29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②[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见方维规主编:《文学社会学新编》,第26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④⑨(13)(37)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Volume 2,Part 2,1931-1934,trans.Edmund Jephcott,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772,p.774,p.768,p.771,p.779.
⑤[美]林赛·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保尔·德曼、瓦尔特·本雅明、萨义德新论》,昂智慧译,第2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⑥[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⑦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Volume 2,Part 2,1931-1934,trans.Edmund Jephcott,p.768.
⑧见方维规主编:《文学社会学新编》,第266页,译文有改动。
⑩(12)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trans.Harry Zohn,London:Fontana Press,1992,p.211,p.234.
(11)Walter Benjamin,Neue Dichtung in Ruβland 2 GS Ⅱ,2,p.756.Quoted in Richard Wolin,Walter Benjamin,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44.
(14)(24)[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第399—403页、第2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See Mao Tse-tung,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Fourth Edition,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5,pp.2,6,12,29.
(16)(17)(18)(19)(26)(30)(31)(36)(3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6、810、811页,第748页,第812页,第823页,第818页,第808页,第833页,第823页,第81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0)(25)(35)《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4—433页、第523页、第4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参见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释部分,《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页。
(22)立青:《提倡微型小说的〈文艺工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3)据笔者查阅,在《讲话》英文版中,“literary and art workers”的译法出现过4次,“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出现过1次,其余都被译成了“writers and artists”。
(27)据谢泳梳理,“思想改造”作为专有名词是1949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已有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口号,而“改造”一词也频频出现在毛泽东那一时期的相关文章中。因此,笔者以为,无论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还是一场运动,都可把延安整风看作“思想改造”的先声。参见谢泳:《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第250页,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28)(2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等著:《文艺工作论集》,第8页、第12—13页,东北书店安东分店1949年版。
(32)Richard Wolin,Walter Benjamin,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58.
(33)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Volume 2,Part 2,1931-1934,trans.Edmund Jephcott,p.775.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39)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0)高华:《革命年代》,第21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1)Mao Tse-tung,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Fourth Edition,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5,p.6.
(42)Theodor W.Adorno,"Commitment," trans.Francis McDonagh,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eds.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New York:Urizen Books,1978,p.305.
(43)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4)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35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