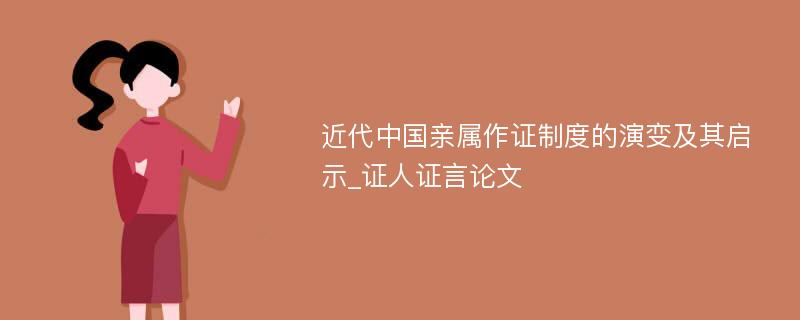
亲属作证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属论文,启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的反思 本轮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定,是证据制度中引人注目的变革。这是1949年以后证据制度对亲属拒证权的第一次接近。但是,由于本规定仅限于庭审阶段的“免予强制出庭作证”,且没有禁止公、检、法等机关在审判以外的其他场合强制近亲属作证。有学者因之指出,与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亲属拒证权”相比对,本规定差距太大。① 本文拟就清末至民国时期有关亲属作证制度立法及其演变的历史进行初步的梳理,将关注作为该制度的话语及其依存的制度知识体系在此间从萌生到渐趋成熟的内在理路,而非仅就此间频繁更迭的政权主体所颁行的证据法律制度进行单纯编排和评述。经由本文,笔者还将探究的是,作为中华法系家族伦理本位精神的“亲亲相隐”制度,在与清季民初法典中的亲属拒证制度表面的断裂中,究竟蕴涵着怎样的蜕变关系;这一蜕变中蕴涵的法理能否对“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在将来的完善带来有价值的启示。 二、亲属拒证制度在中国的早期历程 1906年,沈家本、伍廷芳主持编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该草案因引入陪审制度、律师制度等而成为近代中国引入现代诉讼和证据制度的逻辑起点。但没有确立公民个人权利本位的拒绝作证权制度。 由于《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未能颁布施行,为了解决各地审判厅处理案件无所依凭的问题,《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制定颁布,并成为我国事实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诉讼法典。在有关亲属作证问题上,该法第77条第一款规定属作证者必须履行的强制性义务而非其权利。 真正形式意义上的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一直要到1910年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才得以正式确立。其第152条规定:“下列各人得拒绝证言:第一,被告人之亲族,其亲族关系消灭后,亦同;第二,被告人之监护人、监督监护人及保佐人。”与《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义务性规定不同,本条有关亲属作证与否的规定已转为一种权利话语的表述。稍晚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386条规定:“当事人之配偶或四亲等内之亲族得拒绝证言,其亲族关系消灭后亦同。”同一时期制定的《大清新刑律》第180条规定:“犯罪人或脱逃人之亲属,为犯罪人或脱逃人利益计而犯本章之罪(藏匿罪人及湮灭证据罪——引者注)者,免除其刑。”这里,亲属成为法定的刑事免责事由。现代意义上的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雏型”至此已经具备,上述几部法律草案中的相关制度可视为该制度在中国的逻辑起点。② 1911年,民国北洋政府于1922年先后颁行了《刑事诉讼条例》和《民事诉讼条例》,其刑诉条例第105条规定:“左列各人得拒绝证言:(一)为被告之亲属者,其亲属关系消灭后亦同;(二)为被告之未婚配偶者;(三)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监督监护人或保佐人者。”《民事诉讼条例》第364条前三款亦就有亲属关系之人证者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一)证人为当事人之配偶、未婚配偶或亲属者;(二)证人所为证言于证人或与证人有前款关系之人,足生财产上之直接损害者;(三)证人所为证言足至证人或与证人有第一款关系,或有养亲、养子或监护、保佐关系之人受刑事上追诉或蒙耻辱者,在配偶或亲属其婚姻或亲属关系消灭后亦同。《民事诉讼条例》,还就亲属拒绝作证内容的例外作了规定。其第365条规定了不得拒绝作证事项:(一)同居或曾同居人之出生、亡故、婚姻或其他身份之事项;(二)因亲属关系或婚姻关系所生财产上之事项;(三)为证人而与闻之法律行为之成立或意旨;(四)为当事人之前权利人或代理人而就相争之法律关系所为之行为。而且,证人虽有前述情形,如其应守秘密责任已经免除,也不得拒绝作证。由于两部条例的颁行,亲属拒证制度第一次在实践中得到落实。 1928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左列各人,得拒绝证言:(1)为被告之亲属者,其亲属关系消灭后亦同;(2)为被告之未婚配偶者;(3)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监督监护人或保佐人者。”与之相应,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77条规定:“亲属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谨之脱逃人,而犯本章之罪(藏匿犯人及湮灭证据罪)者,免除其刑。”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证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1)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2)与被告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3)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现由或会由被告或自诉人为法定代理人者。”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67条延续了1928年刑法的规定,为亲属利益而藏匿犯罪、销毁证据的,可以减刑或免刑,间接便利亲属脱逃者得减轻其刑(第162条)、为犯盗窃罪之亲属销赃匿赃者得免除其刑(第351条)。1932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1)证人为当事人之配偶、七亲等以内血亲或五亲等以内之姻亲或曾为此姻亲关系者;(2)证人所为证言,于证人或有前款关系,或有监护关系之人足生财产上直接损害者,或致受刑事上追诉或蒙耻辱者。其在亲属关系或监护关系消灭后,亦同。”1935年修正《民事诉讼法》就因亲属关系而享有拒证权的范围明显缩小,新法规定“证人为当事人之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曾为此亲属关系者”,可以拒绝证言。1945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亲属的证言特免权、第307条规特免权规定了配偶不利证言。1949年之后,随着对“六法全书”“伪法统”的废除,作为权利的亲属拒绝作证制度在大陆就此消失,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失踪者”。③ 三、促成亲属作证制度权利化的内外因素辨析 由于亲属作证制度自义务向权利的演变不仅关涉权利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而且,社会结构、国家性质乃至植基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理念的嬗变,都是促成权利理论及观念渐次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笔者在梳理亲属作证制度及其理论形成的同时,将一并就作为义务或权利场域的社会与国家在组织及其原则、理念上的变更作简略分析,原因如下: 首先,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个人权利获得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至17世纪,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社会契约论,完全取代了早期理性主义和共和主义理想。至此,社会自结构至理念方始完成了现代性转型。这一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意义在于,除了使个人权利凸显出来成为主要公共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依据。 其次,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促使一系列基本权利的产生。在西方,尽管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家权力的确受到了重要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来自罗马政府的制度结构,而不是来自人民的福利。直到18世纪,除了英格兰和荷兰,欧洲的民族都是由专制君主统治的,很少考虑到人民的福利,更不会关心他们的自由。15世纪,民族国家在西欧出现。受此影响,以17世纪英格兰为主要发源地,以控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权为核心的立宪主义现代政治理念逐渐发达,最终定鼎于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正式进入法典。1810年制定的《法国刑法典》及1871年制定的《德国刑法典》皆有相关规定。进入20世纪,刑事诉讼和证据制度中人权和诉讼权利日渐扩展,并呈现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趋势。 第三,亲属拒绝作证权的形成是基本权利自身逻辑发展的应然之果。这里所说的基本权利,是指个人等私主体针对权力(如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权力不得不当侵犯,包括通过立法不当侵犯;二是公权力必须针对其他方面的侵犯而予以保护,包括通过立法予以保护。④在基本权利的发展过程中,最先得到确认并予以保护的是消极的防御权,其后是对积极保护权的确认与维护。对照人格权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因亲属拒绝作证权涉及婚姻家庭保护和隐私权保护,该项权利应系隐私权派生的权利,并且,与隐私权一样,亲属拒绝作证权是现代社会不断扩张以后而新生的一项权利。 四、“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献疑:基于制度场域的分析 亲属作证制度如何从义务向权利衍生的论述,重在梳理该制度在其历史演进中与一定的社会及国家结构之间互为因果或共生的关系,并以此证验亲属拒证权制度的正当性法理:由一种个人对社会、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理论转向个人对抗国家以保护自身的权利理论。现代法治视域中的亲属拒证制度及其理念,在表面的轮回中蕴藏着更多的变革,远非向该制度故有道德伦理的简单回归。事实上,伴随着从义务到权利的转换,支撑该制度的理念或曰制度伦理已从传统社会身份道德的应然性转向现代社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亲属拒证权制度对亲族伦理的拂悖,由于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的正当性必将天然地植入人类的某些道德伦。 另一方面,有关亲属作证制度理论基础前后变化的情形,还具有普适性,说明该制度因应社会结构而变化的某种共相。尽管中西法律文明在此间表现不一。换言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只要其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法治转型,就必须服膺于宪政理念下有关该权利的基本法理。 由此,可以看出,“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是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语义脉络,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为嚆矢,奉行国家优位的理念,更可以发现我国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保障、救济手段仍然面临着改革和完善的问题。 本文通过梳理亲属作证制度的历史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国家制度及理念的变更,以及前者与后者诸因素之间复杂而深沉的勾连及互动关系,借此完成了“亲属作证制度”基础理论自身份伦理向现代法理转向的证立,并由此廓清了关于拒证制度法理传统论述中的模糊和笼统之处。作为一种知识系谱的亲属作证制度,在中国大陆已然经历了帝制时代的“亲亲相隐”,清季及民国时期的“亲属拒绝作证”以及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共三次变更,在历史的磨道中留下了深浅不一的辙印,呈现出令人诡异的历史轮回。通过厘清某一历史现象的流变,在对其原因的分析中,能为现实找到某种参照物,以启迪来者。 注释: ①范忠信:《亲属拒证权:普世与民族的重合选择》,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12年1月。 ②参见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③关于亲属拒绝作证制度消失的原因,有以下几种说法:对“六法全书”的过度性批判、对前苏联诉讼理论及制度的盲目性效仿、历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影响等。参见王剑虹:《亲属拒证特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以下。 ④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