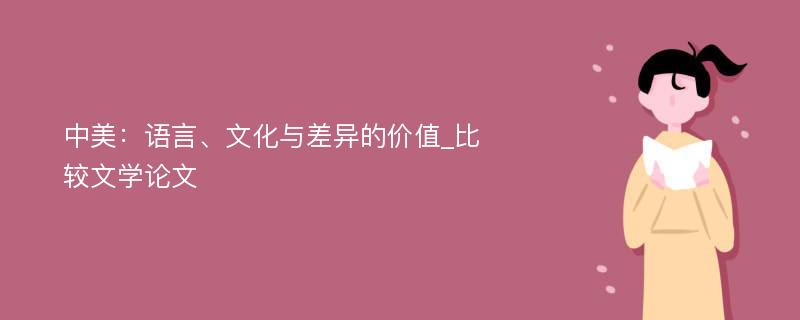
中国和美国:语言、文化与差异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差异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语言文字与人文学术传统
王晓路 黄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安排时间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学术兴趣总是与其生活经历有比较大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学者大多经历过不同的历史境遇,战乱、动荡、“文革”、下乡、新时期等等,各个时期的学者都离不开自身所处的教育条件和特殊背景。但是不论哪一个时期,都有一些知识分子除了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建树之外,同时也坚持对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行独特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目前北美学者的研究正受到大陆学界的重视,他们的选题、研究视角、材料分类方式和学术观点也往往成为讨论的兴趣点,这方面的翻译也逐渐增多。您的生活经历我想也是大陆学界比较感兴趣的。
黄宗泰 谢谢,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和你进行这种交流。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都确实保持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尤其是在上世纪那些动荡的年代,他们与我们的科研条件完全不能相比,但学问却是做得相当好。我看钱钟书的《管锥编》就常常想象他写书和生活的情景,真是十分感慨。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我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兴趣的确与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祖籍是广东,但祖父19世纪就到了美国。你知道,19世纪末美国出台了排华法案,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妻子都不能到美国与家人团聚。所以我祖父不得已就去了夏威夷,因为当时的夏威夷还不是美国领土。我祖母是迟到1896年才到夏威夷与祖父团聚的。我的祖父母都很开明,他们让我父亲上了美国的大学,当时许多美国人的孩子都不上大学,而出去赚钱,应该说我祖父母是很有眼光的。后来我们回到广东老家,继而又到香港新界,再后来又从香港重返夏威夷,辗转往返。我父亲讲英文,我母亲不说英文,由于她家学渊源,家里一直有私塾教育,所以她的古诗文非常好,而她又在北京生活过,所以京白话也会说。我记得她在美国人家里做事时都自己吟诵中文古诗,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自己虽然在大学、后来还在日本和台湾念过中文,但实际上一直是生活在东、西两种文化之中的。我除了讲英文也讲广东话和普通话,我夫人虽然是美国人,但她在日本呆过较长时间,现在也在亚利桑达州立大学教日文,因此各种语言包括方言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是我通过这些文字阅读作品的兴趣所在。这可能是研究文学十分重要的前提,也是我研习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原因吧。
王晓路 美国人上大学比较注重实际,大多选择好就业的专业。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也出现了这种趋势,有所谓的“热门专业”一说,而较为传统的人文社科专业有时在招生和就业时有一些困难。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目前在中学阶段就分文理科,大学阶段的转专业也不像美国这样方便,长此以往,可能又会形成新问题。但根据我有限的体会,也有许多美国学生的确是凭自己的兴趣选择或改变专业的。您的这种家庭背景和影响是促使您在美国上大学时选修文科的吗?
黄宗泰 是的。美国人是很实际的,大多数人在选专业时首先想到的是能否找到好的工作。但是我母亲认为孩子自己的兴趣最重要。所以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文科。我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是从诗歌和小说开始的。中国诗歌确实太美了,好的诗歌真是很难改动其中任何一个字的,所以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把一首好的中文诗歌翻译成符合英文韵律的英文诗,那别人读起来不过是在读英文诗歌而已,这样中文原有的语言传达力就会丧失。另外各个时期的作品在语言上也有不同的特点,这一点如何在另外一种语言中进行转换也是非常难的。如仅看一些英文翻译,你很难区分《诗经》中的歌谣与后期一些四言诗的区别。但我主要是对小说感兴趣。我年轻时曾看过大量的英文小说,但后来看中文小说时的那种废寝忘食的感觉,在看英文小说时却从未有过。我年轻时曾经有一段时间,晚上通宵达旦读中文小说,一大早又赶去上班和上学,而自己并不感到十分疲倦。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有滋味,这种由语言和文化带来的感觉的确很奇特。
王晓路 文学的感觉对文学研究相当重要,而文学性又体现在文字符号的独特编码当中,所以一个人的文学能力与语言能力密切相关。直接解读和通过翻译去阅读在感觉上是大不一样的。因而,文学研究的首要条件是一个人对语言文字的把握能力。如您谈到的钱钟书先生对语言和文献的把握上的确是惊人的,所以他的论述在各种语言和文献间可以穿梭自如,达到“入化”的境界。我自己虽然读过他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但是自己学力不及,尤其是佛学,有许多问题就难以通透。仅语言这一点现在极少有人做到钱先生那样了。另一例证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佐良先生和北京大学的杨周翰先生,他们的英文和中文以及相关的修养依然是当今中国大陆英文学界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我一直认为,上世纪中国大陆的文化断层并没有出现在上半期,因为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具有坚实的西学功底,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亦是相当透彻的。其中一些人不仅研究文学而且也是文学创作的高手。而所谓的断层主要是在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文革”后,弄得一代人不中不西,缺乏底气。我们在下面还可以就这一问题详谈。
黄宗泰 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培根的《论读书》真是非常美,俨然是培根自己在用优雅的中文书写的一样。我在北大时期也见过杨周翰先生。他们的确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其实这一批学者的人格魅力特别大,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坚守个体的精神,持之以恒,这是中国大陆学界了不起的地方。
王晓路 是的,其实这些学者主要是在人格魅力上影响着后来者。中国文学研究正发生着变化。中国古典文学尽管有比较丰富的样式,但在学术研究上却比较单一,其中主要是以几种典型的方法延续下来,即内在理路上表现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意象论,而在外在形式上以选本、摘句、评点等为代表。二者主要围绕言意关系以及情理路向展开①。但是这种位于自身文化语境中的传统方式则在以西学复制为标识的历史阶段中被迫改变了,上述固有的研究仅仅留存在一些个体研究上。西学的复制引发了中国人文学术传统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研究上就表现为文本形态、论述方式、学术生产和学科建制等方面。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人文社科知识学的演进一直是在西学和国学两个谱系中展开的,这就迫使知识界必须借鉴和消化西学和自身传统的双重资源,在此基础上针对知识谱系进行清理。而当代人文学术的再一次外转,尤其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引进和实践,使中国大陆人文学术出现了明显的范式转移。由于文学研究是对文学行为、文本系统和文学主客体经验的解释,所以现存的解释方式必须面对变化的文本形态呈开放的系统。如何利用西学和国学的双重资源一直成为学界困惑的问题。由于中国古典言说的哲学支撑点到了近代成为了一个悬置的问题,如何寻求解说的“民族主义”文化政治立场就成为了问题之问题。东西对立、体用之争等等为框架的观念、“五四”以来的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问题至今依然是思想界的关键词。因而对理论话语的渴望在中国大陆学界自然转换为一种文化政治问题。基于上述的背景,学者们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汉学家的论述和观点,首先就会关注言说背后的文化问题。
黄宗泰 你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观点很有意思。20世纪的确是重要的一个时期,其重要性也体现在中国文学学术中。学术传统的流变与时代有关,在某种外部条件下,学术的内在结构亦会产生相应的调整。但是人文学术主要是个体行为,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的兴趣,如在美国的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他们也坚持用非常传统的方式研究所谓“字无虚字”的“老问题”,用大量的时间进行艰苦的考证。当然有更多的学者采纳了跨学科的方式,将一些“老”问题纳入新的框架中进行再研究。但是在整体上,欧洲大陆的思想和文学观点对美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也注意到,中国大陆的学术方式正发生着很大的改变,如中国大陆随着开放政策的深入,可以不断地翻译和引进许多欧美的文学和文化理论,这对于文学和文化这样一个宽泛的领域而言,无疑是有借鉴和推动作用的。其中一些人的论著引起读者的反响是可以理解的。
二、中国的文学理论
王晓路 已故的刘若愚先生是目前中国大陆学界比较熟悉的学者,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在大陆1987年就出版了中译本,他的学生杜国清教授在台湾出版的译本也于2006年在大陆出版发行了。国内也有学者出版了研究刘先生的专著,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詹杭伦的《刘若愚:融合中西诗学之路》等。硕士和博士有关的论文也不少,我有一名学生从硕士起就对刘先生的论著十分感兴趣。刘若愚先生的这本书后来引发了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些争论。例如,有一些学者认为刘先生借用西方文学分析模式作为切割中国文学理论的工具,将中国文学按照西方的模式加以重新划分,将中国的文学理论分为形上、决定和表现、技巧和审美以及实用等几个方面,这样就有可能损害了中国固有的、整体的文学思想。您作为刘若愚先生指导过的学生,可以给中国大陆的学界介绍一下刘先生的学术思路吗?
黄宗泰 说到刘若愚先生,他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教学、研究和平日的言谈对我研习文学的影响很大。正如你刚才所说,他们这一代学者有一个共同点,如钱钟书先生、朱光潜先生等都是中文西文俱佳。刘先生的西洋文功底不说了,他的古文修养非常好,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不仅细读这些文献,而且进行文学创作,刘先生本人就常赋诗填词,所以他对中国古典诗文的体验是很深的。这样研究起来才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可能现在的一些学者在进行文学研究时,自己比较缺乏对文学的透彻感悟和体验,而这正是文学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刘先生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对学生也特别好。我能成为刘先生指导过的学生是很幸运的。杜国清教授是我的同学,他翻译的《中国文学理论》能在大陆出版我很高兴。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刘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等学者都用一些西方文学的观念来分析中国诗歌和小说,这一点当然是可以商榷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他们实际上对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均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他们在论述中国文学问题时,尤其是用英文论述时,往往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到西方读者在阅读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因而这些学者的论述方式较之某些西方汉学家的论述可能更加对路。例如刘先生的这本《中国文学理论》并没有简单地借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艾布拉姆斯(M.H.Abrams)教授著名的四要素图解形式,而是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有效的改造,其目的是展示中国文学所独具的东西。刘若愚先生的《中国诗艺》(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也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中国诗艺》一开始就详尽地分析中国书写系统、中国文字的典雅传统和语法效果等方面,其中专门有一章分析中国的观念以及思想和情感艺术再现的特殊方式。当然有中国背景的学者也不全是这样,如夏志清教授的做法就和刘先生不太一样,他一般用西方小说传统作为标准,将一些源自18和19世纪欧洲小说的概念和范畴直接运用到中国古典和现代小说中。当然这也不是什么错误。因为中国有很长一个时期,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夏教授也认为中国小说的成就比之西方仍有较大的差距。但刘先生不仅热爱、熟谙和尊重英文诗歌,而且他将有关的知识运用到分析中国诗歌之中,仔细地揭示了其中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那个时代是美国新批评盛行的时期,当时对文学文本进行相对科学的分析方式是学界的主流。你不大可能总是在整体上粗略地谈某一种文学思想或文学观念。刘先生当然也受了西方思想的许多影响。但实际上他对西方思想是持有自己的观点的。他多次就表示自己并不属于斯坦福大学。他还做诗来表示自己的心态。我认为用什么方式,包括西方思想和模式来分析,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对错,主要是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否可以通过这种分析论证出来。这正像我们今天在人文社科研究中需要借用许多哲学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的观点一样。
王晓路 我完全同意。刘先生首先是用英文论述中国文学理论,当然采纳一种语言就难以回避语言背后的文化指涉。但我认为他写作的目的,或他潜在的读者是英文读者,而不是汉语读者。实际上除了刘先生这本书之外,至今西方学界还没有一本有关中国文学理论系统的论著。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思想解读》(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是差不多二十年以后的成果,但这本书也主要是翻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主要语段,再加上自己的阐释②。刘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采纳了西方思想论述中国文学理论是有他策略上的考虑的。因为当时西方文学理论是学界的热门话题,大多数学者都非常熟悉各种批评流派的主要观点。而中国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古典文学理论在论述方式上当然是一种非西方的系统,加之当时中国文学理论还没有得到系统翻译,因而西方读者若没有中文解读能力,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了解就只能是只言片语式的有限了解。所以中国的文学理论至多也只是一种难以被认可的潜在的理论,当时并不被学界重视。我认为,理论是对经验的解释,理论的有效性是针对文本的有效性。文学理论中的每一分支理论都有其针对性。关键是系统的标准为何物。中国最有“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是针对六朝时期的文类和文本特质的。后来有“系统”的《原诗》也有其针对性。因此我想刘若愚先生试图要证明,中国不仅有自身的文学理论体系,而且即便用现成的、西方学界所熟悉的西方文学观念和方法来划分,也可以言之有理。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这部著作的重要性是文化史的意义。
黄宗泰 我很同意。这在学术交流史上也是很有趣的话题,显示了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在文化层面的分支问题。学问和其他事业一样,我们对某一个时期的成果肯定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我们现在看几十年前的某一本书当然会看到不同的问题,甚至是缺陷。但是刘先生的成果其实是有极大影响的,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并不是简单地借用艾布拉姆斯教授著名的四要素,而是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和改造,他在后来的一本重要的论著中专门谈过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参考和比较艾布拉姆斯教授那本《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与批评传统》一书的第6页,即M.H.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53.和刘先生的《语际批评家:中国诗歌阐释》第一章第1页:James J.Y.Liu.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其中艾氏的四要素世界(World)、作品(Work)、艺术家(artist)和读者(audience)的三角形框架已经变为一个圆形结构,即可以更有效地分析中国文学。我相信大家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刘先生的用心。
王晓路 是的。其实艾布拉姆斯著名的四要素也是上世纪中期1953年发表的,更是早于刘先生的著作。这个异常便捷的分析框架,对于后来一些批评旨趣也依然有效。但在今天看来,这个框架不便分析文本到受众这一动态的中间过程、另外也不便分析文本环境以及50年代之后文学理论的外部趋向。实际上美国学界对此也有不少批评意见③。但这并不能减少该理论的原创性。我前几年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也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有好些学者都对这个分析框架进行过补充④。而刘先生在《语际批评家:中国诗歌阐释》中所改造的图形也恰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一些缺陷。宇文所安的这本《中国文学思想解读》由于是中国文论主要论断的英汉对照,有解释,上课可能要方便一些,所以美国许多学校采纳了这本书作为教材。但我想如果美国学生要了解中国文学理论,肯定需要参考刘若愚先生的这两本书和其他一些有关论著才行。
三、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
王晓路 好,我们回过头来谈比较文学。正如您所言,中国大陆步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也反映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一个晚起的概念,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相比,其高等教育的历史是非常短的,其发展几乎与中国现代进程一致。中国大陆的学科建制与学位专业课程设置基本上也是西学复制的结果。其中在学位点上所体现出的等级制又是西方大学中所没有的中国特色。一些课程和学位设置,如比较文学,能够进入中国大陆的高校和中国的新时期是分不开的。要是在过去,这个学科无疑会被套上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标签,如东风压倒西风,还有什么比较的必要呢?但中国大陆自80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文学已经逐步成为了一种体制化的学科,全国的和各省的比较文学学会也先后成立,大学中文系里普遍开设了这门课程,许多学校建立了该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大量的论著、论文和教材开始出现。其中中文系的二级学科也在1990年代后被定义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将“比较文学”前置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突出了比较的意味,同时也将原来的“外国文学”专业在方法论上进行了定性。但实际上,比较文学犹如其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大陆的建制一样,是完全舶来的产物。在欧洲大陆,该学科已经历经了一个多世纪。即便在美国也有相当漫长的历史。但是现在美国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似乎正在分解和消失之中,化为了更为具体的学科,如区域研究、东亚研究等等,或直接合并到文学系中。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黄宗泰 美国的大学分为好几类,公立、私立,包括教会学校,不仅在招生、教学和研究的侧重点上不一样,在经费的来源方面也不太一样。大陆的比较文学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我本人也参加过一些有关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真是美国不能比的。正如你所言,比较文学在欧洲和美国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美国大学的专业发展,除了经费原因,也有学术研究方面的不同情况。比较文学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是和当时的历史、科技和大学等情况分不开的,当然也和法国的文化传统分不开。这个学科在美国的发展也与欧洲大战、知识分子移民和美国的文化传统分不开。但是无论如何,其中实证的传统非常深厚。直至今日,欧洲和美国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都特别强调对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与文本相关的哲学、艺术、宗教以及社会的问题。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大多数人不太愿意去研究那些很大的问题。所以精深的和具体的研究就特别得到倡导。不管哪一类学校,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总体的特点会强调学术思想的自由。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在美国越来越有跨学科的趋势,美国学校的比较文学逐步化解也是很正常的,不仅是比较文学,其他一些文科也有不同的变化,如英国伯明翰大学著名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就由于经费问题解体,分散到社会学去了。而与此同时新的跨学科学术和教学单位则不断出现,如这里的全球研究学院。但是,我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既然是一种打通式的研究、是一种国际的眼光,它就应当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而不是逐步限制在自身的学科之内,要是以这门学科来定义其他相关学科,这可能恰恰违反了比较文学的初衷。此外,真正要搞比较文学研究总是需要几门语言并通晓其间的文化才行,这又回到了语言和文化问题,所以在这个领域出成果当然是不容易的。因为成果是潜心推出的原创东西,并不是挂上某种旗号,或附加某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立场就会自然转化为成果。
王晓路 比较文学的发展必须有历史观念,这一点我很有体会。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座教授张隆溪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体察。他也多次和我谈起过,比较文学在当时的欧洲是和进化论、科技文化观念以及法国的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而欧洲战事,尤其是二次大战,许多欧洲学者,特别是犹太学者都到了美国,包括捷克的韦勒克等人,在美国倡导起平行研究。所以美国的平行研究除去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外,其实是和消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二战时期的恶果是分不开的。现在张先生撰写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最近已经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相信,这本教材将会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国内大一些比较文学论著都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重复一些大的原则,并将该领域的学理问题置换为不同学派间的问题,以至于突出某种简单的民族主义观点,而没有一种历史哲学意识。大陆由于将比较文学主要放在中文系,不太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学文本的解读训练和中外文的艰苦磨炼,因而一些人不看甚至不懂外文,只是根据翻译材料就进行所谓的“比较研究”。而一些原来学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的学生又非常缺乏对中文,尤其是文言的系统知识和相关文化史的认知。所以一些研究成果在材料和方法论上并没有多少新意,甚至缺乏学理性和人文科学的逻辑。台湾和香港的比较文学则多放在英文系中,也是有道理的。又是语言问题!就像您所谈到的,语言问题与文学研究关系重大。我自己认为,由于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是研究的前提,因此大陆比较文学界所反映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通过原文解读和文本分析而进行所谓的研究,具体而言,一是理论的原文不读,二是作品的原文也不读。有一些研究生只是看到了一些西方理论家的翻译成中文的说法,特别是时尚的理论提法,也不对这些提法、范畴和术语进行必要的历史语义学的还原和相关研究,而只是拾起了一些汉语化的术语,就照搬过来,在自己的论文里进行自助式阐释。这种学术时尚化的做法完全脱离历史文化和语言背景,其理解和解释的误解自然是很多的。我在国内曾对此写过专门的文章讨论⑤。另外,中国大陆在新时期几乎把所有的西方文学理论翻译引介过来,大学里也普遍开设相关的理论课程。在学界表面,似乎理论资源特别丰富,但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个案中,又似乎存在着严重的理论消化不良,所以也就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四、理论的差异
黄宗泰 这确实是个基本的、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学研究在传统上是对文字符号编码的研究。没有语言基础,不能通过原文深入了解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这种研究就只能是表面肤浅的研究,要形成真正的洞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是对文字书写的尊重。你可能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像西方社会一样有什么演讲名人,而是有大量的书法家及作家。这又和“书不尽言”的语言观相悖。而作为文化早熟的区域,文字和书写符号记录了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早期某一文化区域的初民对世界的理解。所以,文字的历史也是一种文化史的过程,而中国书写所附加的历史价值就直接反映出中国人对历史有着特别的敬重,所以一些台湾学者对简化汉字就比较生气。中国语言虽然不是拼音文字,当然也有语音问题,但却不是以此为中心的。因为同样的字有不同的区域方言发音方式。比如有一些古诗,可能用今天的普通话就很难读出韵味来,这就有一个古音和方言的发音问题。而中国人对文字的尊重,其实是对“道”的尊重。因此语言文化没有办法截然分开。就小说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小说的作者是十分尊重的,作为“主体性”的作者和读者往往等同于作品本身一样重要。而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名小说的作者常常处于不确定的状况中,作者和版本情况均比较复杂。几乎所有的小说名著都有不同的版本和作者,这里面就有个历史文化问题,我一直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小说的作者观念进行系统地探究。就理论而言,美国现在也存在这种情况,如一些学生在写论文时就特别喜欢引用那些大理论家的话,像福柯、德里达以及包括苏联的巴赫金等等。好像不引用就不深刻一样。我有一次看到学生的论文有大量的理论引文,就对他说,这些理论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理论家却没有看过你读过的这本小说,这些理论对你来说可以解决你自己的实际问题吗?而有些文章,除去那些看似艰深的引用文字之外,自己实际的内容或者真正的观点其实很少。我不是反对理论,我本人也读大量的理论书籍,关键是如何真正地把握理论,其实需要长时间认真思考这些理论的出现是针对什么问题,又是如何确立的。因此,比较文学立足点是文学,学文学是要有感悟的,文学是一种很难完全抽象出来的东西。好的文学是一种很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以至今并没有被哲学所代替。它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精神探索的艺术方式。上世纪最后的一些年,学界的许多研究都有逐渐远离了文学本身的倾向,看来这个问题要注意。
王晓路 您所谈的这种文字简化史、剪接理论的方式的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文学感悟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诺贝尔奖项就会设立哲学奖,而不设文学奖了。由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源自不同的生活经历,而这种生活经历又是在不同的文化区域,由此,语言和文化成为同一事物的两面。而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读其他民族的写作也有不同的感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虽然人类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人类通过文字符号的艺术编码进行人类精神的探索,是否拥有共性呢?比如某一公认的理论之所以有影响,除开其具体的指涉功能外,往往还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普遍适应性,这正如某一观念可以解释许多经验层面的东西一样。但理论又是不同的,是存在差异的,每一种理论均是对原有理论结构性的缺陷进行的弥补。由于文本是一个开放系统,而对文本的解释也是一个理论互文的方式。因而理论表层的差异性和其内在的共性往往构成一种张力。您是否认为看到差异所在,才能看到差异背后的共性,这是否是您所坚持的差异性研究的理论前提呢?
黄宗泰 还不完全是这样。由于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这可能导致一些人产生某种自大的心理传统。如近现代就有不少文化名人就曾以各种方式指出我们在有某种东西的时候,洋人还在山洞里跑,而洋人有的我们都有;近代以来的许多问题大多是西方世界引发的,而西方学界自身也在不断地检讨,今后会出现东方思想大世界等等。这些说法将历史简单化的同时也将西方学界的自识和批判传统简单化了。这些简单化的观点在今天肯定是不行的。我不否认,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与民族在文学和文化上有大量的相同、相近和相通的地方,既然是人类,虽然语言与文化传统不一样,但情感总是相通的。这也是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前提。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完全一样,那还研究它做什么呢?其次,你如何知道他们之间是相通的呢?所以惟有真正通过对表层差异的理解,懂得如何入手进行分析,才能真正洞见出其中的相同或相通之处,才可能避免或化解那种在历史上引来人类灾难的绝对的民族主义情绪。表面的论证或比附都不具备学理性。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广义的西方,两边的差异确实很大。仅以小说和Novel为例,这中间的差异就实在是太大了。那本有名的斯坦福大学教授Ian Watt的名作《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就将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与英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分析。而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你可以注意到,小说的“小”就很有考究,但是在学界却没有人追究。当然,既然是研究,差异性原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价值评价,即评判高低、好坏,而是更加有利于分析。中国的比较文学已经进行了多年,但真正有分量的中西比较论著似乎比较少见。一些比较研究并没有把有关的学术思想梳理清楚,也没有深入到作品中进行自己的解读,而只是将一些作品的表层现象列出,直接套在某些所谓的理论框架中,再提出一些口号,这种研究成果出得再多,也是留存不下去的。
五、跨学科与中国学
王晓路 这些很有意思,我想是否可以理解为,研究若缺乏批评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我想,跨学科的意义对于人文学术本身而言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在北美的高校中参加了不少跨学科的研讨会,同时也担任一门课程的group teaching教学(不同领域的教授针对同一专题的小组教学)。这学期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每周就有许多跨学科的演讲和研讨。我应邀参加四个系所的演讲或讨论,包括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极有特点的全球研究学院等。经常某一个座谈或演讲,都会有许多不同系的教授和学生参加,而且非常自然和频繁。这样的交叉式讨论或课程对于激发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这一点在大陆高校中是相当薄弱的,各个学院和系科基本上各行其是。由于资源的稀缺,各专业主要的兴趣是“跑”博士和硕士点,“跑”课题项目。至于这个点如何具体发展却往往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系统实施方案。加之人文社会科学的单一量化指标的评估方式,使得大陆学人很受影响。
黄宗泰 由于学术思想和学科本身的发展,原有学科已经很不适应。跨学科是必然的趋势。你也看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本科就设立了跨学科学士学位。而美国大学的考评一般是六年一次,也就是说六年你必须要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果一个人一年就能写好几本书,那书的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王晓路 现在大陆对西方汉学或中国学比较重视,欧洲的早期的汉学到美国成为了中国学研究,这似乎是要与美国注重现实的区域研究等学科一致。您能简要地介绍一下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情况吗?另外您目前在进行什么课题的研究呢?
黄宗泰 欧洲早期的汉学比较注重中国典籍的系统研究。美国称之为“中国学”,当然有其注重实际的传统,但你知道,文科的学问大多是个人的兴趣。我刚才也说过,今天也还有不少人系统研究中国的典籍,包括文学的典籍。当然也有许多人在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等分支领域。就美国学界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而言,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三种比较突出的方面。一是对材料、版本的详尽把握,你会看到美国学者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很大的。他们一些人为了一些材料会申请到一定的基金,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区域去搜寻或做个案研究。讲求实证并获得第一手材料,这确实是美国学界的一个特点。其二是进行翻译。因为一些跨文化理解的问题在仔细翻译中就会出现,所以我本人也做一些翻译。第三用跨学科的方式进行背景研究。单独以观念先行的研究是比较少的。目前我正在写的一部书稿暂时定名为《差异:中国范畴中的小说传统》(Differences:the Chinese Fiction Tradition on Its Own Terms)。
王晓路 这很有意思,希望能早日拜读大作。
注释:
① 前者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后者参见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Stephen Ow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此书在中国大陆有中译本《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参见“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Criticism”in Vincent B.Leitch,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1.
④ 参见拙文《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与中国文学理论》,载《文学评论》2005年3期。
⑤ 参见拙文《比较的悖论与困扰——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思考》,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黄宗泰(Timothy C.Wong)教授,1941年生于香港,成长于夏威夷。1963年至1965年曾作为美国和平队成员在泰国工作。1966年至1967年获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资助前往台北学习中文。1975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1984年至1985年担任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主任在北京大学工作。1985年至199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5年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语言文学系任教至今,其中1995年至2002年担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其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语言文学,尤其是晚清和现代中国小说,并涉及比较文学、翻译和中西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其论著主要有《吴敬梓》(Wu Ching- tzu.Boston:Twayne Publishers.)、《星期六故事: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Stories for Saturday: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pular Fic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上海的夏洛克:程小青的侦探小说》(Sherlock in Shanghai:Stories of Crime and Detection by Cheng Xiaoqing.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差异:中国范畴中的小说传统》等以及大量的论文。
王晓路,教授,1955年生于北京,文学博士,四川大学985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杜克大学文学系高级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访问学者;2007年起担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语言文学系、亚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英文刊物《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副主编。研究方向主要为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近期成果有《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文化研究选读》,以及译著《文化研究指南》等。
标签:比较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王晓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