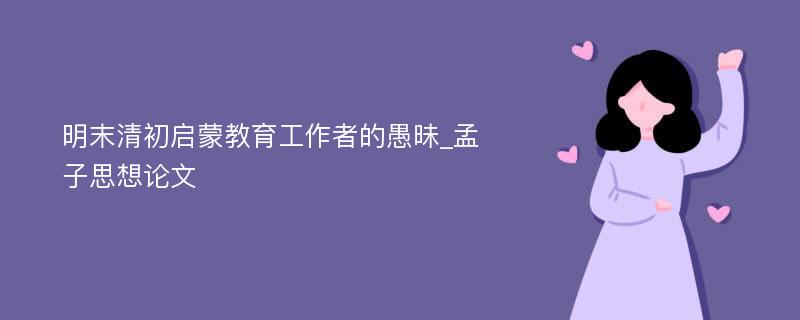
明末清初启蒙教育家的上智下愚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末清初论文,新论论文,教育家论文,上智下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4-0089-05
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智愚之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的智愚是怎么造成的,能否改变,如何改变……这些与教育和人生息息相关的问题,古往今来吸引了许多中国教育家的兴趣与注意。其中,以孔子的论述最为著名,一句“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勘称经典之论,流传千古。然而,惜乎语焉不详。孔子的本意,究竟是以智愚本身分高下,即以智为上,以愚为下呢,还是以社会地位、社会阶层为划分标准,地位高的上层阶级为智,地位低的下层阶级为愚呢?抑或是对智愚所作的价值评判?再者,所谓“不移”说看似明确,其实也是令人费解的:究竟是客观上不可移,还是主观上不去移、不愿移呢?孔子另有一个著名的普适性论断“性相近,习相远”,主张以积极之习去变化人性、培养理想人格。据此似乎可以说,所谓不移指的是主观上不去移、不愿移,而非不可移。但是孔子又有生知、学知的划分,还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之说,这又似乎有些下愚不可以移的意味。诸如此类的问题,无疑使其上智下愚不移论显得更为扑朔迷离,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继续想象与诠释的充分空间。
明末清前期,面对“天崩地裂”、“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和商品经济相对发展所导致的社会阶层身份延续的变化,以及客观上所提出的普及教育的社会需求,启蒙教育家中的陈確、王夫之、戴震等人对孔子的上智下愚不移论作出了一番别有新意的诠释与发挥,使之发生了适应时代的变迁与转换。
一 “习成而不变者,惟上智下愚耳”
对“上智下愚”的问题,陈確是从辨析习性关系为切入口的。在陈確看来,习与性是两个各不相同而又互相联系的范畴,人性具有先天的可能性与规定性,习则制约了人性后天的发展方向。就先天的可能性和规定性而言,人性都是善的,孔子的“性相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论的。如果性有善有不善,那就不是“相近”而是“相远了”。就后天发展性而言,人确有善与不善相远之大别,但这不是因为性中有善不善,而是后天之习的不同:习于善则成善,习于恶则成恶,“其所以有善不善之相远者,习也,非性也,故习不可不慎也。”(注:《陈確集·别集》卷5,《子曰性相近也二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8页。)
极有意义的是,陈確将“上智下愚”均视作“习”的结果而非性的规定:“习成而不变者,唯上智下愚耳。上智习于善,必不移于不善;下愚习于不善,必不移于善”。(注:《陈確集·别集》卷5,《子曰性相近也二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8页。)按孔子的“习相远”说原本揭示了“习”对成性的重要功能,但其人有“生而知之者”一说却将“生而知之”的“上智”排除在“习”的作用范围之外,限制了“习相远”命题的普适性。陈確将“上智下愚”均视为“习”的产物的见解,在理论上扩大了“习”的普适范围,使之真正成为一个有着普遍意义的全称命题。这对人们破除“上智”的神秘性,增强“习以成性”的自信心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陈確不仅一般地探讨了“习”对造成“上智下愚”的决定性作用,他还进一步讨论了“上智下愚”的改变问题:上智是否会移于下愚,下愚能否移于上智?陈確的回答是肯定性的:上智可以移于下愚,下愚也可以移于上智,关键在于习之与否和所习的对象:如果上智将所习之善改为习恶,下愚将所习之恶改为习善,那么上智下愚就会各向着对方的地位互相转化:“上智习于善,则必不移于不善;下愚习于不善,必不移于善。盖移之,则智者亦愚,愚者亦智。”(注:《陈確集·别集》卷5,《子曰性相近也二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8页。)但是,如果不改变自己的原先所习,则上智下愚的地位不仅不会改变,两者间的差异还会日益扩大,愈演愈烈:“不移,则智者益智,愚者益愚。唯其习善而不移,故上智称焉:唯其习不善而不移,故下愚归焉。习之相远,又有若斯之甚者。”(注:《陈確集·别集》卷5,《子曰性相近也二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8页。)上智与下愚本是人中之两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既非上智也非下愚的“中民”。按照陈確的说法,只要注意所习对象,上智和下愚也可以改变,那么处于其间的“中民”当然就更为可移、更没有理由拒绝习善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陈確的“上智下愚”新论,对汉唐“性三品说”将习之作用实质上局限于改变中民之性的一般倾向,应当是一个相当有力的矫正。
二 “生知”非不学而能,全知全能与“无有人生而下愚”
同样是论述上智下愚问题,王夫之似乎更愿意从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的角度予以辨析。这就将讨论从原先比较纯粹的人性论领域引向了人性论与认识论结合的新高度。
王夫之认为:认识及认识能力之是否具备能动的发展性,是否有赖于外界事物的接触和思维器官的思维,是人禽之间的重要区别所在。动物也具备一定的感知与感知能力,“若禽之初出于彀,兽之初坠于胎,其啄龁之能,趋避之智,啁啾求母,呴噱相呼”。(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8页。)但动物的感知与感知能力是先天给定的,无法扩充和提高:“及其长而无以过”。(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8页。)这就叫做“禽兽有天明而无己明”,所以终其身只能用其初命。人则不然,“人则有天道(命)而抑有人道(性)”。(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8页。)人不仅有日新之命,人还具备不断发展与提高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的感觉器官(耳目)与外界事物接触和思维器官(心)之能动思维的综合作用与结果:“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色而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8页。)可见人的认识只能是一个终其身不断展开的过程,而不可能是一次性终了的行为。如果这样来看问题的话,那么那种以不学而能来定义“生而知之”、以为世上真有这种“生而知之者”的说法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甚且是十分荒谬的。因为那种说法不啻于将生而知之的圣人等同于禽兽:“岂暮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今乃曰生而知之者,不待学而能,是羔雏贤于野人,而野人贤于君子矣。”(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8页。)王夫之从人禽之辨的角度否定不学而能意义上的“生而知之”论,应当说是深刻而又机智的。它既揭示了上智问题的认识论内涵,也将那些鼓吹圣人不学而能的论者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同意学知说;要么继续固执己见,那就要冒诬圣之险:诬蔑圣人等同禽兽。
王夫之从认识对象的角度进行的论析亦相当精彩。在王夫之看来,所谓“生而知之”的“之”,并非是一个抽象的全称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部分的甚至是个别的概念:“天下一事有一事之知”,(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9页。)所以孔子的“生而知之”,其言“知之”,应当是“随指所知之一端,而非无所不通之谓”。(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8-459页。)天下事不但各有其知,而且其难易程度对每个人也不总是一样的:此事对甲人易,对乙人难,彼事却对甲人难,对乙人易:“师襄之于琴也,上也;夫子之于琴也,次也。推此而或道或艺,各有先后难易之殊,非必圣人之为上,而贤人之为次矣。”(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9页。)因此上与次的划分是相对的、可变的,而不是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这里,王夫之对孔子“生而知之”之所指的阐释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孔子本意不是十分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所表述的自己的见解及其所隐含的逻辑推论:其一,认识对象是个别的、具体的,圣人对事物的认识尚且不可能“无所不通”,普通人当然更应正视自己认识的局限性。其二、事物各有难易,上与次的界限也各依具体认识对象的不同和所达到的认识程度的不同而不断变动,普通人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去破除圣人无所不知的盲目崇拜,同时对发展自己的认识能力充满应有的信心。
除否定“不学而能”和“无所不知”含义上的“生知”说、提倡注意认识对象的具体性之外,王夫之还进一步以“为学境界”说去界定“生知”。王夫之指出:所谓“生而知之”之“生”,非初生之生,而是生命存在含义上的生:“未死以前,均谓之生”。(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9页。)这样,壮年与老年当然均在此“生”所指范围之内。而壮年与老年是继少年之后的人生阶段。经过刻苦向学和人生的各种历练,壮年与老年期的学术储备和生存智慧应当都有了相当丰厚的累积。(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9页。)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的某种直觉与顿悟达到相当高明的程度是完全有可能的:“迨其壮且老焉,聪明发而志气通,虽未尝不从事于学,乃不拘拘然效之于此,而即觉之于此,是不可不谓之生知也。”(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9-460页。)在这里,王夫之实际上是以为学境界去定义“生知”。这种解释与他的“性日生日成”和“习与性成”说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是十分显然的。王夫之的本意亦是在强调“生知”之归根结底仍以“习”为最终依据。其积极意义是应当予以充分注意和肯定的。然而无庸讳言的是,其间也多少含有某些强为之辩的意味。因为按照“未死以前,均谓之生”的定义,则少年期当也属此“生”之所指范围,何以王夫之将“生而知之”之所指人生阶段仅限壮年与老年期呢?这在逻辑上显然是有所不通的。造成这种逻辑失误的原因,与中国历来的为圣人讳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圣人是人中之杰,其所言是代天而立、句句是真理的圣贤崇拜观念早已积淀为相当浓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即使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启蒙思想先锋们也很难完全摆脱其负面影响与制约。王夫之一面相当坚决地否定圣人的不学而能和全知全能,一面又通过将“生而知之”释作为学的某种境界来维护孔子的圣人形象,就是不愿直截了当地承认孔子“生知”概念中的某种先验偏向,正反映出他所积淀而尚未完全摆脱的圣人崇拜的深层文化心理。但是在这种对圣人的曲为维护中,王夫之对“生”之定义确属别开生面,它使“性日生日成”的命题获得了极为有力的理论支撑:既然“生”是生命存在和生命展开意义上的生,那么人性之生与成就都是与生俱在和终身不息的动态过程,人就永远不应放弃对习的慎重抉择。
比较起来,王夫之对下愚问题的论述并不很多,他对下愚的兴趣似乎远不如对上智那样浓厚。这从一个侧面表露了王夫之相当执着的士大夫优越心理。但他对下愚问题确实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其观点也有若干可述处。主要表现在:其一,指出下愚者也具备理性:“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注: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3,《诚明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8页。)这在实质上是承认了下愚自身转变的内在理性依据。其二、强调下愚由后天之习恶造成,反对将下愚归之于性:“无有人生而下愚”。(注: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3,《诚明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4页。)所谓“下愚不移”,是因后天染于恶习,时间长久便使之日远于本源性之善而后不可改变:“非性之有不移也”。(注: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3,《诚明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4页。)综合以上论述,可以认为:王夫之“下愚可移”的论点虽潜而未露,然亦是呼之欲出:既然下愚者的人性中同样先天地存在着道德理性因素,其现实之愚又是由后天习恶而成而非性中注定,那么,只要充分发挥这种先天存在着的道德理性因素,改后天习恶为习善并持之以恒,下愚不就可以逐渐改变吗?如果愿意再考虑一下王夫之关于人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论述,则王夫之学术系统中隐含的“下愚可移”的内在意蕴当更可确定。按注重现实人性、注重人性的发展性,本是王夫之人性理论极为鲜明的突出个性,也是其人性论的精华所在。他的“性日生日成”和“习与性成”的命题本已揭示了人性的不断发展性和习对成性的重要作用,肯定了人在成就实然性善方面的主体能动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之说更将上述这些发展性、能动性之类一语道尽、极而言之。按照此说,既然后天之习对人性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如此巨大的功能,那么,“已成”之下愚“可移”“可革”应当是合乎逻辑的推论。至于下愚“未成”而“可成”的究竟是“中人之智”还是“上智”,因为存在两个变量而王夫之本人又未明言,后人难以代之定论。但根据王夫之对孔子“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说的认同,认同王夫之可能会倾向于“下愚”首先移于“中人之智”大概可属无妄。
三 “有生知”、“有生而愚者”与“学移下愚”
与陈確和王夫之纯粹从后天之习探讨上智下愚的成因与改变问题有所不同,戴震认为造成上智下愚的原因有其先天的因素,其改变则纯粹是后天所为(戴震归之为“学”)。
戴震认为:人性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正是表现在智愚之别:“人之成性,其不齐在智愚”。“有生知。”(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有生而愚者”。(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4页。)但是智愚差异的存在并不妨碍人性之本善,相反,它是以人性本善为大前提的,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人性的特殊性。比起人与动物善与不善的本质差异,人际智愚差异无疑要小得多,“《论语》言相近,正见‘人无有不善’;若不善,与善相反,其远已县绝,何近之有!”(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页。)“人虽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远者盖鲜”。(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页。)即使是所谓“生而蔽固”的“下愚之人”,虽“其精爽几与物等者,亦究异于物”,(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页。)“视禽兽之不能开通亦异也。”(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页。)而且人与物的类差异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恒久性:“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页。)人际智愚差异却具备了活跃得多的相对可变性。决定这种可变性能否成为现实性的唯一关键正在于学:“惟学可以增益其(按指愚者——引者)不足而进于智”。(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0页。)学不但可以在一般的意义上使愚变明,坚持不懈地学习甚至还可使下愚变为圣人:“益之不已,至乎其极,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则圣人矣。”(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0页。)如果说陈確点明了上智下愚互移的可能性,王夫之道尽了人性的发展性和人的能动性,那么戴震关于学移下愚乃至成圣的提法,则彻底肯定了下愚的可变性和“学”对下愚之“移”的极端重要性。
戴震关于下愚可移的学术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不但一般地肯认下愚之可移,而且明确提出了“下愚者无不可移”的口号:“生而下愚,其人难与言理义,由自绝于学,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怀惠,一旦触于所畏所怀之人,启其心而憬然觉寤,往往有之。苟悔而从善,则非下愚矣;加之以学,则日进于智矣。以不移定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为,知不善而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虽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几与物等者,亦究异于物,无不可移也”。(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页。)戴震对下愚本来就比对上智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在提及上智下愚的场合,他主要论述的都是下愚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戴震眼光向下的学术意趣。戴震论“下愚可移”时特别言明“无不可移”,突出了他的“下愚可移论”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也强化了这一命题的普适性。这对矫正“下愚不可移论”无疑是十分有力的。
戴震的“学移下愚论”甚可注意。(所谓“学移下愚论”是笔者的一种概括,并非戴震的原话。但戴震是确实主张以学益愚者之不足而进于智甚至进于圣人之境的,“学移下愚”的概括信为不诬矣。)本来,孔子论述导致人性差异的因素时,分别使用过“习”与“学”。而在孔子的学术体系中,“习”与“学”的含义是有所区别而又非常接近的。孔子的“学”,“不外乎‘学文’,‘学道’,‘学《诗》’,‘学礼’等等四种对象,均不出政治、伦理范围,其中尤以‘学礼’为主。”(注:参见赵纪彬:《学习知能论》,《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版,第208页。)而“学”是必须有“思”参与方能有所得的:“学而不思则罔”。(注:《论语·为政》。)可见“学”是脱离不了理性思维的。孔子的“习”略为复杂些,当与“学”连用时,“习”字主要指“学”的继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注:《论语·学而》。)当与“性”连用时,其含义则较为宽泛:它指向人之成性的一切努力,兼具认识论与道德实践的双重含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注:《论语·阳货》。)也许因为“习”比“学”的所指更为宽泛,后世学者往往喜欢用一个“习”字,形成了性与习的相关范畴和按此相关范畴讨论人性的习惯。但当宋明之时,陆王心学以尊德性为学术主旨,提倡“工夫即本体论”,否认了“对象性的认知活动对于复性的中介作用”,(注:于述胜等:《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实质上也就否认了“习”的认识论含义,使“习”演变为仅仅依凭道德直觉的活动。至此,中国传统的道德崇拜完全蜕变为脱离了道德理性的道德蒙昧主义,于传统中国后期的伦理学史添加了相当沉痛的一笔。“学”、“习”概念的如上关系与演变概况,也许于索解戴震之主张“学移”而非“习移”下愚的秘密不无助益:过于宽泛的“习”概念为注重“察分理”的戴震所不取,仅仅凭恃道德直觉含义上的“习”概念又为注重理性的戴震所不取。戴震对“习”概念的舍弃和“学”概念的择取很可能都是相当自觉的。
在戴震的学术系统中,知识论与道德论的区分是比较清晰的。在他看来“人之不能尽其才”的大患有两个,其一是私,其二是蔽。内中,私属道德领域,解决的途径是通过道德实践:“走私莫如强恕”;(注:《戴震集·原善》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页。)蔽属认识问题、知识问题;“蔽生于知之失”。(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4页。)解蔽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学习知识、提高认识:“解蔽莫若学”,(注:《戴震集·原善》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页。)“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注:《戴震集·与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这里,戴震对道德问题和认识(知识)问题、对去私与解蔽的两分,实质上是对以往“习”慨念中认识论与道德实践双重含义的两分:道德实践的含义分解给“去私”,由“强恕”负其责;认识论的含义分解给“解蔽”,由“学”任其劳。经过戴震的创造性转换,在戴震的学术系统中,传统的“习”概念消失了,它原先所兼具的双重含义由于被分解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强恕”与“学”,认识(知识)问题与道德问题的边界就显得更为清晰,讨论起来也更加方便。
戴震虽然将道德问题与认识(知识)问题两分,但他绝不以为两者是毫不相干的。相反,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由于戴震十分注重理性的指导作用,认为行必须有知的指导方能无失:“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仁义礼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页。)所以戴震将学德、明德与知德认定为成德必不可少的前提:“学以讲明人伦日用,务求尽夫仁,尽夫礼仪,则其智仁勇所至,将日增益以至于圣人之德之盛”。(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0页。)“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6-327页。)至此,戴震不仅分解了宽泛的“习”概念所兼具的双重含义,而且扬弃了陆王心学“习”概念中过分夸张道德直觉的偏狭内涵。
戴震的“学移下愚”论不仅因其对“习”概念的分解、扬弃与转换,还与他对下愚问题的认识有关。戴震认为,“愚”是一个认识问题、知识问题,是由“学”不足引起心知之蔽所达到的某种状态,“人之幼稚,不学则愚。”(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页。)“蔽也者,其生于心也为惑,发于政为偏,成于行为谬,见于事为凿,为愚,其究为蔽之以已。”(注:《戴震集·原善》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页。)属于认识问题、知识问题的“愚”与属于道德问题的“恶”不是一回事:“愚非恶也”。(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页。)但作为愚而不学不思的一种结果,“愚”与“恶”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任其愚而不学不思乃流为恶。”(注:《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页。)无论从学以解蔽、由愚变明的积极层面,还是从防止愚最终演变为恶的消极层面,“学”之与否对“下愚”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关乎下愚之究否可移。戴震将下愚视作认识(知识)问题,和重视下愚转变过程中学思之理性因素的理解,与仅仅将愚归之于不习善、将愚之改变归之于习善的思维方式之间表现了明显的差异,它体现了戴震道德与认识(知识)两分的思维倾向,也体现了戴震对道德理性自觉性的高度重视:道德实践并非纯粹的道德习行,也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直觉。只有同时兼具道德知识的自觉学习和理性把握的参与,道德实践才会获得永不枯竭的理性动力源泉和明确的道德努力方向。戴震的论述,闪烁着灿烂的理性之光,在宋明以来已经形成道德蒙昧主义的学术大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明末清前期的启蒙教育家们,尽管都不同程度地承认下愚可移或无不可移,在客观上为普及教育的主张提供了人性论方面的理论依据。但他们中却无一人由下愚可移论出发直接过渡到普及教育的实际主张。不仅如此,王夫之还明确表示反对倡优隶卒子弟入学:“学校之造士也夙,而倡优隶卒之子弟必禁锢之,则固‘天’之所限,而人莫能或乱者。”(注:王夫之《读通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页。)这一现象是足以发人深思的。它表明:人性的平等不等同于社会身份的平等,人性理论上的平等也不等同于教育实践中的平等,由前者过渡到后者的关键,取决于也有待于现实社会关系的改变。
标签: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读四书大全说论文; 明末清初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孟子论文; 张子正蒙注论文; 人性论文; 国学论文; 王夫之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