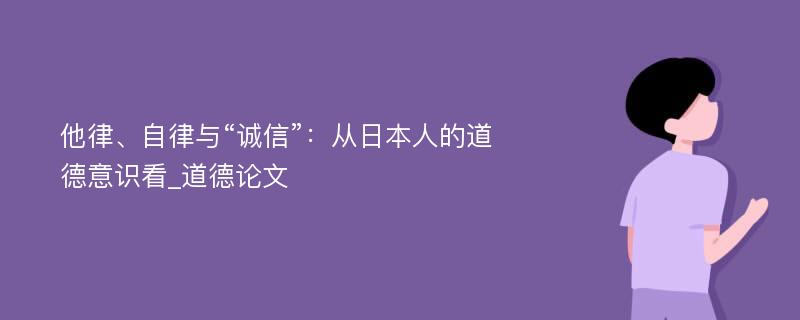
他律、自律与“诚”——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人论文,道德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恐怕没有其他概念能够比“道德”更贴近人们生活的了,故而有关道德的话题也就众说纷纭。有人把道德视为规范的集合,是一系列戒律的体现;有人把道德看作个人良心的自我外化,无愧于己、无愧于心就是道德的了;还有人把道德理解成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或作用,即可以对等交换的约定。这些认识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道德的功能,不同程度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我们认为,道德最根本的特性是它与人的相依不离性,但如何理解人,如何看待人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则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分歧。如果主要强调道德与利益的相关性,将道德的根据放在自身之外的某种集团或社会的隐性或显性的力量,就是持他律的立场;如果主要看重道德与个体,特别是个体内在的信念的相关性,所取的就是自律的维度。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出理论视角的差异,而且常常与民族文化的特性相关;就是说,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生发出对道德所持有的特定倾向,例如,受到千余年基督教文化熏陶的西方社会就比较强调自律的道德观,而在主张德刑相辅、天人合一的儒家宗法文化内,则常常容易将道德视为他律的。与上述二者不同,日本传统文化虽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却保留了浓厚的本土特色,在道德观上也持有明显区别于中国人的主张。日本人习惯于将道德理解为“诚”,一种非普遍的、相对性的或者说强制性自愿式的道德意识。
日本人的心情主义
“诚”是介于他律与自律之间的道德行为方式和评价态度。与他律道德不同的是,“诚”强调当事人的内省、克己和自肃;但又与自律有所区别,“诚”并非“法由己出”,而是针对特定关系、人群所做出的,所以不是普遍有效的。“诚”只产生于有某种缘分或承诺的人们之间,如师生、同事、朋友之间等。
从性质上说,“诚”更接近于道德情感之类的因素,就是说,它包含了较多的情绪、情义性内容,认知、理性等层面的内容明显不足。一些日本学者将之归纳为“心情主义”。
尾渡达雄在《伦理学与道德教育》(注:尾渡达雄:《伦理学与道德教育》,以文社1989年版。)一书中指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表现为心情主义。心情主义就是去掉私心,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自然而然地达到沟通,实现人与人之间整体的融合。在日语中,“善”与“洁净”、“恶”与“污浊”在词源上是相通的。古代日本人认为,肮脏本身就是恶意,洁净本身就是善心。但恶、罪与善、净又有所不同,是指外在、附着上去的东西,它们是非本原性的,因此,罪或恶主要不是内心或动机的问题,它们都可以通过禊或祓等仪式得到清除。这似乎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后者将罪或恶理解为某种实体性存在,而日本人则将罪或恶看作可以清洗、涤除的附着物,肯定了人的努力的有效性,表现出积极的乐观主义。
日本著名思想家相良亨在《传统伦理观的基调》(注:载于《日本人的传统伦理观》,思想社1964年版。)一文中提出,日本人的传统伦理观的基调是重视心情的纯粹性。如果追溯日本人对伦理的自觉方式,就可以看出,把伦理做为客观的法则而加以追求的态度在日本并没有获得成熟发展,也没有构成日本人伦理观的基本内容。日本人在伦理方面的努力表现为求得主观的心情之纯粹性,这一倾向非常明显和普遍。而且,日本人所孜孜以求的,不是针对表现为客观法则的伦理知识或道德意志,而是撇开一切理论化、抽象化的心情纯粹性本身。
相良亨还分析道,日本人的祖先最初所理解的伦理,就文献可知的方面看,是记纪和宣命等古代典籍中体现出来的清明心。清就是指能看透水底般清澈的感觉;明就是源于太阳、没有云彩、一望无际般明亮的感觉。“清明心”是古代日本人视为理想的追求,其原初意义可以理解为“正直的心”。像清流一样,向世人袒露出内心的底端;就像太阳的光芒没有云彩遮挡一样,看出他人的真心,换言之,透彻的清明心就是没有私(注:日语中“私”既可以做“我”讲,也可以做“私心”来理解。)。日本人还强调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然中获得生机,富有朝气地生活着。“清明”(或者说“光亮”)的反对面是“阴暗”、“污秽”(黑、浊、邪),这些又被视为“罪”,此外,妨碍构成自然美、具有生命力之作物的疾病、害虫等也被视为罪。古代日本人就是这样用感官式的词汇来表达人所应有的心情状态,并构成了古代日本人伦理意识的表现形式。
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当吸收外来文化时,日本人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取舍,用本土的道德意识同化、融合外来的道德观念。日本人引进了儒学、佛教,这些外来思想所提倡的伦理学观点大多基于道或道理等抽象、共通观念。日本人却在基本伦理观点上顽强主张独特的心情主义。今日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信仰一神教,但日本人至今仍信奉多神教。日本人倾向于让不同的神“和平共处”,既然同为神(释迦、耶稣、真主等都一样),就值得尊奉。所有的神都是同类的,重要的是信徒们所采取的行动和对待方式。儒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人的精神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使日本人认识到存在着现实社会中人所应践行的伦理。在这之前,日本的道德观念淹没在神道祭祀和村落社会的习俗之中。它们大多是由神话系统的天皇观念和血亲关系的成员互助意识所构成。而儒学宣扬的是不同于“情”的“理”,但日本儒学者却将中国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主敬说逐渐地改造为主诚说。“敬”指正威仪的仪表和攻心中之敌的意志,“诚”则强调对主君的忠诚和对信念的服膺,受到主诚说影响的武士们成为了日后倒幕运动的主力,也成为明治政府主导者。
中世的日本人,也有行为应遵循客观道理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道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就是先使主观的心情变得无私之后表现出来的、此时此地应遵循的道理。所以,讲道理的问题仍然成为了具体地对道理的感觉问题,又被还原成了心情的存在方式。总之,日本人强调的是与这些道理或道相吻合的、有生机的心情存在方式。“诚”常常被日本近代学者引申为“正直”。他们大多不强调仁、孝,而主要关注诚、正直、忠等概念。“正直”指以应当的态度,对面临的事件、事情所具有的是非善恶表现出直观的觉悟。正直不只是知性的直观或情的感受,它还包含了利用当下感受到的心境进行行动的能力。正直有时又可以叫“朴素”,它导致了日本人重视人伦关系、力求在人伦关系中与他人达成心情融合的行为方式。
然而,心情主义也有缺陷。它容易陷入非逻辑、非客观的境地。如果行为者主观上要做恶,就会产生自以为是的心理满足,即便出于纯粹的动机,是当事人以真心而行动的行为,但从行为的手段、方法及结果来看,仍然不能被接受。心情主义直接导致这样的简便思想:只要动机善,一切都可以被允许,结果怎样都不重要。日本社会中的溺爱思想(甘ぇ的思想)、至诚可以感动天的动机论都是这类观念的产物。显然,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与短处是内在相关的,互为一体的。如果要舍弃其短处,恐怕长处也会被扼杀。在长处、短处互为一体的关系中,形成了每个民族的个性。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恐怕就包含了这样的双重方面,我们应对此有清醒认识。
“诚”的道德内涵
从一般意义上说,构成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主要有两类:一是自律性的内在良心,包括信仰、信念以及社会普遍要求的内化。对行为者而言,做或不做的理由在于自己的主动认知和内在根据;另一类是他律性的外在规范,包括他人的监督、规劝,这对行为者来说,做与不做的理由不由己出,而是因为他人的赞扬或贬斥。从伦理学角度分析,出于自律的行为由于是积极、内在的,具有深刻、执著、自主选择等特征,受到了鼓励;相反,出于他律的行为表明行为者尚没有达到主观接受的程度,与社会规范保持相当距离,表现出消极、被动,处于相对较低的道德境界。但是,在日本文化中,“诚”却很难简单地归结为自律或他律中的任何一种,“诚”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道德意识表现形式。
在日语中,有两类“诚”。一是“真诚”、“忠诚”这样的词,它源于中文,与汉语的字义相同,指所做的事与本心的符合。另一个是“诚”,它是和语,即日本原有的词,指对有特定关系的对象所尽的义务。这种“诚”是相对的,而且其内容不在行为,而在心迹,即“诚心诚意”。具体地说,一个日本人的“诚”,不是普遍适用于一切人或对象的,而是针对他所属的集团或对他有恩之人,如他的老师、上司、同事等。我们在此文中所讲到的“诚”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诚心诚意”体现了一种注重主观精神的倾向,这似乎与朴素的宗教情感有关,事实上,有许多人在直观上也感受到,日本人乃至不少日本的经营者、工作人员似乎具有某种宗教式的虔诚态度。不过,这种宗教不是西方的基督教,而是东方的佛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禅宗。一些日本经营者甚至还亲临禅宗的寺庙修行、静心。京陶公司的创始人稻盛和夫在1996年胃癌手术后,到临济宗妙心寺派所属的圆富寺出家,接受了“接心”的修行,据说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能够处处看到他人和自己日常行为中的“心动”,即达到了以天地之心面对万物的澄明境地。不过,他最终没有成为真正的高僧,而是再度回到公司,并以自身的经历和体会教诲年轻人。
“诚”也可以体现在对有恩于己的人的报答上。例如,阪神大地震后不久,本部在大阪的某信用合作社,向受灾者提供5万日元的无期限紧急贷款,不计利息,无需担保,而且也不要保证人,只将本人的名字和联络地址写下便可。一年过后,其中80%的人未经催促就将贷款全部还回。这些日本人感到该信用社救人之难,且又表现出对自己的高度信任,自己也应做出守信的行为以回报。显然,“诚”的约束也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行为力量。
“诚”还可以表现在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上。在日本,相关企业或企业系列内,隐含契约而非正式的、成文契约主导着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基于长期交易关系所形成的相互信任。例如,大企业与下承包企业所结成的稳定而持久的关系,依靠的就不是成文契约,而是不成文的惯例,即日本特有的“商习惯”。其内容主要取决于双方的交易频率、交易的保持时间、交往的历史及相互的信任程度等等。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在交易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原则和短期利益,也要考虑到“商习惯”。“据大阪府承包企业振兴协会1986年对1700个会员企业的调查,大多数下承包企业并不与母企业签订基本契约,其主要理由是‘因为有交易习惯’,作此回答的企业占未签订企业总数的93.1%。甚至还有31.6%的下承包企业在接受订货时并未签订订货合同或接到订货单。他们只是根据口头约定(包括电话)或便条通知等,而没有采取据以防止纠纷的书面交易记录形式。即使如此,他们与母企业之间发生纠纷的现象仍然是非常少的。”(注:《日本模式的启示》,四川人民出版1988年版,第75页。)
“商习惯”的最大优势就是实现了事前的帕累托最优,降低了各种类型的代理人成本,缓解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但它的劣势也正在此,以隐含契约为基础的日本模式在实现了交易方式灵活性的同时,却带来了另一种负面效应:某种程度上的不稳定以及封闭性。对一个没有情感联系和交易经历的外国企业来说尤其如此。这些惯例难以被外国企业所习得,因此,他们就很难打入日本市场。这些缺乏公开、透明操作规则的“商习惯”正是日本企业国际化的极大阻力,也因此常常受到来自欧美等贸易伙伴的指责。
这就难怪“西方人经常为日本人所说的‘真诚’所疑惑,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真诚’并不是坦率地说实话,而是许多种意识的一种复合体。它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真诚的人,就是从不冒犯别人的人(除非他想直接向别人挑衅)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力求协调各种关系的人,那些言行举止都要认真考虑后果的人。”(注:马克·齐默尔曼:《怎样与日本人做生意》,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诚”强调心迹,因此“诚”的体现就不能完全是可视的外在形式。日本人发明的“腹艺”就是体现“诚”的最好方式。日本人认为腹艺是人际交流的最高形式。一个人有问题要问或有求于人时,他是不能或不愿意先开口的,他仅仅只是摆出一些建议。他要求于对方的东西越多,他的建议就越含糊不清。同样,他的朋友也不会感到有要对方直接进行解释的必要,他是靠自己的直觉了解到这一点的。
日本人强调以心传心、心照不宣的表达方式。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在日本国民的生活中,饶舌是被人歧视的,相反,默默地工作被视为一种美德。日本女人所欣赏的男人是这样的:话不多,说出的话却很有分量,踏实工作,任劳任怨,感情不外露,体现在对你的细微关心上。据说,日本人对直率、直截了当的措辞总存有一种抗拒心理,表达请求时,也常常使用间接的、婉转的方式,或者大量使用省略语,只是表明自己的希望,却将对对方的请求省略掉。如说“我想请教您,但是……”(教ぇ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ど……)或者使用助动词,如“稍稍请教您一下,可以吗?”(ちよつと教ぇて けないんでしょぅか)总之,日本人在交谈时,十分强调措辞,好的措辞要充分考虑能否使听者产生愉快的感觉,对此不仅要避免使用命令式或过于直接的词语,而且还要不断观察对方的表情来修正自己下面将要说出的言论。
“诚”也可能导致某种不确定性的道德困惑,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缺乏普遍一致的道德原则,主要强调因人因事而分别采取的当下考虑,即对当事人的具体心境的体察,这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平衡感”。面对道德冲突时,也大多取“美的方式”对待,即以形式、程序的合法性取代内容、过程本身的道德性追问。此外,回避实质的道德原则,以敷衍了事的方式应付道德问题也是常见的倾向。
曾经有日本学者主张,通过扩充日本式的“诚”,就可以达到人类社会的“和”,以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但这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日本人的“诚”有别于现代交往理论,“诚”不是建立在普遍的、公开的规范原则基础上,在日本人看来,“诚”针对的是自己所属的集团,是相对的;而现代交往理论强调的是通过话语,获得所有相关者的赞同,实现理解与相互理解。“诚”不可能提供公共适用的对话、交流的情境,在不相识的人们之间,相互的理解几乎难以企及。此外,在某一共同体中,成员间的“诚”是深度的、相互牵涉的,但是,要在全体人类成员中形成如此深度的交流,成本相当高,恐怕是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的。
日本人的道德意识特征
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兴起,道德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通过“修身”这样的课程强制灌输给甚至是少儿的日本国民。因此,二战后,不少日本人在拒斥战时强制思想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连“道德”这样的词句也不愿提及。50年代中期以后,首先由一些注重传统文化、强调恢复国民自信和社会秩序、来自地方的右翼分子提出了“加强道德教育”的呼声。
那么,日本人所理解的“道德”是什么?他们希望哪些优良道德传统在新时代继续得到发扬?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前一个问题反映了日本人在道德问题上的集体无意识,是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然流露和显现;而后一个问题则因与民族主义、现代化等政治目标相关,成为被人关注的“他在”对象,也经常演变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例如在日本的中小学德育大纲和行为规范中,充斥了许多地缘政治的烙印。我们必须厘清这两个问题的不同,从历史及其流变过程中发掘构成日本人道德意识的底蕴,即由心情主义所衍生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及观念。
“恩”与“义理”是日本人道德意识的重要内容。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儿童阶段子女从母亲那得到的庇护、关爱是“恩”的源头,做为报恩而结成终身的情义,就构成了“恩”的伦理。《日本灵异记》中就有许多关于报恩的故事,宣扬了与恩相关的伦理信条。“义理”是对恩、恩情的回报,特别是当施恩者并不在意时仍然一如既往地回报的情况。如果说“恩”是情绪化、情感性的话,义理则是义务的、理性的内容。“义理”不是交换,而是立下契约之后的履行,获得赠物之后的答谢,常常有时间上的延滞,是一种无期限的长久约定。
“信任”是日本人道德意识的又一个内容。在思想史上,日本人并未认真讨论过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他们不强调对人性的抽象把握,而对人性持本然、自然的态度。因某种缘分(如同学、同事等)而结识后,就会建立起码的信任。随着交往、了解的增多,信任也会加重。但是,一旦对方因某事做出失信或不合常规的处理,对他(她)的信任就会荡然无存。同样,一般地说,日本人不太愿意在许多人集中的会议上对某人的细小问题进行争论,也不会追究别人行动中的详细过程,因为他们强调要让他人产生被依赖的心理。对他人的言行过分挑剔,就显得很不成熟,相信对方,对方就会相信我们,并表现出足够的自觉性。但如果一旦有事实表明对方不能被信赖,那就必须在所有方面、在一切细节上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充分议论、确认,对他就应像对待未成年的小孩一样处处留心。
由意识到“他人的眼目”的存在而产生的顾虑、约束,也是日本人中最常见的道德意识表现。日本人经常关心的问题是:周围的人怎样评价我?他们如何看待我的行为?日本人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都非常在意身边他人的态度,这样的思虑成为了自我约束、“自肃”(即日本人的“自律”)的根源。在主张个体、尊重个性、强调内省自觉的欧美人看来,在意他人的评价的人是缺乏主体性的,但是,对于不得不经营与朋友、同事一体化了的生活、重视与他人的有机联系的普通日本人而言,顾及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却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不少日本人相信,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实际地确立自己的立场和自己应发挥的作用。
不少日本人对政治家、政客的评价非常低,他们常说“政治家都是伦理观念低的人”,或者说“伦理观念低的人都当了政治家”。这当然是戏言,有夸大之嫌,但是,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大都感到在日本人中存在非常明显的“道德鸿沟”。一些普通的日本人有很强的自律、节制意识,并能顾及他人、帮助他人;另一些日本人,如某些官员们,则推委责任、坐享其成等。然而,所谓道德意识低的官员也往往是由日本人自己经过民主程序、投票选出的。从中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对恶的警觉过于软弱、模糊,而仅仅个人的洁身自好并不能自动地影响他人,少数不良之徒就会在“沉默的大多数”眼皮下产生。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在日本国民中,特别是城市的中青年中,出现了严重的“远离政治”的倾向,表现为选举时的极低投票率、人们平日里对政治事务漠不关心、不愿介入政治讨论中等。这些也都反映出工业化之后大众化、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