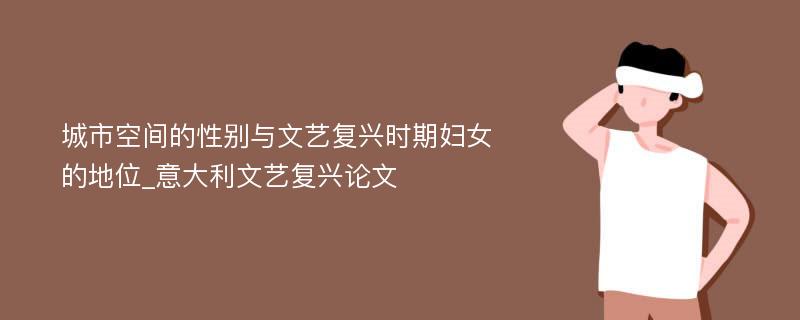
城市空间的性别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性别论文,地位论文,文艺复兴时期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1—0011—06
布克哈特在其186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提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和男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①一个世纪以后,布克哈特的观点遭到了质疑,琼·凯莉(Joan Kelly)就认为,文艺复兴在为男性创造了更多机会的同时,对妇女却有着负面影响。性别的含义是文化的产物,并不存在固定的边界,性别划分总是被不断的改造和强化。②虽然学界仍对妇女有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存在争议,但如果从妇女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来看,与中世纪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社会传统,都在不断建构和强化男性的公共空间和女性的私人空间这一概念:行会大厅、旅馆、主要街道和广场被看作是适合男性的领域,而妇女则被限定在住宅、本地社区、教区教堂以及修道院里,所有这些城市空间都具有私密、家庭和神圣的特征,这正是妇女被期望扮演的社会角色。③可见,城市空间的性别区分,事实上与两性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应,男性企图通过限制女性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方式,最终实现对女性的主导和控制。城市空间具有强烈的象征和道德寓意,它不但有助于界定性别角色,同时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两性、尤其是女性认同现存的两性地位和两性关系,并最终将外界强加的标准内化为自身行动的准则。因此,从根本上说,城市空间的性别化,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程度,从中也可管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妇女,尤其是上层妇女的真实地位。
一 性别理论与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性别化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有关两性差异以及性别与空间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阿波洛尼亚的第奥根尼就认为“与男人相比,女人比较柔弱,如液体一样冷而粘湿,并且不具形体。”④亚里士多德亦认为:女性是不完全的男性,女性的身体就像是孩子的身体一样是不完整的,女性在本质上是虚弱的、冷的,因为她们缺少关键的热量。女性有相当大一部分血流出体外,即月经,月经也是女性身体冷的一个标志。月经类似于精液,但它是不完美的精液;男性则因为精液中的热能量经由血液进入了肉体,因而肉体比较热,不容易冻结,同时也使其肌肉更为坚硬。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女性只是容器,掌握胚胎的完全是男性。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主动的。女人的性格中有某些自然的缺陷,女人在欲望上比男性更少节制,因为她们是更弱的性别。男人和女人虽然都有美德,但他们的气质不一样,男人表现为命令,女人表现为服从。⑤这种“体热说”将男性与热、强壮、主动联系在了一起,与之相对的是女性的冷、被动和软弱,由此人类被分成了两个等级,即男性比女性优越,女性只能服从于男性。身体的差异也导致了两性在城市空间中的不同地位:女性的活动空间被局限在室内,因为阴暗的室内要比日光下的开放空间更适合她们的体质。⑥虽然雅典人推崇男性裸体,但妇女在屋内也会穿着长及膝盖的长衫,如果在街上,衣服将长至脚踝,这已为这一时期的大量艺术作品所证实。女性在各方面都劣于男性,只能臣服于男性的统治,这一观念在中世纪被进一步强化,6、7世纪的伊西道尔说:男性与女性分别是力量和脆弱的代名词。⑦基督教代表人物阿奎那也认为,女性的低劣不只是由夏娃被引诱而导致的一个结果,而是她天生就有的……女人在每一件事上都需要男人的帮助,因为她们在体质和智力上都是虚弱的。⑧女人是原罪,需要以沉默、顺从、朴实、善行和自守、圣洁来得救。这奠定了基督教会认为女人是弱者,是感性的,不具有理性,是性引诱者的基调。⑨在此基础上,基督教教义和世俗社会都坚持将贞洁视为女性最重要的美德,正如佛罗伦萨显贵和人文主义者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所阐述的:妻子们除了必须尽最大努力预防与其它男子有染外,甚至还应避免任何可能的闲言碎语。这种错误是对体面的最大玷污,它损害名誉、破坏团结、致使父亲身份混乱、家族蒙羞,同时在家族内部引发冲突和仇恨,最终将摧毁所有的亲属关系;她不配再被称作是一名已婚妇女,而应该是一名道德败坏娼妓,只配得到公开的羞辱。⑩基于女性的身体特征以及其贪婪、易受诱惑的劣根性,保护其贞洁的最好方式是将其隔离在诱惑之外,即将女性的活动空间与男性的隔离开来,这为城市空间的性别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市空间的性别化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意大利城市国家加强对私人领域进行干涉的结果。随着工商业大族对城市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迫切需要重构与之相应的、全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对两性角色以及两性关系的重新界定本质上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在父权制的社会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事实上与男性对家庭和国家的控制是一脉相承的。限制女性进入城市空间,一方面可以确保女性的贞洁(这对富有家庭、贵族家庭尤其重要),保护家庭的荣誉不受损害,还可以保证所生子嗣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可以限制妇女(主要是贵族妇女)参与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以此确保男性的统治权威不受挑战。比如威尼斯将限制妇女在城市空间中的出现作为一种促进稳定的方式;在佛罗伦萨,国家甚至对妇女的职业、财产和行为也进行了严格限定。
二 城市空间的性别化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市场和主要的仪式空间。广场上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尤其是商业和政治活动,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威尼斯贵族。积极参与商业贸易,尤其是政治活动是贵族证明自己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他们的存在使广场成为了重要的男性空间。里亚托是威尼斯的商业中心,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空间,虽然在此也能发现大量的妇女存在,但贵族妇女却被排除之外。对贵族女性而言,里亚托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危险人物的场所,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里亚托周围的教区里聚集了许多的小酒馆,经常会出现醉酒辱骂和斗殴事件。妇女去那里的话将极易受到语言上和肉体上的攻击;(11)另一个是里亚托的道德危险。那里是借贷和银行活动的中心,而这些活动许多都会涉嫌高利贷。(12)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高利贷者都被描绘成特别卑劣和令人厌恶的人。里亚托同时也是妓女和皮条客的大本营,这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区在道德败坏方面的恶名。由于这些原因,里亚托成了社会上层妇女的禁地(许多下层妇女迫于生计仍会在市场活动,但对上层妇女的要求无疑代表了社会的理想),从而也更加强化了该空间的男性色彩。除了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以外,运河和街道同样也被用于城市的经济生活,许多大街还是庆典游行的必经之路,因此除了实用功能外,它们还展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形象。能否进入公共空间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男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威尼斯男性被禁止进入城市公共空间,那么他的声誉将随即遭到毁坏。例如1323年十人议会所做的一项判决,就是禁止贵族Angelo Trevisan、Michele Salamonhe和Marco Zane前往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进而又禁止他们使用主要的商业大街——马塞瑞阿(Merceria),或者任何其它通往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的主要干道。这个判决虽然非比寻常,但却并非孤例。在大议会的法律中,对违法者的处罚就包括了对贵族是取消现任官职以及将来担任官职的资格,对非贵族则禁止其进入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13)大议会将禁止进入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与剥夺贵族担任官职的特权并列,由此可见有权进入公共空间的重要性。禁止违法者进入圣马可、里亚托以及马塞瑞阿商业大街,就是以一种可见形式将他们排除在城市的政治权力中心和商业权力中心以外。圣马可广场、里亚托以及城市的街道和运河都是男性的活动空间,一旦被禁止进入这些空间,事实上也就剥夺了威尼斯男性的生计、荣誉以及男子汉气概。(14)
如果说圣马可广场、里亚托以及城市的街道和运河本质上都是男性空间的话,城市中的其它空间则通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正如前文所述,住宅、教区—社区以及修道院都被视作是女性活动的场所。需要明确的是,住宅的性别特征并不像其它场所那样分明,它的物质结构,尤其是那些宫邸,通常被作为世系或父系的象征,但住宅内部的活动却受到妇女更多的关注,因为一个妻子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好家事,由此住宅被赋予了更多的女性特征。家事的范围并不如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宽泛。由于男性天生强壮,因此担负供养家庭的职责;女性生性柔弱,所以负责保存和照看男人提供的东西。所谓家事无非就是诸如监督仆人、清点物品等一些小事。妻子是消极的保管人,丈夫是积极的供给者,两者正好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在住宅内部,不同的房间可能也有明确的性别含义。在威尼斯,宫邸的底层一律被用于存货和商业用途,同时这儿也有作坊和办事处。(15)本质上这是男性空间,他们在这里盘点库存、记账和接待客户。楼上的房间包括正厅、卧室和仆人房。由于家族纹章都挂在正厅里,并且从16世纪开始,家族肖像也在此展示,因此它也可以被认为是男性空间。(16)住宅中最为私密的地方——卧室和厨房,这些空间都与女性相关。房间的功能并不固定,它们的性别色彩往往也会因功能的变化而改变,此外也与家庭人员所处的人生阶段息息相关,最典型的就是卧室,在妇女分娩期间,卧室完全成了妇女的领地,这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一般而言,男人并不愿意让他们的妻女在大街上出现,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共同现象。虽然威尼斯下层妇女迫于生计不得不抛头露面,但上层妇女却很少出现在公共空间。许多外国游客这样记述:除了普通妓女以外,所有年轻妇女都被关在家里……因为除了年老的老鸨以外,街上很少有妇女的身影。仅有的几个也无法看清她们的身形面貌,因为她们从头到脚都被包裹在厚厚的衣物以及面纱里。(17)只有在宫邸所在的社区里,妇女才享有一些行动的自由,比如贵族妇女经常被允许到当地教堂作祷告。除此以外,对威尼斯女性而言,似乎便没有了出门的必要,因为她们从不、或者极少拜访朋友,而且也不需要出门购物,所有物品都由男主人负责采买。然而,“社区”所涵盖的具体地理范围原本并不固定,它与男性试图控制女性的程度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共有60多个教区,男性将女性的社区范围界定为她们居住的教区,可能还包括与之相邻的一个或两个教区里。即便是在这些空间里,妇女的活动仍受到限制,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她们穿的高底木屐(zoccoli,类似当今的松糕鞋):它以木料制成,外覆红、黄、白等颜色各异的皮革。……其中许多饰有彩绘,我还见到过镀金的。……它们都非常的高,甚至达到了半码(约合45.7厘米)。(18)另一位游客则写道:“妇女都穿着巨高的鞋底走路,鞋底高度是我拳头的三倍(大约有23厘米),这导致她们行走困难。”意大利妇女穿高底木屐已有很长的历史。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各种高度不等的木屐在意大利非常流行,其初衷可能是为了避免妇女的衣服被街道上的泥泞和垃圾弄脏,但16世纪以后这种风尚就消亡了,威尼斯则是个例外。在威尼斯,高底木屐不仅继续存在,并且高度还有所增加,到17世纪中期时,高底木屐已完全丧失了实用功能。如果没人帮忙,贵妇们根本没有办法穿上木屐,更别说在街上行走了。显然,此时的高底木屐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并且威尼斯的公共空间也素以干净闻名,因此高底木屐负载着更多深层的含义,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妇女的行动进行限制:她们不可能走得太远,也不可能独自行走,如果没有仆人的掺扶,她们几乎是寸步难行。可见,无论从客观环境还是主观愿望来看,妇女的活动空间都极其有限,但这却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即穿着高底木屐的妇女一步一步往返于家庭和教区教堂的过程,一方面让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向邻居展示她和夫家的富有与尊贵,另一方面也更加强化了社区空间的女性特征。
除了住宅、教区—社区外,修道院是另一个典型的女性空间。在男性精英们看来,修道院如同教区,妇女既可以在这里修行又可以与其他女性交往,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她们的纯洁。在文艺复兴时期,女孩能否提供嫁妆以及嫁妆的规模,将直接决定女孩能否出嫁以及嫁入什么样的夫家。根据1370-1389年的数据显示,当时威尼斯上层社会最普遍的嫁资为1000杜卡特,并且这只是一个中间值,最少的也有892杜卡特,(19)随着15、16世纪嫁妆数额的持续上涨,加上当时盛行的婚姻战略(与其给数个女儿小额嫁妆不如给一个女儿准备丰厚嫁妆,这样可以与更好的家庭缔结婚约,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导致越来越多的女孩被逐出婚姻市场。这些女孩被视作家庭荣誉的一大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她们送入修道院。据估计,到1581年时,威尼斯有超过3/5的贵族妇女在修道院里——进修道院也需交纳相应的费用,只是比普遍的嫁妆低;甚至所有贵族家庭都有女儿、姐妹、侄女或远亲在修道院。(20)修女是“基督的新娘”,因此修道院也被视作类似家庭的女性空间,将妇女关在修道院里,与将她们关在家里并无本质区别。
三 城市空间对两性关系的影响
高底木屐在威尼斯贵妇中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城市空间的性别,除了由权力界定外,也是其自身持续发展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国家都深刻认识到了城市公共空间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复杂联系,即城市空间“好像是一种容器,它为种种社会生活活动提供场所,但它又不是消极的容器,它可以促发人的行为、活动,而成为行为的促媒器、发生器。反之,它也可以限制某些行为的发生”。(21)对女性而言,城市公共空间一方面充满了暴力危险,另一方面充满了让她们陌生的阳刚之气,这些不利因素直接限制了妇女在此类空间中的活动。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男性特征更加分明,并促使男性利用庆典游行、竞技比赛、战斗游戏等形式进一步强化这些空间的男性色彩,并对女性进行规训。两性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连续的相互影响,将有助于维护、扩大或挑战当时的观念,即城市中的某些空间应该留给男性,另一些应留给女性。(22)
在威尼斯,宫邸都有水、陆两个入口,社会上层大多选择乘坐自己的私人贡多拉出行,陆地上的大街和广场则留给了社会下层。这些公共空间逐渐成为工匠和工人展示他们男性气概的舞台。其中最能展示男性力量的活动无疑是建造人体金字塔(firza d'ercole),即两群对立派系的男子比赛谁能建造最高的人体金字塔。只有最强壮和最灵敏的群体才能建造出八人高(大约12.2米)的杂技奇观,通常顶端还有一个小男孩在摇旗。另一些展示男子气概的竞技比赛则比较暴力,比如著名的拳头战争。在临时的、象征性的庆典游行中,城中最强壮的男子,少则几十人、多则两千人齐聚在一座桥上像暴民一样群殴。它为从事普通工作的男性提供了向彼此以及外国游客、政要展示自己男性力量的机会。当大规模的打斗比赛上演时,城市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男性力量的展示台。城市里频繁上演的竞技狂欢,比如肌肉展示、辩论、刀战、赌博、演讲、拳击手的游行以及军事风格的操练,使男性彻底控制了城市的街道和广场。在所有这些活动里,妇女发挥的作用都极其有限。她们只能跟随战斗者来到战斗现场:一大群妇女,在后面为她们的丈夫、兄弟、儿子或亲属呐喊助威。由于现场人员混杂拥挤,情绪激昂,并且常常是全副武装,除了那些有钱租用附近阳台当看台的上层妇女外,妇女并不适宜在现场观看比赛,许多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611年9月5日比赛时,因观众发生骚乱,导致28人或淹死或遭踩踏,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女性。参与比赛和观看比赛都成了男性的事情,绝大部分妇女都被排除在外。
“逗牛”或“使狗逗牛”(caccia dei tori)是威尼斯男性表现其对城市公共空间控制权的又一种仪式。这是一项能够充分炫耀男性力量和灵巧度的运动。屠夫的儿子、船坞工人和贡多拉的船夫,在当地显要的支持下,从城市屠场租来12头或更多的公牛,用于当地广场的庆祝活动。体积巨大、训练有素的狗将对公牛展开攻击,而一个或两个青年将利用拴在牛角上的绳子尽力控制住它们:防止公牛脱缰,最终迫使它向狗屈服。随后,胜利者将骑着被他制服的公牛离开广场,并在当地的大街上游行;他们用公牛的血迹宣示了他们对教区周围街道的占有,而他们的妻子或情人则站在露台上或窗边对他们欢呼。窗户不但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的分隔带。男人通过各种展示男性力量的活动、比赛和仪式塑造了公共空间,它让妇女自觉退到了窗户之内——私人的、女性的空间里。
除了展示男性力量的竞技性比赛,以男性为主角的庆典仪式也是塑造和强化公共空间性别的重要方式。相较而言,竞技性比赛展示的多是社会下层的男性力量;而诸如行会或兄弟会游行、贵族运动和比赛,以及国家庆典仪式等,展示的则是社会上层男子的风貌。这些活动不断强化着男性在公共空间中的特权,让女性感到极度的不适。甚至像圣马可教堂、总督宫之类的男性公共空间,社会下层的男子也极少有机会进入。换句话说,以社会上层男子为主导的庆典仪式和活动所要规训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妇女,而是囊括了整个被统治阶级。他们不但以此宣告对妇女的控制,同时也宣告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并非所有的公共空间都能永远不受挑战和保持男性特征。妓女是公然的挑战者,至少从14世纪中期开始,政府便力图将她们限制在特定的城市空间里,“妓女区”完全是当地政府的发明。所有大城市都有一个或数个妓女区:佛罗伦萨在15世纪建立了公共妓院,刚好位于旧市场和洗礼堂之间;威尼斯早在1358年就有了第一个公共妓院,随后又建造了三个或四个,有两个位于里亚托附近。威尼斯的妓女数量非常惊人,正如一位威尼斯绅士向外国游客所形容的:威尼斯的妓女超过了地上的蚂蚁、四月草地上的鲜花和市场上的奶牛。(23)市场是男性空间,妓女区建于市场旁,显然是对男性公共空间的威胁和入侵,并且这种侵犯还在不断扩大。在佛罗伦萨,自政府划定第一个卖淫区开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府又着手建造新的卖淫区,且正对着美第奇宫邸。威尼斯对妓女的控制也不成功,政府只能努力让妓女远离圣马可教堂以及其它的教堂,尤其是远离那些受人尊敬的妇女,然而18世纪时,街头流萤开始侵入圣马可广场,而按照传统定义这是最具男性特征的公共空间。虽然妓女在公共空间的出现导致了空间性别的些许混乱,但这并不影响城市空间的性别划分,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对妇女的另一种规训,即在男性空间中活动的女性都是放荡的妓女,它与公共空间中展示男性力量的竞技比赛等活动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总体上看,城市空间对女性的规训是比较成功和奏效的。威尼斯的妇女不愿意去里亚托,这甚至让大议会面临两难选择。一直以来,威尼斯的金匠和其他宝石匠都在圣马可市场以及圣波罗(San Polo)的教区广场上出售产品,1315年时大议会通过法令,只允许他们在里亚托进行交易。这一法令给威尼斯妇女,包括贵族和平民造成了巨大的不便和困难,“因为他们从来不去里亚托购买这些物品”,这促使大议会在1394年改变决定,允许金匠回到老地方出售他们的商品。(24)这说明妇女已将社会对她们的期望内化为了自身行为的准则。
在文艺复兴时期,性别角色与城市空间概念之间存在着互相补充、彼此强化的关系。男性空间开放、无界的性质使它成为公开的商业和政治活动的理想场所,并促使男人以更为阳刚的方式行事。(25)相反,女性空间有边界且受到许多限制,因此更适合进行被动和私人的活动,并能提升妇女的美德。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妇女在从事着商业活动,但正如佛罗伦萨人阿尔贝蒂在《论家庭》中所吐露的心声:“说实话,如果你的妻子整天都在市场的男人堆里忙碌,整天暴露在公众的视线里,你将不可能赢得我的尊敬;如果我呆在家里与女人一起同样也是对我的贬低;我要干男人该干的事情。”(26)城市公共空间鼓励男性的美德,同时也强迫女性端庄。城市空间的性别化,只是掌控国家权力的男性垄断所有公共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妇女被限制在家里,除了保证血统的纯正以外,还可保证男性权威不受挑战,这与犹太人被限制在隔离区具有相似目的,即确保现有的统治秩序不受任何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地位并未发生实在性的改变,妇女本身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和维护着现存的两性关系和两性地位。
注释:
①[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出版社1979年版,第387页。
②Judith C.Brown & Robert C.Davis ed.,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8,p.14.
③Dennis Romano,“Gender and the Urban Geography of Renaissance Venic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23,No.2,23(Winter,1989),p.342.
④Peter Brown,The Body and Society:Men,Women,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16.
⑤V.L.Bullough,Brenda Shelton and Sarah Slavin,the Subordinated Sex:a History of Attitude toward Wome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8,p.55.
⑥[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黄煜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⑦Angela M.Lucas,Women in the Middle Ages:Religion,Marriage and Letter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3,p.5.
⑧Merry E.Wiesner.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8.
⑨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9页。
⑩Matteo Palmieri,Vita Civile,in F.Battagia,ed.,Bologna,1944,p.133,quoted in Judith C.Brown & Robert C.Davis ed.,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p.152.
(11)Guido Ruggiero,Violence in Early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14.
(12)(13)(14)Dennis Romano,“Gender and the Urban Geography of Renaissance Venice”,p.340,p.341,p.342.
(15)Deborah Howard,Venice & the East: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1500,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137.
(16)James C.Davis,A Venetian Family and Its Fortune,1500-1900:The Dona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Their Wealth,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75,pp.2-8.
(17)Judith C.Brown & Robert C.Davis ed.,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p.21.
(18)Maximilien Misson,A New Voyage to Italy,trans.,London,1699,vol.1,p.195,quoted in 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p.195.
(19)Donald E.Qieller and Thomas F.Madden,“Father of the Bride:Fathers,Daughters,and Dowrie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46,No.4,(Winter,1993),p.686.
(20)Jutta Gisela Sperling,Convents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late Renaissance Veni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12-16.
(21)夏祖华、黄伟康编著:《城市空间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2)Richard C.Trexler,Public Lif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0,pp.358-361.
(23)Gaia Servadio,Renaissance Woman,London:I.B.Tauris,2005,p.124.
(24)M.Margaret Newett,“The Sumptuary Laws of Venic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y”,in T.F.Tout and James Tait,Historical Essays,Manchester,1907,p.270.
(25)Dennis Romano,“Gender and the Urban Geography of Renaissance Venice”,p.348.
(26)Leon Battista Alberti,the Famil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Books One-Four,Trans by Renee Neu Watkins,Wave land Press,Inc.,2004,p.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