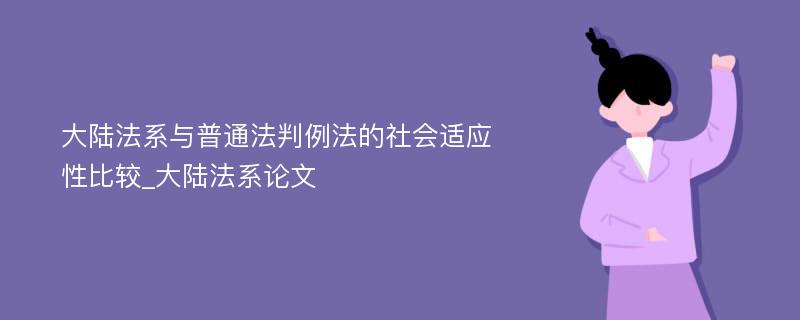
大陆法系法典法与普通法系判例法的社会适应力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陆法系论文,适应力论文,法系论文,判例论文,法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律,是现代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之一。然而,法律只有在适应社会时,它才是有生命的。大陆法系法典法和普通法系判例法均为现代颇具社会适应力的法律,但两者功力之形成和发挥,倒是各具妙处。
一、大陆法系法典法与普通法系判例法各自独特的社会适应力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法是立法者理性思维的产物,法典一旦起草出来,就必定会有一种倾向,即产生许多类似成文宪法的那种永恒性、刚性和不可改变性。《法国民法典》颁后后,法典曾一度被视为万能之物。1804年4月21日一项宣布《法国民法典》正式诞生的法令,其中第7条规定:“从今日起,当该法律开始生效之时,罗马法、法令、普通的或地方的习惯、法律、法规均应废止。无论一般的或特殊的事务都统一由该法典来调整。”可见,法典的至尊地位得到确立。梅尼埃认为:“遵守民法典将成为普遍的道德准则。”波塔利斯认为:“民法典是永恒秩序的体现。”(注: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注1。)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法官只能对法典作字面上的解释,谨慎地寻求法律条文中所体现的立法意图,法官对法律条文的扩大解释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布律尔评论道:“立法者由于被自己完成的巨大而新颖的工程所陶醉,被各方面的赞扬声冲昏了头脑(在今日看来,他们如此老实地相信这些赞誉的确有点幼稚)。因此他们认为,法官将面临的所有诉讼问题,立法者预先已将答案交给他们。他们认为自己提出的规则是合理的,不可改变的。”(注: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8页。)
但是,法典永恒论和法典万能论终究是人们的幻想。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规范的变化只是时间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法典编篡的技术无论多么成熟和发达,也不可能使法典包罗万象,一揽无余。萨维尼曾指出:“可以想象,法典要作为唯一的法律权威,实际上就要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每一个案件作出的判决。人们经常认为:假如凭经验可能并且很方便地透彻了解一些特殊案件,那么就可以根据法典的相应规定对每一案件作出判决。但是任何认真研究过判例的人一看便知,这种做法一定要失败,因为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确实是无法限制的。”(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0、531页。)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情况下,法典法的社会适应性首先立足于洪典法自身的完善。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者一面根据社会需要不断地修改、废除旧法,制定新法。一面注重在法典中提高条文的概括性,诸如使用“善良风俗”、“公共秩序”等高度抽象的概念(自《法国民法典》开始出现),进而使用“一般条款”(从《德国民法典》开始出现),再发展到使用法律基本原则(从《瑞士民法典》开始出现)。特别是法典法中基本原则的出现,使以往法典法的规则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法典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由人调适的规则体系。正如徐国栋所说的:“法律原则的模糊性意味着在法律运作中对人的因素的引入,法律由此被看作是须由解释者补充完成的未完成作品是必须由人操作的机器而不是自行运转不息的永动机,法律的外延由此成为开放性的。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通过解释基本原则,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新要求补充到法律中去,以使法律追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实现法律的灵活价值。”(注: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
普通法系国家的判例法是法官司法经验的产物,有着独特的柔韧性。一方面,尽管普通法系的传统理论声称法官的职能并非创制法律,而是“发现”和“宣布”现存的法律原则,并在审判中加以适用,但每遇新的情况,法官都有权利指出适用于这一情况的法律原则。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法正是通过法官们不断的“发现”和“宣布”新的法律原则逐步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判例法规范是基于个案司法经验之积累而产生的,判例法不在预见一切未来可能发生情况并预先为之设定规则的宗旨,法律的不周延性得到承认,这样,客观上就将补救法律的不周延性,使法律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职能留给了法官,法官的活动必须有较大的创造性。再有,判例法规范的“非法条”形式,使其必须借助于各种“区别”技术,法官在确定和适用判例中的法律原则时必须区别判例中的主要事实和特殊事实,区别判例中的判决理由与附带意见,因而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注: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203页。)具体说来,判例法自身的发展有以下几个途径:(注:参见W·福里德曼:《法理学》,杨日然等译,司法周刊杂志社1983年版,第504~508页。)
1.赋予新救济的司法权。英国上诉法院法官丹宁勋爵曾在Candler v.Crane Christmas & Co.一案中直接了当地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并为情理所容,则应该赋予新的法律救济途径,或大幅度扩张旧的请求权。
2.把不同的常常是零散的法律规则或救济方法整合为一个包罗较广的原则,实际上等于混合了旧法的重述、改造至新法的产生。
3.对于有长久历史的极强说服力的判例,法院可以以正义要求为理由加以改变。
4.有拘束力的判例如不再符合当时法律理想与现实需要,则可通过判例规避的手段来克服。
普通法系判例法自身独特的社会适应力还基于判例法内部衡平法对普通法的特殊补充机制。对于衡平这个概念,梅因曾有过精辟论述:“这个名词的含义是指同原有民法同时存在的另一些规定,它们建立在个别原则的基础上,并且由于这些原则所固有的一种无上神圣性,它们竟然可以代替民法。”“‘衡平’与‘立法’的不同点在于它的权利基础并不建立在任何外界的人或团体的特权上面,甚至也不建筑在宣布它的官吏的特权上面,而是建立在它原则的特殊性上面,这些原则,据说是一切法律应该加以遵循的。”衡平法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上受之于罗马自然法思想,即法律正义必须经常参照自然正义加以运用。衡平法在确认权利内容和保护权利的司法手段上,可补救普通法上的缺陷,使自然正义完善法律正义。
衡平权在理论上似乎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官的固有权利,但衡平法实际上是在衡平法院努力补救普通法不足及缓和普通法僵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衡平法院最初管辖权的对象是信托,衡平法确认了信托的法律地位,通过衡平法院,信托收益人可强制受托人履行其义务,即令其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这种全新的强制被告实行特殊履行的补救方式弥补了普通法上救济手段不足的情况。此外,衡平法还在土地抵押、侵权行为中的欺诈、契约法中的特殊履行等私法进步和改革方面,贡献很多。衡平法的原则体现在逐渐形成的法谚中,包括:衡平法对于应在之行为完成时,始承认其完成;衡平法探求当事人之意思,重实质而轻形式;当事人请求衡平救济之,必须自己为衡平行为;请求衡平法院救济者,必须自己清白;平等即衡平;于两个相等之衡平间加以选择时,在时间上先发生者,优于后发生者;于两个相等衡平间加以选择时,依法律规定;衡平法协助主张权利之当事人,而非协助怠于行使权利之当事人;衡平法以履行债务系由于当事人之意思;衡平法不欲有不法行为而无救济;适用衡平法时,应心量依据法律之规定。(注:参见何孝元:《诚实信用原则与衡平法》,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59~162页。)虽然衡平法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连贯的整体,它是以普通法为先决条件并围绕普通法发展起来的,但如果没有衡平法,普通法只怕早已如一件千疮百孔的衣服了。梅特兰则把衡平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比作注释与本文的关系。(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法律结构与分类》,何力、柯穗娃译,西南政法学院1987年印行,第140页。)衡平法的产生,客观上形成了普通法院之普通法和衡平法院之衡平法的二元造法机制,以人的因素补充了规则因素的不足,大大增强了判例法的社会适应能力。(注: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19世纪英国的司法改革,将原来彼此独立的普通法高等法院和衡平法院合并,成立统一的最高法院,但衡平法始终未改其致力公平解决每一争议的初衷。以1947年的《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大树房产公司案》为例。该案原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委托被告以每年2500英镑的价格出租一批房屋,由于大战爆发,这批房屋没有能全部租出。随后,被告在致原告信中建议以半价优惠招徕房客,原告复信表示同意。这样,剩余房屋以半价全部租出。战争结束后,原告公司改组经理人员,新任经理发现上述情况后,无视公司先前与被告之合意,以减租缺乏协议对价为由,否认该协议有效,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根据普通法之契约原理,除正式契约外,其他契约必须具有对价,无对价之协议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普通法的对价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判定何种允诺应被强制履行的一个标准,是有普遍合理性的,但在该案中,坚持这一原则,则必然导致不公正的结果。为了实现公正的目的,法官丹宁勋爵发挥衡平法的禁止反供原则,冲破普通法对价原理的限制,宣布即使该减租协议缺乏对价,原告仍有义务遵守诺言,无权要求赔偿大战期间减少的租金。随着法院系统的并轨及衡平法判例的积累,衡平法的重心从道德因素逐步转向规则因素,但衡平法的独特性依然存在,它仍然是普通法系判例法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二、司法实践对大陆法系法典法社会适应力之促进
不管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者是否情愿,法典法的司法运用实际上是一个法官对法典的解释引用过程。对法典的解释并不增加法典条文,但无疑会发展法典的内容。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始终如一地坚持法典法是唯一的法律渊源,习惯、权威性学说和判例常被视为准法律渊源或补充性法律渊源,通过法官运用,补充了法典法。
在德国、瑞士等国,由于历史法学派的影响,一直比较重视习惯法。法国虽然在制定《法国民法典》后一度否定习惯的效力,但随着法典的老化,习惯的地位又被提高。例如,《法国民法典》中的合同部分原本只有买卖、租赁、寄托等类合同,以后一些新型的合同,如保险合同、运输合同等,都是通过习惯而演变成为新的法律规则的。(注:参见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布律尔认为:“法律远不是一个凝固的系统,而且具有变化的固有属性,时时处在变化中。那么就必须用一个适当的词来表现这一不断改变社会关系的、既有破坏性、又有创造性的作用,用‘习惯法’这一词来表述这一引申义并不过分。在这一广泛的含义中,习惯法在暗中制定新的法律,它是法律规则的生命力,它的应用范围是无限的。它并非是法律各种渊源的一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法律的唯一渊源。”(注:见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学说在欧洲大陆历来受到重视。“不读阿佐的书就不能进法庭”,“不懂旁注身在法庭也无用”等法谚说明,欧洲大陆从中世纪到16世纪对查士丁尼《国法大全》所作的旁注——学说是极重视的。学说对法典法的完善主要通过法律教育和法学著作两个途径来实现。在法典法较完备的情况下学说的作用主要是已建立在法律体系范围内阐释、改进和发展法典法;在法典法不完备的情况下学说几乎承担了立法者所承担的任务,如确定法律的分类、结构和术语,陈述法律的概念、规则和原则等等。在大陆法系国家,学说常常对立法和判决进行阐述和评论。在法国,对《法国民法典》进行注释的庞大注释书,在司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重要判决的公布,也常常导致法学刊物中对该判决的理论根据提出评价的文章。(注:参见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法国法官本身也认识到这方面的建设性作用。不管这些不同意见如何强烈,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是对法官权威的冒犯。相反地,他们认为这是对司法活动一个不可少的支持。法院经常采纳评论者们所建议的理论。”(注:转引自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关于判例,从理论上或法律上说,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无权创制法律,也不承认“遵循先例”的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5条规定:“审判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据法国法学权威人士赖埃脱诠释此条之命题:其一,使法官不能创立新规则;其二,使法官不得创立一种判例法,以束缚后来之判决;其三,使法官不能以解释之方法纠正法典之谬误。在法国,《法国民法典》第5条的规定仍然有效。法官既不受判例约束,他在法律上、理论上有权作出与判例背离的判决。法律上虽然没有禁止法官在自己的判决中引用判例,但法官不能以判例而不以制定法作为判决的基础。但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判例长期起着补充法典法的作用。(注:参见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在法国和德国,法院判例实际上丰富了《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内容,促使法典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法国,侵权法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法院按照《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发展起来的。《法国民法典》颁布时,侵权法方面仅有五条原则性规定。其中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责任”,确立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侵权行为人有过错才负赔偿责任。第1384条关于行为人对其负责的他人的行为或在其管理之下的物件所致的损害的责任的规定,第1385条对动物所有人因动物造成的损害的责任的规定,第1386条对建筑物所有人因建筑物的保管或建筑不善而造成的损害的责任的规定,都是根据过错推定原则所确立的,与法典第1382条关于过失责任原则的一般规定相一致。进入19世纪末期后,由于科技和大工业的发展,工业事故和交通事故大幅度增长,并成为西方社会普遍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一些国家先后对传统的过错原则进行探讨,试图用严格责任和无过失责任解决事故赔偿问题。法国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发展了过失推定理论。特别是对《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第一款“任何人不仅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而且对应由其负责的他人的行为或在其管理下的物件所造成的损害,均应负赔偿的责任”这一规定,作了扩大解释,确定了雇主和交通事故的加害人的严格责任。在1925年的让德尔诉卡勒理·拜尔福戴斯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确认:《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第一款确立了责任推定制度。这种推定制度与过错推定不同。在过错推定中,被告只要证明事故是无法预见的,事故的结果是无法避免的,事故是由外来原因而不是他所控制的物件造成的,就可以被免除责任。但在推定责任中,被告只有通过证明偶然事件、不可抗力或某种不能归责被告的外来原因才能对推定原则提出抗辩。可见,与过错推定相比,责任推定在对被告的免责条件的限制上更为严格。(注:参见王利民:《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1页。)在契约法方面,《法国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一切作为和不作为的债务,如债务人不履行时,转变为赔偿损害的责任”。但是,法国由于长期受天主教教会法的影响,通常认为契约应该履行,适用于违反契约的正规补救的方法,应该是由法院判令当事人进行特别履行。事实上,法院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法:先是判令履行义务的赔偿责任,赔偿数目自应履行之日按日计算,赔偿数目往往很大,致使当事人宁愿履行义务,这时,法院再酌减赔偿数目,甚至全部免除,法院创造了这一“先减后免原则”。
此外,在劳动法方面,法院发展了有关雇工和职员之社会保护的规定,它们远远超越了《法国民法典》第1780条的规定。法官还运用判例发展了“滥用权利理论”,即所有人依其意愿使用其财产的权利,雇佣契约的解雇权诉讼参与人及其他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如果其权利的行使一旦被法院认为是构成“权利滥用”,即导致损害赔偿请求和玩忽职守请求。在《法国民法典》第121条规定的“订立契约或赠与财产应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的基础上,判例发展了有关保险契约的规定。在《法国民法典》第1376条关于不当得利的一般请求权规定的基础上,判例发展了“非债务清偿”和“逾期罚款”的制度。在家庭法和继承法方面,法院将《法国民法典》中第896条对指定代位继承的严格禁止逐步地缓解,以致于不同顺序的继承人的财产继承顺序如今似乎只是一个灵活的遗嘱起草问题,另外,法院明确地承认了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请求权。(注: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76页。)
在德国,司法判例所发展的诸如“情势不变条款”、“交易基础消灭”、“与事实真相不符”、“失效”等概念,修正了《德国民法典》契约法中最初的个人主义的僵硬性。德国法院以《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这一极富弹性的一般条款为依据,通过司法判例完善了契约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例如,在1919-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使马克严重贬值,债务人极易以支付无价值的货币使自己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这无疑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当时的德国立法机关没有能力提供解决难题的方案。于是,最高法院在1923年运用判例开创了一个先例,认为即便债务人已清偿了债务,但按诚实信用原则,他仍受1923年的新马克的约束。这一判决实际上是法院运用司法权更新了原来已被履行的契约,而强制债务人受新契约的约束。再如,一件从1912年生效的长期租赁契约,规定按指定的价格提供蒸汽。可是市场上蒸汽价格也相应提高。该案说明,契约的履行往往以特定的环境为先决条件,如形势剧变超越当事人的控制,便会导致交易基础的崩溃。在类似案件中,如出现使债务人不公正地履行原契约的形势时,法院有权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扩大交易基础,把契约修改到与所允许的义务相一致的程度。本世纪初以来,德国的大公司、大企业在进行交易活动时多不与客户单独商定契约,而是采用标准契约和统一条款,这就形成交易的一般条件。这些交易的一般条件常被用来转嫁风险或对他方当事人不公正。为了保障交易活动中被动接受交易一般条件的较弱的当事人,法院宣传交易的一般条件必须从有利于对方当事人作解释,违反诚实信用者无效。(注:参见李昌道主编:《当代西方经济法律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53页。)可见,德国法官名义上是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是依靠不断变化的社会一般伦理价值,解决法律疑难问题。通过法官的解释和司法活动,使法典中的诚实信用条款上升到了基本原则的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日益频繁地运用诚实信用原则来解决各种现实问题,从而积累起运用诚实信用的丰富经验。
《德国民法典》的侵权行为法直到现在仍然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德国民法典》关于雇佣人(第831条)、动物监护人(第834条)、房屋或地面工作物占有人(第836条)的责任等,都采用了过错推定的原则。但是,事实情况是过错责任原则已在有关意外事故所致损害的救济方面被立法和司法判例极大地削弱了。司法判例通过许多途径,如通过谨慎注意义务的严格适用,通过直观证据或举证责任倒置及对《德国民法典》831条的突破等,(注:《德国民法典》第831条(执行助手的规定)。)大大改善了意外事故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以致于过错责任和客观风险责任之间实际上常常不再加以区分。例如,在60年代著名的鸡瘟案中,法院认为:在工业产品按其正常用途予以使用的情况下,若因产品制造上的缺陷而致人或物遭受损失,则制造商必须证明他对该产品缺陷没有过错。若该制造商不能提出证明,则制造商须承担赔偿责任。(注:参见王利民:《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再如对重要的意外事故类型,如各种劳动事故、铁路、公路交通及航空意外事故,以及在电力、煤气和核能设置等部门的意外事故的无辜受害人提供损害赔偿时,就无需证明加害人有过错。当然,涉及非意外事故损害的所有物质和非物质损害的场合,过错责任原则依然充分地适用。(注:参见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278页。)
在家庭法方面,《德国民法典》最初带有明显保守的家长制的特征。所以,有关婚姻生活事宜的决定权和全部亲权只存在于丈夫一方,并且允许在能证明被告方对婚姻的破裂有过错时或其患了精神病时方得离婚,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相对于婚生子女有所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立法者对民法范围中的家庭法内容进行重点改革,主张男女平等,与此原则相对立的所有民事法律均于1953年3月31日起失效。但是,由于立法者没能按期采取行动,只好由法官先用判例来填补,直到1957年男女平等法生效。司法判例在实践中确立了夫妻财产平等、父母对子女的监护平等等原则,并为日后改善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以及确立以感情破裂为离婚的条件等方面的立法打下了基础。(注:参见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279页。)
当然,大陆法系的判例远不同于普通法系的判例法。大陆法系国家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先前判决的尊重和依循,并非由于“遵循先例”原则的要求(在大陆法系并没有形成过类似与普通法系的“遵循先例”原则),而是由于下级法院的法官不愿冒自己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推翻的风险,所以几乎是本能地去仿效上级法院处理同类案件的判例,或习惯于找自己过去曾为上级法院肯定的判例加以依循。所以,下级法院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是自愿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下级法院可以不顾上级法院甚至最高法院的判例直接根据自己对制定法(法典)的理解而作出判决。以1927年法国最高法院审理的让德案(该案是一起卡车撞伤孩子的案件)为例。该案上诉时,贝藏松上诉法院以被害人未能提出卡车司机有过错的证据而驳回了赔偿未成年人的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审理该案时认为,一件必须由人看管的物件造成损害时,由于这个物件本身就可能对他人有危险性,所以可以推定看管人有过错。最高法院撤销了贝藏松上诉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但是,重审法院仍按贝藏松上诉法院的判决意旨驳回损害赔偿之诉。于是再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联合庭审会议重新审理,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民法典)第1384条第一款规定无生命物对他人造成损害时推定其看管人负有责任。”在作出这一判决后,最高法院把该案再次发回重审。这时,基于最高法院裁决的权威性,第二个受理重审的法院(本案为第戎上诉法院)必须按照最高法院的意旨判决。但是,如果一段时间以后第戎上诉法院受理另一起内容完全相同的案件时,它完全可依民法典作出判决说,要求损害赔偿必须提出有过错的证据。法国的其他第一审或第二审法院也可以作出背离最高法院主张的判决,今天仍然如此。(注:参见(法)勒内·罗迪埃:《比较法导论》,徐百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由此可见,(1)在大陆法系国家,判例无拘束力而仅有说服力。(2)在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并无独立的法源地位,它是在法典的庇荫下、法典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法典既是判例的限制,又是判例的依托。(3)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审理案件总是根据制定法(主要是法典)的条文作出判决,在例外情况下法院判决以司法判例为基础,也不过是制定法(法典)的释义而已。
三、立法活动对普通法系判例法社会适应力之促进
在普通法系国家,传统学说认为判例法是主要的,制定法占辅助地位,是判例法的改正或补充。17世纪后,随着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加强,制定法的地位逐步提高。19世纪后,制定法从一种次要的法律渊源而跃居为一种引导普通法发展,并与普通法和衡平法相并列的主要的法律渊源。(注:参见(英)R·J·沃克:《英国法渊源》,西南政法学院1984年版,第72、73页。)就现代法学理论而言,制定法有优越地位,因为制定法可改变判例法之先例,在判例法与制定法发生冲突时,判例法应服从制定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制定法往往由法院判决加以解释,重新予以肯定。而这一过程,判例法往往就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制定法。例如在美国,通过判例法的法典化编纂了《统一商法典》,但各州法院在适用《统一商法典》时需结合本州普通法对其进行解释,这样,实际适用的“法律”并不是《统一商法典》本身,而是通过判例法体现的《统一商法典》。当然,法院对制定法的解释不可过分背离立法者的意图,否则,立法者可能通过新的立法来改正法院的解释,但这一新的立法又要受法院解释的制约。在现在普通法系国家中,同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判例法和制定法正处于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循环发展中。(注:参见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制定法在普通法系的判例法体系中常常站在法制改革的前沿对整个法制跟上社会发展要求起着积极作用。与历史悠久的判例法相比,制定法没有陈规旧制的包袱,可以由立法机关根据需要随时制定、修改或废除,因而成为普通法系国家法律改革的重要手段。英国19世纪中、后期包括司法改革在内的法制改革,以及本世纪以来法律制度上的许多重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制定法在这方面的作用。为了促进制定法在法律改革方面的作用,英国还先后成立了法律改革委员会、刑法修订委员会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专门从长远目标出发研究法律的改革,并提出立法建议。(注:参见高桐:《法律的确定性和适用性:英国模式》,裁《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2期。)美国则更加重视制定法的作用,不仅颁布成文宪法,而且进行大量法律汇编工作。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兴起了统一各州法律的运动。其一,成立了“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目的是就各种议案起草统一各州法律的立法案,劝请各州采纳。在它起草的大约60多个统一法案中,《统一票据法》、《统一销售法》、《附条件销售法》等一些商事统一法律被许多州采纳。同时,1926年颁布了美国法律汇编,或称“美国法典”,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法典,是现行的美国联邦法律的系统汇编,把建国200多年来的所有立法汇编进去了(只有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没有收进),规定每6年定期修订颁布1次。其二,1923年成立由法官、律师以及法学家组成的“美国法律协会”,其目的是正确地重新编纂现行判例法,其成果称为“重述”。但“重述”也不是法典,没有法律效力。它所综合整理的都是一些公认的判例法原则,在实践中经常被法院参考引用。但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制定法还是主要在先例留下的空白处和对判例规则的汇编上发挥着有限作用。制定法包含的规范只有被法院所实施和解释,融入判例法体系,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一般说来,普通法系的法律解释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普通词义规则,即根据法规用词的普通词面含义来理解与解释法律。具体说来,要全面理解法律文件,就必须适用法规在语言上的与通常的含义;如果该法规用词属于技术性用词,则必须适用其技术上的专门含义;法官必须根据法律的全文来理解法规的含义,而不能断章取义,作出片面理解;法官必须根据法规全文的内容来确定概括性用词的范围。“词语的通常含义”是该规则的核心内容,按照普通法系的观念,它是指使用英语的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使用的词语的含义。如有疑问,人们可以借助于权威的词典、教科书或者法律的惯例得到正确答案。(注:参见刘星:《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我国法解释方法比较》,载《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2期。)例如,在瓦切尔诉伦敦排字工人协会案(1913年)中,英国上诉法院和上议院采用了这一规则。在该案中,原告(一些印刷工人)指控被告(排字工人协会)从事诽谤和阴谋公开诽谤的行为。英国1906年劳资纠纷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就不法行为被说成工会所为或代表工会所为而言,法院不受理对工会的指控……。”根据普通法,诽谤和阴谋公开诽谤无疑是不法行为。被告虽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不法行为但是要求根据该条款规定免除指控。初审法院认为,该制定法中其他豁免不法行为的条款都有文字说明,受豁免的不法行为是指那种如处理会助长劳资纠纷的不法行为;并认为,尽管该制定法第四条第一款中没有这样文字,但也应合理承认该条款中含有这样的意思,从而判定被告行为不能豁免。上诉法院则拒绝考虑该制定法中有关受豁免不法行为的条件的规定,从而判定被告豁免。从该判决中,工会获得了犯有不法行为可得豁免的通行证。这个判决曾被上议院大法官所援引。
(二)自由心证规则(也称黄金规则)。这条规则是指,如果法官认为适用文字的通常含义将产生一种有悖于该法规目的的结果,那么,法官可以在该文字所包含的许多含义中选择任何一层次含义,作为补救措施。或者,法官可以将他认为必然蕴含在法规词语中的含义表达出来,即法官有权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增加、改变或省略法规用词,防止对法律条款的解释出现晦涩难懂,荒诞不经或毫不合理。(注:参见郭华成:《法律解释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1页。)正如丹宁勋爵所比喻的:“法官应该向自己提出这么个问题:如果立法者自己偶然遇到法律织物上的这种皱褶,他们会怎样把它弄平呢?很简单,法官必须象立法者们那样去做。一个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褶熨平。”(注:见(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三)疑问追究法。这条规则是指,如果按字面解释会造成荒谬的、不公正的结果,法官可以,也应该积极加以补救,以避免字面解释所导致的荒谬结果的发生,补救的办法就是寻找立法目的或立法的意图,并据以选择有疑问的用语的含义。如果首要、主要含义会导致荒谬结果,则选择其次要含义或任何一个比较合理的含义。为了确认立法意图,法官可以从下述方面着手:(1)在制定本法之前,英国普通法是如何规定的?(2)普通法未予解决的疑问与缺陷有哪些?(3)议会对具体问题采取哪些解决方法与补救措施?(4)这种补救办法的真正理由是什么?法官将根据上述各点对疑难问题作出解释,以确立立法意图,克服法规的缺陷,作出补救性措施。(注:参见郭华成:《法律解释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四)目的解释法。这条规则是指根据法律规范目的来解释疑难问题的手段与规则。它是法律解释中最宽泛的一种,法官的权利很大。丹宁勋爵指出:“现在在所有的案件中,在解释法律时,我们采用会‘促使立法的总目的实现’的方法,而立法的总目的是构成法律条文的基础。法官们再也不必绞着手指说:‘对此我们毫无办法’了。不管对法律进行严格的解释在什么时候造成了荒谬和不公正的情况,法官们可以、也应该以他们的善意去弥补它,如果需要,就在法律的文句中加进公正的解释,去做国会本来会做的事,想到他们本来要想到的情况。”(注:见(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5页。)
在事实上,普通法系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要比大陆法系法官持远为严格的态度,因此,普通词义规则作为严格解释的手段是最常用的。
就静态而言,高度体系化、科学化的法典法自然会比判例法有更强的社会适应力,但社会是不断发展的,面向实际的判例法在法的动态运行中真正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社会适应力。不过,大陆法系法典法和普通法系判例法均已注重引入其他法源的补充机制(尤其注重制定法和判例的相互补充)以增强自身的社会适应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陆法系法典法与普通法系判例法在社会发展中的融合趋势。
标签:大陆法系论文; 法律论文; 法国民法典论文; 普通法论文; 判例法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法官改革论文; 社会法论文; 法理学论文; 衡平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