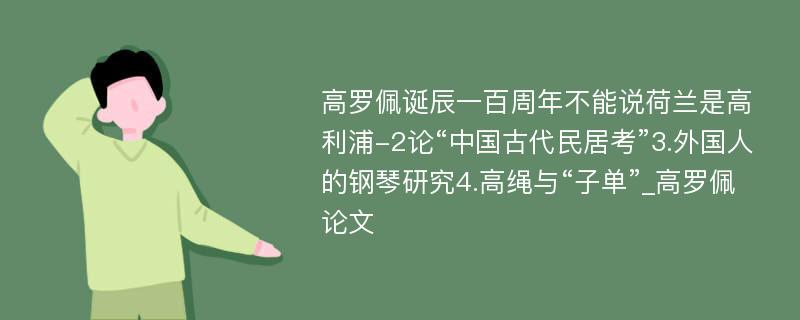
高罗佩诞辰百年——1.说不尽荷兰高罗佩——2.谈《中国古代房内考》——3.“洋客”的琴学研究——4.高罗佩与“悉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荷兰论文,诞辰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房内论文,说不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不尽荷兰高罗佩
陈珏
二○一○年是荷兰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诞辰一百周年。高罗佩是一位职业的外交家,短短的一生,活了还不到六十岁,却因为他业余在汉学研究与侦探小说创作上的特殊成就,与中国因缘甚深,影响甚巨,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传记文学》上,就被人誉为“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六十洋客”之一,又在本世纪初的北京《华声报》上,再度被人选作“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一百个外国人”之一,足见其在中西近代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时至今日,一般读者除了知道高罗佩写过一系列英文版的《狄公案》,风行一时,畅销世界外,对于其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许就了解不多了。更较少有人知道,高罗佩之所以名盛一时,还因为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汉学家,其研究涉及琴、砚、书、画、马、猿、春宫与悉昙等冷门课题,“冷”中见“热”,以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而推陈出新,流传至今。如果要追根究底地问,高罗佩的贡献究竟在哪里?有何与众不同的地方?对今天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种种问题,还真不容易回答。因此,在高罗佩百年诞辰之际,两岸清华主导的一系列学术界活动,就有一定的解谜意义。
二○一○年十月,在北京清华大学近春园举行的“高罗佩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邀请两岸学者分别围绕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悉昙》、《秘戏图考》、《书画鉴赏汇编》、《琴道》和《长臂猿考》六部重要汉学著作,探讨其在今天的性文化史、悉昙文字、春宫图、文物鉴定、古琴音乐文化史与动物文化史等领域的前沿学术意义,别开生面。海峡对岸,台湾清华与汉学研究中心合作,在过去两年中,连续规划了三次“高罗佩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台北国际论坛,将高罗佩汉学研究与目前国际上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连接起来,邀请柯律格(Craig Clunas)、高居翰(James Cahill)、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毕嘉珍(Maggie Bickford)、史美德(Mette Siggstedt)、艾思仁(Soren Edgren)、孔维雅(Livia Kohn)、柏士隐(Alan Berkowitz)、高彦颐(Dorothy K o)等一系列欧美一流的汉学家,群贤毕至,长少咸集,从艺术史、文化史、宗教史、目录学与文学等不同学科的视野,研讨高罗佩对于今天在物质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中开发议题的意义。笔者有幸参与规划推动两岸清华的上述高罗佩研究的种种新近学术活动,在此扼要从性文化史与物质文化史(笔者认为,物质文化研究其实包括了高罗佩之文物鉴赏研究、悉昙文字与古琴音乐研究等内容,所以把这些合为一体)两大方面,介绍一下国际间高罗佩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方向,以飨读者,也作为对高罗佩百年诞辰的一种学术纪念。
高罗佩对中国的性文化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自不待言,而在其《中国古代房内考》与《秘戏图考》两部名著之后,西方这方面的后续研究进展,则较少为人所知。笔者近年曾在台湾《汉学研究》上择要介绍,因不易为大陆读者所见,综述如下:仅就春宫图研究而言,上世纪六十年代,Sheng Wu-shan继武高罗佩,用德文撰写了Die Erotik in China一书,专门研究中国春宫文化,内有大量的明清春宫图。同时,英国研究东南亚艺术史与春宫画的专家Philip Rawson之Erotic Art of the East:the Sexual Theme in Oriental Painting and Sculpture一书,也有专章讨论中国春宫画的传统,显示了西方正统的艺术史家开始把中国的春宫图作为东方艺术的一部分纳入其研究视野。到了八十年代,西方的社会与知识界,经过性解放运动,情色文化的大规模泛滥,春宫图不再是社会上的禁忌,于是以私人收藏为研究基础的中国春宫图专书,也次第面世。例如,德国出版的春宫画册《素娥篇》即是一例,而John Byron 之Portrait of a Chinese Paradise:Erotica and Sexual Customs of the Late Qing Period一书,则以作者本人的收藏品为基础,聚焦于晚清,研究的时段,渐趋于细致。约略同时,日本浮世绘春宫画的收藏家与研究家福田和彦之用意大利文与英文所作之中国春宫画系列专书,更呈现了中日春宫图比较研究的新趋势,展示在这一领域内东亚邻国的文化的同源与异质。接着,时至九十年代,距高罗佩自印《秘戏图考》约半世纪后,新一代荷兰的中国春宫图收藏家Bertholet将其私人藏品陆续公之于世,计有《春梦遗叶》与Gardens of Pleasure:Eroticism and Art in China等两种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和慕尼黑出版,前书为Yimen神甫所编,后书为Bertholet所编,书前有法国汉学家班伯讷(Jacques Pimpaneau)的序言。凡此种种之集大成者,则为高居翰目前尚未出版之Chinese Erotic Painting的大书,学界正在饶有兴致地期待其不久问世。
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中,“物质文化研究”已渐成显学。从历史看,“物质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名词的首先出现,是在一八四三年,这门学问却在十九世纪末即已成为人类学与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中,它逐渐发展成一个跨越历史、文学、艺术史、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跨界”领域,自有其特色,相当引人注目。然而,在很长的时段里,“物质文化研究”在西方并未与汉学界相关联。西方汉学界的“物质文化研究”,一般认为,要到柯律格在一九九一年出版Superfluou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后,才正式起步。不过,近二十年来,汉学界的“物质文化研究”,在美国与欧洲,开展得相当蓬勃,重点集中在艺术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文学等领域,极值得借鉴。高罗佩生前,上述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研究”潮流,还远没有引入到汉学界来,相信高罗佩应该完全不曾想到,其所著的各种汉学专书,是否属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个问题。至少,直到近年也还无人提出高罗佩的汉学研究其实与“物质文化研究”深有关联的论点。于是,笔者提出,高罗佩的汉学著作中,有很大部分是时代超前的“物质文化研究”:例如,《琴道》研究的乃是以“琴”为代表的音乐的“物质文化”在东亚区域内的流传。《书画鉴赏汇编》则论书画的装裱与辨伪,均从传统的文物书画的鉴定出发,融入文化史的视野,与今天所谓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一脉相承。《秘戏图考》与《中国古代房内考》分别从艺术史和社会史角度,深入涉及春宫画乃至性学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悉昙》则从文、字、形、意,研讨其学的难传之秘,对象虽然是宗教文化,其处理的方式与视野却是“物质文化”。同时,笔者在台湾《新史学》的另一篇论文中也谈到,甚至属于动物文化史范畴的高罗佩的《长臂猿考》也与“物质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连。因此,从“物质文化研究”的新视野重读高罗佩,就成为高罗佩研究在其百年诞辰之际再出发的许多新的研究途径之一。
高罗佩的各种汉学著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至中叶相继问世的,离现在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一方面,学术界惊奇地发现,其中很多重要的见解非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历久弥新,可以启发新的诠释。另一方面,时代的前进,也使得其研究的各个方面有待批判性的补正。
谈《中国古代房内考》
李零
《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中文译本,前后出过两个本子,每次都很不容易,每次都留下遗憾,个中甘苦难为外人道。
第一个本子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内部读物)。稿酬千字二十四元,合同十年,一笔买断。此书铺天盖地,有无数盗印本,错字很多(因为不给看校),如“图版”印成“版图”,“那话儿”印成“那活儿”。这个本子,还被转让版权给台湾桂冠出版社,后者错得离谱,没有机会改。
第二个本子是商务印书馆二○○七年版。我们苦苦等了十年,本来取得Brill授权,打算在三联出版,希望出个修订本,流产,这才转到商务印书馆,版税百分之八,又是一签八年。这个本子是正式授权本,经过全面修订,增加了六个附录,印得很漂亮,但也有遗憾。一是图版纸挤进了前言,二是作者介绍有误。他们在付印前让我看过,然而奇怪的是,我指出的问题,他们坚决不改,理由是编辑管不了印制。还有,就是没有印数。
关于高罗佩,在商务版中,我已经说得太多。我很久没有回到过这个话题,没有两岸清华这个会议,我还转不回来。一九九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荷兰大使馆筹备过一个会,纪念高罗佩逝世二十五周年,文章我都写好了,不知怎么回事,会没开成。我没留心,今年是何年,想不到,高氏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高罗佩是我老师那一辈人。他这一辈子,人只活到五十七岁,但写了十九本专著,三十六篇文章,十七本小说,真不容易。
《中国古代房内考》是高氏的传世之作,在他的十九本专著中名气最大。这书是一九六一年出版,当时我才十三岁。马王堆帛书是一九七三年发现,比它晚了十二年。他看不到这么重要的发现,但他的书好像是为这一发现做准备。我在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那阵儿,所里进过这本书。我见此书,如获至宝,复印过一份。我们的翻译就是利用复印本。
高氏对中国性文化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讲都是开创性的。此书从上古讲到明清,跨度很大,但作为支撑的东西,主要是三大块:房中书、内丹术和色情小说,其他,大多是点缀。这三个方面,过去是三不管。第一个方面归医学史管,医学史不管;第二个方面归宗教史管,宗教史不管;第三个方面归小说史管,小说史也不管。专业人士没人搭理,非专业人士又不得其门而入。你只有理解这种困境,才能理解他的贡献有多大。
他的书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很容易给他挑毛病,每个方面都可以挑点毛病,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书可以取而代之。
高氏的学问有两个特点,常人不具备。
第一,他是个外交官,但肩无重任,衣食无虞,有的是时间。他是把主业当副业,副业当主业,兴趣广泛,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很投入,不玩则已,玩,就玩到很高水平。他不是学界中人,自然不受学科限制。“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问题,他没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问题,他也没有。
第二,他是个大玩家,一切跟着兴趣走。他懂多种语言、多种文化,走哪儿玩哪儿,玩哪儿算哪儿,并没有特定的学术目标。这种研究既不同于早期的传教士汉学,也不同于法国的学院派汉学,更不同于二次大战后兴起配合地缘政治的美国汉学或所谓中国学(China Study)。他就一个人,寓学于乐,寓乐于学,自娱自乐。
这种研究很奢侈。
高罗佩是职业外交家,他在五个国家当过驻外使节。五国中,他在日本待得最长,前后三次,长达十三年,在中国只待过五年,但对中国可谓情有独钟。他太太是中国人,她说她的丈夫简直就是中国人。他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研究中国文化。很多人都觉得,他比中国人还热爱中国。杨权先生说,他对中国的赞美,真让我们受宠若惊。
外国人夸中国,李约瑟是代表。他的研究,对纠正西方人的偏见有大贡献。“彼丈夫兮我丈夫”,大家彼此彼此,扯平了。但我们不要忘了,他到中国找科学,标准却是现代科学的标准,非常西方的标准。
外国人爱中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爱。爱或不爱,用不着大惊小怪。日本人,唐代,很佩服,但现代不一样,谁把它打败,它才佩服谁。欧洲人的爱,是博爱。殖民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对王土,王对王土上的一切都很爱。
陈珏先生谈《长臂猿考》,让我浮想联翩。人对动物的态度可以折射人。殖民也好,奴隶制也好,人和动物的关系也好,都不是近五百年的事。现在,埃及考古,发现修金字塔的人吃面包,喝啤酒,所以说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工人,但工人和奴隶怎么定义,吃好喝好,是不是就不是奴隶?奴隶也不都是关在笼子里。
人类对动物的慈悲心从来就不曾彻底过。他们的爱,从来都是以人为中心。再爱,也断不了口腹之欲,不吃牛羊猪,就吃鸡鸭鱼。猫狗不能杀,苍蝇蚊子要不要保护?“杀要人性的杀”,本身就不是动物标准。
高罗佩写这本书,结论很简单:中国人的性生活很正常,不但正常,还很高尚,这个结论有点像李约瑟。
美国有位女学者批评高氏,认为他的书是个大阴谋,他把中国写成男性的理想国,是为了抵制女权运动。这么讲,当然很过分。但高书的主旋律是赞美,这点没错。他的褒是针对贬,不是贬男或贬女,而是贬中国文化。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主要是文人士大夫的风雅生活,如笔墨纸砚、琴棋书画,他怎么会对房中术这么“低俗”的问题感兴趣,主要是缘于画,缘于明代的“春意儿”(春宫画)。他是从“春意儿”顺藤摸瓜,摸到上述三大块。
高罗佩的《秘戏图考》是此书的准备,他的基础材料是收在《秘戏图考》里。《秘戏图考》是他第二次出使东京时所写,《中国古代房内考》是他第三次出使东京时所写。两本书都是他在日本利用他在日本收集到的材料写的。《秘戏图考》附有《秘书十种》,就是基本的文献素材。其中有房中书,有明清小说摘抄,有春画题辞。
高氏研究房中书,主要是追随叶德辉。他对叶德辉的死深抱惋惜。叶德辉在《双楳景闇丛书》中辑过《素女经》、《素女方》、《洞玄子》、《玉房秘诀》,主要来源是《医心方》。《医心方》是日本的医书,里面抄了不少失传的中国古书,很宝贵。高氏讲房中书,主要是利用叶氏的辑本,叶氏错,他也错,在考镜源流和文献校勘上没有太多贡献。但他指出,这些书还有更早的背景和更晚的延续,却很有眼光。
中国的房中书,我做过系统研究。《医心方》的引书,主要来源是道教的房中七经,房中七经前有《汉志》六书,《汉志》六书前有马王堆七书,可谓源远流长。我从我的研究发现,它们代表的传统是个绵延不绝的传统,即使传到明代也没有断绝。例如高氏搜集的明抄本《素女妙论》就是解读马王堆房中书的钥匙。
关于内丹术,高氏的讨论相对薄弱。最初,在《秘戏图考》中,他把中国的采战术看做性榨取。蒙克(Edvard Munch)的画就经常把女人画成吸血鬼。后来,他接受了李约瑟的批评,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他又强调,这是一种“水火既济”之道,不是两伤,而是两利,对女性有利。其实,采战的评价,还是要从多妻制的背景来考虑,中心还是男性。高书对中印房中术的比较研究,很有意思。它们到底谁传谁,高氏说中国传印度,只是假说,但他说,中国的房中术年代早,有自己的独立起源,没错。中印房中术有相互影响,也值得研究。我写的《昙无谶传密教房中术考》就是对高书的补正。
小说这一块,主要反映的是明清时期的传统。小说中的房中术并不神秘,主要是“顺水推舟”、“隔山取火”、“倒浇蜡烛”这一套,很容易懂。大家读不懂,主要是淫器和春药。这次,我的论文,《角帽考——考古发现与明清小说的比较研究》,就是研究出土的淫器。这篇文章本来是应曹玮先生邀请,就秦帝陵博物馆的文物讲几句话,因为开这个会,我就拿它来凑数。杨权先生在会上说,我应该写一部《中国淫器考》。其实,我早就从这个阵地上撤下来了。
“洋客”的琴学研究
沈冬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本业是外交官,但他却触类旁通,因缘际会成了一位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及日本文化——深造有得的学者,著作涵盖宗教、书法、绘画、砚台、音乐、房中术等常人等闲不易涉足的领域。公余之暇,钻研学术之外,高罗佩还舞文弄墨创作了十余本以唐代狄仁杰为主角的英文畅销小说《狄公案》,他著作等身,兼顾了学术研究之严谨与文学神思之富赡,天才横溢,令人叹服。老外交官胡光麃先生,将高罗佩与李约瑟、伯希和、高本汉等学者同列,推崇为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大“洋客”之一。
根据高罗佩好友、另一位老牌外交官陈之迈的记述,高罗佩一九三五年出任荷兰驻日大使馆秘书,对日本文化源头的中国产生了兴趣。这位二十余岁的年轻人多次到中国搜集典籍器物,研习书法绘画。据说他在北京访师学琴,随身携带节拍器一具,以测试琴人抚琴节拍的稳定度,琴人关仲航连弹两次《平沙落雁》,速度分毫不差,让高罗佩大为惊奇。说真的,这个小故事也让我大为惊奇:本来传统琴人抚琴操缦是比较自由的,不像西方音乐强调节拍观念。我本以为高罗佩一心向往中国传统文化,不料还是有着西方人的“赛先生”本质,仍然忍不住要以西方科学的角度对东方艺术冷静客观地评量一番。
无论如何,高罗佩最终拜在逊清贵族琴人叶诗梦门下。叶诗梦原姓叶赫那拉,名佛尼音布,号师孟,后改诗梦,他的姑姑即是系近代中国大政于一身的慈禧太后,其父是晚清两广总督瑞麟。叶诗梦以贵公子而精于艺文,即使清室覆亡,家道中落,他的气度涵养、举手投足之间想必仍凝聚了贵胄世家的典雅高华,让高罗佩这位“洋客”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段师弟琴缘为时甚短,叶诗梦逝世于一九三七年,但高罗佩对老师念念不忘,数年后出版《琴道》一书即是献给叶诗梦,又手绘叶诗梦小像,“遍请中国友人题咏”,可见叶诗梦对高罗佩影响之深。
高罗佩音乐研究主要集中于英文撰作的《琴道》(The Lore of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Ch’ in Ideology)及《嵇康及其〈琴赋〉》(Hsi K'ang and His Poetic Essay on the Lute)二书,其中尤以《琴道》最能呈现高罗佩对于琴的全面及深刻理解,但至今仅有部分章节迻译为中文,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琴道》一书以英文写成,初稿于一九三八年面世,分三期刊载于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的《日本文化志丛》(Monumenta Nipponica)上,一九四○年上智大学结集成书出版,一九六九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全书包括七章、四个附录,插图数十帧,以及一篇作者自撰的文言文后序,文字颇为雅洁。第一章《概论》开宗明义说明琴为文人雅士之器,同时兼具合奏及独奏功能,并由文字学论琴的源流发展,及琴在日本的流传。第二章《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介绍《乐记》之中以礼统乐、礼乐偕配、“声音之道与政通”等礼乐治国的音乐观。第三章《琴学研究》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章,第一节《资料》说明研究资料来源,第二节《起源及特点》,由中国音乐史讨论琴道之所以生成,且归纳了儒、道、释三家在琴道中的体现,可以说是琴学的“三教论衡”。第三节《琴人仪止及规范》,论述抚琴的场域空间、弹奏环境及聆赏对象的规范,如何携琴,琴童、琴社等。第四节《选文》则选译了五篇琴学论文,以显示琴道内涵风格的差异。第四章《曲调的意义》分析琴谱中常用的“调意”,并由标题音乐(Programmed Music)的概念将琴曲分为神秘行旅、历史之曲、文学琴歌、自然之曲、文人之曲等五类,同时以曲例详加说明。第五章《象征》,第一节介绍古琴各部件名称及象征意义。第二节翻译冷谦《琴声十六法》以解释琴的音色和触弦手法的象征意义。第三节介绍弹琴指法及其象征。第六章《关联》,前三节阐释鹤、松,梅、剑与琴的关联。第四节翻译二十二个与琴相关的故事。第七章《结论》。以下又有附录四种,包含《西方琴学文献资料》、《中国琴学文献资料》、《古董之琴》、《中国琴在日本》等。
仅就以上非常简略的内容大纲,已可看出《琴道》的内容闳富,包罗万象。无怪乎此书至今仍被学者推崇为“巨著”、“研究中国古代琴学的权威之作”。但也许是作者的自谦之辞,高罗佩的初心似乎无意于成就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他在序言里自陈本书仅是一篇文学性的“散文”(Essay),提供理解琴的门径,尝试去描写琴。虽然如此,翻开这本问世已七十年的著作,还是很容易震慑于这篇“散文”的深度和广度。首先,此书在取材上异常丰富,包括散见于古籍中有关琴的论述、琴学专著,以及最特别的琴谱。明清两代有大量的琴谱传世,高罗佩显然是由搜集的过程中发现这也是绝佳的研究素材,而《琴道》中有关琴的曲调、曲目、指法、空间场域、抚琴规范等论述,很多就来自于这些琴谱的记载。高罗佩说,有些资料是经过年余的寻寻觅觅,才在日本或中国书店的阴暗角落发现的。这种走街串巷搜集资料的方式,与今日学者坐在电脑前运用数据库可谓大相径庭。其次,高罗佩并非是只精一门的学者,胡光麃说:“高罗佩一样专家都不是,却是一位业余研究汉学范围最广的怪才。”因为视野广,因为天赋高,所以注定他的入手不局限于琴,《琴道》中除了广泛地观照经史诸子,更经常援引书法、绘画、园林、砚石等其他的文人艺术体验来诠解琴,可以说,他是以文人生活的整体品味衬托了琴。其三,高罗佩的琴学研究兼跨了中日文化,这是源于他对东皋禅师的推重。东皋禅师俗名蒋兴俦,字心越,号东皋,康熙年间东渡日本长崎。禅师精于琴艺,为虞山派传人,《东皋琴谱》在日本流传甚广。高罗佩既对东皋禅师感兴趣,辑有《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一书,对于琴在日本的流传也特别关注,这些论述占了《琴道》相当篇幅,体现了他跨文化的宏观格局。
然而,《琴道》毕竟已是七十年前的旧著,此书出版时高罗佩也不过是三十而立的青年,如果我们仅能叹服于此书是古琴研究的“集大成者”,岂不代表了半世纪以来学术的停滞不前?此书其实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例如琴道的儒、释、道“三教论衡”(高罗佩自己并未提出“三教论衡”之名,但表述手法却近似唐代的“三教论衡”),其实“三教”是“失衡”的。再如他将琴译为Lute而不用较为合适的Cither,当时的乐器学权威萨克斯(Curt Sachs)已觉不妥,但高罗佩以为欧洲文化中Lute与游吟诗人有特别的联系,更符合琴的文化位阶与内涵精神。此一观点恐怕悖离了乐器学的科学分析,而文化位阶与内涵精神的认知更是见仁见智。
高罗佩的朋友都知道他最推崇明代文化,他的收藏以明代文物为多,书斋也名“尊明阁”。因而对明代文人生活的向慕追求也体现在《琴道》中,书中取材、观点大抵不脱明人风味。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罗佩是以明代的琴学理想框架了整个中国琴史,历史长河中的琴学发展经过他的筛捡压缩,成为一片明代风景的画片,这也许是本书最大的遗憾。
高罗佩曾说:“余癖嗜音乐,雅好鼓琴。”一九四三年,大战方殷,高罗佩奉派调任重庆,担任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在连天烽火中,他依旧以琴会友,成立了“天风琴社”,与旧雨新知鼓琴不辍,还曾经与琴家张子谦先生一起“琴集”,在张先生的日记《操缦琐记》里留下了一段有趣记载。观察高罗佩的交游过从,以及他与当时学术环境的应对交涉,我们注意到了《琴道》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二十世纪前半期,整个中国沉浸在追求“现代化”的氛围中,当传统艺术面对“现代化”的大纛时,无不努力重整原有的知识体系,为自己在新时代里找到合理的定位点。以古琴而言,不论王露进入北京大学教琴、王光祈译琴谱为五线谱,还是今虞琴社诸公以西方音乐理论诠释琴乐声响,都反映了这种与西方知识接轨的企图,这是《琴道》写作时的时代氛围。但高罗佩却另出机杼,他不以西方音乐理论来合理化中国的琴学传统,反而以明代文人生活的整体品味来衬托琴。他采用了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书写策略,“君子不器”的通才视角,为西方读者建构了以琴为中心的明代文人生活想象。这种书写策略是否隐含了对于当时学界风潮的反思?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这位现代洋客外交官,借着《琴道》及其他众多汉学著作,的确展现了他暂别现代的企图心,以及对传统眷眷不可自拔的向往。异哉!此洋客!
高罗佩与“悉昙”
王邦维
我的这个题目最冷僻,是命题作文。当然,我愿意,因为我最早知道高罗佩的名字,确实是因为“悉昙”。
我可能需要先简单解释一下“悉昙”和“悉昙学”这两个词。悉昙梵语的原文是siddham,意思是“成就”。在印度古代,儿童启蒙,学习拼读或写字,首先要学习一个字母表,称作“悉昙章”。唐代有位义净和尚,到印度去过,在印度有十多年,回来经过印度尼西亚,写了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南海寄归内法传》,书中有一章,叫《西方学法》,开首就讲当时印度人学习梵文的程序:“创学悉谈章,亦云‘悉地罗窣堵’。斯乃小学标章之称,但以成就吉祥为目,本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转,成一十八章。”意思是四十九个母音和辅音,互相拼合,可以拼出许多的音或者字,归纳为十八个章节。义净还说,六岁童子,学这个要学半年。悉昙章这个东西,在南北朝——估计也许还更早——时代,传到了汉地。传入汉地的以及在汉地重新抄写的梵字就被称作悉昙、悉昙字、悉昙字母或悉昙体。这是悉昙的第一层意义,但悉昙还有第二层的意义,那就是,由于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和密宗理论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梵字的念诵和书写具有了特别的神秘的意义,既然这一类梵字称作悉昙或悉昙字,有关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也就被称作悉昙学。这种悉昙,滥觞于印度,后来的发展和发扬光大,却主要是在中国和日本。尤其是在中国的唐代。好些年前,我为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梵字悉昙入门》写的序,就做过这样的表达。
高罗佩的《悉昙》一书,不如他其他的书,尤其是《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出名,书也没有中译本,所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高罗佩《悉昙》一书的内容,然后提几个相关的问题并尝试做一点解释。
高罗佩的书,书名叫《悉昙:中国和日本梵文研究的历史》。书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前一部分是研究部分。先讲中国,分量最大,然后讲日本,篇幅小一些。后一部分是他收集的与悉昙相关的图。
对高罗佩的书,我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高罗佩为什么会对悉昙发生兴趣?
一般来讲,我觉得,一个人对研究题目的选择,如果没有像现在这样政府指定的社科基金研究、行政或某种利益的介入的话,通常会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个人兴趣,二是对问题熟悉的程度,包括自己的教育背景及前期的准备,三就是机缘。
先讲第一条:兴趣。高罗佩对悉昙发生兴趣首先与高罗佩的博士论文有关。高罗佩的博士论文是Hayagrīva: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马头明王古今诸说源流考》),一九三五年出版,二○○五年在曼谷重新印了一个精装本。这跟高罗佩研究悉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Mantrayanic或者Mantra汉语翻译是“真言”,也就是咒语或咒语一类的文献。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都相信,咒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因此成为他们宗教崇拜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佛教的一个派别叫做真言乘,也称密宗。唐朝中期,密宗一度是最有名、影响最大的一个佛教宗派,肃宗、代宗时期最红火。密宗崇拜很多神,其中一个神是马头明王。这个神是从印度过来,随佛教过来的,但在印度教系统里也有马头明王,而且有马头明王的崇拜。高罗佩对马头明王的研究与密宗有关。他对悉昙的兴趣,我想与他当时就注意到悉昙跟真言宗也有密切联系有关,这实际上是他博士论文的一个延伸。
第二条,从教育背景讲,高罗佩此前受到的学术训练、知识体系,为他做悉昙的研究,已经做了很好的准备。另外,与高罗佩个人有关的,就是三十年代初,他在东京,跟荻原云来—当时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位梵文学者——学写悉昙字。今天杨先生讲《秘戏图考》,说高罗佩的字可以叫“高体”,“高体”的风格怎么来的?我觉得就跟他学写悉昙字有点关系。写悉昙字在日本发展出了一套学问,是所谓悉昙学的一部分。
第三条,高罗佩的书,是他在荷兰驻印度大使馆任职期间写的,书也在印度出版。这本书由印度的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出版不是偶然的。支持他出书的两个人,一个是Raghu Vira,另一个是Lokesh Candra,都是当时印度很有名的学者。前者五十年代时跑到中国来,弄了很多东西回印度,国际印度文化研究院就是他创建的。Lokesh Candra是他的儿子,现在还在。他们是当今印度最关注印度文化在亚洲的传播和演变的学者。
我的第二个问题:高罗佩的研究以哪几个方面的知识作为支撑点?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高罗佩的这本书和马头明王那本书,以印度作为研究起点,马头明王也好,悉昙也好,都是这样。马头明王研究印度方面分量更重、更多一点,然后再延伸到中国,延伸到日本。中间牵涉到西藏,因为真言在西藏佛教中也很重要。高罗佩整个教育背景,就是以印度学延伸到汉学,再延伸到日本,最后落在中间一点,也就是中国。至于西藏,他学过藏文,很多其他的语言他都学过,但他真的使用得比较多的是汉语,还有梵语,还有日语,再就是藏语,包括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
我的第三个问题:高罗佩对悉昙的研究,从学术上讲,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悉昙的研究在日本是很成气候的。日本佛教有一个宗派叫真言宗,我们很熟悉的空海,就是真言宗的和尚,在京都附近的高野山还有他们的本宗寺庙。空海也到中国来过,在西安的青龙寺跟当时的惠果法师学习。日本关于悉昙的书很多,但是日本的悉昙学的书很少像高罗佩这样来做讨论的。高罗佩不在学院里工作,但他按照学术著作的框架和要求来写书,同时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他的书在西文的著作里,是第一部,因此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
高罗佩讲到悉昙,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中国和印度文化传统不一样,印度重声音,中国重文字,所以两种传统接触,加上佛教的原因,就往两个方向发展,发展到后来就形成把梵文字母,也就是悉昙字,变成一种神秘的东西,就是抄写悉昙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在宋代以后就断绝了,但日本一直延续到现在,叫做“观想”,写悉昙字,看悉昙字,要静坐,要观想。再有是把那些字母组成不同的图案,叫曼荼罗。修不同的法门时用不同的曼荼罗,中间有很多悉昙字,每个字都有很神秘的意义。
高罗佩说梵文作为一种外国语言,在中国的学习从来没有成气候,因为中国人对语言本身没有很大兴趣,就是对字有兴趣。高罗佩提到了三点理由。我个人认为,高罗佩指出印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不一样,一个重声音一个重文字,这一点是很正确的,但在解释原因上还有些问题。比如说他认为中国人自觉文化优秀,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为什么梵语作为语言在中国影响不大,还有其他原因。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的过程中间,也传到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区,有些地区,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比如和阗,还有龟兹,梵语的影响就很大,而汉地不是这样。这还不完全是汉族对自己的优越感,优越感也有。但我觉得原因是中华文化当时发展的程度相当高,汉语很强势。在古代的新疆或者东南亚地区,当地的语言不是强势语言,所以梵语进入之后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占上风,高罗佩这一点上的解释有点牵强。高罗佩讲了悉昙字在中国和日本的流行,依赖于真言乘的兴起,这是对的。
高罗佩在书里非常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人经常分不清语言与文字的区别。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多人还是没把它弄清楚,最近国内出的研究悉昙的书,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还是没弄清楚。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从高罗佩研究的特点思考我们现在的人文专业教育模式。
高罗佩的研究,从印度开始,延伸到中国,以中国为重点,同时还延伸到日本。说他是汉学家,其实不全面。他是跨界的,研究的选题也跨界。他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做出来成绩斐然。与他早一些或同时的一批所谓的汉学家,例如沙畹、列维、伯希和、戴密微,情形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