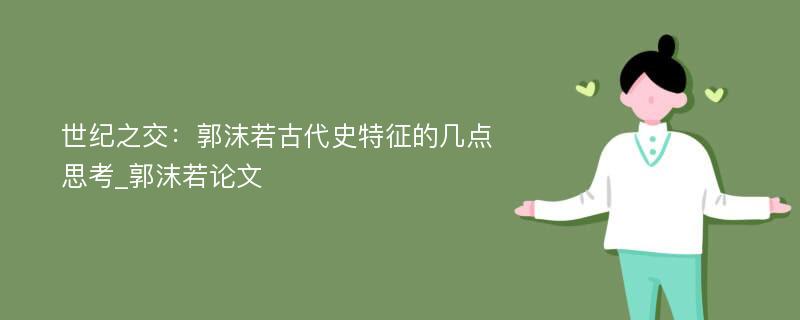
世纪回眸:郭沫若古史研究特色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几点思考论文,特色论文,世纪论文,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2)01-0020-05
站在新千年的开端回首中国20世纪学术史,郭沫若是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远因 而最引人注目的巨匠之一。因此,反思郭沫若古史研究的特色,对于世纪之交继往开来 的中国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谨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的思考。
一
郭氏学术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原创性,这一特色体现在其整个研究及其成果上。在 上个世纪的学术界,郭沫若是引进和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先驱之一。人们熟 知的是他第一个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引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建立,这当然是其学术原创 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对此不少学者已论述甚为精详,勿庸复赘。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 视野开阔,才华横溢,原创动力极强。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身居海外的郭沫若受 欧洲哲学家斯宾诺莎等的影响,就已开始形成“泛神论思想支配下的古史观”。[1](P4 9)就在这一时期,郭氏不仅在诗歌等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独领风骚的巨大成就,而且在 学术研究方面也展示了卓越的原始创新才华。例如,早在他1921年发表的史学论文《我 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2]中,就将秦汉以来封建专制主义所湮灭已久的上古思想文化 ,比喻为西历63年以后长期埋没于维苏威火山灰下的古罗马澎湃(庞贝)城,决意“以我 自由之精神直接与古人相印证”,“发掘我国澎湃城”,并且声明:
所有据论典籍,非信其为决非伪托者,决不滥竽。后人笺注,非经附以批评的条件, 亦决不妄事征引。 其全文篇目为:
上篇 泛论之部——思想与政治之交错
1.滥觞时代政治之起源
2.玄学思想之宗教化
3.私产制度之诞生与第一次黑暗时代
4.第一次平民革命之成功与神权思想之动摇
5.第一次再生时代Renaisance
下篇 各论之部——再生时代各家学术之评述
1.再生时代之先驱者老聃
2.孔丘晚年定论
3.墨翟之宗教改革
4.庄周之真人哲学
5.惠施之唯物思想
显然,作者意欲对上古思想作一次比较系统的探讨。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明确指出 :
“记忆易消灭,由此易于消灭的记忆所曼衍之传说,因之而愈可珍尝。书籍易散佚, 由此易于散佚的书籍所保存之思想,因之而愈可宝贵。传说不可尽信,然其中尽有古代 之精神潜流于其间;”“一片兽骨之化石,一片古器之残存,在无幻想力者视之,亦不 过一片善骨之化石,一片古器之残存而已;殊不知其中正有座虚幻空灵的蜃气楼台存在 !神话传说之类亦如是,谓神话传说毫无历史的价值者,太重视后人所撰述之史籍,重 皮毛而忽视其精神者也。”
这篇论文是西方考古学及其重要成就已经进入郭沫若视野,并引发其创造性研究思维 的生动反映。在20世纪初叶,著名学者王国维以其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及其重大成就 载入学术史册,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郭沫若大约已经知晓,不过,王氏的二重证据是指 考古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而郭沫若上文视野中的出土资料则指一切考古发现,实已较 王氏又进了一步。不仅如此,郭沫若关于古史传说价值的卓识在当时也是极为难能可贵 的,对此,他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1923年新年特号撰写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 》一文中,又开宗明义地指出:
“关于三代以前的思想,我们现在固然得不到完全可靠的参考书,然而我们信认春秋 、战国时代的学者,而他们又确是一些合理主义的思想家,他们所说的不能认为全无根 据。”“所以我们纵疑伏羲、神农等之存在,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时代的思想 为一些断片散见于诸子百家,我们怎么也不能否定。”[3]
成仿吾在此文译后附中指出,“不论是在一般的人或在专门的学者,不论是中国人或 是外国人,没有象我们文化的精神与思想被他们误解得这样厉害的。外国人可不必说, 即我们新旧的学者,大抵都把他误解得不成话。旧的先入之见太深:新的亦鲜能捉到真 义,而一般假新学家方且强不知为知,高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样混沌的学界,能 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 的境地的,以我所知,只有沫若数年来的研究。”年轻挚友的评说固然充满了爱护之情 ,但是,“能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 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确是青年郭沫若的本色。这种并不一味地信古或疑古,把古史 传说人物及其时代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而认定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代的古史观点, 在当时明显卓立于疑古、信古世风之上。在这两篇早期论文中,郭沫若以其深厚的旧学 根基结合新的理论方法得出的上述卓见,已为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所证实,他本 人也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最终坚持和发展了这些正确观点。如他主编的《中国史稿》关 于原始社会部分的章节,就是将大量考古资料结合文献中的古史传说研究后编写成的。 [4]
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原创性成绩是大量的,在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以 后尤其如此。其具体成果在学术界也是人所共知的,本无须一一缕述。但要强调的是, 他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仍然注意积极引进采用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方法,因而一再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如在论证西周为奴隶社会时,他不仅详尽地占 有了文献和出土资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分析,而且进而引用比较史学的方法 ,以古希腊斯巴达的奴隶“黑劳士”与西周的农业奴隶进行对比,并引用了民族学的方 法和材料,具体说即凉山彝族奴隶制的材料作为旁证,探讨的结果虽然只是一家之言, 但这种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多重论证的方法,颇具新义,又如在作为先秦重要史料 的青铜器断代研究方面,郭沫若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即作出 了划时代的贡献。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早在汉代即有发现并初步用于古文字研究,至宋 ,更已成为金石学著录的主要对象,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不过,直到20世纪初,尽 管已被著录的商周铜器已达数千件之多,对之的收集和研究仍未脱离传统金石学的窠臼 。正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序言所说,传统的金石学著录“或仅采铭文, 或兼收图象,或详加考释,或不著一语,虽各小有出入,然其著录之方,率以器为类聚 ,同类之器以铭文之多寡有无为后先,骤视之虽若井井有条,实则于年代国别之既明者 犹复加以淆乱,六国之文窜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载数卷,视《尚书》篇次之有历史系统 之条贯者,迥不相侔矣”。商周积年长逾千载,其大量的铜器倘无科学的断代,则这些 第一手资料的珍贵学术价值就无从实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寓居日本的郭沫若,在尽 可能详细占有材料、吸收学术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研读和翻译德国学者米海里司 的名著《美术考古一世纪》,掌握和运用其介绍的近代考古学理论、方法,尤其是器物 类型学的方法,来研究商周青铜器,按其形制、花纹、铭文内容和字体等因素特点,首 次一扫混沌,将商周铜器分为四期,为科学地区分青铜器年代奠定了基础,无论在史料 学还是先秦史研究方面,这都是开创性的卓越贡献。
二
将治学与明道相统一,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又一特点。在这一点上,郭沫若继承发展 了我国史学明道求真、经世致用的古老传统。中国史学家历来就以“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己任,“述往事、思来者”,以学问来回报生养自己的国家民 族。郭沫若发扬光大了这一优秀的学风,并把明道求真上升到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通 过学术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把史学研究和自己心中的真理追求自觉地合 二为一。为此,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开门见山说: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5](P6)
但是,令郭沫若深深遗憾的是,“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 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 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因此,他特别申明: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地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 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5](P9)
众所周知,这部为回应“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而撰写的书,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流派真正诞生的标志,也是郭沫若学术原创精神最生动突出的体现,在当时和后来都 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正如许多学者已指出的那样,这部书毕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历 史的初创之作,从史料的采用到若干具体论点,都还存在一些幼稚、粗率之处。对此, 作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自我批评道:“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 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5](P3)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本身并不能代替具体深入的学术研究,不能保证具体研究结论天然正确。一方面,郭沫 若古史研究的卓越成就,是在先进理论方法指导下通过艰苦探索获得的,另一方面,作 为一个襟怀坦诚的学者,上述不足或错误之处,也多为郭氏自己以后的研究工作所纠正 改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我怀抱着欢 欣鼓舞的心情,期待着史学界的研究工作会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期待着我自己的错 误会有彻底清算干净的一天”。[5](P4—5)这同样是中国古代史学家追求真理和真实这 一优良传统在郭沫若身上的生动体现。当然,学者的生也有涯,而学无止境。伴随着郭 沫若一生巨大学术成就的,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例如,他在充满激情地撰写《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时,为了论证“由人组成的社会”的共同规律,就否认中国的“国情不同”。这既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更不合于中国的历史实际,虽然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文化背景下也属事出有因,但毕竟难脱削足适履的教条主义毛病之嫌。又如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有多变、善变的特点,这固然与他思想活跃、才华横溢的诗人气质相关,更是其明道求真的治学特色使然,而且所变多是成功或正确的,但也有不成功者,其晚年在杜甫评价问题上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即是一例。
三
不尚空谈的实证研究,是郭沫若历史研究的又一特点。
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如实地揭示人类活动的轨迹,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上个世纪传入中国的唯物史观,把历史归结为充满矛盾而又 有序的、可以认识把握的过程,并且从人们的物质需要入手研究历史的发展变化,为深 刻阐释人类历史的规律提供了最缜密科学的理论体系。郭沫若并不是从国外引进历史唯 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人。早在19世纪晚期,中国的报刊就已出现过马克思和梅林的名字, 但直到20世纪初,朱执信、马君武、刘师培等人才零星地传播过唯物史观的个别理论, 如阶级斗争观点等。唯物史观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据研究,最 早对此作出贡献的是李大钊、杨瓠安,稍后则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达,还有 胡汉民等人。[6](P134)尽管“李大钊、蔡和森、李达在阐发唯物史观的同时,已经结 合历史实际作了初步的运用和探求”,[6](P143)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真正形成 ,始于郭沫若系统的实证研究,而其集中标志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面世。
实证研究本身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悠久而优秀的传统之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的长篇巨制,乃是其在搜集爬梳皇家“石室金匮之书”丰富史料记载的基础上 ,复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7]的辛苦探索而成。此 种求真求实的古老传统,影响极为深远。明代王阳明就曾说过:“以事言之谓之史,以 道言之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8]对于史家来说,所 谓“道”,即社会古今演变的历史规律,它应该寓于“事”亦即具体史实叙述之中,应 该以史论结合、尤其论从史的方式体现出来,决不能空言其“道”。郭沫若继承并发展 了这一传统,他虽然批评自己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之道时犯过“公式化”的毛病,但从 根本上说,他并非以论带史,而是在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即力图用实证研究“来考验 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郭沫若深知实证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而实证研究的首要前提即 是必须占有大量材料。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1954年新版引言中指出:“研究历 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决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 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如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 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5](P4)而在该书1947年写的后记和此前三年写 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存在一些错误,主要问 题即出在对材料时代性的鉴别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本教 条主义的粗率的书。相反,读过该书的人都会看到,那是一本大量占有史料的实证研究 之作。事实上,流亡日本期间的郭沫若在困难的境况下,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花了巨大的力气来收集和整理古代的史料,包括传世文献资料和甲骨金文资料,运用 这些资料,不仅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而且相继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 、《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和《两周金文辞大 系》及其考释等古文字学重要著作,为其古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观郭沫若的整 个史学生涯,尤其是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以来,他都坚持了实证研究、不务空虚的学术风 格。而且他总是站在学术前沿,密切注意新的学术资料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解放以来 ,无论是从殷墟新的发掘,侯马盟书的出土,新疆出土的《坎曼尔诗鉴》和《论语》抄 本等考古新发现,还是从纪念馆中的银币,和在崖县受托整理《崖州志》,郭沫若总是 能以新见到的学术材料为出发点,敏锐地发现或解决问题,高屋建瓴地提出新见解,充 分显示了他实证研究的深厚功力。
郭沫若学术研究的特点当然不止以上所述,但在新世纪开端回眸既往,瞻望未来,要 在总结上个世纪成就的基础上繁荣史学研究,郭沫若学术生涯的上述特点,确实是21世 纪的史学应当切实继承和发扬的。
收稿日期:2002-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