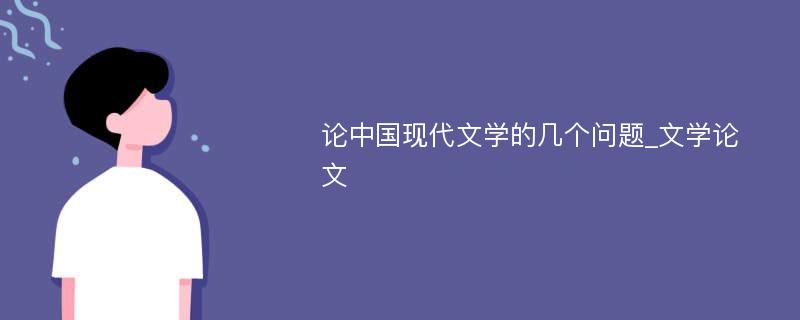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还原与学理原创的互动
杨义
我现在讲的一个命题,就是文献还原和学理原创之间互动的问题。我过去在做现代文学研究时,曾经涉及到这些问题,有一些体会,我称之为文献还原和学理原创之间的互动八事。
第一个问题是版本的鉴定和对这些鉴定的思考。有一些作家20世纪50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选集,我把它们称做绿皮书。这里边有作家在当时气候之下对作品的取舍、修改和自己在序言中的解释,我觉得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对自己的定位,这有很多事例。还有一种并不是因为50年代这个原因,而是作家本人的原因,譬如,谢冰莹的《女兵日记》后来改成《一个女兵的成长》,这里边对问题的解释有很多差异;张爱玲的《十八春》改为《半生缘》后,结局也作了改动,主人公由到美国去改为到了东北的工厂里;还有无名氏,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一节写到他,他给我写信表示感谢,同时说我用的版本是旧版本,不是他修改后的版本。我回信说就是用旧版本。这就是版本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作家思想表述和当时其他材料印证的问题。我的研究生所写的硕士论文曾经写过鲁迅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写在很高的意义上人的审判这么一种现实主义,但有的专家对此提出质疑。如果我们看在《新青年》上1918年周作人翻译的一篇文章就比较清楚了。周作人在这篇译文中讲狄更斯是比较老式的先生,陀斯妥耶夫斯基更带有现代的味道,周氏兄弟可能有共识。这里就有鲁迅前后期思想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个问题是文本真伪和对其风格的鉴赏。譬如,我过去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彭家煌和彭芳草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根据我的阅读和体验,觉得他们是两个人。如果是一个人,那么作品风格的差异和内在精神的差异很难融合在一起。但香港的一位作家就把他们混在一起了,这个问题我后来请教过唐韬先生,他说他认识彭芳草,他们是两个人。像这样一些问题,文本的真伪就必须通过我们的阅读体验来鉴别。
第四个问题是文本的搜集阅读和文本之外的调查问题。因为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很独特,它是隔代修史,时间不远不近,很多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家属还在,我们可以通过访谈、通信以及档案解密来发现一些新的材料。譬如,萧乾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张秀亚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自己对萧乾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朦胧情感,我把这个事情在通信中跟萧乾说了,萧乾说不是他。后来我读到原件,原来他当时在编副刊时,曾经跟张秀亚通信一百多封,但后来这些通信没有找到。不过,对作家本人的表述也不能完全信服,譬如,我曾让一个作家给我写他在沦陷时期的简历,他在简历中说他一直在北京教书。但我看过他作品的前言、后记,发现他曾到安徽去当过警察,这在前言中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对于政治敏感问题的有意回避以及记忆上的误差,使得作家的表述不能完全可信。这是文本内和文本外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印刷文本和作者的手稿、图书馆的藏书和作家自留书版本之间的互补互勘问题。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出版之后,很多作家非常重视。譬如,萧乾说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他一节的重视,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后对他平反的重视,好多作家都给我这样的信。到了写此书第二、第三卷之后,我就有了很多方便,有时有些书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书图书馆没有储藏,那么,我就跟作家联系,很多作家就把他自己留下来的本子给我寄来,我读了之后再给他寄去,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一些书是普通的图书馆中找不到的。
第六个问题是文学材料和史学材料的互证问题。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文学研究应该输入一种史学的素质,因为,我们一些文学研究的事实密度是不够的。譬如,我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凌叔华的家世,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她的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当过保定知府。后来我查了《明清进士题名录》,又查了清代的历史及番禺县的县志,搞清了她父亲不是保定知府,而是直隶布政使。
第七个问题是现代材料和古代材料的借用、引申和旁出问题。譬如,我们读了废名讲周作人的一句话:“渐进自然”四个字大概能形容知堂先生,这里一点神秘也没有,他好像拿着一本自然教科书在做参考。那么,这里的“渐进自然”四个字是从哪里来的?来自陶渊明给他的外祖父孟嘉所作的传,在这篇传记里,陶渊明曾写到有人问孟嘉:“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他答曰:“渐进自然。”这个自然就有了名士气。废名在用它时,则实际上注入了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样一种思想。实际上,这种名士做派和田园诗风味之间是有一些内在差异的。
第八个问题是图和文如何互动的问题。跟文字一样,图应该说也是我们现代文学的原始文献。如果我们把图引进我们新文学的解释体系中去,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问题。譬如,《新青年》1916年前后是反孔的,但郑振铎在1927年编《小说月报》的“中国文学号”时,其卷首图采用的则是吴道子画的《孔子行教像》。刊物首页就有孔子行教像,从中可看出郑振铎这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调整。图看似不说话,但实际上在说话,而且包含的信息量是很大的。再譬如梅兰芳,在京派刊物的北京《丽人》画刊上,有他在《宇宙峰》一剧的剧照,我们看到他凤冠霞帔,仪态严整,明丽照人,一派大家闺秀风范;但海派刊物的《中国漫画》,却把梅兰芳的头安在一个摩登女郎身上,穿着比基尼,载歌载舞,好像百乐门舞厅的摩登女郎。两个一比,京派、海派的味道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文学和图之间互动、互证的互文关系也是我们文献研究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刘涛整理)
作者简介: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20)
意义的创化
——关于治学中如何发挥文献效用的体会
鲁枢元
我很遗憾,我从没有受到过文献学的正规训练,甚至也从未接触过文献学的系统理论,但是,既然混迹于所谓研究者、学问人之列,总不能不与文献打交道,对于治学来说,文献的拥有是一个前提,文献的使用是一个关键。当然,对于某一门学科而言,如果能够挖掘、发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文献,那本身就是一种功德无限的学术贡献——比如在湖南的某个古墓中挖掘出楚国的竹简,或在敦煌的某个秘室里发现了唐代的手写经卷——这样的幸事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在文艺学研究中,我曾经涉猎过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诸多学科,在我的治学过程中,倒是曾经对文献的组织和使用付出过一些努力,甚至也曾获得过由于文献的选择、采用而生发出新的意义的快乐,一种近似于发现与创造的激动和兴奋。这里,我不揣浅陋列举数例,以期得到方家的指点教正。
一、援引:沈从文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这大约是最简便的运用文献的方法,但也是我在早期写作时经常采用的方法,那就是为了说明自己提出的一个观点,而引证别人的一些事例和论断。被引证的文献的出处,一般说来都是这一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作家、学者的文字。如果选取的事例和论断十分地精当恰切,那么的确可以使自己的文章顿时生色,名家的一个精彩的事例、一个精湛的判断往往可以胜过自己连篇累牍的陈述,收到事半功倍的特效。比如,1982年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一文,该文在当时的文坛曾经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原因之一就是大量援引了一些著名文学艺术家、文艺理论家的话。比如,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上的《从文自传》里的一段与情绪记忆相关的话:
……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烧碗处土窖被雨淋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出来虽当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刺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中拔刺的微音,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中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将近20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
以及引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275页的一段论述:
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所体验过的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甚至于很愁惨的现实的以及很粗野的自然主义的体验,过些时间,就变成更美丽、更艺术的了。
现在看来,这种使用文献的方法虽然简便而有效,但一定要适可而止,不宜过于频繁地使用。翻一翻我早年写下的一些文章,我发现援引别人的文字显然有些过于冗繁了,如果还不能说我在蓄意偷懒,那起码也是自己文思稚弱、缺乏自信的表现。
二、类比:苏洵与弗洛伊德
比起上述单独援引别人文字的方法,这里所说的类比则又多了一个义项,引证此项文献的目的并不全在这一文献,而是希望将它与另一文献相互对照、相互映衬、相互比附,从而彰显出崭新的意义来。这新的意义甚至是两种文献各自并不具备的,是它们双向互动、自然撞击的结果,已经含有创生、创化的意味。比如,我在课堂上讲解精神分析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时,突然发现我国宋代诗人兼文论家苏洵在其《诗论》一文中论述的观点竟与这位奥地利当代心理学家S.弗洛伊德的核心学说十分相似: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胜;而愤憾怨怒,有不顾其死,于是礼之权又穷。礼之法曰:好色不可为也;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不可以有怨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岂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无私,和易而优柔,以从事于此,则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殴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
……
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责人太详。好色之不绝,而怨之不禁,责彼将反不至于乱。故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礼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诗曰:好色而无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严以待天下之贤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观《国风》婉娈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伤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1](P113)
在苏洵看来,“忿怨”之心与“好色”之心几乎是人的本能嗜欲,禁之不得,而又与礼法不容。如果强力以礼法禁锢,则“好色之心,殴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由于“责人太详”,反而会造成“水潦大至”,致使礼、法崩溃,酿成大乱。如何才能缓解人性与社会之间、“嗜欲”与“礼法”之间这种严重的冲突呢?苏洵认为文学是一个理想的缓冲地段。
在把文学艺术当做进行社会心理调节的手段这一点上,中国宋代文学家苏洵的设想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苏洵在其《诗论》中讲道:人的原初的“嗜欲”有两种,一是“好色”,一是“作乱”,这就颇有些弗洛伊德将人性的原始冲动规定为“性欲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味道了。进而,苏洵又指出,“好色”和“作乱”是“法”是“礼法”所不能见容的,“礼”和“法”则相当于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超我”。然而要“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却又是做不到的,如果勉强这样做,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凭借社会性的强权和暴力来压抑、禁锢、打击人的这些本能性冲动,那么必然造成“好色之心,殴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的结果,从而酿成礼、法崩溃的社会动荡,这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显然是很不利的。怎么办才好呢?苏洵提出以“诗”,即以文学艺术作为调节人性与社会冲突的机制和达成社会心理平衡的手段。他因此提出了“严于礼,而通于诗”、“好色而无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的儒家“诗教观”。苏洵的主张,无非是千年后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以“宣泄”、“转移”、“升华”、“替代性满足”等方式来缓解人的内心压抑、调节人心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并以此维护个人心理健康、维护社会安定谐调的理论。弗洛伊德是从对于精神病人的治疗实践中得出这一理论的,中国的儒学大师们则是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祖宗遗训中领悟出这个道理的。在两相比较之中,苏洵的诗论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显得更丰富了。
以我的经验,此种类比型的文献运用,两种文献出处之间的差异愈大,效果就可能愈好。比如,在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与欧洲现代量子物理学家波尔之间、英国当代数学家怀特海与中国汉代儒家董仲舒之间的类比,其学理上的张力就会更强劲一些。就像物种的远缘杂交,其生出的后代将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一样。当然,前提一定是这些文献本身就蕴涵有一定的可比拟性,生拉硬凑是无济于事的。
三、融通:王夫之与萨洛特、索绪尔、阿瑞提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撰写《超越语言》一书时,“语言下边”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我不想追随当时正在中国风行的结构主义的理论,说“语言下边”是一种先验的结构、模式,我仍然希望从我较熟悉的心理学领域对个体的言语活动做出深层的探索。于是,我想到W.詹姆斯和S.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在理智清明的意识阈下面存在着一个混沌的、幽微的、涌动的、充满张力的隐秘王国,一种难以言表的心理状态。这种悄然无声的心理状态应当就是日常语言发生的渊源。海德格尔把它称做“寂静的钟声”,接近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法国作家萨洛特依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并以女性特具的敏感对这一心理状态做出了生动的描述:
那是一团数不尽的感觉、形象、感情、回忆、冲动、任何内心语言也表达不了的潜伏的小动作,它们拥挤在意识的门口组成了一个个密集的群体,突然冒出来,又立即解体,以另一种方式组合起来,以另一种形式再度出现,而同时,词语的不间断的河流继续在我们身上流动,仿佛纸带从电传打字机的开口处哗哗地出来一样。[2](P330)
对照女作家的话,我又想起索绪尔写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段文字:
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无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是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线。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3](P157)
这位瑞士现代语言学家关于“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好像是一团星云”的说法,又使我联想起以往我很钟爱的一个汉语词汇,那就是“絪缊”。
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絪缊”又常常被写作“氤氲”、“烟煴”,就汉字构成而言,从“气”、从“火”、从“糸”,被中国古代哲学家用来描述宇宙万物初始发生时的状态,古本《易·系辞下》中写作“壹”。对此,清代哲学家王夫之有着详尽的解释:“絪缊”是一种“阴阳未分,二气合一”的浑沌状态;是一种“非目力所及,不可得而见之”的潜隐状态;是一种“不可以迹求,不可以情辨,不可以用分,不可以名状”的非语言、非概念、非逻辑状态;是一种“生生不息”、“迭相摩荡”内在运动状态。同时,它又像一颗种子一样,虽然尚不具备完整的叶芽、枝茎、花萼、果实,但它已经包含了孕育这一切的无限生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一个“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过程。“动于中”是作为创作前提的心理动因、心理契机;“形于外”不过是具体表达的操作过程。这种作为创作前提的心理状态,也就是“絪缊”。
后来,我在阅读美国当代文艺心理学家S.阿瑞提的《创造的秘密》一书时,发现他特别强调作家的“内觉”(endocept)在创作活动中的作用。他说:
内觉是对过去的事物与运动所产生的经验、知觉、记忆和意象的一种原始的组织……有时候内觉似乎完全不能被意识到,有时候一个人会把内觉当成是感受到了一种气氛、一种意象、一种不可分解或不能用语词表达的“整体”体验——一种相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无边无际的感受”。[4](P69)
阿瑞提的“内觉”,不也就是王夫之的“絪缊”、索绪尔的“一团星云”、萨洛特的“一段意识的湍流”吗?相对于以往大学课堂上的语言学,这无疑是现象学哲学意义上的一个异域。这一异域,通过中西、古今文献的沟通,通过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文艺学之间的融会而渐渐彰显出来。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论的探讨以及“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而言,这一异域的发现使我心旌摇曳、兴奋异常。这种出处迥异的文献之间的融会,犹如一个“优质格式塔”系统,所谓“创造性的发现”,也就是由这一系统“涌现”的一些特性。比起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来,我的这些尝试只能说是零敲碎打,但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毕竟尝到了治学过程中将各方文献融会贯通的甜头。
四、整合:汉字“风”的语义场与生态系统论
治学过程中对于文献的采用,有时也不必一定是那些稀有的、罕见的珍贵资料,有时只要能够改变一下既定的观念、转换一下思维的角度、拓展一下研究的视野,尤其是遵照这些新的观念和视野加以拼接、组合,使之纳入一个新的结构体中,那么,即使从一些常见的、普通的文献中,也可以引发新的问题,探索出新的结论来。
在我开展的生态文艺学研究过程中,我就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在翻阅《辞源》、《辞海》时偶尔发现,“风”,在现代汉语中虽是一个常用字,却又是汉语言中一个历史悠久的基本词。同时,它又是一个拥有旺盛“生殖能力”的“根词”,在它的“主根”上繁衍滋生了数以千百计的汉语词汇,稍加审视便可以发现,这一“风”字辐射的语义场,几乎充盈在炎黄子孙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贯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有层面。
(一)自然层面:指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八方之风、四季之风,刮风下雨的风,风调雨顺的风。如:东风、秋风、风霜、风沙等。
人作为自然界的生物,其身体的生理状况同样要受到“风”的影响。《黄帝内经》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内经·金匮真言》)人体中的“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于天气”,人体之气与天地之气的冲突、失调,是造成各种疾病的根本原因,中医谓之“伤风”、“中风”或“风湿”、“风疹”。
(二)社会层面:世风民情的风。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自然界中的风对于国计民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风调雨顺即意味着物阜民丰、安居乐业、盛世太平。于是,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民众心态竟也和“风”联系在了一起,被称做民风、时风、风气、风尚。甚至,一个朝代的国家法度、朝廷纲纪、民众心态、政府吏治也都被涵盖在“风”字头下,如风宪、风纪、风教等。在中国古代,由于“风”与朝廷的休咎、社会的盛衰、家族的成败、人生的否泰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于是“风”还往往被赋予神秘的含义,成了宇宙的主宰诏告人类的神秘信息,便由此造就了一批操“风”为职业的“社会工作者”,生发出一些以“风”为膜拜对象的学问,那就是“风角”与“风水”。前者大盛于汉唐,后者至今仍流布不衰。
(三)审美层面:汉字“风”的语义场还辐射到了文学艺术领域,与音乐舞蹈、诗词歌赋联系在一起。“诗总六艺,风冠其首”,“风”成了一个地区民歌、民谣的代名词,采风就是对一个地区民歌、民谣、民谚、民俗的收集整理。而风骚、风华后来竟成为文学艺术和文学才华的代名词,“风”字便因此衍生出许多艺术的、审美的词汇,如风雅、风致、风趣、风韵、风骨、风格等等。
(四)人格层面:在以张扬个人的独立人格与精神自由为时代特色的魏晋南北朝,以“风”彰显人物性情、品德等人格心理内涵的话语方式,几乎成了一种充塞整个知识界、文化界的审美偏好。风仪、风姿、风情、风操之类的风韵气度,竟成了品评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绝对标准,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风调雨顺的风、世风民风的风、风骚风流的风、感冒伤风的风、高风亮节的风、风水望气的风……归根结底都是那个古老的汉字“风”的衍生物。“风”的语义场实际上已经辐射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农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文艺学、风水学(现代人则谓之“生态建筑学”)的各个领域,将人类主体与其生存环境,将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融会贯通为一个和谐统一、生气充盈的有机整体。
通过对这些常见的、散乱的文献材料的组织、整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围绕着一个“风”字,真实地存在着一个多层面的、运转着的、有机和谐的生态系统。在西方生态学界,“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一概念,则是直到1935年才由一位英国植物学家A.G.Tansley(1871—1955)提出来的。至于把“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推广到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研究领域,更是近期以来的事。对于陷入重重生态危机的现代人来说,汉字“风”的语义场给我们的启示无疑是深刻的。
以上所谈,只是我自己的一孔之见,错谬之处,在所不免。我希望在文献运用方面与更多的学者广泛交流意见。
作者简介:鲁枢元,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江苏 苏州 215021)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献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小说史论文; 读书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