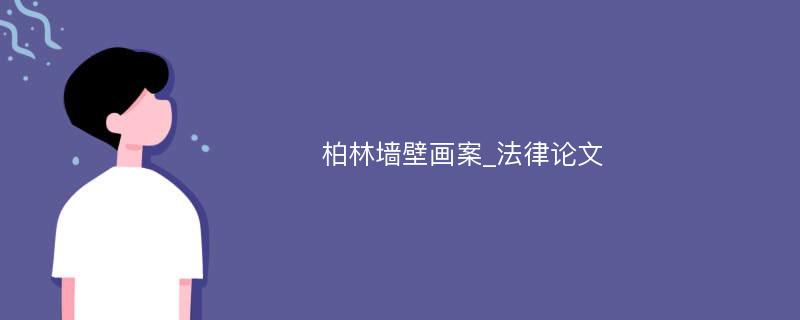
柏林墙 壁画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壁画论文,柏林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画过的墙体卖出后,作画的艺术家有权适当地分享部分价金,因为该出售行为触及了艺术家根据著作权法第17条第1款所享有的发行权。
原告是画家,被告经营柏林墙体的购销及中介业务。双方争议在于,销售带有原告绘画的柏林墙体片段是否侵害了原告的权利。
两原告从1985年到1988年在瓦尔德马街的柏林墙上进行了大面积的绘制,其中第一原告画了主体部分,而第二原告画了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内容。此后,原告又对画面受损部分进行了修复。
1989年年底,柏林城内的边界被冲垮,柏林墙被撤除,原告绘制过的水泥墙面也被切割、撤离。被告将它们运到了蒙特卡洛,并作为举办人之一参加了1990年6月21日至23日的拍卖会。为此被告还专门出版了《柏林墙》画册,从其中的图片上能看到原告的署名标记。
原告认为其著作权和所有权受到侵害,于是诉请被告报告情况并提供帐目。
原告指称,被告通过和当时民主德国的一家外贸企业(即VEBL)合作,承接了销售墙体的业务。拍卖所获价金为180万马克,他们(即原告)应该适当分享其中一部分。
被告表示反对,其理由是,原告并未曾拥有墙体的所有权。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要求也不成立,因为被告对墙体的切割亦不负任何责任。被告并进一步指出,以不当得利为由的请求权同样不成立。因为涉及的是强加的艺术,故不能给原告带来任何权利,即便可能有,其发行权也已经耗尽。
州法院认可了不当得利请求权,先期作出部分判决,责令被告报告情况。
二审法院驳回了原告请求报告之诉(高等法院,《工业产权与著作权》1994年卷,第212页)。
原告的第三审请求获本庭支持,州法院的判决恢复效力。
理由
一、二审法院否定了基于《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第1句中第2种情形和基于过去的民主德国《民法典》第356条所产生的请求权,指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画制作在柏林墙上使得原告的发行权依著作权法第17条第2款耗尽了。虽然耗尽以通过出让方式进行交易为前提条件,“出让”一词应从广义来理解,它包括那些以放弃对其著作物所有权为目的的其他法律行为,特别是交换、赠与、公之于社会。本案中的壁画制作过程即等同于此类弃权的法律行为。这些图画依其性质,如同任何其他墙上的涂鸦一样,不存在通过交易导致继受取得的问题。在公共场合制作本身正是作者所预期的“放弃”。在公共场所发表就是其目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作者的“报酬”。
这种理解和实际情况相吻合。在绘制壁画的时候,原告并没有也不可能指望到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以除了公开展示和(相对而言无足轻重的)销售一些明信片以外的方式使用它。原告在东柏林一边绘制于固定墙体上的图画随时可能被东柏林的边防士兵用白灰涂盖掉。
二、三审请求成立
1.二审法院在其判决中适用了联邦德国的现行著作权法,对此三审诉状和答辩状都没有提出异议。这是成立的。二审法院确认的事实,即原告绘制过的数米墙面固定在东柏林一边,争议的出售行为发生在两德统一之前,并不排斥联邦德国著作权法的适用。根据《统一协定》附件一(第三章E部,第二节第二点第1条第1款),著作权法的规定适用于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之前创作的作品,但是不适用于本案中的过去发生的侵权。然而,这里更涉及著作权法第120条第1款:德国公民对其所有的作品享有著作权保护,而不论它是在哪里创作和发表的。由于案中未作出相反的认定,且当事人证言亦无其他解释的可能,故可以肯定,二审法院的考虑显然是,居住在柏林的原告拥有德国国籍。在本庭听审过程中,第一原告承认这对他成立;而第二原告却是法国公民。对此尚有原告提交的一份出版物可以印证。但这并不能排斥著作权法第120条第1款的适用,因为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6条第1款,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国民应获得同德国国民一样的待遇(参阅欧洲法院Collins/Imtrat案判例,载《工业产权和著作权》1994卷,第280页以下;又见联邦最高法院1994年4月21日Rolling Stones案判例(I ZR 31/92),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125卷,第382页以下),此外,在争议的销售行为发生时,被告已经居住在西柏林。何况根据伯尔尼公约(巴黎文本)第5条第1款也应对第二原告适用国民待遇原则。
2.二审法院还确认,原告的壁画属于著作权法第2条第1款第4项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应受保护,这是正确的,且无需更多论证。从案卷收录的图片来看,这种涂鸦式的艺术表现出了个人创造性。同时,卷宗所收录明信片和广告册证明它们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可,还成为了大型拍卖活动的客体。
虽然本案涉及到一种可能导致民事、刑事制裁的所有权侵害行为(《民法典》第82条、《刑法典》第305条),但是作品创作行为本身违法原则上并不影响对随着创作而产生的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参阅冯·卡姆:《著作权法评论》第2条第17段)。
3.与二审法院的看法不一样,原告对争议的壁画享有著作权法第15条第1款第2项、第17条第1款规定的发行权。
(1)尽管原告将画绘制在他人、即当时民主德国享有所有权的墙上,他们仍能主张著作权法上的发行权。因为对于作品原件的著作权和所有权是彼此独立各自并行存在的;对于载有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标的,所有权之行使以不损害该著作权为条件(《民法典》第903条),故一般而言所有权人物之支配应止于对著作权构成侵害之处(参阅《帝国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79卷,第379、400页,Fresko-Malerei案;又见《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33卷,第1、15页,Schallplatten-Kuenstlerlizenz案;第62卷,第331、333页,Schulerweiterung案)作品原件所有权人对作者人格权和依著作权法第15条以下规定的著作权使用行为的侵害都应制止(参阅冯·卡姆,前引书,第14条第5段)。
然而,在本案中作品创作行为是可能受到民、刑事制裁的所有权侵害行为,故上述原则应受到限制。在涉及这种强加的艺术的时候,艺术自由(《基本法》第5条,第3款)应该受到《基本法》第14条有关所有权保障规定的限制。原则上,不应该要求所有人容忍这种侵害其所有权的行为,不能剥夺其依法防卫的权利。当然,他有权决定是否将一件违反其意愿而强加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艺术品销毁。上述利益权衡在个案中是否会有例外的结论(萨克持肯定态度,见《工业产权和著作权》1983年卷,第56、60页;也参阅施密德尔,《新法学周刊》1982年,第628、630页)并不重要。因为本案中壁画虽然被切割,却没有被摧毁。即使承认所有权人都权销毁作品,但并不等于说,他一律可以为经济目的而利用该作品。因为所有权妨碍的发生只使其有权排除妨碍,并不赋予其独立地为经济使用的权利。即便是那些从作者那里购买到作品原件的所有权人,在缺乏明确约定时也不享有著作权法上的用益权(参见著作权法第44条第1款)。就算壁画是所有权人委托制作的,情况也不无不同。因为,根据著作权法所奉行的目的转让说(著作权法第31条第5款),在无明确约定时,著作权人只出让为实现契约目的所必要的权利,而不出让其他权利(也见联邦最高法院1985年2月6日对Happering案之判决,I ZR 179/82《工业产权和著作权》1985年卷,第529、530页)。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否定,所有权人有权再售出那些即使不带有无法分离开来的“强加的”艺术作品仍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用价值的标的。例如被喷有涂鸦艺术的动产或不动产,比方一栋房子或一辆轿车。否则就会形成对私法自治的过分限制,私法自治在本质上受到《基本法》第1、2条的保护。根据它,所有权人得自由处分他的所有物(《民法典》第903条)。在这种情形下,著作权应该受到约束。不过本案不属于这种情形。柏林墙本身因其性质过去无论何时都不可能成为上述意义上的可交易的商品。只是它被切割成片段以后才成为经济上具有独立利用价值的艺术交易标的。在这种情形下不应完全制止作者主张权利,其依据是被司法判决确定为著作权法基本思想的共享原则。该原则以知识产权学说为基础,认为作者有权尽可能适当地分享其作品的经济效益(这方面判例很多,参阅《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92卷,第54、57页,Zeitschriftenauslage in Wartezimmern案;第97卷,第37、43页,Filmmusik案;第116卷,第305、308页,Altenwohnheim Ⅱ案)。
在本案中也不存在弃权的情形,尽管可以放弃(包括通过向公众作出申明)单项的使用权(也见施里克尔:《著作权法评论》,第29条第18段;埃·乌尔默:《著作权和出版权法》,第3版,第84节五,第366页;以及冯·卡姆,前引书,第29条第6段)。二审法院在其他情节中已作出了如下正确的认定,即原告在其创作和无偿向公众提供其壁画时根本没有预期到作经济上使用的可能性,所以,即便他们有默示的弃权意思,也不可能包括到这种使用方式,可见弃权之说难以成立。和大多数违反所有权人意愿的涂鸦艺术不一样,原告并没有匿名,他们的署名在壁画出版物中亦可以辨认出来。此外,对著作权而言,也不存在类似于物权中放弃占有的弃权,不存在“无主的”著作权。
(2)原告所享有的发行权也没有依著作权法第17条第2款耗尽。二审法院相反的结论在法律上存在错误。
根据著作权法第17条第2款,一作品原件经在著作权法有效领域内享有发行权的人认可并以出让方式交易后,允许自由转售。与二审法院的观点不同,壁画的公开陈列不构成此意义上的出让。
不过二审法院的如下出发点是正确的,即“出让”一词不能仅仅狭义地理解成《民法典》第433条以下规定的出售,而应包括对所有权的每一种让渡和放弃。这里无须考虑要因行为(购买、交换、赠与等)的特征(参阅冯·卡姆前引书,第17条第17段;施里克尔、勒文海姆,前引书,第17条第17段;埃·乌尔默,前引书,第47节一、2,第236页。)二审法院认为将艺术作品绘制在他人的土地组成部分上等同于放弃作品的观点和著作权法第17条第2款的含义、目的是不相吻合的。
著作权法第17条第2款关于发行权耗尽的规定体现了法律上的一种一般的思想。其最基本的思路在于,作者通过出让而放弃了他对一件作品的支配权,故以后的第一次再利用都应该是自由的。作者在使用权上的利益一般通过首次发行行为即得到满足,即他可以以支付报酬作为条件。后来对该件作品的使用原则上是自由的(《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92卷,第54页,第56页以下,Zeitschriftenauslage in Wartezimmern案)。确立这种自由的目的在于维护使用者和公共的利益,即让他们获得可以交易的著作物(参阅联邦最高法院1986年3月6日判决I ZR 208/83,载《工业产权与著作权》1986年卷,第736、737页,Schallplattenvermietung案)。如果一著作物经权利人出售或经由他的认可而出让后,他仍有权干预该著作物的再销售,则自由交易将受到过度的限制(参阅《帝国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63卷,第394页,第397页以下,Koenigs Kursbuch案)。
在本案中却并不存在使著作物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的情形。正如三审诉状所称,柏林墙属于民主德国《民法典》第17、18条规定的全民所有财产的组成部分,它原则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连同它上面的图面在当时不可能成为发行行为的标的。二审法院所确认的情形,即原告在制作壁画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预期到会出现本案争议的作品经济利用方式,非但不能导致,恰恰否认了发行权耗尽的结论。因为这正表明,缺乏原告使其艺术作品作为独立的可交易客体的认同。二审法院认为任公众观摩本身已在一定程度上“回报”了发表行为,也不能证明发行权业已耗尽。(首次)公开陈列只使展览权耗尽——在这个意义上二审法院的观点是成立的。这种通过展览以无形的形式公开再现作品(著作权法第15条第2款)和通过发行艺术品,以有形的形式利用作品(著作权法第15条第1款)有所不同。故它不能引起发行权的耗尽(也参阅联邦最高法院1986年5月15日的判例,I ZR 22/84,《工业产权和著作权》1986年卷,第742、743页,Videofilmvorfuehrung案)。
只有在柏林墙被推倒并分割以后,原告的壁画才能成为著作权法第17条意义上的发行行为的标的。而这些已经可以交易了的墙体正是在非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被以出让的方式投入交易的。
4.……
5.依据《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第1句中第2种情形(也参阅著作权法第97条第3款),原告因其著作权法上的发行权受到不法侵害,而获得了对不当得利的请求权。本庭认为——三审过程中对此亦不存在疑问——当时业已在西柏林居住的被告所为之侵害至少部分地发生在国内(要件参阅联邦最高法院1994年6月16日判决,I ZR 24/92,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126卷,第252页以下,Folgerecht bei Auslandsbezug案)(以下略……)
(译自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129卷,第66-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