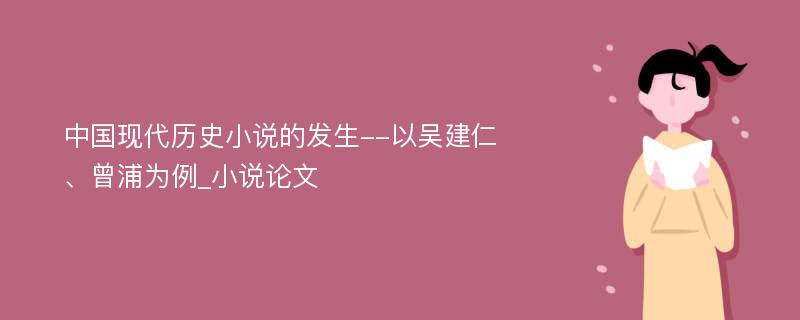
现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发生——以吴趼人、曾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历史小说论文,发生论文,吴趼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339(2008)03-0267-05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发生,不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而是孕育在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中。“小说界革命”是借用欧美“进化”观念及其文学标准重新定义传统中国小说的一场文学革新运动,它促进了“新小说”的诞生,并把小说推至文学结构的中心。作为传统中国小说中最为成熟的一种文体,历史小说受到“新小说”作家的重视,一时呈现勃兴的局面,吴趼人、曾朴、黄小配、林纾等人纷纷写作历史小说,他们使得这一小说形式开始突破传统的约束向现代变革。就贡献而言,吴趼人对历史演义的理论倡导和写作实践,曾朴对全景式历史小说的探索,不仅走在了其他作家的前面,而且为现代中国历史小说开创了最为基本的两种形式,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现代中国历史小说发生的最初过程。
一
历史小说作为类型概念第一次出现,是1902年刊载于《新民丛报》十四号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该文指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实事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釐然矣。故本社同志,宁注精力于演义,以恢奇俶诡之笔,代庄严典重之文”,从而实现“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的目的[1]。历史小说虽然从内容上仍无法摆脱传统演义的窠臼,但作为新的小说类型,从其开始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方面,显然已经开始了对传统历史演义的超越。
从小说与“自治”及“群治”的关系着眼,吴趼人第一个从理论上对历史小说的性质、作用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并大力倡导历史小说的写作。1906年,吴趼人在《月月小说》杂志发表多篇关于历史小说的理论文章,他认为历史小说有两种作用:一是“补助记忆力”,二是在于“易输入知识”,故其“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2]。他把历史小说作为传达并补助民众记忆历史知识的教科书,从而起到替代“正史”的作用。所以吴趼人撰写历史小说的首要目的在于,“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但是,吴趼人在历史小说理论中表现出非传统性的正史观和历史真相观。他并不认同官修的正史,官修的正史因“端绪复杂,艰于记忆”,“文字深邃”等特征,使得非常人所能接受,所以吴趼人认为,“吾将见此册籍之徒存而已也”。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只是一堆古籍而已,不能传达真正的历史精神,因而并非真正的正史。吴趼人的这一历史观颇有现代性意味。贝奈戴托·克罗齐在区分历史与编年史时认为,“编年史是死的历史,……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语文学家天真地相信,他们把历史锁在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室里,……归根结蒂,它们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渊博的或非常渊博的‘编年史’,有时候为了查阅的目的是有用的,但是缺乏滋养及温暖人们的精神与心灵的字句”[3]。克罗齐把这种编年史称作“假历史”。吴趼人把官修的正史看作不为时人所接受的典籍,正好与克罗齐的编年史观念所契合。对于吴趼人而言,历史真相也只能存在于接收者的认知过程中。
为了“发明正史”,吴趼人同样对传统历史演义采取了质疑与批评的态度。因为历史演义自《三国演义》以后,“人见其风行也,遂竞斅为之”。历史演义通俗易懂,易于大众传播,可以激起广大民众汲取历史的兴趣,固然是其文体的长处,但历史演义本身“蹈虚附会”的天性不仅扭曲历史真相,而且使得大众受体反而把演绎附会之虚构故事当成正史来接受,产生以讹传讹的效果,“自此等书出,而愚人益愚矣”。历史演义不仅无法“新民”,于“发明正史”也是歧途异路。这就使得吴趼人批评历史演义这一传统文体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小说,因为历史小说具有“奇、正两端”,可以“寓教育于闲谈,使读者于消闲遣兴之中,仍可获益”。进而他开始了传统历史演义向历史小说转化的工作。首先,吴趼人在历史演义中增加“借古鉴今”现实指涉性。在《两晋演义》中,他以眉批的形式指出历史事件乃“今日之药石”,或者提示古今历史的类似性,从而在历史小说作为“当代史”的现实指涉上引起读者的切身感受及其阅读兴趣。其次,吴趼人特别强调历史小说的“趣味性”,“盖小说家言,兴趣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故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4]。讲究历史小说的趣味,必然涉及作者对小说叙事手法,包括艺术虚构、叙事时间及叙事结构的运用,而这些问题有可能对吴趼人所追求的“历史真相”造成危害。所以他说:“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其叙事处或稍有参差先后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或略加附会,以为点染,亦不得已也。他日当于逐处加以眉批指出之,庶可略借趣味以作阅者,复指出之,使不为所惑也。”[5] 为了历史小说的“趣味”,吴趼人对“附会”、“叙事”、“点染”等艺术手法所表现出的不得已而为之,复又以眉批的形式加以指明的矛盾心态,使之仍徘徊在历史与艺术之间,他在前脚试着跨出传统的关键一步的同时,后脚却仍然顽固地留在了传统之中。
相对于吴趼人对历史演义的现代性改造,曾朴创造出了一种属于全新性质的历史小说形式。在《孽海花》中,曾朴第一次表达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建构一种“全景式历史”的意愿。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到司各特所开创的并为法国19世纪文学广为接受的历史小说形式的影响,而且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的主观性因素。可以说,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作者主观性因素,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产生发生了共同的作用。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是从史诗与小说中发展出来,他通过对环境、景物、风俗习惯的描写,再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人物、事件及其历史氛围,在对往昔历史图景的生动回溯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小说叙述形式。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称:“司各特的历史感不仅使他成了整个一代诗派的先驱,而且使他那些毫无造作的小说对新世纪的全部历史写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6] 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写作手法与风格,启发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对法国社会风俗史的再现,也影响了雨果晚期作品如《悲惨世界》和《九三年》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历史的展现。曾朴对法国文学表现出的持久兴趣,以及他对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深入研究,自然会影响到《孽海花》的写作[7]。研究者曾指出:《孽海花》的世界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世界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的用意是相同的[8]。曾朴把刚刚逝去的时代通过小说艺术以全景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再依据已有的史乘材料,不再对正史进行演义。就其改变过去先有正史,然后演说历史的传统历史演义的写作模式,直接以小说的方式再现历史来说,与欧洲历史小说观念融通,曾朴开创了历史小说写作的现代性新模式。
曾朴用小说再现历史的写作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学主观化进程相联系。普实克把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晚清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词是强调文学创作者的艺术个性和侧重表现艺术家的个人生活”[9]。他认为,这种主观主义是对中国文人抒情文学传统的继承,发展到清代,尤其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强烈,他已经把小说变为可以讨论各种问题,从政治问题直到神学问题,与欧洲小说类似的一个讲坛。这种把小说作为作家表达主观意念和认识现实世界的工具,是中国文学表现出的一种全新的特征。对《孽海花》而言,这种主观性认识主要基于作者的观察与体验。根据曾朴的回忆,小说中人物或为熟识,或为先辈亲友,因此曾朴在描写这些人物时,都能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做自由的联想,表现自己的观点。如他在小说中创造了傅彩云这一“新人”形象。傅彩云以赛金花为原型,不过,曾朴在塑造这一人物时,不仅没有谴责的意味,反而采取一种客观写实的态度展示其行为举止,从人性的角度表现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这样不仅没有使这一人物流于抽象的形式,使小说沦为谴责讽刺的末流,从而颠覆了传统美人“祸水”的类型形象特征,而且还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金雯青的懦弱无能,看到科举制度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没落,看到以科举进阶的这一批达官名士如何在孽海中沉沦,进而指出他们对中华民族生死危亡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通过对傅彩云的塑造,曾朴揭示了晚清历史的基本现实。作家的这种主观性,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中,“开始叙述个人经验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观察或他们本人的私生活中得出的看法,……摆脱了以往官僚作家在经济上和思想上对官僚制度的依赖。因而,在普遍危机时期,他们能够通过个人的认识和解释活动揭示迄今为止被传统观念和法律掩盖的种种社会力量、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10] 它既是对传统观念及其文学体制的一种突破,又体现了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变与传统小说主观化过程之间的纽带关系,历史小说的新观念及其表现手法,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全新事物,而是从后者中生发出来。
作为转折时代的历史小说作家,曾朴在历史小说中表现出的创新常常蕴涵在传统的保守形式中。有论者指出:“傅彩云之所以没有像中国古典小说中其他荡妇那样受到谴责,主要是因为她也是宿命轮回的一部分。”但在新的世界形势面前,曾朴在《孽海花》中尤其表现出一种中西兼容的开放视野:傅彩云的“荡妇”与“新女性”并存的“双面夏娃”形象[11],“小说的场景从苏州、上海和北京一直转到柏林和圣彼得堡;培根和卢梭与中国大诗人李白和苏东坡、隋炀帝与路易十六被相提并论,中国革命者与俄国虚无党人被相提并论;改良主义的公羊哲学与圣西门的社会革命哲学形成对照;才子佳人的浪漫史与俄国虚无主义的情人们的爱国和无私的激情形成对比”[8]170。在《孽海花》的宏阔视野中,可以发现作者着力以写实的现代风格描绘处在激荡变化中晚清全景历史的全新意图。曾朴的保守与激进,不仅使自己成为“中国新旧文学时代”的“一道桥梁”,《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在全景历史的写作中为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并影响到“五四”以后现代历史小说的写作。
二
历史小说就其涵盖的范围来说,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主要是从正面表现历史,历史小说“强调处理在史学上均是信而有征的人、事、活动等”,叙事的焦点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中国“正统”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一类型也称作“历史演义”。一种则是从侧面重构历史,它往往以虚构的人物为线索,重点表现作为背景的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面貌。“历史小说可以指涉所有将时空范围放置于过去某一时代,并描写该时代相应合之举止仪节与道德范围的叙事性小说。这一类型小说主要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过往的气氛,透过模拟,重建、描绘出作者/或其读者心中认为从前可能发生、但不一定真正发生过的实际细节”[11]306-307。这一种类的历史小说以司各特为代表。
这两种历史小说其实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和历史观念。蒲安迪分析,中国强大的史学传统及其强势话语,形成了涵盖历史演义体小说的主观性“真实”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宣称所有的讲述“一切都出于真实”,表现的“或是实事意义上的真实或是人情意义上的真实”[12],这就模糊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相比之下,西方模仿论的哲学观念造就了事实与虚构之间严格的界限,所有模仿,包括讲述的一切都是一种“虚构”意义上的“拟真”性行为。欧洲19世纪历史小说,就其对往昔历史与风俗的表现上只能算是一种“模仿”或“模拟”,它追求的是形成作品拟真性幻象效果。二者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历史观念上——前者是预言/感受性的,后者则是模仿/认识性的,也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保守性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断裂性/现代性之间的差异。
在晚清历史的语境中,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两种历史小说汇聚在同一历史时空,分别被纳入到吴趼人与曾朴这两个具有代表性作家的视野,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土壤里开始新的变革。对于吴趼人来说,传统历史演义向历史小说的转化,是在旧有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小说与文化观念对其进行的现代改造。首先,吴趼人把现代性的线性时间意识纳入到历史演义中。现代性概念的出现,以线性时间意识的萌发为前提,“在一个不需要时间连续型历史概念,并依据神话和重现模式来组织其时间范畴的社会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将是毫无意义的”[13]。相对于回归传统,回到历史的传统历史演义,吴趼人的历史演义体小说把目光聚焦在当下。如前所言,《痛史》、《两晋演义》都是针对晚清被列强宰割的当下现实有感而发的,他在线性进化的时间意识中提出民族国家的现实问题。由此,他打破了传统历史演义中时间的整体性,把古典与现代,传统与当下做了开创性的划分。其次,吴趼人对历史演义“趣味”的强调,表现了现代性的文学意识。他的“趣味”,不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趣味”范畴,此类的“趣”与“味”表现为古典式高雅情调,而是一种具有“时尚”意识与“媚俗”倾向的“大众性趣味”,即对大众文化兴趣的认同。因此,吴趼人的“趣味”说,与晚清社会都市文化的兴起,小说市场拓展形成的小说家的专业化,小说自身商品化的倾向有着必然关系,“小说家的职业化,必然以读者为‘衣食父母’。不再以朝廷的意旨、也不再以当道提倡的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而是以读者大众的阅读口味为‘上帝’”[14]。吴趼人作为职业报人和职业小说家,他对历史演义“趣味性”的改造必然掺杂着现代市场因素。“趣味即时尚”[13]46,吴趼人在其历史演义体小说中对趣味的追求表现了取悦当世的能力,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尽管吴趼人对历史演义的现代性改造充满矛盾和困惑,但他毕竟走出了第一步,在直接面对历史,如何利用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写作历史小说方面,吴趼人做了有益的尝试。
对于《孽海花》,曾朴对全景式历史小说的探索是以传统观念来接纳并改造外来的历史小说形式。以司各特为代表的19世纪欧洲历史小说给予曾朴的影响,更多表现在题材运用与写作方法上,而不是文学思想与历史观念。这就形成一种新形式力图摆脱旧传统束缚的张力局面,现代性就在传统观念与外来形式的折冲龃龉之中展现出来。首先,表现为全景式历史图像的主题与所谓“珠花式”结构之间的冲突。19世纪欧洲历史小说在展现历史风俗画面时,主人公与故事背景融合在整体性的结构之中,即具有情节与人物的统一性。相比之下,《孽海花》的情节线索却分裂为两条:一条为金、傅夫妇的故事,一条为京城众名士的琐闻遗事,前者“波澜有起伏,前后有照应”,后者则显得杂乱无章,牵强附和。胡适批评《孽海花》为《儒林外史》的“产儿”,“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事实勉强牵和而成”[15],胡适的评价虽较苛刻,但也属实,因为《孽海花》毕竟具有“连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倾向。曾朴选取这样的情节结构形式,固然可以拓展小说表现的范围,但这两条情节线之间互不协调的结构局面,揭示了曾朴在外来小说形式与传统情节结构之间依违不决的矛盾心理。其次,小说的革命性进化史观与其预言性叙事框架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孽海花》把对晚清社会颓败局面的描绘与革命党的兴起联系起来,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表达了曾朴革命性的进化史观,即晚清社会的革命必然性。阿英指出:“在这一册书里,不仅昭示了清社崩溃的必然,也是革命必然成功的信号。”[16] 但这种线性发展的现代进化史观,在小说里却被曾朴纳入更为广阔的预言性叙事框架中,不仅金、傅爱情故事一开始就被预言了结局,奴乐岛最终沉入孽海的故事也预言了晚清社会的结局,这样,传统叙事阴阳相克、兴衰交替的循环观念笼罩了整部小说,并与进化的历史观念形成抵牾之势。
曾朴在《孽海花》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历史小说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困境,尽管如此,曾朴就其借鉴欧洲历史小说创造一种中国之未有的历史小说新形式而言,走在了现代文学史的前面。他与吴趼人一起,分别为现代中国历史小说提供了两种可资借鉴与模仿的形式。
收稿日期:2007-09-26.
标签:小说论文; 孽海花论文; 现代性论文; 中国古典小说论文; 吴趼人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