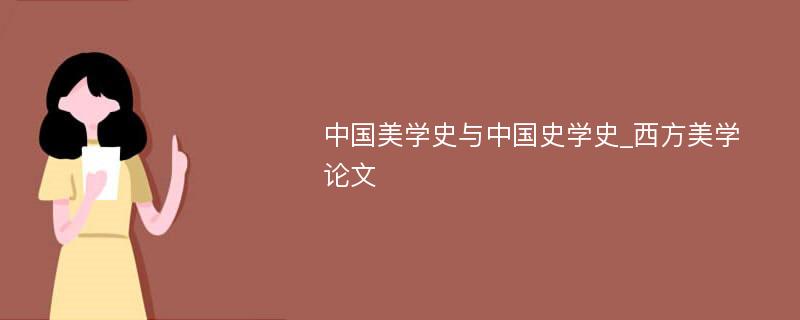
中国美学史与中国史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美学史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2;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06)05—0001—10
如果说对中国美学史与中国思想史所做的是关联—整合研究(拙文《中国美学史与中国思想史》载《南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那么中国美学史与中国史学史之研究则是寻根—建构研究。广义的中国史学史包纳了中国美学史,是其存活仓和生态场。读懂、弄通中国史学史,就能进一步读懂、弄通中国美学史。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为中国美学史所提供的丰饶深厚的资源,揭示其在精神、思维、范畴、价值标准等层面上的转化情形和方式,从而建构成史学—美学范式,便成为一项新的研究命题。
史实之于美学史
传统文史不分、哲美相混,未能形成独立形态、体制的美学和美学史。对它的称谓是近现代人按照西方美学观念从繁博的文化、历史现象中剥离、分割、沏滤出来,进而加以学理化建构所形成起来的。传统思维的经验性特征使其审美理论因子作为潜质深埋在林林总总的资料源中。它们不是像西方那样以显性直接的形式出现,提供现成的理论结果和体系,如黑格尔《美学》,鲍桑葵《美学史》等。这样,研究中国美学比起西方美学来就多了一道工序——“学前”工序——资料的采集、割存、归纳工序。这道工序既需要文献功夫,又需要审美眼力,才能使硕存的中国美学及其史的资料板块真正回归本原。
上述原因,使得中国美学及其史的资源存在,呈现出复杂现象。有论著如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如陆机《文赋》,谈话如《论语》《朱子语类》,序跋如钟嵘《〈诗品〉序》,通信如曹丕《与吴质书》,诗话、词话如欧阳修《六一诗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诗论诗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品鉴如谢赫《古画品录》,评点如金圣叹批《西厢记》《水浒传》等,却缺失了一个存在大项:史著、史论。史著、史论有着为别的形式所无法替代的丰富资源,同时因其存在形式的独特——存在于史学史中,其论述着眼点及其与之俱生的深度、厚度,也较上列的存在形式,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特色。
这方面的资料(指的是正史,尚不包括野史等,如《清朝野史大观》)可谓车载斗量,触手即能拈出一例。凡中国美学史上杰出或成名的各门类美学家,史著均列传。以记人为主体的中国史学以传为构成基石和框架,史传便是人传。对传主加以一生记述时,不仅记述其人生大概、典型事例,而且涉及其审美方面的行为、活动、言论、思想等。就知人论世而言,这些史料是第一手的;就美学家评传而言,所作的评述和定位是权威性或经典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成为某些美学史资料的直接或惟一来源。例如研究六朝美学史、研究谢灵运美学思想的那篇不可或缺的《〈山居赋〉序》,不是存在于别的文献中,而是取之于《宋书·谢灵运传》。该“序”在文体美学和“言意”范畴美学思想上均具有重大意义,成为六朝美学转型的重要标识。“序”文表达了向“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的汉大赋的告别,转而形成“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的小赋。谢灵运提出“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审美理想,审美表达亦与之相应:“废张、左之艳辞”,变为“寻台、皓之深意”;审美对象上,“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成为山水文学审美在六朝勃兴的显示;审美风格上,“顺从性情,敢率所乐”,从主体性情出发,“去饰取素”,回归本色。在“言意”美学上,同时出现于《宋书·谢灵运传》的《山居赋》自注曰:“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耳。”该序亦说:“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这是王弼与欧阳建“言意”哲学之争在美学上的产物,前连陆机《文赋》(“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后接刘勰《文心雕龙》(“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而谢灵运从自身的审美创作实践出发,结合自我经验的审美心得加以阐发,便更为切实。
史料不仅存在于叙述文字中,而且独特地体现在传“序”和传“论”之中,成为观照当时代美学状况、思潮的窗口。所谓六朝文学走向自觉,其标志是美学。对此,不能不了解齐梁时的萧子显,了解萧子显就不能不了解他所撰《南齐书》“文学传”的“序”和“论”。就序而言,一是主张文学审美活动的自然性质,所谓“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这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说的“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养气》所说的“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在精神内涵上具有一致性,非常接近于创作审美所须的心态和学养,给后代特别是宋代苏轼的“文理自然”论以深远影响。二是对传统的“物感型”审美方式所做的诗性化解说和描述。“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在大袑褒衣的正史撰述中,闪现这样一番诗情,令人眼目为之一亮,确实,只有用诗化语言才能解说诗的审美。这与钟嵘《〈诗品〉序》对“物感型”的解说,可谓出于同一机杼,出现史学与诗学在美学星空中的交相辉映。其“文学传论”则有两大贡献。一是确定文学的根本性质:“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其论述依据不是别的,而是审美。这成为六朝时把文学纳入美学,作为其自觉性的最根本说明和体认。由此他认为,审美应是“事出神思,感召万象,变化不穷”。这与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论又是相合的。二是提出文学的审美进化观:“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是中国文学美学史进化论的最响亮口号,求新求变是其内涵,亦是动力。此论回荡千年,时至今日仍保持着新鲜的质地。
另外,史料价值还在于保存了美学论争的生态现场,例如六朝时的声律美学之争。其实际效应是确立了声律在美学中的地位、作用、功能,其深刻影响为后来兴象与声律兼备的盛唐美学作了先声性准备和铺垫。论争的史料存在于《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南史》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南齐书》所录存的《谢灵运传论》、《(陆厥)与沈约书》、《(沈约)与陆厥书》。《梁书》本传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称“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自炫得其声律之诀。但陆厥深持异议,便有前述《与沈约书》,随后则有沈约《与陆厥书》。陆厥认为,声律其实古已有之,只是未能重视罢了,并非“此秘未睹”,由沈约独得。陆厥所言,乃自然性声律;沈约所说,则是人为性声律,即经过规范加工整合的声律。沈约是针对文学审美中的非声律现象而提出问题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就指出:“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祖师。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由沈约提出并经这场论争,便构制了在六朝以至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的“永明体”。这首先亦于史书得以传载。《南齐书·陆厥传》:“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声气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字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梁书·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具体内容也便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载,“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格律诗在声律美学上的形成和发展。
史料对于美学史的提供是全方位的,除文学美学外,绘画、书法、园林、建筑、服饰等诸门类美学均有所载。例如《晋书》、《南史》关于书法美学,新旧《唐书》关于乐舞、服饰美学,《宋史》关于百戏、体育美学,《明史》关于建筑、园林美学,等等,可谓史不绝书。中国美学史之“九层之台”,“起于”史学史之“垒土”。
史撰之于美学史
史著如烟海浩渺,当然覆盖了文学、艺术和美学。这里要说的是史著撰写者的眼光、识见,其富于史学深度和特色的经验概括与理性思考,不仅其本身构合为美学史的蕴涵,而且其史家意识给美学史以深刻启迪意义。现以唐初的八部史著为案例,加以论说。
唐代隋,剪除各路义军后,出现了稳定意义上的统一。艰苦卓绝的战争和马上得天下的艰难使得唐的建国者极其珍惜既得的利益,又极其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接纳诤言。在这样的背景和现实目的催动下,孕育出唐初的“史学热”。唐初蜂然出现八部史书:《晋书》、《南史》、《北史》、《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独得先例、后乏援引。唐初在修史、建史过程中把美学作为“史”的构成内容来看待。撰写者都是一批博古通今的史学家,因此,他们的论析和评价就带有史家意识、观念和视域特征。
其一,宏通深邃的史家眼光。对美学史的发展历程加以描述和评述,《北齐书·〈文苑传〉序》、《隋书·〈文学传〉序》、《隋书·〈经籍志集部〉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等,多有涉及。它们具有这样的特点:宏观扫描,上下数千年纵横贯通,具有强烈的史感。《隋书·〈经籍志集部〉序》描述了自屈宋以来至于齐梁,旁涉北齐、北魏的文体屡变情形。《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则扣合作家和时代审美理想、审美风格,淋漓尽致,洋洋洒洒,可说是中国美学史长卷的缩影图,于描述中有评价,正有史家之风范。这种评述又是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扣合时代风习进行的。《隋书·〈经籍志集部〉序》:“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这已成为对玄风与玄言诗关系论述的经典之论。史著是延续的,在这些论述中延伸了前代之论,例如《隋书·〈文学传〉序》说:“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它便进一步下沿到“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进行评述,形成了史的线索的连贯性。
虽然唐初史家在对历代美学史状况和文学家审美风貌评述时跟六朝美学史家所用的话语有所不同,对涉及的对象所作的评价也不尽相类,但其审美视域和审美思维机制却多有相合之处。他们的审美视域是宏放的,从远古一路评述而来,纵深感、历史感极其强烈,这正是中国美学史之论述特色。他们的描述,包含着审美价值、地位的评价,述中有评。能结合时代风尚、习俗、社会和审美理想,展开评论,使个体审美风貌显现时代特质。评述时特别注重上述时代风习、审美理想的演变和这种演变所带来的审美个体状况变化情形,而评述所运用的语词高度简括凝练。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美学批评史的语境特点,唐初史家正是继承了六朝所形成的美学传统。中国美学理论史对此不可加以缺位性对待。
从隋代以来,在对齐梁文学美学清算时,往往把根源归结于屈原,这一美学思想一直延续到唐初的王勃。其祖王通就曾声色俱厉地进行过这一批判。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写道:“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隋书·〈经籍志集部〉序》则对《楚辞》作出忠实的美学和美学史评述,不含偏见和偏激情绪。对于《楚辞》之成因,尤指出其“言己离别愁思,申抒其心”,触及到抒情美学之本因,独到而深刻。深入其文本,为《楚辞》阐解,概括“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之审美特征,并高度评价其美学史地位:“后之文人,咸不能逮”,不可企及。这便纠偏了王勃等人的观点,使《楚辞》得到了恰当的定位。
其二,把美学作为人文哲学范畴来看待。在中国文化、哲学中人文跟自然相对举。人文观、自然观代表了对于社会、自然的两种不同的阐解及其方式。《晋书·〈文苑传〉序》、《梁书·〈文学传〉序》、《陈书·〈文学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北齐书·〈文苑传〉序》、《隋书·〈经籍志集部〉序》、《隋书·〈文学传〉序》等都无一例外地对人文精神作了论述,继承了《易》学的人文哲学观点。唐初以至整个唐代美学之所以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唐初史家所提供的理论准备不能不说是重要条件。
其三,同时提出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教化功能的提出仍然源于人文精神,而对美学现实效应的重视又具有唐初的理性特征。然而在另一方面,唐初的史家又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隋书·〈文学传〉序》:“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坎坷而未遇,志郁抑而不伸,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这就回归到文学是心灵抒发、郁抑伸展的审美命题上来了。《晋书·〈文苑传〉论》:“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北齐书·〈文苑传〉序》:“文之所起,情发于中。”《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化,形言则条流遂广。”这又是对两晋南朝美学思想的承绪,情为文之根本,为审美之基因。
其四,恰当而有分寸的史学评判。跟隋代李谔、王通一笔撂倒六朝美学的简单粗暴做法不同的是,唐初史家对六朝美学的不同内涵加以区分,对不同时期的美学品格进行界定。例如《隋书·〈经籍志集部〉序》所描述的晋代以降的美学状况,就包含着区别性的评价态度:“爰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这里所进行的阶段性美学史评估,其出发点不是理性和功利,而是美的感性要求和特征。对具体诗人谢灵运、颜延之、谢脁、沈约的评价也持同一审美标准。
唐初史家对南朝美学的评价以梁大同(公元535年~546年)为界,并非对前后代一概而论。对这以前的作家、作品审美评价较高,对此后以萧纲、徐陵等为代表的作家、作品批评较切。《隋书·〈文学传〉序》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其他如《隋书·〈经籍志集部〉序》、《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也是如此。这种阶段性的美学史评价便坚持了美学史现象的具体分析,给予恰当的史的定位。
其五,博融的审美理想。唐初史家经过吸收参化,提出了如下的审美理想:一是和而能壮,丽而能典。《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认为,虽然诗赋与奏议、铭诔与书论之间多有区别,但“撮其指要”,却有共同点,即“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这是对曹丕美学思想的运用。“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其最终要求是:“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二是文质斌斌,尽善尽美。《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这里有着鲜明的文化地理学色彩,时至今日,仍被论者所广泛引用。三是汇合前代,结合当代。唐初所建立的审美标准既不同于南朝的轻靡,但又吸收了南朝美学重感性的因子;既不同于隋代的质木,但又吸收了隋代美学重理性的因子。可以说是熔铸前代之所长,避其所短,并结合唐初的社会思潮、审美理想的需要所建立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并进而奠定了唐人对待美学遗产的态度——宽厚、大度。这是唐人的宝贵之处,也是其伟大之处,同时也是唐人能成就中国美学更大辉煌之原因所在。四是融化南北,铸造新机。南北美学因各种文化条件而产生差异,出现格调、风貌的不同,但南北美学的交流、融合又是必然趋势,而它最终是由南地迁至北方之精英文人所完成。南方美学的精细、雅致、文采融合了北方的朴野、刚健、质实,可以看出南方美学的张力和渗透力。南北美学之融合又须以国土、政局的统一为前提,隋代美学在这一形势下初步得以实现,而唐初史家又在新的背景下提出进一步要求,并且进一步得以实现。
史撰不是史料的罗织、记忆的遗存,追思逝去的历史背景,它应有史撰者的视域识见,即史学的通行语:史识。灌注着对史相的评价、判断,强化叙述立场,在现场与历程,即共时态与历时态的结合中,表明和体现撰写者的理念和姿态。这是史撰中的思想光链,给中国美学史的撰写以深刻启迪。
史论之于美学史
中国史学史之双翼为史著和史论。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是第一部史论著作。此著上下篇二十卷,对前代史著作了评述,就如何撰史,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见解。《自叙》陈说借鉴刘勰《文心雕龙》而著《史通》,虽然一者论文,一者论史,但也从中看出文史互构的性质和特点。清人黄叔琳《〈史通训诂〉补序》认为,《史通》“允与刘彦和(按:刘勰)之《雕龙》相匹”。
《史通》顾名思义是言“史”,又何以关乎“文”呢?刘知幾在《自叙》中表述道:“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呵,人相掎摭,故《文心雕龙》生焉。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以史为主,兼及于文,或者说是以史家眼光看文,这是《史通》的一个重要视点。
史著有其特定的叙述行为方式,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说:“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其具体要求是:“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体现了中和、折中、平衡的观念。而最能代表这种中和之美的是《左传》。《杂说》云:“《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在刘知幾对《左传》所作的叙事特征评价中又贯串着审美评定。以《左传》为范式,刘知幾的史学叙事观表现出鲜明的色彩和特征。
《史通》对中国美学影响最为直接和最有价值的是小说美学。班固《汉书·艺文志》第一次对小说概念作了这样的界定:“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东汉以降经过魏晋,小说创作取得很大成就,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小说系统,但小说美学理论鲜有发展,对小说概念的界定仍未脱《汉书·艺文志》,直到刘知幾的《史通》才有重大突破。《杂述》篇写道: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刘知幾认为小说“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这对于提高小说的史的地位有着极大的作用。他对小说作了细致分类,不是大而化之,而是细加榷论,这又显示了他对于小说研究的深入。“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对十大类别,刘知幾又进行细致阐解、说明,都有规定的内容和特征。在具体阐释中,刘知幾仍坚持他那“实录”原则,这便使中国小说美学形成了现实性的审美品格。另外,刘知幾坚持了小说的审美品位,要求小说有“雅言”,摒弃“鄙朴”。“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这样,便推进了小说审美的雅化发展,可以说,唐人传奇就是这种小说审美雅化的体现,其美学史贡献十分显著。
作为跟刘知幾《史通》相辉映的中国史论双子星座之一的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其书题,就彰显了将文史打通的学术意图,从而更接近于史学—美学的构建。其内容主要有这样几点。
其一,意象论。章学诚史论中的意象论,最富于美学和美学史论色彩,是其史学—美学的核心,现今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无不奉此论为圭臬。首先,勾连了“象”论与传统诗学“比兴”论的联系,这是一项新的发现,也是章学诚贯通性思维的产物。《易教》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也。”比兴与取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比兴借助于形象,是形象间的内联性结构方式,于是“深于比兴”,就是“深于取象”。他认为:“《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这就触及到审美以“象”即形象为基点的论述层面上,见解十分卓越。其次,在总体确定“象”的基础上对“象”加以分解。他认为:“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动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象”是可形可名的,并且处于变动状态中,人们可以循象而觅道。这就把人的认识包括审美认识建筑在取象的基点上。然后,他分解“象”为“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前者为物象,客体存在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则是通常所说的“意象”。他具体解释道:“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意”有着极大的主体能动性质,寻“象”靠“意”,这就把审美回归到“人心”及其“意”上,是知、情、意的自由性主体活动。这样,也就具备了审美体认论的色彩。他说:“然而心灵用虚,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异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人心营构”就是对客体“象”的主体感应和内化,这样也就说明了审美的思维活动及其表现过程。他以佛教中的“象”为例,指出将其定格为“造作诳诬以惑世”之论的谬误,认为“阎摩变相,皆即人心营构之象”。与之同时,他认为:“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重视“人心”,但不玄虚凌空,“营构之象”最终来自“自然之象”,“意象”便是主客体的融合性产物,这是他审美论的归结点。最后,扩大了“象”的存在空间。传统之论,以《易》论“象”。《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而章学诚认为:“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这就拓展了“象”的外延。
其二,“十弊”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指出十类通病:“剜肉为疮”、“八面求圆”、“削趾适屦”、“私署头衔”、“不达时势”、“同里铭旌”、“画蛇添足”、“优伶演剧”、“井底天文”、“误字邯郸”。虽然就史传而言,虽是言史学之论,但因其基本思想是求实性,因此,于美学原理亦相通。
其三,个体论。章学诚虽讲“通”,但不忽视“偏”。这是他甚为了不起之处。讲“偏”是讲个体性,强调个体的存在。他在《文史通义·所见》中以“燕赵”“吴越”美学为例。“人情珍其所罕”,求异,追寻新鲜的审美欣赏心理趋向,使得“燕艺游吴门而声增十倍,吴伶至燕市而贾重连城。”为求“通”、求“相济”,“燕人自雄其歌,而欲得吴舞以和其节;吴人自媚其舞,而欲得燕歌以壮其观”,就形成美的交融和丰富。但是,走向另一面,“吴人至燕,舍其吴胜而强学燕歌以求合于燕;燕人至吴,舍其燕奇而强学吴舞以求合于吴”,就是“强己所短而非效人所长”,放弃了自己的长处,效法别人的短处,结果泯没和消解了自己的长处。他认为,“但学求同于己而非欲取济于人”是一种错误的美学观。这是他对“和而不同”的传统美学观的新运用和新发挥。求异,“擅其偏”,个体性、特殊性,是美学存在的基点和生命。这一美学思想无疑是杰出的,至今仍保持其光辉。
史论除专门的论著论文外,还有传“序”和传“论”需要提及。它们不仅有前述的提供史实的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史论的存在形式。尤其是“文苑”“文学”等的传“序”和传“论”,跟美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些就是就美学而论说的。一般而言,“序”是对全传所作的提絜,但又不是内容提要,而是作总体揭示和评价,概括性和历史纵深感强。“论”是对传主或作传对象所进行的论说和评判,渗透着史撰者的立场、观念,思想色彩浓,其例难以尽述。“序”、“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高屋建瓴,话语姿态宏远,均属于史论范畴。其史论中的历史感和学理性特别显著。例如《新唐书·〈文艺传〉序》概括了“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的状况,并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依据是文学风尚和美学思潮。对各别作家加以归类,其内在尺度是思想和审美倾向。三百年历史概括得了了分明,简捷而有深度。《宋史·〈文苑传〉序》着眼于社会风气,从中寻绎出宋代美学史的演变轨迹。眼界宽又看得深。从世风看文风,复从文风观世风:“南渡文风,不及东都,岂不足以又见世变欤!”堪为不刊之论。《明史·〈文苑传〉序》放眼有明一代的文学、美学的演化历程。明代美学思潮更迭频繁,表现复杂,但短短一序,却概述无遗。“于斯一变”、“又一变”,立足于变,在动态中考察,既切实际,又抓住美学史之症结。非有通盘之把握,则不能得此精当之结论。
史论是论史,但在论析和阐述中运用于或联结着美学,能为美学提供一般性原理,或能解析美学的众多现象,厘清美学史的发展脉络,揭示美学史的演变规律,这便为史学—美学的构建打开了通道。
史传之于美学史
历史不是古朴实事的原始记载和刻录,而是以人物及其活动为中心的当时描述,因此,在实际上是人物传记。人物传记后来发展成独立散文样式,兼备史、文双重品格。小说叙述行为方式首先来之于史著,跟它最初作为稗官小说存在的渊源相关。中国史著一直规避着对历史现象简单枯燥的记述。在形成历史事实的文字化、书写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基本范式,在一开始就规范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方式。这是史传和小说美学会通的基础。
跟先秦诸子散文并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是以《左传》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左传》虽是一部编年史,但记述的中心是人,如《郑伯克段于鄢》、《重耳出亡》等等,人事并举,事中述人。史实因素虽重,但刻画的传神却具备了文学审美素质。初始形成的审美结构形态,作为经验,对应了民族的传统心理,又奠定了基础,培植了世代相传的经验体。作为一种形态、氛围,它影响了后来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标准型史著,也影响了传记式散文,如清代邵长蘅《阎典史传》、汪琬《江天一传》、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等等,还如水渗透般地影响着魏晋小说、唐人传奇、宋元话本……以至于一些选本,对同一题目的作品,或选入散文,或编进小说。貌似混乱的现象,不是说明了人们文体观念的混乱,而是说明了中国文史相通、史传与小说审美因素相互渗透的特殊现象。
全知视角是历史传记的最大特点,故对传记散文的影响也最大。它表现出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全知特点,这实在是来之于史传为“人”立传的叙述行为。为“人”立传的传记本身就显示出叙述者的姿态:知悉对象的一切,评判传主的是非功过,兼具鸟瞰宏观世界和细察微观细件的多重功能质。在空间方位上,叙述者能够捕捉并显露出传主的身世历程以致逸闻、隐私,因而,在空间视角的处理上表现得绰有馀裕。这样,大致奠定了传记散文叙述视角的基本特征。
小说与历史传记的发展关系,经历了一个过程。譬一比喻,如同嫁接在母枝上,魏晋小说是萌芽,接受母枝的营养要更多一些,唐代传奇就相对少一些,至宋元话本则成为独立分枝。魏晋志人小说,记真人、述逸事,叙述视角以一人为中心,以其事为半径,划出一个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圆形,人随事俱来,亦随事俱讫。逸事多采传闻,名为小说,视作传记亦无不可。唐人传奇开始了小说自觉的审美行为,留存着从史传向小说演化的轨迹。一方面传统的叙述视角模式沉积其中,如《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任氏传》、《霍小玉传》,以“传”名篇;亦以一人为中心,次第展开。另一方面,言之凿凿,记为真人,但所述却是假事,如白行简《李娃传》尾端交代人、事的来龙去脉,令人信之不疑,但其间所述之事,却多有增饰,以扩其波澜。至于以“传”名篇的《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真幻交织,完全突破时空限制,神异莫测,更导向小说,并对后代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宋元话本,这种审美素质更得到加强。罗烨《醉翁谈录》概括了当时说书艺术的特点:“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显然把传统史传“踵事增华”的方式加以发展,并愈来愈接近于小说。至于《三国演义》则把这种发展臻于完善地步。在叙述视角时空处理上,在结构组合方式上都是基于史,而又有所摆脱。突出例证有曹操出场、杨修之死的描述,大大突破了史传的时空顺延性和凝固性,更趋于灵动多变。毛宗岗曾在《读三国志法》中指出,《三国演义》“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触及到小说审美的整体性特点。毛宗岗又说:“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这又触及到小说不同于分段、分国的史著而具备有机性的审美特点。在时间的方位、空间的坐标上,《三国演义》虽是“演义”“三国”,但更具备小说的结构形态。《三国演义》虽史有其人,但其事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实录其事”、“虚资增饰”的史传这两方面特点分别加以延伸,在继承中扬弃,产生出小说所独有的审美素质。延及“金瓶”“红楼”,虽非本于史传,但曹雪芹所明言的“实录其事”,却有着史、文在一般精神上的会通因素,由史传所奠定的传统意识输入到纯文学领域。
说书人或小说家的议论插入,体现了史传渊源。《史记》有“太史公曰”,唐传奇沿用史传体式写小说。例如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篇末之论,“前华州参军李肇”之“赞”。《三国演义》有“史官诗赞”,完全以史官身份发表议论。《聊斋志异》四百八十八篇,其中一百八十一篇篇末有“异史氏曰”。何彤文《〈注聊斋志异〉序》说:“至其每篇后异史曰一段,则直与《太史公列传》神与古会,登其堂而入其室。”赞、论式述评,在史传中表现出撰者的史学观,是对传主的历史功过评价和价值判断。像《史记》一类史传,可谓始于记事而终于议论,全知视角的特点更为显著,总是显示出史撰者的无所不在。小说家对于此,是一般叙述方式、体制上的继承,在运用方法上则有变化——《史记》在篇末,小说或在开头,或在结尾,有的甚或在中间。运用方法的变化,导致多功能性——具备了史传对人物、事件评判的功能;交代了作“传”缘起,例如白行简《李娃传》。一些传记小说特别交代素材来源足可征信,又沉淀着史学家的实录意识。不管小说本身与信史有多大距离,但小说家总要像历史学家一样言之凿凿,明其不诬。从小说本身的结构属性看,大有蛇足之嫌,但从体式联系上看,则明显受到史传影响。有的篇末论赞还表述了作者的小说观,如《任氏传》写道:“必能糅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其论代表了唐传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小说观念。有的篇末论赞则成为作家个人的感慨的发抒,主体的个体性更为强烈,例如《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有着蒲松龄个人“孤愤”之情的存在。另外,它脱离史传,灵活地与小说的审美性质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审美间离效果,亦即入乎其中而出乎其外。由人物、事件的叙述突然跳进小说家的议论抑或说书人的评议,作者与故事之间造成疏离,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这没有截断故事本身的完整机体,而是造成艺术的短暂间歇,使得读者或者听众有片刻的回旋余地,领略其中的审美意蕴,得到审美满足。在疏离之外的另一侧面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共同对故事、人物进行评判。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显然缩短了。中国古典小说家心目中有读者,而读者又有一个稳定的群体,其原因大致在此。
这些现象的形成有其深刻原因。正宗的史书乃史官所为,小说则是稗官所操末业。这种未分化的现象形成小说与史传之间的天然联系。唐传奇中凡是记人的小说均署为“传”名,这与《史记》、《汉书》之“传”又何其相似乃尔。《四库提要》史部传记类按语认为“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可见,“传”以记述人为本位,遂构成史传与小说的同一性,连后来的长篇大著也有命名为“传”的,如《水浒全传》。该小说的“武十回”、“宋十回”,集中一定数目章回展示一个具体人物的遭遇、生活历程,形成了性格的独立生命。人物在被“传”的过程中,性格生机盎然;“传”过后,人物的性格生命也就终结,例如林冲。这是“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的特点亦是弱点,形成“传”体的正负值。罗贯中对人物抑扬的审美评价内核则是其历史观。《儒林外史》不管怎么“外”,终究还是“史”,对“史”的依附是何等地难以摆脱。在小说的假想性判断中总有着“史”的如影随形。这可以看到“史”的模式影响之深。当它形成为一种文化意态后,总是不期然地左右着小说家的审美行为,或故意用“史”“传”装潢门面,以显性的方式来适应这种文化意态。
在审美理论上,宋末的刘辰翁是把史传与小说联结起来的第一人,即把史传视为小说,这在文体美学上是一个重要突破。例如他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就直截了当地说:“是一段小说。”他在具体的史传评点中,其人物、情节的评述着眼点,甚至是话语,都用的小说家言。这就从论述系统上进一步实现了史传与小说的链接。
史学—美学之范式建构
中国史学史与中国美学史之间需要加以整合,整合后建构为史学—美学,犹如哲学—美学、艺术—美学、文学—美学等一样,是一种范式,然而又有自身独特的形态和内涵。它是从下述几方面实现和完成的。
审美发生学。创作作为实践活动和行为方式是如何发生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便是司马迁著名的发愤著史、发愤著书论。司马迁将其说引进文学领域,对《离骚》作了这样的解读:“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始于史学,再植入美学,“发愤抒情”便成为中国美学最具民族色彩的审美发生论。以后在史学上,唐代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作了相近的阐发:“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在美学上,钟嵘、白居易、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刘克庄一直到清代黄宗羲、王夫之、贺贻孙、蒲松龄、陈廷焯等人,都一脉相承了这一思想,并演化为“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孤愤寄托”等审美命题。金圣叹批点《水浒传》第六回以直截了当的话语说:“发愤作书之故。”第十八回又批点道:“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这些都正确地说明了审美是主体心态、情绪释放的本体性审美发生论。
史学—美学精神。中国史学精神作为深切的精神文化体验孕育了中国美学精神之硬核。如宋代史学所赞颂和辉扬的淑世精神。《宋史·〈忠义传〉序》:“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况其他哉!艺祖(按:宋太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这种精神滋养了美学,宋人士风特别富于名节气,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重士气、名节,才会出现陆游、辛弃疾、郑思肖等爱国志士,以诗、词、画等审美形式畅达其精神。其审美内核有史学精神、凛然节气,遂使审美风骨如铁城铜垣,壁立千仞。于是,冲决原有的审美格局,改变五代以来词风帘翠幕、浅吟低唱的意象,出现天风海雨般的格调;改变词的固有风味,甚至改变文体美学属性,形成呐喊呼叫的抗战文艺、抗战词。在绘画美学领域则将原有的满幅型山水画卷,变为有隐喻意味的残山剩水。
审美原则。史学所述所论,转化和凝定成审美的一般原则,例如园林美学上的“壶中天地”、“须弥芥子”。《后汉书·费长房传》记“壶中天地”,曰:“(费长房)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之俱入壶,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这虽于信史无征,但却奠定了中国园林美学的根本原则。庾信《小园赋》:“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白居易《酬吴七见寄》:“竹药间深院,琴樽开小轩。谁知市南里,转作壶中天。”刘凤浩《个园记》有言:“以其营心构之所得,不出户而壶天自春。”又如“须弥芥子”,也出自史书。《北齐书·樊逊传》:“(樊逊对问释道两教曰):‘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须弥芥子”跟“壶中天地”同样成为中国园林美学的根本原则。明代祁彪佳《寓山注》论之甚详。清代李渔所建园林以“芥子”命名。其《〈芥子园杂联〉序》说:“此余金陵别业也。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其芥子须弥之义。”这里有着中国美学家宇宙观在园林构建中的意识沉淀和体现。
叙事学。中国史学在根本上是叙事学,对中国美学中的叙事类审美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点是形成了叙事规范。首先是“征实”。这是一个具有传统色彩的命题,既“不虚美”,也“不隐恶”,秉笔直书,如实叙述。真实性是对历史学的本体性要求。刘知幾《史通·直书》说:“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真实性是良史所应具备的基本因素。《载文》批评了五种反真实性现象。真实性引入美学,遂成为审美的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引发了明清二代关于历史小说真实性的论争。《三国志通俗演义》最初版本的一序一引,即庸愚子(按:蒋大器)之“序”、修髯子(按:张尚德)之“引”启开了论争之端绪。一派是张尚德、林瀚、甄伟、陈继儒、余象斗、可观道人、蔡元放、许宝善等人。其理论主张是恪守正史,把历史小说视为“正史之补”。一派是蒋大器、袁于令、熊大木、李大年、酉阳野史、金丰等人。其理论主张是在重视历史小说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要有必要的审美加工和虚构。不管两派论述分歧有多大,但是,真实性作为前提,却是共同遵守的。真实性的另一层涵义是接近于对象。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说:“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其次是“尚简”。刘知幾《史通》认为史书的叙事方式应当简洁。《表历》说:“文尚简要,语恶烦芜。”《叙事》说:“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先,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后来的金圣叹批《西厢记》《水浒传》,毛宗岗批《三国演义》都据此作为叙事审美标尺。最后是“用晦”。刘知幾《史通·叙事》对“用晦”作了具体阐解:“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样,便能“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这跟文学—美学中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论如出一辙。这些叙事规范虽主要由刘知幾所提出,但因其有概括性,因而有普适度。审美创作家以此为范式,批评家以此为准绳。例如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言其“说白”“不容再添一字”。洪昇《长生殿·例言》谈到“发予意所涵蕴者实多”。
叙事学的另一点是宏大叙事性。宏大性就是全景全辐全程式地展示历史和现实的场景、事件和故事的来龙去脉,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发展历程等等。它又转化为叙事审美的一种方式,目光四射,节节叙来,交给读者的是完整的情节。事件结局,人物归宿,均无遗漏。其叙事原则和方法究其根源来自史学。具有叙事因素的杜甫《兵车行》、《北征》、《三吏》、《三别》等,就具备了这一特征。白居易《琵琶行》虽限于浔阳江头的场景,却展现了琵琶女从“名属教坊第一部”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命运历程。《长恨歌》就更有完整叙事、人物命运展示和宏大场面。到了典范型、标志性的长篇小说中则得到完备体现。全过程展现、全方位描述、审美主体全视觉观照、立体式叙事,如《三国演义》。戏剧也是如此。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从叙事学作了这样的概括:“有生有扫”、“此来彼往”、“三渐三得”、“二近三纵”、“两不得不然”、“实写空写”。由此可见,史学—美学建构中,叙事学是其存在和体现的重要形式。
以史称名的审美价值评判标准。其一,以“史”作为“诗”的内核和涵值,是为“诗史”,如杜诗。唐代孟棨《本事诗》言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杜甫传》亦言:“世号诗史。”这是中国文学审美的最高荣誉和境界。到了宋末,文天祥《〈集杜诗〉自序》还说道:“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作,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亦言:“天宝诗人诗有史。”“诗史”总是产生在国家、民族之大灾难时期,又如李珏《〈湖山类稿〉跋》称宋末汪元量诗乃“宋亡之诗史也”。其二,史是美学的评价标准和坐标。不妨引录下面的论述。李肇《唐国史补》评《枕中记》、《毛颖传》:“二篇真良史才也。”凌云翰《〈剪灯新话〉序》:“昔陈鸿作《长恨歌》并《东城老父传》,时人称其史才,咸推许之。”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此予即以当《左传》看。”那么,何以把中国小说美学说成“史”呢?除了因为历代把小说视为“稗史”,属于史的门类以及叙事方式一致外,还在于小说和史在教化功能上也是一致的。《〈五虎平西前传〉序》作了解释:“春秋之笔,无非褒善贬恶,而立万世君臣之则。小说传奇,不外悲欢离合,而娱一时观鉴之心,然必以忠臣报国为主,劝善惩恶为先。”文学在思想功能上接近于史。史家有春秋笔法观念,小说家则以史家春秋意识审视社会人生现象。于是在史的层面上,建构出史学—美学。然而,在另一方面,史又需要有文笔、文采。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说:“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须乎采,食之须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史向文靠拢,在这一层面上,又为史学—美学提供了建构基础。综合起来,则如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便是史学—美学。
主体审美要素。刘知幾为史学家所确定的主体素质是:才、学、识。《旧唐书·刘子玄(知幾)传》载,刘知幾在回答礼部尚书郑惟忠关于“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原因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他具体解释道:“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另一方面,“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他主张史才须学、才、识三者兼备。《文史通义·文德》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也。”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极有影响,为史学家们所恪遵,并为之终生努力。《文德》进一步给予确认并展开论述:“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三者相连,然而他更重“识”,乃是基于其史论要求。非常值得提起的是,清代美学家袁枚在诗美学中完全接受了刘知幾这一史学思想,连话语都惊人一致。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先。”其《〈蒋心馀藏园诗〉序》说:“才、学、识三者宜兼。”《〈钱竹初诗〉序》又说:“作史三长,才、学、识……诗则三者宜兼。”史家素质位移为诗家素质。而叶燮就审美主体素质提出:才、胆、识、力。从语源上看,显然来自刘知幾,尽管略有差异。《内篇下》一开始就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他并对四者分别作了具体阐释。才、胆、识、力,是完整的机体,构合为美学家的基本素质,虽在表述上与刘知幾稍有不同,但其内涵相通。承绪史学,导入美学,在主体素质认知上,构合为从话语形式到意义均十分相近的史学—美学。
史学—美学整合、建构得以实现和完成,成为独立定式,根本原因是中国史学与美学以整一性形式出现。于纯美学,则欠分解,是缺点;就史学—美学而言,则提供了可以整合的基础,是优点。优缺点并存并生,遂能互融互渗。知识者在综合联系中可以一并接受,形成交叉、渗透、参和的结构,思维上未加分化的总体观,进而成为其类本能。倘撇开各划畛域的偏颇,就会如章学诚在《论修史籍考要略》所说的那样:“史学文才,混而为一。”《湖北文征序例》又说到从司马迁和杜甫的文史现象中所获得的认识:“史迁发愤,义或近于风人;杜甫怀忠,人又称其诗史。由斯而论,文之与史,为淄为渑。”二而合一。袁枚《〈蒋心馀藏园诗〉序》一言以蔽之:“作诗如作史也。”儒学祖师孔子修《春秋》,亦删《诗》,成为文史合璧之大家。汉有司马迁,撰《史记》,亦有卓绝的审美见解。南朝范晔、沈约、萧子显,宋代欧阳修、司马光(他就有《温公续诗话》),直至近现代的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均是楷范。而能够整合史学与美学,一是要有贯通意识,如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所说:“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所谓“通”就是贯通、打通,是整合的一种形式。《文史通义·横通》说:“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通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二是要有相应的方法论。方法论是彼此化生的融合剂。例如文史互证的方法。今人文史大家陈寅恪开创此法,《元白诗笺证稿》,是传世范例。郭沫若从先秦社会史出发研究青铜文化美学,而从青铜器的审美造型、纹饰、铭文等,又探寻到先秦的历史状况及其发展情形。一部《青铜时代》已成垂世经典。文史通才们就这样在“大通”思维光照下,游刃有余、举重若轻地进行文化知识结构和方法的奇妙转换、整合、升华、凝定,亦即经过学理化的连手和“光合”作用,终于建构起浑融贯通的史学—美学,成为具有泱泱华夏风采、智慧和涵质的范式。
该文见本刊2006年第5期。
收稿日期:2006—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