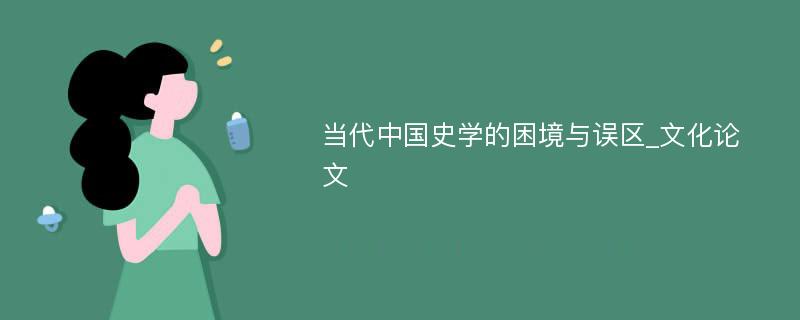
中国当代史学的困境与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困境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当代史学的总体困境:史学主体的分离
所谓史学主体,由两个方面构成:史学研究的主体——史家和史学接受的主体——历史教育的接受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成史学主体的这两个方面,其基本关系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象今天这样,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严重分离,则是前所未有的史学现象。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研究的主体(史家、史官)与历史教育的接受者(官僚、士大夫和即将成为官僚或准备成为官僚的准官僚)是高度统一的。也就是说,史家(史官)要写的,正是历史教育的接受者们所要看的;同样,历史教育的接受者们想看到的,也正是史家们要写的。而对于中国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们来讲,其现实生活的着眼点正是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理想。中国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依托、以王朝代谢为脉络、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格局,正是这种史学研究主体与历史教育的接受者高度统一的必然结果。
进入近代,随着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传统的修史制度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史学研究的主体不再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历史研究开始作为一种职业,而被流放到民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历史研究主体与历史教育接受者之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动态关系。一方面,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存在个体,史家开始摆脱其原有的官方性质,而成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另一方面,历史教育的接受者们也因传统仕途的末路而走上了多元化的人生旅途。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历史教育的接受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角色的转变,加之由西方传入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史学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开始逐渐地脱离以政治史为轴心的传统史学影响,不论是在历史的观念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上,都有着突破性的进展。同样,也正是在这一缓慢的但却又是具体的进展过程中,中国史学终于走出了象牙塔,开始与芸芸众生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然而,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的主体都没有象今天这样面临如此深刻的困境:历史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在根本上的严重分离。一方面,历史研究的主体们所从事的职业,永远是在一去不可复返的过去里上下求索;另一方面,生活于现代社会的史学接受主体们却在当代社会的生活节奏中,偏执地固守着此时此地的存在和意义。作为历史遗产的自觉承传者,历史研究的主体们是史学文化的创造者,而他们所创造的这种文化,与文学、艺术等相比,其审美价值是最次要的;可是,对于史学的接受者们来讲,他们则是文化的消费者,故而追求审美价值(即感官的刺激和直觉的满足)却是最主要的。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这种严重分离,使得史学家们(或史学工作者)在总体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史学家们作了各式各样的积极回应:从史学观念的整体检讨,到史学方法论的探索;从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开掘,到对西方近代史学精神的引进。一句话,一切该做的,我们都做了。然而,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无论史学家们为自己的回应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这一切都无补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必须的学术性与史学研究成果的产品化(著作、论文)所必须的普及性和大众性之间,很难达到某种程度的契合或统一。
造成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这种严重背离,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原因。从社会方面来看,随着经济体制变革中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公众的精神生活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之中。由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以往的政治挂帅和与此相关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退居其次。于是,一向被视作与经国大计密切相关的史学,终于撕开其神圣的面纱,成为一门平凡性和常规性的学术。为政者不再把史学当作一门关乎社稷的“显学”而予以特别的重视;普通大众也不再把史学视作人生龟镜而对它特别亲睐。中国史学在经历了几千年的独尊局面之后,终于还原了其原本的角色:史学就是史学,它最多只不过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常规构成部分。
然而,史学家毕竟是史学的从业者。面对史学现实功用的一般化和史学社会价值的平凡化,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因这种一般化和平凡化而产生的生存困惑时时萦绕于他们的内心。特别是当他们十分渴望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时,却面对着一个叫他们难以接受的现实:文化消费者在总体上的冷漠和拒绝。在当代社会,由于现实生活的斑驳陆离和瞬息万变,造成了今天和昨天的断然分离;以加速度变革的生活节奏,使人们越来越远离其传统的家园。这一切无不从根本上消解着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而且,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现实的个体不仅是生产的主体,而且还是消费的主体。作为主体的普通消费者,不仅消费着物质产品,而且还消费着精神产品。但是,与传统计划经济背景下截然不同的是,精神文化的消费者已不再是传统的被灌输的对象,而变成为有自主性和选择性的“上帝”。今天,普通的消费者对精神产品的消费,是以感性消解理性、多元性消解统一性、世俗性消解理想性、平面性消解纵深性为出发点的。故而,以理性为基础、以人类发展的统一性为信念、以中外古今的历史纵深性为支撑点的史学文化,在总体上与当代消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当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总体困境,一方面是现实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但另一方面也是史学这门学科在自身的发展中所注定的结果。
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分离,其实质是历史传统和当代生活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而中国当代史学也正是在这一基本走向之中得以具体展开的。
传统与当代的分离,在总体上表现为历史遗产与现实生存的分离。面对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人们已不再从过往的来程中来考虑现实的一事一物,因为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与此时此地的当代生活事象,几乎已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关联了。于是,在社会已经转型、而尚未成型的当代,人们已经迫不急待地挣脱了历史的传统,并力图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中以求得个体的独立。当代生活对历史传统的排斥和拒绝,必然导致个体生存根基的全部丧失。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其生存的价值及其终极归宿,在总体上都根基于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必然就意味着个体的被逐出于家园,相应地他就必然成为上无牵挂、下无根基的孤独的宇宙漂泊者。而且,由于生存根基的丧失,必然导致价值中心的丧失,而无价值中心则又在总体上意味着生存意义的丧失——个体存在的无意义。因此,当代生活与传统的分离,表面上只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离,或文化发展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分离,但是究其实际,则是由历史意识危机而引发的生存危机。
由历史意识危机促成的生存危机,是当代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而摆脱这种危机的最直接努力就是文化寻根,并由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热”。中国当代史学的具体展开,正是建立在这一文化寻根的过程之中,而其总体困境和误区也正由此而引发。
二、史学的严重过剩:分离的必然结果
如同经济危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一样,中国当代史学的危机,其主要的表现不在于史学著作的出版难、史学家队伍生活状况的不理想,而在于史学的严重过剩。如果说经济危机是由于广大消费者生活的贫困化,于是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的堆积、腐烂、甚至倾于大海,另一方面则是芸芸众生的饥寒交迫;那么,中国当代史学的危机,则是基于史学接受对象精神生活的贫困化。正象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当代,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一种是以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学者为主体所倡导的所谓“精英文化”,旨在通过对民族文化根基的追寻和民族历史精神的叩问,以求得历史传统和当代生活的统一;另一种是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所谓“大众文化”,其总体精神是通过对此时此地生存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执着,而拒绝昨天的一切。尽管前者力图通过感召、教化等手段,来引导和规范后者;但是,后者却在有意无意之中,或者表现得不屑一顾,或者干脆把前者变成调侃、消解的对象。这两种文化模式的分离,从史学的角度来讲,正是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分离的结果,也是历史传统与现代生活分离的必然。而两者分离的原因,与其说是历史学对当代社会生活介入的无能,还不如说是当代生活状态下消费大众精神生活贫困化的使然。
所谓史学的过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学人才的过剩。在中国,靠历史吃饭的人实在太多了。原本就十分拥挤的历史工作者队伍,每年还要靠接纳数以万计的历史专业本、专科生、硕士和博士。而且,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是以培养未来的历史学家为主要目的,加之史学作为传统学科在当代社会中所处实际地位不高,故而这些研究生毕业之后,大都从事与历史研究有关的工作,很少改作其它职业。此外,当代社会生活从根本上是以拒绝传统和历史遗产为基本走向的,因此,即使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想跳出本行,转而从事其它职业,也是很难为社会所接纳的。于是,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方面是史学研究这条羊肠小道早已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另一方面又是年复一年的后备大军的涌入。如果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盲目生产,必然会导致商品的滞销,从而出现过剩;那么,在当今的教育和就业体制下,盲目招生的结果,也必然会导致史学人才的过剩。这种恶性循环的现状,不仅在总体上加剧了史学研究队伍生存条件的恶化,而且还把历史学推向了更加深重的危机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讲,史学人才的严重过剩,既是史学危机的结果,又是使这一危机不断深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史学研究成果的大量过剩。近年来,在中国的知识界,时有学术著作出版难的讨论。其实,与学术著作出版难相反相承的另一现象,则是学术成果的大量过剩,这一点却一直未能引起知识界的关注。这两个现象的同时出现,看起来十分矛盾,却又实实在在地互为依托。就史学界来讲,史学著作出版难的问题,是每一个史学研究者都可以深切感受到的;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方面,则是史学研究成果的大量过剩,这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据笔者对某一高校图书馆近年来有关史学著作出借情况的调查,90年代以来出版的数百本比较重要的史学著作中,有2人或2人以上借阅的,占11%,有1人借阅的占百分之24%,剩下的65%则多年来尚无一人借阅过。至于各种期刊中所发表的史学论文,其过剩现象则更为严重。笔者曾对某重点高校历史系一个年级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过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35名学生中,只有6 个学生阅读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有关期刊中的史学论文,9 个学生阅读过一种期刊中的有关史学论文,其余的20名学生一种也未看过。类似的情况,在全国的其它高校中,也普遍存在。高校是学术文化的重镇,而历史系的学生又以学习历史为天职。在高校的图书馆里,在历史系学生的案头上,史学著作和社会科学期刊中的史学论文的出借和阅读情况尚且如此,至于其他社会众生,其情况就更加可以想见了。
史学的严重过剩,使历史学变成了仅仅是史学工作者自己的事业。一方面,在现有的就业体制下,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只能在史学研究的队伍中自行消化;另一方面,史学研究成果也只能在同一领域、或对同一问题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之间传阅。于是,历史研究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而研究成果则越来越过剩。中国当代的史学,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怪圈。
三、冲破怪圈的诸多努力:尝试及其误区
面对这样一个怪圈,史学家们作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基于对过去研究思路的检讨,而对自己研究课题进行重新调整。经过反复的讨论,在以下的问题上几乎达成共识:历史学之所以失去大众,主要原因在于自己事先背离了大众,由于我们的史学研究向来关注的只是政治史,而忽视与普通众生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历史事物,诸如社会史、文化史、民俗史等,从而使研究变成了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故而,在80年代中后期“史学危机”的声浪中,通过对自身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论的重新检讨,再到后来文化史和社会史等一大批史学领域的开拓,我们的历史学似乎已与当代的大众文化达到某种程度的契合或统一。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契合和统一中,当代的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误区。
误区之一:选题的趋同化。作为主宰大众精神生活的通俗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同性。某一题材一旦成为消费热点,同一个类型的选题就会纷至沓来。自从蔡志忠以历史为题材的漫画作品在大陆旺销以后,史学界马上就意识到传统史籍白话化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于是,以白话《资治通鉴》为契机,发展到白话“二十四史”、白话“诸子”、白话佛典、白话姓书、命书、相书……凡是可以白话的,都有被白话的可能。再如,自“文化热”以来,我们的史学界一下子也热得忘乎所以。似乎以前所从事的工作不是文化,于是幡然醒悟,逐潮流而浮沉。反正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史,大到宦官,小到蟋蟀,无一不是文化。如果不够,还有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旁参互证,足以取之不竭。近十年来,史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是从“文化”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对象之中,获得灵感,求得饭碗的;而广大读者也正是在“文化”这片汪洋大海之中,暂时放松因紧张、刺激的现代生活节奏而万分疲惫的身心,并在与古人神交、对话的过程之中,消除时间的界域,从而执着于此时此地的存在,而忘却明日的烦恼。这种选题的趋同化,不仅导致了研究成果的大量重复,而且也有悖于从不同的角度、众多的层面来反思历史的学术初衷。
误区之二:成果的泡沫化。当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大众消费的热点,也因此而瞬息万变。于是,所谓的“文化快餐”应运而生。这种“文化快餐”以短、平、快见长,以满足大众消费时尚为己任。面对如火如荼的“大众快餐”,史学界一部分人终于按纳不住长久积蓄于内心的功利主义和浮躁之气,于是如法炮制,为所谓的“大众快餐”添油加醋,或者煽风点火。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和浮躁之气的驱使下,他们追求的不是板凳能坐十年冷,而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而这个一举成名,又是与成果量的多少、选题的是否“新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一年出版数部著作的不乏其人,一年发表十多篇甚至数十篇论文的更是大有人在。然而,仔细地检阅他们的这些“成果”,除了将前人或他人的有关观点进行为我所用的剪裁、糊粘之外,剩下的则是一堆谁也看不懂的名词或术语。于是,看上去洋洋上万言的论文,或者十余万言甚至数十万言的所谓专著,事实上只是一团空洞的泡沫。
误区之三:成果的庸俗化。与成果的泡沫化相联系的,就是庸俗化。为了在“大众快餐”店铺林立、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求得生存,占得一席之地,如同文学家队伍中有人热衷于“产房、病房、卧房”的所谓“三房”题材一样,我们的史学研究队伍中,对历史上所谓宫闱秘事、后宫乱伦、帝王房中术等大感兴趣者,也不乏其人。几年来,有关这些方面的所谓研究著作,不下数十部。历史上污泥浊水的沉渣泛起,也正是在所谓“文化史”或“社会史”的外衣包装之下,为我们史学研究队伍中的某些人挥舞着如椽大笔给搅拌起来的。
误区之四:史学研究的可操作化。如同电视剧的编制有一个程式可寻,也如同流行音乐的创作有一个固定的程式一样,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将史学研究可操作化的和程式化的倾向,已越来越明显。在他们看来,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用某一种或几种理论来观照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于是,历史研究就变成当代理论与作为过去的历史之间的观照与被观照。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似乎就在于将这两者进行某种联系。正因为如此,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搞文化史的每每着力于文化学的理论,而研究社会史的,则又着重于社会学理论的探讨……自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各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几乎无一遗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实际研究的,至今还没有产生出一部成熟的著作来。究其原因,正在于我们的历史学家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历史研究看作是一项可操作性的、有程序可循的活动。由于我们把历史研究的本质理解为用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来观照过去,由于我们把历史研究的过程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可操作的、有固定程式的活动,从而在根本上忽视了历史研究主体自身的一切(理论修养只是历史学家自身修养的一个部分)。试想,如果历史研究只是用某种理论来观照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如果历史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可操作的、有固定程式可循的过程,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只不过是将二者进行某种联系,那么历史学家的工作岂不成了人人可做的工作,历史研究不成了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事了吗?果真如此,历史学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恐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误区之五:研究对象的被肢解化。所谓研究对象的被肢解化,是指历史研究课题的日益零碎化和繁琐化。自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一事、一物、一人的零星研究,弥漫着整个史学界。诸如某某历史时期人们的饮茶习俗、香料的运用、家庭日用的构成等等,成为史学家们竞相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在对传统的政治史进行反思之后,这种肢解研究对象的趋势日益明显。在不少历史学者的眼中,历史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被分割成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许多独立、相互间没有关系的部分。于是,就象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在许多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论著中,学者们对历史时期的政治保持着闭口不谈或十分超然的态度。正如当代德国社会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泽所说:“没有任何社会形成物是非政治地出现,或在其变动中不受政治影响的。”试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诸如家庭结构、人口迁移、婚丧娶嫁等等,哪一种没有政治因素的渗透,并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传统的历史学科之外,再开拓一些新的学科,通过不同的研究重点、不同的观照视角来考察历史,解析历史的整体运作,这种尝试和努力是可贵的,但是,因此而肢解历史,把原本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历史,人为地分割成许多独立的、相互间毫无关联的各个部分,这不仅不利于加深对历史的理解,而且也有悖于历史研究的初衷。
误区之六:历史本体的多元化。自从关于历史发展“合力论”的讨论开展以来,关于历史本体多元化的观点,影响了很大一批学者,当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趋势,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又在总体上强化了这一观点。于是,在很多历史学者的著述中,历史变成了一堆杂乱无章的各种原因的堆积物,举凡经济、政治、宗教、地理、民俗、心态等一切与历史有关的东西或历史事物,都是历史变革或发展的原因,而且在构成历史发展原因的诸要素之中,相互间的地位是同等的,没有轻重主次,没有原生、次生和再生的关系。从历史是人类各种活动的总和这一复杂的、多层次的包容性来讲,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各种事项或构成人类生活舞台的各种要素,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是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动态作用的必然。但是,历史总体进程中的“合力”,并非意味着构成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都是同等的,也并非意味着在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中,没有任何一种因素是最基本的、贯穿始终的。试想,如果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原因的堆积,在历史的总体进程中没有一个基本的、内在的原因可寻,构成历史的诸要素或与历史有关的所有事物,都是历史发展的原因,而且相互间没有轻重主次,没有原生和派生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发展还有什么规律可言?如果历史的发展没有一个规律,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偶然原因的堆积,那么历史研究在总体上还有什么意义?
为弥合史学研究主体和接受主体严重分离所作出的上述种种努力和尝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误区、甚至失败,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史学的前景作进一步的思考。在史学研究主体和接受主体严重分离的当代,在世俗生活排斥以至根本拒绝历史传统的现实之下,史学家如果仅仅希图通过对与大众现实生活有关的课题的研究,来赢得读者,甚至希望有一天历史读物象流行音乐和肥皂剧一样,成为芸芸众生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东西,那么,不论我们为此作出怎样的努力,到头来要么是以牺牲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所必须的学术性为前提,从而使历史著作变成市井摊头的读物,要么只能是经过诸多的尝试之后而终归于徒劳。
历史学的出路只能从历史学的本身来寻找。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的不可复返性,与作为一种传统的现实延续性,正表明了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一两重构造特点。一方面,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它已外在化于我们的现实存在,因而是可以观照的,对现实的我们来讲,它也是对象性的;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它又延续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成为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又是非对象性的不可观照的。这一两重构造特征,决定了历史学学科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正是历史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依据,也是历史学不会为其它任何一门学科所代替的最本质原因。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决定了它既是观照者,又是被观照者;既有可观照的一面,又有不可彻底观照的另一面。历史学也因此而成为人类既观照自我,而又无法彻底观照的魔镜(否则就会变成生理学或解剖学),成为人类一种独一无二的认知途径。因此,我们的历史学家没有任何理由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途丧失信心,更没有必要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因史学地位的失落而自暴自弃。展望21世纪,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也将形成。那时,以人类全部经验为起点,以对人类的本质、价值、意义和终极问题全面关注和整体统摄为旨归的历史学,将会大有用武之地。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对未来的总体态势没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只执着于眼前的细微得失而斤斤计较,或为取媚时尚而放弃学术真理,或为一事一物而肢解历史,甚至为一己之私而制造假冒伪劣成果。那时,当我们的社会需要历史学作出积极的回应,并在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我们的历史学将因此而措手不及。
标签:文化论文; 历史学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