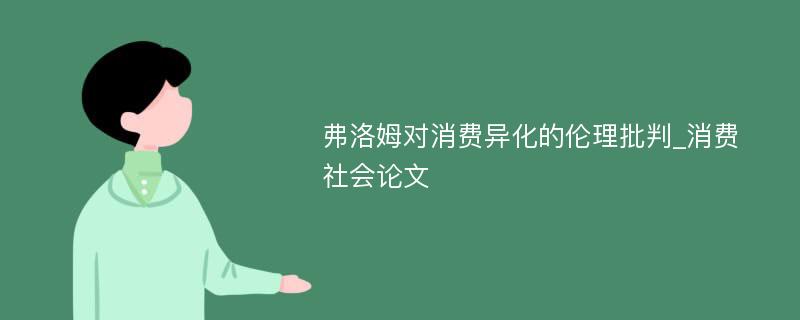
弗洛姆对消费异化的伦理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弗洛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 也是新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始终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基础,致力于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一种人道主义伦理学(humanistic ethics),促成一个健全社会(the sane society), 从而实现人的充分发展,达致人的真正幸福。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只是病态的社会,它使人性极端异化。尤其是在消费领域中异化状况最为严重,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的集合点。他对消费异化的非人道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明确提出人道主义消费原则并大力倡导健康而人道的消费方式。其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实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建构社会主义消费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针对当代西方伦理学相对主义的主导趋势,弗洛姆主张规范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他认为,正确的伦理规范只能由理性构成,人能够依靠理性正确辨别和评价价值判断。但是,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懂得人性。他的规范“人道主义伦理学是建立在理论‘人学’之上的‘生活艺术’的应用科学”[1]。他批判过去在人性问题上否认存在着一般的人性,从而把一切价值判断都归结为个人的趣味问题的主观相对主义观点,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它们是确定道德规范的基础和前提。作为一名伦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生,他坚持理论研究和经验观察相结合,在综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层次的总体人性论。
1.人类具有“自我保存的需求”和“生存的需求”,后者是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弗洛姆指出,根植于人的生理组织的“自我保存的需求”(吃、喝、睡等)是人类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予以满足。然而,“这些本能需要的满足并不使人感到幸福,也不足于使人变得健全……”[2],人类还有“生存的需要”。它们产生于人类特殊的生存处境, 即人类生存固有的矛盾(他称之为“生存的两歧”):生与死、人的潜能实现与生命的短暂以及个人化与孤独感之间的矛盾。人类为了克服这些矛盾,就产生了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根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而每种需要的满足又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如关联的需要可以表现为爱与自恋,超越的需要表现为创造性或破坏性,等等。在这些生存需要中,最主要的是超越和关联的需要。这些生存需要就是弗洛姆找到的人的真正的自我,即人的本性特征,它们构成为人的心理冲动(内驱力),是人性的最重要部分。
2.人性是一种潜能、创造性和理性。弗洛姆认为,人的存在是内在潜力的某种既定的总体性。每个人都“具有人的全部潜能,人类的使命就是去实现这些潜能”[3]。潜能的充分发挥是每个人的生命和全部人类历史的真谛。其次,人性也是一种创造性(生产性)。“生产性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生产性意味着他把自己当作一个他之力量的化身、一个‘行动者’而加以体验;他感到自己与他的力量溶为一体,同时这种力量并没有受到阻碍而与他相异化。”[4] 生产性取向也是自由、美德及幸福的基础。另外, 理性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性是人以思想把握世界的能力,具有双重意义:正是由于理性,人才割断了与自然界的天然联系,产生了所谓的生存的矛盾;而理性又是人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
3.对自由、幸福的欲求是人的天性。弗洛姆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追求自由是个体成长发育的内在需求。自由不是摆脱一切指导原则,而是根据人存在的法则去认识人的潜力、实现人的真正本质。它不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体现于人的历史之中,并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体现出来。一方面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自由是创造的前提;另一方面自由又是人的创造活动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本质(自由)力量对象化,通过劳动和实践来达到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从而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另外,他讨论了幸福的欲求。他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和心理欲望。生理需要是有限的,受生理条件的限制;心理欲望是无止境的,因为它试图克服内心的空虚和无聊、孤独和抑郁,而这些都不是可以通过满足欲望来消除的。在此基础上,他把快乐分为解除生理紧张和解除心理(精神)紧张所带来的感受两种。前者如饮食、男女等生理需要的满足,后者如对名誉的渴望、支配、嫉妒、猜疑、喝酒等心理需要的满足。第一类快乐是真正的满足,是正常的,也是幸福的条件;而第二类快乐最终只是需要的暂时缓减,是“不合理的快乐”,也是本质上不幸福的表现。因为“幸福象征着人找到了存在问题的答案:生产性地实现他的潜能,因此,他既与世界同为一体,但同时却又保持着他自身的人格完整性。”[5]
4.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模式。弗洛姆力图把对普遍的人性研究导向社会性。他指出,人虽有相同的生存处境和共同的心理需要,但他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为满足这些需要所采取的方式却各不相同。方式的不同直接反映了性格结构的区别。性格结构有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的区分。个人性格指一个人的全部行为特性,它们的形成取决于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家庭社会的影响。社会性格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是从共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社会因素,能够造成各种符合该社会经济制度要求的个人行为,从而使个人对社会的行为模式不再有自觉意识,使社会经济制度能够生存下去。他把社会性格分为“非生产性性格”和“生产性性格”。非生产性性格是一种内在潜能未获得完全发展的性格类型,包括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市场型和恋尸型等五种心理定向。生产性性格则是一种创造性,具有生产性性格的人把培育和发展自己的所有潜能作为唯一的目标,使自己所有的其他活动都从属于这一目标,因而“生产性所创造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人自己”[6]。生产性性格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目的,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
二
基于以上观点,弗洛姆提出,如果一个人按照人性的特性和规律去充分发展,他就可以达到精神的健康;如果一个社会以符合人性的、满足真正的个人需要为基准,它就是健全的社会。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不健全的社会,它以病态的人为代价来换取健康经济为基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人性异化”。他认为,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主要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在这种体验中,个人感觉不到自己是活动的主体和行动的创造者,而是其奴仆。虽然异化是人类社会的现象,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几乎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消费领域中,异化情况最为严重。消费原本是满足人们需要和达到幸福的手段,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物质消费,消费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这种消费异化是同人道主义的要求完全不相容的,他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1.消费异化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最终导致了人性(自我)的毁灭。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行为是由道德规范所决定的。然而,到了18世纪,资本主义实现了一场彻底的演变,把经济行为与伦理以及人的价值观念分离开来。经济活动被视为一个完全独立于人的需求及人的意志的自主的整体。经济体系的发展不再受到什么对人类有益这个问题的限制,而是由什么对体系自身的进展有益这个问题所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要求不断地发展生产,因而必须不断地扩大消费。它动用一切宣传机器不择手段地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所有这些手段从根本上说都是不道德的”[7]。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即使富裕的人也会感到贫困”[8]。资本主义使人变成了消费的工具。更严重的是,人们购买消费品,不是为了使用或享受而只是为了占有它们,因为占有可以标明他的社会地位,为他博取名望。这种消费方式使人们对消费永不满足,如饥似渴,从而产生了以商品作为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于天堂的解释“就是一个像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场,里边摆满了许多新产品和新玩意,而且他有充足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9]。然而, 这种无止境的“消费的渴望却已失掉了和人真正需要的联系”[10],只是“人为制造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对这些虚假的需要和欲望的无限制满足导致了人的精神麻木,最后导致了自我的毁灭。因此,他说:如果19世纪的时代表征如尼采所说是上帝死了,那么20世纪的时代表征则是人死了。
2.消费异化生产出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和自由的“被动人格”。弗洛姆认为,现时代,一个幽灵正在我们中间徘徊,然而,只有少数人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幽灵就是:“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它服从计算机的命令,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自身被转变为整个机器的一部分,尽管他吃得好,娱乐得好,然而他却是被动的,缺乏活力和感情的。”[11] 他“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12] 这就是消费异化产生的“被动的人格”。这种人的内心是虚空的,他被购买更多、更好、更新的东西的可能性所迷惑,不由自主地要吃、要买、要拥有和使用更多的东西。只有通过不断地消费,那些空虚、瘫痪和无力的感觉暂时离开,他才会感到自己还是个活人。“被动的人格”不仅体现在他购买消费品时是被动的,而且在闲暇时间里他也是不自由的、异化的消费者。他“消费”球赛、电影、报刊、书籍、演讲、自然景色以及社会的集会活动,就像他用异化和抽象化的方式去消费他买来的商品一样。他分析了消费异化产生被动人格的深刻原因:一方面是匿名权威即利润、经济需要和市场的支配作用。人们在它的支配下,失去了自我意识、主动性、创造性和自由,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力求达到与他人一致。一致性的行为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道德:适应他人就是美德,反之就是罪恶。另一方面是技术宗教的盛行。现代人放弃了偶像崇拜,皈依于“技术的宗教”。这种宗教的主要内容是梦想满足无休止的需要。它使人相信:只要继续行进在技术进步的大道上,就没有不能实现的愿望;满足欲望将指日可待。技术取代了自然的母亲,人们在她的看护下,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永远张开嘴吸吮给予他的一切。它使人们变得懒惰、消极和被动,乐于食来张口、衣来伸手。
3.消费异化造成奢侈浪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建筑在高生产与高消费的基础上,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倾向。浪费倾向不仅导致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它“使消费者不尊重劳动和人创造的成果,使消费者忘记了在他自己的国家和更贫穷的国家中还有许多衣食不济的人,他所浪费的东西对这些人就可能是最珍贵的东西;总之,浪费的习惯表明,我们幼稚地无视人类生活的现实,无视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经济斗争。”[13] 他认为,奢侈就是一种浪费。人类对奢侈或丰富的选择,对好的、坏的富足的选择,直接决定着人类的前途。他赞同马克思等思想家的看法:奢侈和贫穷一样都是巨大的负担,甚至奢侈比贫穷更可怕(奢侈是指多余的富足),这种奢侈最终将导致贫穷与痛苦。
4.消费异化扭曲了人们的幸福观,造成人的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弗洛姆认为,工业社会中的人普遍相信:生产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消费是无止境的,技术可以使人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人无所不知;人的“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饮下音乐、电影、娱乐、性欲、酒和香烟。”[14] 因此,人们贪婪地消费一切,吞食一切;任何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成了消费的对象。然而,消费者的天堂并没有给予它所允诺的快乐,无限制地满足人们所有的愿望并没有带来欢乐和极大的享乐,而且也不会使人生活得幸福(well-being)。究其原因,“除了工业制度内部的经济矛盾之外,还在于这一制度两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前提”[15]:其一是极端享乐主义。它认为生活的目的是幸福,而幸福就是最大限度地随心所欲、满足一个人所能具有的全部愿望或主观需求。然而理论和事实都证明,极端享乐主义不符合人的本性,更不是通向“美好生活”的正确途径。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又回到极端享乐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去了。人们信奉的口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然而,这些享乐只是“给我们的神经不同程度的刺激,不会使人的内心充满快乐。一种没有快乐的生活又迫使人去追求新的、越来越富有刺激的享乐”[16]。如此恶性循环,我们永远都是失望者。其二是利己主义。这是工业制度为了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必须鼓励的性格特征,也是当前人们所奉行的伦理道德的主要支柱。现代人以利己主义的方式在尽情享乐,然而利己主义同样被证明是错误的。奉行利己主义的人希望把一切都据为己有;占有就是他生活的目的。他永远不会满意,因为他的愿望和要求是无止境的。弗洛姆认为,利己主义的性格特征并不是自然的本能,也不是工业社会形成的原因,而是其产物。它只是给人带来无限痛苦的地狱,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
他还分析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对自然的仇视态度。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又是理性动物,超越于自然界。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凭借理性力量改造、征服自然,给人类带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但却使自然界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灾难已经出现。人类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对自然界的敌视态度使人变得十分盲目,而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17] 实际上,现代人在技术上的进步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而这两种危机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三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的深刻危机,弗洛姆并未停留在愤怒的批判与声讨上,而是积极乐观地构想人道化的健全社会,提出总体变革的纲领。他认为,要走向健全社会,就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经济体系,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诸方面对社会进行总体变革。同时,他也同意罗马俱乐部代表人物M.D.梅萨罗维奇和E.佩斯特尔等人的观点,认为应当把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同必须注意全球性问题的伦理方面,同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建立崭新的、真正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改变人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因此,他最终把总体变革归结到人的心理变革和道德更新上。
他清醒地意识到,对人类存在的真正威胁之一,是西方社会内部道德力量的衰落,即资本主义大批量地生产出奉行极端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异化的消费人,他们甚至对能够给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子孙后代的生命造成威胁的情况,即核灾难和生态灾难的可能性无动于衷。因此,要使西方人摆脱困境,关键在于对人进行心理变革和道德更新,这是社会总体变革的必备条件。“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社会才可能出现。”[18] 为此,他倡导人道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善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恶是削弱人的力量,是人对自己不负责。他认为,消费作为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行为,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段,是为人服务的,从属于人的充分健康的发展。他提出人道主义消费原则:“消费活动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和审美趣味应该参与这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19] 在消费领域进行道德更新,就是人应当意识到消费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占有方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人应当以重生存的价值取向逐渐取代重占有的取向,以健康人道的消费方式取代病态异化的消费方式,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取代人与自然的仇视,使人能够实现其全部的内在潜力,确立同他人、同世界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关系,从而实现人的真正幸福。
四
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以其规范人道主义的人性论为立论基础,以揭露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为重点,以发扬重生存的价值取向、建立健康而人道的消费方式为旨归。他积极肯定了消费行为作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手段的必要性,同时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使消费异化,从而导致人的异化的严重后果,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揭示了消费社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机,在道德上对消费社会做出了无情的判决。在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当今世界,深入研究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弗洛姆的消费异化论对正确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加上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福利政策,使社会各阶层的消费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不但统治者、老板们过着吃穿不尽的生活,而且平民百姓也是丰衣足食,以往体现阶级差别的主要因素——消费差距大大缩小。一些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宣称西方社会已进入“消费社会”阶级差别正在消失。弗洛姆并未被表面繁荣所迷惑,以深邃的批判目光剖析隐藏在社会深层的病症,如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物欲奴役人的非人道现象,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及其所赖以生存的极端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两个伦理支柱,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高度的物质文明与极度的精神堕落的两极化。他的批判理论所具有的激情和浪漫主义,在较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热情;他的思想吸引了各种不同社会集团中大量的人,并促进了他们的批判思维的产生和自我意识的增长。德国《明镜》周刊甚至认为:弗洛姆著作出版上的成功表明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时代精神。
其次,他的消费异化论对构建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需要的概念成为消费伦理最富于批判性的范畴。弗洛姆继承这一传统,他对人的真正需要及消费异化现象的分析,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存权利和消费需要的深切关怀;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精神上处于异常痛苦的事实,揭示了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会必然带来人生幸福这一真理;他的观点还说明,发展虽然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基础,但真正意义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两个向度。如果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并以此作为自由和幸福的体验的话,那么这种发展实际上只是异化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物质文明有了重大的发展,然而,消费主义也开始渗透到了社会价值观念之中,有些人的享乐欲望变得无度,道德虚无主义逐渐蔓延。我们同样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严重病症,坚决制止和杜绝消费异化现象,确立起符合人的真实需要的消费伦理,将大众消费引向科学、健康发展的轨道,追求以人的充分、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物质和精神的均衡发展。
再次,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推行高生产和高消费政策,从而导致生态灾难及人类生存危机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早已提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但我们有些人并未重视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水污染、空气污染等触目惊心。事实上,人类的消费行为是与生态文明相统一的,正如弗洛姆所说,如果我们依旧追求生产的无限增长、消费的毫无节制,那么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无穷灾难。我们需要彻底扬弃和超越工业文明的无限制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力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树立与生态文明相符的消费价值观。
还应指出的是,弗洛姆的消费异化论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认为消费异化固然有社会经济制度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放弃了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因此,总体变革归根到底是人的心理变革和道德更新。这种变革实质上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而他也就无法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源性的问题进行彻底的批判与斗争,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开脱的作用。他的思想是典型的改良主义和“清醒的乌托邦”,也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伦理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认为,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社会制度弊病的现成手段,同样也应该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之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存物质状况中发明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弗洛姆怀有拯世救人的善良愿望,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的人道主义乌托邦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标签:消费社会论文; 弗洛姆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人性论文; 经济论文; 伦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