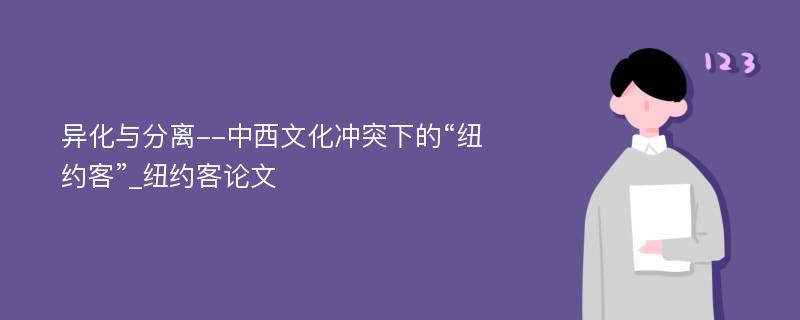
疏离与隔膜——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纽约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纽约论文,隔膜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6)1-0078-05
1963年,白先勇在新遭丧母之痛后,作别英雄垂暮的父亲,一个人飞赴美国求学。这一年,白先勇26岁,已在台湾的《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发表过《金大奶奶》、《玉卿嫂》等短篇小说。尝尽生离死别的年轻作家自此开始经历人生的重重忧患,去国之后,环境遽变,四顾茫然,心境悲凉,创作方向随之改变,留美华人的生活与命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与创作的主要内容。1964年白先勇在《现代文学》发表了他去美国之后的第一篇作品——《芝加哥之死》,自此,开始了他“纽约客”系列的创作,除《芝加哥之死》外,随后问世的该系列作品包括:《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一共9篇。
这9个短篇的创作时间从1964年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展开的。这些在纽约的中国人在二战之后来到美国求学,学成之后,除了《夜曲》的吕芳回国之后,其他的人都因为各种原因而留在美国,成为客居异国他乡的“纽约客”。在这个短篇集中,白先勇表现了这群去国离乡的“纽约客”在美国社会的种种失落、困惑、空虚乃至幻灭。9个短篇中,《芝加哥之死》和《谪仙记》的主人公最后都跳水自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残春》和《喀尔美萝姑娘》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留日学生的生活,在这三篇作品中,都发生了留学生自杀的事件,他们自杀的原因虽然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弱国子民在异国所受的歧视和压抑,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源于一种个人的性苦闷和爱情的苦闷。老舍完成于1929年的长篇《二马》反映的是旅英华人的生活,“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1] 对中国落后的国民性进行反思和批判,而非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自觉反思和主动探索。冰心20年代留学美国期间所写的一系列《寄小读者》温婉动人,有着淡淡的感伤,却没有流落异国天涯的风霜。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优美动人,其中所描写的留学生活真是风花雪月、令人神往,根本见不到留学生活的苦闷或是文化冲突的困惑。五四一代的作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基本是敞开胸怀热烈欢迎,大规模地引进“拿来”,对西方文化的景仰之情真是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在这个阶段,有着留洋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热情接受和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激烈批评和否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对于留洋的中国学生几乎不存在,他们出国留学本来就是以西方文化为皈依的,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文化认同危机。
白先勇这一代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不同于五四一代的作家,他们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采取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对于他们,西方文化不再是可靠的稳定的皈依,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再是彻底否定和背弃的对象。他们这一代的留学生不再把中西文化冲突理解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问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他们必须认知和把握的对象,而非简单的二选一就能了事的。当他们置身于一个异质的文化语境中,他们首先遭遇的是文化认同的危机,为此他们必须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两种不同文化进行独立认知,在这个通过认知而重新建立文化信仰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了种种迷惘和困惑。因此,白先勇笔下所呈现出来的留学生生活具有与五四一代留学生不同的风貌,他们更多的是徘徊挣扎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属于自己的难以认同,属于别人的又难以追求。
美国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中论及美国一战后“迷惘的一代”说道:“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无根之木,在外地上学,几乎和任何地区的传统都失却联系。”这一段话,用来概括二战后从中国到美国去的“纽约客”同样恰当,他们在中国成长,到美国受教育,然后在美国生活,渐渐地与中国的传统失去了联系,而与美国社会又始终存在无法超越的距离,难以建立起精神上的骨肉联系。这些“纽约客”在精神上的状况是与中国疏离,与美国隔膜,这种疏离和隔膜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完成的,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命运。与中国的疏离可以说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这些离国的“纽约客”与中国的感情纽带断裂了,在他们留学美国期间,失去了在国内的亲情、爱情等感情联系,有着故乡意义的家对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的倦鸟;另一个层面则是历史的原因,二战后去美国的这些“纽约客”对台湾政权缺乏信心(“纽约客”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台湾的),对红色中国又缺乏认同感(二战后美国大搞冷战政策,对中国大陆采取敌视态度,造成了美国与新中国的隔膜,这种隔膜一定程度影响了留美学生对新中国的了解认识,原来与国民党政权有着一定背景关系的留学生更是对新中国感到陌生和断裂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大陆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使得这些“纽约客”们更是与中国大陆疏离了,《夜曲》、《骨灰》充分反映了“文革”对这些海外学人的影响。这两个层面的原因共同造成了“纽约客”与中国的疏离。这种疏离并非出自他们的自觉选择和追求,更多的是身不由己。纽约客表面上虽然是与中国疏离了,精神上却始终有一种无以排解的“文化乡愁”,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无法割舍,又无法完全认同。这种“文化乡愁”又直接影响和干扰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造成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的隔膜。
《芝加哥之死》是这种疏离和隔膜的典型表现。吴汉魂一到美国就躲在地下室埋头苦读,同时抓紧时间努力挣钱,其他的一切(如亲情、爱情)都无暇顾及了。六年时间,“吴汉魂一毛一毛省下来的零用钱全换成五颜六色各个出版公司的版本,像筑墙一般,一本又一本,在他书桌四周竖起一堵高墙来。六年来,他靠着这股求知的狂热,把自己囚在这高墙中,将岁月与精力,一点一滴,注入学问的深渊中。”[2] 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世间最最基本也最最重要的感情都被隔绝在这堵高墙之外了,大洋彼岸心爱的女友嫁人,苦等他回去的母亲病逝,他却连伤心和痛苦的时间都没有,在忽略一切感情需求、狂热追求学问的过程中,他不知不觉完成了与中国故土的疏离。当他终于戴上那顶沉重的博士方帽时,人的欲望才在他身上苏醒过来,他将目光从书本转向他生活在其中却一直对其浑然不觉的芝加哥:
“他突然觉得芝加哥对他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吴汉魂立在梦露街与克拉克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他失去了方向观念,他失去了定心力,好像骤然间被推进一所巨大的舞场,他感觉到芝加哥在他脚底下以一种彭湃的韵律颤抖着,他却蹒跚颠簸,跟不上它的节拍。”(见《芝加哥之死》)
六年来,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这里是个纯粹的“局外人”,他这个从地下室冒出来的文学博士与芝加哥竟是如此的隔膜。当他试图进入这个城市(随后的喝酒嫖妓一系列行为是他对这种隔膜的反抗)时,他感到的却是透骨的空虚,天地悠悠,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无所皈依,死亡便成为他唯一的归宿了。这是一个刚刚从书斋里出来的文学博士的悲剧命运。
那些已经在美国社会站稳了脚跟,跻身于美国白领阶层的“纽约客”们如李彤、依萍、吴振铎等,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家世显赫、美艳惊人、心高气傲的李彤,原是父母千般宠爱的掌上明珠,到美国后是众多男孩子心目中的“五月皇后”,毕业后出来工作是拿高薪的服装设计师,这样一个“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的大牌美女,却在美国一年年蹉跎着青春,无处归宿,最后在威尼斯跳水自杀,成为“孤魂野鬼”。李彤为什么死?连她多年的好朋友都不太明白,或者说是不愿明白。表面上看起来,李彤在美国活得好好的,没有什么理由自杀。然而,外表的热闹覆盖不了她内心的空虚与失落,与跳入密歇根湖的吴汉魂一样,他们都是在精神上无所寄托,在美国这个“荒原”上无处生根的异乡人。与吴汉魂对中国(母亲、女友)的忽略不同,李彤是不愿割断与中国的纽带而纽带却自己断了(父母遇难身亡),父母的死意味着李彤从此无家可归,从此之后,李彤就一点点从人生的战场上退下来了,最后是完全退出生命了。李彤的死,使得那些与她一同来到美国的好朋友们一个个纷纷失态,如遭雷击,引发了她们“极深沉极空洞的悲哀”,兔死狐悲,李彤的死,触及了这些同样无家(国)可归的流浪者内心深处最脆弱的伤痛——那是一种无以解脱的乡愁。《夜曲》的吴振铎医生可谓是典型的“美国梦”实现者,地位、财富都有了,然而,多年来却始终有着一个心病:当年学成时没有勇气回国去,未能实现父亲要他医治中国人的意愿。当年学成回国去的吕芳却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又费尽周折回到纽约来,吴振铎听闻“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遭遇,心有戚戚焉,却仍是放不下他的心病。这是放不下的心病,也是解不开的乡愁。与红色中国疏离的“纽约客”心里都有着一个解不开的结。《骨灰》里大伯对侄儿齐生叮嘱他的后事:死后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大海里,任他飘到大陆也好,飘到台湾也好——千万莫葬在美国。大伯从前是国民党的抗日功臣,对红色中国难以认同,然而,到底都是中国,是死后灵魂安歇的地方。
这些旅居异国的“纽约客”,不管他们在美国生活得如何,失意也好,得意也好,与美国社会却都是隔膜的,吴汉魂那样闭门苦读的人与纽约隔膜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像李彤、吴振铎、依萍这些生活安逸的人也一样的难以融入他们的环境。对于他们,美国不是他们曾经梦想过的乐土,纽约也不是他们的家。《纽约客》给我们展现出来的纽约形象或美国形象真是寒气逼人。直接的环境描写在这部短篇集里并不多见,白先勇更多的是通过故事展开的季节、具体时间来渲染环境的气氛,除了《芝加哥之死》、《香港——一九六○》、《火岛之行》这三个是在夏天之外,其他的6个则是在残冬或暮秋,具体时间主要是在夜晚,整个小说集让人感觉寒意森森。即使故事背景是六月份的《芝加哥之死》也透着“一股阴森的冷气”,其他的几篇更不必说了,《上摩天楼去》是圣诞夜“一阵沦肌浃骨的寒气”,《安乐乡的一日》是“仲冬的十二月”,《谪仙记》是雪后“空气寒冽”,《谪仙怨》则有着愈来愈大的风雪,《夜曲》是“暮秋的午后”“迎面一阵暮风,凛凛地侵袭过来”,《骨灰》是在十二月“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竟是寒恻恻的,砭人肌骨”。这种寒冷的气氛之下,蕴藏着的是“纽约客”与纽约的隔膜,这座繁荣的国际大城市,这个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的世界港口,却不能为他们无所皈依的内心提供温暖的慰藉,他们在这里不管生活了多久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纽约客”,是无法在这个城市生根的过客。这样一个寒气森森的美国形象,一方面与“纽约客”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下的特殊心态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军事、文化(二战后,欧洲大批知识分子涌入美国,对美国文化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各方面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数一数二、称王称霸,因而,“美国梦”对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人,真是熠熠生光、魅力无限。关于“美国梦”的魅力和本质,《喧哗与骚动》的作者有着独到的见解:
“我们的先辈并没有把这种梦想、希望和境遇遗留给我们这些后辈和合法的继承人,而是把我们这些后代人遗留给了梦想和希望。我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些梦想,因为从我们出世起,这种梦想就牢牢地控制了我们。它不是我们的遗产,因为我们是它获得的遗产,我们世世代代都被梦想所继承。而且不仅是我们这些美国的子孙后代,还有在受压迫的古老的异族的土地上出生和受教育的人也感受到这种气息、这股拂面的微风,也听到了保证获得希望的余音。”[3]
这种梦想具有魔法一般的神奇诱惑力,使得一代代人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它的祭祀品。从19世纪末以来,“美国梦”一直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具有一种持续而强烈的吸引力,各种肤色的人中,总有人被“美国梦”所俘虏,以为美国这片新大陆真是代表着自由民主平等希望等等一切美好的东西,在这里,每个人只要努力奋斗,就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一代又一代,总有人经历着“美国梦”幻灭的悲哀,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菲茨杰拉尔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说的都是“美国梦”在冷酷现实面前的脆弱和幻灭。
“虽千万人,吾往矣”,对于二战后久经战患的中国人尤其是台湾人,美国在当时依然是个给人以希望、梦想、自由的黄金国土,于是,大批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心怀“美国梦”奔赴大洋彼岸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的这片乐土。当吴汉魂们、李彤们这些正当青春的年轻人离别饱经战患的故国,满怀热情来到美国寻求梦想的时候,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却并非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美好。美国在二战后大力推行冷战(遏制)政策,与苏联大搞军备竞赛,使得人们都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冷战政策不仅给全球带来了核战争的威胁,对当时的美国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冷战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感情现象,是政策的状态,也是思想的状态。它不仅表现为美国对世界事务强行、粗暴的介入,也是美国社会生活充满压抑、沉闷,运行着冲突、反叛的表征。”[4]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遏制政策带来的保守压抑气氛之下,美国社会出现了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嬉皮士运动、反越战、性解放运动等等各种五花八门充满反思或反抗意味的思潮运动。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在路上》、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等,这些在二战后深受美国青年欢迎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冷战政策之下美国社会青年一代精神上的苦闷、彷徨、反叛、悲观,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纷纷遭到挑战、怀疑与否定,美国社会自身正经历着重大的精神危机,个人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感到世界的荒诞、冷漠,精神上的孤独、痛苦、虚无不仅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发达富裕而得到缓解,反而是更加严重了。虽然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别,中国的年轻人不见得就都能认同并参与当时美国社会蜂起的各种思潮运动,但是这样一个自身问题百出千疮百孔的社会,与他们期待当中的“黄金国度”是很有差距的,他们的失望可想而知,他们与美国社会的隔膜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如《上摩天大楼去》,单纯热情的玫宝坐了两天两夜的飞机,终于来到她日思夜想的纽约,然而,在见到她同样日思夜想阔别两年的姐姐之后,她所感到的却不是姐妹相见的欣喜与感动,而是与已经非常美国化的姐姐之间的隔膜,最后,当她独自一人登上世界第一高的摩天大楼,寒风却冷得让她发抖起来,而这就是纽约——黑夜之下寒气逼人的摩天大楼。
相比较于头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中国在当时不论是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都是处于相对弱势,这样的背景,难以为这些奔赴西方文化发达国家的中国年轻一代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撑,他们自然很难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西方文化气势汹汹的挑战。当他们离开了原来的母体文化语境,一头扎进一种陌生的强势的异质文化,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从生活到精神都经受着西方文化“惊涛拍岸”的全方位冲击。生存空间的重大变换,新环境的严峻冷酷,要求这群流落异国的“纽约客”必须成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真的猛士”。当他们离开故国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身上早已烙下了中国文化的痕迹,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来接受美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的。然而,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却未能为他们提供面对强势文化冲击所需的强大自信心和心理平衡,未能成为他们在美国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精神支撑。自身正经历着精神危机的美国社会也不可能为这些异乡人提供足够的精神信仰,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纽约客”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难以认同,精神上的流浪也就自此开始了。他们不像他们的下一代如依萍的女儿宝莉,这些生长于美国的“香蕉”人在感情上精神上都已经与美国社会完全认同,在他们的意识里已觉得自己是个美国人,如宝莉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是个中国人,他们不会再受到中国文化的困扰。“纽约客”们的生命却是分为两端的:一端是中国,一端是美国,他们的悲剧正在于此,他们无法完全认同任何一端,而是挣扎浮沉于两端之间,无法在任何一端停靠,于是,精神上的种种失落、荒凉、幻灭便随之而来。一种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一旦直面另一种处于相对强势的文化,前者往往会感到失落、迷惘,纽约客们对自己原有的文化既缺乏足够强大的信心,又不甘心于(或者无法)对他者的文化完全妥协,于是,这两种异质文化在他们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冲突。
《纽约客》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是“美国梦”幻灭的表现,但这种幻灭不同于德莱塞、菲茨杰拉尔德等美国作家所表现的“美国梦”幻灭,白先勇的“美国梦”幻灭更多的是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旅美的中国人在两种文化冲突中自我的失落与寻找,这是近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主题,白先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此做出了自己独特的探索和反思,因而“纽约客”们的命运在文化层面上具有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