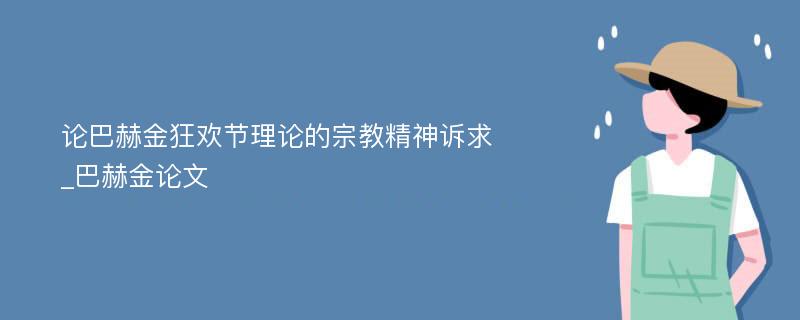
论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精神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宗教论文,理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8)02-0052-05
宗教都含有一种否定现实人生的怀疑态度。如佛教的追求来世、基督教的救赎意识,最终都使人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选择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安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精神诉求也正是通过看似对立的二元关系来彰显的。在其狂欢理论中,巴赫金对物质存在的关注度不高,甚至说没有关系。他在颠覆现有存在的众多束缚中,始终期盼一种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彼岸,一种十分抽象的宗教精神上的东西。在诸如“交替与更新”、“肯定与否定”、“第二种生活”等概念中,巴赫金都赋予其精神解放的深刻内涵。
一、“交替与更新”:生死更替的生命哲学
从基督教的生死观中,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关于“救赎”、“原罪”、“复活”等宗教观念,还可以体会到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因为在上帝的眼里,死并不是如何恐惧的事情,而是回家,是由死到生的复活,是一种永生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放弃一切悲哀、痛苦,沐浴在上帝的博爱之中。同样,在巴赫金的狂欢视野里,狂欢中的“交替与更新”往往是对生命价值所进行的宗教式的乐观注解。
巴赫金在“交替与更新”的论述中,始终追求生命的永恒,演绎着生死交替的生命哲学。其狂欢理论倡导生命的力量和精神的永恒。死亡同样是生命的一种呈现样态。这同原始宗教的思想异曲同工。
卡西尔强调:“原始宗教或许是我们在人类文化中可以看到的最坚定最有力的对生命的肯定。”[1]他举例说道,布列斯特(James Henry Breasted)在叙述最古老的金字塔经文(Pyramid texts)时说,在那里从头到尾主要的和起支配作用的符号(note)的意义就是执著地甚至激烈地反抗死亡。卡西尔早就谈到神话关于死亡与新生的独特解读,“死亡绝不意味着人的生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生命形式的一种变化,即由一种生存方式向另一种生存方式的简单转换。在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鲜明的确定界限。划分生死的界限是模糊的、难以分辨的。甚至这两个概念可以交替使用。欧里庇得斯问道:‘谁能知道今生不是真正的死,并且死不能转向生呢?’在神话思想中,死亡的奥秘转变成一种想象。通过这种转变,死亡不再是一件难以忍受的自然事实,而变得可以理解可以忍受了”。[2]
同时,“众所周知,宗教总要信仰一个神,一个超验的能够主宰人的命运,负责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人格神。你信仰它并终生行善,死后就能被接到天堂或西方净土。但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这种神已死去。但人的精神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以代替神”[3],巴赫金追求的就是这种“神”,“为了与传统的宗教相区别,人们也常把后一种神作为宗教精神。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根本要旨都在于对人的精神的拯救,是靠神对人的拯救,是‘他救’;宗教精神也是对人的精神的拯救,但是却是人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对自我的拯救,是‘自救’。这是宗教精神与宗教的最根本的区别”。[3]
二、“肯定与否定”:情感表达的本能宣泄
早在1947年,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就发现了狂欢的重要性所在。在狂欢中,人们可以获得一种崭新的生存,它打破了一切伦理道德规范和理性限制,大量出自本能、情感和欲望的越轨行为弥散着强烈的快感和新奇,它使人们恢复到前现代社会那种人与自然欢聚一堂的热烈与和谐中。无疑,这正是列斐伏尔所期望的非理性文明、乌托邦社会。
我们可以将狂欢说成是人类一种普遍的精神文化现象,但就其宗教精神意义而言,情感的表达和宣泄更符合狂欢的本意。诚如钟敬文先生所言,“从历史上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狂欢活动。他们通过社会成员的群体聚会和传统的表演场面体现出来,洋溢着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情绪”[4]。而这“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情绪”正是巴赫金狂欢理论中凸现出来的重要内涵之一。与其相似的是,巴赫金的狂欢思想突出了“肯定与否定”在狂欢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肯定人情感的本能存在,否定现实生存困境的压抑束缚。
“食色乃人之两大本性,食色欲望为狂欢的原动力,食色本能的宣泄是狂欢最基本的表现形态”[5]。狂欢不仅是同官方权威话语斗争的文化样态,而且深深地萌生于人类的本能情感。人的情感需求中包含着宣泄和娱乐的成分。狂欢不能被看做是纯粹政治斗争和文化对立的折射镜,它恰恰是人类某种情感的独特表达。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情感并不是感情本身,而是某种情感转化的一种假想,一种粗野、奇异甚至是怪诞的假想,一种消极情感状态的积极表达,即在生存界面上拷问本能宣泄和精神自由,力求在压抑的时代寻求一份情感的表达渠道,尽管寻到的对象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狂欢节,尽管只是暂时的、短暂的感情抒发,却已经取得了情感流溢的表达权。在狂欢理论中,我们可以寻到一种情感的同一性——本能和宣泄、愉悦和快乐。狂欢理论本身追求自由、平等、精神解放,体现了对社会民众的由衷关怀——从生理层面到精神层面——尽管这种关怀只是乌托邦理想。总之,在狂欢理论中反映出的这种终极关切状态,其本身就是宗教性的。
巴赫金传记的权威作者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可尔·霍奎斯特认为,狂欢节是罗马天主教会的霸权鞭长莫及的为数很少的领域之一,“它们既不命令也不乞求……所有这些形式无一例外地处在教会和宗教信仰之外。它们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些形式不仅不属于官方的宗教信仰,而且也不遵循官方的审美规范,“这个文化的狂欢节的核心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并且一般的说,甚至根本不属于艺术领域……事实上,它是生活本身……依照某种游戏形式构成”。与仪式典礼不同,狂欢节不是由某个孤立的特权阶层来组织的,相反,每个人都创造狂欢节,每个人都是狂欢节。“狂欢节不是一个为人们观看的场景;人们就生活其中,所有人都参加进来,因为狂欢节的概念囊括了所有人”[6]。“在巴赫金那里,狂欢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打碎日常生活中各种身份地位的人为界限,使不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欢庆。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是,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突出了狂欢本身的颠覆意义,因而强调了经由广场狂欢的活动。一方面,民间文化彻底地摧毁了正统官方文化所确立的各种僵化刻板规范;另一方面,狂欢本身也是一种在颠倒原则中实现的人人平等交流”[7]。
三、“第二种生活”:世俗之间的自由向往
现实生活往往是有限的、残酷的、异化的,建构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第二种生活成为许多思想者诉诸笔端的理想。
在巴赫金的世界里,基于宗教哲学的观念基础,始终沉浸于一种关系世界里:“第一种生活”和“第二种生活”。“第一种生活”是当今的现实世界,是此岸世界;“第二种生活”是相对于此岸世界的彼岸世界。“第二种生活”是人的精神栖居地,也恰恰是现实生活的避难所。在《拉伯雷研究》的导言中,巴赫金共五次提到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而且每一次的提出所涉及的角度都不尽相同。
第一次,巴赫金侧重强调了“仪式—演出形式”和“严肃的官方的(教会和封新中国成立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二者之间的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所有中世纪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参与,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生活过的世界和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看不到这种双重世界关系,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的文化意识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对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的忽视或低估,就会造成对其后整个欧洲文化历史发展景象的曲解。”[8](P6)第二次,巴赫金侧重谈狂欢节的特质,指出:“狂欢节,这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这是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节庆性,这是中世纪一切诙谐的仪式—演出形式的本质特点。”[8](p10)第三次,巴赫金侧重强调节庆性,“节庆性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8](P11)。第四次,巴赫金侧重从官方与民间的节日特点比较方面的阐释,认为“中世纪的官方节日,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封新中国成立家的节日,都不能使人偏离现有的世界秩序,都不能创建任何第二种生活。相反,它们将现有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固定化。与时间的联系流于形式,更替和危机被归属于过去。官方节日,实际上,只是向后看,看过去,并以这个过去使现有制度神圣化。官方节日有时甚至违背节日的观念,肯定整个现有的世界秩序,即现有的等级、现有的宗教、政治和道德价值、规范、禁令的固定性、不变性和永恒性。节日成了现成的、获胜的、占统治地位的真理的庆功式,这种真理是以永恒的、不变的和无可争议的真理姿态出现的。所以,官方节日的音调气氛只能是死板严肃的,诙谐因素与它的本性格格不入。正因此,官方节日违反了人类节庆性的真正本性,歪曲了这种本性。然而,这种真正的节庆性是无法遏止的,所以官方不得不予以容忍,甚至在节日的官方部分之外,部分地把它合法化,把民间广场让给它”[8](P11)。第五次,巴赫金是从日常生活和民间文化的角度,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民间文化的第二种生活、第二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但必须强调指出,狂欢节式的戏仿远非近代那种纯否定性的和形式上的戏仿:狂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一般说来,赤裸裸的否定是与民间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8](P13)。
在此,我们可以将基督教的“把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与巴赫金狂欢节的“把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区别开来。任何开始研究《新约》的人都会看到,耶稣用他的福音,来向那个同是巴赫金狂欢节目标的“世俗世界”挑战,但采用的方法完全不同[9](P226)。因为一个中世纪的人不可能认为快乐在于知足,在于满足现状、有你所有,因为对于一个中世纪的人而言,快乐只是一种“来世”的状态,必须通过“现世”的许多磨难才能达此境界[10]。诚如巴赫金所言:“节庆活动(任何节庆活动)都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不能从社会劳动的目的和实际条件来对这种形式作出推导和解释,也不能从周期性的休息的生物学(生理学)需要加以推导和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更为庸俗。节庆活动永远具有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世界观内涵。任何组织和完善社会劳动过程的‘练习’、任何‘劳动游戏’、任何休息或劳动间歇本身都永远不能成为节日。要使它们成为节日,必须把另一种存在领域里即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某种东西加入进去。它们不应该从手段和必要条件方面获得认可,而应该从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即从理想方面获得认可。离开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任何节庆性。”[8](p10)
显然,在巴赫金所谓的“第二种生活”里,“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本身现实的(但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是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也可以这样说:在狂欢节上,生活本身在演出,这是没有舞台、没有脚灯、没有演员、没有观众,即没有任何戏剧艺术特点的演出,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由(任意)的形式,这是自己在最好的方式上的再生与更新。在这里,现实的生活形式同时也就是它的再生的理想形式”[8](P9)。
在狂欢节期间,取消一切等级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官方节日中,等级差别突出地显示出来:人们参加官方节日活动,必须按照自己的称号、官衔、功勋穿戴齐全,按照相应的级别各就各位。节日使不平等神圣化。与此相反,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在这里,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而在日常的,即非狂欢节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差异的屏障所分割开来。在中世纪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阶层、行会隔阂的背景下,人们之间这种不拘形迹的自由接触,给人以格外强烈的感觉,它成为整个狂欢节世界感受的本质部分。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8](p12)。
狂欢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游戏,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现象。人是在无尽的狂欢历程中生长成熟起来的。只有在人遭遇禁忌、控制、压抑、极权(包括自然的、生理的、人为的、精神和物质的方面)之时,狂欢才有了存在的可能。狂欢是人类生命存在的自我表现,富含着游戏的成分,从而自由地展示了人类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复原了人类另一种原生态的“第二种生活”。按照巴赫金的论断,“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的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11]。
由此,巴赫金认为,“节日仿佛是全部官方体系及其所有禁令和等级屏障暂时失效。生活在短时期内脱离法定的、传统的常规,进入乌托邦的自由王国。这种自由的昙花一现本身,只是强化了在节庆氛围中所创造的形象的幻想性和乌托邦的激进主义”[8](P103-104)。在狂欢中,社会统一的规范(行为规范、理智、尊严、对传统和社会秩序的尊重、得体的举止和体贴等)都被狂欢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自由的、亲近的交往,等级顾虑的消除,怪异的举止,以及神圣与世俗、高尚与低下、伟大与渺小、聪明与愚蠢之间的狂欢性的“不相称联姻”)打破了。在此类行为被仪式化(即,特殊的情况被排除掉)的地方,它便被社会性地保存了下来;而在其自动崩溃的地方,其结果是使社会行为的习惯变得相对化,从而极度混淆了人们在彼此交往中对自身位置的感觉[9](P119)。
可见,正是在同官方的对比中,巴赫金指出了狂欢生活的独特性质。狂欢的生活只能在非狂欢的生活之中显示出来。正如费斯克所指出的那样,“对巴赫金而言,狂欢提供了打破日常生活的机会,提供了被压制者的声音在最大时可被听到的机会,提供了社会接受它通常所压制和否定的快乐的机会。狂欢的本质是它对规范着日常生活的规则的逆转;狂欢的必要性源自被压制者最终对屈服于社会规范的拒绝。所以狂欢的力量是从属者的日常生活中起压制和控制作用力量的对立面”[12]。当然,这种“对立”,仅仅是学理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抽象的对立,实际上,对立的两种生活却是并存的,共生的。
毋庸讳言,在狂欢节举行的时候,在它之外没有另外的生活,在此期间,生活只从属于它的自由法则。这一天,人们自发自愿地来到广场,尽情地享受着感官欲望的自由宣泄。“公众广场话语”具有一种象征意味,是与官方和权威话语相对立的全民话语,从来不属于任何私人,它不承认任何权威和中心,所推崇的仅仅是“可笑的相对性”。它实际上是一声呐喊,在大批人群中高声呼唤,来自人群,并以人群为对象,讲话者与人群融为一体,既不以人群的反对派出现,也不想启蒙大众,他与大众一同开怀大笑。狂欢节是社会组织中的一道裂缝,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企图塑造成一个统一的文本,一个固定的、完成的和永恒的文本,因此狂欢节是一种威胁,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单世联从美学意义的角度认为:“巴赫金赋予狂欢节以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对抗的力量,它打破一切牢笼的‘公众广场’,它颠倒一切等级秩序的‘笑’,它放荡肉体欲望的生命自由,它把确定置于多义和不确定之中等等,具有远远超出审美范围之外的政治—文化意义,狂欢节是解放的世界:世界不再可怕,而是极端的欢快与光明。毕竟,人类在文明的紧身衣中憋得太久了,以至于给予了至善至美理想的艺术形式也似乎是一种桎梏。黑格尔说审美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尼采、马尔库赛都曾从艺术中寻求人的幸福,但只有巴赫金把这一切说透了。生活有它的强制和压迫,不可能天天是狂欢节,但如果有那么一个片刻、一个瞬间,我们走出一切社会体制、文化规范、功利计较,朗声大笑,尽兴吃喝,痛快淋漓,自由奔放,纵恣自己的欲望,随意自己的身体,生活不才真的值得了吗?即使不可能真的身临其境,那么在我们心境中,在我们的幻想中,也总该有这一点憧憬,有这一点向往。它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但至少启示着我们,人类,就其可能和应当来说,是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的。”[13]正所谓“在变动中见永恒,在不纯洁中见纯洁,在不自由中见自由”[14](P8)。巴赫金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能够始终往前看,从而面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确,“对孤独的个体的需要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14](p9)。这虽然是马尔库塞对“肯定的文化”的内涵概括,但同样适用于巴赫金的“第二种生活”。狂欢生活向我们许下了一个永恒的理想的诺言,并提供给人们一种暂时性的满足。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审视狂欢,可以说,从古至今,狂欢精神就从未消弭过,甚至成为某种人性意义的福祉。从狂欢中透露出的是一种企盼——从现实的废墟走进理想的天堂,以寻求心灵的安宁,排除窒息的压抑。尽管狂欢改变不了非狂欢的现实生存状态,尽管非狂欢的生活也不会因狂欢的短暂存在而出现日薄西山的衰景,但是,当我们从当代精神危机意识的角度来考察狂欢的时候,实则是站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同传统观念展开了时代对话,以期在人性追问中,显出人类生命诉求间的原初样态。由此,我们可以说,巴赫金狂欢理论思想的宗教之维,强烈地表现出了他作为当代思想家的独特个性:不是社会现实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而是人类原初精神家园的追忆者和眷恋者,是一位面向未来的杰出预言家。在肆意狂欢的背后,巴赫金为我们吟唱着一个失去的乐园和一个难以企及的希望,从而抹平了两种生活之间的直接对抗,弱化了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可以说,狂欢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起到了一种“特洛伊木马”式的功能,即能够“把人从困境中解放出来,化悲为喜,化险为夷”[15]。虽然“狂欢节未必总是破坏性的,但破坏的因素总在那里;它也并非总是进步的或解放的,但进步与解放的潜能一直在场”[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