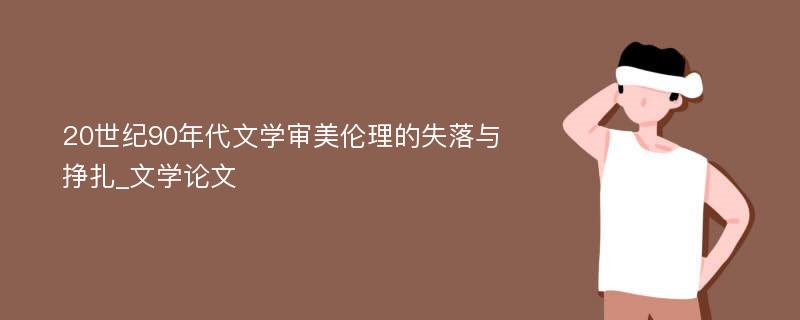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文学审美伦理的失据与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5-0173-07
一
20世纪90年代作家整体上面临着新的美学困惑,这就是“唯审美”的大面积“溃退”和“泛审美”的全方位“滋长”,文学审美精神由“崇高之巅”坠入“流俗之谷”。在既往人们的美学视野里,审美(包含艺术和其他审美活动)具有超拔的形而上的意义,它指向一种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第二自然”,追求一种超然于日常平庸人生之上的纯粹精神体验。既不以满足人的实际需求为目的,也不以满足人的欲望本能为归向。这是一种传统的精英性的“纯审美”或“唯审美”观念,它强调的是审美与艺术所具有的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精神性或超验性内涵,其最适合的审美对象往往是具有强烈的终极关怀意义的、神性思考层面的经典文化或曰高雅文化。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纯审美”或“唯审美”的观念已经被具有明显“泛审美”倾向的“审美文化”话题取代。[1]90同“唯审美”指向经典和高雅相比,“泛审美”却是指向世俗和庸常,强调的是审美的日常性和经验性。
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唯审美”的经典文化所代表的是具有权威性和传统性的文化价值规范,这些文化价值一直模铸着人们的思想,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为何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唯审美”的伦理规约突然失效了呢?
不可否认,“唯审美”的经典文化渗透和层累着世代知识精英的思想精华,可是,久而久之却又常常凝固成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样不但损害了普通大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更有可能扼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然而,在“重义轻利”的传统社会里,“唯审美”因为有其稳定和深广的社会心理结构作支撑,本身又具有强大的文化惯性,人们的审美趣味必然而然地就被格式化在“唯审美”的叙事范式里。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迅速转型,市场逻辑和现代传媒建构了一个完全异样的文化生态环境。
首先,市场逻辑把一切都市场化了。经济市场化,文学也随之市场化。本来文学作为商品具有一般商品所具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属性,然而,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当代社会,一直承续着“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表现在文学上就是重视文学的价值,也即文学的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而文学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文学的商品价值却是普遍地遭受拒绝与藐视。可是,在市场逻辑的操控下,文学的这种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文学中的地位却发生了根本性的置换。能不能赢得受众的青睐?能不能大面积地占领市场?能不能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文学的使用价值即文学的商品价值,成为衡量文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有时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文学的商品价值遮蔽了文学的精神价值、情感价值以及文学的审美价值。
其次,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的崛起,使之成为当下人们接触社会、获取信息、进行文化娱乐的主要管道。大众文化借助于现代传媒和商业化运作机制,不仅事实上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潮,而且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闲暇活动本身,改变了当代文化的走向。大众文化的兴起,意味着当代文化从传统的文字的印刷时代进入了影像的、视觉的时代。视觉文化的到来,使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野变得模糊起来,特别是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大众文化,以追求感官愉悦为旨归,通过欲望化的叙事以及视觉影像的形象性和现场感,对大众的感官进行刺激和按摩。处在市场经济重压下的人们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解放沉重的肉身,普遍追逐具有感性、娱乐和世俗性质的大众文化。这样一来,以厚重、严肃、崇高为特质的“唯审美”高雅文化,其审美特性和审美逻辑就与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发生严重隔膜。于是,“泛审美”的大众文化以其来势汹汹的席卷姿态,不断渗透、消解“唯审美”的高雅文化。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市场逻辑和现代传媒语法的支撑下,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不断地被边缘化,而物质化和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却不断地攻城略地,扩大地盘,并一举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纯审美”或“唯审美”,而是渴望美在生活、实用、通俗和商业的基础上展现自身。美成为日常生活本身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以往的“纯审美”被泛化到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日常生活体验成为审美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趋于审美化,有意无意将审美作为自己的标准,泛审美倾向尤为明显。由此,有的学者认为;“从唯审美的精英文化启蒙到泛审美的大众文化狂欢,经典美学逐渐走出了以现代主义艺术为范本的审美自律的内聚模式,投入到新一轮的学科扩张与理念调整之中;当代美学的建构也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进入到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2]这种新型的社会行为范式美学其主要表征就是泛审美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鲜明的信息性、科技性、商业性和产业性,具有强烈的实用功利价值和娱乐消费功能,具有批量复制和拷贝的创作生产方式,具有快速、直观、应时、随意的创作特点,具有主体参与、感官刺激、精神快餐和文化消费的都市化、市民化、泛社会化的审美追求,特别是具有与西方后现代文化及其广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契合性和呼应性。所有这些特点,不仅在卡通片、警匪片、摇滚乐、霹雳舞、流行歌曲、通俗小说、行为绘画、实证电视等中可以清楚看出来,而且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和市场背景下出现的常规性的录音、录像、广播、影视、书籍、报刊中,也同样可以看出来。”[1]90可见,泛审美的大众文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无处不在的文化景观,被推到文化的前台,处在多元文化格局的核心主流地位,不仅牵引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而且规定着当下文化的美学走向。
二
在大众文化的笼罩下,作家们的写作姿态普遍显得有些张皇失措、无所适从。的确,终止一向视为使命意识的“唯审美”的高雅文化追求,走向“泛审美”的大众文化表达,不仅意味着作家自己主动走下了高高在上的文化神坛,由受人景仰的精神导师变成一个没有任何智慧光环的凡夫俗子,而且还意味着背弃了自己孜孜以求的美学信仰,必然要遭受因文化人格分裂所带来的持久心灵煎熬。在进退失据的精神焦虑中,作家们如果风骨傲然地背离大众文化,以坚贞的“盗火者”姿态毅然决然地奔赴“崇高”,那么,不仅要承受形影相吊的文化孤独,还要承受经济困顿的生存尴尬。置身于这样的文化语境,传统作家虽然有着对唯美理想的深情眷恋,但是在市场化压力的驱使下,他们又不得不屈服于世俗美学的露骨“招安”,在滚滚红尘里随波逐流。不过,与传统作家不同,追随时代一起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作家却没有他们的精神负累,在涌动着世俗美学的文化潮汐里,他们形而下的欲望写作显得尤为放肆乖张、理直气壮。由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审美价值整体偏离传统的唯美诉求,开始奔赴世俗,走向休闲,陷于颓废,表现出扑朔迷离的逻辑脉动。
奔赴世俗。所谓“世俗”,不是一般意义的“庸俗”、“低级”等等,而是指人们的审美指向不再有伟大的理想冲动,不再有宏大的生活目标,也不再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信仰,有的只是实现人际间在日常生活中那份脉脉温情的渴望、满足生活基本享受的热情。它意味着人们不再把确立生活的远大精神理想当作一种现实的目标,也不把重建生活的崇高意义当作自身行动的前提。相反,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活动中,人们开始把自己的眼光从理想的天空收了回来,投向脚下的现实。生活的精神意义逐渐为日常活动的物质要求所取代,思想追索的道路为现实物欲的扩张所截断。综观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审美风尚,其在“世俗化”的方向上显示了:日常生活的享乐追求不仅改变了大众的文化价值理想,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审美的表现形式。检阅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文本,不难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小说叙事中,穷乡僻壤的村庄越来越遁出文学的视野,都市景观一致成为作家紧追不舍的叙述对象。在这些充满欲望化的文本叙事里,摩天高楼的街景,声色犬马的星级酒店、琳琅满目的大型购物中心成为小说人物主要活动场景,物质的诱惑不断消解人们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使人们沉浸在世俗化的物欲迷乱里。同时,这一时期的很多文学文本如“打工文学”,像《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人在东京》等,这些小说往往以“出国”、“海外发迹”为叙事编码内容,将艰苦创业的乐趣置换为个体对物质占有的现实成就感,并以此为人们提供有关“幸福生活”的世俗指南。不可否认,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们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扬弃“假大空”,无疑是一大进步。可是,人们不可能会永远满足平庸,沉潜在世俗化享乐中的人们同样也渴望崇高感的鼓舞,英雄文化的激励。文学放弃对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潜在崇高精神的挖掘,最终不仅会导致文学在世俗中越陷越深,也会导致人们在世俗中越来越随波逐流,难以超拔。
走向休闲。在以往的意识形态话语里,“休闲”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趣味和审美风尚,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根本不可能有立锥之地。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休闲”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之下,汹涌而至,一时间成为中国文化现实境况和人们日常生活最为惹眼的审美化景观。文学迎合休闲风尚,大显身手,形成了一股“休闲”文学潮流。目前流行的休闲文学文本形成这样几个类别:其一,言情和武侠类,前者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登陆,后来成蔓延之势的琼瑶、三毛、席慕容、梁凤仪以及《廊桥遗梦》之类作品为典范;后者以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小说为代表。言情武侠作品在以白领阶层为代表的读者群中常盛不衰,其特征是审美实践活动的层面突出了休闲娱乐性,并逐渐演变成一种专供人们休闲的文学作品。其二,纪实类的历史传记、人物传奇,从曾国藩、蒋介石,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宫廷内幕、政治黑幕、名人隐私等无所不包。在这类文本中,内幕和事件的神秘面纱被轻易撩开,伟人与名人的神圣性、权威性被消解殆尽,并成为普通人在休闲过程中可以任意调侃、谈论、评判的对象,至于其中所蕴含的历史观念、文化内涵绝大多数已被忽略不计。其三,以“布老虎丛书”中的《情爱画廊》、《东方迪母虎》、《渴望激情》以及田雁宁的《都市放牛》、《无法悲伤》等长篇小说为代表,同时还包括《三国演义》、《水浒》、《有话好好说》等影视剧作。它们有着一个比较混杂的文化价值和艺术形态,其休闲性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教化”与“消闲娱乐”的关系予以拨转,即突出“消闲娱乐”的功能而有意淡化、弱化“教化”的功能。“休闲”文学把所有的东西统统纳入到消费领域,突出其隐秘性、趣味性和娱乐性,文学审美的穿越性和超然性已经置之度外了。
陷于颓废。20世纪90年代躲避崇高、阉割理想、消解意义以及渴望堕落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由此,文学书写欲望、追求生理快乐的颓废风尚成为文学叙事的主体景观。特别在新生代作家朱文、韩东、刁斗、邱华栋、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文本里可以看到,他们虽然在题材的选择、创作风格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文学精神上却都不同程度地指向同一个方向——虚无。这使他们的创作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颓废的美学倾向。有人对这种美学倾向进行概括和总结,认为“后现代性的使命,它的伟大实践,就是要让身体培植快感内容,让身体从各种各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摧毁了各种各样对身体的规训机器,这包括律法、监狱、理性以及无所不在的控制性生活实践”,“身体在此则是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它活力四射,外溢莽撞,它是一架脱轨的无人驾驶的高速列车。欲望行动在本质上不是弥补性的,不是对匮乏的填充,相反,它的行动是胡作非为,它的领域是游牧,它的节奏是奔突,它的风格是革命,它的使命是解放。结果,永远流动的欲望机器冲垮了一切既定的秩序……欲望机器最终生产出欲望乌托邦,身体乌托邦,快感乌托邦”。
阅读新生代的文学文本可以发现,“性”、“欲望”成为他们小说狂欢的最为活跃能指,他们拒绝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关照性欲望的表现,而是将性欲望提高到生存本体的高度细致入微描写人的阴暗的性心理过程。朱文将写小说看作是出于“心中不曾平息的欲望”。刁斗认为:“人是一种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3]54。韩东的《为什么?》中,王一民帮朋友办事误了回家的车,朋友安排他在书房过夜,半夜里他却与朋友的妻子在书房里通奸。朱文的《我爱美元》中,“我”千方百计地满足父亲的性欲望,不惜花钱雇妓女,甚至让自己的女朋友陪父亲过夜。在这些喋喋不休的欲望叙述中,人的精神大厦彻底坍塌了,人活着除了对欲望的追逐以外,只剩下虚无在缥缈中漫游。韩东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很同意鲁羊的一个说法,他认为我们的小说就是要指向虚无。”[3]249把虚无作为小说创作的旨归完全暴露了新生代小说的精神疲软,它实质上已经远离了文学提升人的精神的神圣职责,而把它当成精神虚空中的尖利嗥叫,变成一种令人沮丧的情绪发泄。虽然新生代小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生存的尴尬和精神困境,反映了当下这种人的生存现实,但它没有找到超越这种现状的出路,是小说的外观颓废的美学形态。在颓废的审美趋向上,欲望在卫慧、棉棉的小说文本里也成了虚无的东西,她们也表现性欲望,但侧重表达的是生存的无意义和虚无的情绪,主人公完全是一些彻头彻尾的精神虚无者。卫慧的《上海宝贝》、《蝴蝶的尖叫》等作品将颓废的美学形态表达得最为完满。卫慧笔下的人物形象模式、价值取向、社会场景全部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颓废、虚无”。
很显然,以颓废为美的小说范型同样没有把人从一种精神生存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而只是展示了人的精神困窘与虚弱。许多作家都是在这种精神荒芜、物欲膨胀的现实困境中四顾彷徨,茫然无措。20世纪90年代小说整体上的价值失范、精神疲软,以及走向泛审美或者说反审美,正是这种现实的产物。
三
在文学审美伦理失据的“人文精神”溃败时代,虽然大部分作家放弃了对传统文学价值、文学精神和纯审美的坚守。纷纷走向世俗化、大众化和市场化写作,但是文学并没有整体地沉沦,在众声喧哗的文坛依然能够听到异样的、振聋发聩的、抗争的呐喊。这种关于文学精神、文学价值、文学审美的抗争一直持续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审美旨趣和精神操守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
这场持续的抗争首先发生于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面对蔚然成风的文化商业化、文人商人化、商业文化化以及商人文人化等世俗化大众文化思潮,知识分子分化为两个营垒并且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人文精神”和“世俗精神”,以及相应的两种价值取向;道德—审美主义与历史—现实主义。[4]138这次审美对抗于1993年下半年、1994年上半年开始,以上海学者为主在《上海文学》、《读书》等国内杂志上发起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种讨论直接指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初期物欲高扬、人心浮躁、精神被物化的现实。同时也对文化的商品化、文学创作中的价值漂移、作品媚俗现象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讨论牵涉的参与人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影响的声势之大都是不多见的。
现在,回过头来检视这场讨论,虽然由于“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一直没有对人文精神的概念进行界定、语义进行清理,以至使讨论始终在概念模糊、语义不清、所指滑动的知识论基础上进行,最后导致“人文精神”的讨论热闹开场,不了了之收场,但是通过这场讨论,人文知识分子面对市场语境或抗争或顺应或屈服或随波逐流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立场,却清楚地显现出来。正如陶东风所言:“‘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出场,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知识自身发展的纯自律的结果,不能只在思想史、学术史的范式内部加以解释;毋宁说它是知识分子对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分子认同危机与角色危机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回应方式。”[4]141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在社会中处于“精神牧师”地位,他们自己也以启蒙领袖、生活导师自居。然而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浪潮使得知识分子由中心被抛向了边缘。从官方到民间似乎不再需要什么启蒙领袖、生活导师,那些充满超越精神、惯于编织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至上神话的人文知识分子,一时不知所措。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人文精神”话题的提出,不仅是人文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边缘化处境的一种无奈与反思,也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理想被消解,英雄被驱逐,文化审美价值被迫发生偏离的焦虑与抗争。
面对文学审美伦理的失据与精神的流失,一些传统作家诸如张承志、张炜、梁晓声、史铁生等,不仅参与了激烈的“人文精神”理论呐喊,而且还以特立独行的写作实绩进行审美反抗。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张承志和张炜特别是张承志就以决绝激烈的文化姿态对作家拥抱流俗、投身市场化写作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93年,张承志在他著名的《清洁的精神》一文中,抗议“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通过古代许由等人追求正义和清洁的故事,追寻“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在《无援的思想》里,他针对“文学界……一天天推广着一种即使当亡国奴也先乐喝乐喝的哲学”的现象,呼唤“今天需要抗战的文学。需要指出危机和揭破危机。需要自尊和高贵的文学”[5]。为了便于表达自己批判的思想,他以鲁迅为师选择了灵活自由的散文文体。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篇篇像标枪、匕首的散文里,以愤怒、刚烈甚至偏激和极端的方式,对道德滑坡、人心不古、文学溃败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进行了无穷的揭露与批判。朱苏进在《分享张承志》一文中描述张承志的这种创作风格时说:“他的许多篇章既是猛药又是美文,在新奇意境和铿锵乐感中簇拥着采自大地的野草般思想。他的作品个性极度张扬,锋是锋,刃是刃,经常戳得人心灵不宁,痛字当头,快在其中。”
张炜在《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中,这样痛心疾首地批判文学精神与价值的沉没,他说:“文学已经进入了普遍操作的状态,一会儿筐满仓盈,就是不包含一滴血泪心汁。完全专业化了,匠人成了榜样,连血气方刚的少年也有滋有味地咀嚼起酸腐。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必然枯萎,它的制品——垃圾——包装得再好也仍然只是垃圾”,并发出强烈的呼吁“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你还要忍受多久?”“我不单是痴迷你的吟哦,我还要与你同行。”[6]
在对文学理想和文学价值的坚守中,梁晓声也是一个个性坚定、立场鲜明的作家。他一方面在小说创作中关注商品大潮“吃人”的悲剧(《翟子卿》、《激杀》),一方面写下了一部又一部激烈批判现实问题的长篇“杂感”。在《龙年一九八八》中,他为“社会本身已变得厚颜无耻甚至下流”、“种种不平等现象呈现出咄咄逼人的狰狞。民心崩散宛如沙器成沙”而愤怒,为“自我正在死亡”而悲叹。在《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中声明:“我是一个一贯坚持写现实的作家——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现实主义——而是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坚持反映最广大的恶,被叫做‘老百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家。”[7]针对文化的倒置现象,诸如成熟对浅薄媚俗,思考对时髦媚俗,文化品格对市侩哲学媚俗,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对玩世不恭的街头痞子的“理论”媚俗等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
在20世纪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面对信仰迷失、文学落败的精神危机,史铁生虽然也是“抵抗投降”者行列中的一员,但是史铁生的反抗同张承志、张炜、梁晓声等人的激烈、决绝、极端的姿态相比,却是截然不同的。他与张承志等人同样至今仍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与前者相左的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不再以群体为本位,而代之以明确的个人立场;生命的意义不再与历史的或形而上的终极目标发生关联,而是对虚无困境的战胜和超越,他的理想主义也不再是咄咄逼人的,侵略性的,而是温和的,宽容的,充满爱心的。这些价值追求和审美旨趣沉潜于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文学文本里,比如在享有盛誉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中,作家完全回绝了声色犬马世俗社会的渗透、侵扰和包围,以一颗宁静、安详、超越的心,沉醉在对生命、理想、价值等的沉思以及不懈地探求里。在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视阈里,它以虚无为背景,又超越了虚无,它是人生悲剧中的微笑,荒谬命运中的浪漫,俗世社会中的精神乌托邦。史铁生的精神审美抗争充满着富有时代气息的建设性。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群体的纷纷“触电”蔚然成为一种醒目的文化景观。这也成为人们普遍认定作家全面放弃文化抵抗,走向市场化、世俗化的重要依据,从而进一步认定,就是这种文化行为导致了文学精神丧失和文学审美伦理的失据。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审视作家“触电”现象,人们可以客观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视觉文化的传媒时代,作家“触电”与其说是一种放弃抵抗的消极文化逃避,不如说是一种积极抗争的“迂回”文化策略。如果说张承志、张炜、梁晓声、史铁生们的文学抗争,采取的是一种与世俗化、大众化和市场化写作“断裂”的决绝态度,那么,在生存压力驱使和市场欲望引诱下进行“触电”写作的作家,他们却是以“合作”的姿态,“曲线”地与大众文化进行审美对抗。
的确,在传媒成为话语霸权的时代,电视、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了解世界以及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孔道,相反,文学阅读已经变成一种十分稀罕的文化消费行为。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作家“触电”也许起初是经济利益的吸引,可是到了后来,不能不说“触电”已经成为一部分作家拯救文学的理性自觉。正如作家刘恒所言:“数码时代把信息压缩之后在更短的时间里传递更大量的信息,现在信息传输太方便……文学只是信息传输当中的一个小的分支。这个分支如果你不常去利用它,或者接受你这个分支去获取信息的话,你这个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就像你老不用腿走路,它自然肌肉就会慢慢萎缩。”[8]。作家“触电”就是利用现代传媒扩大文学的影响力。确然一部影视剧热播可以引发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学阅读,作家有理由认为,在广告开拓市场的商业社会里,影视剧就是文学阅读的广告,既然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商品,通过影视剧的“广告效应”深度宣传相应的文学文本,就像商品通过广告扩大市场份额一样,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不可否认,有一部分“触电”作家完全放弃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彻底走向市场、走向媚俗。可是,还有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们“触电”主要是在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后,以便可以自己腾出时间,积蓄精力从事纯粹的文学写作。比如万方,虽然从事电视剧本的写作,但是对小说创作始终耿耿于怀:“虽然写电视剧也是一种创作,也可以把你的想法融到故事里,但电视剧毕竟还是商业产品,一个作家如果总在忙于创作电视剧,这种状态肯定是不对的。我希望把手头的两部电视剧写完之后,就好好写小说,我的心里其实始终在酝酿小说的写作。在我心中小说的位置还是要更重要些。”[9]再如作家北村自从《周渔的火车》“触电”红火之后,同名小说也跟着火起来,北村感言,很多小说是靠电影红火起来的,拍成电影,小说就好卖。现在的北村一年用三个月的时间来写剧本,剩下的时间来创作小说。
同时,大批优秀的作家纷纷加入影视编剧和导演的行列,从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影视剧的美学品质。比如,刘恒、刘毅然、周梅森、柳建伟、朱文等作家不仅从事影视编剧,还当了导演。像自我定位为作家的周梅森,从最初卖自己小说版权,到后来担任编剧,直到之后做了电视剧的制片人,他认为,只要市场需要、观众需要,作家“触电”是有益的,这么多作家进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中,对于中国电视剧文化水准的提升也有促进作用。[9]
人们还发现,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坚持的文学精神与价值,在影视剧里同样得到了承续和坚守。许多作家“触电”还是由于一份责任,一种与国家和百姓息息相关的使命感。著名作家张平推出了《天网》、《生死抉择》等反腐倡廉题材的影视力作,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在拍摄过程中,威胁和恐吓时时都在发生。此时,名与利在作家的心目中已经很淡了,而跳跃心头的是为百姓执言的信念,为正义呼喊的勇气。创作电视剧《黑兵》、《黑洞》、《黑雾》三部曲的作家张成功说:“在写作过程中,黑势力不断向我发出威胁,有关部门不得不派出刑警保护我的安全。正是在这一刻,我对黑势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渴求有了更刻骨铭心的理解。一种巨大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便油然而生了……”[10]
可见,在视觉文化时代,作家“触电”已经逐渐从无奈无为的精神放逐里,开始走向积极有为的文化自觉。面对影视叙事的泛审美性,作家也从开始的屈从,后来逐步显现出审美建构的主动,文学叙事的一些积极因子已经融入影视叙事的逻辑里,文学精神、文学的社会承担以及文学的批判理性也开始在影视里挺直了脊梁,文学审美的抗争姿态卓然由面影模糊的状态日益呈现出清晰与明朗的精神轮廓。
标签:文学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美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张承志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