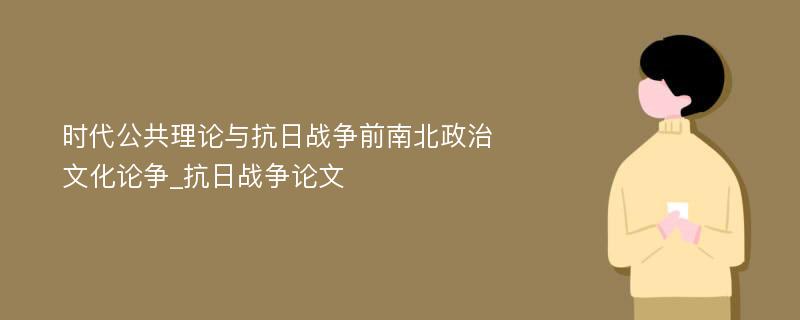
《时代公论》与抗战前南北政治文化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论论文,政治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3-0080-08
“九·一八”之后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学者纷纷公开对中国的政治前途与命运发表看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北方的《独立评论》,多年来学者对此有极大的关注,而对于南方的《时代公论》却鲜有论及①。本文选取《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的论战为切入点,具体分析20世纪30年代南北政治文化的地缘与派分,并试图分析30年代民族主义与权威主义、自由主义的微妙关系。
1932年4月1日《时代公论》杂志在中央大学创办,由杨公达任主编、张其昀为总发行人。《时代公论》社的主要组成人员是以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并且多是国民党党员教授,有着非常明显的政党背景②,核心成员有杭立武(政治系主任)、梅思平、萨孟武、张其昀等。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不久受聘北大)、武育干、傅筑夫、楼桐生、雷震、何浩若、田炯锦等均是其重要成员。这份以政论为主的杂志,是“九·一八”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状况之下,一批体制内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激情的产物。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当下关日本兵舰开炮以后,不特是普通一般逃之夭夭(要人们早已到洛阳去了),就是惯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也就溜烟离开了此间,顿时南京变成了死城,我们学校——中央大学——也就人烟稀少今昔之感了!《时代公论》就是在南京最冷落萧条的一个时期,几个朋友触景生情,像雪中送炭似的,把这个刊物贡献给全国人民。真如古人所说‘穷而后工’,我们在极穷困的时候毅然起来工作的。”③这份杂志的宗旨是“供国人以发表自由思想之机会”,其落脚点在于“俾于国事稍有贡献”,可见是一个时事政论的刊物。之所以定名为“时代公论”,张其昀的解释是:“时代公论公器也,大学教授之公开讲座也。大学既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大学教授所发表的言论,自不受任何政党的约束,即在同一刊物之中两相反对之论调,苟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皆不妨同时并存,而一任读者之比较与选择:此其所以名为公论也。”④可见,这份杂志定位为大学教授的公开讲座,选取时代敏感的话题,对国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以自由讨论的方式来吸引社会民众的参与。
同时,这份杂志也是一份带有浓厚学术讨论性质的刊物,其主要成员均是中国政治学会的骨干。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学术成长过程中的高速发展时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内的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成立。1931年夏,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杭立武、陶希圣、吴颂皋、刘师舜、梅思平、杨公达等一批教授,有意成立政治学的学术团体,于第二年三月开始运作。其公开的目的有三:一是促进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二是讨论现实政治的改良;三是指导后学从事研究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北平,中央大学政治学的一批教授执意在南京成立此学会,当有与北方争锋的意味,稍后北方亦成立中国政治学会可印证这一点。据中国政治学会的发起人之一、第一届干事长杭立武后来回忆,为了能在南京成立中国政治学会,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有意联络南方其他各城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知名政治学者,如周鲠生、王世杰、张奚若、钱端升等,期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让中大教授感到“意料之外”的是,这些学者十分爽快地表示同意,于是中国政治学会于1932年9在南京正式成立。“为借重各方面人才,以便于协调起见”,选举校外的王世杰、周鲠生等人为学会的常务理事,而总干事长由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杭立武来担任⑥。
《时代公论》的出台也是中国政治学会为实现其“讨论现实政治之改良”而创办的。创办之初作者群甚为广泛,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还有文学院教授缪凤林、黄侃、汪东,教育学院程其保,工学院顾毓秀等,这些文章基本是有关中央大学的教育问题,是纯粹的学术文章,如汪辟疆的《论近代诗》(10号)、黄侃的《汉唐玄学论》(11号)等。但随着《时代公论》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与北方的《独立评论》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使其他院系的学者逐渐淡出这份杂志,1933年后就很难发现其他院系学者在上面发表文章。稍后,以文学院为主的人文学者转移到由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倪尚达创办的《国风半月刊》杂志上了,《时代公论》进一步演变成一纯粹的时事政论期刊。
1932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权得到巩固,有着强烈政治背景色彩的《时代公论》出台,其主要的宗旨就是鼓吹独裁。这一杂志与北方自由主义派胡适、任鸿隽、丁文江等创办的《独立评论》针锋相对,成为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南方阵线的主力,《时代公论》社成员也被胡适等人讥为“政府派”的人。故而讨论《时代公论》阵营的言论,离不开与北方《独立评论》的论战,这不仅有助于把握位于首都的中央大学这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而且也有助于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地图的分布。
《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的论战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有关宪政问题
南北学术界之争的焦点在是否立即实行宪政和怎样实行宪政。
“九·一八”以后,中国民间社会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宪政的诉求日益高涨。作为政治评论的刊物自然不能回避这一敏感问题。《时代公论》同仁的总体主张是赞同放弃党治,但反对立即制宪和实行宪政。就其内部而言,对于实施宪政的途径又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渐进方式实现,代表人物有杨公达、梅思平。一派认为国民代表大会与训政相矛盾,反对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人物有萨孟武、何浩若、雷震等。
杨公达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宪政和民主,“我们对于开放党禁,绝对赞同,但对于立刻实现欧美式的宪政,则未能与反对党治的诸君纯然一致”。他主张:“国民党最好是将党治的权,交一部分出来,让与亟待召集的国民代表会,使这个代表法治主义的机关,与代表党治主义的国民党,互相调和,互相控制,浸假而初具民治的规模,渐进而入平民政治的坦途。”⑦这是一种典型的折衷主义方案。由于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目中无人,以为负国之责者,舍我其谁,又谁能有魄力,代替我的党治?党外的人,却目中有人,视国民党的党治为眼中钉,非去之而不可”。因此杨认为解决的方案是:“党治之外,应该设立一民意代表机关,来监督党治”,“这个民意机关——即我们屡次所说的国民代表大会,——是有二重使命的:一方面,表明民权实施的开始,养成民主的势力;他方面,集中全国人才,调和各党各派的争权的哄斗。”⑧梅思平也同样主张在不改变党治的前提之下,划出一部分权力交与国民代表大会,即“党治的方式尽可不必变更,不过将党对政府的指挥权划出一部分来,受国民直接监督”⑨。其后他进一步认为:“对于立即制宪这个主张,我也是实在不敢苟同……我总以为民主政治的进步,决不宜过于急促。我们总要脚踏实地的前进,万不可跑得太快,跌了一个跟斗。”⑩
与杨、梅的主张相对,萨孟武认为国民代表大会与训政是冲突的,其根源就在于“民意”与“党意”的冲突导致“民治”与“党治”的冲突,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国民政府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行政院院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若干人,由国民代表会选举,这样一来就可以确保“党治”的实现(11)。何浩若认为在现在的民生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谈论国民代表大会等民主是无益的,“国民代表大会是实现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而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便是保护有产阶级而压迫贫苦民众的政治。因此我说国民代表大会从中国大多数的贫苦民众看起来,可以说是绝对不关重要”(12)。中央大学兼任教授、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委员、书记长雷震也同样认为:“党治与国民代表会两者,正犹如水火不能相容,如果要实行国民代表大会,自非取消党治不可,如不放弃党治仍旧实行训政,则不能够谈国民代表大会,若谓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实不啻‘三教同源’一类主张耳。”(13)
杨公达、梅思平等的宪政主张遭到北方学者胡适、蒋廷黻的有力反驳,使得南方的学者们明显感觉到“北方的诸位先生,总觉得这次宪政运动,是被我们这班人开了一个大放盘,把他弄坏了”(14)。若单从学术上讲,这只是一场学理之争,但当时正值国民党鼓吹由训政到宪政过渡,正在草拟宪法,因此这一问题的讨论有着很强的现实政治背景。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是中国民主自由的实现,而杨公达、梅思平等关心的是国民党在中国统治的真正实现。杨、梅的主张不仅遭到纯粹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也为国民党内的一批“坚定”分子所不满,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处境让他们备感委屈,正如梅思平所言:“我和几个与我抱同一意见的朋友,关于宪政问题的主张,已经走到被夹击的路上去了。党内的‘忠实同志’们声声口口说我们是背叛总理遗教,是迎合舆论,是投机。党外的宪政论者又说我们的办法不彻底,是移花接木之计,是政府派的调和论。”(15)这种两边都不讨好的处境,或许也正是《时代公论》社的特色,因为从本质上而言他们是与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但在姿态上又表现出学理上的批评架式,其结果,也只落得朝野两边均不满的下场。
(二)有关民主与独裁问题
20世纪30年代之初,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展开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作为中央大学政治立场代表的《时代公论》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公开鼓吹在中国实行独裁,推行法西斯主义。所谓法西斯主义,按照其起源地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时代的百科全书的解释为:“法西斯为积极确定的主义,为政府与祖国的较高利益计,而企图发挥纪律与个人行动,此二者均系代表实际之道德性,而以能继续进步为条件,政府或民族之停滞不进,即为灭亡之朕兆,凡一政府不仅以能施行权力为满足,且须证明在其生存之中具有精神的力量。”(16)法西斯主义在30年代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大政治思潮,对于中国的学界影响颇深(17)。《时代公论》社的一批政治学教授,也及时地以法西斯主义为理论武器来分析中国当时的政治,这方面的主力是杨公达。杨的立论是从国民党内部组织的分析开始,他对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涣散非常不满,半年之内先后发表六篇专门讨论国民党危机的文章——《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4号)、《再论国民党的危机与出路》(7号)、《三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11号)、《关于党部组织的简单化》(13号)、《国民党复兴论》(16号)、《革命的回忆与国民党的复兴》(23号),分析国民党危机的原因,寻找国民党复兴的出路。他认为造成国民党危机的三个错误是:“第一个错误,便是居革命党之名,行普通党之实。第二个错误,便是粉饰党的统一,拒不分家。第三个错误,便是党不自裁,而由他人裁之,责不自负,而由不负责者负之。”(18)对如何挽救国民党的危机,他提出三点建议——“党政思想化、党员职业化、党部要简单化”(19),其重点在于从组织入手改造国民党,具体办法为:“立刻整顿党部组织,立刻造成党部的干部,立刻恢复党部总理制。”(20)这一改革的首要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真正完成国民党的统一工作。不过统一国民党只是其政治纲领的第一步,最终的目的就是以法西斯主义来实现全面独裁。
杨公达在提出国民党统一论之后,又全面提出他的完整独裁论政纲。这方面的主要文章有《国难政府的强力化》(24号)、《九一八以来的中国政治》(25号),其中心就是鼓吹专制独裁。他提出国民党的统一有渐进方法和非常手段两种方式,他认为渐进方法收效迟缓,因而主张以“非常手段”来统一国民党,即“或者国民党现存派别中,有一派能以统一党权为己任,本大无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艰险,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斯基,孟梭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己的派别,举一纲而打尽之,国民党由此而可以统一。此方法收效极为迅速。”(21)杨公达随后又进一步将“非常手段”扩充到政府及国家体制上,主张取消五院制,改用元首制,并且公开提出:“元首的条件不要什么‘年高德劭’,要具有忠诚信义,尤其要绝对负责。不特要负兴国的责任,还须要负亡国的责任;不特要做岳武穆,还须要做李鸿章;不特要下流芳百世的决心,还须要立遗臭万年的遗嘱。”(22)这实质是公开鼓吹和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文章最后又宣告他对于“精诚团结”的不相信,提出“与其多方面的组织政府,不如一方面的组织政府”。其理由是“如果是清一色的政府的话,则亡国兴国,责皆由负,良心所在,能不努力?”(23)
杨公达的法西斯主义主张在中央大学内部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与《时代公论》的独裁论互相声援的,还有中央大学的《新文化》月刊社、《教育与中国》杂志社等社团,《新文化》月刊曾刊登一篇文章,从西方法西斯的起源、定义和纲领来论证法西斯主义对中国的作用,作者强调法西斯的纲领不外两种:一种主张一党专政,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一种承认公共利益超越个人利益,反对阶级斗争。在行动方面作者主张以力还力的直接行动,认为这种主张对于中国革命的复兴是切实有效的手段,因而其结论是:“现在要复兴中华民族,先要发展中国革命之复兴行动,养成一种守纪律、负责任的新风气,造成一个组织健全、力量充实的革命党,在一个为民族牺牲的领袖下面,毫不迟疑的排除一切恶化思想,事事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努力关于中国革命的复兴运动,必能一步一步地成功!”(24)由教育学院教授组成的社团《教育与中国》杂志则从教育学的方法论上,来说明法西斯主义的教育的实现与中国的民族复兴之间的紧密关系(25)。
杨公达所主张组织的一个清一色的政府,即要由国民政府中最有力的一派来主政,而放逐其他派别。这一主张遭到当时刚由中央大学改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陶希圣尖锐批评,他认为这是“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目前社会上的论争,正集中到国民政权的取得和运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于国民党过去几年党治和训政方法不能集中民力以救危亡。现在的问题不是在国民党各派团结或互相残杀,而是在国民党各派即令团结仍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杨先生把问题移到国民党党内纷争,并且把眼光缩小到一派上去,完全是不了解国民党的现状,不能了解国民党的要求。这种论调也只是住在勾心斗角的南京的人会发出”(26)。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短短半年时间里(1932年4月到10月),陶希圣从南京到北平,也从《时代公论》重要成员一变为与《独立评论》同调的同仁。对这一变化,他似乎归结为地域的因素,根据他的观察,杨的论调只有“勾心斗角的南京的人”才会发出,换言之,北平或其他地方的学者是不会有此言论的。显然,陶希圣看到了地域政治对于思想的影响力,他的这一观察对于我们今天把握《时代公论》社为什么会是在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出现,而不是其他地方的大学,无疑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北方的自由派学者对国民党已经非常失望,认为杨的文章也只是关注了派系之间的勾心斗角而已。同样,胡适读到杨公达文章后的反应是“这番话出于国民党中的一个学者的笔下,很可以使我们诧异。”他的批评虽很平和,诸如“这些话都是很明显的主张,表示出一些人,在这个烦闷的政局之下因忍耐不住而想求一条‘收效极为迅速’的捷径,这种心理虽学者也不能免,这是我们很感觉惋惜的。”(27)虽然多少对杨公达等有理解的成分,但在政治原则方面,胡适对杨的独裁主张却加以严厉地批评。
(三)有关国民党的抗日政策
杨公达在励志社的演讲中,提出抗日的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要安内,安内首先就是剿匪,若是共匪不清,一旦举办讨逆,兵没到北平,恐怕长江流域已经失守了。第二个先决问题,是改革现在的政府,我们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28)这与当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调同出一辙。北方的《独立评论》派对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的政策则公开批评,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丁文江的系列言论可作为代表。其一,丁文江认为所谓的“共产党”问题实质上是政府造成的,“无疑的,共产党是贪污苛政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29)。其二,丁文江主张从尊重人民自由的立场出发,共产党也应享受同等的自由,“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我们的要求是绝对的,是普遍的,例如我们以为在不扰乱地方秩序,可不违犯其他刑法规定范围以内,共产党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其三,不妨让共产主义在中国进行实验,“只要共产党肯放弃他攻城略地的政策,我们不妨让他们占据一部分土地,做他共产主义的实验!”(30)虽然丁文江等人的抗日主张还是从政府的角度立论,而且对于共产党的同情也不是没有前提条件的,但其主张还是从民族大义出发,这是值得肯定的。
丁文江对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从“九·一八”以后到1933年初,日本之所以能步步进逼,先后占领了东三省、热河,并直接威胁到平津,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日本的强大,而在于当东北马占山、苏炳文等义勇军英勇反抗时,军事当局没有向热河进兵,这是很大的失策,“到了今天,若是依然以苟安为目的,这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31)。丁文江在论证日本侵略中国既定方针的同时,强调中国只有以自己的牺牲和抵抗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援助。丁文江对中国的抗战策略提出了三条办法:第一,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相不攻击。以上三点办法,尤其是第三条办法,可说是公开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当然他仍对蒋寄予厚望,并解释说:“国家当然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国家,抵抗也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工作,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因为地位的关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为重大,谁也不能还有否认。”(32)
但丁文江的解释却并没有得到《时代公论》杂志社的谅解,该杂志当即发表一篇题为《真蒋介石与假蒋介石》的文章针锋相对,对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大不以为然,开篇即对丁本人的动机进行攻击:“为政要防止蒋介石独裁,临难则不容蒋介石苟免,此非一般包藏祸心仇视政府之流的共通要求,也是他们的矛盾主张……愤慨之极,竟自告奋勇,在《独立评论》上大吹大擂……”(33)言语之中不乏人身攻击。在讽刺丁的同时,却为蒋的地位鼓吹一番,称:“不过象丁先生这样一位命世大才,必须假蒋介石之名以自命,窃蒋介石之位以自居以后,方足以谈抗日,方足以谈救国,方足以号召国人,不啻可以承认今日抗日救国的重任,非但必须蒋介石其人,并且还要蒋介石其名者,才能担负得起。”(34)当然文章的重点在回应丁文江的抗日三个方法上,但也无一处不是为蒋介石的政策进行辩护和对蒋本人的吹捧。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的开头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编者按:“这篇文章搁置了好久,都未发表,因为恐怕一经发表,又有人硬指本刊是‘蒋介石的机关报’!况且在国难日亟的当前,‘个人问题’实无一谈的价值。但是我人反复考虑之后,觉得现在抗日既要蒋介石氏做头脑,而同时还有人拿蒋介石氏个人做攻击对象,是非不明,不特有伤政治道德,亦且有碍抗日的前途。故不怕负‘替个人辩护’的恶名,把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出来。”(35)这种先发制人的自我辩护,显然只能增加此地无银之嫌,再次表明《时代公论》的政治立场。
中央大学杨公达、张其昀、萨孟武、何浩若、梅思平等国民党党籍或亲国民党的学者创办《时代公论》周刊,一开始就站在国民党体制内的立场,从批评国民党与政府的角度立论,一时颇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南京当地的一家销售该刊的书店门前打出了这样的广告——“请看铁面无私的《时代公论》!”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时代公论》的发行量就突破一万份,这让这份杂志的编辑者大感欣慰。但从其创刊之初,就有读者怀疑其背后有“背景”,因而当时编者以“因为我们这般书呆子,个性很强,是不适宜有背景的”加以否认(36)。表面上看《时代公论》是从对政府的批评入手,但其用意却可套用这样一句话——小骂大帮忙(37)。
事实上,南方中央大学的政治学者以《时代公论》为阵地宣扬权威主义,极大地迎合了蒋介石“一党独裁”的需要,他们也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重用。杨公达一年后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从坐而论道转到直接进入到国民党政权高层。张其昀等也学而优则仕,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这些也为当时和后来的学者所诟病。据30年代就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郭廷以先生回忆:“待遇提高,中大教员都是规规矩矩的教书,但论研究精神则略有欠缺,这是因为课多而且接近政府的缘故,许多教员混资格‘做官’去了,所以赶不上清华,清华安定、条件好。周炳琳就说过:‘中大是不错,但好像是缺少点什么,研究风气不盛。’”(38)这些似乎与《时代公论》的过高参政热情是分不开的。
《独立评论》则是站在政府之外的立场,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出路进行一系列的建言献策,而《时代公论》却更多地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立论。需特别指出的是,《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一样,随着论战的深入发展,各自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南北政治立场对立的状况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甚至双方后来也呈现互相靠拢的趋势,如对于建立集权制政府的论证等。这些情况表明过分强调双方的对立立场,而忽视彼此的交流与互动,可能离事实的真相愈远。
从本质上而言,《独立评论》和《时代公论》的政争,表现出民族主义高涨时代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竞争,集中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与民族主义紧紧相连的权威主义得到更大发展的空间,而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最终的结果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让位于权威主义。二者之间的论战并非是不可调和的,随着《独立评论》在政治上的态度最终向国民党倾斜,说明自由主义学者在处理民族与民主关系的两难境地时,最终艰难地选择民族利益至上,不得不暂时放弃民主和自由的主张。这也说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历史境遇和两难境地。而权威主义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正好利用民族矛盾激化的有利机缘,拓展民族意志与力量的巨大道义空间。这种政治的权威主义不仅迎合了当局政治统一的需要,也符合知识分子选择威权主义来加强民族力量的情感需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势力大增,成为战前最为有力量的一股思潮。
从根本上而言,《时代公论》的政治学术评论是将民族主义与功利主义结合起来的研究,结果无非只有一个——为政治寻求合法性的说明。有研究者对中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这种状况进行评论时说:“到3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等院校变成了民族主义学者的天下,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观自然也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样,功利主义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为当时政权的统治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39)30年代中央大学的《时代公论》的学者尝试将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就其当时效果而言,政治当局也多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似乎也多少实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同时他们也因“学而优则仕”,开始从书斋进入权力核心。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将大学与政治之间联结得过于紧密的关系,对中央大学的学术研究无疑是一种损害,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在研究官僚知识分子时所指出的一样:“把追求知识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是成了相当恶劣的政客或不再是一名学者。”(40)
注释:
①早在70年代末台湾学者邵铭煌就从学人群体的角度对《独立评论》进行了研究,见其《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79年)。近年来对近代自由主义者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的研究均涉及到《独立评论》,如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等研究。最近的研究详见张太原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与对《独立评论》研究的热潮相较,对《时代公论》的研究目前仅见邓丽兰所著《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一书的第四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论者多从政制设计的角度来立论。
②关于杨公达创办《时代公论》时是否是国民党党员,有研究者不能肯定,王奇生教授从杨一年后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推测,杨此时应归属于体制内知识分子之列。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笔者发现,杨公达1932年6月在力行社演讲《国民党复兴论》中提到:“同志们抬起头来,恢复党国的威信!不要因为人家咒骂国民党而害羞而灰色。”(演讲词刊于《时代公论》第16号,1932年7月15日)从视力行社为同志的语气中不难判断杨公达此时也为国民党的一员。同样,胡适读到杨公达的一些文章后,其评论说“这番话出于国民党中的一个学者的笔下,很可以使我们诧异”,也可以推断杨此时已为国民党党员(《陶希圣〈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附记》,《独立评论》第20号,1932年10月2日)。
③《〈时代公论〉是“铁面无私”吗?》,《时代公论》第10号(1932年6月3日)。
④这是张其昀给读者陈豪楚的回信,见《读了时代公论之后》,《时代公论》第8号(1932年5月20日)。
⑤杭立武:《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刍言》,《时代公论》第23号(1932年11月4日)。
⑥《杭立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0页。杭立武对于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时的第一届理事回忆与当时发表的理事人选有出入。据当时发表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刍言》所载,当选理事为七人,分别是周鲠生、高一涵、张奚若、梅思平、萧公权、刘师舜和杭立武(《时代公论》第23号,第15页)。而六七十年后杭立武回忆认为当选的理事为五人,分别是周鲠生、浦薛凤、钱端升、王世杰和杭立武(见《杭立武先生访问纪录》,第10页),后者疑有误。
⑦杨公达:《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时代公论》创刊号(1932年4月1日)。
⑧杨公达:《折衷主义与中国政治》,《时代公论》第3号(1932年5月15日)。
⑨梅思平:《党治问题平议》,《时代公论》创刊号(1932年4月1日)。
⑩梅思平:《宪政问题答客难——答蒋廷黻胡适之二先生》,《时代公论》第11号(1932年6月10日)。
(11)萨孟武:《怎样解决国民代表大会与训政的矛盾》,《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12)何浩若:《不关重要的国民代表大会》,《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13)雷震:《两不讨好的国民代表会》,《时代公论》第8号(1932年5月20日)。
(14)(15)梅思平:《宪政问题答客难——答蒋廷黻胡适之二先生》,《时代公论》第11号(1932年6月10日)。
(16)转引自子嘉:《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新文化》第2卷2、3合期(1935年3月25日)。
(17)对中国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最新研究,参见台湾青年学者冯启宏的《法西斯主义与三○年代中国政治》,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1998年。
(18)杨公达:《国民党复兴论》,《时代公论》第16号(1932年7月15日)。
(19)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号(1932月22日)。
(20)杨公达:《三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11号(1932年6月10日)。
(21)杨公达:《革命的回忆与国民党的复兴》,《时代公论》第23号(1932年9月2日)。
(22)杨公达:《国难政府应强力化》,《时代公论》第24号(1932年9月9日)。
(23)杨公达:《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政治》,《时代公论》第25号(1932年9月16日)。
(24)子嘉:《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新文化》第2卷第2、3合期(1935年3月25日)。
(25)如方东澄的《法西斯蒂的教育》和環家珍的《我国教育改造与民族复兴》,分别载于《教育与中国》第1卷第1期和第3期(1933年)。
(26)陶希圣:《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评时代公论杨公达先生的主张》,《独立评论》第20号(1932年10月2日)。
(27)胡适:《陶希圣〈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附记》,《独立评论》第20号(1932年10月2日)。
(28)杨公达:《抗日的途径》,《时代公论》第27号(1932年9月30日)。
(29)丁文江:《所谓剿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5月26日)。
(30)丁文江:《停止内战的运动》,《独立评论》第25号(1932年11月6日)。
(31)(32)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3月15日)。
(33)陶彬:《真蒋介石与假蒋介石》,《时代公论》第49号(1933年3月3日)。
(34)陶彬:《真蒋介石与假蒋介石》,《时代公论》第49号(1933年3月3日)。
(35)《真蒋介石与假蒋介石》“编者按语”,《时代公论》第49号(1933年3月3日)。
(36)《〈时代公论〉是“铁面无私”吗?》,《时代公论》第10号(1932年6月3日)。
(37)这句话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群体对《大公报》的一个基本评论,但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见贾晓慧:《大公报新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38)《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98-199页。
(39)[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40)[美]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51页。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丁文江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梅思平论文; 丁文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