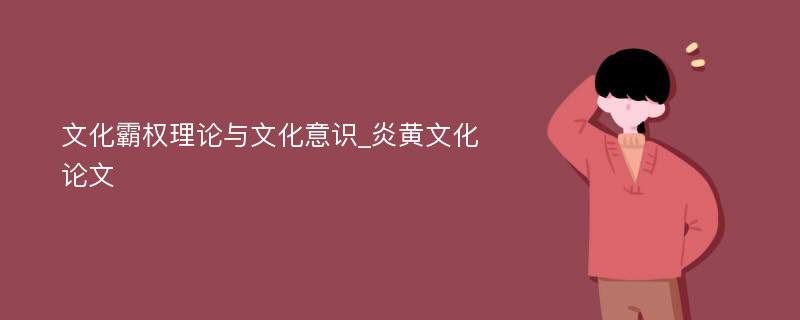
文化霸权理论与文化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霸权论文,自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帝国理论及其发展
2000年出版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由内格利(Antonio Negri,意大利
Padua大学政治学教授,“红色旅”的成员。1979年以恐怖组织领导人之名被捕,1983 年当选激进党国会议员获释,在法国流亡14年,回国后被捕至今)和哈特(Michael
Hardt,Duke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合写。其基本观点是:
“就在我们眼前,帝国正在生长、成形。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化政治新 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帝国是一个中心消解的、无边界的庞大体系,文 化与经济始终处于畅通的流动贯通状态。它没有内外的区隔,在无所不在的虚拟空间操 作,不再以民族国家的国界为区分。统治人类的重任落到超国家的帝国体制的肩上。
“新帝国”的形成是欧洲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型:“旧帝国”有明显的疆土界限,“ 新帝国”不是由疆界而是由多层次网络所构成,它没有界限,可以无限扩大;“旧帝国 ”把殖民地纳入主权范围,实行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有形统治,有明显的侵略性和对他种 文化的毁灭性,“新帝国”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不断更新调整,于无形中进行控制;“ 旧帝国”进行地区性管制和垄断,“新帝国”所控制的生产力没有场域,新技术很快普 及全球,组成网络,只有“帝国”可以掌握全局。“旧帝国”必然制造种族差异,以便 分而治之,“新帝国”通过网络统治,可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
总之,新的“帝国”不是列宁说的寡头的资本主义垂死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复兴,是“超越国界、超越多国协商的惟一的主权”。美国不少人相信可以实施一种“ 温和的帝国主义”,公平管理全世界事务,惩恶扬善。在帝国统治下,工农、体脑、城 乡的差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甚至相信,新的“帝国”使世界连成一气,它将管理 全世界并带来和平,同时,也将弱势群体连成一体,成为制约“帝国”的主体。
然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出版后,“帝国论”又进一步发展为新的 霸权理论。他们认为国际当权者不应再力图维护现存体系,而应从现存体制的解体中得 到最大利益。
2002年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森教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 求权利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分别担任布莱尔和克林顿顾问的玻比次和库泊提出民族国家已变为市场国家,它对内 不再承担公共福利,只提供法律和机会,让公民到市场去寻求利益,对外则通过一切手 段保证其制度在一切地方推行。他们不断推出所谓“新帝国主义”,意思就是由后现代 国家动用其国家力量以控制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制止前现代国 家的互相屠杀。
以拉姆斯菲尔得、切尼、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21世纪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更是提出三项 核心内容:1、极度崇尚军力;2、主张建立美国的“全球性仁慈霸权”;3、强调输出 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他们都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并非建立在均势而是在美国霸权的 基础之上,对美国霸权的任何削弱都会导致其他国家更大程度地按照自身的需要来塑造 他们的世界。他们认为中国、俄罗斯等国如果获得机会,就会塑造一个与目前大相径庭 的国际体系。因此,必须防止在欧洲、东亚和中东出现威胁其领导地位的地区性强国。
克里斯托尔、卡根等人所著《美国新世纪计划》,更是提出中心在于维持一个“单极 的21世纪”。必须“阻止新的大国竞争者出现”,“控制关键地区(欧洲、东亚、中东) ”,“积极推动美国军队和战争的转型”,“控制网络空间和太空的主导权”,“在全 球推行自由民主原则”。总之,“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的无可匹敌的超强 地位的基础上”。他们的新帝国大战略就是先发制人,以假想敌为攻击对象,重新确定 “主权”的含义,主权有限论,轻视和改写国际准则,提倡所谓“后民族时代”的到来 。显而易见,这些并非多数的后现代帝国主义者就是不惜以世界性的血腥屠杀来维持其 单一霸权。
与帝国一元论相抗衡的一些新趋势
“新帝国理论”的出现和伊拉克战争使人们不能不对当前的世界形势进行深刻的思考 。大约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最值得关注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注 :莫兰著有《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方法:思想观念》、《复杂思维:自觉的科 学》等,最近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 世界?”见《跨文化对话》第13期,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9·11”事件后,在法国 里尔世界公民大会上提出的报告“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首先 ,他提出了“两个全球化”的主张,认为90年代的全球化在推动技术经济全球化的同时 ,促进了另一个全球化:它是人道主义的和民主的,是未完成的,不充分的,脆弱的, 但它给受压迫的人们带来了解放意识,进而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引发了非殖民化。他认 为人们需要同西方帝国主义斗争才能采纳西方的价值。90年代的全球化就表现在“统治 ——解放”的双重过程中。
与此同时,文化的全球化并没有使文化同质化,反而激励了各民族文化在其内部的独 创性表达,因而重新创造出新的多样化。例如非洲的节奏与布鲁斯忧郁曲(rhythm and blues)相遇之后所形成的摇滚乐(rock),先是在美国的白人世界里流行,然后传遍全世 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语言演唱,形成了具有各自民族特性的摇滚。
但文化全球化的误区也是很严重的,在莫兰看来,最严重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发展” 观念。这种“发展”观念总是含有经济技术的成分,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加以衡量。 它暗含着经济、技术带动“人类发展”的假设,其成功的模式便是“高度发达”的西方 国家。似乎西方社会的目前状况便是人类历史的目标。这种偏见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被 计算、量度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或爱情。它惟一的满足尺度是增长(产品的 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货币收入的增长)。由于仅仅以数量界定,它忽视质量,如 存在的质量,协作的质量,社会环境的质量,甚至生命的质量。“发展”逻辑忽略了经 济技术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道德的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 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莫兰指出 “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科学、技术、医学和社会的进步,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 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他认为,西方文明的福祉 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技术与兴旺, 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 死亡。
伊拉克之战使欧洲出现了强烈的反战情绪,知识分子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振兴欧洲的 热情高涨。2003年5月31日欧洲各大报刊发表哈伯马斯与德里达联合署名的文章《论欧 洲的复兴》。哈伯马斯强调分析了欧洲的特点:他认为欧洲社会的世俗化相对而言来得 更加彻底,欧洲民众反对逾越政治与宗教的界限;欧洲人更相信国家的组织能力和控制 能力,而对市场的调节能力保持深刻的怀疑态度;欧洲人面对技术进步不是那么盲目乐 观;欧洲人更倾向于从社会团结出发的制度规范,尊重个人人格的完整,并主张在控制 与减少军事暴力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内政等。
还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同时发表文章。他们认为抗衡美国的第一步 就是要让欧洲振兴起来,因为中国和俄国目前还不够强大,建设“核心欧洲”是历史交 给欧洲知识分子的一项伟大使命。美国著名学者理查·罗蒂也参加了讨论,他在《南德 意志报》上发表了《侮辱还是团结》一文,他说:“欧洲掀起重新定位自我的热潮,而 且充满了理想主义,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不管是在美国和中国,还是在 巴西和俄罗斯,都会是这样。……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了,美国人追求霸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顾所作所为对于人类自由的影响 。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已经醒悟过来的美国人有必要应用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 以便让他们的同胞也认识到,布什把他们引上了一条歧途。”
哈伯马斯等人认为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国都经历过帝国权利的顶峰,必 然会从帝国灭亡的经历中有所领悟。对欧洲来说,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一去不返,欧洲 的政权也就得到一个机会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这可能会有利于抛弃欧洲中心论,加快 实现康德对世界内政的美好期望。
其实,70年代以来,就有很多有识之士感到了当前的危机,致力于促进第二种全球化 ,提出了地球公民社会的设想,创立了无疆界的人道主义医生协会,国际绿色和平组织 等。以后,这方面的活动一直连续不断:1999年12月,公民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质 的飞跃,那就是西雅图反经济技术全球化的示威。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 他们的口号是:“世界不是商品。”西雅图引起了后来的多次聚会,最后形成了新生的 “世界公民社会论坛”;2001年在巴西的阿尔格莱德港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社会论坛” 全世界117个国家的4700名代表和12000多名非正式代表与会。2002、2003年在同一地点 ,都召开了规模更大的世界社会论坛,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2004年,大会 将在印度举行。在这期间,2001年还在里尔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提出了《人类 责任宪章》草案。与现存的“人权普遍宣言”,另一个是“联合国宪章”并列。责任宪 章的主要精神是:承担我们的行为造成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后果;联合起来战胜无力感; 承认我们的责任与各自拥有的知识与权力成正比。总之,全球化的“帝国”统一趋势引 起了民族国家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抵抗,要消除这些抵抗因素,就得借助残酷战争和无 情统治,残酷战争和无情统治又会结下新的仇恨。这就是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 义的激烈冲突。要解决这一冲突,西方过去的思想武器显然已不够用,西方的人道主义 ,原则上有利于相互同情和理解,但一遇到同其他社会的尖锐对立,便会退缩;西方的 个人主义有利于竞争和进取,但相对地忽视对他人的关心,由此造成了在家庭、群体中 的有伤害性的隔阂,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除当前已经形成的仇恨的死结!很多人认为人类 精神需要发生一次突如其来的跃进,不是在技术和科学能力方面,也不只是在对复杂性 的认识上,而是指人的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人类需要的,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 个尽善尽美的霸权帝国,而是需要一个多极均衡的、文明开化的、多元发展的联盟。这 就引起了重新认识“他者”,重新认识东方的热潮。
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与东方转向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 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这就是说,西方哲学曾长期把精神 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是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是以“心”、“物”的“外在关 系”立论,或者说其思维模式是“心”、“物”,是各自独立的、二元的。20世纪后半 叶,人类经历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提出了互动认知的现象学方式。这种思维 方式认为“认知”不应只是主体强加于客体的单方面的认识,也不是客体自身单方面存 在的“自在的”特点,而应是二者沟通后产生的新知。过去,认知所叙述的是一个可信 赖的主体,如何去“认知”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已 有的认识论的框架之中。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则是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 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它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了“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 ”相对,强调了不确定的“互动原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总之 是强调对主体和客体的深入认识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一切事物的意 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答案,而是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 穷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性由于种种机缘,变成了现实。
在以上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势必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他者”。正如法国学者于连· 法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所说:“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 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 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 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写了一篇专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 》的著名文章,他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 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 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 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只有从“远景思维的空间”出发,从“他者的外在的观 点”出发,才会构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他最近在北大出版的《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 哲人的对话》中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 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 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 争之中解放出来。”
以互动认知为核心,在西方思想界和汉学界形成了一脉崭新的思潮,如美国安乐哲
(Roger Ames)与郝大维(David Hall)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从汉而思 :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Truth and Transcendence)以及斯蒂芬·显克曼(Stephen Shankman)的《赛琳和圣贤:古代希腊与 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古代中国与希腊:通过比较而思》(Early China/Ancient
Greece: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s)等等。
这样的趋势不仅在汉学界,在西方的主流文化中也不乏其例。法国当代思想家、法兰 西院士让—弗郎索瓦·勒维尔说:“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互相无知之后,在最近二十年里 ,佛教与西方思想的那些主要潮流之间的一场真正的对话已经开始建立。佛教就这样取 得了它在哲学史上和科学史上的应有的位置。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异国情调放在一边,则 佛教道路的目的与所有那些巨大的精神传统一样,都是要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类存在 者。科学既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意图,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注:让—弗郎 索瓦·勒维尔,马蒂厄·里卡尔:《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阮元旭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这是对现代西方文化清醒的反思性认识。
英国学者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书提出并倡导一种与现代经济学相对的佛教经济 学观点,与上述莫兰关于“发展”的批评暗合,给人深刻的印象。例如书中写道:“佛 教徒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把商品看 得重于人,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活动,这是真理的颠倒……既然消费只是人类福利的一 种手段,目的就应当是以最少的消费求得最大限度的福利。”他强调,“科学所揭示的 仅仅是有关物质世界的真理之一面。如果仅仅从物质一面去考察事物,便不可能得到有 关事物存在的全面真相了。”(注: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等译,商务印 书馆,1984年,第33—34页。)另外如奥地利主要心理学家卡尔·容格,从道教书籍《 太乙金华宗旨》中发现了他在西方古籍中苦苦寻觅了几十年而不可得的超级智慧!将这 本书讲述的道教内丹功法奉为“高等文明”的结晶,反观西方的理智主义,则成了“未 开化”状态的写照。(注:容格:《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通山译,东方出版 社,1993年,第76页。)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的心灵呢?容格的建 议是,让西方人放弃科学和理性自大的架子,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他语重 心长地说:“让他们放弃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拆穿他拥有力量的幻象,远比强化 他错误的观念,认为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要重要得太多了。在德国,我们会听 到一种滚瓜烂熟的口号‘有意志处就有路’,这句话已导致千百万人类付出生命。”( 注:容格:《东洋冥想的心理学》,第40—41页。)
主流社会学的重要代表——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论述了“高度的 文明与高度的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这本书为这一惊人论点,提供了异常 生动直观的活见证:现代性的某些本质性的要素,如科学所培育出那种冷冰冰的斤斤计 较的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 ;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 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现 代性始于理性,现在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 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注:鲍曼:《现 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封底页。)
所有这一切都使西方不得不反思,不得不面向东方,以东方为参照,去寻求另一种生 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前文化冲突可能做出的贡献
上述思想发展对中国文化研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往往 受牵制于盲目的爱国主义和“大国心态”,那么现在已有很多中国学者特别重视在世界 语境中来诠释中国文化,改变过去一味封闭地崇尚“国粹”的做法,而致力于从当前世 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视我国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 突中,中国文化究竟能做出何种贡献,同时,也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对自己进行重新 再认识。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已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中国文 化所固有,而又可以作为当前世界文化重构参照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 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 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简作“有状混成”)。一切 事物都是从这个无形无象无实质的“混沌”之中产生的,这就是“有生于无”。“有” 的最后结局又是“复归于无物”。“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无物”、 “无状”并不是真的无物、无状,因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象”和“物”都存在于“无”中,都还不是“实有”,它 只是一种在酝酿中的无形无象的、不确定的、尚未成形的某种可能性,它尚不存在而又 确实有,是一种“不存在而有”。这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
从中国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是不拘泥于已定的、现实变化中未能预见的“确定 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 能性。这也许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理之所在。只有“摸着石头”,向“未知”进 发,才能创造新路。既然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 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那么,基于不变的立场和观点 的世代复仇就不一定有一成不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中国“和为贵”的哲学反对 “冤冤相报,无有已时”,提倡“仇必和而解”,“一笑泯恩仇”。从鲁迅的小说《铸 剑》中可以看到对“世代复仇”的反讽,在金庸的一些小说中也能看到复仇与和解的双 重变奏。
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甚至主体对本 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从“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70年代以来,中国推翻了 “两个凡是”锁定的僵死的“规律性”和“普适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 准”,邓小平同志提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都是纠正了过分强调固定 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西方思维模式,而运用了中国传统智慧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正如朱熹所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要由“人”来彰显。只有通过自由创造、具有充分随机应变的自主性而又与“ 天”相通的“人”,“天”的活泼泼的气象才能得以体现。
上述《道德经》中论述的“惚恍”和“不存在而有”的宇宙观与当今的混沌科学思想 有许多相通之处。《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注:《混沌七鉴——来自易 学的永恒智慧》,约翰·布里格斯(美),戴维·皮特(英)著,陈忠等译,2001年,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再版。)一书的作者指出:“《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混沌 的科学思想源于研究人员对气象学、电路、湍流等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很明显,《易 经》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长期深入思考过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的秩序和无序间的关系,他 们最终将这种关系称为‘太极’”。《易经》的一位英译者布洛非尔德将“太极”概念 描述为:“普遍真理,终极原因,至高无上,永垂不朽,万古不易,变化万千,独一无 二,无所不包,此外无物,无物无此。万物源此,无物源此。万物归此,无物归此。此 乃万物,此非万物。此即太极。太极至显于易——变易。”《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 永恒智慧》的作者说:“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 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 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 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 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 生的一切。”
二、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维方式
1、执两用中,一分为三
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如罗素所说:“笛卡儿体系提出 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也 就是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他们重视以主体为一方的对客体的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 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从客体抽象出来的“规律”,并将之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 ,他们崇尚抽象的规律性远远超过关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 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 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就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 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思维方式却与此全然不同。首先是“一分为三”的原理和由此而产生的中庸之 道。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原则。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 就是由三画组成的,由三而演化,至于无穷。所以说“太极元气,函三而一”。(注: 刘歆:《三统历谱》,见《汉书·律历志上》,并参阅庞朴教授专著《一分为三》。) 《史记·律书》提出:“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为什么说“成于三”?当两种 原不相干的事物相遇,而构成“场域”,就产生了新的、不同于原来二者的第三个东西 ,这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系辞传》明确 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所以《礼记·中庸 》强调:“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天、地是不够的,必须有第 三因素“人”来“赞天地之化育”,才能成其为世界。《中庸》的真精神也就是要从“ 过”和“不及”的两端,找到一种道,即所谓“执两用中”。这个“中”并不是“折中 ”,二是从“两端”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汉书·何武传》中说:“(何武) 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这就是执文吏和儒者两端, 而得到一个既非“文吏”,亦非“儒者”的第三个新的意见。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 ,首先要“执其两端”,然后,“求其中道”。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极高明而道 中庸”。
2、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思想是中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另一个系统,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左传》 、《国语》等多有论述。意谓世界万物皆由五种元素及其所构成的关系所组成。如:这 五种元素是木、火、土、金、水,它既代表颜色——青、赤、黄、白、黑,又代表人体 ——肝、心、脾、肺、肾;方向——东、南、中、西、北;时令——春、夏、长夏、秋 、冬等等。五种元素既相生(水生木,火生土,金生水,木生火,土生金),又相克(水 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循环往复,无有已时。
从多种元素相生相克,广泛联系出发,就必然重视事物的多样性,重视差别和相互关 系,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 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 ,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 只能是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 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3、“反者道之动”
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进化 论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人们竭尽全力往前飞奔,对自然资源榨干了还要再榨,人的生活 享受了还要再享受,人类趋向未来的速度快了还要再快……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思维方 式和生活模式。至于未来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旧”好?万众所趋的目的地何 在?人们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趋向的坟墓而外,没有任何真正具有确定 性的回答可以被提供出来!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却与此截然不同,从老子的《道德经》开 始,就强调“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认为万物的运动都有一种复 归的倾向,都要回到运动的原点,在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再出发,从而 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中国哲学不重视以时间为主体的线性发展,而更重视向原点的复归 ,也就是“反本开新”。既然万物都在不断回归和再出发,而不是向某个方向盲目“飞 奔”,也就没有匆忙的必要,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 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作为中国文化古远根源的《 易》的核心就是发展变易。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正是 很好的参照和缓冲。其实,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 寻找新的途径。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莱。目前,在西 方,回到原点,重新再出发,也已成为一种趋势。
4、“太乙生水,水反辅太乙”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出土:“太乙生水,水反辅太乙,是以成地,天地复相 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所以成四时。四时复 相辅也所以成冷热。冷热复相辅也所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后止。”岁指农 业收成。这就是相辅相成的宇宙模式和思维模式。这对于以现代思想反辅传统思想,在 新的基础上,找到方向再出发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三、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对个人权利、自由意志的强调已发展到极端,但人只能镶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 能生存。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因此在他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如戴震所谓:“ 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义模式那样,将社会作为实现 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也不像集体主义那样将个人作为达到某种社会的手段。儒家认为 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 听自我民听”,孔子既是精简政府职能的倡导者又是建立自治的人类社群的积极支持者 。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听讼,吾犹人也。必 也使无讼乎”。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引导。免,免罪,免祸。格,亲近,归服。《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 齐之以礼,责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儒家的这些主张也许可 以修正西方民主的弊端,同时,吸收西方民主的优点,创造一种新型的、兼顾身心的、 更合理的民主。
